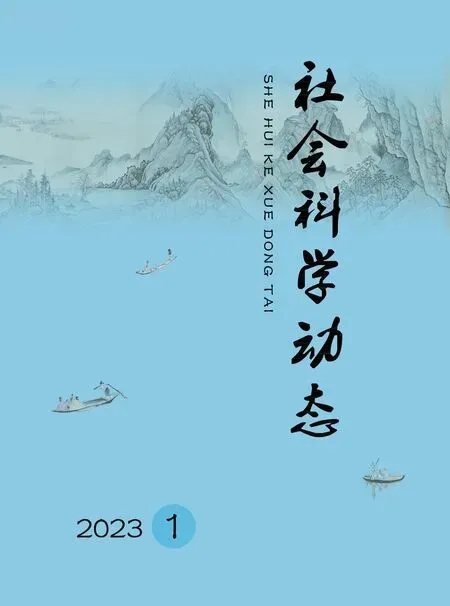数字劳动中人的自由危机和新的统治形式探析
傅华宇
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走过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现在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即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信息化浪潮,计算机互联网诞生平台和数据活动场域,拉开数字资本主义的序幕。传统劳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劳动者需要适应更新的劳动工具,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深度融合,在加深自由危机的同时还伴随着情感劳动的悖论。
一、劳动新形式——数字劳动
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搭建起全球用户网,不管是应用终端还是硬件芯片,都掌握着用户信息数据,这就是一种新型资的本主义形态。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产消者,在使用互联网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被整合再投入下一环节,资本的运营贯穿于生产过程,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第一次使用 “数字资本主义” 概念,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因特网带来的信息化社会,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社会。
日本学者此本臣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货币)的体系。现在数字技术的推广使用,依然是挖掘差异获取剩余价值。要研究数字资本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入手,首先要界定的就是何为数字劳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发现了一种真正不同于传统劳动方式的数字劳动,正如他在《社交媒体批判导言》中写到, “Facebook从来不只是一个社交平台,相反,它利用了我们的社会交往行为,方法就像特百惠的聚会一样……Facebook真正的最终用户是那些想接触并影响我们的营销人员。他们是Facebook的付费用户,而我们是产品。我们是Facebook的工人。无数个小时,我们(特别是年轻人)在Facebook上用我们的个人记录形成未付报酬的劳动,Facebook用它来证明其股票价值的合法性。”①当今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隐性规模的扩大,资本必然与互联网结合谋求商业模式的创新,以便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最终节约成本增加利润。那么移动互联网的表象是 “互联网+” ——提供更多的服务,实质是拉取更多的 “产消者” 。这种作为产消者的劳动方式,在数字时代之前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在互联网应用背后的大数据算法出现之后,用户的浏览、游戏、刷视频、点赞等行为才被定义为数字劳动的。
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劳动工作活动论述为人类的三种基本活动力,她认为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的劳动是最低等的。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后,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劳动一跃成为了最有价值的活动力,彻底颠覆了原先的顺序。从劳动社会向活动社会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劳动者变得一无所有,劳动力变成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劳动创造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被互联网所记录、加工、交易,每个人都在无时无刻地生成信息。这些信息从人的身上剥离下来,成为产出价值的存在。进一步延伸汉娜·阿伦特的理论,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孕育中的 “活动社会” 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 “劳动社会” 相对应的存在。私人领域中的劳动转变为公共领域的活动,人类的活动在数字劳动下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企业支付的薪酬仍然来源于生产者剩余,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化的普及企业挤压生产者剩余,扩大消费者剩余,影响经济发展,最终导致总剩余的中长期缩量。当生产者剩余缩减,工人拿到的薪酬降低时,那么他们的购买力和支付意愿也会随之降低。针对这种情况,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认为,平台公司应该为个人的活动支付一点费用作为 “活动” 的报酬。
根据数字劳动的使动状态,可以将其划分两类。第一类是主动劳动,资本搭建起数字平台,这类劳动者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软件工程师等。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②搭建互联网技术平台和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的劳动者都是主动在为资本家从事生产活动,但他们二者之间也有不同,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配送员是利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在工作之前需要自己投资买设备,不需要固定工作场所,主要是体力劳动;互联网工程师则大都在企业工作,不仅有舒适安逸的办公区,还有企业提供的生产工具,从事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等工作的劳动者主要耗费的是脑力劳动,他们的工资待遇高于前者。第二类是被动劳动,互联网终端用户即网民,这些人既是使用者也是生产者。电脑网页、应用终端和智能手机应用客户端的普通使用者,他们的每一次点击浏览都被平台记录生成数据信息,大数据会根据用户画像针对性推送内容,他们的再次点击或者消费就会为资本创造收益。在这里需要提到一种特殊情况,即不消费的用户是数字劳动的一部分吗?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抖音极速版的受众用户,他们在看视频的同时可以赚取 “金币” (虚拟数字),金币可以兑换现金收益且直可接提现到个人银行账户。这些人成为平台资本的活跃用户,实现资本增加用户粘性的目标,用户沉浸在虚拟化的数字符号中,这里商品拜物教本质没有变化,表现形式从实物到虚拟数字符号。大数据和算法没有消除商品背后的价值规律。
二、数字劳动的自由危机
资本权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转化为数字权力,互联网大数据下劳动无处不在,个体被自己生成的数字所约束监控,个体活动成为资本增殖的新途径。数字劳动时代个体的 “劳动活动” 从工作时间延展到生活时间,马克思说: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③数字劳动依托技术支持带来更多的自由危机。
(一)自由与被监视
数字劳动带来的自由危机需要从现实的自由本质入手。数字生产方式的出现,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者的界线,麻醉了劳动者心灵,不平等扩大化,人的心灵受到数字技术的支配。那么对自由本质的追求,苏格拉底开启理性思维,他追求个体头脑灵魂的自由,通过 “智慧之问” 达到内心深处灵魂独立,他所探寻的自由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自由。康德认为 “人有自由;以及相反地,没有任何自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然必然性。 “他对自由本质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即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后来黑格尔继承和发展康德自由观,认为自由是三个维度的叠加:抽象自由,反思意义上的自由和社会自由。可见自由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数字劳动汇集在互联网中,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描绘用户画像进一步限制了个体自由,人的一切虚拟活动都处于被监视中。弗洛姆用 “逃避自由” 来刻画现代社会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精神状态, “经济制度的特定性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便成为决定整个性格结构的首要因素。”⑤人不是没有感情的劳动机器,和传统物质生产劳动不同,数字劳动下人的行为性格习惯都被记录着,有学者提出 “非物质劳动” 的概念,认为 “非物质劳动作为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比如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一种情感反应的劳动。”⑥因而数字互联网成为更强大的统治人的工具,不仅占用个体的时间精力,还给人带来更多的空虚和自由危机。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从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读 “精神政治” 。他认为, “对自由的感知始于从一种生存方式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过渡,止于这种生存方式被证实为一种强迫模式。因此,随自由而来的便是一种新的屈从。” 人的自由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被操控, “精神政治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控制人们的思想” 。⑦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控制人思想的武器,数字劳动介入人的精神层面。2016年上线的抖音,如今凭借日活跃用户6亿占据短视频珠峰,2019年有超过2200万人在抖音合计收入超过417亿元,同时也为抖音创造营收500亿。用户在发布视频和浏览关注其他用户视频即是被数字互联网控制下的劳动过程。数字技术从被动记录到主动控制,当个人放下手机停止使用抖音之后,空虚迎接而来,抖音视频的几秒钟浓缩的是他人最精彩的一天,用户沉溺于他人的美好生活无法自拔。信息量庞大,情感跌宕起伏,系统理性思考过程被打乱,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遭到严重破坏,使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
(二)新统治形式
数字劳动在资本搭建的平台上利用数据分析和算法收集个人信息,资本掌握着游戏规则,个体不得不接受这种新统治形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到的 “全景敞视主义” 就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最生动的描绘, “我们无时无刻不留下数字痕迹……全盘记录生活的可能性使得监控完全取代了信任。大数据当上了‘老大哥’。对生活的无缝式的完全记录让透明社会更加完满。数字的监控社会有着一种特殊的全景监狱式的结构。”⑧新统治形式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数字资本依然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数字劳动同传统劳动一样仍处于资本增殖逻辑下被榨取的剩余价值,数字资本甚至已经开始开辟 “数字殖民地” ,英伟达宣布推出为 “元宇宙” 建立提供基础的模拟和协作平台,日本社交平台GREE开展元宇宙业务,微软也正努力打造 “企业元宇宙” ,到脸书改名为元宇宙(Metavers)一词中的Meta,2021年的网民还未了解什么是元宇宙的时候,这些资本家已经把他们看作新的用户,开始新一轮的资本扩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李峥认为: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也带来了一系列国家间的竞争与矛盾。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带来的最突出的国际竞争,体现在对于网络核心技术、全球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技术标准等战略资源的争夺,这些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甚至能够转化为对互联网整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相比以往国际政治主要争夺的是资源、人口、土地等,互联网的战略资源具有数字化和虚拟化特征,其边界更模糊,也让国际竞争变得更复杂。”⑨互联网大数据搭建起纵横交错的数字虚拟世界,资本围绕数字领地开辟数字殖民地,在市场谁占有的数字资源越多谁越具有话语领导权,而在这里经济不发达国家数字领地处于劣势可能被占有殖民,世界经济风险增大,从而矛盾争端也会升级加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新的形式统治着世界数字资源。
其二,隐性数字劳动模糊了传统雇佣关系,无形的手在背后支配着劳动者。数字劳动的普及,劳动者不需要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甚至没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仅在物质和身体上被压榨剥削,而且精神状态和思维意识也在被麻痹。在《资本论》中,劳动一般进一步成为衡量资本主义生产的尺度, “劳动对资本的特有使用价值,是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的性质,是这种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性质;但是,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量更大的量。”⑩数字劳动能够掩盖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实质,数字劳动的量难以衡量。信息技术被利用设计简化工作程序,劳动者入职门槛降低,除自由职业者的普通用户也被填充到数字劳动队伍中,散乱的数字劳动者难以走向联合,无产阶级斗争意识模糊弱化。
(三)革命主体自我异化
数字劳动带来自由危机,在数字劳动社会中,不仅要分析数字资本始于资本增殖对人造成的影响,还要深入探析如何不被控制进而解放自由。20世纪末,当代美国批判理论家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同时看到互联网大数据对劳动市场带来的新变化, “在后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时代,在工厂—社会的时代,以及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取得胜利的阶段,劳动彻底处于生活的重心,而社会作业彻底扩展至社会的各个场所。这就将我们引向一个悖论:就在理论无法看到劳动之时,劳动无处不在,并且在所有地方成为唯一共同的实体。”⑪他们思考无形的数字劳动同物质生产劳动一样超越资本,进而实现人的解放。
数字劳动加深人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不可否认数字劳动把部分工人从传统高危险、高污染和高体力的工厂中解放出来,拓展了劳动形式和活动空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它更灵活自由,收入形式多样,个人享受时代创造的红利,同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数字劳动由互联网把人和人连接起来,拓宽了人际关系,推动经济合作共赢。另一方面,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发展,对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具有促进作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但在马克思看来, “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⑫很显然,数字劳动带来轻松的工作条件和繁荣的经济形式背后实质却是异化的加深。劳动是人的本质,但人不能时时劳动,数字劳动下人每时每刻都在劳动。资本的本质没有变依然是增殖,数字资本主义下诞生的平台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都换着形式披着不同颜色的羊皮,以更温和、更轻松和更有趣的方式续写劳动异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带来的产业革命,这种变化体现在一种社会存在的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生产方式, “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⑬异化的本质需要结合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从更深层的生命政治来解读。
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看似追随时代潮流,实则被迫卷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漩涡。首先这种互联网活动本身具有虚拟性,可以极大地麻痹人的精神。此时劳动者在数字资本的权力下,随社交扩大化而来的是消费的升级,人的无意识特征不断凸显,表现出无所事事,精神依靠丧失,对现实的不满需要从虚拟世界中寻找短暂的慰藉。其次,数字劳动者享受互联网大数据的个性化定制,传统社会关系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逐步瓦解。如同消费主义盛行下,高昂的广告费用不是用来凸显新产品的技术升级,而是抹杀上一代产品最后的价值,个体在数字资本的规则下生活,人们行尸走肉在空洞的世界,坐在餐桌前低头发红包而不张口说声祝福。最后,个人数据信息活动在数字劳动中源源不断生产着商品,还生产着 “主体的欲望、社会交往、身体和心灵” 。⑭个人自由危机的来临意味着对数字劳动的依赖和膜拜,自己成为数字劳动商品的傀儡。约瑟夫·巴尔拉说过: “在走锭精纺机出现之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等级关系都没有稳定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机器成为一个制导因素,甚至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本身,而不是单纯的物体:机器和物质对象(包括人和非人因素)彼此结合在一起,不仅构成了工厂体制,也将前现代的闲散的劳动者组织化为工人阶级。”⑮现在来看工人阶级的联合和解放更遥不可及,数字劳动的扩张进一步延伸到生命政治领域,个人陷入生存困境和自由危机的黑洞。
三、数字劳动无法超越资本
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仍然从属于数字资本,上文从数字劳动的性质、劳动者异化和解放的角度分析得出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新形式,虽然劳动者在劳动资料的使用上、劳动成果的分配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被资本控制压榨感下降缓解,但数字劳动作为资本的从属无法超越资本。
(一)加深财富两极分化
由于数字劳动产品具有 “非物质性” ,所以劳动产品可以流转和共享。普通数字劳动者劳动的产出很容易在资本圈流转,例如,资本A公司为游戏行业龙头,月活跃用户数量众多,资本B公司拥有市场上用户数量最多的互联网社交应用;资本B公司想要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用户活跃度通过占股A公司股份,把A游戏内嵌B社交平台;通过这样操作用户数据还可以流转到其他资本手里,这个过程资本变现一夜之间便可诞生千万富翁,而普通数字劳动者收入没有变化且未来还没有保障。正如莫里奇奥·拉扎拉托看待数字劳动的无处不在和数字劳动者的普遍, “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可以是直接操纵符号来生产原创知识的劳动,也可以是图书馆员,快递服务公司的员工,甚至是装配电脑线路和元件的劳工从事的劳动。”⑯数据没有明确的物质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灵活可动,不变的是生产的两端——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步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但劳动者仍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例如,表面看到普通劳动者下班后听的音乐和资本家喜欢听的是同样的歌曲,但劳动者在短暂休息之后又要投入劳动生产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不能消除贫困的地位。
数字资本的轻量化性质决定了数字劳动的财富分配。现在互联网巨头只需要设立一个总部,员工分布在各地,不同于劳动密集型传统企业,互联网公司要做的是去中心化。普通用户和数字资本企业员工做的是数据信息的生成和加工,数字平台给予普通用户激励分成,给予新用户创作奖励金,造成财富共享的假象。数字资本对平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进入平台的用户使用权限不打开用户就无法正常使用,这样资本就强制占有了用户数据信息。数据信息被用作经济目的,从而加速资本积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对数字劳动的理解上升到层级结构, “对资本主义ICT产业中的一些劳动进行批判,其总问题是:什么是数字劳动?⑰如何透彻地理解它的工作条件?” 正是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变,进一步使得数字财富的分配不均衡,用户作为数字劳动者不但没有工资,还要向平台充值会员和购物付费内容,看似 “用户至上” 其实不然,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地位依然不平等且差距越拉越大。这些劳动者在非劳动期间(工作)花费大量时间在数字平台,没有额外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工资,付出的时间生成数据信息被资本利用,反过来销售到自身。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加速资本积累,也会继续加大数字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差距。 “数字资本” 也是资本, “数字劳动者” 也是劳动力即商品,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家付的工资,工资受资本家压制因而有限,在资本商业活动频繁经济增长较好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促进消费下一环节顺便进行加速资本流通,会给予劳动者各式福利待遇,而在资本出现衰减亏损的情况下,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仅够购买最低生活资料。
(二)情感劳动双向互动
数字媒介下与观众互动交流的网络主播他们的劳动属于情感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有自我享受部分。从 “网络主播元年” 2016年发展至今的6年间来看,根据劳动形式不同网络主播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依靠数字媒体平台进行娱乐化在线直播视听享受的劳动形式,跳舞唱歌表演形式是最普遍的直播内容,还有游戏直播等,有竞争力的主播需要有自身才艺和特长,收入主要来源于用户打赏和少部分平台创作激励;另一种是利用自媒体平台和广播电视等渠道进行直播带货的劳动形式,把传统店铺销售模式改造升级为 “无界营销” ,主播通过直播讲解产品吸引用户下单,这类主播收入主要来源于下单提成,而且主播热度越高他们出场费越高,也是构成收入的重要部分。情感劳动中智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条件下,智力的价值是通过机器体现出来,而在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中,智力作为独立的生产资料创造着价值,主播需要运用知识和创新创造出观众满意的内容,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主播作为数字劳动者自我激励、自我管理,并树立口碑和形象。但是其中却出现了两个崇拜,第一是普通观众对网络主播的崇拜,第二是主播对虚拟礼物和数字的崇拜,虽然数字平台使网络主播摆脱了对机器的依赖,但是无形的算法控制着数字劳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生产着剩余价值。
同时,数字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管理组织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表现直接影响着收益,公司不仅需要在物质上给这些数字劳动者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信息和前期宣传,还需要注重在感情上与主播互动交流,在精神上加强关怀。这种共利管理方式可以获取更高的收益,公司对网络主播情感劳动控制力弱化,主播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作为劳动者的网络主播对直播的依附程度降低,许多网络主播并非是纯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⑱在不完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情感劳动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劳动者根据自己日常习惯灵活结合工作时间、第三方要求和创意进行工作。但是,他们的劳动依赖数字资本平台,受市场规则限制,数字劳动信息作为非物质劳动进入资本市场交易运作。事实上,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与数字平台的相互关系并不复杂,是处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符合资本主义逻辑关系。总而言之,在数字资本平台中,每个人都是选择不同角色的玩家,作为互联网大数据的超级个体,既是数字平台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四、结语
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影响的余波,数字劳动以崭新劳动形态同数字资本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新阶段一样一直饱受争议。对数字劳动的阐释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研究,即探明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规律来超越资本主义从而走向自由与人类解放,迈入共产主义。数字劳动从劳动的主要对象、劳动资料的使用方式、劳动成果的分配上看,都使劳动者获得了极大的主动性,但这并不是说数字劳动者就已经摆脱了对资本的从属地位,实现自我管理和控制了。非物质劳动中的知识、情感成为劳动对象,给数字劳动者智力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和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数字资本依旧逐利,一切智力的发展又都指向了资本增殖,数字劳动到头来还会变得单一、片面。通过上述论证,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新变化,对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依然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揭示其本质特征与运行机理,而且可以据此来探寻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破除技术的异化应用,让数字劳动为人民所用好,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⑰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交媒体批判导言》,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165、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③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160页。
④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16页。
⑤ 参见[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⑥ See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Penguin,2004.
⑦⑧ [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108页。
⑨ 李峥:《元宇宙对国际政治的潜在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8日。
⑪ Michea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0.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⑭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32.
⑮ Josef Barla,The Techno-Apparatus of Bodily Production:A New Materialist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 Body,Transcript Verlag,2019,p.29.
⑯ Paolo Virno,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 A Potential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133.
⑱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