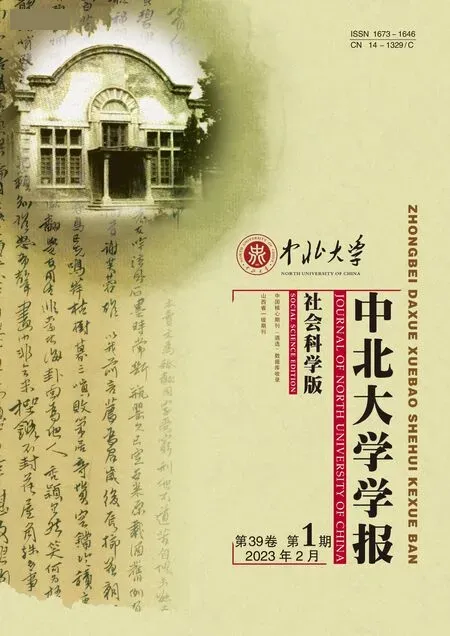里尔克为何不是“唯一的诗人”
——海德格尔的里尔克阐释再评价*
李传通
(浙江大学 文学院(筹),浙江 杭州 310058)
海德格尔的诗歌文本阐释实践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阐释又有着重要的地位。总体来看,海德格尔尽管给予了里尔克高度的重视,但却对其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他称不上是“唯一的诗人”。这个说法源于海德格尔对于诗人与存在关系的独特观点。在他看来,诗人的天职在于道说存在的意义,而存在意义的显现是具有时间性的,只有道出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存在意义的诗人才称得上是“唯一的诗人”。那么,海德格尔为何要阐释里尔克?享誉世界的诗人里尔克又为何当不起这个称谓?海氏对他持保留态度的援引究竟是什么?探究并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1 海德格尔为何阐释里尔克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变,在其思想后期“海德格尔不再试图从理解存在现象的预备性分析出发,去把握存在或存在的意义,而是直接地转向存在去思考存在或存在的真理,转向了‘诗意地运思’,转向天、地、人、神‘四重奏’,转向‘艺术与澄明’,转向‘语言与思’”[1]16。谈到海德格尔诗意思考的转向,就不能不提及荷尔德林和里尔克这两位伟大的德语诗人。在传记《里尔克》中,霍尔特胡森写道:里尔克“有些部分则超前道出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后者也在其1950年问世的《林中路》中根据里尔克的一首诗对里尔克做出了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精彩、最深刻的一种阐释”[2]250。不难想象,若不是惺惺相惜,两者在思想上有不谋而合之处,海德格尔不可能做出如此深刻而又精妙的评论。当然,海德格尔并不只是对里尔克的诗歌做出普通意义上的文本解读,而是深入到“思”与“诗”层面进行了深度的精神探寻。
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诗歌进行阐释到底揭示出了什么?是否如海德格尔所说对里尔克的阐释是出于存在历史之命运?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是借对里尔克的阐释来检验自己的“存在历史”观,是对存在的进一步追问。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里尔克的影响,他找出了里尔克诗作中的一些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借鉴和化用。海德格尔认为:“这些基本词语只有在它们被说出的那些领域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此领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自从尼采完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以来,这个领域获得了展开。里尔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诗意地经验并承受了那种由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3]248海德格尔以此为突破口,深入地探究了存在本身在里尔克诗作中的显现。所以,海德格尔在讨论一些言而未明的论断时,不会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铺陈,而总是使用隐喻的表达手法,用一些带有隐含意义的词汇,曲折地表达其个人理解,看起来晦涩而又无懈可击。他对里尔克诗歌中关键词的挖掘和借鉴就是最好的佐证。事实上,读者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频频地发现这些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在里尔克诗中的很多词汇中找到了属于他们二人共有的精神契合点。
首先,海德格尔对里尔克一首即兴诗中的“自然”一词做出了阐释,他认为里尔克诗歌中所说的“自然”就意味着生命,在具有现代成分的意义基础上还是一种原始基础,是作为人本身这个存在者的原始基础,自然意味着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就自然是我们人本身这个存在者的基础而言,里尔克称自然为原始基础。”[3]251-252因为自然是作为人的原始基础,这就意味着人比其他存在者更深地进入到存在者的基础之中,存在者的基础在海德格尔看来即是存在,也正是存在使存在者处于绝对冒险之中。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冒险,所以依靠存在而在场的存在者就都处于一种冒险之中,无论是作为存在者的人还是作为存在者的其他生物。海德格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里尔克诗中所说的“冒险”也即是存在,存在这一“冒险”对一切被冒险者即存在者起着“牵引”的中心作用,同时,它还赋予存在者重力之“重力”——“纯粹之力的重力”。海德格尔又说:“纯粹之力的重力、闻所未闻的中心、纯粹的牵引、整体的牵引、完满的自然、生命、冒险——它们是同一的。”[3]256在海德格尔看来,里尔克诗歌中这些极具迷惑性的语言为我们所昭示的都是命名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
其次,不得不提的便是两者对于“敞开域”概念的理解,从里尔克自己的语言表达来看,“敞开域”指的是无锁闭、无界限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海德格尔却说,我们不能从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意义上的敞开状态去理解里尔克所说的“敞开域”,因为如果在此领域去理解里尔克所说的“敞开域”,则意味着是被锁闭者,“某物照面之处,即产生界限”[3]257,那样“敞开域”就会被限制扭曲,而不能被称之为自然状态。在里尔克看来,动植物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而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海德格尔却认为“敞开域”是允许人作为存在者进入的,并且人比其他万物更无阻拦地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中,因为这种允许具有存在本质意义上的特征。所以,海德格尔认为里尔克所说的“敞开域”虽然对存在有所经验,但还是一个有歧义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我们要做的是从更源始的存在之澄明的意义上来思“敞开域”。“在里尔克所称的‘敞开域’和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意义上的敞开域之间,张开着一个裂隙。”[4]233一般我们会认为“敞开域”这个词汇是海德格尔常用的概念术语,其实,海德格尔是借用的里尔克诗歌中的“敞开域”一词,虽然在理解上有所差异,但仍不可忽略其原始借鉴意义。所以,考夫曼在《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一书中指出海德格尔写作中的一个现象:“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对语言的暴力,暗示了他想用里尔克喜欢的词汇之一,敞开域,来表达一些新的、极端以及不可言说的事物给新的一代。”[5]39
最后,海德格尔还关注到了里尔克诗中所说的“最宽广轨道”。他认为,里尔克诗中所说的“最宽广轨道”是具有统一作用的“一”,而存在就是源始意义上的“一”,就是在场着,而且这种在场是在敞开领域中的在场,是没有遮蔽的,是区别于在场者的,在场比在场者更本质,同时,在场作为它本己的中心就是“球体”。这个“球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庇护在场者”而“解蔽着的照亮”之特征,在这个“球体”的照亮范围内,在场者才能在场,所以,“解蔽着的照亮”与球形特性都是“一”的特征。海德格尔进一步说,在巴门尼德看来,在场者之在场,也即是“一”被命名为“圆满的球体”,它被看作是解蔽着和照亮着的“一”的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所以,存在就是“圆满的球体”。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存在之球体以及其球形特性,我们也不能用对象性或非对象性来加以描述,因为从这种描述中我们丝毫不能经验到存在的本质,而应该“根据在解蔽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原初存在之本质来思考这一球形特性”[3]273。海德格尔还拿里尔克本人的书信来证明里尔克诗中所说的“最宽广轨道”指的就是“存在”的这一球形特征:
如同月亮一样,生活确实有不断规避我们的一面,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对它自己的完满性和丰富性的充实,是对现实的美妙而圆满的空间和存在之球体的充实。[3]273(1923年1月6日,三王来朝节)
说了如此之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经验存在呢?海德格尔显然是想通过里尔克的诗歌告诉我们,可以从“在场” “具有统一作用的一” “圆满的球体” “解蔽着和照亮着的一” “照亮着的球壳”去体会存在之本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的诗歌进行阐释时,通过“自然” “敞开域” “最宽广轨道” “天使”等意象展开他的思考,而他的思考无外乎是围绕存在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这些意象都是海德格尔从里尔克的诗中刻意挑选出来的,虽然我们可以说从字面看来它们与存在毫不相干,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诗歌中的意象无一例外地指向或者揭示着存在。学者刘皓明对此亦认为:“海德格尔从里尔克晚期几首诗中找到‘自然’与‘生命’ ‘中心’等词语,用来证明诗人讨论的是‘在者的在’。”[6]168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诗人,如荷马、歌德、莎士比亚等,海德格尔却没有选择他们,这真的是存在历史命运之必然吗?其无非是海德格尔自身思想之必然。刘聪对此认为:“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没有脱离开畏惧、忧烦与死亡,而里尔克诗歌的主题是痛苦、死亡与爱情,两者在思想上具有部分共同的切合点。”[7]故在海德格尔看来,里尔克对于存在问题是有所思考的,其诗歌主题更是能引起海德格尔的共鸣,而里尔克本人亦是以艰涩费解而闻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海德格尔不谋而合。再如学者艾士薇认为:“与19世纪的荷尔德林相比,已经跨入到20世纪的里尔克,其现代诗歌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更为深邃。”[8]由此,海德格尔选择诗人里尔克进行阐释的原因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海德格尔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存在问题,从《存在与时间》开始,提出重提存在问题意义的重要性之后,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追寻存在的路上。海德格尔认为,诗人作诗是一件运思的事情,而想要通达诗人的诗歌必然也要采取运思的方式进行,这也是海德格尔一直所强调的“思”与“诗”的对话。既然谈得上“思”与“诗”有一场对话,那么,两者必然具有差异性。海德格尔认为,“思”绝不是表象性的,表象性的东西都是以计算方式而存在的,而表象也就意味着把一切东西对象化,而表象的、对象的、计算性的思维绝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思”,只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维,也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海德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思”其实就是思存在,即思存在之本质,存在之澄明状态。那么,海德格尔看来何为诗之本质呢?“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9]45,诗就是通过语言把存在揭示出来,诗之本质开启着存在之澄明状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诗”不但不存在差异性,甚至可以合而为一,是一种互相归属的关系。海德格尔不管如何强调思的作用、诗的意义,他最终所要追寻的都是存在之本质意义的答案,“思”与“诗”只不过是我们进入存在之澄明状态的途径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对里尔克诗歌进行阐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诗歌中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之思,这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通过解读里尔克的诗歌,海德格尔得以进一步追问存在,帮助我们实现存在的澄明状态。
2 为何里尔克不是“唯一的诗人”
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为“诗人中的诗人”[9]36“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行者”[3]289,给予其至高无上的评价,因为在他看来,这实出于存在历史之命运。那为何在海德格尔看来里尔克不是“唯一的诗人”,海德格尔对里尔克所持的这种保留态度真如他所说是出于存在历史命运之必然,还是在其思想深处自有其根源?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历史命运之必然无非是其自身的“存在历史”观,海德格尔之所以对里尔克进行如此评价是可以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寻找到答案的。
首先,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的即兴诗进行运思时发现,里尔克诗歌的语言本质上是没有完全脱离形而上学的影响的。“‘冒险’一词在这里既指大胆冒险的基础,也指所有冒险者整体……形而上学的语言明显是以这种歧义说话的。”[3]256“即便是‘敞开者’这一名称,也如同‘冒险’一词一样,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是有歧义的。”[3]257由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里尔克的诗中的很多关键词在语言层面上都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歧义的。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算海德格尔认为里尔克的诗歌语言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歧义的,又何以会影响里尔克的地位呢?若想回答此问题,我们必须追问海德格尔自身对于形而上学持何种立场。海德格关于形而上学的立场最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是以存在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根据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阐释,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的意义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问题的耽搁”[10]8。因此,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是一种“对存在的遗忘”,存在问题看似已经澄清,人们只是在不言而明中对存在进行了误用。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无法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因而会把两者混淆,从而使存在一直得不到澄清。所以,海德格尔对于存在和存在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存在者与存在永远都不可能等同,这种区分也是对存在的意义进行深入追问的前提,也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
为了克服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影响,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过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来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并且在追问的过程中时刻警惕和避免存在与存在者的混淆。到了其后期思想,海德格尔则一再强调直面存在本身,从语言层面上彻底消除形而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还认为,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完成时的最后一个哲学家,“这一番指明工作将揭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阶段,它也许是形而上学的最终阶段,因为就形而上学通过尼采而在某种程度上自行丧失了它本己的本质可能性而言,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形而上学的其它什么可能性了”[3]226。这再一次清晰地反映出了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立场,他对于形而上学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而是与之彻底决裂,一直致力于超越形而上学。至此,我们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答,鉴于海德格尔自始至终反形而上学的立场,虽然一再强调其阐释是出于存在历史之命运,也无非是海德格尔自己的“思”在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海德格尔衡量诗人的标准之一就是诗人本身要弃绝形而上学,诗歌语言亦不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在阐释里尔克的诗歌过程中,认为其语言仍具有形而上学的歧义,他必然认为里尔克称不上是“唯一的诗人”。
其次,海德格尔与里尔克在处理人与存在的关系时,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在里尔克看来,植物和动物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是因为动物的意识程度低,所以它们被直接允许进入“敞开域”,而意识越提高则越是被排除在世界之外,因此,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而海德格尔却认为,人应该更无阻拦地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何为“敞开域”,即是存在的澄明状态之所。正如我们所知,海德格尔为了追问存在问题,给予了此在优先地位,此在不仅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具有双重优先地位,同时,“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10]16。这也表明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相比,天然就具有优先地位,是具有源始性意义的。“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10]5所以,存在本身是不可以被定义的,一旦采用了定义法,存在便变成了存在者,如果存在本身是不能直接被触及和界定的,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某种存在者来经验存在呢?“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10]9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论及存在,但可以通过此在这种与存在关系最为密切的存在者来进入存在之思。此在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存在,是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里,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而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用此在来指称人的存在,显然是对人的存在和动物这类存在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海德格尔虽然在后期思想中很少再提及此在的优先地位和生存论存在论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前期的基础存在论立场。“对人之本质的任何一种规定都已经以那种对存在之真理不加追问的存在者解释为前提;任何这种规定无论对此情形有知还是无知,都是形而上学的。”[11]377这说明在其后期思想中,他是想在语言层面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彻底地克服和超越,而并没有否认此在依然是追问存在与人之本质关联的关键。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写道:“人唯在其本质中才成其本质,人在其本质中为存在所要求。”[11]379这所论及的仍是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虽然没有继续沿用此在这个术语,但这无疑是对人的存在的进一步阐释和延伸。所以说,海德格尔在思存在的道路中,始终认为“人已命定要思存在之本质”[11]380。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进行的阐释过程中亦表明:“人的本质基于存在对人的关联。”[3]265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能体现人的本质的是人与存在的密切关系,而人作为与众不同的存在者比任何其他存在者都更有权利进入“敞开域”之中,即更有权利追问存在的澄明状态。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海德格尔在后期诗歌文本阐释中仍然没有放弃早期的基础存在论思想,他仍然认为此在在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上具有优先地位。既然里尔克在处理人与动物与存在的关系时仍然含混不清,这显然与海德格尔自身的思想相悖,那遭到海德格尔的责难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最后,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的诗歌进行阐释时认为,其并没有对世界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做深入的追问。“即便是里尔克,也没有对世界内在空间的空间性作更为深入的思考,甚至也没有追问,给予世界之在场以居留之所的世界内在空间究竟是否随着这种在场而建基于一种时间性;这种时间性的本质性的时间与本质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那种时-空的原始统一体,而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时空成其本质的。”[3]277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表现出了对于时间、空间问题的强烈关注,“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10]131。海德格尔认为,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参与世界的组建,是组成世界的重要因素。当然,这里所说的“世界”不是普世意义下所说的世界,而是在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下所说的世界,是此在作为自身最本己的存在的“世界”。而对世界起组建作用的空间,既非空间是在主体之内,也非世界在空间之内,因此,空间是一种具有空间性的显现为先天的东西。同时,海德格尔区分了形而上学流俗意义下的时间概念,流俗的时间概念不但不会成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甚至还使我们处在一种对存在的遗忘之中,是会遮蔽存在的。如若我们仍然在流俗的时间概念下去追问存在,我们不但经验不到任何关于存在的东西,还会被遮蔽得更深。那么,何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源始的时间性呢?“从将来回到自身来,决心就有所当前化地把自身带入处境。曾在源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10]372也就是说,时间性是一种把曾在、现在、将在统一起来的现象,我们只有在源始的时间性中才能把握存在的意义。
在其后期的同名演讲《时间与存在》中,我们是否能经验到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空间问题的关注呢?他虽然一再强调其演讲内容不是对《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的继续,但不可否认,他的主导问题仍然没有离开时间和存在。“存在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12]2,这说明存在作为在场状态仍显示为时间这种境域,我们如果想要追问存在的意义,是不能绕开时间的。这显然是对《存在与时间》中立场的重申,而不是抛弃。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时间理解为曾在、现在、将在的统一,而在此演讲中海德格尔说:“三维时间的统一性存在于那种各维之间的相互传送之中,这种传送把自己指明为本真的在时间的本性中嬉戏着的达到,就是第四维。”[12]16显然,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对于时间的界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期的更新和超越,但仍不可忽视《存在与时间》的奠基作用。在演讲中海德格尔亦对空间问题做出了阐释:“在《存在与时间》的第70节中,我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12]24这不仅重新确立了空间性对于追问存在的重要意义,而且把空间性与时间性提到了同样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自身一直致力于揭示时间和空间的源始统一性,当然他自己一再强调这种揭示是在现象学的范畴下进行的,即就其自身显示自身。揭示这种源始统一性的目的在于阐释存在之本质,显现存在的境域,揭示被遮蔽的存在,实现存在之澄明状态。而里尔克在他的诗歌中,没有对空间、时间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追问,其实也就是没有对使存在实现澄明状态的境域进行深入的追问。在海德格尔看来,伟大的诗人就是要诗意的追问存在,使存在实现澄明状态,里尔克显然做得还不够,那么,他必然就显得略为逊色。
3 海德格尔的里尔克阐释再评价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诗人荷尔德林、里尔克还是特拉克尔的诗歌阐释都是出于历史存在命运之必然,他所要做的是将思与诗的对话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对现象的还原,让诗歌本身显现为本身。而通过上述对海德格尔为何要阐释里尔克以及对里尔克所持态度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诗歌进行解读时其结论常常是先于过程的,无论他自身如何强调其阐释是出于历史命运之必然,无非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里尔克诗歌阐释的一种理解,难免会存在一定的过度阐释现象。
海德格尔对于里尔克诗歌的阐释可谓经典,以至于有很多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将其奉为圭臬,并且或多或少受海德格尔的阐释影响,把里尔克列入存在主义诗人的行列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海德格尔的解读就一语中的,实现了对里尔克的精准阐释呢?华裔美国学者刘皓明对此显然持否定态度,他宣称:“海德格尔的解读虽然在若干方面的确触及到海德格尔后期乃至晚期诗歌中的一些想法,但是其解读的方式比他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要更反语文学、更任意。”[6]168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中肯的,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诗歌阐释做出了超越诗歌本身的把握,当他在分析理解里尔克的诗歌时,一旦遇到困难与矛盾,便力图通过引用更多的旁证、并无证据支持的文本和思想观念,来廓清那些看起来还不够明晰的意象,从而达到一种所谓的自圆其说。因此,在解读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对里尔克存在一定的误读现象,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里尔克诗歌的原意,有过度阐释之嫌,以至于法国学者默里斯说:“海德格尔用一种闻所未闻的暴力把这位‘敞开’的诗人丢在了杂乱的地狱中。”[13]14
我们何以能认为海德格尔的阐释没有还原里尔克诗歌的原意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让我们返回里尔克的诗作本身,直面里尔克的语言。当然这样做也难免受到诟病,海德格尔在进行文本阐释时亦难免会进行过度阐释,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在解读里尔克诗歌时尊重原意呢?我们只有做到尽可能客观地分析,把里尔克的诗歌呈现出来,不把诗歌想要传达的思想意义预设为任何一种已知的结论,并且对于海德格尔的里尔克阐释大胆质疑,这样才能更客观地看待里尔克的诗歌,表达我们自身对于诗人里尔克的看法。
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的即兴诗进行阐释时说:“里尔克这首诗毕竟诗意地表明了,谁是那种冒险更甚于生命本身的冒险者。”[3]288而他的依据则是“更秉一丝气息……”这句诗后面加了省略号,他认为这道出了许多默默不表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样的论断未免显得太过随意,很难有说服力。单凭这首诗我们很难看出问题的答案,不过海德格尔说里尔克所说的冒险更甚者乃是诗人未免有些过于武断。我们认为,里尔克通过这首即兴诗的确阐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最能体现他所讲的人与动物的区别的诗作乃是他的《杜伊诺哀歌》(第8首):
受造物所有的眼看到的都是
敞开。唯独我们的眼
仿佛反过来,环绕它设置
如同陷阱,在它通畅的出口周围。[6]63
在这首诗中,里尔克所讲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里尔克显然认为动物被允许进入“敞开域”之中,而人则相反,“敞开域”仿佛就是为人而设立的,人只能在其周围徘徊而不允许进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呢?里尔克在晚年一封写给俄国读者的信中作出过解释,他认为是意识的级别造成的:“动物的意识的级别把它们置放在世界里,而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将世界每时每刻都放在对立面;动物就处在世界里;我们则由于我们的意识所取得的转向和增益而站在它前面。”[6]291因此,如果说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域”,在里尔克看来,诗人便同样不会被允许进入“敞开域”。里尔克在他的即兴诗里并没有赋予诗人任何特殊的地位,他只是为我们阐明了人与万物的区别,人由于意识程度的提高而处在一种冒险之中,至于说冒险更甚者是诗人,我们便无从得知,海德格尔阐释其内容所得出的结论只是为自己的哲学立场而服务。
海德格尔通过里尔克的即兴诗告诉我们,诗人的天职就是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歌唱存在。海德格尔自己也说是这首诗的意外之旨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视界,而何为意外之旨?无外乎是海德格尔以主观的方式强加于这首诗之上,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是“领会”,即用感悟的方式来达到对问题的理解领会,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领会”是对现象的还原,是真正进入诗歌作品的方式,而我们可以说没有比这种方式还要主观的解读了。因此,关于诗人天职的答案不能说是海德格尔完全臆断而产生的,但对于里尔克的诗歌他毕竟还是做了过度的阐释。那么,里尔克的诗歌里对于诗人的天职有无道说呢?在他的《杜伊诺哀歌》(第1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是啊,春天着实需要你。很多星星要
你在,好去观测它们。一道巨浪
从已逝的之中掀起,或是
在你经过敞开的窗前时,
有把小提琴呈献上来。这一切全是委命。[6]7
里尔克在这首诗里显然清晰明了地为我们揭示了诗人的伟大使命,那便是歌咏万物。春天是万物的象征,诗人不同于常人而拥有一把可以歌咏万物的小提琴,必然要为实现这种委命而不断吟唱。学者刘旭光对此认为:“我们相信海德格尔的结论并不是最终的,诗并不完全等于存在。”[14]367我们并不否认里尔克的诗歌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之思,但是,海德格尔对里尔克诗歌所作的部分阐释未免过于牵强附会,我们应该还原里尔克诗歌本来的意蕴。
海德格尔同样注意到了里尔克诗歌中的另一基本意象,那就是“天使”。海德格尔认为,里尔克通过这个意象所要道说出的东西,是从存在方面来思考的存在者整体。而海德格尔对里尔克所说的“天使”意象不加辨析地予以利用,那么,里尔克所说的“天使”意象真的指的是存在者整体吗?其实“天使”这一意象贯穿了里尔克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早期的比如1896年出版的诗集《宅神祭》中的天使、写于1898年的《少女对玛利亚的祈祷词》;1901年的《日课书》第2部《朝圣卷》、1903年第3卷《贫与死卷》中都出现过这样的天使。一直到后期的《杜伊诺哀歌》,里尔克都有对“天使”意象的描写:
每位天使都是可畏的。然而,呜呼
我却歌咏你们,几乎致命的灵魂之鸟们,
虽然了解你们。[6]178
《杜伊诺哀歌》(第2首)
里尔克在这首诗里所描绘的天使是可畏的,天使就是那灵魂之鸟,天使是可畏的,诗人若要想了解它们,就必须要歌颂它们。里尔克在这里所描绘的“天使”意象只是他诗作中对“天使”发出赞叹的冰山一角,我们很难穷尽对里尔克所说的“天使”意象的解读。刘皓明在解读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时也说到:“然而我们必须要看到,最初写下的哀歌与其后完成的哀歌在天使意象上有明显差别。”[6]182更不用说里尔克的早期诗作与后期更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其“天使”意象的灵感来源与含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海德格尔在阐释里尔克诗歌时不加辨析地把里尔克所说的“天使”意象归结为存在者整体,难免是对于里尔克诗歌的一种误读。
刘皓明在对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进行总结性评价时认为:“《哀歌》始终是高度主观化的,抒情主体的突出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浪漫派诗歌,这个主体以‘我’或‘我们’直接对读者或听者发言,经常通过向读者直接发言发问以感情的强烈性使读者接受其所表达的内容。”[6]347因此,我们可以说,里尔克的诗歌中仍然饱含了诗人本身的强烈情感在内,我们在阅读里尔克时应回归诗歌本身,如果我们一再以哲学家的标准来严苛要求诗人,那便是扭曲了诗歌本来的意味,过度的阐释便是对诗歌本身的严重伤害,虽然海德格尔的阐释看似精妙,但他显然犯了这样的错误。
孙周兴在《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一书中说到:“荷尔德林的‘诗’与海德格尔的‘思’是‘互释’的,而这种‘互释’实际上也是一切解释活动的本性和准则。”[15]235这里的互释二字之所以加了引号,实际上就意味这种“互释”其实是单向性的,就是解释活动的原则所在,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解释学的方法,是海德格尔用自己的“思”来阐释荷尔德林的诗,这种阐释必然是海德格尔所要“思”的东西所在,我们很难说荷尔德林的诗所要表达的就一定是海德格尔呈现出来的“思”,海德格尔的“思”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他的目的无非是让这种解释服务于他自己的“思”。阐释在本质上就是先入为主的,阐释者难免会把自身的立场带入到阐释的过程中去,海德格尔对于里尔克的阐释也无外乎是先确立自身的立场,把这个立场作为出发点,而阐释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回到这个出发点。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的诗歌进行阐释时说:“我们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因为它们由之得以言说的那个领域,在其形而上学的机制和统一性上,还没有充分的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获得深思,作这种深思是困难的。”[3]249所以,他避开了能代表里尔克诗歌最高水准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不谈,而选择了一首里尔克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即兴诗进行阐释,而在对即兴诗阐释的过程中他却又多次用里尔克的十四行诗和哀歌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前后的矛盾之处不是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海德格尔自身的立场吗?学者刘旭光在评价海德格尔的诗歌文本阐释时亦说到:“如果确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没有一个自在的文本,那么,海德格尔如何让我们相信,他所解说的诗之意蕴就是该诗之本旨,当他说他所选的诗和诗人具有历史的唯一性时,他的解诗的前提确在提醒我们——没有什么唯一。”[14]361所以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运思之结论其实早已得出,他只不过是在拿里尔克的一些诗作来为自己的立场作例证,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梵高的画的解读是如此,在《荷尔德林与诗的阐释》中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是如此,对于里尔克即兴诗的解读也如出一辙,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首即兴诗已经是海德格尔自己的“作品”了。
在这“作品”中,对诗人本质和天职的回答,是海德格尔运思后得出的,其实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诗人的本质和天职是海德格尔赋予的。海德格尔本身不是诗人,但他却也认识到了贫困时代的根源所在,更揭示出了作为贫困时代的人要走出贫困该如何去做,经验到了存在之澄明状态,甚至比诗人里尔克更深入、更透彻,所以海德格尔难道本身不就是那达乎深渊、道说着“神圣者”的贫困时代的“诗人”吗?以至于学者魏朝勇认为:“在贫困时代追问存在、道说神圣的诗人,怕只是海德格尔自己。”[16]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阐释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难免把自身的立场带入到了对里尔克诗歌的理解当中,其阐释显然是“六经注我”式的,当然这对于诗人里尔克本身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对此应予以批判。但通过对里尔克的阐释,我们再一次清晰地领会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并看到了他前后期思想的契合之处。
4 结 语
贫困时代诗人何为?诗人荷尔德林给了我们答案,后继者里尔克也给了我们回答,而最能洞烛此答案的莫过于海德格尔。贫困时代就是遗忘存在的时代,当下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逐渐被形而上学的表象性、计算性思维方式所控制的时代,而技术观念占统治地位更是让人不能本真地居有自身,处于技术摆置之下的人终日碌碌而从不去思考存在之意义。海德格尔通过对里尔克的阐释显然是为受技术统治的人寻找诗意追问存在的方式,在追问的过程中,其难免受到自身思想的影响,而我们应该看到,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阐释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是为了帮助人们学会思考,去指引人们追寻被遗忘的存在,建立属于人们本真的诗意存在的家园。因此,我们不应过于苛责海德格尔在对里尔克阐释时带入了偏见,而应该认识到海德格尔关于诗人天职和存在之思的道说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走出贫困时代,彰显存在的本质和魅力,这也是我们对海德格尔的里尔克阐释进行探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