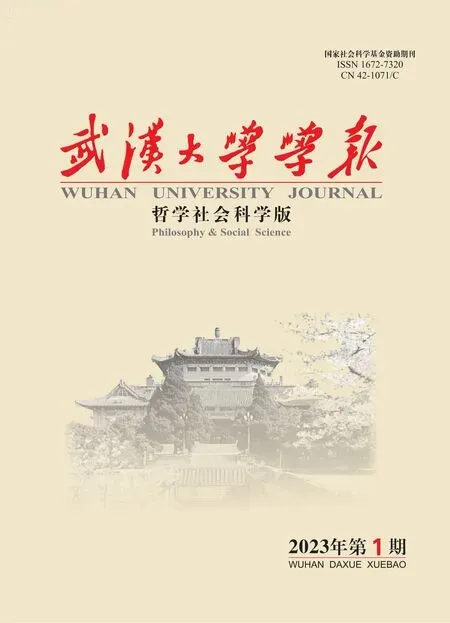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何宗美
帝王之学,是官学的最高层次,也是官学的最深内核,或者说是一种登峰造极的官学。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其实质是清代帝王之学。清代帝王之学,借助《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修纂得到一次最为系统的建构和最为强烈的宣扬。《四库全书》和《总目》从外到内都受到帝王之学的统摄,帝王之学是其灵魂所在。这一认识极其重要,真正把握有史以来作为最大国家政治文化工程及其成果的要害即在此。完全可以说,无论“四库学”研究,还是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研究,都有必要把握清代帝王之学这个最根本的核心。
一、帝王之学的一则简纲
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的政治动力及其操控方向,通常由其政治目标所决定。清王朝前至中期由发展而至盛世,究其原因与其政治目标密切相关。前至中期的几代帝王,都有着极高的政治目标,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也是清王朝统治的稳定并得到深入巩固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此,清王朝对思想、文化政治建构的高度重视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浩大的《四库全书》修纂工程,就是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代最高统治者实现最高政治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修书工程由乾隆帝“御定”“亲览”“天裁”“厘正”,不仅是清代重大的文化工程,更是清代重大的政治工程。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伟大工程,就其外在而言,产生了迄今为止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著作”“人类绝无仅有的‘书籍长城’”的《四库全书》[1](P37)[2](P70),也产生了“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的历史及其演变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梳理、大审视,从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特殊意义的经学通史、史学通史、子学通史和文学通史的书写”的《四库全书总目》;而从其内在而言,这一工程真正的政治目标并不在修书,而是在于一个更为深层也是更为根本的政治动机——清帝王之学的建构,修书的实质是清王朝帝国政治的“灵魂铸造”工程,《四库全书》和《总目》只是其外在载体以及建构帝王之学的举措和途径而已。
所谓帝王之学,不是我们在此为了研究需要的主观追加或臆造,而是切实体现在《四库全书》和《总目》中的原有存在。细心阅读可以发现,列入儒家类著录书乾隆帝所撰《御制日知荟说》提要,在介绍该著的基本内容以后,集中笔墨梳理帝王之学的简要纲领并阐释其大旨:
考三代以前,帝王训诫多散见诸子百家中,真赝相参,不尽可据。《汉书》所载黄帝以下诸目,班固已注为依托,亦不足凭。惟所载高帝八篇、文帝十二篇为帝王御制著录“儒家”之始。今其书不传。然高帝当战伐之余,政兼霸术。文帝崇清净之学,源出道家。其词未必尽醇,久而散佚,或以是欤?梁元帝《金楼子》,体侪说部,抑又次焉。夫词人所著作,盛陈华藻而已,帝王之学,则必归于传心之要义。儒生所论说,高谈性命而已,帝王之学,则必征诸经世之实功。故必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后吐辞为经,足以垂万世之训也。我皇上亶聪首出,念典弥勤,紬绎旧闻,发挥新得。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具备于斯。迄今太和翔洽,久道化成,《无逸》作“所”之心,与天行同其不息,而百度修明,八紘砥属,天声赫濯,尤简册之所未闻。岂非内圣外王之道,文经武纬之原,一一早握其枢要欤!臣等校录鸿编,循环跪诵,钦圣学之高深,益知圣功之有自也。[3](P1233)
这虽是具体一书的提要,但足以称得上是一篇意义完整的帝王之学论纲。它有几个基本意思:其一,帝王之学,由来已久,但此前的帝王之学,或文献不足征,或为依托不足信,特别是思想未醇,体杂“说部”,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帝王之学;其二,帝王之学的核心是传心与经世,既区别于词人的盛陈华藻,也不同于儒生的高谈性命,非词人之学和儒家之学可比;其三,帝王之学的最高代表是乾隆帝,乾隆帝的《御制日知荟说》是帝王之学的巅峰之作,真正达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其四,乾隆时代是前所未闻的盛世,而之所以能创造这一盛世,在于乾隆帝掌握了“内圣外王之道,文经武纬之原”即帝王之学的枢要,实现了帝王之学与帝王之政的完美统一。这种文字虽然是四库馆臣在“钦圣学之高深,益知圣功之有自”的膜拜心态下写的,但对帝王之学的揭示值得高度重视。
上段引文反映的另外两种观念也需要注意:帝王之学,这里体现的是尊今王的思想即尊清的思想——对清廷本朝帝王之学的唯我独尊主张。一方面,自顺治以来到康、雍、乾几朝代,在帝王之学的建树上确实有超越前代的基本事实;另一方面,清廷要借修《四库全书》之机,进一步在法理上确立本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让清人在论帝王之学时站在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拥有了纵论历代、评判在我的话语权。《御制日知荟说》提要对包括“三代以前”在内历代帝王之学,评价是皆不足为范。另如唐太宗《帝范》“其词”亦“不免冗赘”[3](P1202),明太祖《资政通训》等“义或不醇,词或不雅”[3](P1232),都没有建立严格意义的帝王之学。《御定执中成宪》提要更集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御制之书,惟唐之《帝范》敷陈得失为最悉。官撰之本,惟明之《君鉴》缕举事迹为最详。然《帝范》颇参杂说,词意或不深醇,《君鉴》旁摭诸书,义例亦为冗杂。至于宋之《洪范政鉴》,以焦赣、京房之说附会于武王、箕子之文,益离其宗。盖圣人之道统,惟圣人能传之,圣人之治法,亦惟圣人能述之,非可以强而及也。我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上超三古,阐明帝学,论定是编,汰驳存精,删繁举要。凡遗文旧籍,一经持择,即作典谟,犹虞帝传心,亲阐执中之理,殷宗典学,自述成宪之监也。虽百篇之裁于洙、泗,何以加兹!家法贻留,以巩万世之丕基者,岂偶然欤!”[3](P1234)唐、宋、明、清的帝学被放在同一话语场下比较优劣,唐太宗御撰《帝范》、宋仁宗御撰《洪范政鉴》、明景帝御撰《君鉴》,作为帝学都是存在问题的,唯有雍正《御定执中成宪》才真正做到“上超三古,阐明帝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盖圣人之道统,惟圣人能传之,圣人之治法,亦惟圣人能述之,非可以强而及也”,也就是说,此前历代帝王皆非圣人,故历代帝学也就不可能传“圣人之道统”,不可能述“圣人之治法”。出于尊清的目的,历代帝王之学遭到了清代官学的贬低。清帝其人堪称“圣人”“圣德神功”,自古无比,“阐明帝学”的文化使命才真正完成。清代官学的文化唯我独尊意识,在《四库全书》和《总目》的体系上得到了落实。历代帝王之作,除唐太宗《帝范》收入儒家类著录之外,宋仁宗《洪范政鉴》被降低为术数类并附以存目[3](P1472),明太祖《资治通训》连存目都未进入而完全被排除在清代官修“四库”体系之外;明景帝《君鉴》放在杂家类存目,与明太祖敕修的《昭鉴录》《永鉴录》《历代驸马录》《公子书》等一起,都被剥夺了御撰或官修的尊荣[3](P1733)。帝王之著被斥之最甚者,莫过于明成祖的《圣学心法》。胡广等明臣原本认为“帝王之要,备载此书”,但代表清廷意志的四库馆臣谓其“乃依附圣贤,侈谈名教,欲附于逆取顺守”,至于成祖其人“称兵篡位,悖乱纲常。虽幸而成事,传国子孙。而高煦、宸濠、寘鐇之类,接踵称戈,咸思犯上,实身教有以致之……至于杀戮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纣之所不为者,夷然为之,可谓无复人理”,就连谈帝王之学的资格也不具备——“天下万世,岂受欺乎”[3](P1249),成祖说的那一套在清廷看来就是欺天下万世的一派谎言,根本不配帝王之学——尽管清代帝王同样实行残酷的政治专制,淫刑酷暴与明成祖相比并无本质区别。站在清代官学立场的四库馆臣要在《四库全书》和《总目》体系上树立清朝帝王和帝王之学的独尊地位,在清帝王中又唯以乾隆帝为最高代表,体现的思想宗旨是尊今王。帝王之学的专论,不安排在前代帝王之著的提要进行,即使顺治所撰《御定资政要览》,康熙帝所制、雍正阐绎的《圣谕广训》,雍正录编康熙语《庭训格言》,这些无疑都是构建清帝王之学的篇章,但帝王之学的话题没有放在诸著提要中讨论。可见,在乾隆《御制日知荟说》提要正式论述帝王之学,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深思熟虑出于尊今王的需要。
二、“帝王之学与儒者异”
建立清帝王之学,必须在两种参照体系中确立清帝王在思想、文化领域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或者说其本身将面对两种对立因素所形成的干预或动摇使清帝王之学难以拥有绝对权威或话语权。一个来自与其身份相同的古代帝王,另一个来自原本在思想、文化占据优越地位的儒者群体。应对前者,就有了清帝王之学中的尊今王思想,解决如何凌厉前代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自汉以来长期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帝王与儒者的对立在所难免,必须以帝王取代儒者成为清王朝最高话语权的掌控者,以帝王之学取代儒者之学,改造旧儒家。
尊今贬古特别是尊清贬明的清帝王之学,一个显著特点或者说思想意图就是尊王贬儒。《总目》谈论“帝王之学”凡四次,分别在康熙御定《日讲易经解义》提要(卷6)、宋程大昌《禹贡论》提要(卷11)、乾隆《御制日知荟说》提要(卷94)、明张元祯《东白集》提要(卷175),值得一提的是,四次无一例外都与“儒者”加以对照区别,这从表达目的及其效果来说就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场,传达清廷重要的思想倾向信息。《御制日知荟说》提要的相关内容已见前述,以下引录另三例为证:
《易》为四圣所递传,则四圣之道法治法具在于是。故其大旨在即阴阳、往来、刚柔、进退,明治乱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长,以示人事之宜,于帝王之学,最为切要。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非但占验(示旁加几字)祥,渐失其本,即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阐义理者,言心而不言事,圣人立教,岂为是无用之空言乎?(《日讲易经解义》提要)[3](P53)
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大昌讲《尚书》于经筵,不举唐虞三代之法以资启沃,而徒炫博奥,此诚不解事理。(《禹贡论》提要)[3](P142)
元祯以讲学为事,其在讲筵,请增讲《太极图》、《西铭》、《通书》。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讵可舍治乱兴亡之戒,而谈理气之本原。史称后辈姗笑其迂阔,殆非无因矣。其诗文朴遫无华,亦刻意摹拟宋儒,得其形似也。(《东白集》提要)[3](P2399-2400)
“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这是代表清代官学思想的《总目》明确给出的一个基本判断。究其所异,并不是特点不同,而是一个优劣定性。清代官学认为,学之不同有“帝王之学”,有“儒者”之学,二者极不相同。在这种比较视野里,其倾向是明显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目的在于弘扬前者而改造后者。《总目》中所涉二者比较的四处文字,恰是经、史、子、集各一,这必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似又意味着,在经、史、子、集四大知识领域或知识体系中,无不存在帝王之学与儒者之学的区别,即有帝王之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另又有儒者之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在两者关系上,儒者之学与帝王之学有其对立,但二者又不可分割,帝王之学通常不能离开儒者,也不能离开儒者之学。但帝王之学的建立和倡行,必须批判和纠正儒者之学的问题,而其批判和纠正只不过是站在帝王之学立场上,是以帝王之学来看儒者之学,而不是相反。在帝王之学看来:儒者之学的症结在于“高谈性命”“拘泥章句,株守一隅”“徒炫博奥”,或为“空言”而“无用”,或为“迂腐”而可笑;儒者之学的毛病是与高度重视“治乱兴亡之戒”“经世之实功”的帝王之学完全背道而驰。
清代官方注意到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在程大昌《禹贡论》提要中有意识地拿宋孝宗对儒者之学过于繁琐的指责以引出问题,谓周密《癸辛杂识》载“大昌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阜陵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历,虽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铨曹亦如此’,既而补外”[3](P142)。但考其出处,周密所载实出于他的另一书《齐东野语》卷一“孝宗圣政”条[4](P2)。至于宋孝宗对程大昌“进讲《禹贡》”一事的评价,实另有相反的说法。陆心源据彭椿年为程大昌《禹贡论》所作后序载“程公具以其所知为书以奏。上见,大加褒劳”,推理认为“果如密言,孝宗方且厌之,椿年敢伪造褒劳之诏,刊版传布乎?”两相比较,周密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且由此归咎到周密及其祖辈的人品问题:“密游贾似道之门,本非端人,每好诬蔑正人,其祖秘在高宗时专以攻击正人为事。”[5](P24)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用了陆氏的考辨文字,并明确指出后序作者应为彭椿年而非陈应行[6](P76-77)。其实,周密所载与《禹贡论》自序及彭椿年(原误为陈应行)后序所说“殊相乖剌”的问题,四库馆臣也是注意到了的,但仅轻描淡写提了一下。馆臣似乎没有兴趣去做实学的考证,而是顺手拈来周密一家之说引出“帝王之学与儒者异”的实质性话题加以阐发。显然,按彭椿年及后来陆心源、胡玉缙之说,就不存在“帝王之学”与“儒者之学”相冲突的问题。在原始材料与官学立场不一致的时候,代表官学的《总目》宁愿抛弃考据的做法而不失时机地宣扬官方思想,这恰说明其用意并不在澄清事实,而在表达官方意志。
帝王之学与儒者之学两者的亲近关系及矛盾,是通过古代经筵制度最直接反映出来的。经筵制度形成了帝与师的特殊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帝、师分别为政、教的最高权力代表者,政、教二分,帝、师各自拥有一方面的最高话语权。但到了清代,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代帝王在大力巩固政权地位之同时更是强化了其教主地位,推进了政、教合一,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内在机制。清代帝王所致力者在政的方面自不必说,在教之一端尤其有超越前代之处。前面梳理的情况显示,御制、御定等著可以看作皇帝直接以教主身份的立言。《御定资政要鉴》提要明确指出:“惟是历代以来,如家训、世范之类,率儒者私教于一家。”[3](P1232)长期以来儒家的话语权统治在此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挑战。在思想史上,等于是对“独尊儒术”的一种颠覆。这种挑战和颠覆,不是对“百家争鸣”的开放,没有任何思想自由的意味,反而是以皇权向儒家思想领地的强势扩张。为此,清代皇帝不惜亲自披挂上阵,强力霸占原有的儒家话语场。这种做法从顺治帝即已开始。在《四库全书》体系中被置于清代儒家类著作之首的《御定资政要览》,可以看出其所为者,就是用帝王价值观取代儒家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遵循的基本准则,虽然使用的话语大体来自儒家,但话语发出者却被置换了角色,所谓“丁宁诰诫,亲著是书,俾朝野咸知所激动,而共跻太平”,这是皇帝直接扮演教主的表现。该书从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妇道、友道、体仁、弘义、敦礼、察微、昭信、知人、厚生、教化、俭德、迁善等30章,“每篇皆有笺注,亦御撰也”,并以“资政要览”名之,可见其所谓政,实乃政、教合一之政,而最着力处更在于教之上,故曰“盖治天下者,治臣民而已矣”[3](P1232),这是典型基于教化思想的人治观。更重要的是,过去“率儒者私教于一家”的时代被清代帝王改写了。康熙御撰《庭训格言》里,一目了然的是过去的“子曰”已置换为“训曰”了,如“训曰:吾人凡事惟当以诚,而无务虚名……”“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等[7](P13,17)。《总目》该书提要曰:“是编以圣人之笔,记圣人之言,传述既得精微,又以圣人亲闻于圣人,授受尤为亲切,垂诸万世,固当与典谟训诰共昭法守矣。”这里的圣人不是通常所指的尧、舜、周、孔,而是指清代的两位皇帝康熙和雍正。《庭训格言》是“世宗宪皇帝追述圣祖仁皇帝天语,亲录成编”,故知“以圣人之笔”的圣人即雍正,“记圣人之言”的圣人即康熙。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盛赞:“圣有谟训,词约义宏,括为十有六语不为少,演为一万余言不为多。迄今朔望宣读,士民肃听,人人易知易从,而皓首不能磬其蕴,诚所谓‘言而世为天下则’矣。”其中,“十有六语”指康熙所颁《圣谕》十六条,“一万余言”指雍正“推演圣谟”的《广训》[3](P1233),馆臣的评价可谓顶礼膜拜、媚态百出之至,反映了清代帝王树立绝对话语权威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效力。“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原本是《中庸》对“王天下”的君子提出的境界亦即使命,但《中庸》同时又认为这种境界和使命从来没有实现过,历来的事实是“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8](P292)。上焉者指曾经在位的君王,下焉者指没有尊位的孔子,一则无征,一则不尊,结果都是“不信民弗从”,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难以让伟大的圣人思想转化为全民共同思想和共同行为的症结所在。清代帝王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解决中国社会的这个千古难题,而根本的方法就是致力于政、教合一的真正实现,政、教合一的标志则是帝王之学的建立和施行,以之取代“下焉者虽善不尊”的儒者之学,更何况在清廷看来,儒者之学在“虽善不尊”外还存在“不善不尊”的问题,所以帝王之学的优势更让儒者之学难以相提并论。
由经、史、子、集四大板块构成的知识结构体系,子部的思想性质最为特殊,是所谓“百家”著述和思想的汇集,清代官学对子部的思想统摄也必然予以最大的重视,反映在官学所建构的清代子部体系中也显而易见。子部儒家类尤其如此:《四库全书》和《总目》清代儒家类首置“御定”“御制”“御纂”之著达10部之多,超过清代儒家类著录著作18部的一半,在《总目》叙录清代儒家类著作140部中也占了1/14。对于清代儒家类著作来说,这就好比戴了一个“大官帽”,所有著作都被笼罩在这个“大官帽”之下,构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官学统摄作用。再加上这十部贴上皇帝标签著作的提要,清廷意志更是得到了高度强化。所谓“群言淆乱折诸圣”[3](P1234),这是馆臣明确提出来的官学思想方针,而这个方针的贯彻又有两个基本保证:一是顺、康、雍、乾四位皇帝的“御定”“御制”“御纂”之著,二是在皇帝著作基础上撰写的代表清代官方思想意志的提要。可见,清代子部的儒家在《四库全书》和《总目》体系中,无论内容还是价值观念,都被彻底地改造成了清代官学的儒家体系。
原有的儒家并非清代官方期待的样子。从横向来看,“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3](P33),不免造成“群言淆乱”的情形,甚则“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3](P33)。从纵向来说,“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3](P33)这种情状从隋代王通即已开了端绪,“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3](P1193)。儒家史不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而是由纯而杂、方向不断偏离、问题愈演愈烈的历史,与“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3](P1193)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这是清廷心目中儒家的既有现状,显然这种现状并不足以满足清廷的意愿,为此,重新规范、整顿旧的儒家,造就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新儒家,即大力推进儒家的政治化和官学化,也就势在必行,也必然成为借修《四库全书》要实行的重要思想目标。
三、“世为天下则”以统摄百家
处理好帝王之学与儒者之学的关系,意味着解决思想、文化上所面对的主要挑战。百家之学的统摄于帝王之学而言,也势在必然。
“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在《四库全书》和《总目》的清代子部体系中作为思想基础和基本准绳,也就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类,其它诸类概莫能外。兵家、法家与帝王之学宗旨相左,所以非但清代御制、御定著作没有此二类,而且清人著作也一律未入著录之列。兵家“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3](P1294),法家即“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3](P1313),此二者显然不会明确受到帝王之学所提倡,所以清代子部兵家类、法家类自然而然就受到弱化处理。农、医、天文算法等则不一样。农家类清代著录一种,即乾隆敕撰《钦定授时通考》,其提要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作为帝王之学的农家之学与作为“徒为农家言”的根本区别。“重农贵粟,治天下之本也”,即把农家之学上升到帝王之学的高度。举贾思勰《齐民要术》和王桢、徐光启著作为例,或“名物训诂,通儒或不尽解,无论耕夫织妇也”,或“疏漏冗杂,亦不免焉”,而由乾隆帝敕撰的《钦定授时通考》,则“准今酌古,务期于实用有裨。又详考旧章,胪陈政典,不仅以自生自息听之闾阎,尤见轸念民依之至意”,所以“非徒农家言矣”,而前者则不过“徒农家言”而已[3](P1326),这就是帝王之学与一般意义的农家之学不同之大端。与《御制日知荟说》《钦定授时通考》提要一样,凡御制、御定之类著作的提要,几乎都是帝王之学的阐释和宣扬。医家类著作如乾隆敕撰《御定医宗金鉴》的提要,天文算法类如康熙《御定历象考成》《御定数理精蕴》、乾隆《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的提要,术数类如康熙《御定星历考原》及乾隆《钦定协纪辨方书》的提要,艺术类如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和乾隆敕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提要,谱录类如康熙《御定广群芳谱》及乾隆《钦定西清古鉴》《钦定西清砚谱》《钦定钱录》的提要,类书类如康熙《御定渊鉴类函》《御定骈字类编》《御定分类字锦》《御定佩文韵府》《御定韵府拾遗》以及康熙敕修、雍正《御定子史精华》的提要,道家类如顺治《御注道德经》的提要等。这些提要秉持共同的宗旨:
一是尊奉清帝为“圣人”或“大圣人”,称其著作为“大圣人制作”,帝王之学为“圣学”。如,康熙《御定历象考成》:“洵乎大圣人制作,万世无出其范围者矣。”[3](P1395)《御定韵府拾遗》:“圣人制事精益求精,不留丝毫之欠阙。”[3](P1797)《御定星历考原》:“大圣人之于百姓,事事欲趋其利而远害,诚无微之不至矣。”[3](P1446)乾隆敕撰《秘殿珠林》:“圣人制作,或创或因,无非随事而协其宜尔。”[3](P1503)康熙《御定佩文韵府》:“盖圣学高深,为千古帝王所未有。”[3](P1797)乾隆《御制日知荟说》:“钦圣学之高深,益知圣功之有自也。”[3](P1233)
二是以清代帝王之学俯视千古,凌厉前代,塑造清帝唯我独尊、无与伦比的地位。如雍正敕撰《御定执中成宪》:“我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上超三古,阐明帝学,认定是编……虽百篇之裁于洙、泗,何以加兹!”[3](P1234)乾隆敕编《御览经史讲义》:“我皇上深造圣域,而俯察迩言。海岳高深,不遗尘露……岂非前代帝王徒循旧制,我皇上先登道岸,足以折衷群言欤!”[3](P1235)乾隆敕撰《石渠宝笈》:“与前代帝王务侈纷华靡丽之观者,迥不侔也。”[3](P1502-1503)
三是相对于各领域专门之学,清代帝王之学被认为是登峰造极、不可企及,使之站在知识话语的最高点,手握真理,论定是非。比如医学,乾隆敕撰《御定医宗金鉴》提要谓:“自古以来,惟宋代最重医学。然林亿、高保衡等校刊古书而已,不能有所发明。其官撰医书如《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或博而寡要,或偏而失中,均不能实裨于治疗,故《圣济总录》惟行节本,而《局方》尤为朱震亨所攻。此编仰体圣主仁育之心,根据古义,而能得其变通,参酌时宜,而必求其征验。寒热不执成见,攻补无所偏施,于以拯济生民,同登寿域。涵濡培养之泽,真无微之不至矣。”[3](P1363)又如天文算法,康熙敕撰《御定历象考成》提要谓:“案推步之术,古法无征。所可考者,汉太初术以下,至明大统术而已。自利玛窦入中国,测验渐密,而辨争亦遂日起。终明之世,朝议坚守门户,讫未尝用也。国朝声教覃敷,极西诸国,皆累译而至。其术愈推愈精,又与崇祯《新法算书》图表不合。而作《新法算书》时,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深隐不可解。圣祖仁皇帝乃特命诸臣,详考法原,定著此书,分上、下二编。上编曰《揆天察纪》,下编曰《明时正度》。集中、西之大同,建天地而不悖。精微广大,殊非管蠡之见所能测……此皆订正《新法算书》之大端。其余与《新法算书》相同者,亦推术精密,无差累黍。洵乎大圣人之制作,万世无出其范围者矣。”[3](P1394-1395)康熙《御定数理精蕴》提要谓:“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也。”[3](P1409)再如谱录之学,乾隆《钦定西清古鉴》提要谓:“盖著述之中,考证为难,考证之中,图谱为难,图谱之中,惟钟鼎款识,义通乎六书,制兼乎三礼,尤难之难。读是一编,而三代法物恍然如觌。圣天子稽古右文,敦崇实学,昭昭乎有明验矣。”[3](P1529)另如类书之学,康熙《御定渊鉴类函》提要谓:“盖自有类书以来,如百川之归巨海,九金之萃鸿金矣。”[3](P1794)甚至玄之又玄的老子之学也不例外,顺治《御注道德经》:“惟我世祖章皇帝此注,皆即寻常日用,亲切阐明,使读者销争竞而还淳朴,为独超于诸解之上。”[3](P1937)
四是盛赞清代帝王之学其体例之善堪为“著作之轨范”[3](P1502),其影响之深当“流传于万世”[3](P1235),其作用之巨则“以巩万世之丕基”[3](P1234)。以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为例:“分门列目,征事考言,所引书凡一千八百四十四种。每条之下各注所出,用张鸣凤、桂故、桂胜、董斯张《吴兴备志》之例,使一字一句必有所征,而前后条贯,无所重复,亦无所抵牾。又似吕祖谦《家塾读诗记》,裒合众说,各别姓名,而裒贯翦裁,如出一手。非惟寻源竟委,殚艺事之精微,即引据详赅,义例精密,抑亦考证之资粮,著作之轨范也。”[3](P1502)再如顺治《御定资政要览》:“传诸万年,所宜聪听而敬守也”[3](P1232),乾隆《御定仪象考成》“验诸实测,比旧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亦前古之所未闻。密考天行,随时消息,所以示万年修改之道者,举不越乎是编之范围矣”[3](P1396)。
四、帝王之学的文化心态与思想方法
就清帝王之学本身而论,所谓凌厉前代、取代儒者、统摄百家,其前提或者可能性何在,这显然至为关键。其决定的因素实在于帝王之学两个最根本的特点,分别揭示了帝王之学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方法。
首先是“圣人之心所见者大”“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这里的圣人是指清帝。乾隆《钦定西清砚谱》提要讲到帝王文物观与收藏家文物观相区别:“古泽斑驳,珍产骈罗,诚为目不给赏,而奎藻璘(王旁加扁字),征名案状,如化工肖物,尤与帝鸿之制,周武之铭,同照映万古。然睿虑深长,不忘咨儆,恒因器以寓道,亦即物以警心。伏读御制序有云:‘惜沦弃,悟用人,慎好恶,戒玩物。’无不三致意焉。信乎圣人之心所见者大,不徒视为文房翰墨之具矣。”在对珍奇宝物的喜爱上,帝王与其他人相同,所异者在帝王之圣心“所见者大”,能够“因器以寓道”“即物以警心”,而不能“徒视为文房翰墨之具”,这就是帝王的文物观,也是清代官方所要树立的文物观,以此区别也旨在矫正一些收藏家或文人的文物观。顺治《御注道德经》提要则针对思想史上儒、道各异其趣以及道家的老子学说阐释纷杂的现象,指出帝王之学以其“兼收并蓄”之“大”,而独具超越和统一思想分歧的效用:“盖儒书如培补荣卫之药,其性中和,可以常饵;《老子》如清解烦热之剂,其性偏胜,当其对证,亦复有功,与他子书之偏驳悠谬者异。故论述者不绝焉,然诸家旧注,多各以私见揣摩,或参以神怪之谈,或传以虚无之理,或岐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参诸兵谋。群言淆乱,转无所折衷。惟我世祖章皇帝此注,皆即寻常日用,亲切阐明,使读者销争竞而还淳朴,为独超于诸解之上。盖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凡一家之书,皆不没所长;圣人之化神,因事制宜,凡一言之善,必旁资其用。固非拘墟之士所能仰窥涯涘矣。”[3](P1937)馆臣把顺治皇帝的《御御注道德经》吹捧到“独超于诸解之上”的地步,对其他注老之家一概贬低,断言“固非拘墟之士所能仰窥涯涘矣”,这不过是显示帝王之学以政治霸权而滥行思想霸权,在注老史上来说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但从帝王之学来说,却真实地反映了它的一个得天独厚的特点,即所谓“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帝王之学不必偏持一端,而能做到兼取儒、道,包容众说,至少出于思想一统的目的,帝王之学希望平息思想争端,定于一尊。这是帝王之学作为官学最本质特征的体现。就文化心态而言,帝王与任何思想家、学问家都不尽相同,至高无上的身份足以使其拥有胸怀天下、俯视万代的优越姿态,而当帝王与圣人甚或大圣人等同的时候,帝王心态也就与圣人或大圣人心态画上了等号,“兼收并蓄”成为“圣人之心”“圣人之道”的自然所为。
其次是“群言淆乱折诸圣”或者说“折衷群言”。这是馆臣站在官学立场,认为清代帝王之学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构建帝王之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思想史上对“群言淆乱”的忧患由来已久,扬雄《法言·吾子》对此正式提出“折诸圣”的做法。他曾专门设计了一番相关话题的对话,对问题给予回答。“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诸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9](P82)这是征圣、宗经思想的一个源头。这一思想在修纂《四库全书》时受到清代官学的高度重视,直接作为一项基本的方针。自古以来思想史的不断发展,客观上的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言体系,即思想史本身就是一种群言态,无论是扬雄著《法言》的时代还是清廷修《四库全书》的时代,所面对的思想现实都不例外。站在思想一统主义者的眼光来看,思想史作为一个庞杂的群言世界会更显突出,折衷群言的使命感也更强烈。这与思想多元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清廷来说,修纂《四库全书》和《总目》之举,实质就是以官学折衷群言,去其“淆乱”,而归于一统。只是与扬雄相比,折衷的准尺不再一样。在扬雄那里,“折诸圣”的圣是儒家的灵魂人物孔夫子,而清代官学的圣是奉为“圣人”“大圣人”的皇帝,由尊孔变成了尊帝王、尊儒学变成了尊帝王之学。在《总目》中,四库馆臣出于清代官学的立场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拿易学来说,认为宋代之后的易学史一直是“群言淆乱”的状况,《御纂周易折中》提要曰:“自宋以来惟说《易》者至夥,亦惟说《易》者多岐,门户交争,务求相胜,遂至各倚于一偏。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明永乐中官修《易经大全》,庞杂割裂,无所取裁,由群言淆乱,无圣人以折其中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圣祖仁皇帝道契羲、文,心符周、孔,幾余典学,深见弥纶天地之源,诏大学士李光地采摭群言,恭呈乙览,以定著是编……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数千年画卦系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3](P53-54),所以《御纂周易折中》便是易学领域或易学史上“群言淆乱而折诸圣”的帝王易学之著,成为历代易学的最高权威。再如康熙《御批通鉴纲目》,因为朱熹《通鉴纲目》产生以来同样存在“各执所见,屹立相争”的问题,通过康熙的御批,“权衡至当,衮钺斯昭,乃厘定群言,折衷归一”[3](P1170),由此在史学领域实现“群言淆乱折诸圣”,而《御批通鉴纲目》等一系列清代帝王史学之著,则取代像朱熹《通鉴纲目》之类的经典著作而成为历代史学著作的最高权威。文学的领域也是如此。经过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诏编的《皇清文颖》是一部在文学上“群言淆乱而折诸圣”的最高典范之作。在该著提要中,馆臣代表清代官方立场发表了一篇皇清文章典范论:首先认为历代以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帝王曾经完成过“折衷群言”的当代总集编纂,以致出现“或独任一人之偏见,或莫决众口之交哗”的局面;接着依“我国家定鼎之初”“顺治以来”“康熙六十一年中”“雍正十三年中”“我皇上御极之初”分别言述“皇清”文学之盛,从“人心返朴,已尽变前朝纤仄之体”到“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轹古人”,既把清朝塑造成前所未有的政治盛世,又把清代塑造成超越历代的文学盛世;然后直接盛赞四代清帝“并聪明天亶,制作日新”“足以陶铸群才,权衡众艺”,与文人相比,简直就是“譬诸伏羲端策而演卦,则谶纬小术不敢侈其谈;虞舜拊石而鸣韶,则弦管繁声不敢奏于侧”;最后给《皇清文颖》定论说:“迄今披检鸿篇,仰见国家文治之盛与皇上圣鉴之明,均轶千古。俯视令狐楚、吕祖谦书,不犹日月之于爝火哉?”[3](P2660)令孤楚曾奉唐宪宗诏编《御览诗》,吕祖谦则奉宋孝宗诏编《宋文鉴》,馆臣说与《皇清文颖》相比,就像《庄子·逍遥游》讲的“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10](P6)那样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两个因素,一是“国家文治之盛”,二是“皇上圣鉴之明”,使之“轶千古”而不可企及。
经、史、集的“折衷群言”,已略见于上述。四部中子的情况更是特殊,因为子的“群言淆乱”更突出。这一点,在《总目》中一篇《子部总叙》其核心思想不外乎就是“群言淆乱”,特别是其中的杂家更是“群言歧出,不名一类”。“博收而慎取”就成为清代官学对待子部的基本态度[3](P1191)。再到14篇小叙,对子部各类别也基本上是按照“群言淆乱”或“群言歧出”的总体把握来做基本判断的。《儒家类叙》前已有所分析,另如《兵家类叙》“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3](P1294),《农家类叙》“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触类蔓延”[3](P1323),《天文算法类叙》“洛下闳以后,利玛窦以前,变法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3](P1385),《术数类叙》“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3](P1419),《艺术类叙》“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至于谱博奕、论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等等,完全都可以用“群言淆乱”来概括。可以说,“群言淆乱”是清代官学对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总体认识,《四库全书》和《总目》修纂的思想受到这个总体认识的支配。子部是思想史、文化史“群言淆乱”最突出的部分,故子部的修纂和批评也更突出体现了清代官学“群言淆乱”的思想史、文化史判断。对这种状况,清代官学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而严格加以实施。办法就是“折诸圣”,即折诸清代帝王。这里,清代帝王就像扮演成思想和文化法庭的大法官,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行使其决断。而其有力的办法,除清代帝王御制、御批、御注、御选、御定了各种门类的著作,以之作为“折诸圣”的最高范本,供士林和整个社会遵循,这就是《圣谕广训》提要所说的“迄今朔望宣读,士民肃听,人人易知易从”[3](P1232)。同时又借助书前提要和《总目》强化帝王之学的直接宣扬,并将“群言淆乱折诸圣”的思想方法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包括著作的归类、取舍、褒贬等。以帝王之学“折衷群言”使清代统治者找到了思想一统的根本方法。这在许多地方有明确表达,《天文算法类叙》所谓“圣祖仁皇帝《御制数理精蕴》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于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年”,即是以帝王之著为“折衷群言”之“垂范”;又曰“今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古来疏密,厘然具矣”,则是“群言淆乱折诸圣”方法的具体遵循[3](P1835)。《御纂性理精义》《御定执中成宪》《御览经史讲义》《御注道德经》等提要,都反复提到“折诸圣”“折衷以御论”“折衷群言”“群言淆乱,转无所折衷”而以御注“销争竞”[3](P1234,1235,1937)。在没有明确使用这一说法的地方,其思想方法无一不是“群言淆乱折诸圣”。掌握了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四库全书》及《总目》就得到了一个关键认识。例如,《小说家类叙》谓“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3](P1834),就是“群言淆乱折诸圣”做法的结果。而在小说杂事、异闻、琐语“三派”中,清代竟无一部收入著录之列,也显然是“折诸圣”所致——站在帝王之学的角度,对其本朝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当代,清朝统治者采用了更严厉的态度,体现扼制“群言淆乱”局面蔓延的意图。这便可以理解清代官学何以明显轻视子部之小说家类,这种小说观无疑是立足于帝王之学才具有的,与文学或文化的小说观完全不同。
“群言淆乱而折诸圣”,放在清代具体的政治语境来看,实质是用帝王之学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所谓“折诸圣”事实上也就是“折诸帝王”,在《四库全书》和《总目》来说就是折诸乾隆帝的“天裁”[3](P31)。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为帝王之说作为群言的裁定者寻找合理的依据,也确立了如何建立“帝王之学”的思想路径。把握“群言淆乱折诸圣”的“帝王之学”这一关键点,我们理解《四库全书》和《总目》就有了一个基本纲领。抓住了这个纲领,想要大到真正懂得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体系的宏大性和思想的严密性,小到领会《四库全书》和《总目》的每一则提要,就能纲举目张,执本末从,而以宏观的视野深刻认识清王朝及其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也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把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