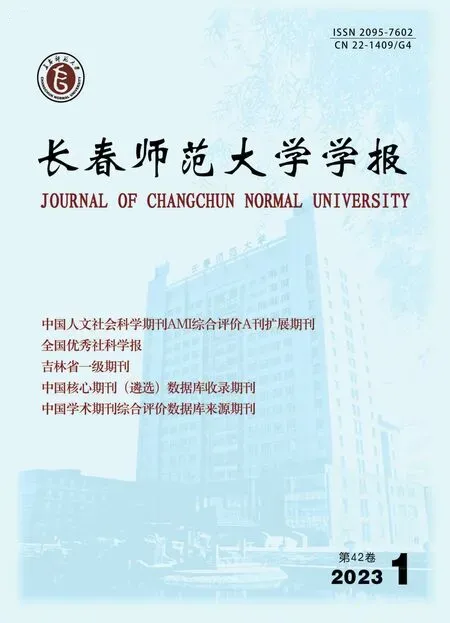媒介地理学视域下国产藏语电影的生产地理空间与文化认同
唐 进,康宗祁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从影像诞生之日起,藏区就以其瑰丽的地理样态和神秘的族群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探索者的目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电影事业从萌芽到成熟,民族题材作品不断产出,藏族题材电影也层出不穷。“我国有关藏族、藏地的影像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由月明影片公司拍摄于1935年的《神秘的西藏》和《黄专使奉令入藏致祭达赖喇嘛》,这两部最早的藏族电影是较为简单的影像和事件记录,而真正的藏族电影是在1949年后才发轫”[1]53-60,《农奴》(SerfsSlaveLabor, 1964)、《盗马贼》(HorseThief, 1988)、《红河谷》(RedRiverValley, 1996)等作品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进入新世纪,随着新的电影制作与发行政策的实施以及电影产业的规范化,“藏族题材电影有了‘藏族母语电影’的称呼,学界亦名‘藏语电影’”。[2]88-95从另一角度理解,“中国本土的‘藏语电影’是新世纪以来在‘西藏题材电影’内部产生的话语分支,也是2004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母语电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31-33。从2004年开始,藏族导演共拍摄了16部藏语电影;在同一时期,非藏族导演共拍摄了13部藏语电影。从影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藏族导演对本民族文化的阐述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自如地运用“原住民”的文化身份,从族群文化的角度本真地反映藏区的地理景观特色与地域文化内涵;非藏族导演则更多地从外部视角出发,重视展现“局外人”想象中藏区独特的风光和风俗。
一、国产藏语电影文本的产生与发展轨迹
2004年10月1日,影片《可可西里》(MountainPatrol)上映。导演陆川拍摄该片时将藏语作为第一表述语言,这标志着“国产藏语电影”概念的基本成型。国产藏语电影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期,且按照主创人员血缘身份的差别呈现出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其一是由藏族导演构成的发展轨迹。例如,《静静的嘛呢石》(TheSilentHolyStones, 2006)是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拍摄的藏语电影,这部影片宣告藏语电影进入了“本土化”创作阶段。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用“局内人”视角讲述藏族故事,影片中藏族文化的内涵表征相较于非藏族导演的视角而言显得更加纯真质朴,民俗形象更具凹凸感。这类影片天然自有的原生性质受到西方影评界青睐,被贴上“民族就是世界”的标签,在各大国际电影节广受好评,并在各个独立竞赛单元斩获不少奖项。在民族自觉环境下,藏族导演向世界呈现出一种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藏区想象。但这些藏族导演接受专业训练时间较短,对电影媒介的运用并不熟练,拍摄手法也存在技术问题,导致作品成片质量良莠不齐。最终,电影文本在国内的传播差强人意,票房也不理想。
其二是由非藏族导演构成的发展轨迹,其特点是电影语言比较丰富,叙事手法也相对纯熟。但是,部分导演对藏族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刻,观察视角不够准确,因此共情有所误差,导致影片试图传达的内容和情感无法与藏区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谐统一,产生文化“误读”、浅表性阐释等现象。
目前看来,虽然国产藏语电影的两条发展轨迹都存在一些问题,但相较于早期藏族题材电影,2004年后的国产藏语电影在镜头叙事(镜头与色彩运用)、视听语言建构(语言、音乐、舞蹈元素的运用)等方面已有整体性提升,显得“藏味儿”更浓。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导演在影片创作中都逐渐形成了“把藏语作为影片的第一语言使用”的自觉,创作者已经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对影片文本传播的重要性。
二、国产藏语电影的生产地理空间
说起电影的物质空间,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是电影拍摄的地域环境。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电影,都会有一个故事行进的时空环境,这种特定环境是故事发展的必要条件。藏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以及当地的经济文化生态景观,作为影片故事的背景,为电影艺术氛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地理与文化的认同是国产藏语电影创作最基本的前提。
电影艺术本体意义生成的环境基础是电影的拍摄地域,而电影本体意义生成过程的前提是创作者对电影拍摄地影像的选择性表达。可见,对电影文本而言,地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拍摄对象的物理空间,它是指地域文化的范畴;其二是被镜头记录下来的地域空间,也是创作者在其文化身份下,对拍摄对象进行选择的行为意义表征”[4]59-66。
(一)藏区的地域范围及自然地理特征
提起藏区,普通大众所认知的地理空间就是西藏。但实际上,藏区除了我国西藏自治区全境外,还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及海北、海南、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区,是一片美丽而辽阔的土地。
历史上,对藏区的地域划分可以追溯到元朝。公元1252—1253年,元宪宗蒙哥汗派兵统一藏区后,将藏区划分为卫藏阿里、朵甘思(康区)、朵思麻(安多)三个行政区域。从今天的地图板块看,“‘卫藏’是指西藏拉萨、山南和日喀则一带。川西高原的大部、滇西北及藏东一带旧称‘朵甘思’,现称‘康区’,习惯上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地区,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部分操藏语康方言的广大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青及川西北一带的广阔牧区被称作‘朵思麻’,即‘安多’藏区,地理范围包括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地区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区”[5]51-59。所以,藏区是一个在地理学上比西藏更加广泛的地理区域。从自然地理来看,整个藏区大部分属于青藏高原。这里高山河流密布,地势起伏大,平均海拔远高于周围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带来了特殊的气候:藏区多日照,低气压,阳光辐射强烈,早晚温差大,冬季多风,夏季多雹。
(二)藏区的文化及社会特征
卫藏、康区和安多三大藏区孕育了三种藏族文化,无论是语言、服饰还是文化样态都存在区别。卫藏是整个藏区的核心,该地区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历史上一直被称为“法域”,是所有藏族同胞心目中的宗教圣地。所以,国产藏语电影中但凡关于“朝圣”的叙事,镜头描述的内容大多发生在前往拉萨的路上。康区与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份接壤,此地的康巴藏族受巴蜀文化、云南多民族文化以及黄河流域中原文明的影响,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康巴文化。比如,这里有著名的民间热巴舞艺术,诞生了伟大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以及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唐卡画派“嘎玛噶孜”等。康巴藏区盛产侠客、强盗和商贾,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域”,因此国产藏语电影中体现人文风貌、文化交流等主题的场景大多发生于康巴藏区。安多基本位于藏区的边缘地带,由于地域接壤的原因,安多藏族人民与吐蕃、匈奴、蒙古等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混居历史长达上千年。多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安多文化,并产生了独特的安多藏语语系。这里有世界知名的黄教寺庙塔尔寺,还有最权威的佛学院拉卜楞寺。由于草原多,安多是藏区中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历史上被称为“马域”,拥有大众印象里最“典型”的藏区风貌形象。国产藏语电影中,“游牧文化”和“无人区”的主题大多发生于此地。
绝大部分藏区属于平均海拔4 000米左右的高原地区。由于地理与气候原因,藏区的生产基本局限于农业和畜牧业,工业并不多。自古以来,高海拔草原就是藏族同胞生产、生活的重要区域,他们在草原上放牧、捡牛粪、诵经,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逐渐成为藏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少量生活必需品需从其他地区交换外,一个藏族家庭基本能达成自我满足的经济闭环。即便如今的藏区已经出现许多现代化城市建筑群,但受自然环境的限制,藏区的地理空间天然不具备现代城市空间特性。基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藏区大部分地区依旧属于传统的农耕社会范畴。我们可以从国产藏语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中窥见一二,无论是藏族导演影片《静静的玛尼石》中的小喇嘛、《五彩神箭》(TheSacredArrow, 2014)中的射手多吉、《旺扎的雨靴》(Wangdrak’sRainBoots, 2020)中的旺扎,还是非藏族导演影片《天上的菊美》(ANobleSpirit, 2014)中的英措觉姆、《冈仁波齐》(KangRinpoche, 2017)中的尼玛扎堆等,这些人格魅力鲜明的角色都是过去乡土社会中以村落为生活单元的人物形象。藏族同胞的生活方式通过影像被大众熟知,极大地影响受众心理对藏区文化的想象。
无论是对于故事发生地还是故事中的人物,电影工作者更习惯用镜头表达当下城市空间中的人生百态,描述对城市的向往、幻想和期许。但藏区的地域环境更多的是乡村空间,当镜头对准这样的空间时,工业文化身份背景下的思考与农耕文化背景下的现实必然会出现碰撞。“当创作者以藏族文化视角进行影像选择性表达的时候,其不同的血缘文化背景往往会对这种选择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6]70-73。因此,创作者的影像选择行为确定了他们表达意义的主体,也决定了传播者意义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在选择的过程中,创作者的血缘文化与藏区地域文化才能真正产生融合,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创作者自身文化身份建构和认同的过程。
三、创作者文化身份的认同
电影创作者是电影文本生产中意义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媒介地理学视域观察,创作者“身份”是由很多外部因素决定的一种认同方式。在多民族共存的中华文化体系中,我们界定的不是创作者的血缘身份,而是其在作品创作中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决定着创作者的立场和行为选择,同时这种身份是在电影文本创作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建构出来的”[7]126-131。因此,在电影文本的意义建构当中,这种立场和行为的选择恰恰是最核心的问题。任何一种对文化的想象,都是基于某种主体立场之上的想象。只有接受和认同藏族文化,才能选择恰当的立场维度和视角,从而把控影片想象空间的建构方向和形式。
(一)藏族导演的族群文化表达
2004—2019年,5位藏族导演总共拍摄了16部国产藏语电影。在这5位导演中,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松太加来自安多藏区,西德尼玛是青海贵南人,拉华加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多吉彭措为康巴道孚人。从地域来看,5位导演中有4位来自安多藏区,1位来自康巴藏区。再来看他们所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西德尼玛《卓玛的项链》(Zhuoma’sNecklace, 2012)的拍摄地是青海贵南、贵德、共和、塔尔寺等地;拉华加《旺扎的雨靴》的拍摄地同样是在青海藏区;热贡·多吉彭措《贡嘎日噢》(GonggaMountain, 2014)的拍摄地选在四川贡嘎山下。不难看出,藏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拍摄地基本都选在自己的故乡,这与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他们长期生活在故乡独特的地理氛围之中,自我习得经验的累积也来自故土衍生出的原生文化,这些源于故土文化的经验成为藏族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最大的“依靠”。就像万玛才旦接受康巴卫视《藏地影像》栏目组采访时所说:“以前拍摄的电影(藏族题材电影),很多藏族人觉得不贴近藏人的生活,跟藏族人的思维差别太大。因此,我觉得一部藏族电影首先应该贴近藏族人现在的社会生活,这也是我的初心。”
对于生活在青藏线上的青海籍藏族导演来说,恶劣的天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表征。在他们的影像表达中,无论是电影《静静的嘛呢石》还是《太阳总是在左边》(SunBeatenPath, 2011),导演镜头下的藏区总是风云突变、风雪连天。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某一位导演或某一部影片的独立表达,而更像是藏族导演达成的某种共识,或者说是常年的影像表达习惯。在电影《撞死一只羊》(Jinpa, 2019)中,开场就是汽车在风雪中行进的画面,金巴到达康巴酒馆的时候,身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雪。通过影片的花絮可以了解到,导演并没有刻意人造雪景,而是真实记录。该片段拍摄当天,当地恶劣的天气就是此情此景的真实情况。此时,观众印象里藏区的美丽风景、神秘宗教和多彩人文都消逝不见,藏族导演为我们描述了藏族同胞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状态的“真实、克制、孤独、焦虑和对抗”。
(二)非藏族导演的异文化探究
2004年以来,非藏族导演共拍摄了12部国产藏语电影,其中有3部影片以藏语和汉语共同完成。非藏族导演的成长地域都不在藏区,同时他们有相似的学习经历,基本都有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学、影视摄影与制作等方面的学习背景。12位非藏族导演中,谢飞、陆川、戴玮、江涛、高力强、苗月和杨蕊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张扬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傅东育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胡雪桦毕业于夏威夷大学。规范的影视摄影与制作学习背景,加上以往并没有在藏区生活的经历,使得这种藏族文化与异文化的对立天然横亘在非藏族导演面前。在他们早期的部分电影中,地域的选择沿袭了藏族题材电影制作的一般规律,藏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背景空间。如同现在许多的商业电影一样,导演只需要完整叙述故事的情节,而时空环境的设定都是为剧情发展服务的。在这样的电影氛围中,现实的地域空间被最大限度地模糊了。
影片文本强调的是故事的内容和情节,所有内容都应该建立在真实的时空关系之上,影片中的一切行为和行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必须是基于影片拍摄的地理环境而真实存在的。所以,电影文本意义的建构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如果基础都不真实,在上面搭建的一切意义也将随之崩塌。非藏族导演的作品中,有不少确实对藏区地理环境的描述进行了弱化处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电影文本故事的失真。例如,影片《冈拉梅朵》(Ganglamedo, 2008)是首部西藏音乐电影,讲述了汉族女歌手安羽演出失声,通过梦境指引到纳木措寻找自己遗失的“声音”,以此成就“自我救赎”的故事。导演采用很多原创的藏语歌曲和传统的藏族山歌突出音乐电影的听觉符号,对目的地纳木措的地理空间特征描写则相对淡化。纳木措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被誉为圣洁之地,象征着宁静、纯洁。对于女主角心驰神往之地,影片却未给予细腻的镜头描写。导演内心也许并不关注纳木措的地理、人文意义,哪怕是在塔尔寺、冈仁波齐等其他藏族地区,同样可以完成影片的叙事建构。再如,影片《喜马拉雅王子》(PrinceoftheHimalaya, 2006)讲述的是藏区久远时代的事件,故事情节却基本“复制”外国戏剧《哈姆雷特》的内容,在青藏高原的地域空间讲述莎士比亚的西方式悲剧,使故事叙事与空间的关系变得极其模糊,影片中的人物行为描写也与藏区地域空间的自然环境不相符。这样的拍摄手法会让故事走向变得虚假、空洞,对受众的解码过程形成阻碍。
另外,一些非藏族导演的藏语电影中存在着“局外人”视角,在一些“特殊人物”的塑造方面尤其明显。比如影片《可可西里》中的北京警察尕玉,《冈拉梅朵》中的汉族女歌手安羽,《鹰笛天缘》(EagleFlute, 2005)中来自北京的付勇、石磊、梁媛三人,《甘南情歌》(ABlossomofLoveinGannan, 2014)中的大学生万鹏,《佐瑞姑娘》(TibetanGirl, 2012)中的“80后”藏族女孩佐瑞等。这种视角让影片产生了一组对立意象——都市与乡村。在非藏族导演的影片中,无论是进入都市的乡村人还是来到乡村的都市人,都是拥有“局外人”身份的导演对藏区地理文化的一种探究。非藏族导演以“局外人”视角拍摄的一系列藏区想象作品,将自己习得经验中的藏族文化符号与要拍摄的故事进行组合,使用自身血缘身份以及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对影片文本进行逻辑编码。在这类影片中,剧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导演的化身,在影片的拍摄和故事推进中不断完成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塑。所以部分非藏族导演的国产藏语电影,“拍摄的一切内容形象都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对藏区的地理想象而不是地理认知”[8]83-89。总之,“非藏族导演选择‘局外人’的身份来想象‘藏区’,突出了‘局外人’对陌生地域的探究心理,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是由他们相对于‘藏区’而言‘局外人’的身份所决定的”[9]48-59,28。
四、结语
电影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诞生于城市,它的制作基础决定了它自身的工业属性和商品属性。因此,以往的电影产业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景观的塑造者,成为人们对城市幻想的“造梦机”。即便是影像的物质材料来自乡村或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导演作品中所运用的影像技术和拍摄技巧也基于城市景观创造的方法,即将一个个地域范畴的地理空间进行景观化表达,在意识上还是逃脱不了将城市塑造成“外来人”奋斗向往的终极地。
对国产藏语电影而言,不同血缘的导演在进行影片创作时对文本意义的建构是从物质材料的选择开始的。同是在藏区拍摄电影,大部分非藏族导演对藏区的范围认识不够、对藏区的社会文化体系理解不深、对藏族文化的认同程度参差不齐,导致影片的画面空间和叙事效果也因人而异。今天,藏族同胞们也拿起了摄影机,将镜头对准了他们熟悉的那片土地和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虽然影片摄制技术和电影媒介运用水平有待提高,但他们通过真实、淳朴的影像表达,让我们不再只从“局外人”的角度去感受和想象藏区与现代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
非藏族导演与藏族导演不同的身份视角对影片的想象空间和消费空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与其说二者的影片拍摄手法和阐释内容有很大不同,不如说这是来自城市与乡村、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局外人”和“局内人”视角对这片地域的不同建构。无论怎样,国产藏语电影的生产和传播建构了与以往藏族题材电影不同的美学视野,极大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创作思路。在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下,国产藏语电影为城市的喧嚣、现实社会的冰冷和无情所造成的情感压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宣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