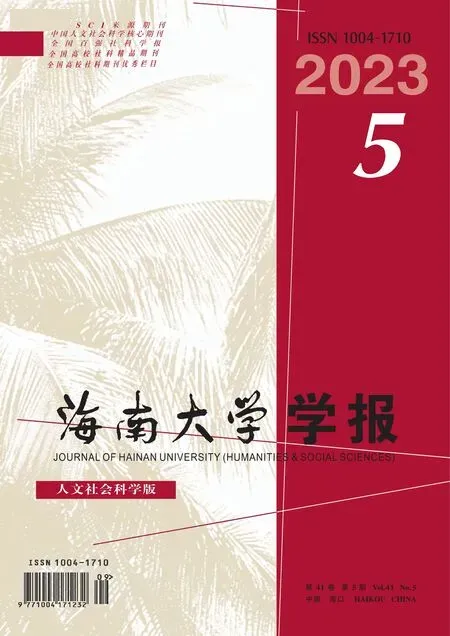海德格尔思想的伦理学蕴含
——以《存在与时间》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为例
周建昊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谈论海德格尔的伦理思想或者其学说的伦理意义,看起来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正像丹尼斯·施密特所说:“把海德格尔和伦理生活放在一起谈论,这是一种挑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1]的确,海德格尔本人很少对伦理学进行具体的讨论,也没有留下相关的系统性作品。在目前学界把海德格尔和伦理学联系起来的研究中,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海德格尔把与他人的共在(Mitsein)视为非本真的存在样式,以及此在(Dasein)从自身的本真存在那里异化并落入“沉沦”状态的原因,“与他人共在”必然导致此在的自我遗忘以及存在意义的无法显现,这导致了他对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学问的伦理学的否定(至少是搁置)。例如格雷戈里·弗雷德指出,对于“做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是强调人权传统(普世价值)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另一种则是强调宗教、国家、种族等身份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而海德格尔强调人类存在的有限性、时间性和历史性,所以他激进地支持后一种观点,因为伦理总是要在特定共同体的传统中被思考,所以不存在普遍的伦理规范[2]。还有的研究者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批评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伦理学内容方面有所缺失,比如宾斯万格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不可能和人类学相分离,而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海德格尔只注意到了死亡和对在世本身之“畏”(Angst),忽略了爱和友情等温暖的情感,而实际上这些积极的伦理情感才应该是人之此在的中心存在原则[3]。
以上诸多的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不那么准确,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其立场基本都是源自对《存在与时间》(尤其是其中的共在概念)的负面判断,而没有反思过这样的判断是否全面,也未及注意到海德格尔后期作品中关于伦理学的讨论及其特殊内涵。当然另一方面,一些立场比较温和的研究者看到了海德格尔思想中也蕴含着某种伦理学资源,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对于伦理学的思考只在其后期作品中才出现,因此,这一派学者往往割裂了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之间的联系。例如刘易斯说,对共在的坚持发展出了伦理与政治的关系,而这些“与早期作品中截然不同”,伦理学在海德格尔的早期作品中是未被思考(unthought)、未经奠基的(unfounded)[4]。而阿特门科则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代表作《哲学论稿》提供了那与他早期思想格格不入的东西——即一门伦理学的可能[5]。
这两方面的看法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可商榷之处。而若想验证这些看法的合理程度,还需要回到海德格尔的作品中,尤其是《存在与时间》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以下简称《书信》)这样的重要文本。
一、本真共在及其伦理学意蕴
《存在与时间》区分了此在本真和非本真的生存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面对死亡这种最本己的、无法逾越的可能性,此在能否对它做出正确的领悟和筹划:本真的此在从中领悟到世界的空无,却更能够承担起责任,它展开死亡、揭示这种可能性,并坚定地在自身中持守着它;相反,非本真的此在却封闭死亡的可能性,把自身投向外部世界,停留在世界中各种与人和物的关联里,以此逃避死亡,这就是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沦”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此在失去了自身,把自己委托给了“常人”(das Man∕They),从而解除自己的责任。在“常人”这一庸庸碌碌的群体中,所有个体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人云亦云、缺乏决断,受着公众意见的统治。由于《存在与时间》中谈到本真存在时基本都是指本真的自己存在而极少描述本真共存的可能,并且在书中,海德格尔一方面说此在“首先与通常”是处在“沉沦”状态中、作为“常人”出现的[6]129,而另一方面又说此在必然是以共在的方式生存,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解读,即共在必然是非本真的,并且它是导致此在“沉沦”、成为“常人”的原因。然而,这一理解其实并不符合海德格尔的本意。要对这一观点进行反驳,还要从海德格尔存在论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谈起。
《存在与时间》中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的起点是所谓“存在论差异”,即存在本身(Sein)和存在者(Seiende)的差异。存在者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实体,其中与存在有特殊关系的只有人,海德格尔称它为此在。它特殊是因为只有它具有含混的存在领会(Seinverständnis),又能继续发问,追求对存在意义的澄清。另外,只有人能走出存在者整体,从外面看待这个整体和自己,这是一种对自身性的反思。从共在走向伦理学之路,正是从这种对存在的认识和对世界之真理的探求开始。
在探究世界的过程中,“我”遇到各种各样的实体,有合用上手的(比如被正常使用的工具),也有现成在手的(脱离了实践而被理论地静观的物品),但还有一些存在模式与它们都不同而是和“我们”一样的存在者,这就是他人,或者说其他的此在。海德格尔指出,与这些其他此在的共在,才是此在的基本生存结构。“此在最源始的生存结构不仅是在世之在,也是共同存在(Mitsein)和共同此在(Mitdasein)。”[6]114由此,对存在的理解也必然蕴含着对他人之存在的理解。既然追求去理解,那它就会对他人有所关怀,而非仅仅与他人保持一种在空间上邻近的关系。海德格尔称这种关怀为对他人的“操持”(Fürsorge),这是一个具有很强伦理意味的说法,与以物为对象的“操劳”(Besorge)相区分。“明确地操持着开展他人的活动,也只有从那基本的、与他人共在的视野中生长出来。”[6]124
在海德格尔那里,共在和个体一样,都面临着“被抛”这一事实,有着“畏”这一基本情态。所谓“被抛”,是指此在发现自己被抛入这世界的某处,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它在此,只是因为不得不在此,它“畏”的就是这一事实。既然个体的此在可以自己选择是“沉沦”还是“抱诚守真”,那么共在就不应当只有非本真的样式,它同样可以是本真的。换言之,共在和个体的此在一样,都拥有非本真和本真的可能,与共在必然相关的是“被抛性”(Geworfenheit)而非“沉沦状态”(Verfallenheit),“常人”并不等于共在的全部,它只代表了其中一部分的情况,即非本真形式的共在。根本而言,把共在等同于非本真存在的理解者,还拘泥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存在等同于现成性(Vorhandenheit)和现实性(Wirklichkeit),从而把共在视为事实层面上个体的多数性(Vielheit)——这种多数性的确可以被“在向死存在中此在只能面对自己”的情况所消除,但导致这种理解的思维方式却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要颠覆的:“即使有十个或更多的人现成摆在那里,此在也能独在;共在与彼此共在(Miteinandersein)之成为实情,并不是靠许多主体一同出现……许多人的存在,并不等于说这许多人只是现成地在那里。”[6]121此外,海德格尔虽然强调死亡之本己性及其地位,但这并不是说此在只有作为孤独的个体面对死亡,摆脱所谓“非本真的匿名性”,才能赢回本真的自身——此在是因为有死才具备其不可替代性不假,但死亡却恰恰为此在打开世界:正是作为“向死存在”,每一个此在才用各自的生存开发出各自的世界。此在不是兀然特立的、孤零零的,而是对外部开放的,具有着敞开性(Die Offenheit)。
在对世界的探究当中,此在发现世界的真理不是单凭自己就能获得的,而是要与其他人联合,一起去揭示它。他们的信念和感知与“我们”的是同一种类型,而且对于真理的确定和“我”的感知同样重要,此外他人还拥有一些“我”无法获得的经验和事实,熟悉这个共同世界(Mitwelt)中一些“我”不了解的地方。由此可以说,“我”和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与他人共在”总是“在真理中与他人共在”(being-in-thetruth-with-others),奥拉夫森把这种情况概括为“作为伙伴关系的真理(truth as partnership)”[7]。更进一步讲,他人不只是真理的共同发现者。人不仅具有认知能力,而且还有意志和行为能力,需要用行动来达成意志的目的。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主要是通过做出选择来本真地负起责任,承担选择的责任才能在行为中实现本真性。“作为如此存在的存在者,它(此在)已被托付(überantwortet)给它自己的存在。”[6]42此在没有实现“当前它所不是的”可能性,这是它对自己负有的一种责任甚至是罪责(die Schuld),需要接受生存论层面上良知的召唤而去开显那些可能。而共在的上述性质和作用就决定了此在不仅需要对自己负责:“我”的选择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而“我”的利益并不高于他人的利益,因此无法只根据自己的喜好做选择,而是受到共在施加的约束——必须在选择中负起对他人的责任。因此责任就隐含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隐含在关系双方对共同世界之真理的共同揭示中。由于“我们”与他人相互依存,二者要相互负责,而人们的利益会受到其所相信东西之真假的影响,便又产生了两个关乎伦理的元素,就是诚实和信任。责任、义务、信任等等东西加起来,就产生和影响了各种具体的伦理观念和行为。不同于以往伦理学大多从前定的准则去演绎行为、评价行为是否与其符合的做法,这里与传统伦理学有关的内容都是从海德格尔对于共在的描绘推导出来的——当“我们”说自己的存在是“与他人共在”的时候,也即是在说,“我们”必然与他人处在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与负责中。这种原初的负责有着一种本源伦理的意蕴。
二、本真共在的内涵及实现:真理与自由
而如导论中简述的那样——另外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哲学人类学而言,海德格尔的此在被面对死亡的“畏”和焦虑所占满,却没有把爱和友情加入到其基本情绪中,这也成为否认《存在与时间》有伦理学意义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一观点也相当有影响力,例如靳希平在《〈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兼论〈黑皮本〉的“直白称谓”》中,引用了舍勒的观点“是爱而不是畏为我们敞开的世界”并进一步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缺乏友爱、团结、同情等正面的伦理要素,可能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缺爱”的哲学,让他用著作在一代德国人当中压制了爱的原则和观念,为纳粹的独裁和暴力屠杀助纣为虐[8]。但这一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接下来,笔者将分两个步骤,以本文开头部分提及的学者宾斯万格为对象,对这种看法进行部分程度的反驳。
其一,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不只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或“人生现象学”。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在《存在与时间》中按计划具体进行探寻一般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论工作,但凭此并不能断定他停留在了“人生现象学”阶段,未去思考关于一般存在的存在论。固然,人有一些特殊之处,是唯一了解存在的存在者,只有这种实体会“操心”、会建立并进入与其他实体的关系,但也仅此而已。此在也不过是诸实体中的一种,也处在和其他实体的双向关系中,每天和世界上的其他存在者“照面”着,此在塑造着它们,而它们也反过来触动和影响着作为行为者的此在。海德格尔关注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但这主要是出于他对人与存在之内在关联的关切:要追问“存在者之存在”,需要先思考清楚“人是什么”,甚至可以说,存在论要首先回溯到一种哲学人类学之上,将其作为问题的开端。也正是因此,海德格尔才把将此在诸生存论环节的意义阐释为时间性的过程称之为对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人类学的问题,和存在与时间的最内在本质是关联在一起的。而那些从人类学立场出发的批评者却忽略了这些事实,无视海德格尔思想系统的内在关联,而仅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进行浅表的解读。这些并不适宜的批评,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和问题意识尚未达到海德格尔的层次,以宾斯万格为例,他的“爱之现象学”倒确乎是一种人类学,只关心“人类要成为怎样存在”(what is it for the human being to be)的问题,从而把基础存在论“人类学化”了。
其二,在文本几乎没有提及爱的情况下①《存在与时间》只在第29 和40 节两个关于奥古斯丁的脚注中才提到了爱(Liebe)。参见HEIDEGGER M. Sein und Zei[tM]. Tubingen:Max Niemyer, 1976: 139, 190.,能否因此断言《存在与时间》是“缺爱”或缺乏伦理学意义的著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分析本真共在的内涵。之前谈到,“我”和他人一起探究世界的真理;然而,这种探究并不仅仅揭示世界和那些作为物品的实体——实际上,“我”和他人彼此也在相互揭示。在共同构筑完整世界的过程中,二者互为补充、互相确认,借此,“我”也更加了解自己并告诉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者。共在让此在理解他人和“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世界,也更了解自己。通过“在真理中与他人共在”,“我”把他者揭示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此在,尊重了他者实存的独特性,从而能够本真地“操持”他人。本真共在的内涵就在于此,它不仅相关于真理,而且也相关于自由:为自己寻回自身(Selbst),也要帮他人寻回自身。因为“一成为常人,任何此在就涣散了,就还得发现自身”,而“如果说此在要对其自身开展出它的本真存在,那这种揭示‘世界’与开展此在的活动也就是去除种种遮盖与蒙蔽”[6]129。可以说在海德格尔这里,本真存在与真理和自由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实现都需要去蔽,从而达到一种“让其存在(Sein-lassen)”的状态。就像《论真理的本质》中所言,真理的本质是自由②在被认为标志着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1930年《论真理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反对流俗的真理概念即把真理当作“知与物的符合”;他认为真理应该翻译成“无蔽”(ἀλήθεια)更合适,因为真理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的本质则是“进入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的展开”,作为“让存在者存在”的自由,就是真理本质的实现和实行,它偏向于动词性,与深入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的那个过程相对应。参见HEIDEGGER M. Wegmarken[M]. F. a. Main: Klostermann, 2004: 220.,而自由是“绽出的、解蔽着的(entbergende)让存在者存在”[9]192。
运用现象学方法对物去蔽,让它们“回到事物自身”,便开显了真理;而对人进行类似的去蔽时,结果便是让人获得了自由。这才是真正的爱:爱,就是让他人作为他本身存在——为什么存在论层面上的基本情绪不是爱而只能是“畏”?因为只有当此在敢于直面在世之“畏”,努力摆脱“沉沦”的状态、离开“常人”群体,让自己和他人都能本真地存在,宾斯万格所设想的那种爱才能被展开。简言之,爱需要此在赋予它存在论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则是“操心”和“畏”的情绪。正如海德格尔的批评所指出的,宾斯万格没有区分人类此在的存在特征和生存问题,因而在层次上混淆了生存论(Existentialismus)和存在论(Ontologie):在海德格尔看来,宾斯万格的“精神病理学的此在分析”是从对此在存在论分析的基本构成中拣选出来作为其学说的基础,但其实它只是一种“区域存在论”(regional ontology),并不是基础存在论的唯一结构,而基础存在论才是每一种表现为“区域存在论”的生存论分析所预设的前提[10]。“为同一事业而勠力同心,这是由各自掌握了自己之此在而规定的。这种本真的团结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把他人的自由为他本身而解放出来。”[6]122这句话即指出了本真共在与自由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此在必须要持身于独立自主的(Selbständig)即“掌握了自己此在”的状态中才能决断去行动,而各自拥有自由,是爱彼此和建立伦理关系的前提条件。
由此不难明白,当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单一性(singularity)时,他只是希望“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不是要否定他人存在的地位和作用。类似地,在后期作品《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海德格尔仍然强调单个此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必要:“存有(das Seyn)只有作为单一和深不可测的存在……才能得到本现(west)。”[11]但此时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仍然是以对彼此之差异性的尊重为前提,而非在提倡一种极端的个体主义哲学。“本真的共处,唯源于在决心中本真本己的存在,而非来自模棱两可的约许和在常人及其事业中喋喋不休的称兄道弟。”[6]298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存在状态首先就是共在而非独在,但如果未经去蔽、未走出“沉沦”状态,那由这样一些被敉平的“常人”聚集而成的就仅仅是人群(Crowd);只有拥有自由、也尊重彼此差异的诸此在,才能团结为一个本真的“我们”(We)。《存在与时间》虽不谈爱,却是在为爱寻找根据和前提,它虽然表面上未直接涉及伦理学的相关内容,却是在为伦理学的奠基做准备——而这种“元伦理学的”(proto-ethical)特征,在他的后期思想中得到了更为鲜明的阐述。
三、居于存在之神近旁的人:后期的伦理学构想
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后期重视的意象——大地,意指着一种主体间的关系,例如泰普尔在论及现象学空间的构造时,将大地作为这种构造的“交互主体性规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主体身体都是以大地为参照的[12]。这一想法某种程度上确实与海德格尔的叙述相符,而且也有具体的文本支持,例如在《林中路》中,海德格尔曾经把大地指作一个民族隐含的共同精神传统[13];《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则说“‘家园’的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14]但总体来看,它们作为晦涩的隐喻,终究只是隐含着伦理学的可能,而无法被足够明确地评估。若论海德格尔明确谈及其对于伦理学思考的重要后期文本,仍应当属《书信》。但在正式进入对《书信》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简述一下海德格尔在《物》和《筑·居·思》等后期演讲中提出的关于“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das Geviert)模型的设想:
四方联动构成一个整体,人在诸神和天空的光线所照亮之真理的庇护下,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①这四方之间的关联,最突出地凝聚和浓缩在“物”(Ding)上。海德格尔用日常通俗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一座桥,它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又“为天气及其无常本质做好了准备”,堵住暴风雨带来的洪流;为终有一死者提供了把他们带往诸神面前的道路,并“作为飞架起来的通道,在诸神面前聚集”。再如一个壶,盛着泉水或酒,其中有岩石、大地蛰伏于其中,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因此,在饮品中有着“天空与大地的联姻”;而它既是终有一死之人的饮料,又可以作为敬神的祭品。这二者就代表着物,它们如此把“天·地·人·神”聚集于自身,也是对“四重整体”的保存和庇护。详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正是从这个角度,米歇尔·刘易斯认为“四重整体”所体现的是一种“物的伦理学”。参见LEWIS M. Heidegger and the place of ethics[M]. London∕New York:Continuum, 2005:4.。在这四方之中,天空(der Himmel)和大地(der Erde)较为抽象(或许二者分别象征着自然与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有死者(die Sterblichen)的人,和代表着一般存在的神。这应当是出于海德格尔对伦理学之内涵看法的变化:如果说从前期文本中,读者还有做出一种贴近传统“伦理道德”之解读的可能,那么此时他明显侧重于探讨一种伦理性存在,并意图借助存在,奠定一种相对于传统伦理学来说更为基础的本源性伦理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人(此在)与神(一般存在)的关系,更普遍而言,也可以说是这个“四重整体”内部各方的交互关系。而将这种关系与伦理学联系起来的根据,则就在《书信》中。
在《书信》中海德格尔这样说:“如果按照ἧθος (ethos)一词的基本含义来看,伦理学这个名称说的是它思考人的居留(Aufenthalt),那么那种把存在之真理思为一个绽出地实存(eksistierenden)之人的原初要素的思想,自身就已经是源始的伦理学了。”[9]356这句话体现了他向伦理学和存在论进一步靠拢的倾向。那么,这个ἧθος 从何而来呢?来自于他对赫拉克利特名言“ἧθος ἀνθρώπῳ δαίμων”的重构——这句话的普遍译法是“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海德格尔则说,这句话意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他居留在神的近处”。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把ἧθος 对应于character,而是赋予它居住(residence)、栖居(dwelling)和建筑(abode)的含义,而居住绝不仅仅意味着“占据着一块地的主权”,而是要去筑造、去躬身参与其中,要去做一些类似于种田、放牧的事情,要爱护和照顾动植物等需要生长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更多是一个动词性的过程,是一种实践。这种“操劳”和前文谈到的“操持”相呼应,共同体现了一种伦理性的原初的负责。而且它也体现了海德格尔后期伦理学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反对唯理论的倾向,而重视实践和思考。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多次表达了对学科化、概念化的伦理学乃至于哲学的不满,认为它们妨碍了真正思想的诞生:“‘伦理学’……学科产生的时代,是一个使思想变成‘哲学’、又使哲学变成έπιστἡμη(科学),并且使科学本身成为学院和学院活动的时代……科学产生了,思想却消失了”[9]354;“在当今的世界困境中必需的是,少一些哲学,而多一些思想”[9]364。
海德格尔用ethos去代替传统伦理学(ethics)的想法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来自古希腊文化的启发。一方面,这个词及其变体确实在古希腊语的作品中以“人或动物感到舒适的、在其上生长的居所”之意思出现,例如在《斐德罗篇》的结尾[15],苏格拉底说到把自己的文章作为消遣时,提出要把灵魂作为“文字的花园”(γράμμασι κήπους),播种文章于灵魂之上,看着自己耕种的事物发芽长大,而他形容播种于其上的单词就是ἤθεσι。这个过程和上面所说海德格尔的筑造非常类似,只不过此时培育照料的不再是农作物,而是自己的灵魂。可以说,这的确可以称得上古老的伦理学思想。另一方面,就像在整个研究生涯中所经历的那样,海德格尔的思考再次深受亚里士多德(此处主要是实践哲学方面)的影响,但在这里他甚至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而如此说道:“在此时代之前的思想家……也不知‘伦理学’……但他们的思想既不是非逻辑的,亦不是非道德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在其言说中比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学’的讲座更为原初地保存着ἧθος。”[9]354在此处,他显然是把亚里士多德的讲座当成了前述知识化、学科化伦理学的一个例子。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海德格尔的伦理学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是无视道德情感的冷血学问。海德格尔并不回避道德情感,他反对的是把所有情感都统一贴上伦理学的标签,把有血有肉的感情都异化成可以由逻辑支配的、思辨的东西,然后便就概念讨论概念的做法。在他看来,与“纯粹情绪”有关的事情属于珍贵的存在论经验,但它们位于一种“前理论”或者“非理论”的维度,可以说永远无法成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因而在建构伦理的时候,海德格尔把实践放在优先于理论理性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忠实地履行实践理性的生活才是本真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一定是被“非理论地”理解的,甚至可以说,理论也要经过对这种生活的体验才能被理解。在这里不难看出其后期思想和《存在与时间》的一脉相承之处:
《存在与时间》说此在的存在一定是在世之在。所谓在世之在,就是说此在是居留在世界中并与之相亲熟的实体,而这个“在之中”(das In-Sein)不仅指定居在里面,也包含要在意和照料(take care of)其他实体的意思。因而,此在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但它绝不是冷漠的,任何有关于它的理论态度也一定是有所关切的(concerned),而非无所谓的(indifferent)。同时在《存在与时间》所代表的时期,相较于一物本身的物性(Dinglichkeit),海德格尔更重视它对于人的“何所用”(wofür),换句话说,在行为中,一物的“为了……的缘故”(for-the-sake-of)和“为……而存在”(being-in-order-to)先于它客观理论方面的“是什么”(what)。当然,也只有会“操心”的“我们”才会受到这个“for what”问题的影响并去思考它,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行为的执行中,被实践地理解。
总之,海德格尔的哲学绝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极关注实践和切身体验。他的基础存在论是关于做事(πρἃξις)和制作(ποίησις)的存在论,而其伦理学正如施密特所言,也是一种“伦理的制作(ethopoetic)”[1],更偏向于动词性而非名词性。他想要用含有居留意味的ethos取代作为学科的ethics,取消可公共度量的道德尺度,返回每个人当下生活的真实情感和关于灵魂的实践。他希望向读者揭示人的ethos①当然,除了海德格尔赋予的“居留”之意外,ethos现在一般被译为“风气”“道德观”,与伦理学(ethics)有含义上的联系,这也使得海德格尔的发挥至少在字面上是有其依据的。,这是一种比概念化更严格彻底的行为方式,它先于理论上的学科划分,却比单纯理论知识蕴含着更多的生存论内容。
四、结 语
海德格尔的伦理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有差异 的。比如,前期它更偏重理论,以概念作为载体(虽然就此在共同揭示世界和彼此揭示的过程而言,这里也已经有了行为的参与),而后期则侧重在实践中制作和实现伦理。再如他所构想的伦理关系,其内涵前期还比较接近传统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或“存在者主体”之间)的关系,后期则转向此在与一般存在的关系。虽然如此,这种状况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其中有一种根本性的断裂。其实,这些差异是他总体思路之转变的体现——前期从此在入手谈存在,后期则从存在反观此在。而无论遵循哪条思路,海德格尔的元伦理学思想都是对遵循刻板道德原则之伦理学的反对,这可以被视作隐含在前后期之间的联系。
海德格尔所反对的并非传统伦理学本身,而是对其前提未经反思就加以探讨的做法。而那个在他看来未加牢固的前提,正是存在及其与人的关系,是它使得人们通常所说的伦理关系在场并得到描述。如果不对它加以澄清,传统的伦理学就只是一些未经奠基的断言。存在是伦理性的存在,而一种原初的伦理关系,首先体现在此在居留于存在之旁,思考和寻求存在。在此本源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和他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才有意义。就像《逻辑的形而上学始基》中所说:“只有在后存在论——生存论地(metontologisch-existenziellen)提问的领域……才能提出伦理学的问题。”[16]“后存在论”(Metontologie)这一用词表明,海德格尔绝不是不重视伦理学,而是觉得只有在完成了基础存在论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处理伦理学。因而,对存在及其真理发生之思本身就具备原初的伦理意涵。
探究海德格尔思想的伦理学蕴含是不易的,因为它总是与玄妙深奥的存在论联系在一起。虽然如此,海德格尔还是认为伦理学与存在论是具有“同等原初性”(equi-primordiality)的(虽然也许就思考的顺序而言,需要优先处理存在论),而非只是作为后者的附庸。就像《路标》中对思想而非哲学之强调体现的那样,他或许未曾留下系统性、理论性的伦理学著作,但却有关于伦理的深刻思想,而其价值在今天应该受到研究者更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