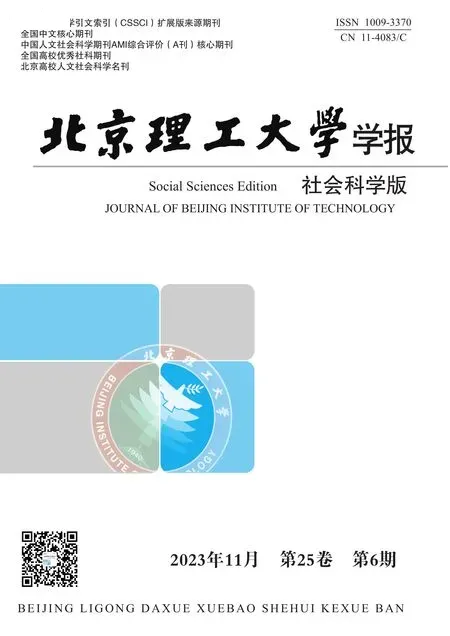格兰特在琉球“分岛”方案中之作用考论
陈大炜,胡小进
(1.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2.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历史所,北京 100088)
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日琉球纷争中,曾有人提出,分割琉球岛,后世称之为“分岛”方案,对于究竟谁是“分岛”方案的首倡者,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访日期间,同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国驻日公使平安①Jhon Bingham,1871—1885 年美国驻日公使。在日期间参与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清政府和日本之间有关于琉球的纷争。举行密谈,向日本内阁提出所谓“分岛”建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日本提出“分岛”这个办法。例如,日本学者永石啓髙在《19 世纪后期东亚秩序的改变和日本领土的划定》一文中说道:“琉球归属问题在日清之间不断交涉,后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下继续开展,最后日本提出《分岛改约》一方法让双方达成一定共识……。”[1]学界对于是何人提出“分岛”方案一事讨论众多,在这一事件中应特别关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其与“分岛”方案的关系,以及其在琉球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持立场,在此或可把整个事件的脉络理清,从而推理出“分岛”方案的提出方究竟是谁。
一、琉球事件缘起
早在19 世纪70 年代,日本就开始筹划侵略琉球一事。日本侵略琉球并非一蹴而就,从1871 年日本第一次和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接触,一直到1879 年日本全面侵占琉球,日本所采取的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1871 年,琉球岛民因天气原因而出现船只遇险,69 人被洋流冲到福建省管辖的台湾岛凤山地方海面,后来死亡3 人,其他人登岛。66 名琉球人在台湾岛南部登岛后,被“生番”②当时的清政府所管理的福建省台湾地区也仅限于台湾西部地区。大部分东部地区并不在福建省的管辖之下,因此,清政府称此地为“生番”。“生番”多是台湾岛的土著少数民族,他们骁勇善战,同样也没有文明开化。虽此地不在清政府管辖下,但无疑是中国领土。“牡丹社”③牡丹社,中国台湾岛土著番社名,位于今中国台湾屏东县,1871 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日本强行登陆台湾岛屠杀牡丹社土著人,该社被焚毁。的人抓到,大部分人被社人杀害。逃出来的琉球人跑到当地清政府官府所管辖的地区。清政府官员得知此事后,对琉球生还者给予安抚和经济补助,与此同时,他们还上报北京并发文给督抚,向琉球传达此事。
此次“生番”对琉球人实施杀戮,成为日本出兵侵略中国台湾地区和琉球群岛的一个借口。日本得知此事后,立刻向清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对此事严查,同时要求给予相关赔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保护”琉球的名义,宣布琉球成为日本的一“藩”。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已经“废藩置县”,因此琉球在被宣布成为日本一“藩”时,就已明了琉球将被日本占领的命运。
为了迷惑清政府,日本内阁和清政府在同一年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建立新型“清日关系”。当时,日本特使柳原前光提出所谓“日清提携”论调,其强调清日这两个东亚独立国展开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以此抵抗列强。直隶总督李鸿章甚至在奏折中也都不断提及和赞赏日本提出的“日清提携”论调,希望朝廷将日本视为同盟国加以利用,以此抵抗欧洲列强侵袭。
然而,日本侵占琉球、染指中国内政的真实目的很快就暴露无遗。1875 年,日本宣布,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并且阻止琉球向中国纳贡。日本此项政策是向中国挑明日本对琉球的侵占,并且剥夺了琉球的主权。继之,日本要求琉球撤销在福州设立的琉球馆;全部商业贸易归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全部和中国的往来和交涉都归日本外务省管辖。随后,日本便在琉球本土驻军,强迫琉球王室迁居东京。而琉球王室仍旧寄希望于清政府帮助琉球“复国”。因此,琉球特派向德宏等人秘密乘船前往福州,求见当时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但是,清政府以所谓的礼节为由,不允许琉球的使节前往北京,所以,向德宏也只能在遥远之地苦苦等待清政府确定处理办法。1877 年,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就任中国驻日本公使,立刻对琉球一案和日本外务省展开交涉。同时,他还同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力陈保有琉球的必要性。
日本在“日清提携”的思想宣传上十分成功,让清政府产生了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共同对抗欧美列强的幻想。因此,以李鸿章为首,清政府在初次面对琉球问题时,其立场并不坚定,迟迟不肯采取严厉的外交态度展开交涉。加之清政府当时面对沙俄侵占西北地区等问题,十分牵扯内部的精力,也牵扯到军事力量的使用。所以,清政府没有对琉球问题给予积极回应,而且清政府内部占据主流地位的人士认为,花费如此之大的力气去保护一个“弹丸之地”,实属得不偿失。
在此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和恭亲王奕䜣希望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了结琉球问题。他们实际上异想天开地想借清政府并不非常了解的“国际公法”等手段,和日本展开交涉。与此同时,何如璋等人虽然提出针对琉球一案的“上、中、下”三策①何如璋的上中下三策分别是:一方面,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另一方面,向琉球派遣兵船,促其进攻(上策)。保证援助琉球人,助其反抗日本,针对日本军队进攻琉球,中国也以军力对抗(中策)。召开国际会议,征求各国公使意见(下策)。,但此举不过是基于双方不会开战前提下的外交威慑。进言之,李鸿章与何如璋还是在“日清提携”的幻想之下同日本展开谈判,导致清政府的立场时而坚定,时而唯唯诺诺,因此其外交交涉的收效也就微乎其微。虽然何如璋向日本外务卿②外务卿,今日本外务大臣一职,也称为外相、外务相。寺岛宗则就日本阻止琉球进贡一事提出抗议,其说道“今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2]但是,日本非但没有把何如璋的言论放在眼中,还以何如璋此番言论侮辱日本国格为由公然拒绝同清政府举行关于琉球的外交谈判。借此时机,日本加快对琉球吞并步骤。1879 年,日本宣布废藩置县,琉球正式被改名为冲绳县,琉球王尚泰移居东京。至此,琉球亡国。
二、清政府邀格兰特调停中日琉球纷争
清政府面临不利境地,虽然其希望同日本就此问题展开交涉,但是日本已经关闭了谈判大门。正当清政府苦于无计可施之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是时携家眷周游世界,计划先在中国旅游,然后再去日本,格兰特为此愿意居中调停,这为中日重启谈判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为此,李鸿章迅速瞄准了这个机会,邀请格兰特居间调停中日有关琉球的纷争。当时,清政府有官员在致李鸿章的信件中曾说道:“窃揣格前总统语意,其于球事甚相关切,尚无推诿,日本能都听从故未可知……。”[3]1271先前和格兰特接触的清廷官员,已经旁敲侧击地与格兰特商讨过有关琉球的事宜,他们觉得,格兰特实际上并不拒绝调停中国与日本的纷争,由此,李鸿章在后续的接洽中,顺理成章地请求格兰特为中日纷争进行调解。但是,清政府在后续谈判中“一厢情愿”地视格兰特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并且相信日本必服从其权威,这或许也成为部分学者一直认定格兰特是最终方案敲定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政府在和格兰特接洽时,希望通过种种方式说服格兰特为清政府做主,劝说日本退出琉球,而格兰特一方已对此事有了自己的理解与立场。1879 年4 月,在格兰特抵达中国后,李鸿章便迅速与格兰特会谈,说明在琉球问题上清政府方面的立场:“琉王向来受封中国,今日本无故废灭,违背公法,实为各国所无之事。……贵国总统声名洋溢,中西各邦人人敬仰,此次游历中、东,适遇此事,若能从旁妥协调处,免致开衅,不但中国佩感,天下万国闻之,比皆称高义。”[4]李鸿章在和格兰特的谈话中,反复谈及琉球主权问题,并且希望格兰特能够站在清政府一方,帮助琉球恢复主权。李鸿章说:“余正欲与贵大总统谈及此事。”格兰特问:“中国果无争朝贡有无之意乎?”答道:“朝贡有无非问题之所在……。”格兰特问:“琉球王为其三十六姓之人哉?”李鸿章答道:“琉球王尊姓,虽未入三十六姓之中国,然尚有几多可报告之理……”,格兰特说道:“贵言极是。余之最恐之处,正是各国不和而开战,若能以善言得以调停解决,众人之齐益也。”后格兰特又说道“琉球原来为一国,而日欲将起并合而得以自扩。中国所力争之处,乃土地而非朝贡,甚具道理,将来需另设特别条款”。李鸿章答道:“贵大总统所见,甚为正大,在此相托”[5]。从此角度看,李鸿章和格兰特第一次谈话时,格兰特一方根据先前的资料就已经把整个问题的要害之处一览无余。格氏认为,相比朝贡,清政府更担心的是领土问题,因此在其后续访问日本进行调解时,也都是以领土与国家利益、地区利益为核心同日本官员展开讨论。
格兰特愿意对此进行居间调停,也是站在了捍卫美国在东亚地区利益的角度所作出的决定。首先,美国和中国有和约保障,能够确保格兰特此次调停活动合理合法:“根据1858 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一款: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格云:(日本)实系轻蔑不公,美国调处亦与约意相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师出有名,可以作为该事件的调解人。另外,当时的美国迫切需要大量中国劳工到美国,参与西部地区建设,并且给予了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前往美国的一系列优待政策[6],但是清政府对于中国人进出境管理十分严格。为了实现美国的商业与政治目标,中美之间有关条约的一系列相关条款还在和恭亲王奕䜣、李鸿章等大臣不断的谈判中,这也就成为格兰特要接受李鸿章之邀请、调停中日琉球纷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格兰特为保证不干涉其他列强、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一直强调自身中立,其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在这几方的势力范围内的利益不受到伤害。格兰特表示:“可惜立约时未将朝鲜、琉球等属国提明,当告以邦者,属国也。土者,内地也。即是此意。”[3]1272格兰特虽然同意帮助清政府调停,但其作为个人并不代表政府,并且强调其将始终在此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不会直接干涉到整个事件当中。虽然格兰特答应调停,但是格兰特只是为中日双方提供一个重新交流的契机,而不是直接下令让双方完成“外交任务”。有关于此立场,在格兰特的随行人员杨约翰①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美国外交家、作家、美国国家图书馆第七任馆长。其跟随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进行了环球旅行,并写下了游记《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John Russell Young)的游记中有相对全面的记载。
在该游记中,格兰特同恭亲王奕䜣进行会谈时首先就强调:“其并不是一个政府官员,他只能代表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政府或者军事代表干涉到其中……。格兰特强调战争是最糟糕的选择,尤其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战争绝对是灾难。”[7]411格兰特和奕䜣的谈话之中反复强调,自身立场将会一直保持中立,并且其能够做到的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让双方回到谈判桌上。他还说明,自己也会在充分了解到日本的立场后,再对中日之间纷争展开进一步调解。在该游记中,格兰特一直恪守中立,并且拒绝直接干涉任何纷争,这一做法符合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利益。但是,清政府却一直希望格兰特成为此纷争的直接调停人。对此,格兰特的回应则是,“中国过分高估了其自身的实力,这并不是他所想看到的局面。”[7]416根据以上内容,虽然奕䜣和李鸿章反复劝说格兰特对此事进行仲裁,但是格兰特拒绝成为双方问题的直接干预者,也不愿意成为真正的“法官”来裁决此事。因此,格兰特没有可能直接要求双方“分岛”或对此事提出直接的处理办法。
但是,格兰特也的确提出过希望双方在争议问题上有所让步,或者相互“牺牲”一部分权益,从而换取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多数学者认为,格兰特是“分岛”方案的始作俑者,但是格兰特在此情况之下提出的相互让步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其核心观点和最早格兰特所说的“和平解决纷争”是同一个意思,并不能被直接解读为让双方实现“分岛”。
三、格兰特在日交涉与“格兰特精神”的确立
格兰特在日本期间分别会见了伊藤博文、西乡隆盛以及明治天皇等。在与日本诸位政要谈及琉球问题时,格兰特一直以建议的口吻诉说着中日双方开战的弊端,以及中日双方应寻找和平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格兰特始终恪守自己的中立立场,在和诸位大臣交谈时都首先说明自己与美国政府的区别,以及声称最终解决问题的决定权在于日本与中国。因此,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奏章中所说格兰特和日本政要谈及了“分岛”一事、主持了中日分割琉球谈判的结论就显得无据可依。
格兰特于明治十二年六月(1879 年6 月)抵达长崎港,日方派遣军舰“金刚”号前往迎接。根据日本史料记载,“明治天皇给予格兰特将军最高礼遇,并且授命前任驻美国使臣吉田清城等专门来安排此次格兰特将军在日本的全部行程。在长崎港口给予21 发礼炮的外交礼遇,并且在长崎女子师范学校内摆设三天三夜的宴席来欢迎美国的客人”[8]112。格兰特一行所到之处,不管是渔村还是城市,皆有日本政府所安排的市民在岸边欢呼,可见,日本对格兰特到访的重视程度超越了当时清政府的预估。
随后,格兰特在横滨、名古屋、大阪、东京、京都等地参观游览,后前往日光修养。在此期间,格兰特会见日本政要,参与调停中日琉球纷争,他提出“格兰特精神”。日本当时瘟疫流行,为了方便日本高官往来于格兰特住处和东京之间,日本选择了日光为格兰特的临时居所。在日光休养期间,伊藤博文和西乡隆盛都数次前往格兰特的居所,商讨有关琉球问题,格兰特反复强调,在此事件中,如果日本和中国发生战争,将不会对双方有任何好处,唯一可以渔翁得利的便是欧洲列强。虽然格兰特在此直接劝谏伊藤博文等人回到谈判桌,但格兰特自己也强调,“我对于此事的出发点就是希望日本和中国双方保持和平,并且一切解决的方法都需要经过详细的研究”[7]559。杨约翰本人也说:“格兰特在此对话之中并没有给出任何意见,这一切真正的处理办法似乎都要等到日本内阁和清政府来商讨决定。”[7]560可见,虽然格兰特一行人答应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中展开调停,但是在各种细节上都在反复强调自身立场,并且说明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应该是中日双方,他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中日双方回到谈判桌。
在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格兰特将军御前对话录》中的内容,格兰特表示:中日双方都深受欧洲列强毒害,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欧洲列强。因此,如果中日出现战端,欧洲列强必定会从中作梗,渔翁得利。就此话题,格兰特特别强调:“日本现在(琉球)已经实施了相关统治,因此还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所相让。如果直接拒绝中国的有关要求,日本也一定会有所损失。因此一定要寻找一个两全之策。”[8]94由此可见,格兰特虽然在此纷争之中逐渐处于核心地位,决定了两方是否能够见面举行和谈。但是,格兰特也一直克制自己,没有将自己视为真正的决策者。虽然伊藤博文等对格兰特都十分尊重,但是伊藤仍然表示,所有决策都要由日本内阁作出,自己不能成为真正的决策者。格兰特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虽然他参与调解中日琉球之争,但是真正能够成为决策方的只有中国和日本。
清政府一直紧随格兰特,并且迫切希望格兰特为其“做主”。格兰特在东京游玩时,再次会见了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着重列举了当时日本对琉球的强制统治的具体行径,“1872 年日本要求中山王把其子送往东京的居住地,并且向日本纳贡……。1874 年,日本再颁布命令,琉球所有事务归内务省管理,其他事情一律遵从旧例……。1875 年,日本使者抵达琉球。不许琉球使者前往中国恭贺新帝登基,并且全部年号改用明治。日本还在琉球驻军,常备驻军二百余人……。1879 年自废藩置县以来,全部事宜由县令管理。琉球国王卸任并迁往东京居住”[8]69-71。何如璋希望格兰特为清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但当格兰特会见日本天皇时,依旧坚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对琉球问题未有偏有倚。
明治十二年八月十日(1879 年8 月10 日),格兰特前往日比谷练兵场,和天皇一同参加阅兵式,两人稍后又在离宫共进午餐。在下午两点十分,格兰特到达浜离宫,在此处一间茶室内和天皇会晤。当时,在场的还有三条实美太政大臣①太政大臣是日本律令制度下的官位,主要职位为辅佐天皇,总理国政。三条实美是日本最后一任太政大臣。和翻译以及其他日方陪同人员。
格兰特首先就其他问题同天皇交换了意见,然后逐渐把话题引向琉球问题,遂借机提出自己的建议。随着中日重新回到谈判桌,局面逐渐明朗,格兰特的作用与地位也越发明确:第一,格兰特是双方的桥梁;第二,格兰特依据西方先前的种种惯例,为双方争议提出解决思路。格兰特和天皇在此问题上都表示了关切态度,并且双方都认可日本和中国是解决此问题的决定性力量。天皇和格兰特将军的会晤,还就本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言论自由等交换了意见。格兰特说道:“现今各文明国家皆有自身之政党相互控制,自身政策失误的事更少,行政效率更高……。本国人民可以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今日贵国的言论当中,很多人倡议设立民选议会,贵国更应在时机成熟之时,设立议会……”[9]4,天皇则说道:“非常感谢阁下的建议”。之后,格兰特又说道国家债务等问题,他认为在当前亚洲国家中,日本和中国是主要借贷外国资本的国家,两国如果出现摩擦或者战争,将会导致欧洲列强的资本迅速占领市场,控制国家命脉,最终干涉国家内政。
此后,格兰特开始详细叙说有关于琉球一案,他说道:“至此,我继而谈及在下中国逗留其间与李鸿章和奕䜣会晤之事。此事件我也和我国(美国)公使多次详谈。并且和诸位公使、伊藤君、西乡君在日光已详谈此事。凡国际争夺事宜都要从两国详细了解情况,但是日本和中国之间就本事件的阐述相差很大……,因此,我也只能说一些鄙见以供参考……,凡确信一国如日本已占地盘而为其不可侵犯的主权,但关于琉球一事,从中国的立场来观察时,又有应注意之物……,互让可以说是维护两国和平的基础。就算有人想要从中生事也无从下手。在琉球之间画经纬线进行分割,让中国可以拥有太平洋广阔的水道,这样中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9]6-8格兰特为天皇分析了中日双方围绕琉球问题保持和平之理由,以及开战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这种分析方式很明显处于第三方立场,其劝谏的核心点就是希望双方能够保持和平,互有相让。天皇提到“此事件由伊藤君等决议”,则是把主动权把握在日本手中,虽然清政府想要和谈,但是最终能否和谈,则由日本内阁来决定此事。对此,格兰特表示赞成,因为天皇此番做法也承认了格兰特处于中立地位,这让格兰特自身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作用和身份,就是作为一位让双方回到谈判桌且以互相理解的精神,友好地解决问题的中间人,同时也让美国不至于身陷于纠纷之中从而造成国家利益受损的局面。
日本在此问题上一直把握着主动权。日本对于格兰特作为中日问题的调停人表现接纳态度,同时,伊藤博文和天皇又都陈述到,琉球问题要内阁共同决定,他们两人谁都不能独自决定此事。日本对于此问题的回应说明,格兰特一直不处于决策的核心,就算是按照何如璋等人设想让格兰特出面为清政府做主,日本内阁也不接受格兰特成为琉球一事的最高裁决者。由此可见,日本才是可以推动琉球一事发展的真正力量,格兰特在此事件当中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双方重返谈判桌,并且提出和平解决此争端的处理办法。
四、“格兰特”精神和“分岛”方案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格兰特返回美国后,中国和日本双方在“格兰特精神”的前提下开始接触谈判,日本拿出最初的“分岛”方案,双方经过激烈谈判,最终以中国拒绝签约而告终。清政府虽然希望美国政府出面为此仲裁,但是“格兰特精神”的核心点就是“保持和平,相互理解”,并没有对任何一方批判或是偏袒。格兰特保持中立的精神与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以美国利益为大局来考虑,美国在当时的琉球问题上只能是权衡且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伤害。因此,让中国和日本双方成为该问题的真正决定者,这也是格兰特所坚持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由此可见,格兰特不会是最终方案的提出者与决定者。
清政府自始至终都一厢情愿地认为,格兰特代表美国政府对此事进行调停,并且清政府也是最希望美国直接插手于此事的一方。当格兰特返回美国后,何如璋致信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说道:“希望您归国后,可以向贵国最高政府详细地说明琉球一案,并予以贵国国会详知此情。”[10]何如璋一直是等待着美国官方对此作出回应,并且相信格兰特等人必定已经在此事上有所涉足,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何如璋认为最终的分岛方案由格兰特提出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与历史真实情况实际上存在较大冲突。首先,根据日方、美方史料,并没有人提出有关说法,此说法目前也仅见于何如璋给李鸿章的信件,而且和格兰特来信更有前后矛盾之处。国内学者戴东阳曾就此提到 “当时,总署收到何如璋来信称格兰忒(特)有三分琉球之说,但格兰忒(特)致总署及李鸿章的函件则称需将何如璋前照会撤销,由两国另派大员会商办法,与何如璋函报情形不同,总署甚感困惑。”[11]后来,李鸿章也在和总理衙门的信件中说道,“今阅格前首领迭次亲笔信函及杨副将函,并未稍露割岛分属之说,或若背后私议,或与日本秘商未经允定,抑或美使以斯言诳子峨(即何如璋),均不可知”[12]477。
虽然李鸿章等希望格兰特代表美国政府仲裁琉球纷争,但是李鸿章清晰地了解格兰特在此事件上的中立态度,这才会导致他并不相信何如璋的信件中提及格兰特直接说出“分岛”一事。李鸿章在奏折中说道;“日本废没琉球,经中国数次理谕,又有美国前总统格兰忒(特)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臣与总理衙门函商谓:中国若分球地,不便收管,只可还球人,即代为日本计算,含此别无结局之法。”[13]112李鸿章的奏折虽提及“分岛”一事出现在格兰特到日本之后,日本才有了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并没有直截了当说明到底是不是格兰特提出这一方案。李鸿章当时也不过只有何如璋一纸信件提到格兰特直接提出分岛一事,再无其他证据。况且,格兰特本人致李鸿章的信件也如其曾表达的态度一样,恪守中立,这完全不符合何如璋的说法。
日本方面则是称其在基于“格兰特精神”,为了和中国“妥协”才作出的分岛决定。因此可知,日本应是“分岛”方案的最终提出方,并且其还曾篡改格兰特之意以试探中国之态度。中国方面有记载道,竹添进一郎①竹添进一郎,日本汉学家、外交家,曾任日本驻天津领事,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日本驻朝鲜公使等职位。在中日开始“分岛”谈判之前曾私下对李鸿章说道过:“会美国前统领格兰氏游历我国,为我说曰:琉球南部诸岛与台湾相接,为东洋咽喉,日本占有之,若有侵逼中国之势者,李中堂所争尽在于此也……”[14]140,由此日本才有分南部之两岛给中国的相关想法。但是在日本方面的资料当中却罕见日本政府代表直言格兰特曾说过中国想取得琉球南部之两岛的说法。
时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曾有一部《世外井上公传》,该书并未曾提及有关格兰特说过琉球南部两岛是中国所求的相关话语,只是有提到:“(日本代表)竹添到中国天津任职,并与李鸿章进行会谈”。在此之际,李鸿章提出琉球三分案,李鸿章表示:“这是美国公使平安和前总统格兰特,向何如璋内示过,在这之后最终提交给我国。”这个琉球三分案是把琉球分成北部、中部、南部三个部分。北部由日本统治,中部琉球以复国,并为中国属国,向中国继续朝贡。南部则为中国统治。竹添由于是第一次得知此方案,便立即向日本内阁报告。日本方面得知此方案后格外震惊。若按此三分法,中国可以占领南部不说,还可以拥有中部琉球国的宗主国权利,使得日本必须放弃琉球的大部分主权,只能有北部一小部分。日本立即对此方案是否出自格兰特和美国驻日本公使平安进行核实。此后,日本驻美公使吉田在发电报中说道:“基于格兰特所说的‘牺牲精神’,日本决定把宫古、八重山两岛割让给中国,并且中国要满足日本最惠国待遇等条件。并没有说过此三分法……。”[15]416可见,中国和日本方面对于此事之记载有一定矛盾,但从历史的客观角度来看,日本迫切想要在中国和沙俄解决西北边境问题之前了结琉球一事,因此,中国方面的记载更加可信。
在《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中也有相关记载道:“格兰特给李鸿章的信中,明确说明了双方要不动干戈,以派遣使臣友好谈判为主。并没有其他办法的记载……。”[16]374对于日本驻美国公使的问询,格兰特还是表示:“至于有关版图之事,是否有所让与,鄙人虽非无见,然深望两国政府不假他人干涉而自行结局,故未在上述书简中揭载之……。”[16]312在此文件中的相关记载便与之前竹添进一所说的情况有极大不符,这从侧面也证明,日本在整个事件当中十分主动,并且在不断利用甚至曲解“格兰特精神”去达到自己侵占琉球,并且强迫清政府开放门户给日本人的目的。
因此,“格兰特精神”和日本做出“分岛”这一决定二者之间的确存在关联,但是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首先,这并不是由一方所提出,“格兰特精神”是基于美国的利益所提出,“分岛”则是日本根据自身利益和野心所筹划,二者的主体和目的都有极大区别。其次,“格兰特精神”是对中日双方的一种呼吁与牵制,而不是单纯针对中国或者日本,但是日本所提出的“分岛”方案则是想要把日本的利益最大化。“格兰特精神”是日本作出“分岛”这一决定的基础,“格兰特精神”中的互相妥协主旨使得日本有了一个借口,拿两个小岛去换取在中国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凸显了日本的“诚意”。所以,当谈及“格兰特精神”和“分岛”方案时,要仔细区分这两者的差别,防止把双方混为一谈。
五、结语
首先,日本是最急于占领琉球的一方,它迫切希望利用格兰特和“格兰特精神”,希望尽快促成对琉球的“合法”占领[17]。1880 年前后,清政府还在同沙俄就西北边患的问题持续摩擦,因此精力大多数被牵制。与此同时,日本勾结沙俄,同意沙俄在长崎港驻兵,以此来威慑清政府,将其用作谈判的筹码,企图侵占琉球全境,获得在中国通商之权利以及图谋占领中国台湾。如果清政府和沙俄完成条约的签订程序后,必定会把注意力转向琉球,甚至可能把海军力量用于此。因此,日本必须要在清政府解决西北问题之前,先确定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这样才能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
与此有相同看法的还有日本学者山城智史。他认为,当时的日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看是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而实际上“此谈判对井上外务卿来说,最大的目的是在《日清修好条例》期限前,获得在中国内地通商的权利”。日本希望是用琉球南部两个小岛换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其也提及到“如果(日本)对不毛之地宫古岛·八重山诸岛进行正式的实地调查的话,该土地的(外交)价值就会下降,不能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调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伊犁问题”(在这期间)很有可能就解决了……。”[18]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是最急于签订有关条约,以便完成对琉球占领合法化。所以,日本势必会根据“格兰特精神”作出所谓的“牺牲”,以便快速实现其最终侵略目的。
其次,清政府高层一直寄希望于美国,以为“格兰特精神”让双方作出让步,这是帮助琉球复国。实际上,美国并不会直接干预此事件,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两国自己在后续的谈判中作出决议。而清政府最终决定否决历经数月和日本谈判拟出来的条约,并计划在解决西北边患后再对琉球问题进行商议。清政府在1880 年就开始同日本就琉球一事正式谈判,其一直秉持着“格兰特精神”,在琉球问题上试图寻找一个可以互相接受的办法。但是,最后拟定的方案在清政府内部受到众人的反对。例如,刘坤一①刘坤一,清末年间军政重臣,曾三次担任两江总督,也是湘军的统帅。他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重要事件当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等人都上书陈述:“臣查球案与倭约本系两事,直隶总督臣李鸿章与右庶子陈宝琛,左庶子张之洞言倭约不宜更张附议,以免另生枝节,诚为有见,至谓:球案宜缓……,中俄定局,勒令日本退球地,重立废王,以张义声……。”[16]126刘坤一在奏折中说道,他认为李鸿章等人和日本如果签订有关琉球的条约,实际上应该是缓兵之计。他也清晰地看出,日本就是在清政府和沙俄有战事之时趁火打劫。他认为,清政府应在同沙俄立约之后,便对琉球问题采取强硬立场,让日本退出琉球,帮助琉球国王复国。在明确格兰特无意为清政府出面作出对此事的仲裁后,清政府直接决定拒绝和日本就琉球一事签订条约。因此,清政府应不是真正希望以“分岛”这一方式来处理琉球问题的一方,并且清政府在理解“格兰特精神”上出现了些许歧义,清政府解读所谓的让步,就是希望日本作出让步,退出琉球,实则不然。
不管是格兰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还是其他美国方面的人员,一直恪守中立,这不仅是为了美国在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考虑,其更是在东亚地区局势的大局之下所判断出的基本外交方针。美国相关人员都对琉球问题表现出在情理上的支持,以及要在客观上置身事外,所以一直不肯直接插手此事。就算到了1881 年,日本和中国最终谈判破裂,日本驻华公使宍戸玑到美国驻华公使馆,希望美国公使安格尔(Angell)对此发表看法,或是帮助日本“劝谏”中国“恪守”“格兰特精神”完成条约签订程序,安格尔也仅仅表示,“我不敢就中日两国正在商议的主要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委员会在最近的谈判中,中国委员在同意签署条约后拒绝签署我们的条约,我就应该撤出首都”[19]。美国公使在面对中国最终并没有签订条约情况下,仍然决定不会以官方形式对此作出任何评论或者采取行动,但是从话语中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谈而不签”的行为颇为不赞成,但是美国官方一直保持对双方的中立立场。因此,美国在琉球问题上一直保持了内部高度一致,所有人都不插手到日本和中国纷争中,并且在任何时刻都坚持恪守中立。因此,美国大概率不可能是真正提出日本对琉球群岛进行“分岛”方案的一方。
综上所述,“分岛”一事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可知日本内阁、清政府、格兰特三方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格兰特在其中的作用:一是中日双方重建沟通的桥梁,二是提供琉球纷争的解决思路,推动双方和解。日本对琉球问题提出“分岛”办法是在历史的客观条件下——即“美国调停、中日对抗”的时局中演变出来的结果,而格兰特在此事当中的最主要的作用便是提出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核心精神——“格兰特精神”。此精神的核心要义只在于规劝双方让步,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琉球一案,这同日本最终提出的“分岛”方案并无太大瓜葛。从全局思考,各方都是最终“分岛”方案的推动者,但若是究其方案的最初提出者,从各方客观的史料来看,应该是日本提出了琉球“分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