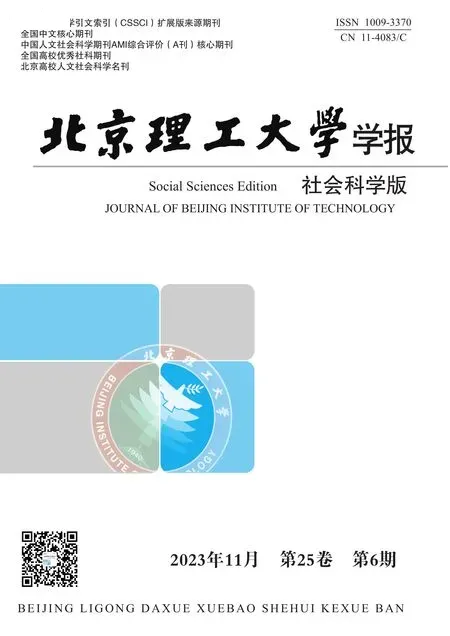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救济:挑战与进路
田 静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1)
2022 年11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问题达成设立基金的突破性协议①2022 年11 月19 日,第2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各方同意设立一个基金机制,以补偿因气候引起的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损害”。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11/1112632。,这反映出气候变化损害救济于未来气候治理的重要性。在传统意义上,气候变化探讨的重心聚焦于环境、科学和经济方面,但囿于气候变化固有的不平等性及其对人类生存与福祉构成的极致挑战,其关注点日益扩大至社会层面,人权立场也开始参与到气候变化损害救济的探讨中来。究其原因,气候变化持续导致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缓发性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已对人权的充分享有与保护造成严重冲击[1]。而且同其他侵害行为相比,气候变化侵害具有全球性、流动性、复杂性、间接性和不可回避性等特性,也使单纯依赖国际环境制度进行规制难以形成有效救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共同的互助行动(mutual action)去实现,而人权根植于道德价值观,可为这种互助提供基础,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决策在国际法律和价值观层面得到最大范围的共享。可以说,以人权为基础的气候变化救济路径虽不能独立且全面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作为国际法更广泛地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一部分,它确实具有辅助价值。然而,鉴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抵牾难以避免,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救济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气候变化与人权法的关联入手,阐述二者的关系,并揭示人权维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障碍,在此基础上对气候变化损害的人权法救济进路作一探讨。
一、耦合:气候变化与人权法的理论关联
人权法是现代哲学的重要成就,以独特的道德魅力和革命力量持续影响并塑造了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成为现行国际法中唯一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体系[2]。人权论述承载着改造世界的愿景,旨在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普遍有效的规范。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开放体系,若将气候变化识别为人权问题,可增强其在社会价值中的分量,使人们感受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一)气候变化经由人权法表达的优势
人权通常是建立在三种意义的基础上使用的,即描述一种制度安排、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以及表达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3]。而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环境退化现象,完全与之契合。经由人权法表述,不仅可以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至相互竞争的社会目标之上,赋予其永恒、绝对和普遍有效性的价值[4],还可为其注入与人权相关的规范价值和直接适用性,体现如下:
第一,在气候危机下为人类生活的核心条件提供保障。当前气候危机感日益增强,人权法作为保护人类和应对多种人类危机的重要法律文书,可在不断恶化的地球生态系统中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劲助力,弥补国际环境法体系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上的不足。国际环境法长期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将以市场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从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逐步过渡到发展中国家,均相继建立了全国性或地方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以市场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更关心利润创造,而非社会公正[5],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疏于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关照。然而一个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福祉的环境,对于人类过上平等、充实及有尊严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人权维度完善气候变化政策,能更好地维护人类生活。
第二,在气候变化诉讼中为受害者提供起诉依据。在气候变化司法中,人权主张可将公众视线转向气候变化对特定个人和群体的有害后果,使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更清晰具体。此外,这种法律论据更具说服力,可促使政府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减排措施,促进对不利人群所承受不平等影响的承认,带来更深远且更不易推翻的政策变革,给予气候变化破坏作用应有的认可[6]。在《巴黎协定》明确承认人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作用以来[1],以人权受损为由提起的气候诉讼便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关案例频频见诸报端。自2015 年“乌尔根达基金会(Urgenda Foundation)诉荷兰政府”案(以下简称Urgenda 案)的第一个判决发布后,世界各地的个人与组织纷纷向作出类似裁决的国家提起诉讼①2015 年,一位农民(Ashgar Leghari) 指控巴基斯坦政府在执行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时不作为与拖延,侵犯了其享有的生命权和尊严权。Ashgar Leghari v. Federation of Pakistan (W.P. No. 25 501/2015), Lahore High Court。 2019 年乌尔根达基金会诉称荷兰政府减排不力,未尽到相对的义务,侵犯了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 条和第8 条享有的人权。See ELAW, Urgenda Foundation v. The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Judgment of 24 June 2015, C/09/456 689/HAZA. 2020 年3 月,19 名青年活动人士向韩国宪法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国的气候变化法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和健康环境权等。Joana Setzer , Catherine Higham, Global Trends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2020 Snapshot, p.42, www.lse.ac.uk/Grantham 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21/07/Global-trends-in-climate-change-litigation_2021-snapshot.pdf。,爱尔兰、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德国、美国、加拿大、秘鲁和韩国等正进行关于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人权义务的法律诉讼②Joana Setzer & Catherine Higham, Global Trends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2020 Snapshot, p.42, 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21/07/Global-trends-in-climate-change-litigation_2021-snapshot.pdf。。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关注人权能促进更公平的气候政策形成,正如有学者指出,“人权占据了司法救济的大部分空间,解决气候变化背景下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人权法规范的一个基本职权范围。”[7]
第三,为气候变化治理的软法之治加入硬法规范。气候变化相关条约在制度安排上以国家为中心,很大程度侧重于强加国家义务或创造国家责任,缺乏法律基础规范私人行为者的行为,在为气候变化受害者提供救济与补偿方面尚存空白。如2015 年《巴黎协定》第8 条虽提及了“损失与损害”问题,但在气候变化导致的人身、财产和环境损害问题上,并未提供相应的补偿措施,也未明确提及国家及非国家行为者的责任。2022 年举办的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各方在保护脆弱国家而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同样地,其补偿主体是气候脆弱国家,仍未解决具体人身、财产和环境损害。而人权法规范无论在国际抑或区域一级都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和成熟的机制来惩戒违法和规范缔约方的行为,因此诉诸人权规范可为气候变化受害者解决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提供一种救济途径[8]。此外,1998 年《奥胡斯公约》作为里程碑式的国际公约,得以成功的原因也在于与人权相结合,将程序性环境权提升至其他人权的保护水平,包括获得信息的人权、参与环境事务的人权和获得司法公正的权利。可见,环境人权条约是最有效的环境条约之一。
从其他人权(生命权、财产权等)角度考察气候变化,可根据问题和情势的变化,对人权的一般性表达创造性地加以解释,而不需要在一个单独的规范性立法中全面和严格地加以定义[9]483。毫无疑问,联合国附属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人权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潜力是正确的,许多国内判例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0]。而且《巴黎协定》呼吁缔约方“尊重、促进和考虑各自的人权义务”,也体现出人权融入气候法体系的一种发展趋势[11]。整体而言,以人权的方式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在规范上是可取的,并且在气候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二)气候变化与人权的互动路径
以人权法规范为气候变化损害提供救济的尝试是建立在环境权和人权之间的联系之上的①国际人权机制通过对环境权的直接规定与间接延伸来为气候变化诉讼提供权利依据。[12]。对于如何基于人权立场为现有环境保护提供制度安排,目前主要存在三种演进路径:扩权型、程序型以及创权型路径。
1. 扩权型路径:“绿化”既有人权
自《斯德哥尔摩宣言》以来,国际社会便更多关注“绿化”既有人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如生命权、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人权(如享有健康和福祉所需的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享有可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等)已逐渐被“绿色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也被允许经由人权途径寻求救济[13]。这种路径的优势在于:通过扩张解释既有人权,不仅可以聚焦于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即环境损害对受到国际公认的主要人权价值的侵犯[14],还可为人权体系增添环境保护色彩。这种试图通过扩展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权利维度的方式来间接达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已成为当前人权领域存在的普遍实践,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判例支持。
但这一路径在气候变化救济实践中也存有弊病。首先,现有人权体系对环境保护的范围较小,加之气候恶化本身不构成诉因,因而对气候变化受害者进行救济须与现有人权相联系,这也致使气候变化问题很难完全归结到现有人权体系中。其次,“绿化”既有人权体系所呈现的理念是,环境损害会危及人权的享有。这一理念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将环境完整性同人类需求相联系,忽视了环境的内在价值。最后,气候变化通常是对未来产生的影响,而人权受损通常是在损害发生后才确定的,中间存在时间差。即便能确定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特定人权损害之间的联系,获得救济也可能为时已晚。因此,扩权型路径难以全面为气候变化损害提供救济,但其作为过渡阶段的一种替代性方法,为之后承认独立环境权铺平了道路。
2. 程序型路径:重视程序性环境权
参与权、补救权和诉诸司法权等环境程序性权利的产生,得益于将“民主治理”理论引入生态可持续性领域,这对增强公民以及组织应对公共决策和政策的能力是必要的②Linda Hajjar Leib,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Philosophical, Theoret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71-108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作为人权法中最重要的环境内容,程序性环境权已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而且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ICCPR)中也有相关规定体现,如寻求信息权和参与公共事务权等。自《里约宣言》在原则10 中阐明程序性权利和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以来,任何编纂人权和环境法的尝试都会考虑到这一发展。最为典型的是1998 年通过的《奥胡斯公约》,它认为实质性权利必须伴之以寻求执行该权利的能力,因而仅规定了程序性环境权,即保障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权利。它强调了公众在环境问题上参与的重要性和从公共当局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被认为是“在联合国主持下的环境民主领域最有冲击力的一次尝试”[15]。
此外,在目前已知的30 多个国家的宪法中,均对环境保护的程序性权利进行了规定。例如,《捷克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中规定,“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的及时和完整的信息”[16]。在确定实质性权利受到侵犯时,裁决机构援引程序性权利的情况也并不罕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96 年评论题为《人权与环境》的报告时便强调,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表明:程序性权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保护个人在健康环境中生活的实质性权利这一目标的手段[17]。总之,环境程序性权利鼓励公民要求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并在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的决策中发表意见,最重要的是,环境诉讼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引入民主实践。但是,若将环境知情权与参与权延伸到“所有受影响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与国家主权这一传统概念相冲突,而且需要全球参与重大环境决定,只有实质性地与国际法相结合,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
3. 创权型路径:创设独立环境权
还有观点认为,“应存在一种拥有令人满意的环境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并且应当有合法方法以一种持续和有效的方式来实施此项权利,问题不再是环境对作为法律关注焦点的其他人权的影响,而是环境质量本身”[9]477,这便是创权型路径。表面来看,似乎这种路径更能彻底将环境保护纳入人权范畴,但囿于所期待的环境质量是难以用法律语言加以界定的价值判断,且会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故很难对环境权作出单独又准确的表述。迄今为止,国际人权法都未承认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实质性权利,包括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在内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也更多的只是认可了环境权,没有将其作为一项独立人权加以规定。曾有观点认为,《斯德哥尔摩宣言》标志着环境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但事实上,该宣言并未宣布环境权,仅暗示了行使其他人权不可或缺地需要基本的环境健康。在该宣言之后,联合国文件通常都采用这种间接暗示或确认的方式,来避免明确主张一种新的环境人权[18]。以至于1992 年《里约宣言》同样没有直接承认环境权,只表述为“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之所以重申这一点,是为明确《斯德哥尔摩宣言》以来人类保护环境的主要用意,以使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免受伤害[19]。
1982 年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作为国际环境法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出发点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一系列行为准则,但其所规定的仍是程序性环境权。其后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21 世纪议程》以及1998 年通过的《奥胡斯公约》,都对实体性环境权作出了回避处理。即便是区域人权条约中也只是将环境权表述为“健康环境权”(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缺乏明确且实质性的内容。正如法国学者亚历山大·基斯所说的“国际环境文件都没有提到环境权,只是强调了公众知情、参与和获得救济等程序性权利”[20]。总体而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未有明确规定环境权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存在,相关软法文件也趋向于间接保护,转而表述为可持续发展理念[21]。
二、困境:气候变化损害的人权法救济挑战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紧迫威胁亟需得到相应的法权回应,国际社会为此作出诸多努力。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巴黎协定》无不体现出国际社会在环境法体系中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艰辛,但国际环境制度愈发政治化,使其经由妥协达成的协议更多体现在机构和程序的安排上。而人权视角的转换无疑为气候变化救济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但由于实体性环境权缺位,将人权法适用于气候变化救济更多依赖于对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进行扩权适用。这种方法虽可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不同维度的挑战。
(一)时间维度:侵犯人权的因果关系界定困难
在气候变化损害规则中,因果链条的确定是一个关键挑战。在界定因果关系时,主要难点是在温室气体排放和侵犯人权行为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包括大气温度上升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影响问题。由于气候变化的时间跨度,对因果关系的调查异常困难。这其中需要对两种因果关系展开调查,第一种是国家作为或不作为与气候的具体威胁或退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22]。目前就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暖这一观点已不存在争议,但确定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对特定地点的具体气候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极具挑战性的。第二种是这种威胁或退化对个人侵犯人权的关系认定。而气候变化毋庸置疑是一个累积因果关系的问题,即气候变化损害结果是由多个独立行为共同导致的[23]。这两种因果关系的调查在实践中都存有重大困难。
在气候诉讼史上,试图在被告的排放行为与原告所受影响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也往往以失败告终。早期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因纽特人(Inuit)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气候变化请愿书一案的结果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请愿书认为,美国是地球上累计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并且对全球气温上升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这一行为侵犯了因纽特人的人权①Sheila Watt Cloutier, Petition to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 Violations Resulting from Global Warming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kcaw.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seitcHRpetition.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11 月6 日。。但美洲人权委员会驳回了该请愿,认为无法确定所指控的事实侵犯人权。有学术观点认为,这暗示了不可能在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和侵犯人权行为之间建立因果关系[1]。类似的情况在2015 年“卢西亚诺·柳亚(Saul luciano liuya)诉RWE”案中也有体现,法院驳回了起诉,并指出在特定温室气体排放与特定气候变化影响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组成部分中无法辨别“线性因果链”①Luciano Lliuya v. RWE - Climate Change Laws of the World,https://climatelaws.org/geographies/germany/litigation_cases/luciano-lliuya-v-rwe。。建立因果关系通常是证明每一案例是非曲直的核心,也是气候归因科学的目标。
(二)空间维度:人权法的管辖权受到域外限制
在传统国际法意义上,素有人权法不能域外适用的理论认知。在这种认知下,国家是人权义务的唯一承担者。但是,在气候变化损害救济的人权转向下,气候变化对人权法提出了域外适用的需求,早在2005 年因纽特人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的请愿书中就曾提出,可以追究国家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在域外侵犯人权的责任②Sheila Watt Cloutier, Petition to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 Violations Resulting from Global Warming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kcaw.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seitcHRpetition.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3 年2 月6 日。。但在国家域外人权义务问题上,首要明确的是,国家域外行为所涉及的情形是否属于人权条约管辖条款所指的“管辖”范围[24]。ICCPR 第2 条第1 款规定,缔约国尊重和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该条款较为宽泛地排除了国家在“管辖”范围之外的人权义务。2004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31 号一般意见中对该条款进行了详细解释,明确缔约国必须尊重并确保在其“权力”范围内或“有效控制”下的任何人享有ICCPR 规定的权利,即使他们不在缔约国领土内③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 General comment no. 31 [80], The nature of the general legal obligation imposed on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venant, 26 May 2004, CCPR/C/21/Rev.1/Add.13, available at: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78b26ae2.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3 年2 月6 日。。由此,“权力和控制”也成为国家域外人权义务确立的标准。但即便如此,该标准在气候变化实践中仍较难操作,一国无法保证域外个人或实体排放的温室气体处于其国籍国的“控制”之下。
此外,有学者认为,可将人权公约域外适用于环境公害[25]。这在美洲人权法院于2017 年出具的一份咨询意见中有所体现,该咨询意见审议了国家保护其领土以外人民人权的责任问题,并指出,“国家有义务防止对其领土内外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在这方面,任何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享有实质性人权的损害都应被视为重大损害”④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23/17, 15 November 2017。。美洲人权法院的咨询意见为未来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可能激励其他人权机构认识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违反国家义务的行为。但需注意的是,即便能够证明人权条约可以对某些跨界环境损害进行域外适用,但并不适用所有类型的环境损害,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损害下,侵害行为的累积加之受害者的多样性,很难完全从对人或领土的管辖权或控制权的角度来界定这一问题。
(三)义务维度:气候变化损害的责任难以确定
除因果关系问题外,责任归属的问题对于确定温室气体人为排放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至关重要。但实践中通过人权法对气候变化损害归责困难重重。正如学者诺克斯(Knox)所言,“尽管气候变化构成了对人权的巨大威胁,但确定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要困难得多”[26]。人权法要求国家承担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义务。虽然人权法的责任模式较为确定,但在实践中追究一国政府的人权法责任被证明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迄今为止,人权法都无法促使国家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效行动。
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判断一国是否承担人权义务,需综合考量该国是否在环境退化与其他社会利益之间取得合理平衡,而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给予各国在此问题上的自由酌处权。如欧洲判例中经常使用的“自由裁量余地原则”(doctrine of margin of appreciation),其宪政基础为权力分立原则演绎而成的行政保留之理念。只要程序步骤得到遵守,法院通常会给各个成员国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尊重他们关于如何取得平衡的判断。其二,尽管传统上将排放归咎于国家,但事实上,很难确定一个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了特定的损害,有时非国家行为者对碳排放负有主要责任。有研究表明,一批跨国公司,包括埃克森、壳牌和CEMEX 等在历史上对大部分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8]。其三,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法律义务是纵向的,一国仅对其境内人员负有首要责任,若在界限之外,该国无法也无暇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义务。而且考虑到气候变化损害分布的不均匀性,单追究本国政府的人权法责任对于解决“气候正义”问题并无太大的现实意义[27]。
(四)规范维度:传统人权法难以提供全面救济
尽管开辟人权法在气候变化损害救济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实质层面而言,各主要区域人权法院充斥着纯粹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是严重的,也只是因为它们干扰了相关人权公约所保障的“个人”的权利范围。而且,环境人权案例法倾向于表明,人权语境下的环境保护确实被认为隐含在有关人权条约和公约的承诺中,但除极个别外,与环境有关的“权利”基本上被认为是“个人权利”,通过解释,是其他明确承认的人权的延伸[27]。在程序层面,2003 年欧洲人权法院在“Kyrtatos 诉希腊”一案中指出“环境完整性只是用于衡量特定个人的生命、财产”,在这项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就《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的适用性作出裁决,认为“环境恶化只有在直接影响到原告的个人权利时才具有相关性,而原告无权生活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也无权使周围环境无限期地得到保护”[22]。这也意味着,“传统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无法对与人体健康无关的生态破坏行为构成有效约束”[14],因而气候变化问题也很难完全归结到现有人权体系中。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现有人权机制对环境权发展不敷使用。从实践来看,“环境权”概念更多发生在区域一级。自1970 年以来,欧洲委员会一直致力于研究各种提案,将环境权纳入《欧洲人权公约》保护范围,但因未达成共识而被搁置。虽相较国际人权公约而言,区域性人权公约处于阐明环境权的前沿,并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丰富的判例。但整体而言,当前环境权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大多人权公约采用对既有人权的延伸性解释路径,间接为环境损害提供救济[28];其二,“环境权”规定多呈现政治宣示形式,具体规则尚待明确,可操作性有限①例外的是,非洲人权法院在环境权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一方面,非洲人权法院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司法实践中直接援引环境权断案的人权机构;另一方面,1981 年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是第一个在这方面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其三,侧重于发展程序性环境权,实体性环境权并未得到普遍承认。但只有将“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纳入人权体系,才能为人在良好环境中生存提供最完整和最充分的权利保障[29]。
三、革新:气候变化救济的人权法进路
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那么,首要进行的应该是法学理论的革新,以使其与实践相契合,而不是理论上的妥协[9]483。同样地,以人权方式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在规范上是可行的,在维护气候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举足轻重,但在法律上仍面临一系列障碍。对此,应在理顺因果关系、域外损害与责任归属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国际人权体系的“绿化”进程,并构建以人权法与环境法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机制。
(一)协调气候变化归因的科学与法律方法
以人权为诉求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所遵循的逻辑主线是,在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广泛享有构成侵犯后,原告试图通过诉讼来获得司法救济。但在证据优势规则下,原告为了胜诉,需要证明以下几种因果关系:(1)将气候现象与大气温度上升联系起来,即气候变化归因;(2)将人权受损与该气候现象联系起来,即影响归因;(3)将被告的行为(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温度上升联系起来,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所受损害的相对贡献,即来源归因[30]。质言之,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人权受损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这其间还包括另外两步,即大气温度上升和气候现象。然而,鉴于累积的因果关系,难以通过设计举证责任规则来解决,只能诉诸于气候变化归因科学的进展和侵权因果关系法理的革新[31]。目前气候变化归因科学发展迅速,已可以满足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例如,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使得大气中辐射力(radiative forcing)平衡改变,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进而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产生影响[32]。但在确定和量化由气候现象造成的人权损害问题上,还须考虑非气候变量,展开高度复杂和多层次的科学调查,这也是气候归因科学或量化气候变化改变某一事件程度的科学目标[30]。
面对无法将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特定损害联系起来的科学难题。有学者指出,可诉诸证明标准予以解决。具体思路是:在事实认定层面,一般因果关系以造成损害为标准,具体因果关系以受害人很可能受损为标准[31]。这在Urgenda 案中就有所体现,海牙地方法院根据IPCC 评估报告,认为“目前荷兰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范围内有限的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些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事实”。因此“可以假定荷兰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现在和未来)对荷兰生活气候的影响之间存在充分的因果联系”①Urgenda Foundation v. The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Hague District Court, Case C/09/456 689/HA ZA 13-1 396, Judgment, 24 June 2015, ECLI:NL:RBDHA:2015:7 145 (in Dutch), ECLI:NL: RBDHA:2015:7 196 (English translation) (hereinafter: Urgenda)。。此外,在确定被告对于温室气体排放贡献大小的问题上,“一般因果关系+排放份额”的归因模式可作为一种有益尝试。具体而言,在人类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损害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确凿无疑的前提下,应当根据各国对于该损害的“贡献份额”来确定其相应的责任份额[33]。而且,在《巴黎协定》设置的全球升温控制目标下,各国履约采取“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方式,并辅之以全球盘点机制。这也使因果关系愈发既定化,明确了“违反温控目标的国家自主贡献义务的行为”即构成“造成气候变化危险或侵害”的因果关系法则[34]。不容忽视的是,在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裁决越来越依赖气候科学,而科学发现也越发积极寻求司法权威的背书,这在厘清因果链条上尤为重要[35]。
(二)明晰气候变化域外人权义务的范围
确立气候变化域外人权义务的范围,是以人权为基础的气候变化损害救济面临的重要挑战。如前所述,“权力和控制”是目前各主要人权机构所普遍认可和适用的标准,但在气候变化中根据此标准确立一国的域外人权义务困难重重。在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突破口:第一,域外人权义务并不以同样的方式限制所有人权,自决权是其中的一种例外情形。该人权在ICCPR 第1 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ICESCR)第1 条中都获得了承认,并有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人民都不得被剥夺自己的生存手段[1]。2015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出,“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国家居民在其固有领土生活,及享有和行使自决权构成了挑战”②HRC, Devandas Aguilar et al,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ul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2015。。因此,可基于自决权要求一国对他国国民采取适当减缓和适应气候政策。
第二,将不损害原则适用于国家域外人权义务中。根据国际习惯法,不损害原则是指“各国有义务不损害或侵犯其他国家的权利”。在环境法中,这一义务已经转换为“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和任何管辖范围以外地区造成损害的义务”[36]。在国际实践中,最早适用该原则的是1941 年的“特雷尔冶炼厂”一案,该案仲裁员明确指出“任何国家都无权利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致使烟雾在他国领土内或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人员造成伤害”③Trail Smelter (USA v. Canada), Award of 1941, III RIAA 1911, 1965。。自该案后,不损害原则也被规定在《斯德哥尔摩宣言》和《里约宣言》中,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并且在防止气候变化损害方面,还存在三个标准用于判断是否违反不损害原则:(1)采取行动或预防的机会;(2)损害的可预见性;(3)为防止损害或最小化风险而采取的措施的相称性[36]。事实上,不损害原则适用于人权法领域早有先例。2012 年,人权理事会在第21/11 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极端贫困与人权的指导原则》中就明确提出,国家有义务避免损害其境外生活贫困者享有人权的可预见性风险④Resolution 21/11 Endorsed the Final Draft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UN Doc. A/HRC/21/39。,由此将不损害原则延伸至人权法。
(三)厘清国家与企业的人权尽责义务
1. 明确国家“自由裁量余地”的标准
国家基于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人权义务,难免会与其他经济、社会或文化权利有关的义务相冲突,而如何在履行人权义务与其他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公正平衡,是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的重要考量。鉴于该问题的复杂性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国家通常被赋予“自由裁量余地”。这一原则源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理论,即只要程序保障到位,便可认为环境对人权造成的影响是合理的。但即便如此,很多情形下造成的损害都被认为超出了判断限度,或者政府某方面的程序失误导致了侵犯人权的裁决,这也表明“自由裁量余地”原则的适用并非不受限制。通常而言,该原则的宽窄取决于被干预权利层级的高低[37],权利越重要,裁量余地越窄。例如在环境申诉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主要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2 条(生命权)和第8 条(个人及家庭生活权)进行审理,但生命权层级较高,仅在恐怖袭击涉及时才可使用。而第8 条在适用时,也需通过“相称性检验”的考查,即运用手段和追求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相称性关系。而其中的手段,即国内公权力机关的干预行为,也要依法律规定,符合“合比例性”或属于“民主社会之必需”等条件[38]。
2. 整合国家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的人权义务
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确立国家责任包括以下步骤:(1)确定可归咎于一国的损害行为;(2)确定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3)确定是否违反国际法;(4)违反对受害国的注意义务(尽职调查);(5)在法院的步骤:量化损害并分配责任[36]。同时结合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规定可知,违反国际义务是国家责任产生的前提。那么,归根结底,在气候变化中国家的人权法责任,取决于其履行人权义务的性质与范围。一般来说,国际法规定的人权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三个层次。具体表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尊重义务”则要求各国采取行动防止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保护义务”与“实现义务”同属积极义务,前者要求各国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与实体免受气候变化损害,包括采取必要的适应措施以及规制境内私人实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后者指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行政和经济等多种手段逐步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改善环境质量,为充分实现人权创造良好条件[27]。此外,在国家承担的注意义务上,Urgenda 案明晰了国家注意义务的最低限度为“危险疏忽”,以此作为责任归属的主观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荷兰政府本应努力预见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影响,并应相应采取行动防止这些影响,以避免疏忽责任。虽有必要在国际法中逐案确定责任归属的主观过错程度,但“尽责”标准已符合为追究侵犯人权行为而设定的最低门槛,特别是在保护基本权利的义务下[1]。
3. 明晰公司在气候变化中的人权尽责义务
在以人权为基础的气候变化诉讼中,国家作为管理者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被告,但近年来人们也愈发关注实际的碳排放者,特别是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大型化石能源企业。有研究显示,在1751—2010 年,90 家“碳排放巨头”(Carbon Major)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工业二氧化碳和甲烷累积排放量的63%[39]。此类诉讼的数量目前相对较少,但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而且正在增加的同类诉讼也在不断明晰企业的人权尽责义务。2021 年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就荷兰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一案(以下简称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案)作出的判决,是世界上第一例由法院以国际人权法为依据,对跨国公司追究气候责任的判决[40]。该案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不成文注意义务,主张企业必须在人权尽责流程中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应当承担不损害国家履行自身人权义务的能力的责任。但囿于国际公约约束的是国家而非私主体,法院援引了《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经合组织跨国企业指南》等国际软法对公司的人权义务进行了认定。《指导原则》所阐述的“国家保护义务”和“企业尊重责任”的范畴,也正日益成为国家和企业人权尽责义务的内在维度[41]。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将《指导原则》中的企业责任纳入国内侵权法体系中,不仅难以服众,也绕开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公司责任更加复杂的关节[40]。
(四)推动国际人权法体系的“绿化”
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危机亟待国际人权法体系开启“绿化”变革,以便让现有的人权法条款体现对气候变化人权危机和气候正义的关注与应对[42]。在具体“绿化”进程中存在两种途径:(1)“绿化”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为气候变化损害提供间接保护。这种路径在国际社会已存在,并取得广泛认可。(2)将气候变化救济人权转向的视野转到第三代人权(如环境权)。不仅可推动人权体系的“绿化”进程,还可起到真正维护环境的作用。但环境权由于争议颇多,其独立且实质性人权地位并未取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在此,可从健康环境权作为着手点,其作为人权法与环境法交叉的体现,对于维护人类尊严和克服生态危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其独立人权地位已获得联合国大会的认可。2021 年10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第48/13 号决议,首次正式宣布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权利是一项独立人权,并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合作落实这一权利。2022 年7 月,联合国大会首次正式承认,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普遍人权,并在法律中明确健康环境权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①具体包括清洁空气、安全气候、获得安全饮用水和适当卫生设施、健康和可持续生产的食物,无毒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环境以及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及以参与权为主的程序性权利,如获得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司法救助和有效补救等权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正式记录,A/HRC/43/53。。
事实上,作为第三代人权,健康环境权在气候变化损害救济中具有更明显的优势。第一,可巩固国家在气候变化下的人权义务,使其在人权机构中更清晰一致。以欧洲为例,当前欧洲人权法院气候变化损害索赔的依据是非环境权利,主要是《欧洲人权公约》第2 条(生命权)、第8 条(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以及第3 条(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环境权被其他非环境权利边缘化,造成了国家环境人权义务的不确定。而健康环境权的确定无疑会加强政府对环境与健康福祉的保护责任,同时也为法院在审理气候变化损害索赔案件提供合法性依据。第二,通过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义务来裁决国家对气候变化损害的责任相当复杂,健康环境权可简化证明过程。首先,可以缩短气候变化与侵犯人权之间的因果链条,如前所述,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受损之间,需要证明的是间接因果关系,而在健康环境权受到侵犯时证明的是直接因果关系,并将举证责任从原告转移到被告。其次,在第三代人权下国家的人权义务也得到减轻,仅需对向大气层释放过量温室气体的唯一事实负责。再次,因果关系的简化也有助于解决责任归属问题[1]。
四、结语
面对气候变化的双重打击——侵蚀生态系统和削弱复原力,人类生存和生态完整性都遭受到极致挑战。为塑造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国际社会自20 世纪80 年代将气候变化问题提上全球政治议程以来,一直将国际环境法作为主流应对措施予以推崇。但进入21 世纪后,在人权法语境下探寻应对气候变化损害救济途径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人权为基础应对气候变化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措施,但囿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累积性、全球性和代际性以及人权法本身在规范、结构和方法方面的制约,这种路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此情形下,若能摒弃环境法体系和人权法体系的二元论范式,构建一元论范式,将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就气候变化造成的典型财产和经济损失提出法律索赔,还可以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由此为国家和国际一级强有力、有效和可持续的气候应对政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