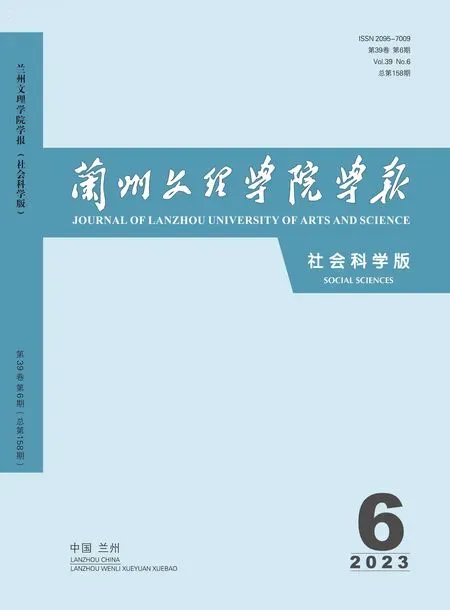空间·话语·认同: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文化指向
王 怡 飞,何 佳 仪
(1.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2.西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在时代主题呈现、叙事策略考量、平民话语转变以及情感认同建构等多层面都有着新的探寻。在主题呈现层面,尝试从时代视角审视历史,注重主题内涵与流行文化元素的融合,更多地将思想性与故事性兼容并蓄。在叙事策略层面,以艺术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新影像书写思路为导向,注重多个空间维度的描绘。在平民话语层面,利用小人物的小故事支撑起更加轻快的影片节奏,并融合喜剧元素为升华主旋律思想做铺垫。多样化的艺术形态相碰撞下,形成了符合时代潮流,满足受众期待视野的影片创作风格,并以此建构主旋律思想下的情感认同。
《我和我的家乡》是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国庆献礼片,该片讲述了五个不同的故事,在五位风格迥异导演的指导下,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又各有侧重。
宏大的叙事囊括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地域的多维度空间,以小人物小故事为切入口,展现脱贫攻坚背景下中国的社会风貌变化。故事主线紧紧围绕家国情怀与时代特征,将家与国的概念紧密相容,深刻表达了中国人的家国认同。通过平民化的小人物,小故事反应大时代背景,使得主旋律的宣扬变得更加亲民,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其主旋律的思想呈现不再刻板,并具有较强的电影叙事张力。符合当代受众的审美,是时代的真实写照,成功引起观众的共情。
一、空间叙事:时代主题的多维度呈现
《我和我的家乡》以家国情怀为主题思想,讲述了来自北京、贵州黔西南、浙江千岛湖、陕西毛乌素沙漠、东北乡村等五个地区的五个故事,着力表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各地区的社会风貌。整部电影的叙事框架以空间概念为核心分为存在空间、文本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在宽阔叙事空间内,通过不同的剧情、人物关系与导演风格将时代主题故事化,使主题思想融入进每一个单元的故事细节中。通过五个故事的书写,将脱贫攻坚这一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面呈现给观众,深入浅出而不显细碎,在小人物与小故事中反映出了时代主题。
(一)存在空间:视听呈现与时空交错
存在空间是一个背景和场所,它展现了事件的全貌,限定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1]。《我和我的家乡》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我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向观众呈现了幅员辽阔,地理风貌多元的中国。影片叙事紧紧围绕主题,通过视听语言建构叙事空间,将鲜活的生活场景带给观众。通过时间的流动,将历史与现实交织,表达时代的巨变。
影片的视听语言是存在空间建构的基础,在视觉层面,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地域的画卷:《北京好人》中胡同、故宫、天坛、长城、香山公园、鸟巢、水立方等在剧情场景中自然流出,亲切且寻常。《天上掉下个UFO》的取景地在贵州黔西南,山川秀丽,民风淳朴,依山而建的村落相续排列,茶山、木屋、路上行走的水牛、民族服饰等完善了场景细节布局。《回乡之路》中陕北土地上上演的故事是几十年来毛乌素沙漠的人沙斗争,如今人进沙退,荒漠变绿洲。《神笔马良》所呈现的是东北的乡村,以万亩稻田为画布,书写丰收的场景,歌颂时代美好。在听觉层面,苗族的歌舞、村落里的蝉鸣鸡叫、各地的方言是空间拓展的重要组成,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让空间话语变得生动。
其次,时空的交错将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交叉呈现,也是影片重要的叙事策略。在《最后一课》单元,当望溪村接到海外电话,开始筹措还原1992年的最后一节课时,在众人的话语中,拼凑出了这个村庄的沧桑巨变:曾经的猪圈现在成了望溪村的村委会;曾经夏天苍蝇闹灾,现在却连蚊子都难找一只;曾经村里都是露天的房子,现在的猪圈都是有顶单间。影片的最后,当范老师循着记忆里的道路去找寻当年的颜料,交叉蒙太奇剪辑手法下是破败与繁华的交织,现实与回忆的矛盾,也是这一方土地的巨大变化,时代的发展带给中国乡村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乡村再也不是那个贫困的山村,展现出了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果。
(二)文本空间:并置叙事下的小品化剧情
影片叙事的同时也是文本空间的生产,如果说存在空间所讨论的是影片包含的真实或虚构的背景或场所,那文本空间则是影片的内部形态的建构[2]。约瑟夫·弗兰克的著作《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具体阐述了文本空间的形态,并将其分为“并置”“重复”与“闪回”三种方式。
“并置”是一种“橘瓣式”的文本空间模式,是指构成影片文本的所有故事或剧情围绕同一主题或概念展开。各个故事之间没有具体的因果逻辑或时间顺序关联,以拼盘形态被串联,强化同一个主题[3]。《我和我的家乡》全程153分钟,分为五个单元进行讲述,每个故事平均只有半个小时。为了在半个小时的时长中将主题思想内涵与观众的审美指向都能照顾,每个单元故事都采用了小品化创作理念:成熟的IP+喜剧剧情+大团圆结局。这样的理念不需要太多的剧情铺垫,却能迅速让观众沉浸。同时,各单元之间的转场是影片串联的纽扣,通过无数网友用自拍的方式诉说对家乡的记忆,将原本小品化的故事情节拼接,同时完成与观众的一次互动,并与影片的平民话语转向的叙事策略相吻合。
可以说,小品化的剧情让影片富有喜剧色彩,而不同故事时空的交错增强了叙事的段落感,无形中建立了影片的文本空间。并置叙事的形态则会引导观众去思考故事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明确影片主题。
(三)社会空间:时代事件的影像投射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社会空间”的论述,认为社会空间蕴含着社会关系,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因而社会空间主要呈现形态是一种具有生产潜能的社会关系[4]。主旋律电影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关照革命历史题材或现实主义题材,反映平民生活与世情百态,在其叙事线索蕴含大量社会关系生产,亦可以说是社会空间建构。
首先,《我和我的家乡》的每一个单元故事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出处,是当下社会事件的隐喻。影片投射了普通人的生活梦想,农民工看病医保问题,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发展致富话题,乡村教育发展话题,陕北地区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东北乡村旅游经济等近年来的社会热点。其次,影片利用大量日常的社会生活符号建构社会空间,多次出现了手机、微信、直播等元素。《回乡之路》故事里闫飞燕的人物身份是电商主播;《天上掉下个UFO》的影片开头就是黄大宝在直播间催促粉丝刷礼物;《神笔马亮》剧情线索用视频通话进行串联。
可以说《我和我的家乡》的电影叙事建构,注入了诸多形态的时代社会关系与现实事件,打造出富有社会空间属性的电影叙事,其内涵意指是当下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特征,最终实现对电影主题的呈现。
二、平民叙事:小人物透视大社会背景
平民叙事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另一个话语转变方向,所谓平民叙事,就是以平民的视角为介入点,以平民为主角,重点书写平民身份,关照平民生活。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用较为写实的影片风格,以平民人物塑造为线索,贴近社会发展现状,讲述现实生活,反映了真实与自然的社会形态。影片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出自社会底层群体的小人物形象。从地缘阐释,覆盖我们国家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域;从职业来说有网约车司机、喜欢搞发明的村民、乡村教师、带货主播和乡村企业家、扶贫干部等。着眼平民生活,融合地缘、情感、血缘、家国等主题元素。这样的人物刻画,跳出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中人物脸谱化的局限,从而使得形象显得有张力与维度,用平凡人传递主流价值观,容易被观众所接受,鲜活且更具有价值。
(一)乔树林:平民英雄的形象反转
乔树林的人物塑造存在着深刻的形象反转:世俗与神圣,虚荣与无私,这样矛盾的形容词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示出了导演的功力和电影艺术的魅力,邓超的演绎更将这两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开头,夸张的演绎让乔树林的形象标签包含了油腻、虚荣与市井这样的关键词,而剧情最后对他热爱家乡、无私奉献的描绘却显得举重若轻,并不算浓墨重彩。这样的反转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一个虚荣且油腔滑调的中年大叔,背后却是带领家乡村民种植沙地苹果,努力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如此刻画的平民英雄将人的本性与对家乡的热爱糅合在一起,显得有血有肉,真实且生动:不平凡事的主角只是一个平凡人。而影片《回乡之路》的点睛之笔在结尾之处,当片尾出现治沙标兵张炳贵、牛玉琴、石光银、郭成旺、李守林、漆建中、张应龙以及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等真实人物的照片与姓名时,电影的虚构与现实相交织,瞬间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突出表达了平民书写历史的思想内涵。
(二)张北京:市井化小人物的塑造
张北京这个角色在《我和我的家乡》姊妹篇《我和我的祖国》中出现过,且深入人心。承袭前作,在《北京好人》中,张北京的形象拥有着明显的葛优式小人物的味道。一个梦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车的专车司机,在乡下的二舅因为肿瘤找上门来借钱时,想出了让二舅冒用医保卡这样的策略。他平凡而且普通,一身市井气息说明他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没有属于主角的光环。影片用曲折的情节表现了这样的人物性格:他舍不得将买车的钱借给二舅,又不想失去义气和面子,一系列乌龙事件过后,还是决定借钱给二舅。这样一个角色是感性的,是鲜活的,就像街边的大爷、楼下的邻居。但恰恰是最普通的角色塑造才会给人情感上的共鸣。北京好人真的是好人吗?一方面,张北京带着二舅冒用医保卡“唱双簧”,入院后又绞尽脑汁“越狱”,另一方面,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方法,放弃了买车的梦想帮助二舅。多个侧面的演绎让人物形塑具有了更多的维度,也将好人重新定义——好人也是平凡人。
(三)马亮:正能量人物的喜剧化演绎
以往的主旋律影片的正能量人物都是扁平式人物,所呈现的都是人物风光无限的一面,显得大而空。而《神笔马亮》中的马亮被演员沈腾赋予了不一样的平凡色彩,他怕老婆,为了掩盖自己没有到俄罗斯留学而是选择了下乡扶贫,联合全村人演了一场戏,制造自己正在留学的假象。整个故事看下来,被关注的重点就被放在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中,而马亮放弃留学机会而选择扶贫的这件大事反倒显得被忽视。但影片却用细节将角色的正能量渗透在一点一滴中,他帮助茴香村发展乡村旅游,完成稻田画,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栩栩如生的画卷。正能量人物往往会给人一种口号式的形象特征,过于扁平的设计在突出了正能量一个方面后,其他方面都显得相对薄弱了起来。情感是带领观众投入与引发共鸣的重要因素,马亮跟随着自己的情感选择了下乡扶贫,同时也跟随着自己情感的选择没有告诉妻子。喜剧方式的塑造让正能量人物真正的走下神坛,变得鲜活、生动,更能为观众所接受。
三、情感认同:集体记忆、仪式与喜剧化书写
莫里斯·哈布瓦赫将记忆置放于社会总体框架中进行分析,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他指出集体记忆是指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5]。电影将本属于个体空间对家乡和往昔记忆的回归,转化为群体空间对集体记忆的反思与建构,从而形成一种仪式化的视听场域,因而群体化仪式是集体记忆建构的温床。在费斯克的定义中,仪式被认为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形态,是参与主流社会文化建设与历史文本书写的手段,也是集体记忆建构的可行方案。《我和我的家乡》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用影像话语进行仪式场域的建立,以此唤醒观众对家国情怀的情感认同。
(一)情感认同的仪式呈现
纪念仪式是以重要节日、事件、人物为纪念对象,借助规范的仪式操演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来凝聚人心的一种活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个体归为群体。在《最后一课》单元中,剧情以范老师家中的画这一记忆符号引出,以复原最后一课这一仪式为线索,将家乡情感、师生情感贯穿始终。
影片开头,装饰画的特性镜头,表现了范老师对于支教生涯的难忘与思念。即便患病后,对于范老师来说,最重要的记忆仍然是执教生涯的最后一节课。从范老师再次回到那间被临时搭建起来的记忆空间时,故事的情感便开始逐渐升温。范老师对于每个同学的记忆,对于那节课的记忆,唤醒了场景里每一个角色的记忆与场外观众的心。在记忆被打破之后,范老师所表现出的绝望与无助更是让情感再度提升。在范老师出门去寻找记忆里的颜料时,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将现实与往昔交织,表现出了物是人非的迷茫。在片段的最后,曾经的学生小峰,把曾经的画变成了现实,展现在范老师眼前时,记忆照进现实,几十年的家乡变化早已沧海桑田,情感也随之走向最高峰。《最后一课》表达出了属于那个时代最朴素的社会追求,用人物细腻的感情写照推动故事发展,激起观众的共情。
(二)集体记忆的符号唤醒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里提到,个体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进行定位,而这种唤起、建构和定位记忆的文化框架即是记忆的社会框架。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往经历的怀念,也是个体在群体中身份的认同。主旋律电影中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是观众群体意识的投射,是群体精神的呈现。当电影剧情与观众经历产生情感共鸣时,其内涵的情感认同自然也会产生共鸣。《我和我的家乡》五个单元的剧情围绕家乡两个字并置,以空间为叙事核心,以地域为背景,将有着相似境遇、经历或身份的人群的共同记忆唤醒,家乡就是其共同记忆的焦点。从小故事透视大主题,在每一个个体对家乡的记忆和守望中,呈现给观众的是时代的巨变和对家国的认同。
《回乡之路》的记忆建构依托于“回乡”这一时空。围绕着“回乡”,有着共同记忆的一群人聚在车内,故事依托闫飞燕和乔树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境遇来推动情节,将对家乡的情感认同贯穿在回乡路上的细节中:话语间家乡的美食、口中的方言、共同怀念的人物都是唤醒记忆的符号。其中对于人物高妈妈的描述展现了从乡村中走出去的孩子对于家乡如母亲般的眷恋,也是影片记忆建构的焦点,当闫飞燕不顾劝阻,徒步艰难的走上一处土坡,在高妈妈的坟前热泪盈眶时,可以真正地展现出一个再次回到妈妈怀抱的孩子形象。在影片的几次插叙中,黑白的画面将记忆闪回曾经风沙漫天的毛乌素荒漠,讲述了闫飞燕和乔树林不同的奋斗历程,也讲述了陕北毛乌素荒漠人们为了家乡建设而艰苦奋斗的那段记忆,透视出时代的沧桑巨变。
(三)主旋律题材的喜剧化书写
早期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给观众的印象多为人物脸谱化、剧情套路化、并且带有刻板与乏味的标签。如何在主旋律思想谱写和满足观众的娱乐、审美、情感需求的两个目标之间平衡取舍,达到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和谐共生,发挥电影艺术的文化宣教功能是电影艺术家们重点探索的方向。
神笔马亮单元是对脱贫攻坚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描写,用喜剧化的手法将扶贫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表现和颂扬,对脱贫后的乡村风貌进行了展现,其最深刻的艺术内涵在于小人物对于家国情怀的坚守。本可以去俄罗斯留学的马亮瞒着妻子投入了脱贫攻坚的工作当中,其身份形态从艺术家被重新定义为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马亮作为一个小人物是有血有肉的,既害怕又时刻牵挂着怀着孕的妻子,而自己又要瞒着老婆投身脱贫事业。这样的驻村干部在整个脱贫攻坚时期有无数个,反差强烈的戏剧矛盾推动着剧情,喜剧的外衣让原本严肃故事的原型变得荒诞与可笑,笑声背后是观众对于这样千千万万扶贫干部工作的认可和赞扬,正是这样一个个的小人物,舍小家为大家,书写着这个时代的家国情怀。而这样书写方式兼顾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喜剧的姿态引发了人民群众对家国情怀的思考与认同。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曾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6]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和我的家乡》是主旋律电影话语转向的集中体现,是主旋律电影向着亲民化改变的一个巨大进程,通过以小故事表现大主题的主题呈现,生动地折射时代发展的面貌,用小人物刻画人物群像,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找到归属与认同,最终建立影片与观众的情感认同,将国与家这两个概念完美融合。同时主动地寻找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品味的融合,通过全明星阵容的演绎,融合流行文化元素,引导着当道主旋律电影朝着新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