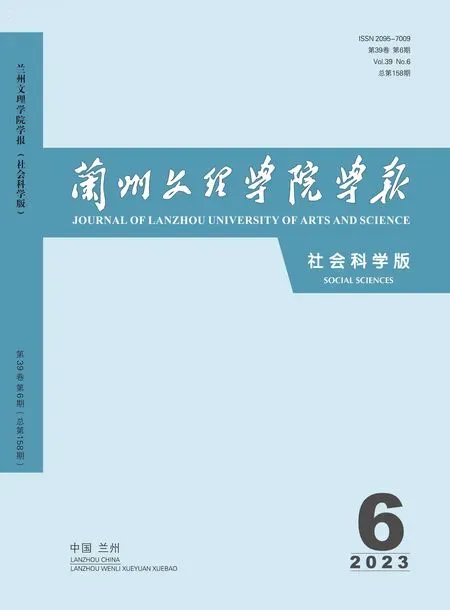文学的信念和批评家的坚持
——孟繁华先生的当下文学现场研究
张 维 阳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4)
一直站在批评最前沿的孟繁华先生,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始终致力于当下文学的现场与“新世纪文学”相关的研究。他投身于文学现场,关注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思潮的研究与评价。迄今为止,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三本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论著中,它们分别是《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现场》和《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与作品》。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孟繁华先生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基本态度,也可以了解“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成果和发展走向。
一、消费主义浪潮中的文化抵抗
对于“新世纪文学”这个正在生发中的概念,学界对其的讨论和阐述远没有充分,学者对它的内涵和特征还没有形成共识,它的边界尚不清晰,关于这个概念,尚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有关“新世纪文学”的一些方面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这一概念是针对过去的,它是对新文学启蒙传统的反思与超越,是对“新时期文学”这个模糊概念的清理和确认,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接续与呼应,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规避和对文学性的张扬。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是直面当下和面向未来的,这一概念是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语境中被提出的,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概念要处理的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文学和本土文化资源的关系问题。作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全球化是西方世界主导的一次“单边行动”,它不仅带来了西方经济体制的全球性散布,也意味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世界性蔓延。被这种强势文化扫荡过后,地方的文化被所谓的世界性的文化所淹没和覆盖。这种强势文化的覆盖不会带来地方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只会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一片片的文化焦土。吉登斯曾对此有过论述:“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1]而且,在文化渗透的背后还隐含着西方世界对于经济和政治的诉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输出的背后必然伴随其对市场和资源的觊觎。葛兰西于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创建性地提出文化的政治功能。他认为文化霸权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统治阶级统治市民社会,必然借助知识分子与文化机构传播和宣导其伦理观念和文化价值,使之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行为方式,使被统治者“自由”和“自愿”地服从统治者的意愿,统治者的宣导和被统治者的认同共同构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葛兰西揭示了文化的政治属性,为当代西方学界的文化批判思潮奠定了基础。萨义德继承了葛兰西对文化政治的思考,将这种思考延伸至国际领域。一开始他借助福柯的方法,从话语的角度揭示政治与“东方主义”的密切关系,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来描述和分析,后来他将研究的范围由中东扩展到了世界,关注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强势文化的传播是帝国主义延伸其统治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2]孟繁华先生敏感于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压迫和渗透,他深知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和冲击,他承袭了葛兰西和萨义德的文化批判理路,站在本土的立场,以激情洋溢的笔触给西方文化霸权的弥漫以最有力的回击。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他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中产阶级趣味的蔓延是当前中国遭遇的严重的文化危机,他对于中产阶级趣味的批判,可视为他对新世纪文学“文学场”的清理。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生活的合法性随之确立,随着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进步,一种新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将“人民”和“群众”置换成了“消费者”,市场以诱惑的方式对消费者和民众进行驯化。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与政治的关系被人和物的关系替代,公平正义的政治愿景被舒适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所替代,人从大历史中出走,步入了自己的小生活。孟繁华先生认为,媒体对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3]和《媒体与文学的时尚化》[3]370~379这两篇文章中,他详述了媒体诱发和散布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以及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90年代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运动”,这之后出现了时尚化的杂志,这些杂志表达和制造着中产阶级的趣味,构成了中产阶级的话语空间。这种中产阶级趣味的魅力和导向作用是明显的,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在短时间内被大面积传播,并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同,这种趋势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因此他判断:“这些中产阶级杂志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支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3]372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它不仅扫荡了网络文学,严肃文学也受到了它的冲击和侵蚀,不仅出现了严肃作家向时尚文化的献媚,甚至出现了文学思潮向时尚话语的转向。面对这种危险的趋势,孟繁华先生大声疾呼:“文学关心的不是市场,文学关心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的心灵领域,现在这个领域已经不大被关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内心总要遇到危机,总要寻找心灵安放的地方,这就是心灵家园。心灵不能总在流浪。文学恰恰是能够提供心灵、理想安放的家园的。”[3]377孟繁华先生意在痛斥文学的时尚化与市场化倾向,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正本清源,明确文学的方向,守护文学的尊严。为了抗拒这种中产阶级化或者时尚化的写作倾向,孟繁华先生力倡“新人民性”文学,他在《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3]176~182中对“新人民性”作了如下的解释:“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显然,孟繁华先生在提倡文学介入性的同时也强调警惕“人民性”概念中的民粹意识,从而强调文学的批判作用,“新人民性”的命名表明了其在继承中国“社会问题小说”传统和来自俄国文学的“人民性”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五四”文学的批判传统,是对不断建构和丰富的中国文学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之后被命名为“底层文学”的创作思潮俨然受到了“新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影响,其突出的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意识使文学又一次与当下生活建立起了联系,从而备受公众的瞩目。
二、面对文化霸权的本土立场
很多人将西方文化视作是18世纪以来所推进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因此将其视作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模式加以推崇甚至膜拜,然而亨廷顿明确地指出:“现代化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4]也就是说,亨廷顿认为完全可以在保留民族文化自足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吉登斯在谈论全球化时指出:“现代性,就其全球化倾向而论,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吗?非也。他不可能是西化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性意识。”[1]153但是,如何在避免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保存本土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性文化转型,就成了摆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面前的严峻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孟繁华先生就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目前国际文化处境的时候,我们深感第三世界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异化的威胁……对我们来说,多年来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大量真空地带需要填补,无论是理论还是娱乐的,第一世界文化的涌入是不可阻挡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经过自己的整合、吸收、批判之后用于发展建构自己的本土文化,以新的、开放的、自由的创造精神焕发出本土的光彩并赋予其现代意义,使其重新获得生命力提供给整个世界。”[5]当时他只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孟繁华先生始终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来到新的世纪,就这一问题,孟繁华先生给出了具体的方案,那就是:守护“民族性”。关于什么是“民族性”,他是这样定性的:“只有与传统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确定我们的文化身份,这就是民族性。在过去的理论表达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才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民族的,才能够保证国家文化安全而抵制强势文化的覆盖和同化。”[3]144孟繁华先生认为,只有守护我们的“民族性”才能确证我们的文化身份,才能突出中华文明相对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和独特性,他站在中国本土的立场,以激情洋溢的声音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力图让中国和西方形成对话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具体到批评实践当中,要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守护我们的“民族性”?孟繁华先生的做法是深入作品文本,发现其中的“中国经验”。对“中国经验”的提取、归纳和积累就是对“民族性”的物质确证,对“中国经验”的开掘和发现是孟繁华先生采用的批判西方强势文化的批评策略。
对“中国经验”的重视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推崇西方趣味倾向的矫正,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然而,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背后,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当中国的几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已经发展到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城市比肩的同时,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滞留在缓慢而安静的前现代的乡村秩序当中。自“五四”文学就开始关注的那个中国传统的乡村世界并没有消失。即使是那些走出乡村,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源自乡土社会的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支配着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所以乡村无论在社会的意义上还是文化的意义上,都应该是文学研究者和文化学者持续关注的对象。孟繁华先生深谙乡村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密切关注那些描写乡村生活、表达乡土经验的作品,注视着其变异与动向,从中发现了不少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在《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6]一文中,孟繁华先生先是厘清了“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和“新乡土文学”这三个概念,之后归纳了在“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中国作家在书写农村时,其文学观念和塑造人物性格等方面的变化,以此来探寻新世纪文学农村书写的特征和走向。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孟繁华先生认为“新乡土文学”割去了“农村题材”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打破了民粹主义的乌托邦,在文学精神上接续“乡土文学”,继续深挖国民性,剖视国民的深层文化结构,揭示了国民内心深处对权力的痴迷和对暴力的热衷,呈现了革命未能改变的人的冷漠、孤独和无助的现实境况。在《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世纪初长篇小说乡村文化的多重性》[3]41~53一文中,孟繁华先生通过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解读发现了乡村文明的危机,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失衡造成了乡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割裂,作品中呈现的城乡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前现代”与现代冲突的表征。而乡村文明的危机又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整体危机的一个侧面,文学对这种合目的性的现代性发展路径与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心理抵牾的表现,隐含了中国社会复杂和曲折的发展历程,从而具有了民族精神史和文化史的意义。在《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3]64~81中,孟繁华先生归纳了新世纪文学讲述乡村故事的叙事方式。首先他发现了对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的瓦解已成为普遍态势,这之后,作家讲述乡村的故事多采用碎片化的书写方式,在这样的讲述中,日常的叙事取代了宏大叙事,对生活片段的书写取代了对整体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的呈现,琐碎无聊的庸常生活取代了总体性的历史进程,通过这样的讲述,作家呈现了乡村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尖锐对立,表达了其对当下乡村现代性发展的反思和困惑。除此之外,孟繁华先生指出,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也有人拒绝对乡村进行碎片化的书写,而致力于对乡村中国“整体性”叙事的重建。他以周大新和关仁山为例,通过对其文本的精到分析,认为他们虽然明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但当下乡村的变革所透露出的微亮曙光使他们对于中国乡村的未来满怀渴望与期待。在文章中,孟繁华先生还总结了新世纪文学中作家对乡村的第三种叙事态度,那就是在“溃败”和重建之间的犹豫不决。他以贾平凹的《高兴》和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为对象,指出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在被迫由乡村进入城市后,并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无关紧要的配角,是遭到城市冷遇的一群尴尬边缘人。他们即使重返故乡,也必然带回在城里留下的酸涩与伤痛,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只可追忆而难能经验,他们无处安身,更无法安置自己的心灵,漫无边际的困惑和迷茫笼着他们,让他们孤独而无助。孟繁华先生认为,作品中人物在城乡之间的尴尬处境和无辜无助隐约地透露着作家们迟疑矛盾、犹豫不决的创作心理,更表达着他们对当下乡村变革方式的彷徨和踟蹰。由此他认为,作家书写中国的乡村,对当下乡村变革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不同叙述方式的选择,现实的复杂性导致了作家观念的分化,迥异的逻辑和思想作用于写作,导致了不同的乡村书写的形成,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共同构成有关乡村的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经验。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导致了乡村文明的溃败。在《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3]219~235中,孟繁华先生通过文化研究和对当代文学文本的解读,勾勒出了这一历史情境的样貌。他同时指出,乡村文明崩溃之后是新的文明的崛起,对这种由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转型的文学叙述,是孟繁华先生着意发现的中国经验。由于这一变化的切近,他没有急于对其进行命名,他认为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还没建构起来,属于这种文明形态的新的文学也尚在孕育之中,只有通过都市文化经验的建构,才能促成都市文学的发展。而由谁来通过作品建构新的都市文化经验?孟繁华先生认为从80年代至今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50后”作家难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他们过于珍惜来之不易的成就,在写作中为了“安全”的考虑而固守过去的“乡土中国”,刻意回避面对新的现实,他们的谨小慎微让他们丧失了表达新的现实和新的精神问题的能力和愿望。而在这一方面,“60后”与“70后”作家却表现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时代感与批判意识让人感到了建构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的可能。
社会的形态决定了文学的面貌与发展走向,乡土文明的溃败必然导致文学关注的焦点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孟繁华先生自然地将关注的目光从新乡土文学延伸至中国的城市文学。他认为这个正在生发和成长中的文学样态还很不成熟,作家对都市生活经验的表达还处在艰难的探索期,表现在作品数量上的创作的繁荣难以掩盖其反映都市生活还处在表面上的事实,都市生活的深层经验还有待挖掘。在《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3]236~251这篇文章中,孟繁华先生指出了新世纪文学中存在的几个对都市书写的问题,既是对城市文学写作的鞭策,也是对城市文学新的增长点和生长空间的探索和想象。问题之一是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作家往往接续“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理路,致力于反映文化转型期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而忽略了对于具有“共名性”的文学人物的塑造,孟繁华先生希望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不要成为作家塑造典型人物的障碍,作家应该在杂乱而丰富的现实中发现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所共同面对的精神问题,以此来创造出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能让人们记住的文学人物。其二,他认为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没有青春。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开始,具有丰沛的生长力量的朝气蓬勃的少年形象逐渐被国人确立为想象中国的标准范式。“五四”时期,革命风潮中的社会和文学将对少年的想象化作了对青年的呼唤。“十七年文学”和80年代的文学虽然源自不同思想资源的规训和指导,但它们对于青年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在不同的时代,青年都被作为一种新生的具备无限的创造力和可能性的力量而备受关注,但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青年形象消失了。方方笔下的那个备受关注的形象涂自强,面对失落的爱情他没有痛苦,面对不公的命运他没有愤怒和咆哮,他以无可奈何的淡定从容接受了命运强加给他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他是一个有着中年心态的年轻人。激情、绝望、痛苦与迷茫,这些文学所表达的基本的情感方式都与青年有关,文学遗忘青年就是遗忘文学自身,孟繁华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方方作品的解读阐述了文学关注青春的重要,因为“一个没有青春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此外,他还在文章中揭示了新世纪的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孟繁华先生认为,文学是虚构艺术,生活现实是文学的必要素材,但文学追求的是想象力的卓越展现,当下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刺入生活的表层,探究生活的肌理,关于时代文化的深层结构应该是文学表现的对象,但目前的城市文学所呈现出的非虚构性质和报告文学特征表明其距离这一目标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新世纪的城市文学虽然有如此种种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孟繁华先生并没有表现出失望或者愤怒,他像关爱一个孩子一样呵护它的成长,他相信城市文学目前虽然步履蹒跚,但一定会顽强地生长,他虽然不确定城市文学未来成熟时的样态,但他坚信它代表着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方向,它将创造出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中国经验”。
三、地方文化景观的开掘与呈现
为了避免被“世界文化”吞噬,“地方文化”必须突显自身的异质性和独特性,这样在遭遇具有所谓“普遍性”的文化时,才能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获得生存的空间。中国在西方建构的世界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种特殊性正是由“中国经验”而逐步体现和揭示出来。然而,中国在面对西方时,在文化的意义上是一个整体,但进入它的内部,其辽阔的疆域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多种的文化类型,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在现代性目的论的规约下,这些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被隐藏或者遮蔽了,但随着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时代的到来,总体性不复存在,隐匿的地域文化又显露出了其独特的价值。这些地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拼图被打捞和发现,成为新世纪以来独特的文化景观。为了表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孟繁华先生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在文学的视域内,发现独特的地方文化经验。
中国西部的高山大河与大漠幽谷曾经见证了大秦帝国往日恢弘的气魄和不朽的荣耀,这里的冰川雪原和遍地的格桑花目睹着圣洁藏地的纯粹透明和清澈悠远,这里隐藏着中华文明绚烂辉煌的过去,也存留着宗教文明的奇异和神秘。对于西部文化资源的发现无疑是对“中国经验”的填充和丰富,孟繁华先生始终关注着中国这片辽阔而雄浑的疆域,他在文学的领域,用批评的方式,观察当下文学对西部文化的继承和拓新。《西部文学的气魄和力量》[7]就是这样一篇论述西部文学经验的文章。在文章中,孟繁华先生通过对书写西部文本的解读,揭示了新世纪文学对西部气象的传承方式,以及其对雪域高原这个宁静祥和的神秘世界的表现方式。《大秦帝国》是一部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孟繁华先生肯定了作者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认为在消费市场的推动下,当下很多历史小说肆意漫话和戏说历史,在满足读者阅读欲望、营造阅读快感的同时消费了文学也消费了历史,历史在这些肆无忌惮的扭曲和曲解中变成了一个混沌不清的不明之物。而《大秦帝国》的作者以其严肃的历史观念和对秦帝国历史的细致研究,以想象的方式复现了秦帝国时代的历史场景,“为我们重塑了那个遥远而又心向往之的大时代”。在这里,孟繁华先生着重强调了作者孙皓晖的“大秦史观”的特殊价值,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叙述而被建构起来的,而作为叙述的主体,他的历史观会直接影响历史叙述的形成。作者开宗明义地宣布:“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事实上,这不是关于中国文明源头的新论,而是表明了一种以中国西部为中心的历史视点的确立,在这种史观的观照下,中国的西北不再是遥远的塞外边地,而中国文明的源头,更是历史的起点。姑且不论这种史观的学理依据或是科学性,这种史观所表露出的丰沛的自信和惊人的胆魄正是对自秦帝国开始的雄浑的西部气象的最显露的继承。在文章中,孟繁华先生还分析了两个关于藏地的文本,一个是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一个是范稳的《水乳大地》。他认为这两部小说以不同的方式构筑了一片澄澈透明而又神秘奇异的冰雪圣域。前者描写的人物,在物质欲望的裹挟下遭遇了深重的情感危机和精神危机,她们进入藏地后发现了另一种人生,满载着青春、理想和热血的藏地官兵让她们见识了一种单纯而不贫瘠,安静而不寥落的人生,正是这片神秘的世界赋予了他们这种明净的生命形式。她们的藏地旅程让她们的精神受到了雪域高原的洗礼,让她们的灵魂得以涅槃。而后者以复杂的故事和众多的人物,表现了滇藏交界处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和冲突。在这片土地上,不同信仰的揪斗以及世俗利益的渗透使这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但最后信仰战胜了欲望,宽容战胜了狭隘,范稳以想象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复杂而艰难的命题,凸显了这片信仰高于一切精神圣地的神圣和伟大。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论述美国当代文化时指出,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和消费意识的蔓延,新教伦理这种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被享乐主义所取代,而清教精神被消费欲望所置换,他认为如此的社会环境促成了新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他称之为“时尚和时髦的庸俗统治”,而关于时尚的本质,他认为是“将文化浅薄化”。他将改善这种文化环境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意识到探索世界有其界限的那种文化,会在某个时刻回到彰显神圣的努力中”[8]。贝尔的分析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着借鉴意义。孟繁华先生对于新世纪小说中宗教特征的开掘与分析似乎是对贝尔理论的隔空呼应,但孟繁华先生并没有将宗教作为挽救世风的精神寄托,而是将小说描写的宗教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他者和镜像,映照现实世界的不堪,为重建一个高扬正义、心存敬畏、追求高尚的文化环境寻找可能。
孟繁华先生以十余年之工关注和研究新世纪文学,可见他对新世纪文学的重视,然而,10年对于新世纪文学来说还只是开始,它必将以不确定的方式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孟繁华先生会一如既往地注目、勘探新世纪文学的动向,为学界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与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