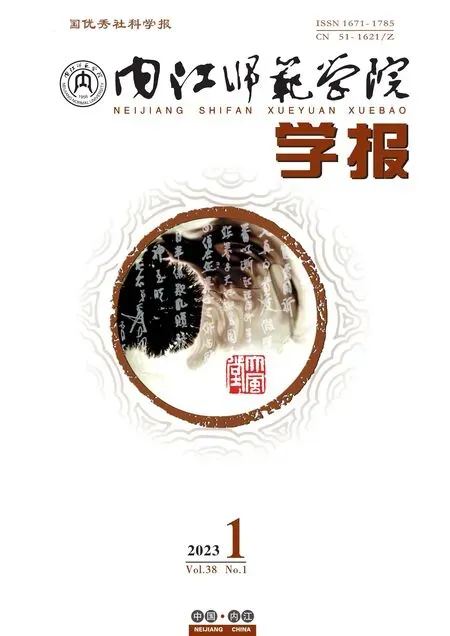不可能事物喻与矛盾修辞格: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的细部展开
明 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一、“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的提出与界定
“艺术准不可能世界”(The quasi-impossible world of art)是“可能世界理论”(possible worlds theory)范围之内的新推演。在《广义叙述学》一书中,赵毅衡先生[1]176-178认为,源起于哲学、逻辑学、语言学领域的“可能世界理论”,或许能理清文学艺术虚构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解决几千年来模仿论、反映论、或然论、形式论等文艺理论都未能攻克的难题,甚至能更进一步明确纪实性与虚构性叙述的本质区别。但是,如果要应用“可能世界理论”于文学艺术,则必须把握文学艺术特有的品格。
因此,不同于神学领域18世纪《神正论》中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说,不同于分析哲学家刘易斯等人用来解决语义逻辑学问题的可能世界理论,甚至也不同于符号学家艾柯对可能世界理论的应用,《广义叙述学》中讨论的可能世界理论,展现出新的面貌,“以人文化的方式来理解”[1]178和推进,并且揭示此理论与叙述学之间的联系,解释叙述文本如何能够在实在、可能与不可能世界之间穿梭,这种跨界旅行又为文本自身带来了怎样的风格倾向。
所以,在认识“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理论时,需要关注三个要点,一是“艺术准不可能世界”自身的定义,二是“准不可能”的“准”何谓?三是跳出逻辑的讨论,看到艺术可能世界的跨界通达性及其对艺术本身的影响。
不同于实在世界和逻辑可能世界,艺术准不可能世界“可以分成各种相对异常的反常识世界,以及绝对的逻辑不可能世界。它们构成了一个‘准不可能’连续带,其种类之多,很难清晰地分类描述。可以说,各种不可能实为艺术文本的特有品格”[2]8,因为艺术的品格依循的不是现实逻辑,而是意识想象。“任何艺术再现的世界,都有强烈主体性,都以意识的强大的想象力为基础。这里不仅是指再现主体(艺术家)的创造想象力,也指艺术接受者的解释想象力”[2]7。想象力带来的“准不可能性”在艺术文本中占有大片领地,这也是讨论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在。
艺术准不可能世界可划分为“相对异常的反常识世界”以及“绝对的逻辑不可能世界”两部分,对应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做的“事物之不可能”(physical impossibility)和“名理之不可能”(logical impossibility)的二分[3]605,前者主要指违反常识、分类和历史的物理和心理之不可能,而后者则是违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逻辑之不可能。前者可以对应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列出的西方古修辞学之“不可能事物喻”(adynata, impossibilia)[4]19,后者可以对应《管锥编》卷二,《老子王弼注》中阐释“正言若反”时所用的概念——“冤亲词”(oxymoron)[3]463,即修辞学中的“矛盾修辞格”。
从这两种修辞格切入艺术准不可能世界,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合集可以大部分覆盖我们所讨论的“准不可能”的范围;另一原因是,修辞格能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围绕文学艺术进行讨论,不偏不倚,遵循从人文角度进行推演这一路径。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清晰且“人文”地从细节着手,展开整个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的无边地图。
二、不可能事物喻中的各种“事物之不可能”
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钱锺书论及南宗画创始人《卧雪图》“雪中芭蕉”一景,引金农《冬雪集拾遗》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王维画中的“禅”,言:“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飚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王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4]19钱锺书认为,金农虽然感受到了王维画与禅的联系,但他并不熟悉“禅理”,不知道禅宗“有一类形容‘不可思议’的‘话头’……类似西方古修辞学所谓‘不可能事物喻’(adynata, impossibilia)。例如‘山上有鲤鱼,海底有蓬尘’、‘腊月莲花’、‘昼入祗陀之苑,皓月当天。夜登灵鹫之峰,太阳溢目。乌鸦似雪,孤雁成群’,……假如雪中芭蕉含蕴什么‘禅理’,那无非像海底尘、腊月或火中莲等等,暗示‘希有’或‘不可思议’”[4]19。
相似的例子也出现在《管锥编》中,钱先生论《九歌》,指出《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池无薜荔,山无芙蓉”;《湘夫人》“鸟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鸟当集木,罾当在水”“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麋当在山林而在庭中,蛟当在深渊而在水涯”等等,都指向“蝉翼为重,千钧为轻”这样颠倒世界、违背常理的“不可能之怪事”[3]601。就《九歌》的文本而言,处于错误之地点的麋鹿和蛟龙,寓意小人当在野却入庭,贤能当居尊却为仆。这些与禅宗的非逻辑语相似,“日出当中夜,花开值九秋”“木鸡啼子夜,刍狗吠天明”[3]604等“话头”,不追求语句的明白晓畅,而在于打破、违反常规逻辑,在极端的思维张力中,走向修辞背后的思想目的,开启听话人的悟性,达到“非理性的禅体验思维状态”[5]92,重点不在于字面呈现出的意思,而在于这种话语和思维方式本身,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这样说”和“怎么说”。

Adynaton,古希腊罗马诗歌中多有出现,在《希腊和拉丁诗歌中的adynaton形象》(Figure ΑΔYΝΑΤΟΝ in Greek and Latin Poetry)一文中,坎特分类了近二百个例子,对此修辞格进行了简短而系统的研究[6]。而在早于坎特研究,但晚于坎特发表的《古代诗歌中的adynaton主题》(LethèmedeI'adynatondanslapoèsieantique)一书中,厄内斯特则按时间顺序讨论例子的语境、阐明诗人的特点,并在索引中将所有希腊拉丁诗歌中的adynaton归入13个类别。厄内斯特认为,“诗人为了表现一个不可能的、荒谬的或不可信的事实或行为,把它与一个或多个自然不可能联系起来。”②[7]ix如普罗佩提乌斯挽歌集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段落:
在麦田里肆虐的大火被迅速扑灭
flamma per incensas citius sedetur aristas
河流也回到它的源头
fluminaque ad fontis sint reditura caput,
凶险的塞利特斯滩为水手提供平静的港口
et placidum Syrtes portum et bona litora nautis
野蛮的马莱亚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海岸③[8]311
praebeat hospitio saeva Malea suo(Elegies, III, 19, 5-8)
我现在把手放在神坛上,我请我俩之间的圣火和神祇给我做见证:
Tango aras, medios ignis et numina testor: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意大利各族的和平和联盟不许破坏
nulla dies pacem hanc Italis nec foedera rumpet,
绝不让这样一天到来;任何力量,它可以用汪洋波涛淹没大地
quo res cumque cadent; nec me vis ulla volentem
把大地埋葬在洪水里,让苍天解体落入地狱,但不能改变我的意志[9]330-331
avertet, non, si tellurem effundat in undas
diluvio miscens caelumque in Tartara solvat (Aeneid, XII,201-205)
这种修辞格常常是为了营造一种荒谬感,体现自然力量的反向运作,或表现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事情。河流逆流而上,敌人结为伴侣,树木结出奇异的果实等等。因此,虽然在史诗(epic)、抒情诗(lyric)和讽刺诗(satire)这些较为严肃正统的文体中也能见到adynaton的影子,但其在乡村诗(bucolic)、挽歌(elegiac)和戏剧诗(dramatic poetry)中更为常见,体现出一种传统性和谚语性,故adynaton常常被认为包含在谚语(proverb)之中。而罗韦[10]392认为,虽然大多数adynaton可以追溯到寓言、童话、魔术、神谕、奇迹等民间主题,但许多adynaton存在于谚语集之外,adynaton并不等同于谚语。
adynaton其实仍是“尚有可能的不可能”,即艺术“准不可能”中的事实、物理、心理的不可能。“雪中芭蕉”看似不可能,在如今科技发达的年代却不一定不可能,即使身处热带雨林地区,高海拔的山顶也会有积雪,只需用直升机把山脚下的芭蕉运上去即可。如果发生了地理条件改变,或人工干预修建了工程,凶险的塞利特斯滩也真的能够“为水手提供平静的港口”;相对于普罗佩提乌斯所处的时代,麦田里的大火在现代社会也能够相对较快地被扑灭;沧海桑田,大地也的确会被“埋葬在洪水里”,等等。这反映出反常识的世界从某种意义来说依然“有可能”,它们所违反的常识是目前我们能够触及到的知识边界,反常识世界并不是逻辑不可能,也许只是尚未被实现出来或尚未被发现的可能世界。
“雪中芭蕉”可以代表禅宗那些种种不可思议的格外谈,它们常常是超乎理性和言说的,井底尘、山中浪、火中莲,难以被经验世界的理性解释。但这就是“道”之所在,格外谈和adynaton能够在艺术的想象边界内带来一种具象体验,并将抽象的含义蕴含其中。超出理性认识能力的是“不可思”,超出语言表达范围的是“不可说”。荒谬与真理冲突,但荒谬不与信仰冲突,甚至“因为荒谬,所以信仰”(Credo quia absurdum est)。苏格拉底用哲学家的方式是无法证明神的存在的,这是宗教与哲学理性抵牾之处,但却恰恰是证明宗教虔信程度之处,否则也不需要强调“信望爱”中“信”(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的重要性。同时,这些“不可思议”,也是艺术的拿手好戏。
三、矛盾修辞格中的“名理之不可能”
oxymoron有其“宗教性”或“思想性”,并不仅仅被用来为诗歌添彩,在思想性更强的著作中,oxymoron能起到一般的表述无法达到的效果。如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一九论“正言若反”:
夫“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五千言》中触处弥望,即修词所谓“翻案语”(paradox)与“冤亲词”(oxymoron),固神秘家之句势语式耳。翻案语中则违者谐而反者合矣,故四五章云:“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复有两言于此,一正一负,世人皆以为相仇相克,例如“上”与“不”,冤亲词乃和解而无间焉,故三八章云:“上德不德”。此皆苏辙所谓“合道而反俗也”。[3]463-464
Oxymoron,代表了绝对的不可能,即艺术“准不可能”中的逻辑的不可能。逻辑不可能在实在世界中是绝对的,违反基本逻辑规律,触及实在世界的基本运行原则,而不仅仅是实在世界的存在物的问题。一个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薛定谔的猫在盒子里时既死又生,但一旦打开盒子,它便被实在世界的氧气包裹,在实在世界中揭示它的存在状态,猫就能且只能表现为死或生中的一种。虚构世界中,却可以存在既是又不是的事物,冷的火、方的圆、白昼般的黑夜……叙述者描述出这些事物,虽然以我们的实在世界经验,想象不出它的样貌和它带给人的感觉,但我们知道它切实存在于那个被叙述出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异于一般表述的悖论话语,则可以达到一种“辩证的”智慧境界。而若脱离“思想性”,仅从文学艺术的特性出发,oxymoron使绝对不可能在艺术之中成为可能,在极大的张力中无限地拓宽了艺术所能蔓延的边界。
四、艺术“准不可能”之“准”的限定
“准不可能”的“准”何谓?反常识的事物充满艺术的世界,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讲述春梦婆时涉及的种种想象:手指只有玛瑙那么大,蚂蚁拉着马车,挽索是如水的月光,车子是榛子壳……[12]101反常识的事物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拥有所有民族的童话、传说中都会有的那种炫目奇幻的色彩,异于现实经验世界,却构造出一个出色的艺术想象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可能的不可能”,艺术世界是锻炼我们想象力的体操场,在那里,我们脱离地球的引力,任自由的精神漂游。而在实在世界中的处于绝对位置的逻辑不可能,在文本之中也依然有可能,甚至形成了一个定型的修辞格、自成一派。
所以对于文学艺术,甚至对于某些哲学思想来说,任何“不可能”都是“quasi-impossible” ——“准不可能”。如果不以“准”进行限定,那么事实不可能和逻辑不可能无论在经验世界还是在艺术世界,都是绝对不可能。“准”的限定,对于实在世界来说,使事实不可能仍然有可能,对于艺术世界来说,使事实和逻辑不可能都成为可能。
艺术准不可能世界,融合了“反常识世界”(物理、事实、心理)和“逻辑不可能世界”。反常识的世界从某种意义来说依然“有可能”,它们所反的常识是目前我们能够触及到的知识边界,反常识世界并不是逻辑不可能,也许只是尚未被实现出来或尚未被发现的可能世界。逻辑不可能在实在世界中是绝对的,违反基本逻辑规律,触及实在世界的基本运行原则,而不仅仅是实在世界的存在物的问题。在实在世界中,不存在“光明的黑夜”“邪恶的圣人”“方的圆”“既死又活的人”“既在又不在的事物”,因为内在于前后二者的本质属性是相反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这个世界勾勒为“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而是事物不能同时既是又不是。
艺术的准不可能世界,看似“非理性”与“无意义”,虽不与经验世界的现实逻辑契合,但却与艺术本身的想象意识自洽。想象力是无边界的,不能且不应总囿于实在世界或逻辑可能世界,如果艺术真的进行自我局限,那么也就不是“艺术”。艺术家是且必须是天马行空的,永远不畏惧越界、挑战常识,对所有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充满好奇心,而不是在自己意识所能照亮的一隅实在世界中昏昏欲睡,必须像法厄同一样敢于要求驾驶阿波罗的马车,即使无力操纵,但他已经具有成为艺术家的潜力。在犯框越界的探索欲望这一层面上,艺术家与科学家殊途同归。
艺术的准不可能世界,漂游在逻辑和艺术之间,事实、物理、心理、逻辑的不可能,在艺术世界中都会出现,且出现得很频繁。就文学作品而言,其中很多“准不可能”已经成为我们习焉不察的谚语,或者见怪不怪的修辞。艺术天马行空的想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知识,但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艺术的偏离日常性,所以在艺术中见到任何“不可能”的事物,都不会像在生活中见到“不可能”的事物一样大惊失色,因为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默认,艺术本就该拥有一种极致的想象力带来的陌生感、疏离感、虚构感。
五、“通达性”理论与纪实叙述、虚构叙述的区分问题
前文已提出,艺术可能世界理论或许能帮助我们理清文学艺术虚构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解决几千年来模仿论、反映论、或然论、形式论等文艺理论都未能攻克的难题,甚至更进一步找出纪实性与虚构性叙述的本质区别。但是,艺术可能世界理论通过怎样的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即引入“通达性”或“跨世界同一性”理论。“任何叙述文本,包括虚构叙述文本,都是跨世界的表意行为。任何叙述文本中都有大量的跨界成分,这种情况称为‘通达性’(accessibility),又称‘跨世界同一性’(cross-world identities),即某个因素既属于此世界,亦属于彼世界。”[1]187
艺术准不可能世界包括事物不可能和名理之不可能,名理之不可能可以是绝对的“不可能世界”,物理、生理、事实、心理等事物的不可能则完全可以成为广阔的“可能世界”的一部分,“可能世界”分别处在 “不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的对立面,是三个世界的中项。逻辑与艺术用符号再现出的一个世界(叙述世界)并不是单独立足于这三界中的某一个,对于虚构世界来说,它可以“触及并包容逻辑不可能世界,虚构文本可以通达‘二界’(实在世界、可能世界)甚至‘三界’(通达不可能世界)”[1]192。

同时,《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通达可能世界。莎士比亚创造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生活的世界,读者与作者均无法进入这一世界,实在世界或许没有“罗密欧”和“朱丽叶”,但可能世界可能有;实在世界或许没有“罗朱之恋”,但可能世界中则“切实”存在“罗朱恋”。“罗密欧”和“朱丽叶”对于此在的我们是虚构的,对于他们彼此却是真实的。虚构叙述的基础语义域本就是可能世界,是我们的实在世界也许会成为,但没有成为的世界。虚构叙述“坐虚探实”,通过地点、语素、情感等途径与实在世界通达,虽然在细节饱满度上不如实在世界(也不会有一个虚构叙述文本能在细节饱满度上媲美实在世界),但依然使我们在“虚构”中感受到深切甚至更“本质”的真实。
另外,虚构叙述可以通达不可能世界。不过,前文提到的种种“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等修辞性的表述无法支撑起整个叙述世界。而更大范围内的“时间旅行”设定和“回旋跨层”的叙述结构,使虚构叙述“卷入不可能世界”之中,这种类型的“不可能”实际上在虚构叙述中很常见。
在通达性理论之下,虚构与纪实之间的区别也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判断标准,虚构文本和非虚构文本并不是简单的前者表现可能世界,后者再现实在世界。纪实性叙述“坐实探虚”,“以实在世界为‘出发世界’”,却总会探入可能世界;虚构叙述“坐虚探实”,“以某个可能世界为‘出发世界’”[1]187,但总探向并寄生于实在世界。
模仿论、反映论、或然论、形式论几千年来都在回答文学艺术虚构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说法也早就成为陈词滥调。如果从可能世界理论、三界划分和通达性理论来看,艺术必然与实在世界通达,没有一个文本不接触实在世界,但艺术不仅仅是“来源于生活”那么简单。
一方面,艺术带来无边的想象力,它引领我们走出实在世界的角落。被引力吸附在地表的人们,无法“凭虚御空”,而只有在艺术的“准不可能世界”中,才可实现一种凌空蹈虚的逍遥,才能见到“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伟观。实在世界的“生存-存在”在宇宙尺度之上,就如不知晦朔春秋的朝菌蟪蛄一样微渺,但艺术引领此在进入那些无穷尽的、虽然未被“上帝”选择、但奇幻多姿的可能或不可能的世界之中。艺术是有限生命指向无限世界的无穷大符号,敦促我们从自己身处的某一隅中走出,让意识照亮无边界的寰宇,在思维的宇宙中漂流冒险。
另一方面,艺术并不简单地是实在世界的模仿和延伸,“而是‘寄生’,像水蛭的吸盘,一有机会就附着在实在世界的经验关系之上,但是并不是整体都浸入现实”[1]194。极端一点说,虚构之所以从现实中吸取血液,是为了使在漫漶无涯的想象之中,使虚构的细节无限接近它所再现的实在世界,以使虚构获得一种伸手可触的“真实感”。
总之,艺术准不可能世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指虚构在本质上依从“心理可能性”,任意创造、毁灭、生成、重生任何事物,心象不是逻辑或事实,“用眼神杀人”不能被实在化为法律之罪;不逾矩,则是说明艺术准不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框架间隔,艺术中的准不可能或许会被实现出来,实在世界也从未断绝与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的通达来往,但它们之间始终隔着两层。如果框架消失,会破坏艺术准不可能世界的创造性,因为一旦来到实在世界,就必须受限于实在世界的物理和社会规则;也会破坏实在世界的唯一性。
引入艺术可能世界与“通达性”理论,除了可以从实用的角度,帮助理清文学艺术虚构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剖析纪实性与虚构性叙述的本质区别,也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出艺术准不可能世界自身的禀赋与特质。
注释:
① adynation或impossibilia是一种自然的夸张的表达,从人类的原始时代起就一直在被使用。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两个最常见的类型,一是“sooner than type”,意即某人提到的事情将会发生,二是“impossible count type”,指的是海滩上的沙子、海里的波浪、田里的玉米穗等事物的数量。相关修辞变体在中世纪文学中从未,或者说极少出现。不过,古法语作家使用了一种不同的类型,fatrasie,来处理不可能或荒谬的事物。普罗旺斯作家使用了一种因彼特拉克十四行诗而流行起来的类似形式:Pace non trovo e non ho da far guerra。然而,希腊和拉丁的类型被欧洲各地的彼特拉克主义者大量复兴,他们主要利用这些修辞来强调他们的心上人(对待爱情)的残忍,或者肯定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永恒之爱、赞美、忠诚等品质。在彼特拉克主义之后,这一修辞在文艺界明显消退。(Preminger, 1974, p.5)
② 引文为笔者翻译,原文为:Le poète, pour représenter un fait ou une action comme impossible, absurdes ou invraisemblables, les met en rapport avec une ou plusieurs impossibilités naturelles.(Dutoit, 1936, p. ix)
③ 中文引文为笔者据英译本译出。
④ “至少从贺拉斯时代开始,oxymoron就已经是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手段(‘concordia discors rerum’—刺耳的和谐 [Epistulae 1.12.19]),它也是彼特拉克主义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巴洛克时代的卓越特质。……oxymoron在唤起宗教神秘性,或诗人认为超出逻辑区分或普通意义的方面特别有效。文艺复兴晚期oxymoron的流行则归功于那一时期高度的宗教关注,也归功于类比思维习惯的复兴。弥尔顿在《失乐园》的早期书籍中经常使用这一形象,部分是为了唤起上帝不可想象的荣耀。”(Preminger, 1974, p.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