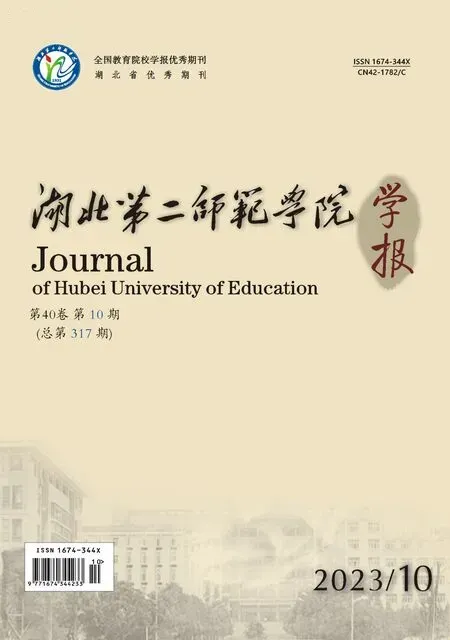近代“戏曲”观念的建构与演进
戴 峰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 430205)
本文所说的“近代戏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戏曲,这一百余年是中国戏曲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戏曲批评、戏曲观念从古代型向现代型逐渐转化的重要时期。
在整个近代的一百多年间,民族的兴亡、中西的碰撞、新旧的博弈、思想的激荡等等因素相互结合,不断地将一向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推向思想文化建设和舆论批评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戏曲的发展和变革,也自然地带来了戏曲批评的转型和戏曲观念的改变。不过,这种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胜旧或者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直线式向前发展的过程,它在不同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
一
戏曲批评主要是对戏曲作品以及与作品相关联的诸多问题的分析评价,而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建立在批评者拥有相对明晰、稳定的戏曲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戏曲观念”,主要是指批评者对戏曲本质特征的理解和认识,涉及戏曲的内涵、外延、作用、价值等方面,还包括戏曲的历史和理论。“戏剧观念问题,几乎显现在戏剧的各个方面,诸如戏剧文学、戏剧表演、戏剧形式等等,但是核心问题是两个,即戏剧‘是什么’和戏剧‘干什么’。前者关系到戏剧的样式问题和本体问题,后者关系到戏剧的功能问题。”[1]我们把这里的“戏剧”置换为“戏曲”,也是完全可行的。但这里其实也隐含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戏曲”和“戏剧”的关系是什么?
只要对中国戏曲学术史稍加回顾,就会发现,戏曲观念问题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将“戏曲”与“戏剧”进行绑定并成为建构戏曲观念的核心问题,也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自近代以来,讨论什么是戏曲、什么是戏剧以及二者之关系的论文可谓层出不穷,直至今日,相关的辨析仍然没有停止。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戏曲生态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国人对于戏曲和戏剧的理解与前人有了巨大的不同。无论是京剧取代昆曲的霸主地位,还是西方戏剧传入我国,成为一个明显的“他者”,都会对中国传统的戏曲观念和思维习惯产生强烈的冲击。再加上在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变革浪潮中,戏曲和戏剧几乎总处在舆论的漩涡之中,这也迫使国人要不断地去调整戏曲和戏剧“是什么”“干什么”的答案,有时这种调整还非常剧烈,这自然会带来追问的深化和研究的深入。这其中尤需注意的是,中西方两种戏剧观念在思维方式、概念运用等方面毕竟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冲突、隔阂和交流势必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
在历史上,“戏剧”和“戏曲”这两个词汇虽然分别在唐、宋时期就出现了,但从宋金到清中期,文人们既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来指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戏曲,也基本没有将二者进行比较和辨析的热情,“院本”“杂剧”“戏文”“传奇”“乐府”“剧戏”“北曲”等称呼比“戏曲”“戏剧”二词更为常见。在观念上,古代文人大多将戏曲看作是传统诗词的延伸和变体。叶长海在《戏曲考》一文中指出:“元明清诸代,‘戏曲’多指戏剧的‘曲本’或‘本子’。但必须指出,古代作文很少着意用‘戏曲’这个词,只有到王国维才开始大量用这个词而使之流行开来。”在该文中,他还指出:“今天,‘戏曲’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从时间上看,包括南戏、杂剧、传奇直至花部等所有古代及近现代传统戏剧;从空间上看,则涵盖昆剧、京剧以及所有地方戏总计三百多个剧种。从其基本特点来看,这是一种以歌、舞、诗三位一体的方式表演故事的综合性(或总体性)的演出艺术。”[2]这一说法,与张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对“中国戏曲”的定义非常接近,张庚指出:“中国传统戏剧有一个独特的称谓:‘戏曲’。……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3]
我们之所以引用两条今人对“戏曲是什么”的权威表述,主要是为了强调两点:一是在现代戏曲观念建构史上,王国维是众所公认的奠基人;二是今人的戏曲观念较之王国维,显然是有所发展的,如上述引文中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其实并未进入王国维的理论视野,但这种发展又是对王国维戏曲理论的合理延伸,恰恰说明了王国维戏曲理论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我们在梳理近代戏曲观念的演变历程时,就有必要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予以特别的关注。
约而言之,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前,国人对于戏曲“是什么”和“叫什么”的关注度并不高,概念的运用仍较为随意,总体上延续了元明清时期的习惯,但对于戏曲“干什么”的理解则是有因有变。在《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其影响力并未即时显现,而学界和演艺界对于戏曲“是什么”和“干什么”的论争则渐趋激烈,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
考察近代戏曲观念嬗变的历程,有必要对“戏曲”“戏剧”二词在近代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和辨析。
近代前期,几本重要的曲学著作如《藤花亭曲话》《今乐考证》《艺概》等,仍然多用“杂剧”“传奇”“乐府”来指代戏曲,但在一些杂记和报刊文章中,“戏曲”“戏剧”的使用率已有明显的提高。比如,徐珂《清稗类钞》中的《戏剧类》,主要记载清末的戏曲传闻掌故,其中有《欧人研究我国戏剧》的记载:“晚近以来,欧人于我国之戏剧,颇为研究。”“瓦尔特著一书,曰《中国戏曲》,分四期,……并就《琵琶记》及其他戏剧之长短略评之。”“哥沙尔著一书,曰《中国戏曲及演剧》,分八章。”[4]该书中像这样杂用“戏剧”“戏曲”地方还有不少,二词的所指基本相同。报刊中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夏晓虹教授曾对《申报》的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出了这样的结果:“自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04年底,32年多,‘戏曲’一词仅在《申报》的22篇文献中现身;而1905年至1911 年短短7 年间,这一数字已提高到46 篇。与之相对照,‘戏剧’在1905 年以前的出现次数要高得多,为270篇,后一阶段则与‘戏曲’比较接近,为59篇。”“二者用于中国语境时,在内涵上本不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混用的现象并不少见。”[5]这些例子似乎可以说明,用“戏剧”“戏曲”而不是“传奇”“乐府”来指代中国的戏曲,已逐渐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风尚。至于其中的原因,除了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和日本学界的影响之外,也可能是因为这两个词汇更具有集合名词的意味,用来总称中国传统戏剧更为通顺。
20世纪初,戏曲改良运动兴起,声势浩大,参与者众多。梁启超、陈独秀等倡导者颠覆传统的文学观念,将过去为文人雅士所不取的小说、戏曲视为“文学之最上乘”[6],同时还极力提升戏曲和伶人的社会地位:“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7]此类提法可谓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促使国人的戏曲观念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跨越。同时,在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中,用来指代戏曲的术语不乏“小说”“说部”“曲本”“班本”“歌曲”“演剧”等等,但都不如“戏曲”“戏剧”二词使用广泛,这从文章题目上就能一窥而知,如:佚名《编戏曲以代演说说》、健鹤《改良戏剧之计划》、马裕藻《论戏曲宜改良》、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陈独秀《论戏曲》、渊实《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王钟麒的《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剧场之教育》、佚名《实行戏曲改良》、皞叟《论改良戏剧》、唯心《滇省改良戏曲纪事》、少少《戏剧改良说》等。此外,如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佚名《春柳社演艺部专章》等,也都明确倡言“戏剧改良”和“改良戏曲”,这说明在当时的知识界,“戏剧”“戏曲”事实上成为了广受认可的学科名词。
1907 年,成立不久的春柳社进行了首次公开演出,标志着“新剧”——即中国早期话剧——的正式诞生,这一事件非同凡响,它使西方的戏剧和演剧形式开始具象化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丰富了国人对于戏剧的理解。
辛亥革命不久,戏曲改良和新剧发展几乎同时走向衰落,双方所期待的“完美新剧”[8]都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并没有结出多少实在的果实,这也折射了中西两种异质戏剧文化走向融合的艰巨性。而正是在这个时期,王国维接连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戏曲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集其大成的《宋元戏曲史》,堪称划时代的学术论著。王国维戏曲研究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9]的治学方法。他广泛借鉴西方现代的文学、戏剧和美学观念,以及注重系统性和思辨性的研究范式,对戏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王国维给戏曲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10]同时,他严格区分了“戏曲”和“戏剧”二词的含义,将上古至宋金时期的歌舞、百戏、参军戏、宋杂剧等称为“古剧”或“戏剧”,而将元杂剧、南戏及明清的杂剧、传奇等称为“戏曲”“真戏剧”“真戏曲”。从古剧到真戏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乐曲上之进步”,二是“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11]王国维的研究表现出了严谨的学理性和鲜明的现代色彩,其结论和方法被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所普遍接受,“通过《宋元戏曲考》,王国维将‘戏曲’一词确立为一个稳固的学术概念,用于指称宋元以来成熟了的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与文学,并使其普及开来。尽管在后世的学人间,这一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异,但基本上再没有出现能与它构成竞争的词。”[12]同时,“戏剧”一词的含义也得到了确立,即它是一个包含古剧、戏曲及其他演剧形式的大概念,其本质内涵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戏剧”已经高度一致了。“戏曲是什么”和“戏剧是什么”的疑问,在学理上基本得到了解答,这为我国现代戏剧学、戏曲学的研究,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不过,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虽然在当时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但其学术示范效应并没有立即得到充分的显现,绝大部分的学者和文人仍然在混用戏剧、戏曲和旧剧等概念。这也是近代学术研究新旧杂糅特点的一种体现。
三
五四运动前后,由《新青年》文化先驱们发动的新旧戏剧论争使国人的戏曲观念再次发生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先驱对封建专制思想和传统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主张“反对孔教”“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3],于是,作为旧艺术代表的戏曲,就成为了《新青年》派先驱们进攻的矛头之一,有关新剧旧剧的论争迅速展开,这场论争对国人的戏剧观念所造成的冲击也是远超以往的。
参与论争的《新青年》派代表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他们秉持文学进化的观念,对旧戏所存在的思想之腐朽、文章之恶劣、模式之单一、舞台之幼稚、化妆之离奇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定戏曲乃是旧时代的“遗形物”、艺术上的“百纳体”,完全无法起到针砭时弊、启蒙大众的作用,因此主张将旧戏“全数扫除,尽情推翻”[14],去全力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而论战另一方的代表只有张厚载、冯叔鸾等人,他们从维护戏曲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戏曲具有格律谨严、动作规矩、唱腔动听、表演写意等优点,因此认为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完全可以保存。”[15]“新的用不着去迁就旧,旧的也不必去攀附新。”[16]
这次论争声势浩大,言辞激烈,但双方的重心其实不在同一层面。《新青年》革命派的目标是呼唤现代新文艺的诞生,而张厚载等维护派的目的则是要证明传统文艺的合理性,这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文艺观念的大对撞,如果能够认真反思和总结,这种论争其实是有益于戏曲的近代化转型,也有益于中国话剧的健康发展的。
1926年前后出现的“国剧运动”似乎正是对新旧剧论争进行反思的结果。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闻一多等人以西方戏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戏曲时,反而发现了很多可贵的特点,如写意、象征、综合等等,所以他们希望以戏曲为立足点,创建出一种融合中西戏剧美学之长,又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17],他们将这种近乎完美的戏剧称为“国剧”。余上沅等人非常强调戏剧的民族性,认真研究中西戏剧的特点,其理论思考具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当时日渐严峻的社会现实承载不了他们的艺术理想,国剧运动很快消歇,成为了一个“半破的梦”。但他们关于戏剧民族性的主张,却在日后以不同的形式获得了响应,证明了其理论的超前性。
1930年代,梅兰芳先后到美国和苏联访问演出,程砚秋到欧洲考察戏剧,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反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戏曲的国际地位,这不仅激发了国人对于民族戏曲的自豪感,也部分地改善了戏曲批评、戏曲研究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新旧戏剧的比较趋于理性客观。
抗战全面爆发后,戏曲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的社会属性不断加强,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戏曲“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戏曲批评和理论建设的焦点。而民族形式问题的核心,主要是戏曲和话剧如何融合,并“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8]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自戏曲改良、新旧剧论争以来关于中西戏剧融合问题的再展开。因为“五四”以后,话剧主要沿着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方向发展,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大众化程度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而戏曲虽然始终拥有最广大的受众群体,但自身如何提高思想性和现代性,也始终是个难题。在国统区,戏曲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运用旧形式”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来展开。在解放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主要围绕“旧剧现代化”和正确对待“民族遗产”问题而展开。1942 年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推陈出新”成为了延安戏曲改革的两大指导方针,这从政治和艺术两方面明确了戏曲发展的方向。延安平剧研究院“以扬弃批判的态度接受平剧遗产,培养平剧艺术干部,开展平剧的改造运动,以创造戏剧上新的民族形式”[19]的创办宗旨表明,将戏曲视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以扬弃的态度,在继承中创新,已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戏曲改革的重要政策。
结语
在近代,国人的戏曲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将戏曲“向来是看作邪宗”[20]的思维定式被彻底打破,现代戏曲观念得到确立,并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调整和演进。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1]在近代,影响戏曲观念嬗变的因素至少有四点:即现代文明观念的贯注、中国政治形势的干预、外来理论资源的吸收和自我传统遗产的挖掘,这四者各自均有独特的价值和贡献,而如何总结历史教训,努力平衡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和开拓戏曲研究的理论体系,对于近代戏曲学和当代戏曲学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