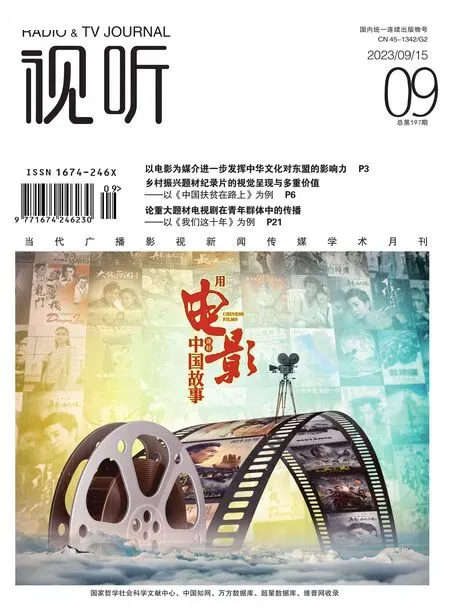类型互渗·文化叙事·家国同构: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满江红》的创作启示
◎王立斌
电影《满江红》是导演张艺谋继《狙击手》后的第二部春节档影片,该片延续了《狙击手》“一叶知秋”式的叙事视角,采取了以小见大的美学原则。但从电影类型的角度来看,《狙击手》具有明确的新主流电影类型特征,例如“祛魅”英雄的人物设置、电影语言的通俗化编排等。而“悬疑管够,笑到最后”这一电影海报宣传语足以说明,《满江红》是一部融喜剧与悬疑元素的喜剧亚类型电影,从而使得受众群体能够在笑闹之余获得悬疑解谜的心理快感,满足了受众对春节档影片的观影诉求与心理期待。与此同时,张艺谋导演还执着于运用电影艺术的方式来展现与传播中国文化。不论是其早期影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还是新世纪以来的商业电影《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从色彩影调、音乐音响、画面构图等叙事元素的基本运用,到伦理价值、民族精神、人文关怀等意蕴层面的诗意表达,都体现出了导演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叙事策略,进而为电影创作增加了具有东方意味的文化底蕴。电影《满江红》整体采用“走马灯”式的叙事结构,在喜剧、悬疑等具有商业意味的叙事脉络中有意采用文化意象的叙事策略,从而将家国同构下的东方情怀进行诗意化表达,以此赋予了电影商业性、民族性与人文性并存的风格特征。
一、类型互渗:喜剧“本体论”的亚类型“变奏”
作为春节档影片,《满江红》融合了多种类型风格。正如张艺谋导演所说:“悬疑、惊悚,凶杀、反转、卧底,包括喜剧、幽默、冷幽默,可能还有荒诞等各种类型叙事元素放在了一起。”①影片最大的类型突破就是采用了“喜剧+悬疑”的叙事模式,并选用一众喜剧明星进行演绎。该片在达到春节档影片给观众带来“笑果”的同时,还完成了以“反转”为主要叙事策略的悬疑故事的讲述,从而实现了喜剧电影类型“本体论”的亚类型“变奏”。《满江红》所选用的喜剧演员沈腾、岳云鹏等人在电影中展现出了自身优秀的喜剧才华。例如,影片中沈腾饰演的张大在被易烊千玺饰演的孙均踹倒在地、拳打脚踢时,张大捂着大腿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能不能不朝我一个地方踢。”此话一出,便为观众呈现出了张大怯懦的性格特点。从电影花絮中可以看到,这句台词是沈腾随性发挥的对白,而这句具有喜剧意味的台词获得了张艺谋导演的认同并将其保留在了正片中。由此可见,《满江红》中的喜剧元素并不只是导演、编剧独创的结果,还包含了喜剧演员凭借自身喜剧经验即兴创作的成果。正如张艺谋导演对于喜剧演员的评价:“他们有很多灵动、睿智的东西,很多包袱是在现场嬉笑怒骂之间蹦出来的,甚至是在有点不正经的氛围之间蹦出来的。”②因此,《满江红》并没有一味追求纯粹的喜剧噱头,对于喜剧元素的运用也并不是“为喜剧而喜剧”的生硬插入,其对喜剧元素的把握以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和故事的情节走向相契合为选取原则,从而使喜剧元素能够在赋予电影喜剧风格的同时助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剧情发展。
除此之外,悬疑题材中的“反转”叙事也同样会产生别样的喜剧效果。“反转”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即原则中的行动转到相反的方向中去。反转叙事在电影中体现为情节的转变和人物命运的转变,而情节走向与人物命运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满江红》中,在与张大、孙统领争夺信件归属权这一情节点上,武大人的背景身份由最开始张大编造的武贵妃堂弟的虚假身份反转到了由张大自曝自己是武贵妃内侄。人物身份的颠覆性揭露不仅使信件争夺的情节走向再次发生了转变,而且武大人的个人命运也随着真实身份的表明产生了逆反性的翻转。电影的剧情反转就是通过制造意外在反转的那一刻颠覆观众的想象,突破观众的心理预期,刺激观众的感官和情绪,让观众获得深刻的体验并享受这种感觉。③《满江红》正是在身份的虚假性与真实性的对立中进行反转叙事,进而对人物情感与心境产生影响。但从武大人对张大说的“你猜对了一半”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电影中所设置的“虚假”与“真实”并不是处于完全二元对立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张大之前所编造的“武贵妃与武大人具有亲密关系”,使得此处所运用的反转叙事具备了预设性。因此,观众的心理预期也并不是完全地被打破,当接收到预设性反转的观众将反转前后联系起来进行重新解读与认知时,他们不但能够获得反转叙事所带来的刺激性快感,而且可以感知到张大这一歪打正着行为所产生的戏剧性喜剧效果。由此,《满江红》消解了反转叙事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感,弱化了“悬疑”剧情所营造的紧张氛围,进而使得影片“喜剧+悬疑”的喜剧亚类型特征更加明显。电影《满江红》将极具风格化的多重类型元素进行融合,以喜剧的形式涵盖了悬疑、惊悚、侦探等叙事特征。类型互渗的创作原则不但丰富了国产喜剧电影的叙事元素与叙事策略,而且实现了国产喜剧电影类型“本体论”的亚类型“变奏”,使得国产喜剧从“类型融合”的初级阶段走向了“新类型”的高级阶段。
二、文化叙事:意象“表述”与诗意“言说”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独具民族特色的核心范畴之一。从已知文献中可以溯源,“意象”概念的使用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对于“意象”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意中之象和表意物象。意中之象即主观意识中的虚构象,如“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的浪漫想象;表意物象即客观世界中的实在象,好比“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现实描摹。两种解释将“意象”概念中的“象”划分为了主观之象与客观之象,但不论是意中之象还是意外之象,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以象为载体来实现达意的意图。时至今日,意象论不仅于文学艺术实践中日臻完善,还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发挥了指导性作用,电影工作者通过对电影意象的创构,使得本土电影具有了民族化的审美风格。电影《满江红》中运用了大量的民俗意象进行叙事,其既是地缘文化最直观的形象载体,也是精神伦理最质朴的表现形式。电影中的民俗意象,无论是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语言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承载着独特的地缘文化与民族精神。影片的拍摄地为山西太原拥有2500 年深厚历史底蕴的古县城,导演张艺谋在保留山西大院基本建筑特色的基础上,还根据拍摄要求,在场景改造上以迷宫式的“走廊”连接起两个大院。“长廊”连接“亭台楼阁”的建筑方式不仅展现了独具东方韵味的居住环境与生存空间,而且在影片中承担了封闭性空间叙事的功能,为片中人物的行动提供了饱含民族性的叙事环境。封闭空间中的物态对象在特定的范围限制中会产生更多的抽象意义,使得封闭性空间具有了意义生产的开放性。电影《满江红》将故事场景置于“迷宫”式的封闭大院中,与自然界的“迷宫”不同,人造的“迷宫”往往利用“迷宫”自身的游戏特质,使“迷宫”更像是某种大型的实验室,令“迷宫”中的人们经历种种智力、体力甚至是人性上的考验。④影片中,张大与孙统领等人一次次穿梭在由大院长廊组成的“迷宫”中寻找线索。错综复杂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影片营造了具有紧张感与压迫性的环境氛围,还在叙事中隐喻着线索之间扑朔迷离的相关关系,以及张大等人寻找线索时的坎坷程度。
除此之外,当影片以人物“穿梭长廊”这一动作为叙事节点时,民俗音乐的声画同步运用也为人物的行动做出隐喻性的暗示与铺垫。例如,影片中张大与孙统领走在长廊中前去审问领舞艺妓,此时所穿插的背景音乐是曲剧《包公辞朝》。该剧讲述的是刚正不阿的包公通过计谋保护了受奸臣陷害的杨家将的故事,而张大与孙统领所做的是为宰相秦桧寻找其“犯罪证据”。该情节与此颇具正义性的民俗音乐看似具有完全背反性,但是此处穿插曲剧《包公辞官》实则是在指示着张大与孙统领两人隐于内心深处的正义思想。当众人看到何立所放花火后纷纷前往其所在的院子,此时背景音乐《花火》随之同步响起。《花火》改编自豫剧《打銮驾》,讲述的是包拯奉旨陈州放粮,查办曹国舅等克扣赈灾粮之弊。曹娘娘恐兄获罪,便借来皇后半副銮驾来阻挡包拯。而包拯识破其假,命人打了銮驾,闯道而去。戏曲中的曹娘娘假借皇后銮驾以阻挡包拯的桥段,与电影中何立假借放花火欲使刘喜同伙暴露的情节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民俗音乐的运用与电影叙事之间产生了连通性关系,因此民俗意象便作为叙事元素参与到了故事情节的建构中。除此之外,电影还运用了《包龙图坐监》《探阴山》《穆桂英挂帅》等大量的戏曲民俗元素。在电影的创作中,当叙事主体有意识地把音乐视为情节的制造手段时,音乐就不再作为一种辅助的表现方式,而是从平行的叙事空间进入到画面的叙事空间,音乐本身成为故事情节,并且推动剧情的发展。⑤《满江红》中民俗意象的运用不仅有助于影片民族化风格的确立,而且进入到了情节架构中,还承担着民俗叙事的功能,以此使得电影在意象的“表述”中实现了诗意性“言说”。
三、家国同构:自我救赎下的“情怀”共聚
梁启超先生曾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⑥顾名思义,“家国同构”意味着家庭、家族与国家之间的组织结构具有相似性,作为“小国”的家是作为“大家”的国的重要组织成分。正如《孟子·离娄上》所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句话体现了“家”与“国”之间相辅相成的同构关系。电影中的“家国同构”往往以一个或多个家庭为中心视角展开讲述人生追求与家国大义,并将个人荣辱、家族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采用“以小见大”的美学原则将“家国情怀”进行凝练与抒发。《满江红》将叙事重点放置于张大等一众小人物身上,这些小人物始终在“生与死”之间不断进行抉择。影片围绕着“失踪的密件”展开叙事,而这一密件正是宰相叛国的证据,因此在宰相庞大势力统治下参与到找寻任务的边缘小人物便始终处于“自我救赎”的反复阶段中。当面对自己的爱人瑶琴即将受到处罚时,张大决定选择招认信件内容以保全瑶琴。而面对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选择前者的张大,瑶琴即便被他所救也仍对张大说:“软骨头,你是男人吗?”由此可见,影片中人物的“自我救赎”与“家国情怀”产生了不可平复的对抗性冲突。深陷困顿中的瑶琴虽然面临着无法自救的绝望境地,但在看到张大做出舍弃国家大义来换取她安全的行为后,瑶琴依旧决定牺牲自己以追求大义。从瑶琴的这一人生选择中可以看出,她所追求的正是“舍生取义”的精神内涵。相比于生命来说,具有崇高性的“家国”精神通过人物的行为隐喻于影像中得以升华,并由此展现出以瑶琴、张大为代表的小人物以“自我救赎”的方式走在了“舍生取义”的理想之路上。
家国情怀是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以忠孝一体为价值凝练,以经邦济世为社会实践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⑦《满江红》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把小人物的“家国情怀”与宰相秦桧的“通敌叛国”进行并置演绎,其中对于秦桧罪行的揭露反映在张大、瑶琴等小人物群体的自我救赎之中,由此可知影片中人物的自我救赎与其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同样有对立性色彩,因此影片的终极主题便是从人物对于对立二者的抉择取舍中进行呈现与升华。正如影片中一心只求自救的孙统领,在看到张大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后便得到了正义性的感化,最终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选择了民族大义,即逼迫“秦桧”在众将面前背诵《满江红》。军队荡气回肠的传诵声不但蕴含着岳飞的爱国之心,而且使得“精忠报国”的集体意识得到了视听化的表达。把《满江红》激情澎湃的传诵声音与张大等人“以死向义”的画面结合分析可以看出,双轴共现的声画关系将以张大为代表的边缘人物在“自我救赎”中所共聚的“家国情怀”进行了凝结与升华。与此同时,影片在“家国情怀”的意蕴笼罩下也对普通个体形象进行圆形化塑造。张大、孙统领等底层小人物在为宰相秦桧这一大人物寻找信件的过程中,通过种种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人际交往,不但展现出张大等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呈现出了底层小人物懦弱惜命的性格特点。但正是影片对人物进行了具有鲜明优缺点的形象塑造,才使得以张大为代表的底层人物在追求“舍生取义”时能够将“家国情怀”通过人物形象的衬托获得绝对的崇高性,以此使得电影在家国同构叙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突出性表达与抒发。
四、结语
“新类型电影”是中国银幕新文化的复归,是一种兼具娱乐性和疗救作用的视觉欢宴,它们以商业化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民族意趣,摧毁国产电影向来的单一、凝重和自恋风格,在被重置和被建构的历史与想象空间中进行复调式混搭化表意,对国产电影视域和空间的拓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叙事的全新再造是其成功的最重要原因。⑧电影《满江红》融合了喜剧、悬疑、古装等多种类型元素,在喜剧类型的基础上进行“亚类型”变奏。喜剧亚类型或新喜剧电影类型的产生一方面是对原初电影类型的扩展与创新以加强电影的商业属性,另一方面是在迎合观众审美趣味的基础上拓宽电影的叙事元素,使得电影艺术的表达具有更大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满江红》还采用了大量的中国民俗意象进行叙事。民俗意象的运用在扩展电影叙事元素的同时,还为电影增添了民族性的风格特征,进而使电影以诗意化的表现方式将文本中的东方情怀进行呈现,以此来实现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电影的商业性、民族性与人文性的多重建构。
注释:
①②张艺谋,曹岩.《满江红》:在类型杂糅中实现创作突围——张艺谋访谈[J].电影艺术,2023(02):92-96.
③顾浩东,李竹君.电影反转叙事话语建构与审美心理探微[J].电影评介,2021(11):18-22.
④孙建业.从“方寸之间”到“孤岛之上”——论电影中的“封闭空间”[J]. 电影新作,2016(04):37-43.
⑤孔朝蓬,王珊.电影音乐对影片情节叙事的构建[J].文艺争鸣,2010(12):31-33.
⑥教育部高教司,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⑦张倩.“家国情怀”的逻辑基础与价值内涵[J].人文杂志,2017(06):68-72.
⑧周安华.作为媒介艺术的绰约变革叙事——21世纪中国电影的银幕姿态[J].电影评介,2019(19):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