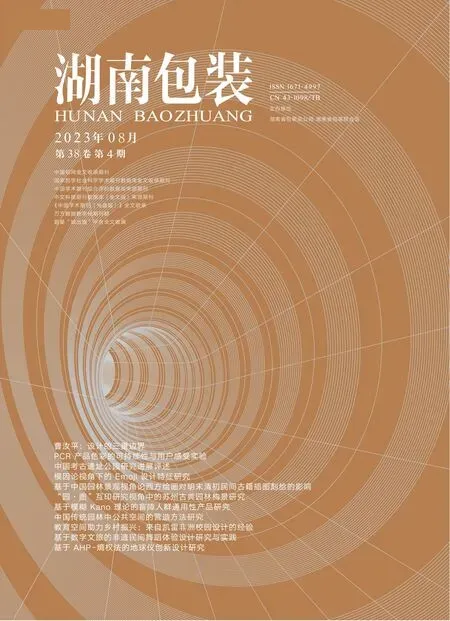临川文化区域传统乡村聚落建筑文化研究
——以流坑古村为例
马晶晶 嵇立琴
(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传统的聚落建筑是中国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产物,而建筑作为聚落文化的载体,同样承载着各时期的盛行文化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1]。建筑的文化特征、空间布局、装饰工艺等则反映各时期的盛行文化、建筑特色、审美层次。对临川文化区域的聚落建筑文化探究同时也是对我国建筑历史文化的剖析。
在建筑形式多元化的今天,传统的聚落建筑虽然为现代建筑提供着丰富的设计思路与灵感,但针对其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然非常匮乏。文章选取中国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境内的流坑古村作为课题研究素材,流坑古村的聚落建筑对建筑的空间秩序感有较高的要求,建筑群落外观简单、朴素大方。通过对其建筑的文化与空间布局特征、建筑空间结构特征、建筑装饰组成部分等多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此来发掘其乡村聚落文化内涵以及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瑰宝。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针对传统聚落建筑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并梳理出临川文化区域聚落建筑的文化内涵,从而为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1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的文化特征与影响
1.1 儒家传统文化对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的影响
流坑古村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个缩影,流坑古村地处偏僻,其与诸多村落都相隔甚远,这便使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居住环境,但是并不代表该村落的文化落后,相反该地也出了不少的文人墨客。正因为如此,流坑古村的文化氛围和思想观念还是非常活跃的。
流坑古村的儒家传统文化从它的建筑形态上就得以体现,空间与空间之间由一系列的虚实空间、开放与闭合空间相贯通,墙体内部构成的封闭空间为虚,四周的砖木墙体为实,公共空间中的街巷为开放,厅屋居住空间为闭合,两者相辅相成、融合贯通,处处都体现出其物质文化层面上朴素的自然生态观“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流坑古村的建筑以聚落为单位,其街巷四通八达贯连整个聚落,内部居住空间又以大中小划分,建筑空间大部分为天井式住宅,且左右空间相对称,其中天井的巧妙使用不仅使原本昏暗闭合的空间得以采光通风,而且将天与人相结合,做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除此之外“阴阳理论”学说也在建筑的形制中得到了体现,从空间结构角度来看,天井与厅堂空间相互影响,则互为阴阳;厅堂与两侧的厢房也互为阴阳关系。通过流坑古村的建筑可以充分地体现其统一与对立的思想理念[2]。
封建的法规制度同样对其建筑产生着思想层面的影响,封建礼仪制度一直以来就是“儒家”观念的精髓。从建筑的景观到建筑内部空间全部都要遵循“尊卑有序,大小有论”的儒家思想。流坑古村的建筑形态受其影响颇深,从建筑的规划布局或者建筑的室内空间布局就可以得出此结论。从建筑进门处设置的天井以及明亮的前堂就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行礼、会客等方面尤为重视,建筑的入口处整体明亮大气,然而紧挨前堂的后堂虽与其只有一墙之隔,却明显的在视觉上更加阴暗。后堂作为生活居住的场所并不像前堂一样明亮大气,相反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室内空间中左厢房通常为长者居住,右厢房大多为家中除了长者的男子居住,而女性只能居住在后堂的厢房,采光与通风上都不及前堂的左右厢房,从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其儒家思想中尊卑有序大小有论的思想。所以封建法规制度对流坑从居住环境到等级空间上有着很大的影响。
1.2 传统家族观念对流坑聚落建筑空间布局的影响
流坑古村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因其地处“半封闭”的居住环境以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其具有传统的延续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3]。建造之初为了维持整个村落的秩序,流坑的董氏建立了严密的制度并且还修建了祠堂,在流坑居住的人全部都是董氏一族,所以在规划布局时就已经将血缘与家族观念融入到了建筑之中。
建筑与建筑之间虽然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家族观念的联系。这样的建筑布局不仅按照家族进行划分,还有利于邻里之间的交流,使得整个流坑形成“千门万户是一家”的聚落建筑空间布局。村中大大小小的祠堂也成为家与家之间的枢纽,每年的祭拜以及活动等都使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这也证明了中国古代时期注重家族血脉的传承发展以及很强烈的家庭归属感,这不仅在家族观念上有所展现,同时也在建筑空间布局上得以展现。
1.3 傩神文化对流坑古村聚落建筑文化的影响
流坑古村的聚落建筑除了深受传统文化以及家族观念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受当地傩神文化的影响。因为流坑村信奉傩神,傩文化对当地民居建筑有着很大的影响。流坑村的“巫傩”文化相对来说较为发达,傩神文化其实也相当于一种宗教活动,它不同于人们在祠堂举办的活动,它是一种以在街上行走来达到祭拜目的的鬼神文化。其通过祭祀和舞蹈等供奉来保佑村庄,当然,傩神文化不仅仅从思想上影响着流坑当地的文化,还通过建筑有所体现。
当地人将大门作为一宅之气口,宅门的艺术处理多按照趋吉避害的防护目的为主。关于趋吉避害的思维模式,分为“冲”“镇”“避”等,“冲”即驱赶,在宅门上安装可以辟邪的装饰将邪气进行驱赶,使其敬而远之,在这一点上当地村民还有着强烈的迷信色彩,在流坑古村的聚落建筑中应用极为广泛。“镇”和“避”相对“冲”来说相对温柔一些,是属于保佑以及防御的状态,它主要不是进攻,而是采取防御姿态,让不好的东西自行退离,不同于前者的强烈进攻寓意。“镇”是通过在前堂和房门上书写类似于咒语的东西来进行镇压;“避”则是通过建筑形态的改变来达到抵御效果,比如在实地调研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建筑的大门不是直接对着街道的,会采用照壁来起到一个隔挡作用。
在对流坑古村进行实地调研的时候可以发现,当地的建筑空间格局很多都采用了“冲”“镇”“避”这3种中的一种,有的通过建筑角度的改变来达到抵御效果,有的是通过咒语符咒,有的通过物品的陈列,例如镜子、剪刀、木质剑等进行辟邪。
1.4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所展现的文化含义
流坑古村的聚落建筑也蕴含着许多的文化含义,通过调查可以得知,流坑古村的整个村落对建筑的装饰是很重视的,比如木雕、石雕、砖雕等在村落中随处可见,那么构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当地村民古时候多为商人,其经济基础雄厚。既然当地村民的经济是富裕的,那么必然会在追求使用居住功能的基础上,同时也追求装饰观感需求,这和明代家具的由来大相径庭,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流坑古村传承下来的丰富的装饰纹样,为该村落建筑文化的探讨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2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特征分析
流坑古村的整个聚落建筑特征可以从“独”与“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从“独”来看,其做到了“墙倒屋不塌”的建筑特性,因为建筑外墙是独立的,且墙与梁互为包裹关系,即使建筑的外墙坍塌,建筑的整体框架也不会发生改变进而坍塌。同时,建筑均采用庭院式的布局特点,通过多个小的空间来组合成一个大的空间,这也是其“独”有的特性。从“重”来看,街巷属于一个开放空间,而建筑内部就属于一个封闭空间。街巷是贯穿整个村落的纽带,而居住空间与外界相连的手段便是——天井。天井设在前堂这一开放空间之上,建筑有两进一天井、三进两天井等,是根据建筑的大小以及屋主的身份来定夺的。通过天井与外界联系,这样一来在空间交流上是互通的,也就体现了“重”这一特点。
2.1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独”的特征分析
从“独”来看,流坑古村能够做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特性,同时也能说明其建筑用材的精妙之处。流坑古村的建筑大致都是砖木结构的,这与地理环境有着必不可少的关系。在其村落周边拥有大面积的樟木林,所以在材料选择上木材不仅便于运输,而且在建造成本上也会更低。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仅仅使用木材这一单一的材料,而是结合了天然石材。流坑除了拥有大面积的木资源,同时也拥有丰富的麻岩、石灰岩、青石板等。流坑的青砖是其建筑一大特色,通过烧制等工艺手段使其更加美观。
整个村落的建筑主要利用这两种材质实施了富有装饰性变化的设计。首先木材的灵活性、可操控性、隔音、美观等特性也使得其给整个村落增添了实用性与美感;其次在石材上也同样进行了设计,通过堆砌方式的变化以及雕刻等手段也使得其不仅满足建造需求,同时也充当了建筑的装饰手段。
2.2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空间“重”的特征分析
从“重”来看,流坑古村主要由一系列的虚实空间、开放与闭合空间相贯通,墙体内部构成的封闭空间为虚,四周的砖木墙体为实,公共空间中的街巷为开放,厅屋居住空间为闭合,两者相辅相成、融合贯通。天井是建筑内外空间联动的窗口,在满足采光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
2.2.1 街巷组织特征
流坑古村的街巷既分割又串联了实体空间,具有物质功能、社会交往功能、文化功能、信息传递功能,是室内通往室外的沟通桥梁。其街巷空间窄而长,采用高墙窄巷,街巷空间的变化丰富,有“步移景异”之趣;整体平面布局又好似枫叶一般,街巷则如叶脉贯穿整个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如广场、宗祠、庙宇、古塔、戏台、书屋以及通往村外的路都是由街巷空间相贯连的[4]。街巷满足了人们对各种户外活动的需求,并为居民的日常交流提供了场所。
人们从室内空间到街巷空间即是闭合到开放,街巷空间形成的大小、宽窄变化与公共节点相结合,形成了富有当地聚落建筑空间特色及组织特征的居住空间。街巷带来的温暖感和历史感正是流坑古村永恒的魅力所在。
2.2.2 天井的功能与特点
天井是古人采光、通风、排水、防潮的一种建筑装饰技术,临川文化区域的流坑古村建筑中的天井四周环绕着4座建筑,中间形成一个空心空间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与思想。天井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结构,从功能使用的角度来看,其属于建筑的内部空间。但是从建筑结构方面看它属于外部建筑空间,屋脊的构建由不同高度的瓦片以及燕尾脊组成,如流坑古村中环中公祠的天井,其天井构造高低错落,使得光线的照射面积更加广阔,扩大了采光面积,使得整个厅堂空间也更加明亮。站在厅堂里面向上望去,透过天井的檐向天看去,“天”和“井”浑于一体,使得内外空间相连,打破了室内空间的死板与阴暗。
临川文化区域建筑的天井式民居大部分是三开间的布局,流坑古村同样如此,一般人家从街巷进到屋内为一进式,经济富裕的居民建筑可能达到三五进甚至更多。整个室内空间围绕天井展开,天井也有其固定的特点。古时候的人们喜欢对称性强的建筑空间,他们认为对称的空间显得庄严,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审美。不仅天井本身是对称的,其檐下空间同样也是对称的,以天井中轴为分割线,两边的居住空间全部相同,从墙面上的雕花造型到门窗的开合流通全部为对称布局,这也体现了当时人们追求稳定的想法[5]。因为对称的物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实现稳定的平衡关系,人们追求对称的美,对称意味着平等和庄严。同时,天井屋檐高度也是住宅室内空间最低层的高度,天井下相应的坑是室内空间的最低部分。
3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砖木混合结构是流坑古村聚落建筑的显著特点,建筑的承重选用木柱,建筑周边的砖筑墙体则只做围挡作用。建筑空间的主体构架采用的是传统的穿斗结构以及抬梁结构。整个空间以横纵结构组成,两种结构各有特点,纵向结构为房屋提供了稳定,横向则是聚落建筑的面阔方向,整个空间合理划分并满足各种使用需求。
3.1 穿斗式木结构聚落空间特征
流坑古村因山林面积广阔,村落周边拥有大面积的樟木林,所以在建筑时木材既可以满足房屋的承重构架需求,又可以作为装饰构架。木材作为承重构架一方面可以增加立柱间距增加使用空间,另一方面可以支撑起整个阁顶天花的结构。穿斗式木结构在流坑古村的应用尤为广泛,因为流坑古村的聚落建筑是采用木柱承重即可承托屋面的重力,建筑四边的砖筑墙体只作围护,所以建筑的主体构架采用的便是穿斗式木结构。穿斗式木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梁架,柱子直接承接檩条,檩条置于柱头的位置,再用穿枋将柱子之间相互串连起来形成房屋框架[6]。穿斗式结构的组成是非常灵活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居民对居住环境空间的使用需求的增加,穿斗式木结构也在不断发展。
3.2 抬梁式木结构聚落空间特征
上述说到流坑古村的聚落建筑多采用穿斗构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房屋均采用相同的建造手法,穿斗式只属于建筑的纵向构架,那么既然有纵向构架就必然还需要横向构架的牵制与固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整个屋子的稳定性与美观性。抬梁式木结构又称叠梁式,是临川文化区域传统建筑中常用的主要木结构形式。流坑古村也同样使用该抬梁式木结构,这种结构减少了短柱之间的跨度,使得整个空间更为开阔美观、稳固牢靠。流坑古村的抬梁式木结构是在立柱上面架梁,梁上又抬梁,梁逐层缩短向上,再在最上层的屋梁中间部分设立脊瓜柱,由此构成一组屋架;最后用枋在相邻屋架的柱子与柱子之间做横向的连接,从而组成框架。抬梁式木结构的使用范围很广泛,是木构建筑的代表,常应用于宫殿、寺院等大型建筑。房屋屋顶的重量通过椽子、檩条、横梁、柱子到地基,抬梁式木结构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对流坑聚落空间的布局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形制简洁大方,减少了过多的装饰图案,配合着整个聚落建筑质朴的视觉感受,给人一种沉着稳定的感觉,使人身居其下有着安全感的同时又不失防潮减震的功能。
4 流坑古村聚落建筑装饰文化特征
临川文化区域的建筑装饰也是多种多样的,因其受到当时的多种文化影响,所以使得流坑古村建筑的装饰种类也丰富多彩。明代初期,赣江水运的地位因为受到“海禁”的影响得以上升,这不仅为临川文化区域的江右商人提供了经济与运输便利,而且再加上江西地区的人们对于考取功名尤为重视,所以江西此时的经济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正是因为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发展直接推动了临川文化区域聚落建筑的装饰艺术发展。
在聚落建筑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中除了建筑组成的闭合居住空间以外,建筑的装饰元素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建筑装饰不仅为建筑增添了美观性,而且在功能上还有很大的作用。村落建筑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砖雕等的作用都是双重的,它们组合在一起既融洽又美观,是临川文化区域传统聚落建筑空间的标志性建筑装饰部分。
4.1 木雕
明清时期以来临川文化区域的木雕装饰最为突出,木雕是流坑古村聚落建筑中尤为重要的装饰特色,因为流坑古村的建筑室内空间多以木结构为主要结构,室内空间的梁、门、装饰物等均是木质材料。整个建筑空间外观是清一色的青瓦灰墙,但是室内空间又非常注重装饰,所以室内空间的木雕装饰造型优美富有内涵[7]。
临川文化区域不同时期的木雕艺术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比如相对于明代时期的简洁古朴,清代的木雕艺术就显得更加华丽精细一些。流坑的聚落建筑木雕类型分为很多种类,例如雀替、牛腿、斜撑、槅扇等,但其在功能和造型上又不是一样的,它们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室内空间具有承重功能的木雕,如雀替的造型丰富,可从多个角度观赏,雀替上的图案各不相同,寓意也根据屋主人的愿望而改变,其造型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以及美好寓意,它是结构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8]。
4.2 石雕
石雕在临川文化区域的应用不少于木雕,石雕在流坑古村中的祠堂、书院、戏台等空间都可以看到其身影,例如戏台间立柱为抹角四边形,前柱为全麻石石雕,后柱下半截为麻石段,各柱之下均有石础,造型古朴,纹样大方,形制多样[9]。这从侧面说明了石雕对于流坑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流坑古村现存的许多石雕石刻虽然陈旧残破,它蕴含的古典风貌、端壮气势却令人叹为观止。
流坑古村的石雕雕刻手法分为很多种类,例如线雕、浮雕、圆雕等。石雕的用材也是采用村落周边丰富的花岗岩以及红石,其质地坚硬,相对于木雕,石雕的保存时间更加久远,不会受当地潮湿多雨气候的影响,反而经过长时间的洗礼会显得更加古朴厚重[10]。从石雕艺术可以看出,临川文化下的人们受当时政治思想的影响,将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在石雕艺术中得以体现,石雕与流坑古村的建筑完美融合,甚至将建筑文化进行了升华,是临川文化在聚落建筑文化中的体现,有着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4.3 砖雕
砖雕同石雕与木雕一样在流坑聚落建筑的装饰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前两者组成了临川文化区域传统聚落空间的标志性建筑装饰部分。砖雕的由来可从东周说起,东周的瓦当与汉朝的画像砖是砖雕的前身,以前还经常被使用在官家以及大门户的居住空间中。流坑古村虽然交通闭塞,但是因为达官贵人较多,所以也将砖雕这一建筑装饰手法引入到了当地的建筑装饰空间中。
从雕刻蕴含的文化来看,在流坑古村被运用在许多建筑之上,例如门楼、墙壁、天井墙等显眼的位置都可以看见砖雕的身影,这足以说明砖雕在整个建筑空间的装饰中有着突出地位。砖雕的图案也是根据屋主人的身份与期望来进行雕刻的,其不仅体现了屋主人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雕刻的手法来看,其地理环境有着丰富的麻岩、青石板等天然岩石,村落建筑材料以青砖为主,砖雕大部分的原材料也使用青砖来雕刻。明代以前,砖雕的风格较为典雅和简洁。清代开始,砖雕逐渐走向繁杂,但是总的来说,工艺技术和造型审美上都达到完美的统一,题材内容多为表现人们理想生活的场景[11]。
流坑古村这3种雕刻艺术不仅表现的是一种雕刻形式,更是临川文化区域社会发展的一面缩影,体现了当时的建筑装饰文化,同时也是传统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通过对3种雕刻艺术的分析,可以深入研究学习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以及审美,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临川文化区域的雕刻艺术高超且技艺精湛。流坑古村的建筑装饰艺术为我们展现了临川文化区域的传统建筑艺术精华,不仅让我们了解古人的建筑装饰手法,而且也为现代古建筑的保护以及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文化理论支撑。
5 结论
临川区域的传统聚落建筑文化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是从传统文化、家族观念影响、信奉文化、建筑用材、空间特征、装饰手法等多方面进行展现。在空间环境上,这类传统村落更注重民居建筑与景观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展现了诸多的极具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内涵,同时还留下众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12];同时半封闭的居住环境又使其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形态,人们的活动与思想又牵制着整个聚落建筑的演变与发展。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与探索,了解到在整个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对临川文化区域传统乡村聚落及其建筑形态演变研究有着厚实的文化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