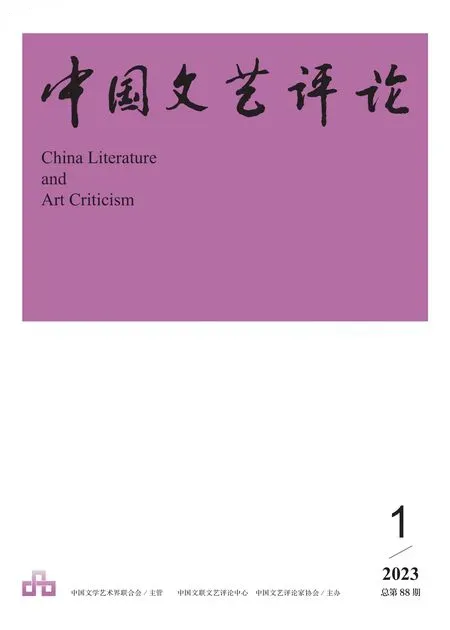皮娜·鲍什舞蹈剧场中的身体语言及文化逻辑
■ 马春靓
皮娜·鲍什是非常受欢迎的德国现代舞蹈家。她带领的乌珀塔尔舞蹈剧场是德国重要的文化窗口,也是当代三大新舞蹈流派之一。每当人们谈起皮娜,都会用一种深情且痴迷的口吻来描述对她的喜爱。每当人们讨论起皮娜舞蹈剧场的肢体语言时,却众说纷纭,有时还会争论不休。众所周知,皮娜舞蹈剧场的肢体语言区别于其他现代舞派别的典型性特征:舞者的肢体语言抛弃了规范化的技术身体,将肢体语言回归日常,舞蹈剧场中舞者的身体以一种“无形”的状态呈现在舞台上。皮娜让舞者在表演时说话、抽烟、喝水……使作品呈现了复杂的日常场景,为此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与争论。对于这一身体特征,有的人认为舞蹈剧场作为一种以肢体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舞蹈形式,虽然增加了台词等表现形式,但还是属于舞蹈的范畴;有的人认为日常化肢体语言和台词的加入,使舞蹈剧场更接近于传统的戏剧,让舞蹈剧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从舞蹈走向戏剧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无论评论界如何争论,他们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是,皮娜舞蹈剧场的肢体语言特征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因此,舞蹈剧场中肢体语言的“无法言说”[1]埃里希·弗洛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佛洛依德》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的过滤器”这个体现意义压抑性的有趣观念。一个社会总是会通过允许言说或鼓励言说,从而让无法言说的东西通过过滤器一样的东西被截留,社会的过滤器往往通过语言生产共同经验的方式,从而阻止一些共同经验所不允许的个人经验成为社会意识。与此同时,当人们面对新鲜的事物,没有办法用具有共识性的语言将其进行描述。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种类的常识,不同类型的思维,不同的逻辑体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他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当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时,这个‘社会过滤器’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变……在一定时期,不能通过其‘社会过滤器’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也就‘不能言传’”。参见[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佛洛依德》,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成为讨论舞蹈剧场的焦点。在这里,由肢体语言的非技术化、日常化问题引发的概念之争,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舞蹈剧场背后的矛盾,这种接近于生活行为的肢体语言还是舞蹈吗?我们如何对舞蹈剧场中的肢体语言进行分析与界定成为本文首先要讨论的话题。
一、日常行为是舞蹈吗?
从舞蹈发展的历史来看,舞蹈是一种对自然的模仿与想象。最早的舞蹈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模仿,人们通过身体模仿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记录生活、表达对自然的崇拜。在人类还未建立语言系统的时期,舞蹈成为人类的主要交流方式。早期的舞蹈中包含着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直接经验,成为“一种混杂着敬畏与非现实性的灵韵,包含了‘精神性’与‘理想性’的舞蹈形式”[2][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日常的劳作从手工制作转变为机械制造,从而导致人们日常的动作经验变得相对单一。由此,舞蹈也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的、充满生存经验的表达方式,而成为彰显身份的附属品。其中芭蕾舞作为具有阶级身份和高尚趣味的象征,是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其精准规范的表现方式彰显着资本主义贵族精致且奢华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追求,成为一种精致生活的再现。但其表现形式与内容“从普通的经验中分离开,成为趣味的标志和特殊文化的证明”[3]同上,第10页。,导致芭蕾舞作品与现实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裂痕。18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现代舞也随之应运而生。现代舞者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试图通过身体的解放追求心灵的自由与平等。科学理性看待身体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不再盲目崇拜个人情感,用身体塑造一种具有社会反思性的语言成为现代舞不断发展的动力。肢体语言上的独立、抽象与神秘是现代舞肢体语言的标志,但现代舞看起来似乎与日常生活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距离。
在20世纪70年代,皮娜·鲍什专注于继续发展“舞蹈剧场”的概念。皮娜舞蹈剧场中的身体语言,既没有像芭蕾舞那样束缚人的身体,也没有像之前的现代舞那样不断创生一种解放身体的训练技术。“皮娜·鲍什对以往的舞蹈几乎可以说是破坏,她居然经常让演员不去做展示身体美和技巧的舞蹈,而是让他们像平常人一样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甚至是做化妆、送咖啡、说话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1][德]约亨·施密特:《皮娜·鲍什:为对抗恐惧而舞蹈》,林倩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有的人说,皮娜是采取了戏剧的表现形式,因为在戏剧的表演中,吃饭、说话等行为在舞台上发生是被允许的。但与戏剧不同的是,皮娜舞蹈剧场主要的表现形式还是肢体语言,只是更多地使用了非技术化的肢体语言,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用一个明确的概念对舞蹈剧场中的身体语言进行界定与总结。“皮娜被称为‘完全令人震惊的、令人兴奋的、运动中的身体奇观’。然而,这并没有完全捕捉到它所创造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图像世界。”[2]Jeremy Foster ed., Dancing on the grave of industry:Wenders, Bausch and the affectivere-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Cultural Geographies, 25: 2(2018).于是,皮娜舞蹈剧场的身体语言的独特性在这里凸显。
首先,在皮娜的舞蹈剧场中,身体背离了技术化的肢体语言,呈现多种生命的感知强度。在传统的现代舞中,艺术家尽可能创生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身体技术,以此作为具有标志性的训练方式。而皮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作品是对传统舞蹈形式和戏剧的攻击,动作不再是以舞蹈为主要对象和媒介。相反,语言、演讲和表演,音乐和唱歌”[3]Siegmund Gerald., Doing the Contemporary: Pina Bausch as a Conceptual Artist, Dance Research Journal, 50: 2 (2018).等多种艺术形式都出现在舞蹈剧场的表演中。在皮娜的舞蹈剧场中,舞者的表演极少使用规范化的身体技术,更多地使用日常姿势或手势作为表现方式。舞者经常采用日常奔跑或行走作为上下场的动作;舞者时而挥动手臂,在下肢动作的配合下站立、移动、跳跃或跌倒;时而与观众说话、呐喊;时而用生活化的动作,如画口红、穿衣服等行为进行表演。为了让作品的日常行为更加真实与丰富,皮娜还大胆地启用非职业舞者的身体,让真正的日常化身体介入表演。在《交际场》的三个版本中,中年版由专业舞者表演,而青年版和老年版都是由非职业舞者表演。在作品中,男女演员相互拥抱、追逐……大量地使用日常行为。由于在三个版本中表演者的年龄、生活经验与表演经验各不相同,在相同的动作编排下,作品分别呈现出年轻人面对异性的羞涩、中年人面对异性的期待和老年人面对异性的从容三种表演效果。因此,与皮娜舞蹈剧场之前的现代舞相比,舞蹈剧场中的肢体语言不再做技术化动作的加工与抽象性的表达,而是将动作回归日常,缩减动作空间,并通过重复动作释放舞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使身体成为某种情感性的外化。皮娜说:“重复不是重复……同样的动作会让你在最后感觉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我重复了一些东西,三次之后,这个人就会作出反应……观众还是舞者?……两者都有。”[1]Alexandra Kolb., Choreography in the Age of Post-Privacy: Sex, Intimacy, and Disclosure in Pina Bausch and Michael Parmenter, Dance Chronicle, 43: 1 (2020).也就是说,皮娜通过重复动作制造一种视觉冲击力,让观众在观看时与舞者共情,体验剧中人物的感受,从而释放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情感强度。
其次,皮娜舞蹈剧场的身体逃离了音乐对动作的限制,使音乐成为身体的“见证者”。在传统的舞蹈表演中,音乐作为宣泄情感、营造氛围的主要形式,限制着舞者动作的节奏与速度。在皮娜的舞蹈剧场中,舞者的肢体动作自由运动,动作不跟随音乐的节奏而表演。笔者通过观察发现,作品中舞者的身体主要呈现出三种节奏:积极的、消极的、平稳的,而舞者的身体所呈现的自身节奏却与音乐无关。舞者在积极的身体节奏中,动作会表现出强大的力量,而且力量会逐渐加强;舞者在消极的身体节奏中,动作会表现得无力,而且逐渐轻柔;舞者在平稳的身体节奏中,动作既不强也不弱,身体节奏保持一种平稳的状态。在表演中,这三种节奏虽然没有主次之分,但会相互衔接、重叠……从而构成舞蹈剧场独特的身体节奏。在这里,舞者不再演绎音乐或配合音乐的节奏,而是通过身体不同的强度创生节奏,使节奏成为一种释放感觉的形象,以此将观众带入到某种感受中。而音乐在作品中则成为了舞者身体的背景,舞者时而与音乐同步,时而与音乐分离,完全不受音乐的控制,甚至还让舞者在表演现场控制音乐的节奏(例如《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后面统称为《蓝胡子》)。如此看来,在舞蹈剧场中,舞者的身体“节奏达到了一种极大的强度与广度,进入一种被迫产生的,为它带来自足性的运动,并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时间的感觉”[2][法]吉尔·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页。。皮娜舞蹈剧场中的音乐仿佛不再是支持肢体语言表情达意的手段,而是帮助身体从固有的编舞经验中逃离出来的背景或借口。具有积极的、消极的、平稳的节奏的肢体动作仿佛就是人生命经验的投射,将人存活于世的态度与选择呈现在观众面前。这里的肢体动作逃离了身体语言的日常秩序,以一种生命感知的强度呈现在舞台上。
再次,皮娜舞蹈剧场中的身体逃脱服装对身体的束缚,以裸露的身体宣示着身体的主体性回归。在传统的舞蹈表演中,服装是交代人物身份、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例如在现代舞的表演中,宽松肥大的服装成为暗示身体解放的标志。而在皮娜的舞蹈剧场中,她喜欢让女舞者穿上晚礼裙、男舞者穿衬衫或西装。但往往在表演的过程中皮娜会有意无意地让舞者的服装逐渐脱落。甚至有的时候女舞者根本就不穿上衣(如《康乃馨》中女舞者只穿一条内裤,上身挂着一台手风琴)。在舞蹈剧场中,服装不再是传递人物特征的象征,而被看作束缚身体或是思想的桎梏。舞者的服装从身上脱落,仿佛是身体对服装的逃逸。逃离服装的身体不再是作为一种客体依附于服装中,而裸露的身体则作为感受周遭的主体,呈现自身的纯粹性。
最后,皮娜的舞蹈剧场试图挣脱舞台空间对身体的限制,制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表演。皮娜让舞蹈剧场的表演不局限于剧场的舞台上,她将观众席,甚至是街道、工厂等都作为表演空间。与此同时,皮娜让观众也不再仅仅是观众,观众在接受舞者的茶杯、为舞者送硬币等行为中被无意识地带入作品,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以此将剧场空间制造成具有沉浸式体验的空间。这种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从看舞者感受日常变成了和舞者一起感受日常,使观众和舞者之间快速共情。当观众无意识地走进作品的表演时,作品也走进观众的内心。观众通过参与作品,将隐藏在心中不会言说、不能言说、不敢言说的感受进行了体验,从而使观众对舞蹈剧场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既喜欢又憎恨的矛盾感。这种矛盾感所产生的精神撞击,让观众脱离了日常情感的逻辑序列,直面真实的生活。由于这种体验太真实了,没有合适的语言将其表达,由此,观众对皮娜舞蹈剧场就留下了不可言说的印象。
由此可见,皮娜舞蹈剧场通过肢体语言背离了技术化的身体,逃脱音乐、舞台、服装对身体的限制,形成以身体为引导的、打破舞台原有空间的身体冲动,从而创生一种新的充满感情张力的表演方式。其中,舞者的身体在不同的作品情节下呈现出的肢体反应,没有边界与规范、找不到规律。身体与剧场中所有的非舞蹈之物进行互动,制造出一种身体的力被外界的环境所控制的感觉。皮娜以此拓宽身体的表现形式,不再以规范动作界定身体形态的美与丑,而是以一种身体的反规训让肢体语言和舞台上的物一起回归到现实的经验中去。皮娜试图通过日常姿势与日常物的互动,唤醒被人类遗忘的历史、社会或生活的本质,以此解放身体,让身体拥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舞蹈剧场在沉浸式的剧场空间中,舞台上的突发事件使观赏者猝不及防,以至于无法用原有的观赏经验对舞台上的动作进行思考,导致观众产生无法言说的感受。在这里,笔者将这种无法言说的表意方式暂且称为“反重力”的身体冲动。
二、身体姿态作为“反重力”的身体冲动
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皮娜的舞蹈剧场大多数“通过一系列的姿势来呈现爱情产生的冲突,这些姿势描绘了一种对接触和了解的温柔渴望如何转化为一种控制所爱之人的暴力和强迫性欲望”[1]Meg Mumford., Pina Bausch Choreographs Blaubart:A Transgressive or Regressive Act?,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57: 1 (2004).。在这里,“姿势”[2]姿势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意为身体呈现的样子。在众多哲学家、理论家的研究中,姿势往往指向英文Gesture。Gesture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中文名词含义为手势、姿势、示意动作或者是姿态、表示。虽然多个翻译版本对Gesture有不同的中文翻译,但都从属于英文Gesture的概念范畴。Gesture在布莱希特的研究中,大多数被翻译为姿态,认为姿态是说话时说话人对其他人所采取的态度,强调言语主体处在某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而产生的行为上的选择与示范。在安托南·阿尔托的研究中,Gesture被翻译成姿势。阿尔托对于戏剧表演中身体姿势的独特性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想法。他认为戏剧身体美学在于通过身体的姿势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而身心合一是通过身体感官出发,促进心理变化,以此发泄内心中的感受,达到释放生命力量的目的。他所研究的残酷戏剧就是通过演员将残忍的内容在舞台上表演,激起观众内心的恐怖力量,从而引起观众肉体、精神、道德层面的变化。在吉奥乔·阿甘本的研究中,英文Gesture分别被翻译为姿态或姿势,他认为Gesture不仅是身体意义上的某种姿势,更与历史、政治、哲学密不可分。身体姿势中既有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有对未来的展望,是一种生命经验的表征。阿甘本的姿势论探讨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为生命政治论打下了基础。关于Gesture还有很多理论家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笔者就不在这里逐一赘述。从动作层面来看是指日常生活中由身体各部位的变化呈现身体的整体性运动。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身体动作,而是指人在某一个环境或情境下呈现的一种身体状态,例如走路、说话、睡觉、系鞋带等动作。它是一个瞬间的停顿,是在一个动作序列的铺垫下凸显出身体某一个停顿的瞬间。在这里,“每个姿态都是一种命运”[3][意]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陈国年校,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也就是说,姿势强调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动作,而是人在某种环境下受情感支配的一系列身体反应。姿势可以展现人的内心世界,既可以表达对自我的感受,也可以表达对外在环境的一种态度。而手势指的是由臂部、手部,甚至细微到手指的动作构成的身体局部运动,主要强调手臂上的动作,多用于与人沟通时的辅助动作,具有更强的指示性。
姿势和手势相比,姿势是全身各部位运动的综合,动作逻辑更为复杂。姿势具有功能性,也具有表达性。无论是内在感受还是外在感知,均会通过姿势进行有意和无意的呈现。而手势局限于手和臂部动作,动作逻辑相较简单。手势虽然同时具有功能性和表达性,但更强调动作的功能性。手势更多地伴随着语言的表达而发生。特别强调的是,手势一直以来作为一种代替语言的表达,是特殊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在这里,日常的姿势、手势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都是特指舞蹈剧场中舞者身体的动作方式。姿态在这里指一种具有态度的姿势或手势,表达着动作施动者的心理活动。而姿势、手势与姿态之间呈现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姿势或手势表现出一种心理活动时则构成姿态,即有态度的姿势或手势。这里的姿态是被赋予文化性内涵的身体符号,是研究皮娜舞蹈剧场肢体语言的文本参照。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无意识地产生大量的姿势或手势,有意或无意地呈现当下的某种状态。姿势或手势包含着人类生活中丰富且复杂的生命经验,是充满生命力的情感的外化。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中曾经分析了主观意识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或主要行为者把行为与主观意识联系起来,行为就是人的一种态度(而不管是外在举动或内心活动,也不管是疏懒或忍耐)。”[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姿势或手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内在意识的外在呈现,而这个动作更应该被称为姿态。姿态中不再指具体的动作,而是指向作为主体的施动者其表达的内心思想或感受。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提出:“躯体是思维达到非思维,即生活,而要存身或者必须存身的地方……生活的类别,准确地讲,是指躯体的态度及其姿势。身体在困倦、酩酊大醉、忍受剧痛和抵抗疾病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能干些什么。”[2][法]吉尔·德勒兹:《时间—影像》,谢强、蔡若明、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人物受限于自身躯体的态度,而应从中提炼的,是姿态。”[3]同上,第305页。德勒兹认为,在电影的拍摄中,对日常生活姿势的拍摄试图消解姿势的日常表意功能,回归身体自身,探索姿势的纯粹性,就是姿态。以此类推,如果把皮娜舞蹈剧场中的肢体语言看成是具有主观意识的姿态,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行为的再现,其背后隐藏的生产逻辑在这里凸显出来。由此,在对皮娜舞蹈剧场的肢体语言的研究中,笔者试图将姿态看作由动作力度配合身体所使用的空间、流动感知,以及动作速度共同构成的一种身体状态。笔者通过作品分析,发现皮娜舞蹈剧场中的肢体语言主要呈现为坠落与漂浮两种姿态。
坠落的姿态体现在舞者的身体动作表现出一种对地球引力的回归。即舞者的身体从高处向地面坠落,其中受身体节奏的影响,舞者表现出不同空间、不同力度、不同节奏的坠落。首先,低空坠落表现在舞者身体从站立的中空间姿势向地面(低空间)坠落。例如在《蓝胡子》中,男舞者将女舞者推倒在地,女舞者从站立姿态毫无反抗地跌倒在地。低空坠落的方式是舞者将身体充分回归到由地球引力而形成的与地面的接触,并表现出一种顺从地球引力的姿态。其次,中空坠落体现为舞者在身体保持站立的形态下,主动或被动地向低空间下沉。身体没有从中空间完全跌入到低空间,而是尽可能地支撑身体,从下沉的坠落再回到直立的姿态上,由此形成通过膝盖弯曲颤动或身体起伏的姿态。例如在《春之祭》中,面对穿红裙子的舞者,其他舞者通过颤动膝盖让身体的重心快速下沉并快速回弹。舞者通过这个动作的重复,为舞台制造了紧迫而冷漠的氛围,让观众感受到献祭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村民们事不关己的冷漠。在直立的姿态上,舞者通过具有空间变化的动作和空间的摇摆与不确定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身体态度。最后,高空坠落是以舞者身体从高处瞬间向低空间坠落,制造出一种出其不意的危险而紧张的气氛。在《华尔兹》中,一名女舞者站在一位男舞者的肩膀上,并扑向站在前方的另一位男舞者的身上。由于另一位男舞者和站在别人肩膀上的女舞者的高度差距之大,人们会担心站在地面上的男舞者可能会接不住女舞者而让其受伤。在作品中,女舞者奋不顾身地向男舞者扑去。这种突如其来的高空坠落让人看了心惊肉跳,许久不能平静。因此,高空坠落呈现了身体由高到低的下沉与坠落,将身体对地球引力的主动顺从进行了演绎。
除此之外,肢体动作对音乐节奏的逃离、服装从身体上的滑落、舞者从舞台上走下进入观众席……都可以被视为坠落的姿态。动作与音乐的不配合,使得音乐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中立地存在于作品中;服装从身上被动地滑落,舞者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感受着身体的逃逸;舞者从舞台上走向观众席,放弃了舞台上神圣的光环,积极地将身体投入日常空间,以此构成了具有视觉张力的舞蹈剧场。在这里,每一位观众被发生在眼前的坠落所震惊,深陷其中,那种恐惧感和紧迫感仿佛就要从身体里迸发出来。这种感受正是皮娜通过作品想要达到的一种效果,她要让观众知道“我舞蹈,因为我悲伤”的艺术哲思到底意味着什么。坠落的姿态是舞者身体对重力的多重顺从,观众通过这种顺从的感觉带领着身体与意识回到现实中来,从而认清现实、释放情感。皮娜通过低空、中空和高空三重空间中消极的、中立的、积极的坠落,分别对现代社会的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表达。不同程度的坠落仿佛将被困顿的、无法言说的、充满差异性的个人感受进行了讨论。
有趣的是,不同空间与形式的坠落,表面来看是对地球引力的一种顺从,其中也有对坠落的抵制或反抗,即矛盾式坠落。在中空间坠落中,反复颤动的膝盖在坠落中不断回归原始站立状态的姿势。这个姿势将简单的顺从式坠落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使其中充满了反抗的意味。借此,我们可以看到皮娜舞蹈剧场中肢体语言对规范的抵抗,即通过不同程度的坠落实现了对生命经验同一性的抵抗。皮娜用多重坠落呈现了一种复杂的身体力量,从而形成一种运动的运动。这种运动是来自于身体上的各种力量,这种力量时而从上到下、时而来回反复、时而直击地面,因此舞者的身体时而自由无形、时而紧张拘谨。“坠落构成了它最内在的运动……坠落是感觉中最活生生的东西,感觉在坠落中能够感到自己是活生生的……它可以是一种舒张、膨胀或消散,但也可以是一种增强。”[1][法]吉尔·德勒兹:《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5页。舞者的身体力量通过与外界空间的交合,不断地生成新的姿态,从而发挥身体各部位组织极大的自由性,积极地创造出无形的身体。这种无形的身体打破了传统身体语言,让观众无法用一种技术或语言将其完整地概括与总结,让观看皮娜舞蹈剧场的人产生暂时性的“失语”。但是,正是无法对皮娜作品的肢体语言进行概括与总结,才使得舞蹈剧场中肢体语言的无法言说成为皮娜舞蹈剧场区别于其他现代舞、充满特异性的表意方式。
在皮娜的舞蹈剧场中,由内力引导身体外形形成的姿态并不是单一的。除了坠落之外,舞者的身体还呈现了第二种姿态——漂浮。漂浮体现为一种轻盈的、自由的、沉浸其中的身体状态。舞者以一种看似轻松的姿势来传递一种自我沉浸式的体验。通过观察,漂浮姿态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漂浮姿态是消极地漂浮,即舞者的身体在外界力量牵引下被迫呈现脱离地球引力的轻盈感。例如在作品《交际场》中,被男舞者抱起称重的女舞者、在《蓝胡子》中被“伯爵”抛在空中的妻子……舞者的身体通过外力的干预,被动地离开地面,身体呈现出一种被迫离开地球引力的感觉。第二种漂浮姿态是中立地漂浮,体现在舞者既不主动、也不被动地漂浮。这种漂浮通过自身力量与外界环境调和,在外界环境的牵引下呈现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例如一名男舞者安静地躺在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缸里面,不做任何动作,只是让身体借助水的浮力漂浮起来。这种漂浮是人通过借助外界环境产生失重的感觉。第三种漂浮姿态是积极地漂浮,体现在坠落前失重的瞬间,舞者主动地停留在空中,从而体验到宛如飞翔的瞬间漂浮。例如在电影《皮娜》中,女舞者在树林的空地上行走,她一只脚踩在椅子的椅面上,另一只脚踩在椅子靠背上,通过身体重量的前倾,把椅子踩倒,身体在伴随着椅子向地面倾斜的过程中逐渐坠落到地上。在椅子倾倒的过程中,女舞者身体向天空挺拔而起,尽可能地将身体停留在空中。伴随着椅子的跌落,舞者的身体会体验到瞬间的失重感,并伴随着椅子共同跌落到地上。在这里,舞者让身体以多种形式漂浮起来,仿佛人们在积极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无能为力时,虽然要坠落,但还是要积极地漂浮。
坠落姿态在与漂浮的姿态之间建构了充满身体张力的感觉系统,让观众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充满差异性的生命经验。在这里,坠落是对地球引力的顺从,而漂浮则是对地球引力的反抗。舞者让身体以多种形式漂浮起来,仿佛在释放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无能为力时的多种选择。正如舞蹈剧场中呈现的那样,有的人选择顺从,有的人选择反抗,有的人则沉浸其中不加思考。有趣的是,人不可能真正地漂浮,正如人永远离不开地球的引力一样,只能让感觉漂浮起来。两种姿态的呈现需要通过舞者与环境的调和,无论是积极的、中立的,还是消极的。漂浮是身体各部分力的集合,是微妙而无形的。漂浮与坠落两种姿态通过舞者以多重不确定力的交融状态得以实现。
因此,反重力身体冲动不仅指向舞者身体对地球引力的顺从或抵抗,而且是一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身体感受的释放。皮娜通过不同形式的接纳和放弃身体的重力,试图创造一种对重力既反抗又接纳的身体冲动。这种身体冲动来自现实生活中那种被身体之外的力所控制、却不断抵抗这种力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皮娜在作品的创编上经常使用重复某种姿势来制造氛围,从而表达某种情感。在这里,“重复是破坏任何线性时间序列的核心策略。由于重复的姿势,舞台上的场景似乎被时间冻结了。它们创造的印象是静止的和超越时间的图像,而图像是通过‘歇斯底里’的重复姿势和运动,通过重复在时间上产生了一种失语,一种东西(一个动作,一种情感)的失语,这种失语不会消失,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因此,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一个场景是由许多重复的时刻组成的表演结构,这些时刻拒绝离开,但从现在开始。没有解决,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或目的地,姿态就会退回到它自己身上,展示自己,拖着过去,过去没有在现在找到它的位置,无法继续前进”[1]Siegmund Gerald., Doing the Contemporary: Pina Bausch as a Conceptual Artist, Dance Research Journal, 50: 2 (2018).,由此构成了皮娜·鲍什舞蹈剧场身体姿态的生产逻辑。
在这里,皮娜让身体不再具有象征性,而是让身体回归物质层面,表达某种失语或无法言说。她让身体与周边所有物产生连接,并以多种充满情感冲动的、具有杂多力量的身体姿势进行拼贴组合,以此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充满差异性的、无法言说的感受。在皮娜舞蹈剧场中,从微观的层面上看,接近日常行为的动作本身是凌乱无章的,虽然有重复,但是无法总结其规律。从宏观的角度上看,由众多力量构成的身体冲动凸显了舞蹈剧场身体语言的内在逻辑。因此,由充满差异性的身体冲动构成的舞蹈剧场,其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重点内容。
三、身体姿态的二律背反
皮娜舞蹈剧场与之前的舞蹈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创造的漂浮姿态作为一种身体反重力的尝试,与人类探索宇宙未知一样,打破空间与时间的界限,以不确定的、无规则的、充满差异的、碎片式的身体语言,消解传统技术的权威性,摧毁、打破话语霸权根深蒂固的统治。与此同时,皮娜不仅让舞者的身体漂浮,也让舞者的身体坠落。因为无论人类怎样努力漂浮,终将坠落。皮娜似乎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以一种从容的态度让身体在漂浮与坠落之间来回抉择。而皮娜似乎冷静地面对现实,既不逃离,也不抗拒,只是在作品中表达着这种感受。那种对坠落的逃离和对漂浮的期待作为一种隐喻,将人复杂而矛盾的思想通过舞者身体的姿态呈现在舞台上,仿佛将人一生中的欲望与追求、矛盾与抉择在漂浮与坠落之间进行了表达。
在这里,我们能够理解皮娜为什么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因为她认为关于无法言说的体验,每个人都深陷其中,谁都无法逃脱。因此,皮娜在作品中设计了坠落与漂浮的姿态,并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呈现身体内在的冲动。也就是说,如果坠落的姿态是通过对地球引力的顺从来呈现现代人面对生活的沮丧与无奈的话,那么漂浮则通过暂时逃离地球引力呈现一种对美好的想象。正是因为坠落的姿态是人类不可抗拒之举,漂浮则显得尤为珍贵。漂浮以一种不在场的形式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映衬出现实中坠落的无奈。而在这样充满强烈生命气息的想象中,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漂浮去追求那一瞬间的掌控感。但殊不知,现代社会的人们被机械化、被物化、被景观化……之后,人们仿佛已经忘记真正实现自由的漂浮是怎样的。因此,皮娜舞蹈剧场中舞者所呈现的漂浮是一种被现实生活挤压变形的、扭曲的、疯狂的姿态。
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哲学概念。“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指由于人类理性认识的辩证性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体,误把宇宙理念当作认识对象,用说明现象的东西去说明它,这就必然产生二律背反。”[1][英]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近代哲学的兴起》,杨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190页。而皮娜舞蹈剧场中坠落与漂浮的姿态作为一种身体的冲动,则呈现了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漂浮与坠落的身体分别暗含着顺从与抵抗的内涵,双方分别以不在场的形式成就着对方。在作品中,皮娜通过人们无法脱离地球引力的召唤,不断地让演员坠落,以此来呈现现实中的冷漠、顺从与自投罗网。而漂浮作为坠落的补充,瞬间呈现在舞台上,成为坠落中的美好瞬间。与之前技术化的舞蹈形式相比,皮娜的舞蹈剧场仿佛通过释放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顺从了人在情感驱动下的一种应激反应,制造了一种虚情假意的反规训,以此创生出一种反重力身体冲动。这种身体冲动从表面上来看,已具有二律背反的漂浮与坠落的姿态,释放身体的本能,对现实生活的多重经验进行隐喻。进一步来说,皮娜通过漂浮与坠落的姿态,试图动摇理性主义下的艺术编码。她通过对矛盾姿态的坚持,释放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感受,以此推翻原本被理性控制的冷静世界,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身体语言。这种震撼的效果,不是让观众在剧场中通过理性的分析想到什么,而是让观众在演出的现场感受到什么。皮娜似乎以此唤醒人们的感知系统,对理性主义进行抨击。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经在对辩证法的阐述中提出:本不相关的事物碰撞在一起的震撼,可以让你获得批判现实的武器。皮娜舞蹈剧场的身体姿态,以一种暗含二律背反的身体姿态与艺术哲思,将无法言说的生活体验勇敢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直面这种体验。这种感受太震撼了,观众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和词汇对其复杂性进行描述,只能通过对不同程度的坠落和漂浮来体验与感受这种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情感,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获得对理性社会进行批判的辩证态度。因此,这种看似反抗实则逃离的反重力身体冲动给了我们全新的观赏体验。这种感受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一种不遮盖、不掩饰,只是将感受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方式。正如在纪录片中,记者问皮娜未来会怎样时,皮娜非常确定地回答:“世界有那么多严重的问题,我不敢问自己希望未来能获得什么。当然拥有很多力量和爱吧。”[1]转引自[德]约亨·施密特:《皮娜·鲍什:为对抗恐惧而舞蹈》,林倩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在皮娜的舞蹈剧场中,由于坠落与漂浮的姿态过于琐碎与繁杂,以至于有些动作无法通过文字进行描述。但也正因为如此,反倒印证了皮娜舞蹈剧场无法言说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研究者绞尽脑汁地分析与整理皮娜舞蹈剧场肢体语言的特异性,但也无法用语言将其进行完全的整理与界定。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法规范和统一的肢体语言,构成了皮娜舞蹈剧场的身体独特性。虽然皮娜已经不在人世,其作品是有限的。但每次欣赏她的作品,都会在琐碎的动作中体会到新的感受。遗憾的是,新的发现未必可以用恰当的语言将其言说。皮娜将身体无法言说的情感作为创作动机,也许这才是舞蹈剧场肢体语言的真实面孔。然而,这种姿态是富有诗意的,通过以现在的姿态作为媒介,不仅重复过去,也展现未来。这种诗意不仅是一种永恒回归的、体现生命强度的姿态,更是一种敞开式的、时刻迎接一切未知的姿态,通过生命中的差异和强度呈现其真实的形态。她想通过舞蹈剧场告诉观众: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只要你感受到了,即便无法言说,那就慢慢地体会吧。
总的来说,皮娜创生了一套特立独行的身体逻辑,正如她勇敢地接受来自身体内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感受。她试图抛弃记忆的理性思考,通过身体感受的具身化呈现自身、寻找答案。皮娜将这种来自身体内部的、杂多的、不可区分的经验,以碎片化的拼贴呈现在舞台上。这种充满冲动的身体是个性的,也是独特的。皮娜深知这种身体冲动是对历史语境桎梏的逃离,是对秩序社会的反叛。舞蹈剧场中的身体语言通过多重无法言说的力的叠加与汇聚,成为皮娜创作作品中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也是皮娜思考未来的重要方式。这种对未知的探索方式揭示了为什么皮娜从来不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阐释,因为她在等待事件的发生与结束。即便“皮娜·鲍什习惯坐在剧场里面的最后一排观看自己的舞作演出,观众常常会往她的身上吐口水,扯她的头发”[2][德]约亨·施密特:《皮娜·鲍什:为对抗恐惧而舞蹈》,林倩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页。,皮娜也只是静静地接受这一切。就算是很害怕甚至是恐惧,她也会将这种感受铭记在心,将其视为创作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动力和源泉。或许,这就是她寻找答案、解疑答惑的一种方式吧。
四、结语
一个舞蹈作品的魅力来源于作品给观众带来的精神上的震撼。皮娜的舞蹈剧场不再像以往的现代作品那样,通过技术解放身体,从而呈现思想的超越。皮娜让舞者的身体处于情绪的释放状态,让情感从已有的理解和认知中释放出来,让内在的、看不见的力量变得看得见。在这些作品中,舞者的姿态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多重情感的综合,是一种在本能驱动下的情动,是一种对看不见的力量的截取与测定。正如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所言:“艺术不是再现、概念或判断,它是以非认知和非智性的方式来进行感受性的思考。”[1]转引自[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由于皮娜舞蹈剧场中的感觉层次过于丰富,多重感觉的混杂成为创生肢体语言的起点。以外在的肢体语言表现身体内部感受的速度、力量,是一种内在的延续。作品中看似日常化的动作都是在现实生活感受驱动下的一种情感的释放。其肢体语言让舞者和观众都回归到真正自我的经验中,去除技术性动作塑造外形的创作模式,实现从艺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退化与回归,将内在经验从身体的起伏中迸发出来。
与之前技术化的舞蹈形式相比,皮娜的舞蹈剧场仿佛通过释放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以积极的、中立的、消极的漂浮与坠落呈现人生百态,将人生命经验的多种选择与可能性表达出来。皮娜摒弃了现代舞原有的抽象化、技术化的肢体语言,通过回归日常行为的姿态,创生身体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肢体语言的日常化顺从了人在情感驱动下的一种应激反应。作品中坠落与漂浮的姿态是不同程度感知的体现。漂浮的姿态代表着人勇敢面对真实世界,迎接一切可能性的态度和敢于想象未来的勇气,而坠落则是迎接挑战的结果。正如在分析坠落与漂浮时阐释的那样,漂浮终将走向坠落,坠落才是拥抱现实世界的姿态。皮娜通过肢体语言的日常化,试图动摇理性主义下的艺术编码,通过对具有众多力量的矛盾姿态的坚持,推翻原本被理性控制的冷静世界,创造出一种本不相关的事物碰撞在一起的震撼,让观众获得批判现实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