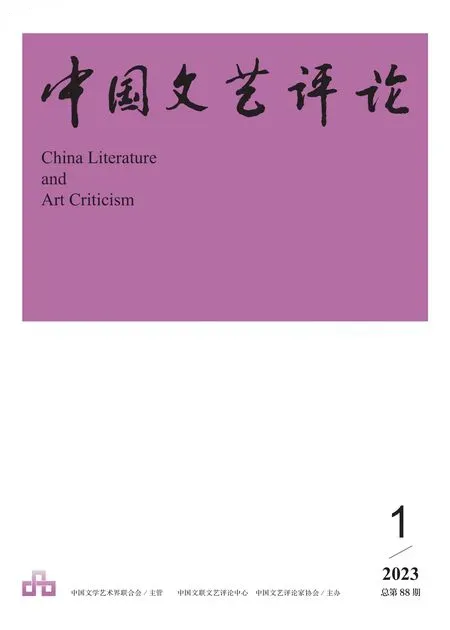艺术创作立足“情感之维”的意义辨析
■ 周 星
一、艺术创作与感知的要旨在于“情感之维”
关于艺术的认知有种种角度的差异性存在,“先辈们对艺术这种特殊的精神现象的探索早就开始,但迄今为止,人言言殊,莫衷一是”[1]仇春霖主编:《大学美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古今中外的“艺术”概念也千差万别,至今没有为人所共同首肯的艺术概念取得决定性的接受信用,但这似乎一点都不妨碍人们基本指向艺术是什么和艺术对象的自然所在。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对艺术对象大同小异的理解却都聚焦于音乐、绘画、戏剧、舞蹈等表现形态的“艺术”对象而毫不生疑。反而是理论家一旦需要解说自己的艺术观念认识时,用了不少的理性语言去辨析,似乎有隔创作感兴的概念理解,于是对于创作者而言时常觉得匪夷所思。在这里,如何看待创作和认识的角度值得探讨。而理论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可以评价创作的内在理解,创作何以保持自身的规则而实现理论思想的理解,都需要加以辨析。时至今日,人们所共知的艺术是一个称谓宏大而错综复杂的对象所指,支撑每一门艺术的感性思维的独特性,不仅仅依赖于艺术语言的完善性,实际上也牵连着是否能被理论感知和批评,这就是艺术自身的思想透视力,也就是高峰创作上直抵美学精神的认知。由此艺术自有其审美作为贯穿其中的一致性,而形成区别于艺术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独有性。也许我们需要强调艺术的本质是个性的创造,所以创造的对象是不是被既有观念和习惯认定就有了差异和误解。所以贡布里希曾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1]参见[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似乎并没有我们习惯的可以背诵答题的艺术概念条文,却也可以这样来指证艺术的奇特性。事实上我们理解的艺术出现,从岩壁上的远古绘画开始有艺术呈现,追寻到前人所说的劳动号子一般的音乐诞生,或者依据中国古人记载的感受,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毛诗序》)之“情动于中”就是其本源所在,即基于人特有的情感丰富性而寻找生发点,从而突破物质形体的约束而向外生发,则有感叹的情感舒张表征、不能不放歌的音乐张扬、手舞足蹈的肢体韵律灌注其中等艺术呈现。艺术与文学一样,“情感是文学活动的表现对象,也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能力”[2]金雅:《说艺论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7页。。所以就不难找到艺术的最基本盘是情感舒展,最超越日常生活的是观念异于常态的畅想,而最为凸显的是形象凝聚思想。艺术基于想象的促发,而想象的内在动因却由于情感的跃动缠绕不得不借助艺术形态来呈现。
谈论艺术不能离开其根本所在,即艺术情感之维的核心在于和审美极为密切的关联。艺术连接着支撑其价值的审美,而审美具有人类精神体验中高端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审美的精神理论概括又不能不归到哲学层面的美学范畴,这样理解的艺术就具有贯穿一致的从创作感性到内涵蕴积再到理论思想标识的系统性。艺术本身之美借助情感之维度来划开艺术形式存在的价值,既是作为整个审美对象最重要的枢纽和关键,也是透视艺术有别于理性思维的哲思范畴的确认。艺术之美的核心是通过多样的艺术形态表现出人们对审视对象美感的创作韵味,而美学是关于人类在哲学上对于美的理论认知和逻辑论证的综合。也许美学理论家会觉得艺术攀附美学的抽象论过于随意宽泛,理性思维的逻辑未必恰切,尤其是对于美学认知的简单化。但当我们将艺术和美学并驾齐驱谈论时,我们会有一个将形而上的美学、与具体包容的艺术多样性的审美和艺术的核心三者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可能。用艺术化的语言来佐证依然具有情感形象的特点,这就是艺术的特征,这在中国传统审美大家的认识中可以发现其指向。如宗白华有许多出色的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意境论和艺术情感生发论,他曾引述《礼记》里的《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3]转引自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9页。这里将音乐感于心而外化涌动的创造表现说得栩栩如生。一切艺术的初始点必然来自于人的情感萌发所带来的原初冲动力,艺术从情商开始是必然基础,而要能找到和美学的关系,则要升华为格调。事实上艺术自有其独立的情感魅力,但它又被美学加以指导,以及给美学提供一种审美规律性的佐证,乃至于艺术之为艺术不可忽视其生存要旨,即情感之胜,乃至于情感之盛大之盛。由此我们谈论艺术也有一种超越于美学理性逻辑的一些东西,那就是他在“道”“术”之外具有的特殊性。
我们自然明白认知艺术未必只有一种角度。学理性的艺术认知无论中外其实都有概念上的差异,而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上对于艺术的认知。对于中国认知的艺术而言,人们时常会去追究艺术本身之“艺”是“种植”意思的由来,由此去展开另外一种艺术的实践性的解释。但毫无疑问,时至今日东西方共同推向的一个方向是:艺术是一种和审美相接近的对象。如何将艺术的多元性和多样形态与人们观念上的审美或美学相互联系,自然需要抓住“艺术源于人自身的一种内心情感”这一角度,这就是我们要提出“情感之维”对于联系着艺术的产生、艺术的生发、艺术的形成和接受乃至于在艺术的评价上必须要把控到的要害,由此才能剔除一种对于艺术作品言不及义的洋洋洒洒的理论剖析而失去了它的审美要义的重心所在,真正适应关于艺术认识的吻合性。
二、艺术审美与美学的纽带是“情感之维”
艺术自然不能离开技巧形式的呈现,艺术的形式内容是否和谐完美,需要借助美学判断来印证。“情感之维”的聚焦自有其内涵的支撑,显然其思考的层面是通向对内的艺术创作根源所在,也包括向上的接续美学观念的评价。也许有人会注意到“情感之维”似乎借鉴了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这一命题。在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将审美形式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艺术作品不是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完满的整合。因此,从审美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本身就具备一种独立自足的整体性。实际上艺术就是超越既存的现实,通过艺术创作以审美形式的想象或幻想来摆脱现实,达到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艺术境地。由此,“在中西方历史上,传统美育观念在突出‘本于自心’的个体追求的同时,大多重点指向对人的终极性完善要求”。[1]王德胜:《“以文化人”:现代美育的精神涵养功能——一种基于功能论立场的思考》,《美育学刊》2017年第3期,第19页。从审美思维所受到的启发就在于需要综合性来看情感生发的问题。我们借鉴审美思维而聚焦于情感之维,同样是定位在创作这一最本质的出发点所在。无论何种作品的创作,其形式和内容必然有多重需要。但维系其核心的是人们力求创造,突破所受到的物质限制,于精神世界的审美期望的需要,各种艺术都因此产生出能够满足人精神需要的多样的形式。如宗白华所论:“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2]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他所论及的就是在艺术多样的形式之中能够加以牵制联系的是人的情感,也就是作为人最本真的情感律动和人精神满足的高下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用情感之维来牵扯创作的动因、效果和创作所达到的高度,也就是抓住人们判断创作的高下是不是具有情感所能呈现出的表现意味而实现审美的厚度。这样,我们就把艺术创作归于多样形态之中最本真的审美冲动,而审美会推向美学形态的判断,由此来看待理性认知,从而实现对于情感价值的判断。
还是回到艺术各式各样的形式价值的论说上,即其具有双重的审美实践意味,也就是艺术在整体美学形态表现上不断地扩充它的审美理念和观念,也不断地给予审美呈现以美学观念为要旨去随时代前进,从而更多地去扩展其美学观念的外延或内涵。在这一层面,我们说艺术审美和美学构成了一种微妙关系。我们当然没有去冒犯美学,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孤高自傲、指导所有人审美的一种规律性的简单认知。但我们有理由提出,在美学的范畴之中,艺术之美或者对于艺术的审美及美育,必然是和美学发生紧密联系的,并且成为了某种角度的支撑、佐证和实证的对象。古典美学不管在西方何以有这样承上启下不断延续而形成系统和思辨的理论体系,它在中国几十年来关于美学的主观性、客观性和主客观融合的辨析中总在构成我们的疑惑,因为对于舶来的美学要义我们还存在认识差异,这毕竟不是本土产出的美学的理论根据,与中国的美学观念之间要卯榫合拍还存在不少难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对于人生美学、生活美学多元性的认知,都在证明美学是一个开放而且根基深厚的基础。美或者审美一定有它的理论依据和拓展的核心所在,那么艺术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美学观念得以牵连关系,比如说审丑指向、审美感悟的辨析、审美创造性、现代审美差异性乃至于怪异性,等等。审美的多元复杂导致现代艺术的认知难度,但抓住“情感之维”来掂量艺术表现是一个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审美抵达的是精神世界的收获,艺术创作的本源来自于情感驱使,而获得共鸣与否也最容易从情感是否激荡来得到验证。
毫无疑问,审美必然是艺术最终被人们认可的核心所在,以审美为核心才能更好解说艺术创造的目的和效果。从终极意义上看,艺术是创造人类梦想中的对于未知和对于人身体感知无限扩展的一种对象,其必然会和美学的哲学思维相互联系。确定了上述这一点,我们说创造性的艺术必然要区分道和术的关系,而“道”是艺术的根本意义所在,“术”是如何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来感知美之道,而这正是人类伟大之处。无论是旋律、线条、明暗、光影、身姿以及影像艺术,一直到智能时代互联网所产生的新的艺术形态,都是为了超越人的局限向无限世界拓展。在艺术的创造性中,必然有审美作为永久粘连的牵扯。艺术在不断地扩大边界又拉回到具象创造才会与美学产生或多或少、或紧或疏的关系。但毫无疑问,美感、美育、审美意识和人类对于冥冥之中的复杂性的美的追求,是终极意义上的艺术创造和美学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联系,也许还要回到古人的艺术审美感悟中来佐证,如王国维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2页。境界或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家、理论家用来形容和判断艺术创造的美学追求的。有境界则为高品,故王国维又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2]同上,第9页。这里的“真感情”才有境界者,即来自于情感又超越情感的境界。境界既是艺术之道的凝聚,也是美学哲理的升华。显然这里从审美衍生到艺术审美,落脚于关键性的人类情感作为创作源泉和欣赏理解批评的支撑,才足以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做到切中要害的把握,否则就是哲学思维的概念判断周全与否,而不是艺术对象审美的动人与否了。
三、情感之维与逻辑之维、思辨之维的比较
我们用情感之维透视和延伸艺术审美,指向的是审美的精神和人的艺术需求所内在期待的一种情感律动。这是强化创作根源和认识创作厚重度的要旨,其审美高下的尺度取决于情感之维所蕴含的分量,以及美学精神投射到创作上的浑融几何。于是需要在创作完成后,从理论认识的角度和批评的角度加以微妙区别。为此,理论所具有的逻辑思维的特点和批评所需要的思辨判断的特点,二者似乎可以套用(情感之维)来进行命名。即强调艺术作品给予人的是“情感之维”所激发的人的心灵律动,那么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就应该是理论所构成的“逻辑之维”最为恰切。因为理论给予人们的是理性思考,它的深浅和周全性取决于逻辑的环环相扣、逻辑自身的周延性,以及逻辑伸展后具有的一种理性的力量。由此延伸到批评,尽管批评也需要理论的支撑,但显然区别于理论而略有不同。观照批评可以从思辨、思维的角度来加以看待,不妨以“思辨之维”来指称。当理论思维或者说逻辑之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阐释的所有过程都由一种严整的逻辑所带动,它给予人们的是逻辑所构成的理性层面的理性启发性。因此,学理的范式和学理在逻辑层面的自洽性,是理论思维让人们信服的关键所在。而批评则不同,其固然需要一定理论思维的支撑,也有理论的假说和理论的支撑决定了批评的深度之说,但关键是要从理论的角度去投射创作针对性。批评所关涉的是作品的形式、内容、创作者,以及通过创作潮流透视作品内涵的复杂性,是要剥去创作的外在看到其中的得失和深浅。不言而喻,我们用思辨之维看待理论投射到创作的鲜活性之中,分析何以展示出或者说抓取到其中的鲜活意味。特别是要对感性的形象情感所透射出的未必恰切之处给予指出,并且提供得失的合法理由。显然我们这样比较的时候,是从情感之维到思辨之维的盘点,再到逻辑之维的理性认知,才能上升到是否符合美学意义的高度。比较情感之维与逻辑之维、思辨之维的不同,也许对于辨别时常被创作者忽略的创作本性和高下所在,以及被理论简单投射的不合时宜,与一些批评中不得要领、忽视创作自身思辨要素的分析等情况,具有警示作用。与情感之维相比较,理论的逻辑之维注重的是人类对于理性思考的一种聚焦,而通过思辨之维进行的批评则要站在理论的基点上去看待创作,从而层层剖析和抽丝剥茧,抓取到创作者或作品中所蕴含的理性以及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吻合。因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情感之维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情感生发出一种质感和心灵期待,包括浪漫的、现实的、激愤的、忧郁的、希冀的,等等,这些情感以形象表现出来,通达审美的愉悦。因此,情感之维是艺术审美的形象性通达美学理性的一种勾连和纽带。
由此,当艺术创作完成后,人们常谈论作品的思想高点、哲学性以及美学观念,等等。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一定是有创作者的某种理念或者说思想蕴含其间,我们能够通过作品抽绎出创作者蕴含其中的思想深度,于是我们通常可以把它提升到和美学相关联的高度。即作者以形象的方式构筑作品,其中必然蕴含某种思想观念,但它毕竟是生发于人情感的形象性,氤氲其间的翻腾的情感构筑了人物形态,或在视听形态中表现出可感可知的对象。因此它的感召力对于不同艺术形式而言,或是线条、明暗,或是视觉形态、身体语言,乃至于声音的悦耳与否,等等,都是一种有节奏的有规则的艺术形象的呈现,此即为艺术。而人们感知艺术作品,必然是透过立体的形象去和自己的情感乃至于灵魂产生互动。因此好的创作者且不论他后面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创作理想或者说审美趣味,但它是通过形态形象以情感折射的方式来打动人、感染人,乃至于悦动人心。所以无论是观者对艺术作品的感知,还是批评者对于作品的分析评判,首先就需要从情感之维这一角度来透视深浅得当与否。此时所说的情感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哭泣、欢乐、悲哀等,它实际上是精神受到了立体的晕染而起伏变化的一种情绪和心理波动。当这些东西聚集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人们观赏作品时的慢慢回忆或者直抵灵魂所感受到的巨大的轰鸣力量,在情感烘托之中使人们顿悟出某种审美的精神世界。如果用理性的逻辑之维来表达,那就是它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味,而这深厚的思想意味就和思想层面的哲学观即美学的思想体系挂上了钩。
但我们绝不能反过来说创作必然是以一种理性逻辑来构筑的,那样的话即使可以分析出其逻辑脉络,却往往是干涩的,好比是教科书中的概念,而不是鲜活灵动的具有艺术情感的作品。我们可以援引王国维和他在《人间词话》中关于人生所必经的三个境界来印证。他的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43页。这里我们不阐释其丰厚的意味,只论说三个人生境界,也就是其在具有了理论判断的思想阅历后所给予的认识,环环相扣而给人启发,被公认具有深邃的“世事洞明皆学问”的意味。但我们都知道,这一理论概括却是从中国词史上著名的三首经典词作中抽取出来的名句。其第一境界出自晏殊的《蝶恋花》,第二境界出自柳永的《蝶恋花》,第三境界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在这三首词中,不论是思夫情深,还是思妇哀怨,或是更为复杂的思绪,都充满着情感的抒发。因此从情感之维来解析词作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三个词作者而言,他们内心积郁的情感、辗转难眠的哀思、仰望亲人的情愫、寻求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得的痛楚等等,都是那样的凄风苦雨,遭遇着环境与人事的周折,从而折现出某种难以言表的意味的形态。所以理解原词,人们能以自己的身体感受和眼目所及产生一种共鸣性,具有美感。当集合三首词的时候,无论是王国维的初衷,还是人们感知的思考,都升华为以审美为基础的具有逻辑推演性的思想认知。情感所发却用理性的方式抽绎出来,并列在一起来形容人生情感追求的不同层面,这就是“情感之维”—“逻辑之维”的形象说明。如果我们再从中勾连去探究这三个境界的词句,能发现其中包含着:急切要去寻求所爱登上高楼而不舍远望的孤寂身影,为自己刻骨铭心的所爱忍受凄风苦雨而终身不悔,败落于灯红酒绿的大千世界失落惆怅却偏偏在黯淡稀疏的光影小道上偶然发现自己的所爱,等等,由此伸展出超越三首原词的情爱绵绵的不同凡响和别具一格的境界。以上给予人的启发似乎是偶然所得,但事实上是人只有不懈地努力寻求,才有可能或偶然天成地、或水到渠成地集聚一种美好的收获。这样就从“情感之维”—“逻辑之维”—“思辨之维”的合拍上,实现了浑然天成的效果。也许逻辑之维并非是原词作者在逻辑思维上所得出来的,却恰恰是在情感的审美中慢慢延伸出来的。在王国维的笔下,他从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词作中延伸出这样一种思想性,直达美学层面的思想认知,最终和审美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巧妙的联系其实未必是那样简单的,而是具有美学意义的思想之光。
四、艺术创作和思辨的情感之维不可或缺
由此,我们问题的核心就是情感之维的价值,以及与审美之间关系的一个阐释。我们说艺术的对象,从最早的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中,就产生出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美学观念或者宗教观念,就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观念形态的解说。而谈及艺术的起源,又会从人的欲望、期待以及观念上的迷幻创造去触及它,更不用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艺术是第三重关系的一种复写,从而通向了观念、理念上的一种认知。回到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后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或者教育家,他们对于艺术的认知,都更多地通向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比如在孔子和弟子的交谈中,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美妙景象,孔子将暮春之时沐浴的景象描绘成审美的一种气息,比附于人生理想的说辞,但我们却已看到情感的荡漾和蕴藉无穷的美感升华、充斥在这样的气息之中,夸张一点也可以说情感之维戳中了圣人之心。再如诗人屈原,他偏偏喜欢用香草、兰花等作他人生不幸的借喻、暗喻,或是指摘现实,却有一种审美情感的凸显。可以说,中国人的艺术审美一定是一种情感之维的审美,这一直延续到高科技年代的电影电视作品中,中国人骨子里头承传的依然是这种人和情感相联系的精神审美、需要。因此,情感之维既是一个艺术审美的角度,又是艺术审美立足的一个基点。
由此,在中国的艺术之中,审美的牵扯一定会成为人们看待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为人在现实之中情感很难舒张,很难实现某种困境的抒发,因此人对于艺术的情感能够纾解身心的困境。事实上,无论是何种艺术形式,人们更多的是从观赏中去体会到心灵的愉悦的审美。而这一切,都可以以美学的角度去透视言说。美学在形而上的角度看到了艺术多元性之中的美的因素,而中国人更多在艺术的审美之中看到了情感的浑融和它的审美价值。依然可以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的佳句来佐证:“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5页。这自然是情感投注的浑融,强化了情感之维对于艺术审美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把情感当成包容万象的东西,不能只把情感当成激情或者是情绪波动的对象,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情感之维的情感,指的是人们内心之中升腾起的一种欲望,是追求理想而超越现实的一种趣味。
艺术以哲学思维连接着美学,受到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艺术表现中可以找到理性的成分,并且可以升格成为美学来指点、分析和确认。但艺术的本质应该是感性的,因此理性的解释和美学的确认必须通过情感这一维度来加以展示和提升。如果只在理性上拿着概念去套用艺术作品的观念和形态,就常常会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吻合。例如一些批评的大而无当其实就是忽视了艺术创作中对于情感内涵的感知,以简单的理论去套用,或闭着眼睛以自我逻辑论说,自然难以为创作者接受,也不能被观赏者所理解,更谈不上具有理论的价值。这一类的评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具有极大的伤害力。在情感之维上没有尊重作品、没有聚焦作品,就无法实现思辨之维的合理性,也就不可能有理论思维的信服度。如关于电影《战狼Ⅱ》(吴京,2017),一些人凭借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概念投射,认为电影展现出中国不甘寂寞的对外扩张,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观念偏激的人的赞许,他们完全抛却了主人公冷锋的情感世界——他对于战友亲人以及对于国家的爱恋,也完全忽略了影片中个人浓烈的情感——主人公对于失去爱人的激愤、对于战友牺牲的强烈情感等等,用生搬硬套的理论逻辑和臆想出的认识对影片大加挞伐。由此可见,没有情感之维支撑的认知就会成为一种无厘头的理性,从而产生一种无厘头的批评,更谈不上对于艺术创作的审美认知以及对于影像审美的理解。类似案例还有以往对于古典戏曲的指责——认为其是迷信,是装神弄鬼,是和时代格局不符等所谓的理性投射,漠视了其在传统道德层面和民间情感上能够被接受并理解的一种艺术感知。若是如此理解艺术作品,当然就会使艺术作品的审美荡然无存,更谈不上对艺术作品的美学阐释了。
当聚焦于情感之维、逻辑之维、思辨之维去探讨艺术、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时,显然有所放大了情感的独特性,但我们还是有清晰认识的。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我抓取其中“最浓于热情”的字眼来佐证艺术情感之维的不可或缺不免有所褊狭,但前文引述王国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确实是对于艺术情感投射的绝佳认识。任何形态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上升到一种哲学思维的程度,无论是当下艺术学新学科目录的调整,艺术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实践性的专业学位;还是艺术必须拥有技能技巧,以术与实践的精深丰富来实现创作高峰,都要意识到如果没有思想和审美精神的武装,以上都难以实现。对于艺术的理解、批评和分析,绝不能无的放矢地拿着他者的理论框架来投射到艺术之中,而忽视其内在的情感、艺术形式和自身的自主性。反向而言,人类永远不要忘记,人们最终追求的其实正如康德所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那必然是和艺术的哲学思维及美学引导息息相关的。
最后要强调一点,对于艺术创作审美习性的情感之维的谈论,是要确立艺术给予人德行熏染的意义,古代孔子等圣人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礼乐相济”的理论基础。[2]参见彭吉象:《艺术鉴赏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页。所以我们确认“美育与德育融合是中国美育思想的根本特征”[3]杜卫:《论美育的内在德育功能——当代中国美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之二》,《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第50页。。艺术创作是为了实现对于人完善性的提升,向内发现和阐扬“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4]王德胜:《美学:历史与当下——王德胜学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8页。。但我们必须强调中国的艺术创作在时代风云之中绝不能缺少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坚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当一个创作者具有坚定的主流价值观和对于生活的丰富性认知时,他的情感之维的表现就会呈现出端正、端庄和动人心弦的魅力。强化主流价值观这一理性思维给予艺术创作和艺术创作者的精神引领,绝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我们从情感之维和逻辑之维、思辨之维的比较中可以坚定地认为,当主流价值观给予人们一种优秀文化熏染的时候,创作者情感的向上向善和对于国家精神的维护、对于优秀文化的吸纳、对于人民责任感的体现,就会呈现出它审美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