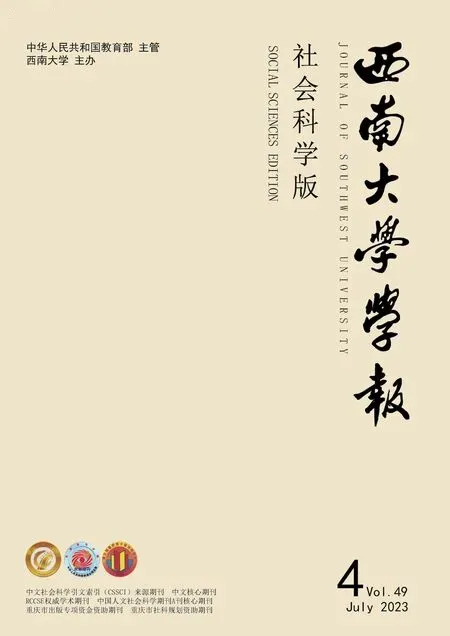定位艺术的内涵、形态及其审美特征研究
——虚拟艺术之后的公共艺术实践
张 忠 梅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一、定位艺术:虚拟艺术之后数字公共艺术实践的一种新形式
自20世纪初达达、未来主义等先锋派尝试运用新的媒介与技术拓展传统艺术领域以来,艺术史见证了活动艺术、影像艺术、计算机艺术、光雕塑、声音艺术、数码艺术、网络艺术、虚拟艺术等多彩纷呈的新媒体艺术实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新媒体艺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中,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21世纪,随着普适计算技术的发展成熟与广泛应用,“计算机可读数据的‘虚拟性’……被带入了物理世界”[1],数字艺术实践及话语开始出现位置转向,更准确地说,转向基于日常位置、充满数字信息的增强物理空间。本地的日常位置取代了遥渺的虚拟空间,成为数字体验的中心,数字体验方式由传统的视觉中心转向基于在场的具身表演,由此产生了新兴的数字艺术实践——定位艺术(locative art)。定位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最早由海门特于2006年提出。在他看来,定位艺术是“使用便携式、联网、位置感知计算设备进行的,用户主导的地图绘制、社交网络和艺术干预……其中,城市环境和地球轮廓成为‘画布’”[2]。不同于虚拟艺术、元宇宙、上传智能等时兴数字实践对身体和在场的摒弃,定位艺术强调技术支持下万物基于位置的具身在场表演,体现了数字艺术实践由虚拟艺术所代表的“视觉中心主义和非物质主义的交织”,经由增强现实艺术中虚拟对物理的叠加增强以及遥在艺术中肉身与物理的有限交互和远程在场,发展至定位艺术中“物质主义和数字化具身”[3]的变革。相关实践及探讨在西方蓬勃发展,蔚然成风。西蒙·佩尼聚焦“虚拟”十年(1990年代)和普适十年(2000年代)的话语及技术变迁,将数字实践由虚拟向定位的转变归因于普适计算作用下普适界面的发展[4]。布拉德利认为定位叙事可视为一种“声音考古”[5],强调定位等媒介与技术支持下的空间增强和历史叙事。弗罗德舍姆认为定位映射实践颠覆了关于空间、知识、权力和表征的传统概念,在其中,空间和知识表现为一种动态生成,权力关系交织缠绕,艺术不再关注表征,转而强调行动和表演[6]。麦克戈尼格尔探究了普适计算作用下的普适计算游戏、随境游戏和普适游戏,认为它们创建了玩家基于混合空间的具身表演和交互,也建构了“游戏性和日常生活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7]。基于这些研究,拉里萨·霍思、阿德里安娜·德·席尔瓦和克拉尔·兰森于2020年共同编纂了《劳特利奇移动媒介艺术指南》,该《指南》囊括了“移动媒介艺术”“手机媒介艺术实践”“混合现实”等十个主题,全面介绍了当下基于移动媒介的创意艺术实践及理论[8]。
国内的定位艺术实践及研究刚刚起步,且发展缓慢。在实践方面,既有的定位实践多集中于日常、商业及旅游服务,如各类数字导航及“KEEP”“咕咚运动”等可移动追踪、记录数据进而生成映射的程序应用,旅游景区内供游客在特定地点聆听相关历史及叙事的“云导游”等。这些服务、应用与实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定位技术创造了新颖的体验,然而在创设艺术情境以激发情动体验方面仍有待加强。在研究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数量有限,且多集中于定位叙事。黎杨全于2015年从“重回自然空间”、生成“地方”、促进“底层发声”三个方面论述了定位叙事的积极意义和影响,首次将定位叙事引入中国学界[9]。随后,黄鸣奋发表了四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或剖析定位媒介在影视创作中的创意叙事策略[10-11],或从技术、幻术和艺术三个维度阐释位置叙事的新颖创意[12],或提出“以位置叙事学为理论依据”的“位置批评”,倡导建立“以‘位置’作为核心范畴的一种批评方法”[13]。值得关注的是,黄鸣奋于2017年出版了国内关于定位叙事的首部专著《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三卷本,系统梳理了位置转向后叙事学的转变,建构了基于社会、产品、运营三个层面,包含主体、对象、中介等九要素的位置叙事框架[14]。此外,韩模永将定位叙事视为网络文学场景书写的最新形态,指出定位叙事体现了文学书写的位置和空间转向[15]。关于定位映射,国内既有研究多从媒介视角探讨定位媒介对空间生产[16-17]、场所建构[18]和场所经验[19]的影响。对定位映射的艺术实践分析在金钰婷关于电子地图的研究[20]中有所提及,但目前尚无专论。关于定位游戏,在周帅[21]、曹晓静[22]、何鑫[23]的移动游戏研究中,游戏的移动性和随身性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探讨,但这些研究均未谈及定位游戏的典型特征——混合空间。此外,丁肇辰[24]、刘佩[25]也探讨了随境游戏(pervasive games)。这些研究强调了游戏空间在技术支持下由传统数字空间向物理空间的渗透,但仅止步于案例介绍、体验分析等,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均有待挖掘。
可见,目前国内的定位艺术实践及研究数量不多,关于多元的定位艺术形态、艺术体验及审美研究都较为薄弱。在人类技术化栖居的今天,定位艺术与当下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艺术、生物基因艺术以及元宇宙实践一样,均代表着技术环境下艺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值得关注、探索与实践。那么,定位艺术是什么?它产生的技术文化背景如何?作为技术产物的定位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主要实践形态有哪些,具备怎样的特征,又产生了怎样的审美体验?关于定位艺术的考查对中国当代数字艺术的发展有何启示?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对定位艺术的系统梳理和分析,以此管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影响,从而更好地认识人类技术化栖居的现状及未来。
二、 算法转向、位置转向与定位艺术的构成
鉴于定位艺术实践开展的技术前提,本文提出,定位艺术指基于普适计算,运用定位媒介以及GPS(全球定位系统)、RFID(无线射频识别)、Wi-Fi(无线保真度,即无线网络协议)等定位、感应及通信技术与设备所开展的多元艺术实践,它具有移动情境、混合时空、万物互联和具身表演等特征。定位艺术实践的兴起与当下的算法转向和位置转向息息相关。大体而言,普适计算通过将计算“深深地嵌入世界”[26],实现了物和空间的信息化。物质对象越来越多地为信息所渗透,成为具有能动代理的智能物,日常环境也成为可定位、可注释、可互动、可建构的响应空间。相应地,普适计算环境下的感知体验方式由对传统对象物的知觉转变为一种“泛在的感觉”,它超越了对象、个体与意识,是一种气氛的、非个体的和微感知的感觉[27]。基于此,威廉·乌里奇奥提出了“算法转向(algorithmic turn)”,认为算法产生了“表征和看待世界的新方法”,颠覆了代表现代秩序的表征体制,创造了新的参与和体验,从而开启了一个以算法为特征的新时代[28]。算法转向使全球定位系统、无线网络、无线射频识别、地理信息系统(GIS)等获得迅猛发展,产生了使“几乎所有事物都位于或可定位”[29]的位置转向。物和位置成为承载信息和跨界沟通的节点,在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这种“位于或可定位”的能力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数字文化实践方式,人们的数字实践开始从数字的虚拟空间重返物理的日常位置,经验方式也相应地由传统的视觉中心转向当下在场的具身表演,并由此产生了基于定位等技术与媒介的定位艺术。定位艺术以定位技术为前提,其开展离不开作为算法基础语言的代码、普适能动的界面和作为行动者的物。这三者共同建构了定位艺术实践发生的内在结构。
表征为0和1的代码产生了所有与计算相关的多元交流,也为当下的算法转向和位置转向奠定了技术语言基础。代码具有多种形式,可以在各种硬件上运行。不同形式的代码主要以“编码对象、编码基础设施、编码过程和编码组件”[30]四种方式嵌入日常生活环境,赋予物和空间以能动性,并由此构成定位艺术实践中的基础界面——代码界面。代码界面进而与中介界面和表征界面共同组成定位艺术实践的多元界面。
从生成的过程性视角来看,定位艺术实践的发生源于代码界面。代码通过表征为0和1的通用语言和算法逻辑,获得了对事物编码、定位和赋能的能力,实现了数字层和物理层的沟通与连接。代码的普适通用性实现了普适计算和算法转向,代码语言的可更改性也赋予了用户更多的能动代理性。基于代码和普适计算,物和空间成为可定位、可交互的智能物和智能环境。这些基础设施、移动媒体和其他技术物、人文物及大气、风、太阳、星星等自然物共同构成了物的网络式集合。它们作为定位艺术实践的中介界面,连接着代码界面和表征界面。最后,文本、声音、图像、视频等增强信息层作为定位艺术中的表征界面,是参与者跨越物理世界进入虚拟世界的中介和桥梁。在定位艺术实践中,参与者借助嵌入了代码信息的基础设施、各种定位、感应、通信媒体以及多元物的中介界面,通过行走、聆听、注释、映射、追踪等方式参与、体验和制作表征为文本、声音、图像、视频的增强信息层,实现混合空间的多元定位交互与表演。
在其中,物“和具身人类行动者一样,也是能动代理”[31]。在算法、代码和界面的共同作用下,定位艺术实践中的行动者突破了传统的人类,扩展到普适存在的物,不仅包括信号发射塔、天线、网络基站、手机等技术物,也包括人类、动植物、高山流水、日月星辰等自然物,还包括如游戏中的虚拟角色、本初子午线、风俗礼节等人文物。这些行动者关系性地动态交互和表演,共同生成移动情境的、混合空间的、万物互联的动态艺术体验。如《鸽子博客》(PigeonBlog,2006)[32]中配备了GPS电子空气污染传感器的鸽子,通过在城市各区域上空飞翔,可实时动态地检测并生成各地的空气质量数据。鸽子的飞行路线被远程映射到谷歌地图,人们可以通过点击映射图上的任意轨迹点,查看由鸽子调查收集的地方空气质量数据。值得关注的是,鸽子博客的书写离不开各种物的协同交互:整个GPS定位系统、电子空气污染传感器等技术物,可能影响鸽子飞翔轨迹的气流、气压、雨水、雷电等自然物,鸽子驻足休息却可能影响信号接收的建筑群落等人文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定位艺术表演,形成关系性的行动网络,进而共同建构了鸽子博客的能动书写。
三、定位艺术的主要形态与特征
定位艺术实践的早期萌芽可追溯至1990年代的声景漫步实践,如珍妮特·卡迪夫的《森林漫步》(ForestWalk,1991)、《路易斯安那步行》(LouisianaWalk,1996),泰瑞·鲁布的《踪迹》(Trace,1999)等。这些早期的基于位置的艺术实践,虽然囿于GPS的不可访问而未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但艺术家通过应用其时可及的多元技术与设备,成功地将声音嵌入日常的物理环境中,并通过邀请参与者具身移动和聆听这些嵌入位置的声音,生成“会说话”的地方和移动情境的具身情动体验。鉴于此,我们将这些声景漫步实践视为定位艺术实践的开端,它们的出现开启了丰富多彩的定位艺术实践。根据实践类型,定位艺术实践大体可分为定位叙事、定位映射和定位游戏三种。
(一)定位叙事:位置性、流动性和个体性
定位叙事(locative narratives),指基于普适计算且借助于一系列定位、感应及通信技术与设备,通过将声音、数字文本、图像及视频等多元叙事类型嵌入、诱发或拼贴至物理的位置,生成位置性、流动性和个体性的增强叙事实践。作为一种新兴的增强空间叙事,定位叙事摆脱了传统印刷文字的束缚,拥有了更加多元,也更加去实体化的表达形式——声音、数字文本、图片及影像,并表现出鲜明的位置性、流动性和个体性特征。
艺术家们最早将声音嵌入物理空间以创造新颖的定位叙事体验。珍妮特·卡迪夫的《森林漫步》是最早运用移动媒介创作的移动声景作品之一。继卡迪夫之后,泰瑞·鲁布制作了一系列运用GPS定位系统、定位及感应媒介的定位音频作品,如《漂移》(Drift,2004)、《岩芯样本》(CoreSample,2007)、《蔓生》(Grimpant,2013)、《沼泽》(Fens,2017)等。这些作品借助定位技术与设备,创造性地将自然物、观念和行动等转化为能动响应的界面,如《漂移》中的潮水,《岩芯样本》中的海拔等高线,《蔓生》和《沼泽》中行动者的运动,从而使参与者在具身行走中感受视觉、听觉、动觉空间的动态交互以及虚拟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交织缠绕。除了以自然环境为艺术场景的声景漫步,许多定位叙事以人们居住的城市街区为背景,通过开展“叙事考古(narrative archeology)”[33],挖掘社区的历史故事和市井群体的边缘话语,如《北纬34度,西经118度》(34North118West,2002)、《自由的媒体肖像》(MediaPortraitoftheLiberties,2004)、《低语》(Murmur,2003)、《城市挂毯》(UrbanTapestries,2002)等。在这些叙事作品中,参与者不仅能够借助设备收听基于位置的叙事,还能够参与分享个体的经历、见闻、故事或创意,从而使定位叙事成为一种“公共创作”或“面向21世纪的大众观察”[34]。此外,定位叙事还可采用数字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形式,如《黄色箭头》(YellowArrow,2004)中的短信文本,《樱花》(CherryBlossoms,2006)中如樱花般漫天飞舞的数字图像,《岔路之城》(TheCityofForkingPaths,2014)和《爱丁堡夜行》(NightWalkforEdinburgh,2019)中的视频等。
作为增强的空间叙事,定位叙事表现出鲜明的位置性、流动性和个体性。位置性是定位叙事的首要特征。艺术家运用算法技术将代码赋值给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和位置,将不可见的注释附加到空间、地点、人和事物上,从而实现了基于位置的定位叙事。相应地,参与者的阅读和书写也以位置为中心展开。如在《北纬34度,西经118度》中,参与者需要走进这些街区,通过技术设备聆听特定于位置的,嵌入楼宇、车站、座椅等物体中的市井人生故事,实现对地方、对人群的叙事考古。流动性表现为定位叙事体验的流动性而非静止性,以及叙事内容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一方面,定位叙事提供的是一种流动而非静止的体验。在定位艺术中,作品并非固定于某一地点,往往覆盖一片区域,因此,参与者需要通过行走等方式去参与和体验作品。静止的观众由此变成了移动的听众,他在空间中的移动使作品存在。另一方面,定位叙事的内容也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定位叙事通常由面向大众敞开的叙事片段拼贴组成,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性、非线性和去中心性。参与者在体验作品时没有固定的顺序可循,叙事的接受和建构都具有相当的开放度和流动性。最后,定位叙事还表现出鲜明的个体性。叙事往往代表个体观点而非官方话语,因此可视为一种颇具草根元素的地方叙事,如《城市挂毯》《低语》《黄色箭头》等。正如马克·谢泼德所指出的,“《黄色箭头》代替了贴在‘重要’城市机构或空间表面的、提供‘官方话语’的青铜牌匾,为普通市民提供了对日常城市场所的非官方注释”[35]。此外,定位叙事内容的非线性和去中心化也使参与者能够自主选择不同的路线、顺序或时间体验叙事,生成个体化的叙事体验。
(二)定位映射:使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变得可见、可听、可触
定位映射(locative mapping)指基于普适计算且借助于一系列定位、感应及通信技术与设备,通过将基于位置的物、行动和观念进行数字可感化呈现,生成移动情境、实时涌现、主观体验的映射实践与过程。定位映射开辟了参与世界和绘制地图的新途径。根据映射内容,定位映射实践可分为经验映射、权力映射和心理地理映射三类。
经验映射(experiential mapping)关注多元具身体验,通过对人和非人行动者经验数据的收集和代码转换,动态揭示和呈现经验及其过程。如《GPS绘图》(GPSDrawing,2000)和《经络》(Meridians,2005)[36]等对艺术家行程的追踪映射;《我们的人生画卷》(TheDrawingOfOurLives,2003—2013)中对艺术家十年间身体动作和行程轨迹的记录与呈现;《生物映射》(BioMapping,2004)中对城市居民个体及整体的情绪映射和呈现。这些经验映射实践采用数据可视化的诗意形式,将行动者鲜活的具身行动和体验抽象映射为代表踪迹的点与线,从而以数字平面方式动态呈现了行动者的时空体验。以这种方式,经验映射融入了时间和过程,由此超越了传统地图的二元表征,建构了一系列空间事件。
权力映射(power mapping)关注社会权力和话语,通过对表征权力话语的物(如监控网络、GPS追踪、本初子午线等)的代码嵌入和数据收集,动态揭示和呈现了权力话语的经验和轨迹。《追踪追踪器》(TracktheTrackers,2003)是一个网络装置,通过为参与者提供城市公共领域视频监控的增强听觉体验,质疑和挑战了遍布世界的政府监控设施及其权力象征——摄像头。需要指出的是,摄像头的位置信息是由参与者不断向现有数据库添加创建和完善的。作品基于来自不同地方的参与者的步行体验和自主参与,由此生成了一幅关于城市权力和监控的声景地图,表达了大众对监控的抵制和反抗。类似的项目还有《火痕》(TracesofFire,2004)、《位置、位置、位置》(Location,Location,Location,2004)、《0.00导航》(0.00Navigation,2009)等。
心理地理映射(psycho-geographic mapping)强调运用情境主义国际所倡导的漂流、异轨等心理地理策略,通过参与者的具身运动生成替代性的映射地图,进而重塑参与者关于城市、城市结构和城市关系的心理和认知。《来自另一个地方的阴影:旧金山<>巴格达》(ShadowsfromAnotherPlace:SanFrancisco<>Baghdad,2004)提供了基于“交互式地图”的定位叙事和游戏实践。该“交互式地图”通过将巴格达地图折叠、进而覆盖在旧金山地图上制成。在其中,艺术家通过两份地图的叠加映射,将2003年美军首次袭击巴格达的轰炸地点对位标注在旧金山地图上,并相应嵌入了被轰炸地点的GPS坐标、照片、地图和相关事件的声音等信息。同时,在旧金山每一个对应的“被轰炸”地点上,艺术家还放置了一个地理缓存(Geocashing),即基于物理位置的、供游戏玩家寻找的容器。缓存中包含战争信息、美国总统的相关演讲以及战争阵亡人员的姓名汇编[37],供参与者实地寻找、阅读、倾听和感受。以这些方式,旧金山仿佛一面镜子,镜面映射着巴格达所遭受的暴力,也迫使参与者“身临其境”地见证战争及其所带来的创伤。在此,艺术家挪用了德波所倡导的“任意调换两个不同地区地图”[38]的策略。作品通过将两座城市的地图及现场进行映射和并置,对旧金山城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使个体得以“重新想象与城市空间的关系”[39],收获新的城市体验和认知。类似的定位映射还有《你不在这里》(YouAreNotHere,2006)等。
定位映射往往通过使不可见变得可见、不可听变得可听、不可触变得可触,揭示和呈现不同形式之间的潜在关系,生成多元新颖的体验。在《牛奶》(Milk,2004)中,艺术家通过运用GPS等设备定位、追踪、映射牛奶从拉脱维亚农场运输至荷兰出售的商业路线,并邀请参与者分享沿途的经历和感受,使不可见的商品生产、流通和销售及其背后的自然、社会与人文景观变得可见。除了可视化,许多定位映射运用技术将不可感的事物、过程和关系映射转化为声音,从而为数字和物理空间的中介互动开辟了新的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视觉中心主义。在《声音映射》(SoundMapping,1998)[40]中,四名参与者各自携带一个发声手提箱。这些手提箱运用卫星和运动传感系统,结合发声设备和计算机控制,能够对参与者的运动及其附近的建筑物特征作出有声响应,生成“音乐”。基于此,《声音映射》将运动和环境特征映射输出为声音,使“地方感、物质性和参与(a sense of place,physicality and engagement)”变得可听,由此创建了日常生活与艺术体验之间的新颖关系。此外,定位映射还通过使不可触变得可触,进一步扩展了艺术的体验方式。典型的案例如戈丹·萨维奇的《约束城市:日常生活的痛苦》(ConstraintCity:ThePainofEverydayLife,2007)以及尼基·普的《景观反应式腰带》(Landscape-reactiveSashes,2013)。在其中,身体成为感知的界面,作品通过将环境中不可触的电磁波和GPS信号转换为身体的触觉,映射和揭示了环境中的不可感知。
(三)定位游戏:混合、具身与移动
定位游戏(locative games)指基于普适计算且借助于一系列定位、感应及通信技术与设备,通过将游戏空间从虚拟数字空间扩展至物理日常空间,生成移动情境的、混合现实的、多元具身的增强交互体验。依据游戏中虚拟—物理空间的融合程度,定位游戏大致可划分为城市定位游戏(urban locative games)、基于位置的移动游戏(location-based mobile games)和混合现实定位游戏(hybrid reality locative games)三类。城市定位游戏强调以“城市空间为游戏板”,如《大型城市游戏》(TheBigUrbanGame,2003),占地108平方英里的两座城市街区成为棋盘,两座城市的居民为线上或线下玩家,开展了移动巨型充气棋子的竞跑游戏。游戏通过将日常生活空间“变成陌生和崇高的场所”[41],建构了引人注目的城市奇观,也生成了新颖有趣的游戏体验。基于位置的移动游戏强调“根据玩家在物理空间中彼此的相对位置来协调”[42],在此类游戏中,游戏进程围绕玩家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开展和推进,因此具有GPS定位功能的手机、PDA等成为游戏的必备装置,以实现玩家之间位置的跟踪和互动,如《地理缓存》(Geocaching,2000)、《机器人战士》(BotFighters,2001)、《城市标签》(CITYTAG,2004)等。混合现实定位游戏强调“融合物理和数字空间”[43]以及由此产生的虚实混合体验。在此类游戏中,游戏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同时进行,玩家穿梭于虚实交织的游戏空间并展开交互,收获新颖的空间感知和深度的沉浸体验。如在《现在你能看见我吗?》(CanYouSeeMeNow,2001)中,两类玩家分处物理和虚拟世界,借助于定位和通信设备沟通、协作以推进游戏。相较前两种游戏,混合现实定位游戏强调的不仅是混合空间更是“混合现实”[41]。在其中,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分别成为“可居住”的空间,建构着玩家基于虚实深度混合的“现实”交互。类似的混合现实定位游戏还有《罗伊叔叔就在你身边》(UncleRoyAllAroundYou,2003)、《PAC曼哈顿》(PACManhattan,2004)等。
定位游戏以混合性、具身性和移动性为特征。混合性指混合空间,它可被视为定位游戏的首要特征。定位游戏借助技术将传统数字游戏的虚拟空间延伸至物理的日常街巷,由此生成定位游戏体验的混合空间。游戏空间的扩展带来了游戏方式的改变。在定位游戏中,玩家的具身表演,如奔跑、追击、搜寻等取代了传统数字游戏中玩家的中介化操作,如点击按钮、操作操控杆等,由此产生了定位游戏的第三个特征——移动性。与传统电子游戏不同的是,定位游戏以玩家位置为中心,游戏体验跟随玩家移动产生的移动情境而展开。以《地理缓存》为例,为了玩游戏,玩家需要登录Geocaching.com游戏网站,注册并查看附近的缓存地图。然后,玩家需要运用GPS等移动定位技术和设备,具身前往缓存坐标位置所对应的物理空间。在此过程中,玩家通常需要不辞辛苦地“跋山涉水”、途径多个地点以最终抵达缓存所在的位置。然后,玩家需要仔细搜索该位置的每一个角落,直至成功找到缓存。可见,寻找缓存的过程不仅包括玩家在混合空间的多元具身表演,还包括由玩家运动产生的移动情境。以类似的方式,定位游戏如《罗伊叔叔就在你身边》《现在你能看见我吗?》以及《精灵宝可梦》(PokémonGo,2016)等,都是基于玩家在混合空间的具身表演,在移动情境中展开和推进。
四、基于具身表演的情动体验
定位艺术通过将地理位置由“地球上的经纬度坐标点”转化为“存在、居住、体验和生活”的地方,致力于创造一种数字、物理信息融合的“地理空间体验”[44]。在其中,参与者基于技术的可供性和身体的具身表演——或聆听注释,或映射呈现,或嬉戏交互——探索混合空间中虚实涌现的艺术体验。在此过程中,技术、物和空间交织作用,生成多元的情动体验。
(一)聆听、注释与生成地方
在技术的作用下,定位叙事以地理空间为书页,建构了基于位置的、虚实混合的多元增强叙事。参与者携带定位媒介具身进入作品所在区域,借助全球定位系统的实时追踪定位,激活嵌入位置的多元叙事,生成由参与者具身表演所触发的定位叙事体验。杰里米·海特将这种运用定位媒介和技术呈现地方历史的叙事模式称为“叙事考古学”,认为它“利用科技将随着时间流失的地方文物呈现于当下”[45],“通过位置、历史、故事和意义的地层向下挖掘,被体验为四维的”[46],由此凸显了定位叙事的时间维度和记忆属性。肖恩·米卡勒夫进而指出,这些故事能够“建立亲密关系和归属感,生成地方”[47]。需要指出的是,迥异于传统叙事的文本书写和阅读,在定位叙事中,参与者的身体成为读取和体验增强空间叙事的界面。作为新型界面的身体通过行走、聆听和注释,表演性地参与基于位置的空间叙事,生成地方和情动体验。
如在《岩芯样本》中,参与者被邀请沿着奇观岛的环岛步道漫步,通过聆听嵌入步道的景观叙事进而加入个体注释,了解和建构关于奇观岛的历史、文化与记忆。历史上的奇观岛曾经是6—16世纪美洲土著的垃圾填埋场,17—20世纪的殖民者定居放牧和工业发展之地,继而再度作为垃圾填埋场,最后被改造成今天的开放生态海岛公园。这些历史的陈迹都已化作地质沉积,沉淀为奇观岛的地表和岩芯。艺术家依据这些历史变迁编制了声音叙事,并依据叙事所代表的历史久远程度嵌入到环岛步道上相应的海拔位置。由此,在《岩芯样本》中,历史与当下、物质与虚拟、在场与缺席、人与非人的声音交织融合,共同建构了一座关于地方和记忆的声音雕塑。参与者当下的具身在场和行走唤起了历史上的彼时存在与述说。声音和叙事表征着海拔的高度和历史的记忆,也允许参与者在漫步海岛的同时,仿佛透过地表,深入岩芯,穿越历史,纵览奇观岛的前世今生。漫步过程中,声音的切换和覆盖暗示着海拔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参与者漫步的路线、节奏和速度,以及天气、环境如飞机驶过等因素都会导致通信信号的强弱变化,引发声音变化,从而生成具有“多重暂时性和主观性”[48]的艺术体验。
在此过程中,《岩芯样本》建构了“从任意一点出发,可以直接连通到任意别的点,而无需经过中间的点”[49]的平滑空间。与线性发展、产生秩序的条纹空间相反,平滑空间恒定运动、不断变化和发展,由作为“游牧民”的参与者发明创造。在平滑空间中,作为“个别体”(haecceity)的生命自由游弋。在《岩芯样本》中,异质的时间、物质、生物、社会和文化记忆,如现场录音、偶得的环境声音、电子过滤和原始声音、音乐片段、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生活叙事等,共同构成了个别体在“平滑空间”中流动、生成和涌现的基础。通过参与者基于“平滑空间”的游牧和技术界面的能动作用,这些异质的声音涌现、消逝、交织与更替,使奇观岛成为动态展开的“生成—地方”。这种“生成—地方”不是作为本体论上的稳定类别而存在,也不再是二元对立中的“他者”,而是一种空间与时间的过程性展开和生成,充盈着人类和非人类各种力的纠缠、作用与流转,呈现为一种动态变化的情动生成。
(二)映射、呈现与生成事件
定位映射不再是对事物的静态表征,而是对行动者在移动情境中主观具身表演的动态映射与呈现。通过使不可见变得可见,不可听变得可听,不可触变得可触,定位映射“敞开时空的生成可能”[50]352,生成一系列空间事件。此外,定位映射在技术支持下融入了时间,表现为一种过程性的展开。它朝向多元的身体、不规则的流动和不可预测的生成敞开,体现为身体之力的流转,虚拟的潜能实现以及身体与人物、事件和环境的关系性生成,由此建构了一种“生成—事件”的情动体验。
以《生物映射》为例,该项目邀请参与者佩戴测量“皮肤电反应”(GSR)的生物传感器并在城市中行走,进而运用GPS实时跟踪参与者的位置并采集其情感状态数据,生成城市居民的情感映射图。该项目的制作者诺尔德指出,《生物映射》呈现的“不是地形地貌特征”[51]或代表个人主观感受的情绪,而是参与者的情动体验,“是与外部环境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如意识、感官知觉和惊讶”[52]。在此,有必要借鉴马苏米关于情绪(emotion)和情感(affect)的概念阐释,以更好地理解《生物映射》折射出的情动体验。马苏米认为,情绪和情感“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属于不同的秩序”。情感是“强度(intensities)”,因此是前个人(pre-personal)的,是“不限定的……无法被拥有和辨认”;而情绪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容,是从社会语言学上确定一种经验的性质,这种经验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是个人的。情绪是有限定的强度……被拥有、被辨认”[53]34。换言之,情绪是一种主体的主观经验,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因此能够“被拥有、被辨认”;而情感是身体的强度,是前个人的,由此逃离了身体的意识或语言的规定,从而“无法被拥有和辨认”。可见,情绪是情感的身体表现和语言表达,而情感则是身体之力的流变。情感生成多元的情绪,但无法限定和表达。在《生物映射》中,这些代表身体强度和力之变化的情动体验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表现为参与者“具身体验的感官空间,其中,个体的反应似乎是由各种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刺激引起的”。也就是说,第一层情动体验表现为参与者在具身体验过程中的感官感知,如“摔倒,狗屎,下雨,冰淇淋,吃汉堡,看到有吸引力的人”[54]。这些感官体验引发身体之力的流变,生成情动。第二层表现为参与者观看踪迹映射和情感映射后的注释层,这是参与者对自我情感映射的反思和注释。这些反思和注释体现了情感的前个人性,因为情感是“一群热切的发端和趋向”,逃离了意识和身体的管控,发生在“丢失的半秒”,而感觉只能在发生之后进行“回溯”。同时,这些表达惊讶的反思也揭示出情感的虚拟性,它归属于“潜能的领域”[53]35-38,表现为一种不可预测的潜能生成。第三层是“最引人注目”和“突出”的,表现为“人们的社交互动,这种社交空间可能是短暂的,包括与朋友、邻居和陌生人的意外相遇”[51]。这些社交互动集中揭示了参与者“存在之力或行动之能力的连续流变”[55],如遭遇不喜欢的人时身体之力的减弱,偶遇好友时身体之力的增强。对此,诺尔德评论道:“虽然我看到的只是一条相当随机的尖尖的小径,但他们看到了一份关于他们旅程的亲密文件。它包含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危险的交通路口,与朋友的相遇,遇见他们喜欢的人,或者途经前伴侣的住所时的紧张。”[52]
正如德勒兹所言,“真正的事件恰恰不是‘事实’,而是蕴藏于事实之中的那些‘虚’的维度”,真正的事件是一种虚拟的潜能与生成,它“拥有超越‘可见’的力量……令你探问背后的玄机”[50]347。通过记录、可视化和分享参与者的身体及情绪状态,《生物映射》激活了踪迹背后的“玄机”,使不可见的情感、互动和社会关系变得可见,从而生成了开放涌现的话语事件。类似地,前文提及的各种定位映射项目,如《声音映射》《牛奶》《景观反应式腰带》均借助技术将时间、空间、环境、社会等因素引入映射,使不可感变得可见、可听、可触,从而生成踪迹和事件,触发参与者的情动体验。
(三)增强交互与生成关系
基于普适计算及定位、通信等技术与设备,定位游戏由传统的数字空间延伸至物理的日常空间,生成多元的游戏具身以及介于虚实混合空间的增强交互体验。传统数字游戏中隔着屏幕点击按钮、操纵游戏杆的玩家得以在日常空间中具身地移动、奔跑和嬉戏,游戏交互也由数字空间转向混合空间,扩展至游戏之外的路人。基于此,定位游戏的交互摒弃了传统数字游戏耽溺于屏幕内数字世界的孤独、自闭和沉迷,通过跨越物质与虚拟、存在与缺失、同步与异步的边界,建构了一种增强的具身交互体验。在此过程中,定位游戏向多元身体、力之流变和虚拟潜能敞开,生成多元的关系联结和流动的情动体验。
如《现在你能看见我吗?》中存在两种游戏的具身:作为物理肉身奔跑于城市街巷的线下玩家和在数字虚拟城市中呈现为数字化身的线上玩家。两种玩家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交流、协作推进游戏的顺利开展。作为奔跑者的四名线下玩家可以通过私人音频频道交流、沟通和调整各自的追逐策略。同时,他们可以通过公共音频频道与各自的在线玩家交流。游戏中,作为线下玩家的奔跑者通过“实时描述其行踪以及分享他们在城市街道上的见闻,如实时的交通状况,所在街道的场景等”[56],增强在线玩家的游戏沉浸感。类似地,在线玩家也可以通过网络或短信与线上、线下玩家交流。以这些方式,技术成功延伸了玩家的感官,使相距万里的玩家能够跨越数字与虚拟、存在与缺失的界限,实现共在与嬉戏、交互与协作。玩家的身体成为增强的身体,实现了穿梭于混合世界、跨越物理和虚拟具身的嬉戏和交互。
此外,定位游戏的增强交互还表现在异步的时间交互上。如《地理缓存》的游戏体验包括作为物理肉身的具身行走和缓存搜寻,还包括大量的线上文档创作和阅读,如签署日志和在线分享寻宝过程与发现。这些文档既是体验游戏、获得游戏乐趣的重要组成,也是游戏玩家之间交流分享、动态交互,进而获得社交具身感的主要途径。其中,日志的创建和阅读是异步发生的,玩家之间的在线留言与沟通可能同步,也可能异步。基于此,玩家的身体实现了异步时间的增强交互,成为一种跨越时间的增强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布莱恩·马苏米将身体的力之流变视为情动的本质特征,提出情动“一般是指身体进行感应和被感应的能力,或者身体之行动、参与和衔接能力的增强或减弱”[57]。在定位游戏的增强交互过程中,玩家的身体向力之流变和虚拟潜能敞开,生成多元的关系联结和流动的情动体验。如《精灵宝可梦》运用定位和AR技术将日常和熟悉的环境转化为重要的游戏场所,使宝可梦作为游戏内的虚拟生物出现在增强的物理世界,进而成功激发了玩家身体之力的流变,生成情动体验。一位玩家分享了自己在抓捕宝可梦过程中身体之力的流变——从满怀期许、身着睡衣的即刻出行,到竭尽全力搜索和追捕,随后是捕获未得的失落,最后是意识到身着睡衣出行而引发的尴尬与惭愧[58]。这种力之流变使身体由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进而影响和改变了玩家的日常行为与关系建构。许多玩家会为了捕获自己喜爱的宝可梦而增加户外运动时间,更改行走路线等[59]。同时,游戏内玩家与虚拟生物及其他玩家的关系也延展到物理世界,生成新的社会关系和体验。
同时,游戏空间向日常空间的扩展也使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与非玩家的身体相遇变得寻常。这些不期而遇可能激发玩家情感与身体的多元潜能实现,进而改变游戏进程。如在藏宝游戏《地理缓存》中,非玩家作为“影响的身体”出现,触动和搅扰着玩家。玩家“身体活动的力量”受到“阻碍”而不得不“减退”[60],心跳加速、行动放缓、不知所措,继而跟随身体之力的激荡流淌和意识介入,在放弃、暂停或继续游戏的潜在趋势中作出“艰难”抉择,最终转换为行动之力。类似地,这里的非玩家也存在着情感和身体的多元潜能实现。如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游戏的存在,很快离开;可能对玩家的行为产生疑惑甚至兴趣,选择故意留下,一探究竟;也可能因为意识到游戏的存在而加入游戏,成为玩家;甚至可能因为发现缓存,怀疑是炸弹等危险物而选择报警……在此过程中,玩家成为“影响的身体”,其行为可能引起也可能不引起非玩家的注意。玩家的身体或缓存的发现也触动着非玩家的身体之力发生流转,从而激发着玩家身体和情感的潜能实现。概言之,玩家与非玩家的身体相遇是一种“积极的情感遭遇”[61],它触发了一种激情的力场,以特殊的方式联系和影响着身体,表现为一系列虚拟潜能、多元的潜在关系和流动的情动体验。
五、涌现美:万物参与、新颖生成和增强关系
借助多元技术与设备,定位艺术逃离了传统数字艺术中日益封闭、离身和非物化的网络虚拟世界,重返动态敞开、具身和物质化的日常世界。日常环境成为虚实混合的世界剧场,上演着以参与者位置为中心的多元定位艺术实践。这些定位艺术实践通过万物在混合时空下的具身移动表演,凸显了万物的参与性、新颖的生成性和增强的关系性,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涌现美。
定位艺术的涌现美首先表现为混合时空下的万物参与。在定位艺术中,代码的嵌入和算法的赋值赋予了物和空间以信息和能动性,使物和空间成为艺术实践中普适存在的界面和积极能动的行动者。基于此,定位艺术实践跨越了人和非人、物质和虚拟、在场与缺席、同步和异步的界限,生成穿梭于物理—虚拟混合时空的、万物互联的增强交互和表演。由此,传统数字实践中基于网络的大众数字参与被扩展至定位艺术实践中基于混合时空的万物具身参与,从而在更广阔意义上实现了去中心的参与性。无论是定位叙事如《低语》,还是定位映射如《生物映射》,或是定位游戏《精灵宝可梦》,定位艺术已成为万物基于混合时空的具身表演,践行着拉图尔所倡导的“万物议会”理念以及德·塞托所推崇的日常生活美学,并由此表现出众声喧哗的复调之美和万物参与的涌现之美。
其次,定位艺术的涌现美表现为不可预测的新颖生成。在技术的支持下,定位艺术面向万物、时空和过程敞开。在其中,作为行动者的物通过在混合时空的能动参与和个性化表演,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开辟了新的空间实践和互动模式,生成“被体验为四维的”定位叙事,使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变得可见、可听、可触的定位映射以及基于多元具身增强交互的定位游戏。这些“新的、不可预测的”[62]2的空间实践和互动随着时间展开,“由小至大,由简入繁”[63],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生成,由此呈现出基于新颖生成的涌现之美。
最后,定位艺术的涌现美还表现为增强的关系性。定位艺术实践中的物和空间不是独立自足的实体对象,而是基于代码、普适界面和作为行动者的物的关系性和交互性存在。这些代码、界面和物由内而外、层层相扣地动态交互与作用,共同生成多元涌现的定位艺术实践。如在《0.00导航》中,艺术家以人文物“本初子午线”为参照线,运用GPS接收器在整条本初子午线上导航行走、映射和表演。行走表演的成功有赖于一系列技术物、自然物和人文物的持续动态交互,如GPS接收器、天线、光纤线路、数据服务器之间的“对话”,GPS卫星的正常运作甚至地球等星体的自然运行。这些物之间的交互是能动和关系性的,其中任何一个物的失效都将导致定位艺术实践无法顺利进行。可见,定位艺术可被视为一个“格式塔整体”,其生成“源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62]2,因而呈现出基于关系性的涌现美。
需要指出的是,涌现(emergence)作为科学哲学、认知科学、系统理论和人工生命领域的重要概念,指“在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出现的新颖连贯的结构、模式和属性”[64]。涌现的本质特征是“由小至大,由简入繁”,表现为一种“新的、不可预测的、源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格式塔整体”。在定位艺术中,普适算法和代码嵌入创生了增强的物和空间,也进而创造了面向万物的时空和过程开放的定位艺术体验。这些体验基于万物在虚实混合空间的能动参与,生成“新的、不可预测的”的新颖体验,随着时间动态展开,“由小至大,由简入繁”,其开展离不开万物的关系性交互,因此可被视为一个“源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格式塔整体”。基于此,定位艺术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涌现美。
六、定位艺术:虚拟艺术的物质性回归及其作为公共艺术实践的中国前景
定位艺术借助普适计算及其所衍生的定位、感应及通信等技术与设备,通过创设面向大众的公共技术情境以增进交互、分享体验、建立联结,生成涌现的情动体验。不同于虚拟艺术、增强现实等早期的公共数字艺术实践[65],定位的公共艺术实践表现出强烈的日常性、参与性和后人文性。首先,定位艺术的发生场域从传统的数字虚拟空间延伸至日常的物理位置,建构了基于物理位置的、虚实混合的日常空间体验。其次,定位艺术的体验方式由传统数字实践中以视觉为中心的静观或有限具身交互转向移动情境下的完全具身表演,进一步实现了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艺术理念。最后,基于代码嵌入和算法赋值,定位艺术实践中的行动者超越了人类,扩展至包括技术物、自然物和人文物的物之网络。这些能动的物关系性地动态交互,建构了万物互联的涌现体验,由此进一步增强了定位艺术实践的公共性和大众性,也体现出技术作用下公共艺术发展的后人类趋势。
从艺术史看,定位艺术体现了艺术实践由去物化到再物化的物质转向。因此,定位艺术可被视为虚拟艺术的物质性回归,其产生与技术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1960年代以来,艺术实践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技术理论的影响下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和表演转向。艺术不再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表征,亦不再囿于媒介的平面性或纯粹性,艺术走出了白立方、黑盒子,走向广袤的大地与街巷,通过将自然、现成品和日常行为等纳入艺术世界,成为一种系统性、关系性和过程性的空间实践和表演。基于海尔斯关于控制论发展脉络的分析,早期基于屏幕和数字图像生成的人机交互可视为第一波控制论中信息—反馈动态平衡理念的艺术表达,而极少主义、大地艺术、表演、行为及偶发等艺术实践则反映了第二波控制论的反身性理念。在其中,观察者及其所在空间被纳入艺术世界,共同构成一个协同交互的控制论系统。兴盛于1990年代的虚拟艺术大量出现,集中反映了第三波控制论对虚拟性的强调。在其中,艺术家秉承“物质对象为信息模式所渗透的文化感知”[66]4-5的虚拟性概念,营造了虚拟的数字环境和参与者以视觉为中心的离身沉浸体验。兴起于本世纪初的定位艺术实践则集中体现了第四波控制论的技术理念——混合现实,其特点是技术作用下虚拟和现实的泛在交织[67]。在其中,物和空间通过代码嵌入和算法赋值成为能动的行动者,赋予了非物质的数字虚拟以物质性的“具身虚拟性”[66]1,由此颠覆了1960年代以来艺术实践中以观念艺术、数字艺术为代表的去物化和非物质倾向,实现了“世界的重新复魅”(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68]。在此,技术不再作为技术对象,而是嵌入到物理环境中,生成定位艺术实践中技术—物—空间交互作用的新型空间实践。基于此,定位艺术实现了技术与艺术、虚拟与物质、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在场,由此链接了技术理性与诗意情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在西方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笛卡尔身心二分思想。
当然,定位艺术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和局限。首先,定位艺术以算法和定位为技术前提,这使得定位艺术实践难以摆脱其与监控及权力话语的关系。其次,由于定位艺术对技术的路径依赖,各类定位艺术实践往往在网络普及程度高的城市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定位艺术实践陷入服务于城市生活的精英立场。最后,定位艺术实践与当下逐渐兴起的元宇宙话语及其实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定位艺术实践致力于将传统数字艺术的空间和体验物质化,即从数字的虚拟时空转向基于物理位置的混合空间和具身表演,元宇宙却力图使物理的日常生活与数字的虚拟实践实现无缝对接,以期全方位实现人类在元宇宙的实践和生存。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智能定位手机、5G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定位艺术因其可具身移动的日常性、定位媒介(手机)的随身性和万物的参与性,已日渐“介入”人们的生活日常[69],成为继虚拟艺术之后新时代“数字青年”喜闻乐见的数字公共艺术形式[70]。如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的公共定位艺术实践——“城市定向跑”中,组织者通过网络线上征集队员,现场随机分组,同组成员结伴前往特定位置,继而通过执行指定任务、上传照片完成定位打卡,然后前往下一个打卡地执行任务和打卡,直至完成小组路线的所有规定打卡点。在此过程中,参与者通过手机导航具身访问特定位置、实地了解嵌入该位置的数字化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并通过多元游戏任务与他人交互、沟通和协作,生成经验的地方、不可预测的事件和涌现的关系,也由此收获多元的情动体验。此外,无论是活动前的线上报名,活动中的导航定位、聆听以及作为定点打卡的上传照片或视频,还是活动后潜在的关系联结,“城市定向跑”运用技术成功建构了面向大众的、基于位置的另类混合空间体验。在其中,网络、手机、信号站、乌云、建筑物等都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共同参与建构涌现的定位体验。类似地,以成都“鱼说”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有限公司,秉承“世界万物皆是文化载体”的理念,通过基于位置的文化挖掘、内容创建以及增强现实技术的支持,致力于开发“文化传播应用、位置场景应用、文化创意应用和角色运营应用”,以实现人、物与地方的深度内容交互,创造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71];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设有基于位置的定位叙事服务——“云导游”;基于位置和数据追踪的程序应用,如“Google Earth”“悦动圈”“小步外勤”等大量出现。它们在追踪用户、记录数据的同时,能够生成用户基于位置的轨迹映射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算法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诗意结合。
展望未来,定位艺术实践借助技术的可供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公众乃至万物的能动参与,有效促进万物之间的交流、协作、互动与共生,由此实现技术与艺术、虚拟与物理的深度融合,因此代表着数字公共艺术实践的未来发展方向。事实上,定位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为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理念的技术实现。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崇尚“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的齐物论,推崇万物有灵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万物和合的生态之美类似,在定位艺术实践中,万物通过代码嵌入和算法赋值,实现了能动代理以及万物互联的交互共生。与《庄子》强调“理想化个人情感的自然维度、空间化和具身化”类似[72],定位艺术实践也强调日常的物质空间以及具身的在场表演。可见,定位艺术不仅展现了技术条件下移动情境、混合空间、万物互联的涌现之美,也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和合、情以物迁的宇宙情怀与情动魅力。在技术理性和算法控制日益渗透人类社会,虚拟现实、元宇宙、上传智能等数字实践试图消弭物质的身体与在场的当下,定位艺术不仅通过诗意的万物互联和具身的在场表演而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义,也通过运用新兴科技而代表着技术环境下艺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亟须进一步关注、探索和实践。具体而言,我们一方面需要树立跨学科的教育理念与合作意识,努力培养兼具技术、媒介及人文素养的新时代艺术人才;另一方面,鉴于定位实践与监控的如影随形,我们也需要积极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大数据、云存储、定位系统及相关媒介与设备,从而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开展多元的定位艺术实践。唯有如此,中国的数字公共艺术实践才能运用新兴科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位情动和涌现体验,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3],进而建构技术环境下万物和合、共生互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