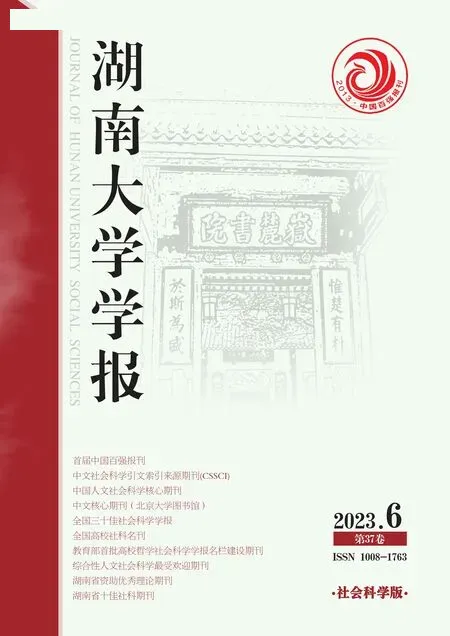检视中国刑法视域下的危险犯*
陈 洪 兵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近年来,有关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讨论一直是刑法理论的热点话题。《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设的危险驾驶罪,曾引发理论和实务的持续关注。《刑法修正案(九)》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大量的危险犯,其中抽象危险犯的大量增设更是引起理论界的警惕和担忧。抽象危险犯是公认的法益保护早期化、刑罚处罚前置化的犯罪类型,虽然对于法益保护即打击犯罪很管用、很好用,但对人权保障存在极大隐患。“陆勇代购抗癌药物案”和“天津大妈赵春华非法持枪案”的处理结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在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观备受推崇的当下[1],系统梳理、检讨和审视中国式危险犯,对深化理论研究和指导司法实践尤为重要。
一 危险犯传统分类的问题
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一般被刑法理论二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需要在司法上结合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而抽象危险犯只需依照一般生活经验判断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性即可。换言之,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造成法益侵害的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是司法人员在具体个案中认定的危险,系司法认定的危险。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般的类型性的危险,是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得出的危险,是立法推定或者拟制的危险。张明楷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刑法》分则中,采用“足以……危险”“危害公共安全”之类表述的条文是具体危险犯。既没有“危险”之类的表述,又未凸出实害结果的个罪条文,原则上属于抽象危险犯[2]。
但是,传统的危险犯二分法“不仅无法准确指导相关罪名的解释与适用,反而还进一步造成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争议”[3]。其一,按照张明楷的观点,单纯毁坏交通工具零部件的行为还不能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只有交通工具上路行驶在下坡、转弯等需要紧急刹车时因交通工具零部件遭受破坏而发生具体、现实、紧迫的高度危险时才成立犯罪。这种观点忽视了司法实践的做法,与法官的判案理念背道而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决策是依据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产生的,不能完全忽视判决所存在的合理性[4]。此类案件,诸多判决认为,只要存在毁坏交通工具重要或关键零部件的行为,即便还未形成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也应肯定犯罪的成立。例如,张某因感情纠纷对程某心生报复,遂将程某停放在某处的汽车左后轮的五颗螺丝拧松,导致程某准备驾驶汽车时,左后轮轮胎移位。法院认为,张某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1)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刑终939号刑事裁定书。。又如,杜某为报复王某,用刀将王某停在某处的汽车发动机上的连接带和电线割开,后又将沙土塞进机油管道。法院认为,杜某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2)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7刑终57号刑事裁定书。。其二,如果认为“足以”“危及公共安全”与“危及飞行安全”都是具体危险犯的表述,那么,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在广为接受的作为具体危险犯的标志性表述的“危害公共安全”之外,另用其他表述。其三,认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对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只有对公共安全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威胁,才能成立犯罪,也不符合事实。实践中,诸多判决认为,没有必要对行为是否存在具体危险进行判断,换言之,只要携带前述所称的危险物品进入特定场所即可成立犯罪[5]。其四,按照张明楷的立场,因为条文中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和盗窃、抢夺、抢劫危险物质罪均为具体危险犯[6]。但是,危险物质犯罪条文中的“危害公共安全”,只是限制处罚范围的要素,而非表征此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这是因为,成立具体危险犯,必须对行为是否存在现实、紧迫的危险进行具体判断,如此一来,不但容易放纵犯罪,而且增加了控方的证明难度[5]。实践中,在行为人主观明知属于放射性的物质的情况下,依然为他人联系出售,无疑成立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刑初字第03943号刑事判决书。。行为人明知车间的测厚仪属于放射性物质,依然将其盗走,亦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7]。
因此,传统的危险犯二分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8]。其实,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存在另一种中间形态,即准抽象危险犯,成立这类犯罪只需在个案中结合行为属性及对象性质判断其是否具有某种危险性即可。
二 具体危险犯的实质解读
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是司法认定的危险,是司法人员必须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断的危险。我国《刑法》分则中属于具体危险犯的罪名并不多,《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等罪可谓典型的具体危险犯。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放火罪,只有结合行为人在什么地方放火,周围是否有可燃物,当时天气如何,能否形成火势蔓延等情形具体判断,才能得出放火是否形成具体、现实、紧迫、高度危险的结论[9]。其他可以认为属于具体危险犯的罪名有危险作业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军人叛逃罪等。
立法者之所以在原本一系列责任事故犯罪之外增设危险作业罪,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将具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因此,对于关闭、破坏设备设施,篡改、隐瞒、销毁数据和信息,拒不执行整改措施,擅自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行为,只有造成了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才能以危险作业罪定罪处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类型多种多样,只要行为引起甲类传染病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就足以肯定此罪的成立。由此可见,引起传染病传播是指造成了实害结果,属于实害犯。由于该罪中的实害犯与危险犯并列规定并适用同样的法定刑,为了限制危险犯的处罚范围,应将该罪中的“有传播严重危险”,限定为造成了传染病传播的具体危险,而不是抽象危险。应该说,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司法实践将大量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不遵守防疫规定的行为也作为该罪定罪判刑,是错误的。此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但书”的规定,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不利于维持当时的疫情管控秩序[10]。这也说明,若不将该罪限定为具体危险犯,会不当扩大本罪的处罚范围,肆意践踏人权;同理,也应该将《刑法》第332条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及第337条规定的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限定为具体危险犯。
一般认为条文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志[2],但其实未必如此。例如,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条文也采用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但并非具体危险犯的标志,而是强调所破坏的设备设施必须是正在运营的公用设备设施,成立此类犯罪无须判断破坏行为是否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换句话说,只要破坏的是正在运营的公用类设备设施就成立犯罪。因此,这些犯罪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
有学者指出,危险物质犯罪的条文采用“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达方式,因此这类犯罪属于具体危险犯。[11]但是,司法实践中,只要行为人盗窃了氰化钠(4)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4)即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含铜废液(5)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7)深福法刑初字第750号刑事判决书。、内含放射源镅的测厚仪(6)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2014)霸刑初字第146号刑事判决书。等危险物质,即认定相应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进而认定为盗窃危险物质罪的既遂。这充分说明,危险物质犯罪中“危害公共安全”要素的功能仅在于限制处罚范围,旨在将具有一定毒害性、放射性但尚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物质排除在危险物质犯罪的对象之外。所以说,上述危险物质犯罪是准抽象危险犯,而非所谓的具体危险犯,只要危险物质的毒害性、放射性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实施相关行为就能构成犯罪[8]。这也符合功能主义刑法观导向,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12]。
《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的成立条件是“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要求行为必须产生导致职务不能或者明显难以执行的具体危险。因此在我国,妨害公务罪是具体危险犯,而不是抽象危险犯。作为特别条款的第5款,其适用以符合普通条款为前提,故而第5款的适用以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为前提,袭警罪也是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13]。
三 抽象危险犯的个罪梳理
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立法推定或者拟制的危险。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没有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不可能作为犯罪处理。即便是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也允许反证,即如果确实没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或者说没有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就不应认定成立抽象危险犯[12]。
有学者基于危险性产生来源的不同,将抽象危险犯进一步区分为古典的抽象危险犯、学习的抽象危险犯及拟制抽象危险犯[14]。还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抽象危险犯的下位类型包括抽象危险性犯和实质预备犯两种[15]。这两位学者基本上是照搬国外的分类,未必适合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张明楷将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抽象危险犯分为五种具体类型:1)接近实害型抽象危险犯,如侮辱罪、诽谤罪,这类抽象危险犯的本质是,行为极大概率地对法益造成了实害,只是举证难度过大,故无法苛求司法机关证明。2)紧迫危险型抽象危险犯,如销售、提供假药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非法邮寄爆炸物罪,劫持航空器罪,法官认定此类抽象危险犯只需结合行为内容判断是否产生紧迫危险即可。3)普通型抽象危险犯,如非法持有枪支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这些罪来源于立法者总结和提炼的社会生活经验,换言之,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一类行为通常具有法益侵害的高度危险,则需对其类型化处理并予以禁止。4)累积型抽象危险犯(7)虽然累积犯与抽象危险犯不是等同概念,但累积犯至少是抽象危险犯。,如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这类犯罪的本质是,单个构成要件行为难以对法益产生具体危险与实害,只有同类行为大量累积之后才可能对法益产生具体危险与实害。5)预备型抽象危险犯,这类抽象危险犯就是预备犯,如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生产假药罪,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2]。当然,即便是抽象危险犯,危险程度也会存在差异。根据危险程度对抽象危险犯进行分类,有助于对各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分则罪名中存在大量没有理论争议的抽象危险犯。例如,《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的(1)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2)帮助恐怖活动罪;(3)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均属于抽象危险犯(8)《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属于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还有:(1)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2)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3)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4)劫持航空器罪;(5)劫持船只、汽车罪;(6)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7)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8)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9)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10)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11)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又如,食品、药品安全事关每个消费者,近年来发生的有关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刺痛着国人的神经。因此,《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将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此外,该章中属于抽象危险犯的罪名大致还有:(1)伪造货币罪;(2)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3)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4)变造货币罪;(5)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9)《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属于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还有:(1)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2)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3)妨害信用卡管理罪;(4)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5)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6)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7)泄露内幕信息罪;(8)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9)逃汇罪;(10)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2)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3)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14)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15)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员发票罪;(16)非法出售发票罪;(17)伪造有价票证罪。。再如,《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规定的侮辱、诽谤罪和遗弃罪均属于抽象危险犯。还如,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抽象危险犯的罪名最多,大致有:(1)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2)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3)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等(10)《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属于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还有:(1)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2)非法生产警用装备罪;(3)非法生产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4)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5)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6)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7)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8)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9)传授犯罪方法罪;(10)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11)非法组织卖血罪;(12)强迫卖血罪;(13)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14)非法行医罪;(15)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16)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17)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18)非法捕捞水产品罪;(19)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非法狩猎罪;(21)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22)非法占用农用地罪;(23)破坏自然保护地罪;(24)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25)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26)盗伐林木罪;(27)滥伐林木罪;(28)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29)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30)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31)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32)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33)传播性病罪;(34)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罪;(35)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此外,《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也分布着一些抽象危险犯。例如,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和雇佣逃离部队军人罪等属于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抽象危险犯(11)《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属于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还有:(1)接送不合格兵员罪;(2)伪造、变造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3)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4)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5)伪造、盗窃、非法提供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6)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7)战时拒绝、逃避服役罪;(8)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9)战时拒绝、故意延误军事订货罪;(10)战时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军事秘密罪和战时自伤罪等罪属于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抽象危险犯(12)《刑法》分则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属于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还有:(1)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2)遗弃武器装备罪;(3)遗失武器装备罪;(4)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罪;(5)私放俘虏罪。。以下做几点说明。
张明楷认为,持有犯一般是抽象危险犯,因而持有犯都是持续犯(继续犯),持有犯的追诉时效从不再支配特定对象物之日开始计算[6]。但是,认为持有犯都是抽象危险犯和继续犯,可能存在疑问。持有犯其实是立法者对违禁品的来源与去向所做的一种推定。当查明了来源与去向时,就应当按照来源与去向进行评价,而没有持有犯适用的余地。非法持有枪支,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行为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存在持续性的危险,因此,认为这些个罪是抽象危险犯和持续犯,当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认为持有假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对货币的公共信用、公众健康、国家税款具有值得科处处罚的持续性的抽象危险,进而属于继续犯,则存在疑问。这是因为,即便出售了数额特别巨大的假币、贩卖了一吨海洛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抵国家一百亿的增值税款,超过二十年一般也就不再追诉了,而行为人持有几千元假币、捡拾私藏一小包海洛因、一叠面额几元的伪造的定额发票,追诉时效却一直不开始计算,恐怕有失罪刑均衡。所以,本文倾向于认为,只有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与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是抽象危险犯和继续犯,其他的持有犯都不宜归入抽象危险犯和继续犯范畴。
理论上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16]。可是,《刑法》第133条对危险驾驶罪罪状的表述是“追逐竞驶,情节恶劣”“醉酒驾驶机动车”“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危及公共安全”。这说明,无论哪一种情形的危险驾驶,都要进行具体判断。至于“两高一部”将“醉酒”驾驶的标准确定为“人体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其实就是为统一司法以进行具体判断。按说在道路上酒后驾驶机动车就对公共安全存在抽象性危险,立法者强调必须是“醉酒”驾驶机动车才成立犯罪,就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或者说,“醉酒驾驶机动车”与“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等表述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强调司法人员在具体个案中必须进行有无公共安全危险的判断,所以,应该认为危险驾驶罪不是抽象危险犯,而属于准抽象危险犯[3]。理论上一般认为环境犯罪是累积犯。累积犯的本质是,单个的不法行为无法对集体法益造成损害,但如果多人实施不法行为或个人多次实施不法行为,则会导致集体法益遭受实质性侵害[11]。也就是说,单个人猎捕杀害野生动物、毁坏植物、非法采矿,不会导致整个环境资源状况的恶化,但如果法律不予制止,在多数人实施的情况下,势必导致环境资源的彻底破坏。正因为此,可以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绝大多数罪名属于累积型抽象危险犯(13)这些罪名分别是:(1)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2)非法捕捞水产品罪;(3)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4)非法狩猎罪;(5)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6)非法占用农用地罪;(7)破坏自然保护地罪;(8)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9)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10)盗伐林木罪;(11)滥伐林木罪;(12)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
理论上通常认为《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所谓选择性罪名。但是,应认识到就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公众健康的侵害而言,走私、运输和制造毒品的行为对于公众健康只具有抽象性危险,而抽象危险犯,是无论如何也不宜适用死刑的。因此,行为人只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不能判处死刑;走私、运输、制造大量毒品,但实际仅卖出其中少量毒品的,应以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与贩卖毒品罪数罪并罚,不宜判处死刑,不应笼统地认定其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进而将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认定为整个犯罪的数量,从而错误适用死刑。虽然“两高”将《刑法》第363条第1款罪名确定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但应认识到,单纯制作、复制而不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对法益只具有抽象性危险。而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并非重大法益,对于非重大法益一般来说不宜处罚抽象危险犯。所以,制作、复制不是该罪的实行行为,单纯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四 准抽象危险犯之提倡
准抽象危险犯概念其实强调的是,“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存在一种需要司法上具体判断有无行为危险性的独立危险犯类型”[3]。认为刑法分则中有关“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危及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都是所谓具体危险犯的标志性表述的观点[2],明显存在疑问。按照这种思维逻辑,搬一块大石头放在两三天才有一趟列车经过的铁轨上,并不能马上成立破坏交通设施罪,只有等到两三天后列车快要到来时才能肯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成立;在公共汽车晚上入库后剪断刹车油管,还不能马上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只有等到第二天公共汽车出库上路行驶转弯、下坡等需要紧急刹车时才能肯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行为人在自家小作坊加工病死猪肉时还不能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只有等到行为人出售病死猪肉,甚至等顾客消费病死猪肉时,方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等。很显然,这种迟延处罚的理解势必放纵犯罪。其实,刑法分则中的“足以”并非具体危险犯的标志,只是对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的要求。只要破坏了交通工具的关键部位(如刹车油管),即便还未形成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也能肯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只要在正在运营的铁轨上放置石头,足以导致火车脱轨,无须等到火车快要驶来时,也能肯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成立;行为人只要生产、销售的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食品,即便还没有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就能肯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成立;行为人只要生产、销售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医用器材,即便还未对患者的健康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也能肯定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成立;行为人只要生产、销售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就能肯定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成立;行为人只要采集、供应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血液,制作、供应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血液制品,即便还未对患者的健康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也能肯定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的成立。因此,上述《刑法》分则中的六个“足以”型犯罪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
理论上认为有“危及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表述的罪名都是具体危险犯。可是,若认为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只有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才能成立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会导致处罚过于迟延;若认为携带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对这些特定场所的安全形成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才能肯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的成立,可能导致该罪的处罚范围过小而不利于保护法益;如果认为违反相关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只有对公共安全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以及行为人采用暴力或其他方式干扰驾驶人员正常驾驶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形成了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才能肯定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成立,则无疑导致此类犯罪与作为具体危险犯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混淆。因此,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化品运输型危险驾驶罪与妨害安全驾驶罪,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
张明楷认为,成立污染环境罪必须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后果,因此,该罪是实害犯[17]。但是,如果认为只有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实害才能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刑法修正案(八)》为了降低入罪门槛、加大打击力度,而将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其实,“污染环境罪”的表述旨在将排放、倾倒、处置没有超出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的排污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司法实践中,诸多判决认为,超过国家标准排放含有铬、锌等重金属的电镀加工的废水(14)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4)温乐刑初字第615号刑事判决书。,违规填埋电镀污泥(15)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3)太刑初字第0617号刑事判决书。,将超过国家标准的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废液、废物直接排放、倾倒于河流、土壤中(16)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4)茂南法刑初字第163号刑事判决书。,非法对医疗废物进行碎粉、分拣等行为(17)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4)宿城生刑初字第0006号刑事判决书。,均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既遂。显然,排污行为给环境造成了具体、现实、紧迫、高度的危险并非认定该罪的要件。相反,只需根据排污行为可能严重污染环境的事实即可肯定该罪的既遂[8]。由此可见,污染环境罪既不是实害犯,也不是抽象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
五 总 结
危险犯的传统二分法存在疑问。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存在一种中间形态——准抽象危险犯。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作业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军人叛逃罪,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是具体危险犯。并非所有的持有犯都是抽象危险犯和继续犯,只有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和持续犯,其他持有犯,如持有假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不是抽象危险犯和继续犯。危险驾驶罪是准抽象危险犯。可以认为除污染环境罪之外,其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基本上属于累积型抽象危险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对公众健康只具有抽象性危险,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宜判处死刑。由于单纯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只具有抽象性危险,所以制作、复制不是实行行为,单纯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刑法》分则中有关“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公共安全”与“危及飞行安全”的表述不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志。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中的六个“足以”型犯罪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化品运输型危险驾驶罪与妨害安全驾驶罪,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污染环境罪既非实害犯,也不是抽象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