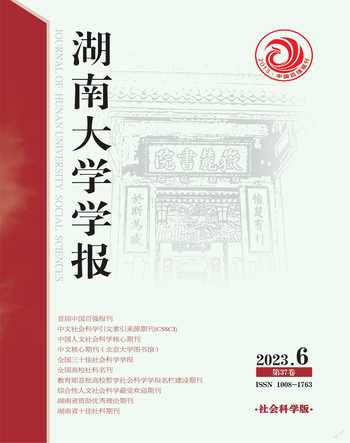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法输入与研究
——“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
陈 煜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0)
江户时期(1603-1867),日本自1639年之后,即开始全面锁国,所以特别是江户时代前中期,可称为“锁国时代”;而中国在康熙时期(1662-1722)之后,也厉行海禁,闭关锁国。这段时期,除有限的贸易交往外,中日双方并无正式的邦交。且此时期,两国政治体制和治理形式不同。中国延续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日本虽然由将军掌握实权,且集权程度达到了武家政治的最高峰,但是政权构成依旧是“幕藩体制”,全国除将军外,还有二百六七十个大大小小的藩,这些藩的藩主(大名)在领地内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两国的立法体制迥异。故而这段时间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流。间接表现在双方并无法律人士的往来,而是法律文本的交流,且只有中国法对日本的输出,而无日本法对中国的输入。至江户后期,随着幕藩体制的松动,部分具有实力的藩,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模仿明清律例乃至以此为范本,制定仅适用于各藩的“藩法”。但在幕府层面,则始终维持其武家法传统。故,在幕府控制力较强的江户前中期,在立法层面上,中国法对日本的影响始终有限。这一时期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中华法律文本及律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以及日本相关人士特别是儒学家对中国法的研究上。本文主要考察此时期中国法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对中国法的研究,以深化对中日法文化交流的理解。
一 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
虽然日本锁国之后,只有长崎一口通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贸易往来间断,相反,每年开进长崎港的中国船只络绎不绝,带去大量的中国货物,(1)关于每年开进长崎港的中国船只量,参见木宫泰彦的统计表“来日清朝船只一览表”,载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639-647页。其中,中国书籍就是货物之大宗,备受日本重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日本幕府偃武修文的治理趋势和儒学重光的刺激之下,整个社会对各类书籍特别是儒学方面的书籍需求量大幅度增加。诚如大庭修先生所云:“幕府实行文治政策,奖励学术,从而使嗜好读书的大名和市民文人与日俱增,书籍的需要量亦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与日俱增。”[1]110而在这数量巨大的汉籍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法律方面的书籍,包括各类法典和律学作品。在日本对中华法律文化研究最具浓厚兴趣的德川吉宗(1716—1745年在位,退位后依然操纵幕府,直到1751年去世为止)时代,卷帙浩繁的中国法律书籍已经出现在幕府将军、大名及众多儒士的眼前。以输入的时间排序,至宝历三年(1750),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书籍如下(2)参见[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日]《有德院殿御实纪》,载《续国史大系》(第十三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4年版;等等。:
1.元禄七年(1694)之前
《大明令》《皇明祖训》《教民榜文》《诸司执掌》《吏计职掌》《大明集礼》《大明会典》《吾学编》《皇明泳化编》《律条疏义》《读律琐言》《大明律律附》《律解辩疑》《大明律读法》《大明律管见》《大明律集解》《大明律会览》《大明律全解》《详刑冰鉴》《大明律正宗》《刑书据会》《大明律注解》《直引释义》《吏学指南》《吏文辑览》《类书纂要》《无冤录》《六言杂志》《萧曹遗笔》。
元禄七年(1694),纪州藩儒士榊原玄辅(篁洲)作《大明律谚解》,就参考了上述诸书,可见这些书必在此年之前已输入日本。
2.宝永七年(1710)
《大明律读法》《大明律管见》《大明律会解》《大明律直引》《大明律详注分解大全》《读律琐言》《读律私笺》《律解辨疑》《职源》。
以上诸种,除《职源》为宋人王益之所作以外,其余均为明律注释书。
3.正德元年(1711)
《大明律附例》《大学衍义补》。
以上前者为当时的法典,后者则为明代著名学者邱濬的名作,对江户律学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4.正德二年(1712)
《大明律释义》《大明律例添释旁注》《大明律例附解》《大例附解》《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
以上诸书中的《大清律》,应为顺治律;《大明律例添释旁注》为明人舒化所作。
5.正德三年(1713)
《大明律笺释》《大明律私笺》。
6.享保五年(1720)
《大清会典》《定例成案》。
7.享保六年(1721)
《六谕衍义》。
原书由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范鋐所作,1721年被琉球使臣程顺则自福州带回琉球,并由松平萨摩守吉贞献给幕府,后成为幕府用来教化普通民众的重要教科书。
8.享保七年(1722)
《大清会典》《定例成案合镌续编》《大清律辑注》。
《大清律例辑注》为康熙年间的沈之奇撰,为清早期著名律学作品。该书1723年被收入江户幕府红叶山文库。
9.享保八年(1723)
《江南赋役全书》《福建赋役全书》《山西赋役全书》《本朝则例类编》《本朝续则例类编》《续增处分则例》《六部考成现行则例》《御批处分则例》《大清品级考》。
10.享保十年(1725)
《乐书》。
此书乃清人朱佩章献,德川吉宗命荻生徂徕训译。
11.享保十二年(1727)
《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
12.宝历三年(1750)
《成案汇编》。
此书由清人周学健编辑,选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十一年(1746)之成案,又加康熙年成案编辑而成。
以上所列中国法律书籍输入日本的时间和书目,主要是根据大庭修先生的统计和相关史籍得出。可见,这段时期输入日本的中国法律书籍,必定存在着散佚情形,且大量的书目无法考证出确切的输入时间。可以推知,至吉宗时代为止,输入日本的中国法律书籍必定比上述所示还要多。不过,即便是从这种挂一漏万式的举隅,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其一,输入日本的中国法律书籍品类相当齐全。就法律规范而言,有国家大典,如《大明律》《大清律集解附例》等;有皇帝谕旨或诏敕,如《皇明祖训》《教民榜文》等;有部院则例,如《本朝则例类编》《大清品级考》等;有各地省例,如《江南赋役全书》《福建赋役全书》等。就律学作品而言,有律例注释考证类,如《大明律读法》《大明律私笺》等;有案例汇编类,如《定例成案》《成案汇编》等;有司法心得类,如《详刑冰鉴》《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等;还有法医学著作,如《无冤录》等。其他与明清律例相关的书,尚有官箴类书,如《吏文辑览》《吏学指南》等,甚至还有讼师秘本,如《萧曹遗笔》等。除了未见图表类、歌诀类律学作品外,主要的明清法典和律学作品几乎都在日本得以流传。
其二,对于较为经典的法律规范和律学作品,日本会一而再地输入。明清律例和会典自不必说,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中国法律书籍,且坊肆易得,故各种版本都被一再输入。除此之外,明清著名律学家的律学作品,也是一传入日本即受到重视,需求量也随之提高,所以得以一再输入,如杨简的《律解辩疑》,雷梦麟的《读律琐言》,应槚的《大明律释义》,王樵、王肯堂父子的《读律私笺》,等等。这些律学作品后来无疑成为日本律学家解读和研究中国法律的津梁。
其三,中国法律书籍输入日本,基本上延续了其在中国内部传播态势。一般而言,书籍的出口会滞后于在国内的销售,自不能同步,尤其在资讯和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但是传播到日本的中国法律书籍,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新潮”的情形。明律自不待言,清朝的立法成果和律学作品也很快就被传播到日本,以《大清会典》的传入最为明显。享保七年(1722)传入的《大清会典》,只可能是康熙朝的,因为雍正朝的《大清会典》,要到雍正十年(1732)才编纂完成,而康熙朝的《大清会典》,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可见不过30年时间,该书即已传入日本。考虑到康熙《大清会典》有一百六十二卷的巨帙且最初仅在官府中辗转,其后才得以流入坊肆,再加上刊刻不易,则该书传入日本已属非常迅速,同样的情形还有各部院的则例。整体上看,日本从中国输入法律书籍,是既全面又迅速的。
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输入各类中国法律书籍,除了其能体现儒学思想(“一准乎礼”),引入这些书籍有裨于弘扬儒道、推行儒学之外,另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川幕府较之于镰仓、室町两幕府,更加注重以法制治理天下。诚如日本法学家鸠山和夫、阪本三郎所云:“家康以不世出之英才,识见颇高,谓统制天下之道,莫如赖法律之便。”(3)[日]鸠山和夫、阪本三郎:“法制一斑”,载[日]大隈重信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第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开幕江户之初,即多方刊刻古籍,鼓励诸大名献书。庆长七年(1602),在江户建立国家图书馆(红叶山文库,又称枫山文库,位于江户富士见町),来收储各类典籍。(4)《东照宫御实纪附录》卷廿二,载《续国史大系》第九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2年版,第331页。这些典籍中,就有从中国舶来的《大明律》和《大明会典》等书,家康也借鉴了《大明律》和《大明会典》中的某些制度,来实行幕府统治。[2]52-53而幕府将军中,最热心于法律之学者,莫过于八代将军吉宗,史载:
对于本邦往昔古书,(吉宗)下令搜求。一遇唐商携来,必先遍览书目,就中择有用之书购之。诗词歌赋文人文集之类,无意强求,而有辅政道,可备治具之书,则广寻博收。唐土府州县志之类不可计数,是以御库藏书陡然倍增。(5)《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十,载《续国史大系》第十四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3年版,第294页。
由此看来,中国法律书籍显然属于“有辅政道,可备治具之书”,所以吉宗会孜孜以求。吉宗时代,也是中国法律书籍传入日本的一个高峰时期。典章制度之书,对幕府而言是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所以吉宗在充实文库藏书时,给予特别重视。如享保七年(1722)正月,他下令收集古书,除经史之外,还特别强调政书法令类典籍,如《律集解》《令抄》《弘仁式》《法曹类林》《为政录》《本朝月令》《律令集解》《类聚三代格》《式目追加三十三条》《建武式目》,以及《贞观式》(该法为日本贞观年间所定之式,非中国唐朝之式)等等。(6)见《有德院殿御实纪》卷十四,载《续国史大系》第十三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4年版,第721页;另见《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十,载《续国史大系》第十四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3年版,第292页。这些都是在日本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法文化书籍。吉宗在幕府行政和立法方面,就多方参考了古代日本典章制度和从中华传来的明清法制书籍。
二 江户时代的中国法律研究
江户时代的中国法律研究,至享保时期达到最高峰,二十年间,律家辈出,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也因而得以深化,继而为此后的日本法制借鉴吸收中国法律特别是明清律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我们且将江户时代关于中国法律研究的学问,简称为江户律学。日本律学家通过对中国法律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律在日本的传播。因此,这也是一个中华法系在日本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
江户时期,日本关于中国法研究的律学成就斐然,尤其是明律研究名家迭出,蔚为风潮。一般认为江户的明律研究起自榊原玄辅(篁洲),史载:
篁洲岁过不惑,好读《文献通考》《(唐)六典》《通典》等书,专研讨历朝之沿革制度,故如明律,尤其所精究,尝奉侯命,撰《明律谚解》三十一卷。自是而后,若高濑学山,物徂徕之辈,讲明律者往往有矣,其讲明律学、政书,起自篁洲云。[3]23
榊原玄辅兴趣广泛、学问渊博,《明律谚解》可视为其典章制度研究的代表作。此书是他奉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贞之命所作,1690年底开始动笔,至1694年6月书稿初成。该书由目录一卷和本文三十卷组成,为江户时代最早的明律注释书。该书首先将明律例原文用日本假名进行训点,使之符合日本人阅读的习惯,然后将文中需要解释的地方专门框出来,进行注释。在注释时,玄辅广泛参考了各种汉籍,在旁征博引之后,参以己意,确定文义,再用通俗易懂的俚谚形式表达出来。
玄辅殁后八年的1713年(正德三年),对明律素有兴趣且有研究、时为纪州藩主的德川吉宗,命篁洲之子榊原霞洲(武卿,1691-1748)及一二通明律者来对玄辅的《明律谚解》重行参订。此事见于《〈大明律例谚解〉序》一文中,内云:
法律之详,莫若《大明律》矣!只因律文少解,条例无注,而读者往往不能通晓焉。顷岁榊原玄辅为之注说,凡三十一卷,其书以俚语解,教人易晓,名之曰“谚解”,然而尚未脱稿也。今兹之夏,其子武卿,及一二通律者,相与参订,聊成其业。惟恐引证或爽、解意不当,故尚未敢缮写,以俟后之考正焉。夫本朝拟刑,原有成宪,然罪之可疑,议之难决者,参之此书,则或得其情矣。此谚解之所作业。于时正德三年冬十一月。(7)“《大明律例谚解》序”,转引自[日]松下忠:《纪州の藩学》,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4年版,第128页。
上文“一二通明律者”,乃高濑忠敦(又名喜朴,号学山,1668-1749)和鸟井春泽(1668-1742)二人(8)参见[日]松下忠:《纪州の藩学》,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4年版,第128-129页;[日]高盐博:《日本享保时期对明律的研究及所受的影响》,载刘俊文、[日]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鸟井春泽为同藩大儒李一阳(1636-1700)的弟子(9)李一阳为李梅溪的养子,而李梅溪则是朝鲜归化人李一恕之子。李一恕于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文禄之役时,被时为纪州藩主的浅野幸长俘虏,后带回纪州,因其为朝鲜大儒,后世代仕纪州藩为儒官。,亦精于明律,而霞洲则继承了玄辅之学。是以霞洲在忠敦与春泽的协助下,共同参订玄辅遗稿。所谓参订,主要是校正原典与引用文献,也改正和增补所作的解释,共改正大小谬误187处,书名由原《明律谚解》修订为《大明律例谚解》。据高盐博先生考证,改定的187处单独被订成一册,名曰“订正一卷”。此“订正一卷”上呈吉宗后,吉宗仍不满意,于1815年命年纪稍长的高濑忠敦主持,霞洲辅助,继续对“订正一卷”进行修订,此次修订为“考正”,再将这次考正后确认无误的内容列入玄辅原书中。最终形成了后世所看到的《大明律例谚解》三十一卷。(10)[日]高盐博:《日本享保时期对明律的研究及所受的影响》,载刘俊文、[日]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1页。
虽然玄辅的研究存在缺憾,但是其开日本研究明律风气之先,于中国法在日本的传播及之后渗入立法和行政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大明律例谚解》亦当之无愧地成为江户时代日本研究中国法最早之名著,此后的律学家皆受益于此书。
继玄辅之后,第二代明律研究者开始走出纪州,围绕在八代将军吉宗周围展开研究,从而在江户形成一个律学家群体,并达到了日本明律研究的巅峰。成就最著者为高濑忠敦、荻生徂徕和徂徕之弟荻生观三人。
高濑忠敦是继篁洲之后,纪州藩中明律研究最著名者,著述丰赡,尤以《大明律例译义》闻名于世。如上所述,此书是吉宗因篁洲的《大明律例谚解》不够清晰,乃命忠敦重译而成。忠敦于1720年初受命之后,即开始译注,至当年底告竣。
《大明律例译义》分卷首和正文十二卷,共十三卷。卷首列有“律大意”“译义凡例”“目录”,卷一至卷十二,为“名例律”至“工律”的译义。忠敦此书较有特色的地方在于正文前专门列有“律大意”,此为其他诸家注律所无。“律大意”共分39条,其并非忠敦自撰,而是从8种汉籍中摘录出来并直接译成日文的,按照摘录条数多寡,分别为《律例笺释》(明王樵、王肯堂父子撰)15条,《大学衍义补》(明丘濬撰)10条,《汉书》(原文写成《前汉书》)5条,《新唐书》(原文写成《唐书》)3条,《尚书》2条,《孟子》2条,《周礼》1条,《论语》1条。就所引典籍来看,其中前二者为律学著作,后二者为史籍,后四者为儒家经典。就所引用的内容来看,其主要涉及明律的制定始末与明太祖的立法思想,汉文帝、唐太宗、宋孝宗等皇帝与法律相关的嘉言懿行,中国传统重视人命、慎重用刑的思想和实践,重视证据、理性审判的观念,监狱管理与刑罚执行应该注意的要点,等等,集中突出了德主刑辅、先教后刑、明德慎罚、哀矜折狱等法律观念。(11)参见[日]高濑忠敦:《大明律例译义》“首卷·律大意”部分,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至于正文,高濑忠敦主要是对明律律文和例文进行直译,而不列中文原文,译文简洁流畅。比如《户律》之“户役·收养孤老”条,明律原文:
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4]51
忠敦首先对“收养孤老”这一律目进行解释:
对幼而无父、老而无子及因个人生理原因等难以自存者,由官府负责收留养育。(12)[日]高濑忠敦:《大明律例译义》“卷四·收养孤老”条,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这就将该律的中心精神做了一个交代。接着,忠敦开始解释律文,他对于某些字词,是通过在律文中做小注的方式来解释的,与明清律例中夹注小注的方式庶几相似。我们来看其对该条律文的注释:
凡鳏(老而无妻者)寡(老而无夫者)孤(老而无子者)独(幼而无父者)及笃疾(患病如槁木乃至生活无法自理者)之人,且贫穷又无亲友可以投靠,无法自存者,其所属官府应于养济院收养存恤,其有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已收养而应给衣服食物而官吏克扣者,并赃以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处理。(13)[日]高濑忠敦:《大明律例译义》“卷四·收养孤老”条,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对比明律原文,忠敦的译文十分忠实于原文,对特定的语词进行了释义,如上文括号中内容即是。并且,在原文未交代或者语义模糊之处,如收养在何处,忠敦专门标列出是在“养济院”。这一释义显然受到了明律注释书《明律笺释》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绎忠敦此书,会看到他在很多地方都引用了《明律笺释》的内容,此书亦是江户律学家最常援引的作品之一。
除了此类简洁的字词注释之外,忠敦也会假设某种情境,将抽象的条款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如对《刑律》之“斗殴”条,在按原意译完“因斗互相殴伤者,各验其伤之轻重定罪”之后,忠敦假设了一个情境来加以说明:
设如平太、弥太二人互殴,弥太首坏平太一目,平太继还弥太二目。则弥太因坏平太一目故,按律当杖一百、徒三年。平太则因坏弥太二目故,杖一百、流三千里,且付财产之一半予弥太。(14)[日]高濑忠敦:《大明律例译义》“卷十·斗殴”条,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此处忠敦将日本人名代入明律条款中,设想互殴的情境并提示处罚结果,这样的译法应该很容易让日本读者产生代入感,对于日本读者理解明律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继忠敦之后,最杰出的明律研究者已然从纪州转向江户,其中又以荻生兄弟为代表。尤其是荻生徂徕(1666-1728,以下简称徂徕),又称物茂卿,名双松,小字总右卫门,号徂徕,又号蘐园,为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流派“古文辞学派”的创立者,因号蘐园,故其学派亦称为“蘐园学派”。徂徕在中国法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作品就是《明律国字解》。关于《明律国字解》成书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目前,日本的天理图书馆中藏有徂徕该书手稿,不过是一个未定稿。但据徂徕的高足——同样为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太宰纯(春台,1680-1747)的记载,至晚到1724年5月,《明律国字解》已经完成。[5]124该书写作有一个背景:1722年10月,幕府的儒官、徂徕的胞弟荻生观(号北溪)在吉宗的授意下,完成了《大明律》的和文训点工作,翌年8月,此书在京都、江户等地的书肆上即已刊行,之后几度重版,传播很广。因为这是幕府认定的权威版本,故出版时定名为《官准刊行明律》。幕府在推出这部作品之余,趁热打铁成立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明律研究会”,发起人即为荻生观。参加者皆为幕府高官或著名儒者,除荻生观外,徂徕的高足太宰纯等皆参与这个明律研究会。徂徕是否正式入会不得而知,但是其《国字解》的写作,极有可能与该研究会的需要有关。有两点似乎可以证实此点,其一,研究会的盟约名为《徂徕先生条约》,可见徂徕必为研究会宗旨进行过一番设计;其二,就在1724年,荻生观推出了其明律研究的作品《明律译》三十卷,而同样在当年的5月,徂徕的《国字解》完成,弟兄几乎同时对《官准刊行明律》进行注释,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工,弟弟忠实地将明律译成和文,而哥哥则用和文对明律条款进行解释,这不都是为研究会同仁研究明律提供便利么?
因此,高盐博先生亦推测,徂徕可能也参与了弟弟《明律译》的翻译工作,且是在将军直接授意下写作《国字解》的。[5]124再结合《国字解》并非对明律条款逐字逐句的翻译和解释的情形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字解》是对《明律译》的补充,为避免重复,《明律译》中介绍过的《明律国字解》就省略了,这也是徂徕之书思想内容上的一个特色。整体而言,徂徕该书的特色在于:侧重于名物制度的训诂;注意对律文的历史及制度源流进行梳理;强调在特定的语境下解释字词,并且注释详略得当,带有强烈的比较法色彩;注意以官制为脉络来解读律例。《国字解》纂成之后,因其语言通俗平实,且对于明律做了最适合日本人阅读的“本土化”解释,再借助徂徕儒学的影响力,所以一经付梓,风靡一时。这自然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在日本的传播。而且,因为徂徕本身就是蘐园学派的创立者,他的研究也带动了其门人弟子的中国法律研究,如荻生观(可视为广义的蘐园门人)的《明律译》,三浦竹溪的《律学正宗国字解》《详说明律释义》《明律口传》,荻生金谷(本为徂徕兄徂徕春竹之子,1720年被过继给徂徕为养子)的《明律译义》等。这些作品既是受徂徕中国法律研究推动所致,又是徂徕学本身结出的硕果。此外,荻生徂徕的《明律国字解》,还作为门人弟子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材在使用,如松下忠先生所论:“明律研究可能是日本人获取中文知识的不二法门,对于想了解中国整体情形者,尤为必要。在最强调中文修养的儒学流派——‘蘐园学派’中,更是将明律作为学习中文知识的经典教材。”[6]142关于荻生徂徕明律研究的成就和特色,笔者另有专文详论,在此不赘。[7]
再来看徂徕之弟荻生观(北溪,又名物观,1669-1754)的明律研究成就。从《德川实纪》等史籍的记载来看,他的研究成果亦颇丰,除律学外,最为重要且为中国所知者,乃是其对纪州藩儒臣山井鼎所撰的《七经孟子考文》进行了补遗,后来此书于1730年(日本享保十四年)进呈给吉宗,得到允许后1732年于东都书林刊刻出版。此书很快即传入中国,共计199卷,计《周易》十卷、《尚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毛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这部校勘学上的巨著,乃是《十三经注疏》校勘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时唯一收录的日本学者的著作。(15)参见 [日]山井鼎撰 , 物观补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即此一点即可看出荻生观的学力之深厚。
荻生观在明律的成就主要有二:一是为《大明律》加注训点,撰成训点本三十卷,这项工作在1722年完成,当年即在江户以《官准刊行明律》之名出版,次年又在京都刊行;二是于1724年完成了《明律译》三十卷。后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律学注释本而作,是以比较正式的文字来翻译明律,旨在疏通句义,仅有写本存世,未刊行。而前者则是为了给世人提供一个便于利用的明律版本,荻生观用适合日本读者阅读习惯的方式,将明律系统地点校一遍,又加上了日本训点和假名。因点校精良,荻生观这一版本,此后就成为日本通行的明律标准版本,江户诸多明律研究成果,亦以此训点版本流传最广。
从荻生观为《七经孟子考文》进行补遗获得中国学者阮元等的赞誉,以及另外受命校订《唐律疏议》和会同训点《大清会典》等事迹来看,荻生观有很强的古文献学功底,长于校勘之学。所以,其明律研究最大的成绩就在于校勘训点明律,从而使得明律能为江户一般儒者所用,这对于推动明律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同样至关重要。
第三代明律研究者,除前述纪州藩的榊原霞洲之外,以荻生徂徕“蘐园学派”门人弟子最为杰出,其中尤以三浦竹溪(平义质,1689-1756)和荻生道济(金谷,1703-1776)为代表。这里仅对三浦竹溪的《明律口传》作一考察。三浦竹溪有吏才,先后出仕甲斐(在今山梨县)和吉田(在今爱知县),史载:
竹溪尤留志经济,精于律学。享保中执政滨松侯信祝(笔者案:即松平信祝,原为伊豆守,后移封吉田藩,时任幕府老中)厚聘之,不肯起,物金谷(笔者案:即荻生道济)强之而后可……竹溪有吏才,尤通知执政参政之所事、诸官之所职,以其所掌皆政府之要务,留意先朝之旧典、历朝之沿革。故自六经诸子及传记小说,亦其所务,专在经国之业也。其练达时事,如视诸掌……[8]25-26
由此可见竹溪的学问倾向,《明律口传》为竹溪出仕吉田藩时,应该由藩武士奥村保之(又名源保之)所请而口授再由后者缮写润色而成,书成于1752年,保之在该书“序”中提到:
吾前君列相之日,吾亦掌相府之事,常时鞅掌不遑,然偷闲方卒明律之业……而欲刑期于无刑至刑措不用,若能如此,则夫礼乐在其中,然则何可言唯一学法律哉!是以学之竹溪先生之门……于是即以先生之口传之言及物子之训诫之语,具列于左,并记其所由,以备忽忘焉尔。(16)[日] 奥村保之“《明律口传》序”,载[日]三浦竹溪口述,奥村保之笔录《明律口传》(不分卷),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因此,可见奥村保之为裨益藩政治理之故,向三浦竹溪学习明律,竹溪即口授于他。为了回应何以要学异邦之法而不用礼乐之道治世,保之除了用“刑期无刑”之说来辩护之外,还特别抄录了“徂徕先生条约”(主旨是中国法律为异邦之法,学习当慎重,不可轻易传授奸佞之徒,不可随便应用),可见其学律的慎重。
《明律口传》不分卷,是对当时通行于世的荻生观训点的《官准刊行明律》的解释。从其内容来看,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解释洪武皇帝“御制序”、刘惟谦“进大明律表”以及“名例”诸条,这一部分解释得相对详细,将明律制定的始末、基本精神及罪刑要点都做了阐释,内容占到了全书的一半。第二部分则是解释自“吏律”至“工律”六篇诸条以及部分条例,相对简洁。整体《明律口传》并不是逐字逐句解释明律内容,而是挑选重点词句进行解释,有的则根本忽略。这一做法符合“口传”的特点。笔者推测,极有可能是奥村保之持着训点本明律,就疑难字句向三浦竹溪发问,而其已经理解者则略过不谈。是以该作品整体上并不连贯,更像一部中文词汇或个别句子的注释书,颇有点“汉和法律词典”的味道。比如“户律”的 “婚姻·逐婿嫁女”条原文:
凡逐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百。其女不坐。男家知而娶者,同罪。不知者,亦不坐。其女断付前夫,出居完聚。[4]61
作者在每条律目前用“○”这个符号来引出律文,而对于要解释的词句,则用“△”表示。对于该“逐婿嫁女”条,作者在“招婿”“断付前夫”“男家”“出居完聚”四个词前加了“△”,意在表明解释了这四个关键的词,整个律文的含义就明白了。(17)[日]三浦竹溪口述,奥村保之笔录《明律口传》(不分卷)“嫁娶逐婿”条,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口传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疏通律意的。
如此,以榊原玄辅、高濑忠敦、鸟井春泽、榊原霞洲四人为代表,形成明律研究的“纪州学派”,与以荻生徂徕和荻生观两兄弟代表的“蘐园学派”,成为江户律学成就最高的两大学派,松下忠先生形象地将之比拟为明律学“两横纲”(18)横纲(Yokozuna)是日本相扑运动员(日本称为力士)资格的最高级,见[日]松下忠:《纪州の藩学》,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4年版,第128页。。
明律研究自然是江户律学研究的重点和亮点,除此之外,其他中国法典,也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清会典》和《唐律疏议》。吉宗在藩邸时,即爱好法令典章之学,就任八代将军之后,又广泛收集各类典制书籍。他不仅收集,还命儒臣校订、训点、翻译各类日本古代以及明清时期舶来的典制之书。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不能以统治者个人爱好所解释,观其将军任内所进行的“享保改革”诸种举措,可以认为,他是在为改革寻找理论依据、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当然,他之所以重视《大清会典》,还有一层深意,就是希望能像康熙皇帝那样,兴利除弊,成就一代治世。
据大庭修先生的考证,吉宗应该很早就接触过162卷的煌煌巨著《大清会典》(《康熙会典》)。《大清会典》无疑是清代各项典章制度的大全,涉及各部官职政事,此尤吉宗感兴趣者,是以他曾下令于1720年、1722年两次加价购进此书。虽然有书,但作为异国之制,素称难读。于是在购得书之后翌年,吉宗即命手下儒臣深见有邻翻译此书。[1]221-117《德川实纪》载:
深见新右卫门玄岱,其子新兵卫有邻(此时称久大夫),奉命翻译《大清会典》。(19)《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十,载《续国史大系》第十四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3年版,第295页。
翻译大清会典,深见有邻,即久大夫(1691-1773)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1721年赴长崎,至1727年回江户复命,前后经历了6年。他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至少在1722年至1724年间,荻生观在江户同样从事此项事业。荻生观在1722年完成明律的训点之后,配合当时吉宗的需求也开始翻译并注释会典部分内容。
经过深见有邻、荻生观长期辛苦的工作,至1727年左右,《大清会典》基本上被译为日文。深见有邻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疏通字句之外,还进行了一定的考证,完成了《明清会典考》《满汉品级考拔书》等作品。此外,自1722年开始,在江户幕府短期任“天文御用”的长崎著名儒者、天文学家卢草拙元敏(1671-1729),即开始训点《大清会典》,至1727年训点完毕并受到幕府奖励。[9]175
再来看《唐律疏议》的校勘,其同样是荻生观受吉宗之命校正而成。荻生观于1725年底即校订完毕,为此还受奖银15锭。(20)见《有德院殿御实纪》卷廿一,载《续国史大系》第十三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4年版,第852页。荻生观为此版《唐律疏议》,改正了误字3142字,补漏脱字496字,删除衍字171字,改写颠倒字序79处。在校勘过程中,荻生观参考了《唐六典》《大明律》等中国典制以及《养老律》遗文等本国律令共计11种,校勘后还请赴日的清人沈燮庵复行校阅, 最终成就了一个精良的版本。此版本后又传到中国,为中国士人所重。《大清会典》与《唐律疏议》的训点、翻译和校勘,是江户律学在明律研究之外,所结出的又一硕果。
江户律学中,除了以上对中国律例的研究之外,另有一卓异之作值得我们注意,即仙台藩儒官芦东山(芦野德林,1695-1775)苦心孤诣耗时20余年始完成之《无冤录》一书,该书借鉴并模仿明代大儒丘濬(1420-1495)的《大学衍义补》“慎刑宪”一篇的体例和内容,总结汇辑儒家关于法律的论述和思想,以发扬光大儒学及为藩政改革之鉴。日本法律界对此书评价甚高,明治维新之后,参与明治初期法典编纂的原昌平坂学问所儒学教授,后来成为法官的水本成美即认为:“东山此书采收博而精,密而精,密而不冗,而各条案语,亦能贯穿和汉古今,折衷至当……”(21)[日] 水本成美:“《无冤录》序”,转引自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5页。
此外,还有一类作品,研究的既非中国律例,又非中国法制历史或法律思想,但是其中贯穿了中国法律的事例及对之的看法,我们暂且也将之作为广义的律学作品涵盖进来,如室鸠巢(名直清,通称新助,1658-1734)的《文公家礼通考》和太宰纯的《经济录》等。前者是对明清比较流行的《文公家礼》进行礼仪制度上的梳理,考证了祠堂、庙制、正寝、龛等制式及应用之道(22)参见[日]室鸠巢著:《文公家礼通考》,[日]板仓胜明辑:《甘雨亭丛书》(第一集)1844年雕版,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其论述方法与律学考证之法庶几相通。而后者则是太宰纯最负盛名的著作,体现了作者“通经致用”的儒家经世情怀,共分十卷,分别为“经济总论”“礼乐”“官职”“天文·地理·律例”“食货”“祭祀·学政”“章服·仪仗·武备”“法令·刑罚”“制度”“无为·易道”。尤其是第八卷“法令·刑罚”中,太宰纯梳理了中国法制的变迁,强调了法贵简洁、法尚公平、不得朝令夕改等法律思想,并且提到圣人治国,以德礼为本,需明德慎罚,哀矜折狱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华儒家法思想。(23)参见[日]太宰纯著:《经济录》,载《日本经济丛书》(卷六),东京:日本经济丛书刊行会1915年版,第211—241页。太宰纯在论述这些思想观念时,举了中国古人嘉言懿行的正面事例和坏法败德的反面事例来论证,其同样可以视为广义中国法思想的阐发。这类作品在此仅举这两例,意在表明江户儒者中,关注中国法律者甚多,儒者与律家无截然之界限。
总之,江户律学以明律学为中心,旁及多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现在将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总结如下(24)参考[日]《有德院殿御实纪》,载《续国史大系》(第十三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4年版等;[日]原善著:《先哲丛谈》,东京:江户同盟书屋1879年版;[日]东条耕著:《先哲丛谈后编》,东京:江户书林三家合刊,1830年版;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Kanseki Database”;[日]松下忠著:《纪州の藩学》,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4年版;[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1.榊原玄辅
玄辅撰《明律谚解》三十一卷,1694年初成(写本)。玄辅为江户大儒木下顺庵弟子,纪州藩儒官,《明律谚解》系应纪州藩主德川光贞所请而撰,江户时期的中国法研究由此兴盛。
2.新井白石(君美)(1657-1725)
白石对明清律例有广泛研究,将明律相关制度应用于幕府实际施政措施中;作《田制考》《职官考》《车舆考》《冠服考》等,内容广涉中国法。他同样为大儒木下顺庵弟子,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七代将军家继的幕府儒臣,主导推行“正德新政”。
3.室鸠巢
他与荻生徂徕一同撰《〈六谕衍义〉大意》(1721),并作《文公家礼通考》等。他同样为大儒木下顺庵弟子,1710年入仕幕府,后成为八代将军吉宗智囊,在吉宗时期最受尊奉,系地位最高的幕府儒官,毕生奉朱子学为正统。
4.鸟井春泽
他和榊原霞洲对榊原玄辅的《明律谚解》进行参订,最终于1713年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明律谚解》,即他二人的修订本。春泽为江户大儒李一阳的弟子,也是纪州藩儒官。
5.榊原霞洲
他和鸟井春泽对榊原玄辅的《明律谚解》进行参订。他是榊原玄辅之子,嗣玄辅之职。
6.高濑忠敦
忠敦撰《大明律例译义》十三卷,1720年撰成;《大明律例详解》三十一卷,1744年撰成;此外尚有《明律决义》十四卷,《明律私考》十七卷,《明令考》一卷,《唐律解》九卷,《唐律谚解》十六卷等。他是江户大学头林凤冈的弟子,其父高濑松意为纪州藩儒医,忠敦袭职,后为纪州藩儒官,忠敦的律学著作多以写本形式流传。
7.荻生徂徕
徂徕与室鸠巢一同撰《〈六谕衍义〉大意》(1721),撰《明律国字解》(1724年完成),系江户儒者,他的《明律国字解》大概系为其弟荻生观所训点《官准刊行明律》一书所作之解释,为江户时代最为著名的明律注释书之一。
8.荻生观
荻生观为《大明律》加注训点,撰成《官准刊行明律》三十卷(1722年完成);撰《明律译》三十卷(1724年完成);校订《唐律疏议》(1725年受命,1730年左右最终完成),同时与深见有邻共同研究和翻译康熙朝的《大清会典》,系荻生徂徕之弟,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幕府儒官,《官准刊行明律》为其唯一公开的著作。
9.卢草拙
卢草拙训点《大清会典》(1722年训点,1727年完成)。此人为长崎儒者,1709年任长崎圣堂(孔庙)学头,1716年任长崎书物改役,1718年奉调江户改役,1718年奉调江户任“天文御用”,晚年回长崎圣堂讲学。
10.太宰纯
太宰纯撰《经济录》等,其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法。他是荻生徂徕的弟子,主张通经致用、捍卫古学,以经学名世。
11.三浦竹溪(平义质)(1689-1756)
竹溪撰《律学正宗国字解》《详说明律释义》《明律口传》(1752年完成)。他也是荻生徂徕的弟子,先后为甲斐、吉田藩儒官,《明律口传》为三浦口传,由吉田藩武士奥村(源)保之纪录并润色缮写成书。
12.成岛道筑(信遍,又名锦江)(1689-1760)
道筑为八代将军侍讲《礼记》等儒家典籍,并作有《明律讲读》,他是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幕府儒官。
13.鹰见爽鸠(字正长)(1690-1735)
爽鸠精研法律刑名政书仪制之学,错综和汉,无不宏通。他为荻生徂徕弟子,后仕田原藩,藩内功令多出其手。
14.深见有邻
有邻与荻生北溪一同翻译康熙朝《大清会典》(1721-1727),此外撰《明清会典考》《满汉品级考拔书》等。他是大儒深见玄岱(高玄岱)之长子,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幕府儒官,主管幕府红叶山文库。
15.冈白驹(字千里,号龙洲)(1692-1767)
白驹撰成《明律译注》九卷,他是活跃在京都地区的一代大儒。
16.芦东山
东山撰成《无刑录》十八卷(1755年完成),其中受邱濬的《大学衍义补》影响尤大。他是仙台藩儒者,仕本藩为儒官。
17.青木昆阳(字厚甫,通称文藏)(1698-1769)
昆阳撰成《刑法国字译》十二卷,《官职略记》十三卷。他是江户儒者,曾仕肥后秋山藩,亦为日本兰学(荷兰学)先驱人物。
18.荻生道济
道济撰成《明律译义》。他是荻生徂徕兄荻生春竹之子,1720年继徂徕嗣,系江户儒者。
19.涩井太室(字子章)(1720-1788)
太室撰成《明律详义》。他从昌平坂学问所大学头林榴冈问学,后仕为佐仓藩儒官。
以上只是江户时期较为著名的中国法律研究者,有的虽无系统著作流传,如新井白石、室鸠巢、成岛道筑、鹰见爽鸠等人,但因从其事实际幕政或藩政工作,故而研究中国法,主要在事功而不在立言,在他们的文集中,可以见到关于中国法的零星论述。当然这个统计依然存在着遗憾,如由荻生徂徕主持订立“明律研究会”的“条约”中,参与订约署名的人就有“物观,服南郭,藤东野,平义质,刘世马,冈正敏,增胜净,葛西正对,丹玄,松贞吉,严容,落敬,崎严,盛遂质,室伟丈,江机,祝隋延,森公绥,田尚足,小西切尚绮,三谷逵”(25)见[日]佚名著:《蘐园杂话》,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另见[日]三浦竹溪口述,奥村保之笔录《明律口传》篇首,写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二十一人。其中除了二三人有中国法律研究专书流传下来,其余的都没有留下律学作品。而未署名但参与研究会活动者,必定也不乏其人。故可想见,在这段时期之内,中国法特别是明律的研究是十分繁荣的。而自德川吉宗薨逝之后,从历史记载中来看,日本的中国法研究逐渐退潮,但即便如此,到19世纪,依然有人赓续此项事业且有作品问世,如名儒羽仓简堂(1790-1862)、菅野白华(1820-1870)等,菅野还留下了《明律汇纂》一书,可算是继享保年间日本律学的流风余韵了。
不过,与同时代注重为司法适用而注释法律的明清律学同行相比,江户律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与明清律学迥然不同。一方面,江户律学本质上是一种“书生事业”,是儒学研究的一环。小早川欣吾先生认为,伴随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兴盛,来自中国的法典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注意并被作为儒学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传统的律令学本来就是儒学中特别的一支,所以将律令作为儒学文本来研究也就自然而然了。(26)参见[日]小早川欣吾:《明律令对我国近世法制的影响》,载《东亚人文学报》第四卷第二号,“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45年3月,第394页。故而江户律学在整体上还是一种理论探讨,如大庭修先生提到的那样:“实际上,在江户时代,对明律的研究,除去两三个藩法部分地采取了明律之外,主要都是为研究而研究,是理论上的研究,或者是不出作为参考性的用于法律解释的范围。”(27)[日]大庭修:“江户时代的中日典籍交流”,载王勇、[日]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另一方面,江户律学基本上是一种“命题作文”,主要满足幕藩领主的需要。作为儒学知识,中国法集中体现了儒家的道德礼教,对于雅好儒术并意欲倡导儒家伦理的领主而言,中国法尤其是明律,是再好不过的载体。而对于治理幕藩,中国法和日本历史上的法制一起,可以给现实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故而从德川家康起,诸幕藩领主就有要求儒臣研究中国法之举。至吉宗,更是动员学者研究明律和日本古代法,除上文提及的榊原玄辅、高濑忠敦、荻生观等人的明律研究作品外,尚有人见美在、林信如、人见浩训点的日本古典法律典籍《令义解》《令集解》,成岛道筑的《明律讲读》等作品,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在幕藩领主命令下完成的。
所以,江户律学作品,对于律学家本人而言,主要是作为儒学的一种而进行研究,且这项研究,大多是幕藩统治者指派的“命题作文”,故而极少被用于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这就意味着,作为儒学研究的一环,它还是相对封闭的学问,没有如一般儒学那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三 结 论
以上对“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做了一番鸟瞰。在两国都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表面上并不热烈。中国甚至都感觉不到日本对中国法的反应,但是在日本,的确出现过传播、学习并研究中国法的热潮。故而这段时期这样的法律文化交流,就体现为中国法在日本的传播与日本对中国法的研究这两大维度上,主要是通过书籍这种载体而实现的。这类书籍以明清律例文本和注释律学作品为主,在江户前期,随着日本近世儒学研究热潮的萌发,从中国输入日本。其除了作为法律书籍之外,更作为广义上的“汉籍”乃至儒学作品,而为日本士庶所接受。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日本儒学和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幕末幕府和各藩的立法创造了条件,其影响在明治维新之后愈发凸显。
因为中国法律书籍在日本的广为流传,加上儒学研究的深化和幕藩治理的实际需要等原因,日本逐渐开始对这样的中国法律(主要是明律)进行相应研究。但这样的研究,并不是主要服务于司法适用,因为当时日本有自己的幕藩法制,与明律迥然不同,明律作为“外国法”,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司法使用中的法律渊源。明律作为儒家精神的典型体现和中国法典的代表,对于治国理政和推行儒家礼教方面,有着显然的优势,这令幕藩统治者心向往之,虽然其不能直接服务于司法适用,但是不妨碍其作为立法和行政改革的参考。所以江户幕府方面有意识地组织儒学者翻译、注释、研究中国法,这也促进了江户律学的繁荣。
虽然日本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研究的成果,除部分流传于世,并作为汉语教学的素材广泛流通外,绝大多数则留于“秘府”,供幕府命题者服务,相当于重要的“内参资料”。不过江户律学作为沟通中国法律和日本法律的“冰人”,终究是不甘寂寞的。到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若干强藩和明治政府,曾经仿照明清律例制定藩法和全国性的法,虽然未必全是由江户律学推动,但未始不可看作江户时代中国法律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所结下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