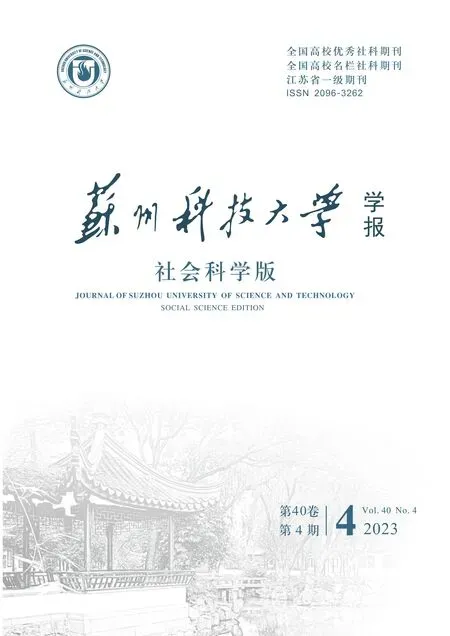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文本建构
韩正路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中国古代以鬼魂作为叙事视角的小说,以亡灵的云端视角俯察人间,更能还原现实与人性的本真面目,展现沉潜于世俗人性中的诸多病象。不仅因其新奇性吸引了一般读者,更因其兼顾现实剖析与审美提升功能的亡灵叙事为当代作家所青睐,并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被更加广泛运用。“亡灵叙事就是一种以亡者的灵魂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的行文方式”[1],作家以亡灵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让死者本人来叙述真相,使得文本的陈述更有说服力,更能增强文本叙述的诗性魅力。亡灵叙事类小说和中国传统的鬼故事有差异,其故事情节并无恐怖惊悚的元素,亡灵形象也不像鬼怪那样狰狞丑恶,而是充满人间世俗的理性色彩。新时期的亡灵叙事类小说,诸如方方的《风景》(1987)与阎连科的《横活》(1989)、《鸟孩诞生》(1993)等,在创作上尝试进行此类创作,开亡灵叙事的先河,且以中短篇体制为主。此后,新世纪涌现出亡灵叙事类长篇小说,在文本建构层面有了创新性的突破。新世纪也出现一些中短篇的亡灵叙事类小说,比如晓苏的短篇小说《金米》(2002)、段爱松的中篇小说《审判》(2017)等,但由于数量极少,且大多延续新时期的风格模式,影响力有限,姑且不论。
有学者指出:“数量繁多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文体形式上呈现出几种潮流化、规律化趋向,其一便是不约而同地运用亡灵的叙述视角,即以亡灵作为叙述者。”[2]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长篇小说涉及新老作家的创作。老作家的代表作包括阎连科的《丁庄梦》(2006)、莫言的《生死疲劳》(2006)、余华的《第七天》(2013);新作家的代表作包括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2012)、雪漠的《野狐岭》(2014)、艾伟的《南方》(2014)、孙惠芬的《后上塘书》(2015)、陈应松的《还魂记》(2016)、张翎的《劳燕》(2017)、梁鸿的《四象》(2020)等。新世纪亡灵叙事类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在真正意义上发展为一种潮流和文学现象,而完善的文本建构无疑是这类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和重要原因。
学界关于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研究大体呈现两种趋向:一种是侧重对某一篇代表性的亡灵叙事类作品进行探究和分析(1)周珉佳《“亡灵隔空对话”——〈劳燕〉的叙事新法》(《东吴学术》2019年第4期第73~79页)侧重分析了小说中“亡灵隔空对话”的技法;李雅妮、彭岚嘉《〈四象〉之“象”与梁鸿的叙事突破》(《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第132~138页)在分析小说思想内涵的同时,着重阐述了《四象》的亡灵叙事和疾病叙事;丁婷婷《〈第七天〉的亡灵叙事论》(2015年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从美学特征及文学史价值层面论述了《第七天》的亡灵叙事等。;另一种是从宏观层面上探究新世纪小说中的亡灵叙事(2)候登登《新世纪小说亡灵叙事的死亡意识》(2017年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从理论阐释、语境与叙述体验、文本建构、艺术策略等层面分析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死亡意识;杨敏的《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鬼魂叙事研究》(2019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系统阐述新时期以来鬼魂叙事兴盛的原因及鬼魂叙事的多重价值;晓苏的《论当代小说中的鬼魂叙事》(《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第156~161页)分析了鬼魂视角的叙述边界以及特有的神秘感、荒诞感与新奇感;杨潇羽的《2000年以来中国小说中的亡灵叙事研究》(2020年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从存在形态、艺术特征、出现因素及价值问题层面剖析了新世纪小说中的亡灵叙事。。由此可见,以往关于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研究多集中于艺术手法、叙事价值及美学特征等层面,部分学者对于这类小说文本建构的分析还停留于表层的文本主题、文本人物等要素的阐述,缺乏文本建构模式的深入探究。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读新世纪涌现的各类亡灵叙事类小说,聚焦新世纪亡灵叙事类长篇小说的文本建构策略。
一、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时空结构
1.“死后—死前”的时间结构
新世纪前后的亡灵叙事类小说都惯以倒叙的形式铺展小说情节。新世纪之前出现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在时间模式上即开启了“死后—死前”的文本建构,但是这一时期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往往并不在作品的开头交代亡灵叙事者死亡的事实,而是偏向在小说的中间或结尾部分点明叙述人物死亡的现实,从而给读者以恍如隔世的惊悚感和心灵的冲击感。如方方的《风景》在开头大段叙述汉口“棚户区”一家十一口的亲情荒芜和生存挣扎,继而在小说的中间部分才点明叙述者小八子已故且仅活15天的现实。莫言的《奇遇》(1989)写“我”回家乡探亲与已变成幽魂的邻居赵三大爷相遇交谈的故事。小说前文平淡自然,结尾笔锋突转,借母亲的话点明邻居已死的事实,让人倍感神秘与悚然。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在时间维度的建构上偏向以“死后—死前”的倒叙模式进行小说情节的铺展和亡灵心悸的追寻,在时空的穿梭与跳跃中还原亡灵较为完整的生命传奇。这类时间建构模式往往使得新世纪的亡灵小说家在作品开头即交代亡灵个体或群体死亡的现实,进而通过幽魂的回忆性述说,逐一还原亡者的身世经历、死亡原因,以及死前遭受的迫害摧残与心灵困境等。这种“死后—死前”的时间建构在新世纪诸多的亡灵叙事类小说中均有所表现,且时常以重复交替的形式呈现,通过多个亡灵的轮番叙述打破阴阳两界的隔阂,还原出亡灵群体复杂隐晦的精神状态。
余华的《第七天》在小说的开头即叙述了亡灵主人公杨飞赶往殡仪馆接受火化的情节,进而以杨飞回忆性的叙述阐述了其死亡的原因、感情经历和身世背景。与杨飞同在死亡的彼岸世界相遇的李青、谭家鑫、刘梅及伍超等人,他们的生前境遇都在“死后—死前”的第一人称回溯模式中得以完成叙述。孙惠芬《后上塘书》中死后现实与死前回忆的文本内容,以不同字体不断交替呈现,小说在开头便阐述了刘立功妻子徐兰的意外被杀惨况,进而以亡灵主人公徐兰的第一人称叙述,回忆了她的身世情感以及丈夫刘立功的发家史。艾伟的《南方》在开端即交代了女主人公罗忆苦死亡的事实,进而以三种不同视角和三类不同叙述人称的搭配讲述了杜天宝(“他”)的故事,肖常春(“你”)的故事和罗忆苦(“我”)的故事,还原了罗忆苦和罗思甜、肖俊杰、杜天宝等人跨越几十年的爱恨纠葛。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在开头就以亡灵主人公的口吻,讲述了“我”(仇胜惠)死亡的事实以及化作鬼魂回归故乡梨花庄探望父亲的情形,进而以亡魂“我”的视角叙述了梨花庄三十多位男性抗战牺牲、女性沦为寡妇、“我”被丈夫残忍砸死的经过,揭露了不为人知的人性之恶与伦理纠葛。张翎的《劳燕》在小说的开头便通过三个男性亡灵的自述交代了牧师比利、军官牧恩以及四十一步村村民刘兆虎死亡的事实,进而通过三个男性亡灵“死后—死前”的回忆性叙述,以不同称谓逐一描绘了姚归燕的成长背景、爱情抉择以及经历的抗战磨砺,勾勒出这一抗日女性较为完整的生命轨迹。雪漠的《野狐岭》以沉埋沙土中的齐飞卿、陆富基、巴特尔、沙眉虎、木鱼妹等幽魂的回忆性述说为主线,在“死后—死前”的交替自叙中揭开了百年前蒙汉两支驼队意外失踪的诸多谜底。
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死后—死前”的时间建构正是在交代死亡事实的基础上,以亡灵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追忆叙述,去发掘死亡真相以及不为人知的潜在细节。祖国颂曾就第一人称的客观性问题进行讨论:“我们通常认为第一人称小说中因为叙述者‘我’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不可进入别人的意识而成为全知。其实不然,很多论者已清晰看到,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者也可具有全知式的特征。”[3]新世纪亡灵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非正常死亡,他们熟知过去种种现实情形,内心满怀着愤怒和怨气,死后不能入土为安,也得不到理想的超生,于是以鬼魂的身份飘荡在生前地区的上空或角落,观察着死后世间发生的一切,人间现实的一举一动都尽收亡灵眼里,人间过往的种种姿态也尽藏于其记忆中,亡灵主人公也自然成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亡灵叙事实际上可视为传统的上帝视角的转化,上帝视角中的叙述者是隐匿的,而亡灵叙事则直接将隐匿的上帝赋形为具体的亡灵,故而第一人称的亡灵追忆就具有了全知全能的叙述体验,也使得“死后—死前”的叙事建构实现了时空节点的适时对接。
2.“圆形嵌套”的空间结构
“圆形嵌套”空间结构是“出发—回归”的主体圆形结构和其他的叙事结构共同形成的内外嵌套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往往以人与亡灵的轮番叙事形成内外互补的空间架构,以跨越阴阳两界的叙事交替建构特有的文本张力。新世纪以前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在空间层面主要遵循着线状结构,即以倒叙的模式呈线状延展,逐步勾勒事件发展的完整面貌。这类线状结构有的以亡者的回忆性述说贯穿始终,如阎连科的《鸟孩诞生》叙述了乞丐鸟孩的亡灵以一只鸟的怪诞形式落在飞檐上,观摩自己的死去并回忆自己生前与凤子及傻男的悲惨过往。也有的是以人物与鬼魂的对话交谈形式还原事件的主体真相,如莫言的《战友重逢》(1992)写“我”在返乡过桥时突遇大水,忽闻昔日战友呼唤而攀援上树与之交谈,“我”在忆及往事过程中忽然领悟到之前见到的水中沉尸正是自己。新世纪以前的亡灵叙事类小说既没有形成回归循环式的圆形叙事主线,也未形成人物与亡灵群体之间的隔层独立叙事。新世纪的多篇亡灵叙事作品正是采用这种循环嵌套式的结构表现出丰富的文本魅力。莫言的《生死疲劳》采用佛教“六道轮回”的形式来开展文本的叙述。小说开篇西门闹的叙述和小说结尾蓝千岁的开讲都定格在了同一时间点——1950年1月1日。地主西门闹投胎转世的过程被反复述说,由此形成典型的循环往复的圆形结构。在这一圆形结构下,西门闹转世化身的驴、牛、猪、狗逐一阐述自己的经历传奇和命运轨迹,读者从这些动物的言说中可以联想到不同时间段的历史现实。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蓝解放、蓝千岁、作家莫言三位叙事者的价值判断和话语体系。三位叙事者的更迭叙述和话语交锋形成内部的叙事层,这一叙事层具备的内部力量助推外围的动物叙事完成顺接,形成重复式的圆形叙事模式。两类叙事层依托环形的错位互补,形成表里交织的文本叙事张力。“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格局也使得内外叙事层实现了无缝嵌套,从而以动物和人的双重视角还原了较为本真的细节面貌。
这种“圆形嵌套”的结构在梁鸿的《四象》中同样有明显的表现。梁鸿的《四象》讲述了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韩孝先返回家乡后在河坡边放羊,意外遇见三个墓地亡灵韩立挺、韩立阁和灵子,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跨越阴阳的对话的故事。整部作品采用四个性格、形象、思绪各不相同的叙事人,从四种不同的角度轮换阐述自己的复杂心绪和见闻履历。作家以亡灵、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同眼光观照现实世界,以春夏秋冬四时作为不同章节的题目,以韩孝先的行走轨迹和精神起伏勾勒出从河坡出发又重归河坡的圆形结构。作家既以韩孝先的自我述说建构起“乡村—城市—乡村”的圆形叙事主线,又以韩立挺、韩立阁和灵子三个亡灵的对话互补形成内部的深层叙事结构。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中的“圆形嵌套”结构无疑使得亡灵叙事的时隐时现和主人公叙述的文本贯穿在阴阳语境的跨越下实现了嵌套互补,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叙事空间,增强了叙述的厚重感。“亡灵叙事的最终旨归是介入生活与时代,接近生存本相,探寻生命意义,挖掘人性本真,抵达生存困境,逼近人类的终极存在。”[4]两类叙事层的空间分割与对接穿越了时空与心空,以哲理的思索抵达了生命的本真。
二、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情节模式建构
1.“重返—离开”的情节模式
新世纪之前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往往以“突转”的情节模式引人入胜。如余华的《古典爱情》(1988)在小说的开头以温和浪漫的语调叙述了进京赶考的书生柳生邂逅小姐惠的感人情节,之后却笔锋突转,讲述了小姐惠沦为亡灵且一条腿被砍下待售的惨象,被埋葬后的小姐惠奇迹般长出新肉又难以复活的离奇情节更是营造出“暴力美学”式的血腥、冷酷的气息;阎连科的《横活》先是以死去的鲁耀的口吻阐述其在阴间的见闻感受,进而情节陡转,以亡灵的身份追忆其在开封“横活”的一生;莫言的《奇遇》和《战友重逢》亦是以转折式的情节表明叙事主人公死亡的现实。这种“突转”式的情节模式在早期的亡灵叙事类小说中屡见不鲜,以小说情节的突变与扣人心弦传达出前后迥异的情感氛围和艺术情调。
而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小说普遍存在“返乡—离开”的叙事模式,即亡灵的“故地重游”。作家往往安排人死后的灵魂回到生前的居住地观察、自语或对话,以现实与回忆的交叉叙事讲述生前身后的故事。作家安排这些亡者的幽魂回归故乡,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亡者生前遭受了意外、暴力等残酷迫害,心愿未了且对人间尚存眷恋,于是以返乡的形式寻求灵魂的合理归宿;另一方面,叙事亡灵是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亡灵叙事的背后是作家的意志和意愿的表达,作家偏向和善于书写自我熟悉的生活,返乡的轨迹更贴合作家的叙事思维和逻辑。
《南方》中的女子罗忆苦被害后化为亡灵,返回永城的上空俯视着故乡的一切;《后上塘书》中的徐兰被误杀后化作亡灵,回到故乡上塘村察看;《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的仇胜惠被砸死后化作亡灵,回归故乡梨花庄去寻找未曾获得的人间亲情;《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以亡灵投胎的形式回到自己的故乡西门屯经历着六道轮回……正如昆德拉所说:“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5]没有世俗纷扰的亡灵四处飘荡,由于心中的怨气而难以入土安息,又由于突发性的死亡而来不及与熟人告别。他们企图在死后回到生前地获得灵魂的解脱,也怀揣着好奇的心理、对亲人的挂念渴望了解死后故乡发生的诸端。然而返乡后的现实却是事与愿违,他们回乡后感受到的多是人性的冷漠、丑恶和世间的苦难。如《还魂记》中的乔燃灯回乡后听到的是村长老秦等人的阴谋奸计,看到的是少年五扣的纵火伤人;《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的仇胜惠返乡后感受到的是父亲的冷漠和久妮婶等人的仇视;《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投胎转世回乡后,经受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苦难和摧残……故乡的冰冷现实和残酷窘境使得亡者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奈与惆怅,魂牵梦绕的故地终究无法抚慰和安放他们饱经沧桑的灵魂。于是在经历短暂的“重游”与述说后,他们终究会怀着潜在的遗憾和自我的慰藉回归远离世俗人伦的彼岸世界。这种“回归故乡”到“离开故地”的叙事过程体现出的正是死亡的另一种延续。
2.“悬疑—侦破”的情节模式
死亡“既是一个人不能不猜的谜,……又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一个永远摆在你的面前、至死都困扰着你的头脑的谜,一个只要你活着,你就得不停地把它猜下去的谜”[6]。死亡本身的神秘感足以激起人们探寻死亡的欲望。基于人们对死亡真相的好奇,新世纪的小说家们特意采用倒叙的手法来营造死亡的神秘氛围,将读者带入死亡情节的轨迹探寻中,与作家一起层层揭开死亡的真相与潜藏的秘密。
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小说类似传统的“悬疑—侦探”类小说,在小说的开头设置命案和死亡的悬念,引发读者的注意力和探索的欲望。之后叙述亡者的生前经历和人世纠葛,或隐或现地点明死亡的线索,最终在层层揭秘中侦破案件。这种过程使得作品呈现出“悬疑—侦破”的叙事模式。孙惠芬的《后上塘书》以徐兰的意外被杀作为小说的开端,用寄给刘杰夫的三封书信步步设疑,以线索的汇聚层层解疑,最后还原出难以置信的死亡真相。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在“引言”部分便提及了“我”(仇胜惠)死亡的事实和化为亡灵的回归,以设问的形式吸引读者去探寻亡灵主人公被害的来龙去脉。之后便以亡灵“我”的视角讲述自己的身世经历和梨花庄女性在战争背景下经受的伦理压迫,引出父亲安排的不合理婚姻和自己被丈夫残忍砸死的经过,死亡真相也在亡者平静忧郁的叙述中水落石出。新世纪的亡灵小说正是采用悬念设置的方式来吸引读者进入文本,进而在现实与回忆的叙述更迭中揭露凶案的细节线索,并直达死亡的真相。采用悬疑模式的亡灵叙事类小说与真正意义上的犯罪悬疑小说有一定的差别。“鬼魂叙事小说和悬疑小说虽然都与犯罪有关,但是后者更注重对犯罪过程进行严密科学的逻辑推理与演绎”,前者“更注重对除犯罪凶案以外的人物、事件的描绘和思考”。[7]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悬疑—侦破”模式以类似事件回放的形式打开了死亡叙述的另一扇窗口,再现了死亡现实的荒诞隐喻,在死亡真相的揭秘中投注了人性伦理的深度反思。
三、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的“多声部”叙事模式
在文本叙事模式的建构上,新世纪以前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往往全篇都是选取单一亡者的叙事,以单一幽魂的窥视还原死后人间的现实,并通过单一亡者的追忆式述说揭露人性的复杂与阴暗。阎连科的《寻找土地》(1992)以修理房屋而不幸亡故的“我”(马佚祥)的视角,叙述了刘街的唯一亲人舅舅不愿收留“我”的骨灰盒而马家峪人收留了“我”并为“我”配骨亲(冥婚)的故事,揭露了商业利益对人性的扭曲和冲击;苏童的《菩萨蛮》(1997)通过华金斗的幽灵叙述还原其妹妹在人间照顾五个孩子的艰难境遇;阎连科的《自由落体祭》(1993)以从房顶跌落致死的亡灵春生的视野来追忆一生,在跨越阴阳两界的隔阂中透视人性的冷漠、麻木和丑恶……此阶段涌现的这些亡灵叙事类小说均是以单个幽灵的全知式叙述探索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追溯亡者心灵的悸动纠葛,并以灵魂的透视描摹了在欲望和利益的诱惑下人性所经受的层层拷问。
在文本叙事模式的建构上,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小说摆脱了早期单一亡者的叙述设置,创造性地采用了多重视角,巧妙形成叙事的“多声部”。不同亡灵视角下的故事面貌也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以身份细节的互补揭露出较为完整的现实和更为隐秘的人性。多重视角有节奏地适时转换,文本声音内部的复合与交响牵引复杂的历史真相,文本空间被视角分层,各层彼此独立又相互对话。诸如《第七天》《野狐岭》《劳燕》等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都呈现出文本叙事模式的“多声部”特征。雪漠的《野狐岭》便是一部多重亡灵叙事视角交织的“探秘”类小说。作品以无数嘈杂的亡灵声音建构小说内容的主体,还原了百年前不为人知的西部传奇。在探险主人公“我”用古老的招魂方式打通阴阳两界后,沉埋地下的幽魂们逐一亮相讲述剧情。整部作品的多重声音在交织、碰撞、对话,每个幽灵都在讲述着自我视角下的隐秘细节和幽微真相。讲述的幽灵有自始至终不现身的杀手,有因革命暴动被杀的凉州英豪齐飞卿,有受到“倒点天灯”酷刑的陆富基,有身怀深仇大恨从岭南追杀到凉州的女子木鱼妹,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沙眉虎……诸多亡灵的讲述创造出纷繁复杂的视听盛宴。由于不同幽魂的生前经历和聚焦的事实不同,他们对同一事往往有着迥异的看法,野狐岭的故事在诸多幽灵的叙述中显得越发玄妙莫测、耐人寻味。
除此以外,余华的《第七天》和张翎的《劳燕》也同样呈现出亡灵视角的变换与多重声音的交集。《第七天》除亡灵主人公杨飞在叙述自己的死亡经过和身世传奇外,还穿插了割腕自杀的杨飞前妻李青、爆炸致死的饭馆老板谭家鑫、自杀坠楼的打工妹刘梅、被强拆压死的郑小敏父母等亡灵的叙述。这些亡者同在死无葬身的彼岸世界相遇,他们交错登场轮番叙述自己的身世遭遇,叙事视角的多重性在文本中实现了人物事迹和故事情节的衔接和替补,进而还原了事件的全貌和更为本真的细节。《劳燕》则以“亡灵隔空对话”的方式来回顾过往,通过三个男性亡灵的不同视角叙述了一位在抗日战争中受侵害的中国女性姚归燕的生命传奇。三个亡灵的叙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超越时空,实现了跨越大洋国籍的隔空交流。三个亡者的追忆在文本中轮番交错进行,且通过彼此的错位对话形成适时的互补。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和称谓还原了姚归燕各个阶段的生命轨迹。姚归燕在三个男性亡灵眼中的不同名称影射了她人生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境况,她的成长成熟正是在三个男性幽灵的回溯叙事中逐渐得以完成。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小说以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与束缚,以声音交叠互补的方式重塑历史事件、时代变革和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各类物象的轮番登场与叙述差异营造了故事多声交织、多音齐鸣的“复调”效果。多个亡灵的发声和多方位视角的窥测使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中的“看”“听”“说”异彩纷呈又相互融合,从而展现出人物事件的完整脉络和全方位的透视。
四、结 语
亡灵叙事以亡灵观照世俗人间,总是给人以一种忧郁的美感、对凡俗生活地域化的沧桑感,包括站在生命的终极形态上,超然性地看待人间现实的宿命感。鬼魂视角“不仅可以用过去完成时态回忆人间的生活,还可以用现在进行时态描写阴间的景象”[8]。新世纪小说的亡灵叙事在新时期亡灵叙事小说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文本叙事的空间,将传统性和现代性进一步融合,摆脱了政治叙事和精英叙事的模式束缚,在文本构造的策略上体现出创造性的突破和多样化的设计。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有以时间维度分层建构的“死后—死前”结构,也有以空间分层架构形成的“圆形嵌套”的错位互补的结构。在文本情节的建构上,新世纪亡灵叙事类小说以“重返—离开”和“悬疑—侦破”的诸多模式消解了鬼魂的恐怖性,以亡者的游归与诉说层层揭开死亡的真相,表达亡灵对人间现实的诸多眷恋,以不同的叙事轨迹表现出死亡意识的多重旨归。在文本叙事视角的建构上,小说叙事的“多声部”营造了叙述声音的多维碰撞、交集和错位添补,以声音的适时调换实现了文本层次的另类划分和情节内容的无缝衔接。可以说,作家不仅借助亡灵的口吻更为真实地还原了人间苦难和人性罪恶,也将自我内心的无奈和痛楚进行了合理的宣泄,彰显出特有的神秘感、荒诞感与新奇感。新世纪的亡灵叙事类小说在文本建构方式和策略等层面的创造性革新和突破,对于当代小说叙事模式的探索和美学开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