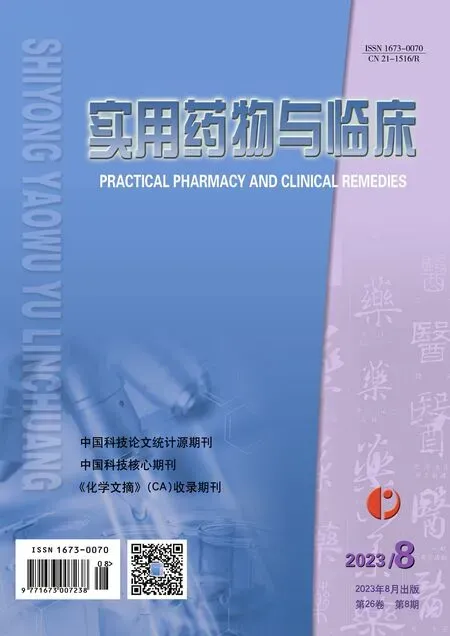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对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疗效评价及不良反应的研究
何润田,冯 洁,丁天娇
0 引言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是糖尿病患者严重的眼部并发症,有1%的失明是由于DR所致,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是伴随DR发展出现的并发症,26%的DR患者出现DME,病程超过20年的糖尿病患者中有29%合并DME[1]。当DR进展到增殖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PDR)时,视网膜出现新生血管。新生血管的形成是PDR的病理基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新生血管生成的关键驱动力[2]。DR患者视网膜长期缺氧,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进一步损坏血-视网膜屏障,VEGF进入眼内各部分,诱发虹膜新生血管的形成,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3]。
有研究表明,DR患者眼内的VEGF浓度亦与DME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4],抗VEGF药物可以降低DR患者眼内高浓度的VEGF,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显著改善DME[5]。因此,除非患者有禁忌证,抗VEGF应当是所有DME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6]。基于抗VEGF药物的广泛使用,本文回顾并评价近年来抗VEGF药物治疗DR的不良反应及疗效。
1 VEGF与DR的关系
VEGF是一种在多个器官中表达的大小为45 kDa的二聚体糖蛋白[7],其家族包括VEGF-A、VEGF-B、VEGF-C和VEGF-D 和胎盘生长因子(PIGF)[8]。VEGF-A主要与血管系统有关,在内皮细胞分化、增殖和存活中起重要作用,并且促进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和增加血管通透性[9-10]。VEGF-A可以与表达于内皮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而发挥生物学作用[11]。VEGF在眼部主要分布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层、内核层、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等[12]。
VEGF对视网膜血管的形成起关键作用,而VEGF受缺氧状态的调节,视网膜缺氧时,在常氧状态下正常降解的缺氧诱导因子-1 (HIF-1)降解受到抑制,促进VEGF转录增加[13]。增加的VEGF诱导了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不正常的新生血管可以进入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进一步诱发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等。VEGF具有血管高通透性,可引发黄斑水肿,降低视力。
2 抗VEGF药物在DR中的应用
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抗VEGF药物有培加他尼钠、雷珠单抗、贝伐单抗、阿柏西普和康柏西普。前3种药物可与VEGF-A结合且时间较短,阿柏西普可与VEGF-A、VEGF-B等更多的VEGF家族成员结合[2],对VEGF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康柏西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VEGF药物,是从中国仓鼠卵巢细胞中克隆得到的143 kDa重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融合蛋白。康柏西普对VEGF的亲和力是贝伐单抗的50倍,其阻断VEGF-A、VEGF-B、VEGF-C及PIGF。研究表明,康柏西普和阿柏西普是治疗DME有效且安全的药物[14-15]。
抗VEGF药物注射有不同的治疗方案,目前大体分为固定方案(fixed)、按需治疗(PRN)和治疗并延长(T&E)方案。相比于按需治疗以及T&E方案,固定方案治疗对某些患者来说,从经济和时间成本上可能难以坚持。汪彬等[16]发现,康柏西普1+PRN(第1个月1针,而后再按需给药)和3+PRN(每月1针,连续3个月,而后再按需给药)的疗法均能对糖尿病黄斑水肿患者起到改善效果,两组患者视力无明显差异,但1+PRN疗法注射药物次数较少,经济压力小。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康柏西普3+PRN与5+PRN(每月1针,连续5个月,而后再按需给药)方案治疗DME效果相近,但5+PRN治疗次数增加,且疗效较难持久,但两种方案安全性无差异[17]。张祺等[18]发现,使用雷珠单抗3+PRN以及康柏西普T&E治疗DME,1年后,两种方案治疗DME所获得的疗效相同,但T&E方案的经济成本低。以3+PRN为基础进行治疗并持续观察病情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方案,但PRN或T&E具体方案的选择还需要深入研究来探索。
3 抗VEGF药物的不良反应
3.1 抗VEGF药物的肾脏毒性 长病程的糖尿病患者易并发糖尿病肾病。抗VEGF药物会影响DR患者的肾脏状态,导致新发肾损害或原有肾病进展[19]。Yang等[20]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会增加透析的风险,与未经抗VEGF治疗的患者相比,这一风险高达85%。抗VEGF药物多次给药后肾功能呈现恶化进展趋势,肾损伤风险增加[19],抗VEGF药物具有潜在的肾脏毒性[21],高透析风险可能与此有关。
抗VEGF药物肾脏毒性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VEGF-A在糖尿病肾病发生中发挥一定作用,在肾脏中VEGF-A由肾小球足细胞产生[8],早期在糖尿病大鼠肾脏病变的模型中发现VEGF-A的表达增加[22]。然而,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肾活检显示VEGF-A表达减少[23],VEGF-A基因表达下调[24],推测肾脏VEGF-A下降可能会损伤肾小管上皮细胞和肾脏血管,造成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而过多的VEGF-A同样会损伤肾脏,因此,在糖尿病状态下,肾小球中过多或过少的VEGF-A都是有害的[8]。DR患者视网膜的VEGF-A水平升高,与DR肾脏低VEGF-A相反,可能是因为VEGF在视网膜和肾脏中发挥的生理作用不同。此外,大鼠和人类在糖尿病肾脏病变中的VEGF-A水平相反的原因尚不明确,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对DR患者的抗VEGF药物注射中,要密切关注患者的肾功能、尿蛋白及肌酐情况,尤其是短时间内多次注射药物的患者。
3.2 抗VEGF药物对血压的影响 研究表明,抗VEGF药物注射会改变患者血压状态,VEGF可以通过一氧化氮释放来产生血管松弛作用[10],推测抗VEGF药物通过降低体内VEGF水平来影响血管收缩状态,进而影响血压。
Balci等[25]回顾性分析了550例注射抗VEGF药物的患者,不论患者之前有无高血压,在注射药物之后,血压在短时间内(注射时、注射后30 min、注射后60 min)均会升高,且舒张压升高持续时间长于收缩压,但舒张压变化程度较为显著的原因不明确,可能与患者本身血管状态有关。Rasier等[26]发现,注射抗VEGF药物后,有高血压组(A组)血压升高程度高于无高血压组(B组),且A组血压开始升高的时间早于B组,表明抗VEGF药物对已有高血压疾病的患者血压波动影响较大。然而,Glassman等[27]在对660例注射雷珠单抗、阿柏西普、贝伐珠单抗的DME患者进行2年的随访后发现,血压水平无显著变化,这可能与大部分研究人群在研究开始时服用抗血压药物有关。当前关于血压与抗VEGF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注射抗VEGF药物后血压开始升高的幅度与时间差异较大,认为VEGF对血压的影响除了客观的生理机制外,紧张、焦虑等情绪主观因素也发挥着作用。
抗VEGF注射的患者治疗期间要注意血压变化,术前有高血压的患者要谨慎评估血压波动带来的风险;而关注无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化可能更重要,因为该类患者平时没有监测血压的习惯。
3.3 抗VEGF药物对视网膜的影响 部分PDR患者在玻璃体内行抗VEGF治疗后,会逐渐进展为牵拉性视网膜脱离,有学者称之为“抗VEGF紧缩”,通常表现为在玻璃体内注射抗VEGF后1~6周,患眼突然视力丧失[28]。然而,有报道,3例PDR患者在行抗VEGF治疗后,原本的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减轻,发生了视网膜复位[29],这与大多数“抗VEGF紧缩”不同,可能是抗VEGF之后的纤维膜收缩,以某种形式缓解了原本的视网膜牵拉状态。
在治疗严重PDR和既往存在严重纤维增殖膜的患者时,应谨慎使用抗VEGF药物,并且密切观察抗VEGF后眼内情况,注射抗VEGF药物距行玻璃体平坦部切除术(PPV)的间隔不能太久。对于之前轻微牵拉性视网膜脱离采用抗VEGF治疗后,出现纤维膜紧缩的患者,PPV应在1周内进行[28]。
4 抗VEGF药物治疗DR的疗效评价
4.1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影像学 DR患者视网膜的情况可以在OCT影像学检查上得到良好的展示。
4.1.1 视网膜高反射灶 视网膜高反射灶指其高反射率等于或高于色素上皮层的离散点以及边界清楚的、排除通过眼底照相与典型硬性渗出物在空间上匹配且大于50 μm的高反射团块[30],高反射灶具有和典型硬性渗出相同的高反射率[31]。DME患者高反射灶可分布在视网膜内层和外层,经抗 VEGF 治疗后,内层视网膜及外层视网膜中高反射灶的数量均明显减少,外层高反射灶的数量和视力预后呈明显负相关,而内层高反射灶和视力预后没有相关性[32],所以对抗VEGF治疗后的DME患者,可以通过OCT检查观察高反射灶来判断预后。但不同种类DME和视网膜高反射灶呈现何种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1.2 视网膜积液 视网膜积液在DR患者中较为常见,通常在OCT上可以观察到不同位置的低反射积液区。Santos等[33]通过量化OCT中低反射区域分析视网膜积液,发现抗VEGF治疗后,视力预后可能与视网膜外层,特别是外丛状层和光感受器外节附近异常视网膜积液的减少程度相关。推测视网膜外层附近积液影响较大,这一表现可能与光感受器有关,光感受器附近的积液会对视觉的电生理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损害视力。
4.1.3 视网膜内层紊乱 视网膜内层紊乱(Disorganization of the retinal inner layers,DRIL)定义为OCT显示神经节细胞内丛状层复合体、内核层和外丛状层之间没有可识别的边界,与其他视网膜病理改变无关。在Sun等[34]的研究中,4个月内DRIL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对应着8个月时的视力下降或提高,在4个月内,DRIL范围每增加299 μm,可预测8个月后的视力将比基线时下降1行。DRIL可以作为预测视力预后的指标,而且DRIL无需根据视网膜是否存在其他病理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分级标准。
4.1.4 外界膜与椭圆体带 研究表明,外界膜(ELM)和椭圆体带(EZ)的完整与视力密切相关[35],DME与ELM和EZ损害有关,从而导致视力下降[36]。外界膜在OCT上表现为一条高反射的膜样线条,但ELM不是真正的膜,而是由Müller细胞和光感受器之间的黏附连接组成的网络。ELM的广泛破坏表明Müller细胞和光感受器受到广泛损伤。ELM的破坏与DME患者较差的视力有关,广泛的ELM破坏是耐抗VEGF药物治疗的一个较强的预测指标[37]。EZ是指在OCT上可观察到的ELM后的一条高反射带,曾经被称为IS/OS带,代表光感受器的完整性,其高反射率是由于光感受器细胞内节的线粒体密度高;EZ与DR的严重程度和视力下降显著相关[35,38-40]。De等[41]观察显示,抗VEGF治疗后,DME患者的ELM和EZ会恢复,ELM先恢复,EZ后恢复。ELM与EZ可以作为评估患者视力的指标。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血清尿素和肌酐水平与DR的严重程度以及ELM和EZ破坏程度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血清尿素和肌酐可作为ELM和EZ破坏程度的替代标志物[38]。Chatziralli等[42]对36例行抗VEGF初始治疗的DME患者进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OCT、FFA等检查后发现,对于初期的DME患者,完整EZ、ELM、无视网膜前膜(ERM)和中央视网膜厚度(CST)<405 μm可预测DME治疗会产生良好的治疗反应。因此,EZ、ELM、ERM、视网膜高反射灶、视网膜内积液以及CST厚度都可以作为抗VEGF治疗情况的影像学检查中重点关注的部位,但在OCT中哪个是最佳视力预后评估标准,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血清生物学标志物 除了影像学检查,血清生物学标志物也可作为评估疗效的标准之一。
4.2.1 缺血修饰蛋白(IMA) 氧化应激为高活性分子自由基的产生与人体抗氧化剂中和消除有害影响之间的平衡失调,会导致细胞内稳态的破坏和其他活性分子的产生,从而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在DR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3]。人体白蛋白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IMA是一种氧化修饰形式的白蛋白,用来测量糖尿病氧化应激状态的升高。有研究显示,DR患者中的IMA水平明显高于糖尿病患者以及健康人群,较高的IMA水平反映了DR中氧化应激状态的增加[44-45]。Kumar等[46]病例对照试验显示,抗VEGF治疗1个月后,DR患者血清IMA水平显著下降,视力明显提高,而未经抗VEGF治疗的DR患者血清IMA水平显著上升。Soiberman等[47]的研究也有相类似发现。因此,IMA水平可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用于评估DR病情严重性以及抗VEGF治疗的效果与预后。
4.2.2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在糖尿病患者中表达和信号转导增加,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48]。杨洁等[49]在研究VEGF-A与TGF-β在接受雷珠单抗治疗后的DR患者血清中的变化时发现,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后,VEGF-A在非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NPDR)与PDR患者体内的水平均会下降,且二者之间无明显差异;治疗后,NPDR患者体内TGF-β水平显著下降,而PDR患者并无此变化,这可能说明DR越严重,TGF-β水平越难以下降。因此,血清TGF-β水平可能用来评价抗VEGF药物治疗DR的疗效。
血清生物标志物可以和OCT中的影像标志物共同评估DR的严重度和抗VEGF治疗后的疗效,但是以上各种标志物的评估能力强弱还未有定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5 总结
抗VEGF药物在治疗和缓解DR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OCT等技术可以较好地辅助判断DR预后,但较高的经济成本以及一些潜在的全身和眼内副作用制约了抗VEGF药物的应用,在未来应注重探索不良反应更少的抗VEGF药物以及更高效的评价抗VEGF药物治疗DR预后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