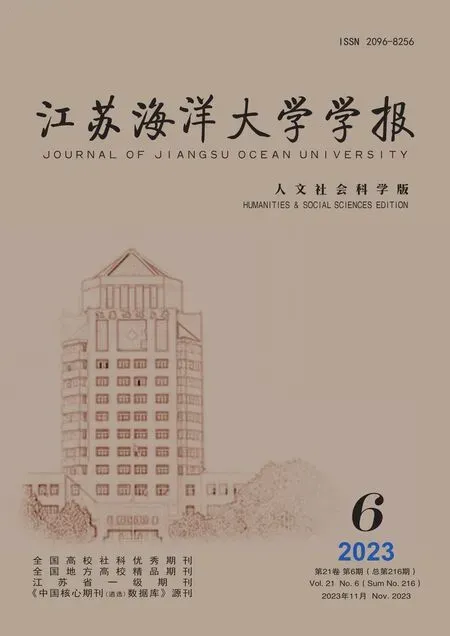《无可慰藉》的后人文主义释读*
胡作友,蹇雯雯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他是当代风靡文坛的小说家,其小说《无可慰藉》一经出版就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目前国内研究大多聚焦石黑一雄小说的叙事风格、创伤主题与人文情怀,如孙玉晴[1]、任冰[2]、魏文[3]等。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叙事、美学分析和社会文化与民主层面的思想,如Mead[4]、Castellano[5]、Ryle[6]等。上述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然而从后人文主义视角进行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而作者对主人公瑞德“救世主”地位的刻画、对城市精神危机的强调、对瑞德一个又一个任务失败的描写,无不体现出后人文主义的色彩和韵味。因此,本文拟从后人文主义对《无可慰藉》进行解读。
一、后人文主义:“牢笼”的破除
“人类主体”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萌芽,当时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明确了人在整个世界中的主导地位。伴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人们重视自身地位,维护人类自身的尊严,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然而,随着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人类的很多功能变得远远落后于人工智能。同时,生态危机的显现也在提醒人类应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平等,而不应凌驾于“他者”之上。在不确定性的技术时代,人类的主导权正逐步丧失,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各种问题的涌现,使得后人文主义时代的到来成为必然。
19世纪末俄国神秘学家布拉瓦茨基在其人类演化理论中最早提出“后人类”一词;1976年,哈桑提到“后人文主义”虽看上去是一个新词,但却暗示着500年的人文主义已经蜕变为另外一种东西,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后人文主义”[7]。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应处于世界中心,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世界[8]。后人文主义解构了传统人文主义赋予人的优先权、中心性、绝对性、超越性、自主性等一系列特权,宣告了传统人文主义神化的人已经死亡[9]195。世界不断变化,而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人应随之变化。在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人的思想亟待解放的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在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反对神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时,“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事物,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但是,人类只能相对认识事物,却不能绝对地把握事物,因为一切都不是给定的、已知的[9]198。万物的发展变化会导致人的变化,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被世界改造着,“人”的定义不是永恒的、僵化的。蓝江认为,人文主义者们所定义的“人”的概念是替换了上帝、自然、王权等牢狱的新的牢狱[10]。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控制下,人的本性就像是提前被规定好了似的,所有人都在特定轨道上前行,在特定规范下生活。然而,社会不断发展,人对自身的认知和定位也应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后人文主义聚焦于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人文主义理想的批判[11]。人文主义二元论的根源在于其对人类本质的追求与定义[12]。为了强调人的价值,反对宗教神学,人文主义者们过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在整个世界中的作用。人文主义理想已然成为新的“教条”和规范,一部分人习惯于高高在上,自愿将自己囚禁于这座“牢狱”中,不愿面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当人们自以为居于世界的中心时,忽视了“他者”,其结果便是世界的不平衡。张剑认为,现当代他者话语是“主体退隐与他者凸显”[13],这是对自我中心地位的抨击,也是对陷入二元论中的人文主义的一种纠正。
“人类不应该成为衡量其他所有生物的标准”[14],人类也不应该成为衡量整个世界的标准。世界不是处于绝对的二元对立状态。王宁指出,早在后人文主义文学批评之前,生态和环境文学批评就已经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使人类从高雅的神殿返回到自然万物中;酷儿理论模糊了性别差异,消解了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15]。人不应该固步自封,而应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应如何做出相应的改变,人文主义那种把人类视为主体,把人类之外的其他一切视为他者的行为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了。“如何包容差异,建构起真正平等正义且具有伙伴式亲密关系的多元生命‘共同体’,应该是人文主义拓展的新方向。”[16]时代对人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平等地看待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关系,适应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主动付出行动,构建和谐的后人类社会。这正是《无可慰藉》中瑞德的失败遭遇所带给现代人的反思,也是这部作品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所体现出的成功之处。在《无可慰藉》中,主人公瑞德不能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进行清晰的认知,导致不管在完成大任务还是小任务时都事与愿违,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瑞德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将自己困于人文主义的“牢笼”中,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能对安排给自己的各类任务进行适当的取舍。
二、自我与他者:身份的枷锁
《无可慰藉》的中心人物是著名钢琴家瑞德,他被托付通过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来化解一座不知名城市危机的任务。瑞德声名远扬,事业有成,城中的人们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瑞德对自己也满怀信心,相信自己的到来一定会成为城市的转折点,为城市带来光明的未来。正因如此,当其音乐天赋被用来满足市民们无穷无尽的需求时[5],他也完全接受并且尽力而为,因为不管在瑞德自己还是市民的心目中,瑞德都是万众瞩目的“救世主”。
瑞德被赋予这一身份的真谛符合西方哲学二元论中“自我”与“他者”的含义。Ryan认为,他者性是“自我相对于他者”的概念,它涉及到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且通常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17]。在这一关系中,他者被边缘化,而“自我”占据主导地位。对应地,瑞德在小说中扮演“自我”的角色,而市民们安排给瑞德的众多小任务则扮演“他者”的角色。瑞德被相信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并且全盘接受这些任务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自我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也是人与非人不平等关系的体现。若说瑞德的优点是热情、能力强,并且完全相信梦想通过努力可以实现,那么这一角色与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设定完全符合;而瑞德最终的失败也证明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弊端。
巴利·路易斯曾说过,“瑞德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不会说不”[18]116。在城中的四天三夜里,瑞德虽背负重重压力,但他对市民们请求自己解决的“小问题”全盘接受,这说明他对自身能力总体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整个行程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结果发生在瑞德这样一位“天才”身上好像是荒谬的,但其实是合理的。Castellano指出,瑞德是一个创造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不创造任何东西的创造者[5]。瑞德虽然才华横溢,能力高超,但他无法在短短的四天三夜完成所有的任务,满足城中所有人对他的期望。在刚到小城的第一天,瑞德就被斯达特曼小姐安排与市民互助组会面;被古斯塔夫央求去老城区与索菲谈话;被霍夫曼经理要求看一看其妻子的剪报册……在之后的几天也是如此,即使在周四之夜已经到来时,瑞德也未被允许全身心准备自己的表演。虽已身心俱疲,但他还是答应了所有人的请求,因为这可以证明自己过人的能力,保住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全能形象;瑞德表示他这一次的旅行非常重要,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19]245。这一举动和意图与身处后人文主义时代却不愿承认自身弊端、在改变与守旧之间痛苦挣扎的人如出一辙。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并没有人文主义者所定义的那么全能。瑞德把自己困在了人文主义者创造的“人”的“牢狱”中,安于他人加之于自己的荣誉,安于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和对他人“固有”的责任,不愿走出这座“牢狱”去面对外面的世界。瑞德要完成所有的任务,意味着他要扮演他在这座城市中被安排的所有角色,包括父亲、丈夫、“救世主”等。很明显,事与愿违的是,瑞德未能成功兼顾所有身份。瑞德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小说对瑞德的这种傲慢态度提出了批评[20]。
瑞德把自己困在了“虚构的人文主义的长城里”,而这座长城“可能只是一道幻影般的空壳”[10]。瑞德就像是小城中唯一一个完美符合人文主义对“人”的定义的人,而小城中的其他人,也可被称作“他者”。这些人在小说中被处理为“庸俗”、低级的边缘性角色,他们面对危机无能为力,一切都要依靠瑞德一人拯救。但是,几百年前人文主义对“人”的定义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社会的需求,人类已经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代。人们不应该主动退出,将整座城市、各自家庭、个人感情的希望都寄托在瑞德一人身上,瑞德的能力趋近于完美,但他远远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不可能在短短的四天三夜圆满完成无数个小任务后,还有足够的精力圆满完成最后一个大任务。“追问普通人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是石黑一雄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21]瑞德尽管音乐能力出众,但他只不过是小城中一个普通市民而已,他最大的失败在于他自己和其他市民们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有义务做好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市民们也有义务处理好各自的危机,而不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瑞德一人身上。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危机正是由市民们各自的家庭危机构成的。在城市危机的解决问题上,瑞德与其他市民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并不高人一等,他不应该大包大揽市民们的小问题,市民们也不能将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瑞德一人身上。换句话说,瑞德和市民们都将自身和彼此囚禁在了人文主义的“牢狱”中。在后人文主义的时代,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人也不再处于绝对的优势和征服地位;相反,正是故事中的非人——形形色色的小任务,给自以为是的瑞德和过于相信瑞德能力的市民们上了一课。
三、愿望与现实:梦想的粉碎
人文主义者认为,世界总体上正朝着文明和进步的方向不断发展[22]。瑞德对自身能力与城市危机解决的总体态度与人文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态度是一样的。瑞德在小城中可以逗留的时间不多,行程异常紧迫。每一次被市民们要求帮忙,瑞德虽然全盘接受,但却很不情愿,这是因为他明白周四之夜的钢琴演奏才是他最重要的使命。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意识,他还是将所有的任务都大包大揽,不管是“帮市民们处理各种各样的家庭危机”这样的小任务还是“在周四之夜进行钢琴演奏以化解城市危机”这样的大任务。魏文认为,瑞德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无条件承担对他者的责任[3]。瑞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凭借自己出众的能力,能够在准备周四之夜之余完成“微不足道”的小任务,而这些小任务的圆满完成又有助于完成周四之夜的大任务。所以,在人与非人的这一关系中,作为非人的大任务并没有让瑞德退缩半分;相反,瑞德恰恰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从而便可彰显自己超众的能力,又能够解决城市危机,毕竟瑞德是公认的“国际最顶尖的钢琴家,而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19]12。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在周四之夜,在即将登台演奏之时,所有家庭的关系彻底破裂,瑞德未能登台进行钢琴演奏,城市危机未能得到解决,而瑞德在市民们心中“超人”“救世主”的形象也彻底崩塌。这说明人文主义所规定的完美、乐观、作为万物尺度的“人”从来都是不存在的,这种定义只是把人类囚禁起来的枷锁和监狱。“人类”的概念是如此的容易变动和表面上的不可解构,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22]。尤其是进入近现代以来,科技的进步与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传统的人类在生活与生产等许多方面远远不及计算机所发挥出的作用,而此时关于“人”的定义已然悄悄发生了变化,只是囚禁于人文主义“牢狱”中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的优越性而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或者,他们早就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却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
几千年来,人类高高在上,地位优越,俯视着万物,自然不能接受“当今的人类已经不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类”的事实而导致了或大或小的失败。故事中的主人公瑞德在面对市民们委托给自己的小任务时,觉得会占用自己宝贵的时间而不愿意接受,这其实折射了在现代社会人的形象已经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的社会现实;而面对“通过‘周四之夜’化解城市危机”这一大任务时的信心以及强调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可以证明身处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在面对自身能力的相对下降时却依然努力在“非人”面前保持完美形象与征服“非人”的挣扎与倔强。在瑞德与“周四之夜”这一人与非人的关系中,瑞德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只要演奏一首钢琴曲便可化解城市危机,圆满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瑞德之所以如此自信,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无法走出传统的人文主义对自身完美人格的设定,总想着自己完全有能力可以征服一切非人的事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瑞德没有认清这次城市危机的本质,导致在解决问题之时本末倒置。瑞德所在城市的危机是精神危机、情感危机和家庭危机,这并不能够指望通过一场音乐会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是随着世界现代化的普及、科技的突飞猛进、生活节奏的加快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有效沟通的缺失。在这座城市中,音乐并没有扮演它真实的角色[5],音乐只是这座城市中“无可慰藉”的人们寻找的一种慰藉方式而已。要想真正解决这座城市的危机,瑞德应将精力放在引导人们解决家庭问题和情感危机上;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瑞德是否能够处理好自己的家庭矛盾。但是,瑞德的做法偏偏是本末倒置的。他完全没有把处理家庭矛盾这件事放在心上,即便周四之夜计划几乎就要宣告失败了,他还对自己的能力持有盲目的乐观态度,他要坚持保留他“天才”的形象[5]。这样的选择和态度必然导致他一直充满信心的“化解城市危机”的理想陷入绝境。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天才,是这座城市的中心人物,是完全能够通过音乐会化解城市危机的“救世主”。但是,后人文主义观察到,世界上从来没有统一的“人”[8]。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由具体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人的本质不可能是规定好的、规范性的,人也是不可能甘愿被困在这样的“规范”中循规蹈矩地活着的。这种关于人的本质、地位与作用的“规范”就如代码一般单调,必然使人的一生空洞而无聊。可以说,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定义恰恰限制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人文主义对人的能力的强调背道而驰。事实是,世界已经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代,但是,瑞德没有顺应时代潮流,依然把自己囚禁在人文主义的“牢狱”里,最终一事无成。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设定了一个机器人的角色。对此,尚必武认为,这是为了提醒人们,在人工智能遍布的后人类时代,机器并不一定能够替代人类[23]。类似地,盲目自信、终日忙碌的瑞德就像一个沉迷于“指令”而不顾情感的机器。化解城市危机仅靠他“天才”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应依靠所有人的力量。普通市民是不完美的,但却是真正的“人”。瑞德的失败表明,人文主义对于“人”的定义不免片面和偏激,而“人”究竟应是什么样的,或许永远不会有确切的答案,因为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的产物,人的梦想要与客观现实相适应,主观能动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制约性。
“西方语境中的‘人’,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24]。在市民们的观念中,只有符合人文主义者所规定的“完美的人”才能作为城市的领袖解决危机,而这一领袖无疑是整座城市的焦点,处于中心位置。在瑞德到来之前,为了化解危机,市民们先是将希望寄托于克里斯托弗,又寄希望于布罗茨基,结果都是失败的。不管付出多少努力,市民们都不会达到目的,因为他们努力的方向是错误的。从克里斯托弗到瑞德,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市民们并没有调整解决问题的思维;相反,他们一直在固化解决问题的错误方式——将所有希望都完全寄托在单个人身上。在后人文主义者看来,普遍的、不变的人的本性是不存在的。人们应该抛弃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概念,因为人并不是人文主义所认为的那种拥有不变的理性、可以自我存在的存在,而应该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9]197。人性不可以被定义,因为人性是变化的。市民们需要认识到,美好和谐的城市必须是市民们共同创建的,而不应单单指望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变得与之前人们所信赖的那样完全不同,那么,整个城市的未来也会变得不再光明。事实证明,克里斯托弗变得狂妄自大,布罗茨基成为了一个酒鬼,瑞德也迷失了自我,最终导致所有人的梦想都未能实现——城市精神危机因而变得愈发严重了。瑞德作为整座城市的救命稻草、市民们的偶像,没能帮助市民们实现心愿,周四之夜的失败代表瑞德的梦想终成泡影,整座城市寻求慰藉的结果遗憾地成为“无可慰藉”,不切实际的梦想只能是破碎的梦想。
四、主次与取舍:成功的壁垒
肖建华认为,处理“后人类”问题的药方应是重构身体与心灵、男人与女人、科技与人文等的和谐统一关系,塑造和发展具有新的心理、新的伦理、新的审美、新的对社会和文化认知的“后人类”主体[25]。社会的发展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主体,人可以选择忽视社会环境对自身的要求,将自己困在人文主义为自己建造的“壁垒”中,继续人文主义的传统;也可以选择克服人文主义的危机,削弱“上帝已死”的意识,勇敢改变陈腐的观念,以先进的思维和方式创造美好未来。瑞德在处理市民们委托给自己的小任务与“化解城市危机的大任务”时遭遇的双重失败,证明了困在人文主义的“壁垒”中而不敢改变自己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瑞德虽有时感到应接不暇,但也对城市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结果却是命运坎坷,导致自身与整座城市的未来都不乐观。石黑一雄曾表示,在写《无可慰藉》时,他想表达的是一种绝望的、略带悲哀的乐观主义,到头来,所有人不得不依靠这种乐观主义继续前进[26]。之所以略带悲哀,是因为此时的乐观主义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乐观主义了,而是夹杂着故事中的人物对社会变迁的清晰感知与对自己身处何种境地的深深迷茫。城市的大危机与市民们所面对的家庭、情感等小危机使他们痛苦且焦灼,这个城市便可被视为当今的后人类社会的缩影,而故事中的市民们代表的则是现如今身处后人类社会却无法转变对自己身份认知的人,这其中主人公瑞德最具代表性。瑞德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定位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完全符合人文主义对“人”的刻画,即坚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只要刻苦努力就一定能够拥有美好未来。瑞德在城中只能够逗留四天三夜,却要精心准备一场钢琴演奏来化解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危机。时间紧张,任务艰巨,尽管会因为接踵而至的小任务和意外情况而烦恼,但他一直保持乐观。在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天,为了帮市民们解决各种小问题,他甚至没有睡觉和吃饭的时间,自然也没有时间为周四之夜做准备。但是,他却乐观地安慰自己“如此短时间内就有如此收获”,“到这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呀,问题的答案必将在不久以后显现”[19]175。即便在周四之夜即将到来之时他也信心满满,在进行唯一一次钢琴演奏时他发现曲子的方方面面尽在其掌握之中,而他在这之前的焦虑和担心愚蠢至极[22]。不论是对小任务还是大任务,他都是乐观对待的。瑞德对任务的全盘接受折射出的是后人文主义时代人们对自身能力的盲目自信以及对于保留住传统人文主义时代完美的人类形象的倔强渴望。但是,瑞德本身并没有他自己和市民们所认为的那么无所不能,因此,若想此次旅途有成功的可能,他必须将全部精力放在周四之夜的钢琴演奏上,而不能够盲目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所有的任务。人文主义推崇以人为本和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也使人的价值与能力成为中心和焦点[27]404。然而,这并不代表人可以盲目相信自身的能力;通过自身努力追求幸福要求的是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使用正确的方法,当面临多重任务时要分辨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根据自身能力进行适当的取舍,以保证将精力都放在最重要的任务上,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在人文主义盛行时期,对人的大肆夸赞是为了挑战神的权威,争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不免成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如今,人类几乎已经不再面对其他因素对人的地位的威胁,甚至开始把非人的一切看作人类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对象,这难免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在后人文主义时代,人与非人应是多元主体关系,而不能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瑞德所面临的任务不是“他者”,也不可以被认为是瑞德可以操纵的对象。相反,在这些任务与瑞德平等的关系中,瑞德应怀有敬畏之心来应对这些大任务和小任务,知道自身能力有限,将市民们要求自己完成的任务分出层次,主动放弃一些繁杂的小任务,比如查看霍夫曼妻子的剪报册、在菲奥娜的邻居面前露脸为菲奥娜出气等,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谋划周四之夜的钢琴演奏上。人文主义首先给予个性以最高的发展,其次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28]336。瑞德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与对任务能够圆满完成的信心符合人文主义对人的定义,但是,在面对大任务和小任务的分析和取舍时,他却没有做到对自己做最彻底的研究,导致大任务和小任务都没有完成,整个旅途以失败告终,整个故事以悲剧收尾。在这里也能够看出后人类社会中固守人文主义传统的人在面对社会的变化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慌乱和难以适应的无能为力感。
扬·阿斯曼指出,自我的形成若不经过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就不可能完成。个体认同是对自我本身的认识,同时也是他人对自己的期望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责任[29]139。一个人的本质,并不是由先天规定好的,“人”不是统一的、不变的社会存在,而应该在交往、运动和发展中逐渐被认识。从人文主义的盛行到后人文主义思潮的悄悄到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应随之改变,要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社会的要求。人与非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人类不能够在后人文主义思潮主导的社会中企图像之前那样征服和控制一切非人的存在。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30],而他者通常是地位较低、被边缘化的角色,这种划分边界的二元论已成为后人文主义抨击的对象之一。《无可慰藉》中,无论是市民们委托瑞德帮忙完成的小任务还是瑞德为化解城市危机证明自己实力而接受的大任务,都在故事中扮演“他者”的角色。瑞德在完成这些任务时所遭遇的焦虑以及任务的最终失败都证明后人类社会中人与非人之间“自我”与“他者”的划分是不正确的,人与非人都应是后人类社会中的多元主体,而过度相信自身能力、不分主次地企图控制和征服“他者”的做法,更是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石黑一雄是一名构建全新人文哲思场域的杰出文学家代表[16],拥有“更具国际化的视野和更为开放的文化生存直觉”[31],无论是对主人公的刻画,还是对次要人物境遇的描写,《无可慰藉》都反映了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现实要求。
五、结语
优秀文学作品总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反映社会现象,引人深思,《无可慰藉》也是如此。社会发展使“上帝已死”的时代正逐渐向“人已死”的时代过渡:人类社会不再一味地遵循二元生活模式;人类在整个世界上不再是主宰者,而应该与一切非人的存在和谐共生;人拥有通过自身的能力努力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也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辨出主次,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成功。
《无可慰藉》中瑞德的故事刚好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他被市民们奉为救世主,并且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化解城市的精神危机,但他的能力不足以圆满完成别人所托付的所有任务。他把自己视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解救城市的力量,而整座城市的命运只能取决于自己。在城中能够逗留的时间只有四天三夜,但他却全盘接受市民们的请求,应接不暇,手足无措,导致这些小任务都没有得到圆满完成。因为接受了所有的小任务,导致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周四之夜的大任务做准备,所以大任务也失败了。
故事中的这些任务在与瑞德的关系中处于“非人”的位置,而正是因为瑞德并未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处于后人文主义时代,才对自身的能力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务而忽视了自身能力的不足,最终导致了所有任务的失败。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文主义已经悄悄开始向后人文主义迈进。后人文主义不仅仅是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解构,更是一种建构,它主张人类打破人文主义的枷锁,顺应社会发展要求,正视自身的能力和地位,实现人与非人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