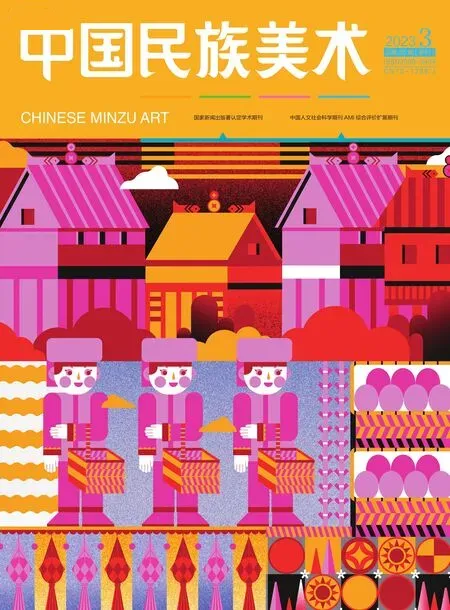广彩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述评(1949-2019)
文/图:曾科斯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科研助理
刘菲菲(通讯作者)教授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引言
“文献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文献整理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研究质量的高低。”[1]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销瓷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与实物和文献整理研究密切相关,由于时间较近,广彩在内的清代外销瓷是中国外销瓷中保存有最丰富的实物和文献资料。“17 世纪前后,随着大量的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作为外销瓷器的广彩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最早出现的全球性商品之一。”[2]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时间里,广彩文献依旧以贸易记录档案为主,大部分的研究在中西方陶瓷史、陶瓷论著、中外美术史等的文献中只是简扼提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时间里,地方意识不断增强,广彩在外销瓷研究领域越显重要,特别是2008 年广彩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彩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形成了起源考析到理论研究等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广彩的创新传承、风格特征、文化交流、与岭南绘画关系等方面,梳理并探析文献研究对广彩研究的影响与推进作用,并促使对外销瓷研究有所突破。
广彩全称“广州织金彩瓷”“广州彩瓷”,是广州地区在各种白胎瓷器上绘制和烧制具有程式化装饰图案的地方传统手工艺,以绚丽华美的色彩、金碧辉煌的外观闻名于世,具有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质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广彩从始创阶段发展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从继承景德镇彩瓷技术开始,18 世纪中期初步形成广彩的地方风格,到19 世纪出现制式化的织金彩瓷,发展至20 世纪广彩趋于民族化、地域化和时代化,“20 世纪的广彩瓷器风格,一种主要延续晚清传统风格为主,销往欧美;另一种是临摹景德镇和日本彩瓷风格,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和东南亚地区。20 世纪的广彩瓷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采取多元化及变革之路,创造了广彩瓷器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多元及新的辉煌”[3]。以输出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包含相当多定制瓷,逐渐形成了以广彩为核心,涵盖政治、文化、贸易、历史、艺术的广彩资源。
一、广彩研究现状与文献分析
“广州彩瓷究竟始于何时?怎样形成的?在过去的文献中还未有找到明确的记载。”[4]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的刘子芬著《竹园陶说》中首次提出“广彩”一词:“清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烧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南。盖其器风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长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5]文中对广彩定义、出现原因、出现年代、制作目的、制作模式、制作地点等的阐述被广泛接受,因此几乎成为了研究探析广彩定义的必引文献。但“广彩”概念在文献研究中出现时间较晚,在此前的陶瓷文献中以“洋器”“广窑”等进行混淆阐述。

广彩花卉纹章纹汤盅连托盘 清·乾隆(广东省博物馆藏)
宋良璧较早以广彩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他对广彩的年代进行考订,对广彩的各类纹饰、色彩等风格特征做了考辨和介绍。1981 年宋良璧在《古陶瓷研究》发表了《广彩与外销》一文,文中通过广彩艺人的口述对广彩出现的年代、外销作出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其一,推论了广彩制作技艺是由康熙年间景德镇彩绘师傅杨快和曹锟所传授;其二,认为广彩生产始于康熙时期,雍正时期初具风貌,成熟于乾隆时期;其三,推断了广彩生产的初期,匠人、素坯、颜料等大多来自景德镇,或依照景德镇彩瓷纹样,或来样加工,因此早期的广彩无鲜明特色。同年,在广东新会召开了“中国古外销陶瓷首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会上就广彩的外销问题进行了讨论:“广彩的出现专门是为了外销。”[6]
广彩艺人赵国垣一生从事广彩事业,较为系统地搜集、整理、研究广彩历史,1987 年其根据父辈口传和自幼的广彩学徒经历,撰写了《广彩史话》,对广彩制作的朔源、行会组织、地方风格、颜料与彩绘技法进行详细说明,并认为广彩的出现与广东珐琅工艺的兴起有关,举例分析了广彩地方风格形成的三个阶段,为广彩研究提供了以往史料未曾记载的关于广彩制作、颜料、工序等诸多细节。
此后的广彩逐渐掀起研究热潮,部分学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的辩证后加以运用,也有些学者从制作技艺、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西文化交流等为主要方向研究广彩,结果是广彩各个方向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文献数量,形成了以广彩为核心,涵盖政治、文化、贸易、历史、艺术的文献资源。

广彩龙凤花蝶纹双象耳瓶 清·道光(广东省博物馆藏)
(一)关于广彩的现状与分类研究

广彩描金花蝶纹菱形盘 清·道光(广东省博物馆藏)
近70 年来,在中国陶瓷史、外销瓷论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关联的广彩文献比较丰富,内容比较宽广,形式多种多样。如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1960)中阐述了其在东南亚各地收集广彩的部分史料,探讨了广彩研究的各种可能的议题;[7]杨伯达在《从清宫旧藏十八世纪广东贡品管窥广东工艺的特点与地位》(1987)一文中指出“广彩不作为贡品进入清宫”[8]。林明体在《广东工艺美术史料》(1988)的部分内容梳理了广彩历史源流、制作工艺。[9]自清代记载以来对广彩的研究都是一脉相承的基调,但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针对广彩本身的研究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如介绍广彩各时期阶段发展情况的《绚彩华丽的广彩瓷器》[10]和《广彩瓷器》[11]等。广东省博物馆对其现有广彩藏品进行分类,出版了《广彩瓷器》(2001)展示了清代到现代近百件馆藏广彩作品,并记录一批广彩工匠学艺历程,及对颜料与纹饰说明介绍;[12]陈玲玲所著《广彩—远去的美丽》(2007),系统梳理了广彩的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和不同时期广彩器型类型、装饰风格等,是目前广彩研究比较完整的著作;[13]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根据广彩艺人赵国垣的手稿、日记、文件等,出版《赵国垣广彩论稿》(2008),对广彩艺人的经历、颜料和纹饰、彩瓷厂经营架构等内部珍贵文献进行介绍说明,[14]同时还出版了《世纪嬗变:十九世纪以来的省港澳广彩》(2008),收录了关于19 世纪以来的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广彩各个方面研究的专题文章[15]。这些文献资料为广彩研究奠定了基础,即广彩是清中期根据市场需要,专门为出口生产的的低温釉上彩瓷,其白瓷坯等材料主要来源于景德镇,以绚丽华美的色彩、金碧辉煌的外观为特色,在技艺上吸收了岭南绘画和西洋绘画技法,融合了西方审美情趣,同时装饰题材和内容等民族化、地域化。此外,相关研究还有莫彭《广彩瓷器》(2001)、李焕真等人《堆金织玉:广彩彩瓷》(2011)、高伟利等《论广彩繁荣的历史意义》(2011)、李灵宁《十八至十九世纪广彩瓷器盛行原因研究》(2012)、郭学雷《广彩起源及其早期面貌》(2017)等等。
从1949 年至1979 年关于广彩现状与分类整理的研究表明,涉及的专著论述不多,但仍旧有较好的成果,如陈玲玲、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通过广彩的实物和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统整广彩研究,形成广彩起源、发展阶段和绘画技法的共识,具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具有专论性文章,如冯素阁、贺海燕等人的研究和论证亦成为资料收集的来源。
(二)关于广彩传承与艺人的研究
广彩技艺主要通过家族和师徒两种途径以口传身授的方式进行传承,有着严格的传承规则和管理制度,对广彩艺人的谱系和技艺口述进行研究尤为重要。但关于清代广彩艺人的相关研究,除了口传有少数的记载,专门的研究文献较少,更多的是广彩行会、各类彩瓷场的记载。
关于现当代的广彩艺人记录和研究有一定的成果,主要有赵国垣的《广彩史话》,对广彩行业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分类别地记述了20 世纪初的广彩名家;曹荣枢的《荣枢先生口述广彩掌故》(2008)对抗战时期迁至香港地区的广彩艺人进行了阐述:“这段时间里,我接触过不少艺人,各有特色。出生于清光绪年间的艺人主要有:何苏擅绘鸡,谭万擅绘花卉,司徒章是大揽家。”[16]1956 年省港澳共63 位广彩艺人相应号召,回到广州成立广州织金彩瓷厂恢复广彩业,广彩传承形成了“赵兰桂堂”家族五代传、广州彩瓷场师徒传承、父子和高校教育相结合的现代传承方式,广彩传承人的研究逐渐增多,如曾应枫等人《织金彩瓷:广彩工艺》(2013)中对广彩家族和传承人进行了梳理。[17]另外还有周翠玲的《华南手工艺人系列之五:满地富贵,一地流散—广彩大师和他的作品》(2004)、邱彦昌《翟惠玲:为广彩艺术甘做苦行僧》(2016)、罗竹君《流金溢彩的人生—广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司徒宁访谈录》(2017)、曾应枫《百年广彩手艺人的家风家训—以“赵兰桂堂”家族为例》(2018)、何雪莹《“双导师双学徒”人才培养模式在广彩瓷传承后备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2018)等。
整体来看,从近70 年关于广彩传承与艺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较少有相关的专述性文献,大多有关研究主要是在章节中阐述,对广彩传承谱系、绘制技艺等详细分析较少。
(三)关于广彩装饰风格与艺术特征的研究

广彩山水人物纹碟 民国 广东博物商会 制(广东省博物馆藏)
广彩以其绚丽华美的色彩、金碧辉煌的外观闻名于世,18 世纪广彩在欧洲“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影响下形成“华风欧韵”,19 世纪广彩的装饰题材和内容出现新的变化,形成了织金彩瓷的独特风格并达到成熟阶段,20 世纪广彩开始向民族化、地域化发展,增添了符合国人审美要求的广彩装饰类型,出现了用色淡雅、线条优美的作品,给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觉。
装饰风格与艺术特征的研究是广彩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1949 年至2019 年间这部分内容的文献数量较多,且取得了较大成绩。如赵国垣在《广彩史话》中将广彩地方风格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陈玲玲《广彩—逝去的美丽》和广东省博物馆《广彩瓷器》对广彩的风格、特征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又如梁正君《近五十年以来广彩人物纹饰绘画风格的演变》(2009)、宁钢等人《绚丽华章:广彩瓷器艺术特征分析》(2009)、江涛《岭南风情与欧洲洛可可的完美交融—由广彩瓷的视觉特点解析其文化特质》(2013)、江涛《欧洲中国风背景下广彩瓷来样定制的特点》(2014)、金锐等《论19 世纪广彩装饰艺术的发展》(2014)、黄艳《海上丝路中的非遗—广彩的文化特质何当代传承初探》(2015)、何芊芊《广彩的装饰色彩研究》、黄芳芳《清代广彩瓷“满大人”纹饰定制化特征研究》(2017)、曾玲玲《试论清代外销瓷装饰艺术的几个问题》(2019)、焦流《清代广彩纹章瓷装饰艺术特征研究》(2021)等文献。
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广彩的装饰风格、艺术特征,分析和探讨了广彩的各方面的特色,从研究材料、内容、方法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路径,为近代外销瓷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佐证。
(四)关于广彩技艺实践与创新的研究
广彩技艺的实践和传承是由艺人口传身授,目前未发现完整的文献理论体系,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较少,需要全面剖析广彩工艺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场景、人文形态、中外交流等,寻求岭南传统人文思想、审美等核心价值。
关注广彩技艺的记录,进行创新实践等一系列问题,赵国垣较早介绍了广彩制作的整体技艺流程,将广彩制作工艺分描线、填色、积填、封边斗彩、炉房、新样板设计六个过程。叶军峰《广彩工艺技法》(2017)全书分为十个模块,详细阐述了广彩的绘制工具和陶瓷坯的选择、颜色与应用、基本绘画技法、动态变化以及广彩的烧制等。该书在广彩技艺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18]广彩传承人翟惠玲的《广彩瓷艺创作见解浅谈》(2017)、《广彩艺术理论研究》(2018)和许恩福的《谈广彩人物画识别》(2013)、《广彩的继承与创新》(2012)通过艺人的视角对广彩技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梳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李琨等人《广彩花鸟草图案模块化设计研究》(2014)、黄方芳《广彩瓷的色彩演变及设计应用研究》(2017)、柴柯《广彩传统纹样与现代服装设计的诗意化整合》(2016)和《广彩传统开“斗方”构图形式之美学探徽》(2018)等,从实际案例分析及实践应用,对广彩的创新应用等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

广彩人物纹八棱形盘 清·乾隆(广东省博物馆藏)
(五)关于广彩收藏鉴赏与文化交流的研究
广彩从早期的艺术欣赏品,到中晚期的生活用品,再到现代的工艺和艺术品,其收藏鉴赏目前还是冷门类别,相关的收藏鉴赏究是近几年产生的议题。
收藏与鉴赏方面的成果有曾波强《清代的“清明上河图”:乾隆广彩潘趣酒大碗中的十三行场景》(2007)、《广彩研究与鉴赏》(2012)、《洛克菲勒纹饰广彩瓷鉴赏》(2018)、《广彩皇冠上的明珠:洛克菲勒纹饰广彩瓷》(2019)等系列研究从广彩的器型、颜料、锦地、边饰、人物等进行详细解读,并就广彩对外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为广彩的收藏与鉴赏提供参考。此外,还有刑荣波《极具收藏潜力的广彩瓷—清代外销瓷浅谈(续二)》(2004)、赵勇《收藏新宠—艳丽多姿的清代广彩瓷》(2010)、毕树珍《浅析“广彩瓷”的制作工艺与收藏》(2011)、刘卓《广彩瓷:中国陶瓷器收藏中的“非主流”》(2011)等,对广彩收藏作了详细分析,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广彩作为“海上丝路”贸易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独特艺术形式,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艺术形态之一。朱培初在《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1984)阐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陶瓷贸易交往,其中部分章节内容涉及广彩纹饰,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19]此外,还有袁胜根《论清代广彩瓷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关系》(2004)、郭东慧《清代广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2013)、黄芳芳《“海丝路”背景下“广彩”的艺术形态研究》(2016)、童心《浅析广彩瓷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17)、何东红《从广彩瓷器看海丝路上的粤商》(2017)、胡宇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清代民间广彩陶瓷设计的影响》(2018)、《广彩在海丝文化中的特质研究》(2018)、张弛等人《早期广彩瓷中的中英设计交流》(2019)等,以海丝文化为背景,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思维来探寻广彩的文化特质。
随着外销瓷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的广彩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未形成比较完整系统化的广彩资源库,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六)关于广彩与岭南绘画的研究
清末到民国初年期间,岭南画派画家参与了广彩创作,广彩得以创新,出现了浅绛彩和新彩的影子,让人耳目一新,这种吸收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为广彩的发展和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关注广彩与岭南画派研究的一些问题,取得了系列性成果:陈文彦《岭南绘画之广彩烙印》(2013)、《岭南绘画对广彩瓷的影响》(2014)、《广彩瓷上岭南绘画的价值与影响》(2016)、《清末民初广彩瓷的岭南绘画研究》(2017)、《广彩瓷山水装饰纹样研究—以清末民初受零年那绘画影响的广彩瓷为例》(2018)等,对今后系统挖掘广彩与岭南画派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彩寿星挑桃纹碟 民国 广东博物商会 制(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另外,卫风《岭南画派与瓷画艺术》(1999)、葛秀支《岭南画派与广瓷》(2014)、曹宇匆《岭南画派中广彩的文化艺术特征》(2016)、梁秋亮《岭南绘画对广彩瓷器的影响研究》(2017)、林蔚然《创新中的遗失—浅析高剑父以国画入瓷导向下的广彩改良》(2019)、《清末民初广彩瓷的绘画艺术探究—以岭南画派对广彩瓷的影响为例》(2019)等论文,也都是从岭南画派与广彩瓷关系的研究角度出发,分析了各个方面的资料,为岭南画派与广彩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七)关于广彩与其他彩绘的比较研究
广彩承载中国传统彩瓷制作技艺,在岭南文化基础上结合西方审美和需求融合创新。随着五彩、粉彩、珐琅等陶瓷彩绘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在彩瓷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研究广彩与其他彩瓷的关系问题,如冯素阁与宋良壁的《略述五彩、粉彩与广彩瓷器》(1993)、《五彩粉彩与广彩瓷器之区别》(1999)是目前较早的研究文献,让我们大致了解广彩与其他陶瓷彩绘的关系。
此后,出现的一批相关研究的成果,如胡继芳《珐琅彩瓷与早期广州彩瓷之比较》(2007)、吴星明《广彩与新彩瓷的装饰》(2009)、王健丽等人《康熙五彩、珐琅彩、粉彩、广彩之饰》(2014)等展开了多种多样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现阶段的广彩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
二、广彩研究成果的评述
通过广彩研究现状与文献分析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 年间广彩研究成果较少,进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销瓷的研究迅速推进,广彩的专题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已取得成果

广彩婴戏图碟 清·嘉庆(广东省博物馆藏)
1.广彩现有的研究成果范围广
从现有的综合研究来看,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观点,不但有历史、艺术风格领域,还有文化、经济价值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如从陶瓷发展历程的综合视角进行广彩历史变迁和艺术风格研究,朱培初的《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文中通过详细阐述广州贸易发展的背景,指出广彩在广州形成发展,是由于为了适应外商的特殊要求,广州从景德镇运来素胎瓷器,在外商的直接指导下,描绘西方的纹章、风景、纹样,同时还写上英文。陈进海的《世界陶瓷艺术史》(1995),通过对世界陶瓷史的归纳,将陶瓷与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生活、审美等内容进行陈述。[20]从民间工艺视角梳理广彩历史源流、制作技艺的研究,有林明体的《广东工艺美术史料》(1988),从传统工艺的手工技法、艺术特色两方面介绍了广彩的风格;广东非遗丛书的《织金彩瓷·广彩工艺》,对广彩的发展源流、制作技艺、艺术价值、行业发展、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全景式地展示了广彩的独特魅力;以岭南文化为基础,探讨广彩蕴含的文化内容和地域特色,有李权时的《岭南文化》(1993)等。
2.广彩个别方向的研究取得较大突破
现有的广彩研究,主要是借助广彩实物、文献资料和口述技艺的回溯,根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和留存实物进行分析和探讨,个别方向的推进具有较大突破,如与岭南绘画的关系、欧洲装饰艺术的影响、教育的传承、装饰纹样等。陈文彦《清末民初广彩瓷上的岭南绘画研究》《广彩瓷上岭南绘画的价值与影响》《岭南绘画对广彩瓷的影响》、葛秀支《岭南画派与广彩瓷》等,系统地阐述了岭南绘画与广彩瓷的关系。陈昊武《广彩外销瓷与欧洲洛可可艺术的审美趣味互动》(2018)、《浅析欧洲近代符号象征学中的中国清代广彩外销纹章瓷》(2018)等,在中西贸易交流背景下,指出广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21]齐喆《从高校教育的角度进行文化遗产的传承—作为新装饰艺术材料的广彩教学研究》(2012),李红《非遗研培计划的实践与思考—以广州美术学院广彩瓷烧制技艺普及培训班为例》(2016)、《“非遗”进校园的实践和思考—基于广彩瓷烧制技艺的调查》(2019)等,指出广彩进入高校普及推广、技能培训、设计创新等,确保核心技术传承和振兴手工艺。
3.实物整理和图像记录方面有一定的积累
由于广彩的年代较近,因此保留较多的实物与文献材料。随着研究的热潮,一批批广彩实物得到整理和保存记录,如广东省博物馆的《广彩瓷器》、郭学雷的《广彩起源及其早期面貌》、曾波强的《洛克菲勒纹饰广彩鉴赏》、李黎的《广州彩瓷鉴赏》等,对现有广彩实物进行分类,图像记录了清代到现代近百件广彩作品,并记录一批广彩工匠学艺历程,对颜料与纹饰说明介绍,为广彩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资料基础。
通过整合梳理,近70 年的广彩研究成果呈现了广彩根植于民间、蕴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浓郁的岭南特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在文化、历史、艺术、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二)存在的不足
从上述研究现状整理看来,近70 年关于广彩研究如装饰元素、工艺技法、图案构成、艺术鉴赏等内容成果颇多,但整体性研究较少,为今后的研究留下较大的研究空间和创新空间。
1.目前研究未形成较完整的整体性研究
广彩的繁荣发展带动了清中期海外贸易的发展,目前保存有较为丰富的实物、贸易记录和文献材料,涉及面广,广彩研究涉及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民俗等,不同领域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联系性。这需要我们系统地整理广彩的文献资源,深入研究广彩的制作、交易、传播、影响,正确把握广彩对当时广州文化、经济的影响。目前的广彩研究,主要在介绍型梳理、艺术特征、设计应用几方面的取得较大突破,但介绍性阐述较多,在从制作技艺、经济网络开展广彩中西贸易的历史见证研究较少,因此,我们可以从广彩师承流派、绘制技艺等进行整体化、系统化等深入详细分析。
2.研究方向不够开阔,理论部分内容相对较少
近70 年的广彩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彩传承与创新、装饰应用进行相应的研究,在当下热门的谱系和技艺口述开展实证研究较薄弱,例如各个时期的广彩器型、色彩、纹饰以及广彩出口后西方工匠对其进行重新改造,甚至有部分改变其原有功能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将专著、学位论文、系列论文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广彩的研究体系。广彩是中西贸易、文化交流的物质体现,因此,广彩研究还需要我们从中西贸易、文化交流、技艺特点等层面扩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角度,进一步将实物和文献研究结合,运用叙事、问答等形式进行口述等跨学科研究方法。
3.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扩充
广彩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贸易、文化交流典型代表之一,国内外已整理部分广彩研究,但现有研究成果中结合中西文献与口述史的整理相对较少,未能满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研究需要,实现助力“一带一路”,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和创新空间。
三、结语
通过1949-2019 年的广彩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广彩是18 至19 世纪我国出口贸易主要商品之一,在中国陶瓷领域具有出口量最多、题材最广泛、器型最丰富、表现形式最多样的特点,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亮丽的文化名片,承载中国彩瓷制作技艺,在岭南文化上结合西方审美和需求融合创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广彩特殊性与重要性在于其具有外销艺术的商业特质和作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媒介的功能。
广彩文献整理作为基础研究其速度和水平影响着广彩的研究质量,广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销工艺美术,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广彩文献整理研究的速度与水平,重视广彩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进一步挖掘其在中西贸易、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全方位研究,塑造新岭南人文精神的名片和形象。因此,对于广彩的整体性研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