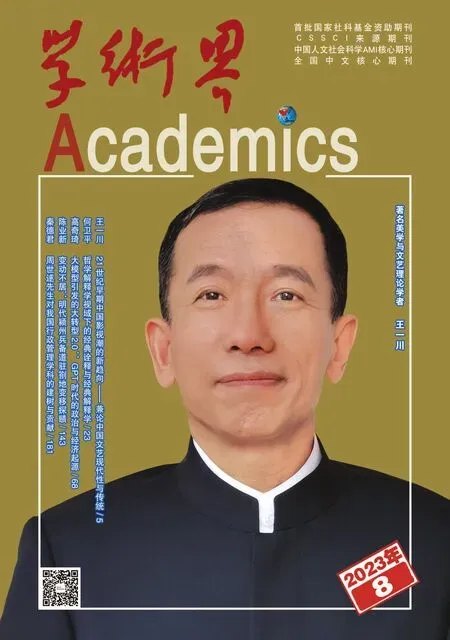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
唐 莉, 邓 锐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数字帝国主义是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的结果,属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产物”。〔1〕数字帝国主义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形成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已经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视角来看,数字帝国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于数字劳动碎片化的特性,数字帝国主义在奴役和剥削劳动群众方面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对革命目标、革命对象、革命主体、革命领导等具有多方面的消解作用,存在着阻碍世界革命的极大危险;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和研发,引发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与世界革命具有一定的融合性。在数字技术持续浸润人类生活的时空背景下,如何消解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奴役,化危为机,不断推进世界社会革命进程,是新时代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悖离: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形成对世界革命的阻碍
数字帝国主义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出极具迷惑性的数字景观,不遗余力地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形态的终极性,正在从革命目标、革命对象、革命主体、革命领导等多层面消解社会革命因素,给世界社会革命造成新的阻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一)数字帝国主义对革命目标的阻断
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世界革命的终极目标,同时主张社会革命的近期目标与终极目标的统一,认为无产阶级不应“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而应“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做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因为他们始终把社会革命的近期目标视为通向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阶梯。〔2〕数字帝国主义却以数字联盟的方式阻挠社会革命的近期目标,打造出符合资本意志的数字景观,旨在阻断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实现。
数字帝国主义正在隐蔽地阻挠无产阶级近期革命目标的达成。社会革命的首要目标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3〕然而,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国际上加紧构建数字霸权联盟,企图切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4〕近十年来,美国在全世界拉拢“共同价值观”联盟,启动“清洁网络”计划,利用数字网络技术手段,构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意图压制新兴崛起的中华文明和第三世界文明,驱使广大亚非拉传统殖民地人民沉醉于美式文明之中,根本目的在于阻断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进程。
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构建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数字景观,意图切断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追求。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终极目标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5〕数字技术正成为监视和控制人类生活,约束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认为,资本主义创设出的数字化景观世界是一种虚假认同和遮蔽现实困境的意识形态,是大数据经验主义者和数据拜物教用数字资本构筑的社会形态。〔6〕此种数字景观全面接入人类的社会生活,将人圈禁在数字资本创设的“乌托邦”中,增加了丢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可能性。数字帝国主义通过给定的信息,为每个人塑造出舒适的信息茧房,表面满足了大众的社会需求,实则完成了对人的精神奴役。〔7〕数字帝国主义运用数字技术,使人们在数字空间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忽略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淡化甚至放弃社会革命的目标。
(二)数字帝国主义对革命对象的遮蔽
由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构成的数字帝国主义——“资本—国家”,形成了世界社会革命的整体对象。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社会革命意味着“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8〕然而,数字技术的推广并未实现无产阶级所希冀的技术解放图景,反而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隐藏起“资本—国家”这一革命对象。
数字帝国主义竭力掩盖数字霸权和平台垄断背后的资本剥削和压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数字资本无疑是当下世界革命的根本对象。“今天,企业殖民的新形式正在逐步形成”,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主导了搜索引擎、操作系统、云服务、社交网络、交通运输、商业网络等领域,建立起庞大的数字帝国,遮蔽住“资本—劳动”的剥削关系,造成资本剥削从“有形”走向“无形”。〔10〕宏观上,数字帝国主义正是“基于将有酬工作时间外包给无酬工作的众包”实现资本剥削的隐藏。例如,古书籍的图文识别工作被拆分为验证码识别工作,用户在输入验证码的过程中无偿帮助企业完成了古籍翻译工作。诸如此类的无酬“众包”工作大量存在于数字帝国主义中,对用户而言,在网络时空中的每一次浏览、点击、上传、点赞和评论都是生产性的活动,但资本家却不向用户支付占用其劳动的费用,造成资本剥削事实性的隐藏。微观上,数字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他人剥削”被包装成追求上进的“自我剥削”。〔11〕换言之,工人被塑造成追求绩效的独立单元,承担起“老板”和“员工”的双重角色,在利益的驱动下,作为“老板”的自我必须强迫作为“员工”的自我努力工作。例如,从事电商直播的主播群体,在追逐销售业绩的过程中会主动自我增压,延长直播时间,增加劳动负荷,其结果是更多的剩余价值被直播平台占有。可见,绩效驱动下,数字帝国主义一改资本直接剥削的形式,转而通过工人“自我增压”的方式挖掘剩余价值,进一步隐藏了“自我剥削”背后的资本剥削事实,造成革命对象被遮蔽。
数字帝国主义还竭力掩盖构筑于数字资本之上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2〕工人阶级必须把“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13〕“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14〕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出现了新的变化。数字平台越来越多地被赋予统治的权力,对内数字政务、数字税务等新兴治理手段的出现使数字平台被赋予统治和管理人民的能力,对外数字平台被赋予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全球监听和窃密的能力。无论数字平台被赋予多少职能,本质上只是数字资本的提线木偶,是数字帝国意志的体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无论数字资本及其上层建筑如何被掩盖,都不能改变“资本—国家”力量作为革命对象的事实。
(三)数字帝国主义对革命主体的消解
马克思认为,作为“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15〕无产阶级是“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16〕如果说前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社会革命主体“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17〕那么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社会革命主体则是作为数据献祭者才得以存在的“数字无产阶级”,他们沉寂在被数据主义者编造的技术解放愿景中,“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18〕
其一,数字帝国主义对人的“最小完整性”〔19〕的破坏,造成主体革命意识的弱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革命”。〔20〕数字帝国主义借助“数据监控”,达到对个体生命的全景监控,数字监控下人之为人的基本界限受到侵犯,作为一个“最小完整性”的自我开始受到威胁,人作为主体的完整性不复存在,使得唤醒主体的革命意识越来越困难。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产生的“自动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注射”到数字化的景观世界之中,再通过议题设置、内容输出、情绪引导、价值扭转等手段,轻松抹煞革命主体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造成革命主体的信仰体系崩塌。
其二,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技术阻止无产阶级的联合。恩格斯说:“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和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遭到孤立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21〕数字帝国主义阶段,人们的交往从物理世界的现实交往转向数字世界的虚拟交往,交往形式深刻变化的背后是个体交往日益疏离,导致“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22〕这个“虚体”代替主体与他者交往,除了使个体感到交往的便利之外,更多的是削弱主体的现实交往能力,令其失去走出数字空间走向现实联合的能力。
其三,数字帝国主义通过蚕食革命意识进而阻碍主体的革命行动。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是“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双向互动的产物,然而“大数据使思考变得多余。我们不假思索地任自己沉湎于‘事情就是这样’”。〔23〕其结果是,人们沉沦于“刷屏”带来的感官刺激,却不能“生产出他的全面性”,〔24〕更无暇顾及人类解放的宏大议题,最终放弃社会革命的信念,难以形成统一的革命行动。
(四)数字帝国主义对革命领导权的削弱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5〕然而,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公司及平台,建立全球性权力中心,实行干涉主义,正在削弱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革命的领导。
其一,削弱共产党的影响。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据技术,通过数字平台,支持反动势力、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制造政治动荡、社会冲突和暴力恐怖,以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抗争。其二,阻止无产阶级政党“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6〕数字帝国主义利用舆论优势,随意加工和剪裁新闻内容,避重就轻、断章取义地过滤信息,煽动和策划网络舆情,弱化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意愿。其三,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能力。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以获取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机密并在经济政治上实施精准控制,从而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能力。
数字帝国主义通过上述手段,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中,达到弱化乃至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导权的目的。
二、融合:数字帝国主义内蕴着世界革命的因素
数字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无疑具有一定的融合性。数字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的革命,必然会引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领域的变革。数字垄断与反数字垄断成为21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最新表现形式,并随着数字垄断、数字殖民的不断深化,正呈现逐渐激化的趋势,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带来新的动力。
(一)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世界革命的新动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以生产力的解放为逻辑起点的,因为生产力是“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27〕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不仅为资产者带来更多利润,也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每一次技术形态的更迭,都意味着无产阶级距离社会革命成功更近了一步,就如蒸汽动力的出现催生出现代工厂生产形式,加速了无产阶级的联合,催生了巴黎公社革命;电气动力的兴起一方面导致出现了托拉斯、辛迪加等国际垄断组织,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加速了广大亚非拉殖民地的解放。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经济上,数字技术的兴起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创造可能。数字产业的勃兴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极大地提升了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更高水平的物质基础。数字数据和信息作为新形态的生产资料,以其共享性为真正公有制社会的到来开辟道路;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基础设施为有计划生产和计划管理创造条件;数字设备的广泛使用,为人类争取到更多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留足空间。政治上,数字技术的推广为社会自治创造条件。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决策透明度;数字政务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数字监督可以增强权力监督的时效性,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加强社会监督和反馈,保障人民权益。文化上,数字技术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全球影响力创造可能。数字互联网的普及可以分享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促进全球无产阶级的思想交流;数字社交的兴起可以增进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友谊,促进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为行动;数字媒介可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帮助无产阶级获得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总之,数字技术的出现,极大促进了数字社会主义和数字共产主义的到来,使人们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28〕
(二)数字垄断对数字技术的桎梏,是数字帝国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形式
数字帝国主义保留着帝国主义垄断的一般特征,同时带有新的垄断特征。尼克·库尔德利指出“数据殖民”作为“一种新的分配世界资源的方式”,“将带来一种新的,通过数据控制人类”的垄断资本主义。〔29〕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主要表现为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发达国家,通过自身所控制的数字资源,对数字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数字监控、数字渗透和数字产品倾销,旨在从中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垄断利益。数字垄断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深刻的矛盾。数字垄断标志着以垄断为代表的旧的生产关系对数字技术这种新的生产力的束缚和桎梏,数字技术本身内蕴着冲破这种束缚和桎梏的强烈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不断加剧。数据本身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30〕但数据被资本垄断之后,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被挖掘、收集、整合、利用,成为生产资料的一种新形式。随着数据这种生产资料不断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形成了利用数字去垄断和控制世界的数字寡头,数字寡头表征着数字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
首先,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他们会为了争取更多的数字时空、数字资料、数字市场而相互倾轧。例如,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盟友的无差别侦听,充分说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尔虞我诈。其次,发达国家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排挤加深。近年来,美国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数字市场,抢占全球数字治理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挤压中国数字合作空间的意图愈加明显。例如美国主导的“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东南亚智慧城市伙伴关系”“美国—东盟网络政策对话”等计划都是有意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表现。再次,劳资矛盾在加剧。当前,数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在深化。空间上,数字资本创设出“劳动—休闲”一体化的“数字工厂”,数字劳工在点击鼠标的过程中完成“游戏”与“生产”的结合。时间上,开放的“数字工厂”24小时在线,随时榨取数字劳工的剩余价值。时间与空间的压迫放大了劳资矛盾,增进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统计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全球16至64岁的互联网用户每天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逐渐增长,从2013年的6小时9分钟增长至2021年的6小时58分钟,增长了近50分钟。〔31〕可以看出,全球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性日益增加,更长的存网时间意味着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被创造出来。根据联合国劳动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美平均周工作时长超过36.4小时,其中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37.7小时,高于社会平均水平。〔32〕
第二,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和两极分化正在加剧。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数字赤字在拉大,加剧数字世界的两极分化。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202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网络普及率分别为87%和65%,最不发达地区仅为25%。〔33〕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通过盟友协议达成瓜分世界的同盟,在分得巨量社会财富的同时,造成数字技术弱势地区发展缓慢、两极分化。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7.3%。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超过75%,按照经济水平划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是发展中国家的约3倍。〔34〕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拿走了更多的财富,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其次,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存在数字鸿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中提到了美国与欧洲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差距。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中占比36%,而欧盟仅有16%;美国在全球数字平台收入中占比48%,而欧盟仅有11%。同时发达国家内部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在欧洲,2019年,城市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87%,而农村地区仅为79%;在美国,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7%和86%,但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就业中,女性只占28%;在日本,2019年,25~34岁年龄段的互联网普及率为98%,而65岁以上年龄段仅为56%;在加拿大,2018年,高等教育毕业者的互联网普及率为97%,而没有高中文凭者仅为76%;在澳大利亚,2018年,最高收入五分位组的互联网普及率为99%,而最低收入五分位组仅为86%。〔35〕
(三)反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社会力量正在集聚,形成了世界革命的新力量
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都在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网络空间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国际规则和标准,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反对网络霸权和网络保护主义,促进网络空间的发展和治理。其中联合国制定和实施的《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全球数字契约》等宣言、准则、倡议发挥着反对数字帝国主义扩张的积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协调起反数字霸权的国际力量。
欧美发达国家反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社会力量正在集聚。在民众的支持下,欧美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来限制和监管数字平台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行为,例如《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美国反垄断法》等。同时,欧美国家的数字化民主和社会运动兴起,一些社会运动组织,如反监视联盟(Anti-Surveillance Coalition)、数字正义联盟(Digital Justice Coalition)、数字权利基金会(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等,通过宣传、教育、游说、诉讼等方式,参与到“黑客民主运动”“维基解密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反对政府和企业对公民的大规模监控、数据收集和隐私侵犯。
发展中国家为反数字垄断正在积极行动。一些地区性组织和倡议,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一带一路”等,都在加强网络领域的政策协调和能力建设,深化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合作,共同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等威胁。例如《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亚太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倡议》等,通过加强南北沟通、南南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的共享和普惠,缩小数字鸿沟和不平等,统筹起区域内国家数字监管的同时,加强了双边及多边的数字合作。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正在加入反对数字帝国主义的队伍,是世界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国将网络强国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中国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出台《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网络行为,保护网络主权和数据安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发起《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多个倡议、宣言,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积极利用双边或多边的对话与协商机制,如中美网络安全高级别对话、中欧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对话、中日韩网络安全政策对话等,增进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及时共享网络威胁信息,有效协调处置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探讨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和合作原则。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由数字垄断、数字殖民导致的数字剥削和数字鸿沟,最终将引发世界革命,因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6〕
三、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策略
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和策略。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反对并克服数字垄断,消除数字帝国主义给予世界革命带来的挑战和负面效应,必须从世界革命战略的高度,围绕革命目标、对象、主体、领导、方式等多个层面,系统谋划世界革命的策略。
(一)革命目标:逐步构建数字社会主义和数字共产主义
数字技术蕴含着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潜力。人类有理由相信,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繁荣的社会制度,使得世界更加接近共产主义。
首先要建立并逐步实现“数字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现存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别在于“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37〕与工业时代土地、资源、机器等生产资料具有绝对的排他性不同,数字时代物质生产高度依赖的数字和数据本身具有极强的共享性和包容性,以此为基础构建“数字公有制”,可以从制度上阻断数据的自由化和恶意垄断,利用数据资源的非排他、可共享特征,实现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共享,将极大改变数字财富分配,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
其次是组织有计划的数字化大生产。恩格斯认为,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以此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38〕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实时抓取市场大数据,科学分析和引导市场需求,高效组织企业生产,将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纳入基于市场的计划体系成为可能。这样一来,传统计划经济的滞后性、转型慢等弊端将得到根治,计划经济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实现资源的灵活配置、市场信息的及时反馈、大幅提高社会生产率,减少因市场无序波动带来的经济危机。
再次是运用数字技术逐步实现劳动解放。共产主义意味着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39〕数字技术、数字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使人类从繁重的、重复的、有毒有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获得大量自由时间,不再将劳动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第一生活需要”,人们得以自由、自觉、自主地参加社会劳动。原有的占用他人自由时间,剥削他人剩余劳动时间的现象将会消失,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0〕
当然,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从近期目标向终极目标不断递进。我们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打破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垄断,消除数字鸿沟、数字赤字,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中实现共产主义目标。
(二)革命对象:限制并逐步消灭数字帝国主义
数字时代,拥有雄厚资本的数字资本家不但可以在生产领域中剥削劳动者,而且在日常消费和社会交往中掌握着国家上层建筑,联合成压迫广大数字穷人的数字帝国主义。面对数字资本与国家公权力日益交融的事实,“无产阶级不应当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那种已经落后的政策去反对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41〕而是应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彻底消除数字帝国主义。
首先,限制并逐步消灭数字私有制。数字资本通过数字平台从微观层面控制社会大众的行为、思想和社会交往活动,形成资本对微观个体的滴灌渗透,长此以往广大无产阶级自然沦为资本的“玩物”。〔42〕在恩格斯看来,“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43〕即一切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都是社会革命的对象。数字时代,数字私有制表现为数字数据等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依赖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积累起来的私人数字资本。要限制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数字无产阶级要主动提高数字保护意识,保护数字隐私,维护数字痕迹,争取数字信息要素在社会分配中的权益。要加大对掌握社会数字信息企业的监管,尤其是加强对数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行为的监督,引导数字企业共享数字生产资料,最终实现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要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数字技术的开发依赖大量数字资本要素的投入,在保证资本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支持引导数字资本有序扩张,限制其无序扩张,是数字帝国主义早期阶段应当采取的和平策略。应当指出的是,消灭数字私有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建立数字公有制条件的成熟,才有可能最终消灭数字私有制。
其次,限制并消灭数字资本—国家复合体。数字时代,数字平台的管理制度越发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管理制度,同时社会给予管理者的公权力越发被赋予数字企业,双向赋权的数字企业与国家公权力构成的资本—国家复合体,〔44〕是数字时代社会革命的对象。掌握人类日常数据的数字—国家复合体与广大工人阶级的矛盾随着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日益加深。当这种国家化的资本剥削行为随着数字资本渗透率的提高变得日益剧烈,双方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只能由无产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推翻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媾和的资本—国家复合体。需要注意,消灭数字资本与国家的复合体是要消灭剥削者(资本家)及其剥削职能,对于其中有利于无产阶级自由发展,有利于社会公众福利的部分要予以保留和加强。
(三)革命主体:以数字无产阶级的联合作为革命的主力军
数字时代,被数字资本殖民、剥削和奴役的数字无产阶级构成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它既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剥削和奴役的“数字穷人”,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被剥削和奴役的“数字穷人”,两者的总和构成世界范围内抵抗数字帝国主义的革命主体。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我们既不能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深度异化而将无产阶级神话,也不能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新穷人而将无产阶级抛弃”,〔45〕而是要继续提升数字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将革命意识转化为自觉的革命行动。
首先,提升数字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培育革命精神。人类经历了前现代社会关系下的家庭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经济人,到如今数字关系下的数字人阶段,已无可能让高速运转的数字社会停止运转,能够做的就是摆脱前数字时代理性人的桎梏,重塑新的数字时代生存方式,造就数字时代的新人类。这一转变过程离不开对人的持续教育:必须坚持终身教育理念,加强人民群众的数字素养教育,推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数字专业技能的结合,努力培育出既能掌握先进数字技术,又有崇高革命理想的社会革命接班人;必须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打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为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提高全社会数字化水平;必须鼓励知识型劳动,培育无产阶级数字劳动能力,构建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共享的数字社会形态。
其次,促进数字无产阶级的全球联合。马克思主张,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必须组织起联合的“革命无产阶级”。〔46〕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加强国际间数字无产阶级的联合。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不仅是“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47〕国际无产阶级要抓住数字帝国主义内外的一切“缺口”和“导火索”,以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于全体劳动群众的结盟战胜数字帝国主义。联合国正在制定的《全球数字契约》围绕连接所有人、避免互联网碎片化、保护数据、网络空间人权、误导性和歧视性内容问责、人工智能监管、数字公域七大板块,构建“所有人共享开放、自由和安全的数字未来”,将有效加强无产阶级的数字联合,为消灭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提供有益的指导。
(四)革命领导权: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推进数字时代的世界革命要遵循党性原则。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8〕数字时代的社会革命也概莫能外,只有坚持党对数字时代社会革命的领导,才能在数字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下获得国际话语权,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牢牢掌握数字技术的领导权。数字时代,掌握科技革命的领导权是引领世界革命的关键力量。首先,坚持“党管数据”的理念。数据是构建数字社会的基石,党管数据意味着党要在数据生产、存储、分析、应用的全流程中发挥规划、架构、监督、运维的职能,确保数据成果为人民服务。其次,无产阶级政党要发挥宏观指导、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的作用,在领导物理空间的社会革命同时,尤其需要注重在虚拟空间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诈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再次,要协调各方,助力重大科技任务攻关,抢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空间发展制高点。以中国为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加强党在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着力加强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八大重点领域的工作任务,充分展现了党在重大科技攻关中的领导作用。最后,无产阶级政党要积极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相互连接的快车道,积极参与、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重点布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领导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创新。
加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消解数字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图谋。发达国家共产党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必须制定联合的策略并实施统一的行动。增强无产阶级政党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挑战的能力本领。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投资、金融、能源领域掌握他国战略资源命脉,拉拢、腐蚀、贿赂他国政府要员刺探核心机密,操控媒体、互联网发动舆论攻势等方式长期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势必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增强识别、抵御、反击数字帝国主义的技术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军事能力,在数字革命的各条战线应对数字资本的侵袭。
中国作为新兴数字大国,应当发挥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从世界革命趋势看,数字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受到数字帝国主义压迫和打压最重的国家,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各压迫民族”的代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联合起全世界的数字无产阶级,成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筹划组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积极参与到互联网国际标准制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为世界互联网公共治理,实现数字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出巨大作用,这充分证明,加强国际间政党合作交流可有效统一起无产阶级的行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数字秩序。〔49〕
(五)革命方式:阶级斗争与和平治理相结合
首先,不放弃暴力手段消除资本—国家的联合。马克思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0〕数字技术本身所蕴含的暴力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所运用的,对此加强数字技术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帮助无产阶级掌握数字核心技术,打破数字企业背后的资产阶级垄断,“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1〕是无产阶级战胜数字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其次,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2〕面对控制力日趋强大的数字帝国主义,广大无产阶级不能将自己的战斗限定于局部的经济抗争中,应对整个经济特权阶级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完善数据存储保密机制、数字平台监管机制、数据算法非歧视机制、数字劳动保护机制等,确保数据公权力始终掌握在广大无产阶级手中,彻底破坏隐藏在数字设备和数字企业背后的资本—国家力量的媾和。
数字时代,应积极采用和平治理的方式。恩格斯认为:“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硬的,还是看起来最温和的。”〔53〕只有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际遇选择适合的策略,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首先,科学精准治理数字资本,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加强数字治理的需要,又是遏制数字垄断的关键。这既涉及法律制度规范,又涉及行业标准制定,只有有效规制和约束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出台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有效消除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其次,采用符合数字时代的斗争手段。可以通过开拓数字空间的斗争、加强对数据隐私的保护、监控企业的数字获取权限等手段,突破传统手段的思维束缚,积极拥抱新手段和新办法,防止反抗数字帝国主义垄断过程中出现革命教条主义。再次,加强对数字垄断行为的日常监督。数字帝国主义日新月异,各种垄断手段层出不穷。对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与数字资本垄断行径的斗争,围绕数字资本的数据垄断、平台垄断、劳动垄断、技术垄断,开展数字反垄断调查和惩戒,争取公平竞争、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力求反垄断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注释:
〔1〕李江静:《帝国主义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0页。
〔4〕〔4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9、6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6页。
〔6〕〔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7〕〔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8〕〔13〕〔14〕〔15〕〔39〕〔48〕〔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194、207、160、435、228、159页。
〔9〕〔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861页。
〔10〕〔美〕迈克尔·奎特:《数字殖民主义:美帝国与全球南方的新帝国主义》,顾海燕译,《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
〔11〕〔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页。
〔12〕《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6〕〔25〕〔26〕〔36〕〔40〕〔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44、44、591-592、53、134页。
〔17〕〔18〕〔38〕〔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590、689、679页。
〔19〕刘皓琰:《云帝国:一个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基于对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解读》,《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0〕侯惠勤:《真正的社会革命必然是意识形态革命——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七十周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21〕〔37〕〔52〕〔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5、588、106、579页。
〔22〕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23〕〔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1页。
〔28〕孙伟平:《智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29〕常江、田浩:《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数字文化批判》,《新闻界》2020年第2期。
〔30〕管星淼、秦兴方:《数据要素的双重属性及其交互效应》,《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8期。
〔31〕《2022年全球及各个国家、地区互联网用户数量,互联网用户占比、上网时长及上网原因分析》,智研咨询,https://www.chyxx.com/industry/1106494.html。
〔32〕数据来源:联合国劳动组织,https://www.ilo.org/shinyapps/bulkexplorer55/?lang=en&segment=indicator&id=HOW_TEMP_SEX_ECO_NB_A&ref_area=USA。
〔33〕〔3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字经济报告2021》,https://www.suibe.edu.cn/gfhy/2021/1014/c12038a141094/page.htm?eqid=ad59cca2001ee7fa0000000564904b64。
〔34〕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P020221207397428021671.pdf。
〔42〕蔡万焕、乔成治:《大数据、数字化与控制: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财经》2022年第6期。
〔44〕Wier T.G.,“The Megacorp and American Capitalism:Eichner’s Theory and Munkir’s Analysis”,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1,28(1),pp.119-129.
〔45〕巩永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形塑——当代西方左翼主体理论的样式、困境及矫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
〔47〕《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49〕陈家喜、张基宏:《中国共产党与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经验》,《光明日报》2016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