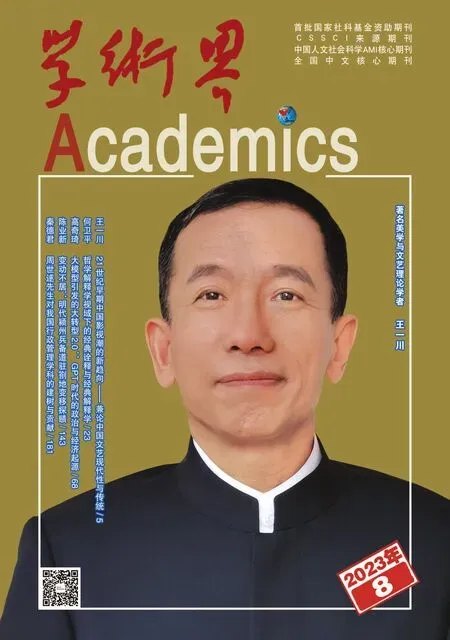创造力的社会文化哲学研究与创新观的“海变”〔*〕
高新民
(华中师范大学 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现当代创造力研究和关于创造力的观念或创新观(idea of creativity)由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社会文化哲学和系谱学分析等多学科的介入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用德国知名社会学家和文化哲学家雷克维茨(A.Reckwitz)所说的“海变”(sea change)〔1〕加以形容亦不为过,而且耐人寻味。其主要表现是,传统创新观的重要错漏和深层次问题不断被暴露,离经叛道的创新观纷纷涌现。根据新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创新观,传统的把创造力看作是人类独有现象、人之为人根本标志的观点,犯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碳法西斯主义的错误,因为它无视非人类创造力如进化创造力、生态创造力、人工智能创造力等的客观存在。根据以具身论、延展论等为中心的情境主义创新观,传统的创新观有这样的传统,即在研究人的创造力时,把目光锁定在个体的人之内,以为创造力是发生于个体的人之内的纯粹的精神现象或心理能力,纯属私人的自我表现。根据新的外在主义、反内在主义的创新观,这犯了内在主义、个体主义的错误。因为创造力作为心理能力或自然潜能是“假象”,〔2〕充其量是创造力的局部特征,除此之外还有具身、延展、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等构成和特征。社会文化哲学的创造力理论和计算创造力理论走得更远,认为传统的创新观只看到了创造力的自然性、内在性和个体性等方面,而没有同时看到它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究竟该怎样看待这些在传统观点中新发现的所谓错漏和问题?怎样看待新旧创新观的冲突和论争?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考察社会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从其特有的角度展开的创造力和创新观研究,特别是弗罗里达(R.Florida)、雷克维茨等人在创新观上的创造性建树,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创造力哲学特别是本体论和社会文化哲学的思考。
一、现时代创造力的社会文化本质与“制度”维面
从语言哲学角度看,“创造力”或“创新能力”至少有两种用法和指称:一是指每个人天生具有的作为潜能、心理属性的求新、生新、识新能力;二是指现实发生着的或已实现了的创造力,如科学家正在从事的创造性劳动和像爱因斯坦等人已完成的改变了世界思想面貌的创新过程。第一种创造力由于没有现实发生,因此就其存在方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内在个体性现象(当然从发生学上说,它得益于过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因此必然有起源上的情境主义性质)。第二种创造力由于必须以领域知识、专家团队、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作为它现实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一定具有延展性、超个体性、社会文化性,用情境主义术语说,一定是宽的(超越于皮肤这样的窄界限)。现在学界以及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后一种创造力。由于它有上述宽性质,因此就有可能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对象。由于各种宽因素是这种创造力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只有仰仗多学科的协力攻关,其本质和机制的全面揭示才有可能。由于这种创造力有社会文化的条件和构成,而社会文化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变化的,因此创造力与社会文化一定具有相互塑造的关系,创造力一定会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特点而有不同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及特点。
根据社会文化哲学对创造力发生和发展史的研究,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现当代创造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审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力的存在方式、形态和面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如突破原先起作用的科技、艺术、物质生产等狭窄领域势如破竹地涌进了人类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后物质主义中产阶级的文化逻辑之中,使所有这些领域都按创造力的原则、命令重构或重组。雷克维茨说:“创造力已成了西方社会的关键组织原则。”〔3〕另外,创新在以前主要是精英们自我表现的方式,而现在却有了社会取向的特点,如重塑大城市的建筑空间,帮助城市转型升级,帮助建立新的文化机构和营造吸引人的氛围等。由于有创造力的把关,城市不再仅履行提供工作和生活空间的功能,而追求永恒的审美上的自我创新,力图成为创新城市。总之,当今的创造力的出场方式奇妙无比,已被公认是社会和个人的不可避免、普遍有效的模型和行动方案,甚至显现出这样的、以前不可想象的二元性,即每个人、每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既希望、期盼创新,又必须或不得不创新”。〔4〕质言之,创造力已被提升为强制性社会秩序,固化为各种社会制度。正是看到这些,雷克维茨借鉴并改造福柯的“制度”或“体制”概念,将其作为揭示和说明新时代创造力构成、机制和本质特点以及建构新的创新观的理论基础。
对福柯所说的“制度”(dispositif)一词,常见的理解和翻译是“装置”或“设备”(apparatus)。雷克维茨认为,这样的理解让人觉得它是一种机械性的、不变的东西,因此没有抓住它的实质,必须重新阐释。再者,将它移植到创造力语境下,必须作适当改铸。这里,我们根据雷克维茨的重新阐释和赋义把它译为“制度”或“体制”。从渊源上说,该词是福柯在对有欲望的人及其性经验和观念作系谱学分析时创立的一个概念。雷克维茨承认,将它搬到创造力语境下作为关键词使用受到了福柯的影响。但雷克维茨同时强调,他只是借用了这一概念以及福柯的系谱学方法,充其量吸收了福柯这样的思想,即审美是取代现代性制度的一种力量。在其他方面,雷克维茨完全另起炉灶了。这是因为,福柯在讨论“制度”时关注的是基督教的性经验史,而雷克维茨则是要用制度来说明创造力的被遗忘的本体论地位、存在方式和本质。〔5〕众所周知,福柯开创并重视系谱分析,而创立dispoitif一词在福柯那里则是完成这种分析的一个基础和工具。该词的字面意义有“设备”“机器”“建构”和“装备”“制度”等。在福柯的系谱分析中,指的是这样的制度、机构和机制,它们在社会系统内帮助加强和维持权力的运转。在福柯那里,制度不仅是一种机构,一种封闭的功能系统,而且是一种话语体系或一组价值和规范体系。它由分散的社会实践、话语、人工制品系统和各种主体性所组成的完整社会网络所构成,其内的这些方面通过知识秩序相互协调。大致说,制度有三大类构成因素,一是异质的构成元素,如(1)隐含着知识的实践和技术;(2)各种形式的话语体系、科学陈述、道德命题,想象和集体的问题化或主体化;(3)人工制品,如工具、建筑、媒体技术、车辆等;(4)主体的形式,塑造人的方式,人让自己的能力、感性、愿望等适应制度的方式,如决策、法律、政策、制度。二是这些元素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三是它们组织起来的外显形式和特定的作用、效果。这些东西的集合体就是制度。〔6〕
经雷克维茨的重新阐释,制度有一般和特殊之别。特殊的制度是特定领域如政治、经济和创造力中的制度,一般的制度是有这样独特而重要功能的系统,它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变化着的应急情境作出反应,因此是一种独特的有制约、约束力量的机构、制度。制度的文化逻辑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特定社会和个体得以生存的条件也与它有关。它同时还是一种革命的力量,能积极应对别的制度、生活方式、话语体系的冲击。不同的领域可有不同的制度,但一定同时有其共同性,例如制度都有把不同的片断关联起来的作用,有把分立的要素排列或组织成新秩序的能力。雷克维茨在这里的创新还表现在,强调在对制度展开分析时,应同时关注社会制度的社会情感特征,这是因为制度也有自己的情感结构。制度要能为群体认可和接受,除了要有纯粹的支配作用之外,还要有自己的持久的情感刺激。由这些所决定,制度的内部尽管有异质性,但整体上是协调的。在他看来,创造力符合制度的所有标准,因此可以说,创造力事实上以制度的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就形式而言,创造力制度包含这样的实践过程和情绪,它们是在社会领域中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的,然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并相互渗透。创造力已成了一种话语体系、一组价值和规范体系,有知识、话语体系、人工制品和主体性等构成因素。它还包含各种技术,从创造性的工作过程到私人决策,从心理学的话语到创新人才的叙事的想象的概念。特别是,创造力已跃居多元化社会形式的顶点,成了社会文化运动的引擎。〔7〕
由于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能对变化着的应急情境作出反应,是活的而非机械的、死的东西,因此创造力也一定是变化的。既然如此,要揭示创造力的发生发展进程,就必须有对制度的系谱学分析。系谱分析不同于传统的追溯历史进程的方式,后者的特点在于,通过发现在前、逻辑上独立的因果起源来解释历史现象。而系谱分析则不同,以问题为例,系谱分析用“怎样”的问题替代了“为什么”的问题,如它有这样的追问,即我们该怎样追溯文化模式在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突现及传播?雷克维茨试图用改造过的系谱分析方案分析创造力制度。从发生学上说,如果从现在返回过去,如从20世纪一直回溯到18世纪后期,那么如此追溯可以让人看到,创造力同福柯所说的“性”一样,是一种谜。这谜中包含的困惑是,创造力怎样被公认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创造力的制度是怎样在实践和话语的异质复合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它如何发展出来,留待后面来揭示,这里先追溯它的发展史。根据雷克维茨的梳理,创造力制度在现当代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第一,准备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话语、实践、人造物和各种主体性形式开始聚集。这些因素都是作为社会模式的创造力的长期准备因素而出现的。第二,形成阶段,1900—1960年代,其特点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实践,新颖性和新产品随之激增。第三阶段是1960—1970年代。由于制度的因素被整合了,因此便伴随着危机的发生,如反文化、年轻人文化和各种批判、抵制运动。第四阶段是1980年代以后的支配地位的取得阶段。随着创新产业和创新心理力量的壮大,以及明星体系和创新城市的发展,创造力制度逐渐跃居主导地位。特别是,城市空间和城市政治的发展及转型为创造力制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80年代后,创造力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城市创造力的政治规划之上。它已成了一种系统,这一系统能动用自己的资源协调一致地运转,并果断地抛弃无用的东西。
经过上述进化,创造力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普遍主义倾向。在西方,18世纪以后就开始了创造力的普世运动,其理论基础是人人都是原创者这样的命题。根据这一命题,人人天生都有原创能力,当然有些人没有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教育和环境所使然,既然如此,让人人成为创造者的出路就是教育。〔8〕现当代社会已稳固地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和制度,即它被看作是最有力量、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每个角度,创新既是命令、强制,又是愿望、期望。每个人、每个组织既有创新的希翼、冲动,又有创新的压力。这种状况是由社会文化力量所塑造和内化的。雷克维茨说:“创造力制度无处不在,这根源于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正是这一力量使它难以找到匹敌者。”〔9〕
由于创造力制度拥有看不见的霸权地位,因此社会秩序只有以它为根据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制度让创造力成了普遍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成了能量的集散点。不仅如此,由于出现了创造力制度,因此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即表现为创新的生活方式。它不再是少数人的私生活,而是大众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制度要求每个人都参与到创新之中。创造力制度由于与审美生活相结合,因此其核心同时包含有情感和感性的因素。而这又让它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因为情感是现代性所排斥、压抑的东西,现代主义坚持理性主义和去审美化原则,必然导致情感的缺失这一问题。而创造力制度是有望弥补这一缺失的,由于其核心包含有情感因素,因此就有望解决现代性缺乏动机和动力的问题。
在创造力制度内部,注意力极为重要,其表现是,它是创造力制度中一项重要调节机制。这是因为,创造力不再是个人或天才内在的隐秘能力,而成了通过多种多样的刺激展开的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这样一来,社会和个人的注意力便有两面性,一方面很专注、很专心,即关注创新、喜新厌旧、盯着新、热爱新,以新为最高价值。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在专注不同的刺激、符号及其组合,让它们表现在知觉中,并把它们加工成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创造性的生产又离不开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一般是围绕着新颖性运转的,而新颖性经常从一个载体移至另一载体。相应地,注意力就会分散于不同的对象。被观察者知觉为新的东西会受到优先关注,并较长时间存在于注意力之中,更有机会产生审美效果。市场和学术上的竞争,其实是注意力的竞争,即把受众、消费者的注意力争取到自己手上。
创造力及其制度塑造了现当代社会,并将使之不停变化。它们塑造的社会和个人有这样的结构特征,即对突出、张扬创造力的强制。在创造力制度内,创造力不仅仅是自愿的、愉快的行动,而且是社会内在固有的一种愿望、规范和强制。根据这种强制,创造力是每个人天经地义要做的事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创造力既是人的工作的需要,也是人际关系的需要。其必要性还在于,富于创新的自我要解释自己,解释叙事同一性和传记上的、关联于创新成就的成功,都必须诉诸创造力。对每个人的创新强制不是通过国家机器的镇压之类的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氛围、舆论、潜规则之类无形的手完成的,例如有这样一种社会认同标准,即只有有创造力,有创新成就,人才有地位,否则就会被社会边缘化,被降级。因此在创造力面前也有一种优胜劣汰。一个人不发挥创造力,没有相应成就,就会被淘汰。人不仅需要与他人比拼创造力,还要与过去的自己比,即是说,每个人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过去的行为,比过去更富有创造力。在创造力制度下,创造力及其成就成了衡量人的社会地位、荣誉、经济状态的标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甚至有这样的氛围,即“没有创新成就会被认为有人格缺陷”, “低级的创造力意味着低级的个体性和真实性”。〔10〕
当然,作为制度的创造力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绝对普世,而有其对立面和内部冲突,其作用也不都是积极的。雷克维茨认为,创造力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开始于处在艺术边缘的浪漫主义。从那以后,创造力开始渗透到了全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力内部经常出现制度化与反制度化的冲突、张力。由于资本主义需要创造力,便逐渐将创造力的需要制度化,但坚持创造力需要自由、自主的人则反抗这种制度,于是便出现了创造力的反制度化愿望与创造力的制度化需要之间的冲突。创造力制度当然有其负面影响,如有一种观点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抑郁、焦虑、恐惧和上瘾等不健康心理的急剧增加与创造力制度营造的创新压力是有密切关系的。研究表明,心理疾病会让艺术家更有创造力,疾病越严重,创造力越强,或者创造力会让人得精神病,创造力越强的人,其害病的可能性越大。尽管这需要被进一步验证,但创造力制度的这种辩证性至少有这样的警醒意义,即现在是严肃认真地看待和思考创造力这种设置、机制的本质和作用的时候了。因为创造力太复杂了,其观察和研究不仅有认知、政治、经济、文化维度,而且还有情感维度。
二、创造力的“爱多斯”特点与创造力本身的创造
用“制度”来描述揭示创造力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显然比过去把它描述为人身上的一种属性或能力前进了一大步,更靠近它的复杂的、超越性的、非个体主义的存在状态和内隐的秘密,但在一些人看来仍有遗漏,未能反映现时代创造力的全貌和深层本质。尽管雷克维茨在重新规定福柯的制度概念时强调要抛弃过去理解中赋予它的机械的、不变的、形而下的装置、设备之类的赋义,但雷克维茨重新阐释的制度概念仍有重制度、机构、构架之类形而下的东西的问题,没有反映创造力的更深层、抽象的精神文化和形而上的存在方式和本质。为解决这一问题,弗罗里达引进并改铸了“爱多斯”一词。
弗罗里达认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与其说是技术方面的,不如说是文化方面的。最近几十年文化方面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创造力爱多斯”(ethos)的突现和迅猛传播。“ethos”的意义太多、太复杂,如包含气质、精神特质、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社会思潮、潮流和社会风气等。由于在中文里面没有一个词能同时传递这些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五不翻”方法,将它音译过来。在理解时,最好将这个译语作为一个为表述新发现的所指而在语言史上新造的一个词看待。就这个名对应的实或所指而言,只要我们不拘泥于经验科学中的借助仪器之类的方法去观察它、揭示它,而用我们现象学的意识、超然性的心去感受和体验它,特别是“返流全一”,由在社会文化中体验到的“用”去追溯其后的“体”,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社会文化中现实存在的创造力的确有爱多斯一词所说的时代精神、时尚、思潮、潮流、民族精神甚至世界精神等构成、特点及其统一体。如此看待创造力,创造力当然“旧貌换新颜”。其爱多斯的载体是“创新阶层”或“阶级”。这是社会分工中新生的、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特权群体。在这种变化中,创造力不再仅局限于个人的自我表现,而演变成了劳动界和职场的普遍的经济需求。〔11〕
雷克维茨不仅承认,应该用创造力爱多斯来补充创造力制度,而且进一步认为,由于创造力成了爱多斯,因此围绕它便产生了这样的新文化现象,即伴随着创造力的制度化,出现并迅猛发展着一种二元性,即一方面是人们迫切希望得到创造力,另一方面由于创造力成了时代精神、社会时尚、制度、最高价值等,因此人们必须有创造力,否则就会被淘汰,至少会被边缘化。换言之,创造力内部包含着这样的两种冲动和力量,一方面是个人对创造力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创造力带有压迫性的期望或命令。总之,创造力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时尚、潮流同时包含着想成为创造者和必须成为创造者两种精神或冲动。
由这些所决定,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创造力的一个深度文化是,创造力本身在自我创新,人们对创造力的关注不只是局限于人的活动、实践,而扩展到了与发明创造有关的组织和机构。它们必须不断地重新设计,不断生成新产品,而要如此,又必须不断创新内部结构和程序。由其深度文化所决定,当代社会无形地形成了对每个人的创新压力,好像在向每个人发布命令:你必须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而就每个人自身而言,可能是由本能所使然,每个人都有创新的内在冲动。〔12〕这两种力量的双管齐下,已超越了工作、组织和职业的界限,渗透到了人的私人生活背后的文化逻辑之中。反过来,这种文化逻辑又不断改变着个体的创新形式和个体塑造自己主体性的形式。这种文化中的个体不仅源源不断地创造新产品,而且与时俱进地创造新的自我。这就是罗蒂(R.Rorty)所说的“自创新”文化。〔13〕
创造力组织社会的作用的另一表现是城市的转型,即在更大城市中重塑建筑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大城市都在以这种方式重塑,如改造整个街区、建立新文化机构,营造有吸引力的氛围,进而出现了所谓的“有创造力的城市”或“创新城市”。创新城市不再只是满足于提供劳动和生活的空间,而更加注重追求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功能。现在的城市都在追求成为“有创造力的城市”。
由于创造力有爱多斯的存在方式,因此以前的边缘文化、亚文化思潮现在开始了对话语权的争夺,不仅如此,以前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充满审美诉求的创造性理想也渗透到了现当代文化的血脉之中,制约着人们的工作、消费和交往方式,例如“希望创新”和“必须创新”这样的力量已开始融为一体了,并超出了工作和消费领域,进入了社会和个人的整体结构之中。已出现了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即以前被边缘化的创造力观念已被提升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并逐渐固化到各种社会机构之中。这一制度已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它们不得不按照创新的需求来进行重组。〔14〕这不是创造力观念的历史,而是对这样的矛盾过程的重构,通过它,技术和话语同时出现在了不同的社会领域。
创造力在现当代社会中的这种渗透到结构中心的地位、状况和特点,可被称作社会的创造力情绪。它是创造力的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复合的情绪,值得从文化角度反思。其作用在于,让我们渴望创造力,让我们用适当方法来训练和提高创造力,让每个人迫不及待地成为创新人才。它不仅反映了创新的发生这样的事实,而且推动了作为审美事件的新颖性在许多领域的动态生成和广泛接受。它促成了新的创新实践和技术,促使人们关注审美新颖性和创新成就。〔15〕
创造力不断创新自身的突出表现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出了新的创造力,如人工智能系统表现的创造力、“数字创造力”,其最突出的例子是ChatGPT。它们是人造工具上凝结的创造力,是创造力的新的存在方式。这可看作是社会和文化中爆发的改变世界的创造力革命。〔16〕其表现是,知识都汇聚于媒体之上,人通过数字媒体创作和表现自己,存钱、转账等都可在手机上完成,手机成了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讲授、教学可在网上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翻译、写作可以完全在电脑上完成,等等。总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提供的是一种“声音”,通过它,任何人都可把自己创造的东西传递给其他人,将以前没有的发明创新大众化。这场文化运动或飓风的风眼是数字技术,它们能让我们用复杂的工具来创造、丰富媒体内容,来分享、讨论和传播思想情感。不仅如此,新的创造性技术还在为下一波文化运动准备地基,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去设计、创造未来的世界,而创造性技术就是这样的条件,它们将激励和支持这样的创造。〔17〕
创造力的发挥,数字创造力的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是,人人都成了创造者,例如借助多媒体和互联网,每个人都“自己动手”(do it yourself)从事创造。这种创造促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all to all)的交流形式和格局,培育着自己动手从事创造的新文化。
三、“审美化”与创造力的审美诉求
改造、重构过的“制度”和“爱多斯”等范畴把现当代社会中的创造力的存在方式和本质囊括无余了吗?进一步的批判性审视的结论是否定的,雷克维茨的看法也是这样。通过对创造力的进一步解剖,他认识到,现时代的创造力是具有“审美化”特点的创造力。由之所决定,这种创造力生成的新颖性不仅能满足人的认识和发明的需要,也同时具有被体验、欣赏的审美作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充满审美诉求的创造力成了现代社会的关键组织原则。〔18〕借助它的这种组织作用,资本主义从工业、市场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审美资本主义”。其基础是超出了劳动者通常所完成的活动的各种劳动形式,如创新阶层的劳动。这些劳动的特点是能生成新的产品,包括文本、图像、沟通、程序、审美对象、游戏等。消费文化催生了对这些有审美价值的创新产品的欲望,随之而来的是创造力产业的生成和发展。在创造力经济中,已出现了专业的创新职业,他们不同于原先狭隘的职业。因此,要全面、深刻把握现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中的创造力,就必须同时关注审美化及其与创造力的关系,因为创造力内在包含和渗透着审美诉求。
创造力的充满审美诉求的创造性理想,以及在现当代社会中的这种渗透到结构中心的地位、状况和特点,如前所述,可被称作社会的创造力情绪。它促成了新的创新实践和技术,促使人们关注审美新颖性和创新成就。雷克维茨将这样的创新实践、技术以及人们对审美新颖性的关注及成就称作审美化。要理解审美化,得从作为形容词的“审美的”一词说起。它的意思很模糊,指的主要是一般的感觉、知觉。从创造力哲学的角度看,可把它看作是引起审美化的东西。它有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促成了一个跨越感性、想象力、创造力、情感、情趣、无目的性、崇高和美丽的变化多端的语义域。从社会学上看,这个概念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凝结在人类行为中的感性的复杂性。它的多层次性质让它与社会、文化历史具有了特殊的关联性。在雷克维茨看来,后现代社会可看作是审美化社会。在这里,审美化类似于强化、合理化、差异化和个体化,指的是塑造社会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与合理化等一道促成了现代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它有审美性或美学特点。就此而言,审美化以审美为前提条件。审美化意味着以牺牲非审美化为代价来扩大和强化审美化。就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审美化与去审美化的矛盾运动促成了现代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有合理化倾向,正是它促成了去审美化,另一方面,相反的力量重新将审美化注入社会之中。
在现代社会,尽管审美化与合理化有对立之势,但它们不仅没法完全克服对方,反倒必须与对方结合在一起,而且客观上,它们共同推进着社会的进步。当然,主导现代性的是合理化和去审美化,但它们又为审美化的异质形式所伴随,并在对抗中与之调和,共同发挥作用。
就审美创造力、审美化与“创造力制度”的关系而言,它们直接关联,但没有同一关系。因为审美实践和审美化过程存在于现代性之中,当然在别的地方也可看到,同时有不同表现形式和走向,而创造力制度是这种审美化的一种特定形式。这种制度将审美化与特定的非审美的形式或实践的情绪结合起来,将一种由更具体的方面主导的结构强加到这些形式之上,就此而言,审美可理解为这样一种更广泛的情境,创造力制度是它的一种具体形式。其特殊性和作用在于,通过关注新审美事件的产生和认可来强化审美化过程。这样一来,现代社会一开始就被组织成能在政治、技术和美学中增加新颖性的东西。两者的差别在于,创造力制度使审美向新的方向发展,同时又使新的制度向审美方式发展,进而,它就成了审美和追求新颖的社会制度的交汇点。从根源上说,创造力制度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审美化、审美艺术运动、传媒革命、资本主义兴起、主体性的突现,不仅如此,这些方面还成了它的构成因素。以前分散的、边缘化的审美文化碎片在创造力制度中得到了巩固,授予它们以普遍的效力和影响力。当然也必须承认,现代社会也有不属于这种制度的一套审美实践,如审美残余文化、历史遗迹等。
创造力制度建立起来后,也有自己的反作用,如帮助审美化形式建构和改进。其表现在于,审美实践和审美化过程正是按创造力的原则,即求新和生新去发挥作用的。由于审美实践和审美化存在着无数可能的形式和内容,因此创造力情绪至少可起两种作用,一是它致力于追求审美的动态新颖性;二是它将审美新颖性归因于作者,认为他创造出了新的实在。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力的制度确保了这种追求的实现,因此可以说,创造力制度成了审美化过程和新社会制度的交汇点。〔19〕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也有自己的情感结构。它要能为群体认可和接受,除了要有纯粹的支配作用之外,还要有一种文化想象,有自己的情感。它包含有这样的实践过程和情绪,它们是在社会领域中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的,然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并相互渗透。在这种制度下,创造力被推举到了多元化社会形式之内的文化运动的顶点。这种创造力不再是过去只能完成理论、技术之发明创造的力量,而同时包含有审美创新等大量元素。〔20〕
由于创造力有这样的复杂性,因此由创造力塑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成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而且成了审美经济。所谓审美经济即是具有强烈审美倾向的经济,注重美学上的创新,试图让经济指向永久的新颖性、创新和审美效应。审美经济与“创新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密切相关。创新产业一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说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注重创新的特点。自从福特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后,就有设法产生符号和感性印象而非实物的经济实践。这种符号经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和贵族的奢侈文化。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符号和感性经济在开始时被边缘化了,而后来的审美经济则热衷于发展这样的东西,如时尚、广告和设计。〔21〕从审美经济的发展学可以看出,它一直遵循这样的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创造力制度的特点,在这里,生新的社会制度与审美化过程交织在一起。生新的制度不需以审美为导向,就像审美化过程不需以生新为导向一样。而创造力制度构成了两个过程的交汇点。审美经济的起源以典范的方式说明了这种交叉是如何发生的。
雷克维茨注意到,创造力审美化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审美过度的问题。这首先是因为,审美化与创造力制度尽管相互依存、互利互惠,但有时有极端化的问题,其表现是,在创造力制度的促进下,审美化会出现这样的过度化或扩张问题,如无限制地推广到广泛的社会领域。促成这种过度还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一是对创造力定向的情感冲动,这种冲动对现代主义的客观化和市场化有补偿作用;二是审美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化、技术调解作用密切结合。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审美便不停地向以前与审美无关的领域泛滥,进而消解着现代性的威胁。以前,审美生活在理性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现在,由于有了创造力制度的支持,情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然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问题。
由于有这样的问题,因此审美化过程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一是艺术批评,它强调,仅关注社会实践所实现的审美价值不足以对社会实践作出全面评价。这一批评以前只触及现代性的表皮,现在深入到了创造力制度的要害。二是社会批评,它根据社会正义来评价社会实践。根据这一关于审美化的批评,社会现象很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审美。因此这一批评有对抗审美过度的作用。尽管如此,从审美的角度研究创造力毕竟开辟了一种切入创造力研究的新的维度,它至少有助于我们看到创造力制度中的审美过程对社会结构的真实的影响,看到创造力在现代社会存在方式和本质的复杂性。雷克维茨的下述评价尽管有溢美之嫌,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说:“它们是当代社会的看似不受控制的变化的发动机。”〔22〕
四、创造力的本体论发现与进一步的社会文化哲学思考
创造力或创新能力肯定有本体论地位,既然如此,就一定有本体论问题,如有哪些存在样式?其存在程度如何?是第一性的存在还是高阶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等等。传统内在主义和个体主义把创造力作为一种能力,尽管抓住了创造力的部分存在构成及特点,但又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甚至像盲人摸象一样遗漏太多,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同时看到创造力的超越内在性和个体性的“宽”构成及其本质,特别是没有看到社会文化创造力哲学所强调的社会文化的构成和存在方式。就此而言,我们上面考察过的浸透着后现代精神的社会文化哲学的创造力研究及其创新观尽管有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即重视非个体性而忽视了个体性、内在性的片面性,但由于建立在扎实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和系谱学分析之上,同时借鉴了形而上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特别是强调通过感受、体验创造力施加于我们每个人的作用来接近创造力的本体论,进而看到了创造力的“制度”和“爱多斯”之类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看到了创造力变成一部分人(特别是“创新阶级”)的生活方式,变成一种像紧箍咒一样的制度这样的现实,因此必须承认,这一研究对创造力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有积极的贡献。它有理有据地暴露了过去创新观在创造力认知上的大量本体论遗漏,有新的本体论发现,如发现了创造力不只是心理能力,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现象,里面有“制度”“爱多斯”和审美诉求等构成和机制。当然,应同时承认的是,这类发现不是社会文化哲学一家的功劳,而同时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部门的共同成果。当然,社会文化哲学有自己的特殊发现,如制度、爱多斯和审美化的发现就是如此。
多学科的共同的本体论发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创造力中的确还有以前的心理学和哲学等遗忘了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构成、机制和本质。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创造力由于同时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超越于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的存在方式,因此其产生、存在和作用之发挥也一定以社会文化为其必要条件。这便为人们从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创造力提供了可能。例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明确强调,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心理学的创造力研究只关注创造力的个体差异而很少有对决定创造力的社会因素的专门研究这样的片面性。因为社会变量是影响创新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若没有这个维度的研究,是难以获得对创造力的全面认识的。从理论上说,要研究创造力,当然要关注动机变量,但动机变量的生成和起作用的方式是离不开社会变量的,因此只有同时关注社会变量及其对创造力的动机的限制,才能全面揭示创造力的机制。〔23〕扎加罗(N.Zagalo)等人的跨学科背景下的对创造力的文化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也有类似的意义。他们关心的创造力主要是数字时代创造力,他们把它称作“数字创造力”。这里的跨学科的幅度极大,因为这里涉及的学科同时包括计算机科学、哲学、心理学、工程学、艺术、语言学、游戏、多媒体等。不过,在具体实施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工程时,他们又更多地侧重于对数字创造力的文化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对创造力展开跨学科研究是数字时代向研究者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综合性知识的欠缺促使人们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新技术又要求在广泛的领域合作和探讨。〔24〕这一研究的本体论发现是,创造力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现象,而同时成了社会、文化、人文现象,创造力无处不在。在人们的心中,它们成了人类能摆脱“黑暗时代”的大救星,是拯救人类的力量,因此平地里多了许多神秘色彩。其次,它还发现了改变世界的创造力革命。〔25〕
尽管揭示创造力的社会文化存在方式和本质是众多研究的共同成果,但充满后现代情趣的社会文化哲学的创造力研究进路仍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强调通过感受、体验创造力施加于我们每个人的作用来接近创造力的本体论。再者,尽管对创造力制度的揭示像对审美化的论述一样有极端化问题,但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首先,这里应看到它是对居于现代社会中心的理性化和客观化所引起的异化经验的一种反应和纠偏,关于创新的追求享乐的审美文化模型是对根源于客观化倾向的动机缺乏的一种抗议。对异化经验的社会批判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对改变这种动机缺乏并没有什么作用,相比较而言,创造力制度则有其实实在在的作用。其次,创造力制度尽管与审美化有联系,甚至可看作是它的一个特殊的版本,但由于其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已有的审美过度的批评不一定适用于它。再次,创造力制度尽管主要表现为一种有强大力量的氛围、机制,一种文化制度和秩序,但在对创造力本身的探讨以及创新观的建构上也有自己的建树。这表现在,它批判、否定关于创造力的内在主义、个体主义模型,认为创造力不是局限于创新个体或群体内部的现象,而是一种情境性的、关系性的、更宏大和复杂的现象,例如一过程、一成果之被认为有创新性,既离不开创造者的作用,也离不开受众的参与和认可。由于有这样的复杂性,因此创造力就同时有普遍性或大众化与稀缺性或珍贵性的特点。一方面,人人都是创新者,因此创新无处不在;另一方面,由于创造力离不开受众,而受众要求它的成果具有稀有性,不然就不会接纳和青睐。由于它有取决于受众的变化莫测的兴趣、要求的一面,因此创造力作为一种需求比其他需要更加难以预测。然而,由于创造力保留了带有失败可能性的期望结构,因此有一致于现代社会加给人们的要求的一面。还要看到的是,创造力制度催生了一种创新的方式,即世俗创造力。这是一种不受受众约束,不服从比较和过度宣扬的创造力,不同于创造力的精英模型所说的创造力,不是专业的创新能力,没有文化中产阶级的支持,但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和网络中,并无缝隙地融入了社会的不受重视的地方。其形式很多,如即兴表现的创造力,实验试错中的创造力,个体行为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个体语义和叙事过程中的解释学网络所蕴涵的创造力,等等。
最重要的是,雷克维茨等人在纷繁复杂的创造力现象中剥离出的“创造力制度”“爱多斯”不是人为的捏造、猎奇,而是对现实世界,对变化莫测的文化,对本身发展着的创造力的本质结构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和独具匠心的揭示。因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着的西方,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创造力制度不仅客观存在着,制约着人们的心理、工作和生活,而且还呈强劲和稳定发展之势。其表现是,各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想象力都强烈地指向了创造性生产、自我创新和追求审美新颖性的永恒经验。〔26〕各种社会组织、结构在其他方面可能分歧很大,但在对这一制度的营造、保持和发展上却出奇的一致。由于有这样的制度,因此便有这样的突出的表现,如审美资本主义扎根于城市中心,技术特别是最近的数字技术发挥着它的调节机制,将感性的、情感的新颖性制度化,国家的大政方针将创新城市以及它对创新资源的利用看作是持续发展和未来前景的重要参数,自我的隐私文化以惊人的力量维持和推进着自我实现的表达模式。所有这些都使创新生活方式成了大众所羡慕和竭力追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前主要流行于西方,流行于少数精英阶层,现在在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并逐渐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开花。
要对创造力制度和爱多斯作出公正评价,要让其合理、健康发展,尽量放大其积极作用,消除至少减轻其负面效应,必须超越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评价范式和方法,创立新的、科学的评价标准。这里当然有多种选择,雷克维茨开出的诊断和处方是,要从审美的角度看问题,看到创造力制度中的审美过程对社会结构的真实的影响。他说:“它们是当代社会的看似不受控制的变化的发动机。”〔27〕这种选择当然有理由被判定为片面的、浪漫主义的,但不失为多种发展创造力制度的一种可能的方式。除此之外,无疑还有很多选择,当然这是留给承认创造力制度范式之合理性的人的工作。
创造力的上述带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社会文化哲学研究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两种对审美化过程的批评也适用于雷克维茨关于创造力制度的独创理论。一是艺术批评,它基于创造力的社会实践的实现审美价值的能力来评价它的社会实践,这一批评以前只触及现代性的表皮,现在深入到了创造力制度的要害。社会批评是根据社会正义来评价社会实践的。根据这一关于审美化的批评,社会现象很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审美。因此这一批评有对抗审美过度的作用。既然创造力制度与审美化、审美过度密不可分,因此对审美化等的批评也就是对创造力制度的批评。笔者认为,以创造力制度、爱多斯与审美化为核心内容的创新观有极端化、片面性错误,但基于前面对创造力的本体论的认识,我们又认为,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论在分析创造力时少了分析哲学的维度,这是其带有极端性和片面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创造力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实在上说,都带有规范性特点,例如作为“创造力”的语词有许多不同的用法和指称,它们在特定的规范下都有其合理性,“创造力”可指我们在社会文化中所感受到作为由创新主体、过程、社会文化、成果等因素构成的大系统的创造力,这种意义上的创造力的确有制度和爱多斯的特点和力量,但“创造力”还可指纯粹的创新能力或潜力,或指内在的发散思维、灵感爆发过程,或指闪现了创新的思想火花,等等,它们都是带有内在主义性质的存在或力量,因此就不一定有制度、爱多斯这类的存在方式和力量。
注释:
〔1〕〔2〕〔3〕〔4〕〔5〕〔7〕〔8〕〔9〕〔10〕〔12〕〔14〕〔15〕〔18〕〔19〕〔20〕〔21〕〔22〕〔26〕〔27〕A.Reckwitz,The Invention of Creativity:Modern Society and the Culture of the New,Trans by S.Black,Cambridge:Polity Press,2017,pp.11-13,14,10-11,10,32,33,52,212,228,11,13,13,11,32,33,109,237,237,237.
〔6〕M.Foucault,“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1977〕”,in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C.Gordon,Brighton:Harvester Press,1980,pp.194-228.
〔11〕R.Florida,The Rise of the G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Basic Book,2002,ch.1.
〔13〕R.Rorty,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6ff.
〔16〕〔17〕〔25〕N.Zagalo and P.Branco,“The Creative Revolution That Is Changing the World”,in N.Zagalo and P.Branco (eds.),Crea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London:Springer-Verlag,2015,pp.3,7,3.
〔23〕T.Amabile,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3,pp.127-170.
〔24〕N.Zagalo and P.Branco (eds.),Crea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London:Springer-Verlag,2015,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