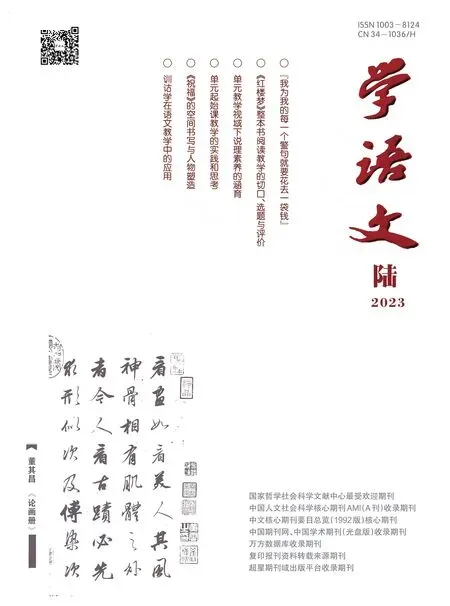《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切口、选题与评价
□ 俞晓红
经典常谈常新,亦常读常新。随着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整本书阅读”要求的推出,文学教育的历史再次选择了《红楼梦》。80年前,朱自清就明确提出,经典训练是中等教育的必要项目,“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1]1。“新课标”规定高中语文必修课8 学分须有1 学分修习“整本书阅读与研讨”,选择性必修和选修阶段不设学分,但要求“穿插在其他学习任务群中”,而明显涵括《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和“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两个任务群,又分别设置了2 学分[2]10。显而易见,高中语文教学如果漠视“新课标”、新理念、新高考,原地固守单篇课文阅读教学,拒绝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必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
指向高中生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语文教师的教学和指导不可或缺[3]。面对《红楼梦》这样一部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寻找科学的切口,谋划合适的选题,确定评价的维度,是很多语文教师所期盼的、也是教学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找好切入角度,提高阅读性价比
本文所谓“切口”,指的即是切入点、切入的角度。为什么要寻找切入点?从《红楼梦》第一回开始,依序翻阅,一直到第一百二十回,难道不是最直接、最本体的“整本书阅读”吗?的确,是有不少中学教师采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让学生“通读”《红楼梦》,也有学者积极回应并逐回解读成文。但从阅读实际看,仅让学生逐回阅读的“整本书通读”效果不佳。一是因为《红楼梦》艺术特征与众不同,相对于其他长篇名著,《红楼梦》故事纷繁,人物众多,含有多条主线、多层主题和复杂交错的网状结构,中学生初读不易把握小说的整体风貌;二是因为高中生阅读时间短缺,很多学生原本没有阅读名著的习惯,在多学科刷题程式的挤兑下,甚至连整本书通读一遍都成了奢望。
那么,如果以10回为一个单元,每周阅读一单元,12周完成整本书的通读,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阅读方法呢?相较于逐回推进的单篇阅读,这已接近于一种化零为整、集散为束的“群文阅读”法。这种选择已经兼顾了教师指导方略和学生阅读效率两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有限课时与完整阅读的矛盾;除前五回应该单独设一单元,其他章回皆可如是划分。但这样设计会带来另一种缺陷:它有可能会割裂原著本身内在的叙事逻辑,打断故事描写的连续性和形象塑造的贯通性,因为小说故事的进程与章回序数的递进并不一定严格对应。例如将第六回到第十五回作为一个阅读单元,这一部分基本上叙述的是“可卿之死”故事,但与之密切相关的“秦钟之死”却叙在第十六回;10回一单元的阅读法,在切去尾巴的同时,也阉割了“可卿之死”这一关键情节所要表达的小说题旨。又如将第十六回到第二十五回作为一个阅读单元,虽则突出了造园缘起与元妃省亲的主题关联,园中布局与园内居民的个性比配,园内春景滋蔓与宝黛爱情滋生的共生共振,但却割裂了第二十三回“宝黛共读西厢”“黛玉独聆牡丹”与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显得有失允当。
在这样的状况下,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与指导就需要设置科学合理的切入角度,以便在“新课标”所设定的时限内使学生获取最大的阅读效果。
事实上,有不少研究者都已在探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切入点问题。天津中学吴奇提出,“如果对‘阅读内容’不加限制,在实际操作中……要不是走马观花,要不是走‘专业研究’之路”。他提出了宏观通读与微观细读相结合、按大小专题重点读的思路。按专题重点读,就是一个阅读切口的选择问题。吴奇认为可以从主要情节切入,也可以从重要人物切入[4]13-15。这种阅读教学思路,可以视之为“两重点”说。与此同时,广西师大梁冬丽、白钰提出,应将家族、青春、爱情、生命、悲剧这“五大关键词”,作为品析《红楼梦》思想意蕴的路径、打开其艺术宝库的钥匙;阅读时可以由“小角度”走进“大长篇”,由“教师教”走向“学生读”,兼顾“个性化”与“多样性”[4]22-27。显然,这五把钥匙就是五个切入角度,借由它们以点带面、从小到大,可以串联起整本书的大部分章回,对中学生阅读《红楼梦》而言,称得上是一种涵括性与趣味性兼容的阅读策略。
上海师大附中余党绪提出“三聚焦”论,即聚焦大观园、聚焦人物论、聚焦思辨性,认为这样能删繁就简、提纲挈领[5]27-28。这是提倡用思辨的态度,重点阅读、评析大观园中的人物群体。这样将阅读重点聚焦于主要人物形象及其故事,非常贴近成长中的高中生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而“青春”与“毁灭”两大关键词,也将一群青春女性的悲剧与家族败亡的悲剧紧密关联。当然,教师采用这样的方法指导中学生,如果不能准确理解“三聚焦”理论的全部内涵的话,也容易撇开或放弃对大观园以外的人物及其活动的审视,而《红楼梦》里诸多关乎主题的重要情节,却又的确是在大观园外发生的。俞晓红提出,将小说的关键情节作为切口,局部切入,故事为主体,人物为核心,而后追溯因果,关联文本整体,适当作文化拓展。围绕每一关键情节,均可圈出10个章回,可以在保持章回互不重复的状态下,以模块化的解读方式,促进阅读时的整体性融通[6]。
“新课标”第一个学习任务群,在“指定范围内选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部分,已经给出明确指导,即“从最使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等方面入手,反复阅读品味,深入探究”[2]11。显而易见,故事、人物、场景、语言就是切入阅读的四个角度,或曰四个层面。相较于“两重点”“五钥匙”“三聚焦”,这个“四层面”更有高瞻性,也更符合《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特质和阅读策略。从教师而言,能够高屋建瓴地找准切口,在百万字的经典文本里提取关键情节、重要人物、精彩场景和优美语言,进而驾驭整本书阅读教学,达到以简驭繁、以少胜多的效果,是值得去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的事。从中学生而言,能够在教师的高效引导下,读懂《红楼梦》的关键故事,理解系列重要形象,熟谙诸多经典场景,感受小说语言魅力,从而取得较短时限与较大阅读量之间的平衡,进而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思维,这也是特别值得推许的事情。
歌德曾说:“向着某一天终于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目标迈步还不够,还要把每一步骤都看成目标,使它作为步骤而起作用。”[7]5“找切口”是实施整本书阅读教学的一个步骤,也是一个起步目标。“对标”找好切入角度,目标求准,迈步求稳,“把精力集中在有价值的东西上面”[7]44,助力学生提高长篇小说整本书阅读的性价比,是实践“新课标”、落实“新课改”的重要一环。
二、把握选题幅度,促进教学有效性
在找好切口后,应选择恰当而丰富的文本专题进行阅读教学;基础文本与切入点的对应度越高,阅读与教学的有效性也相应更高。由于故事、人物、场景、语言这四个层面涵括而不限于两重点、三聚焦、五钥匙的内蕴范围,围绕它们来设计选题并把握其幅度,自然更具“整体性”意义,更能促进教学的有效性。
作为长篇小说标准的《红楼梦》,哪些故事是不能绕过的必讲故事呢?元妃省亲时曾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脂砚斋在此点醒读者:这四出戏分别伏贾家之败、元妃之死、甄宝玉送玉、黛玉之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8]299。四出戏所伏的情节均发生在八十回后,以“戏中戏”方式绾结四大关键情节的元妃省亲,乃是至为重要的“大关键”情节。它是贾氏内部的一场庄严神圣的政治文化活动,是贾氏家族到达鼎盛阶段的重要标志。因此,将元妃省亲视为全书的“大过节、大关键”情节,毫不为过。仅就前八十回情节而言,由于宝玉挨打、探春结社、刘氏进园、香菱学诗等故事都很醒目,都发生在大观园中,因而通常会成为中学阅读教学的必选项之外,可卿之死、探春理家、鸳鸯抗婚、二尤之死、抄检大观园等故事也是不可忽略的“大关键”情节。它们可能不一定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但它们对于表达《红楼梦》的主题内涵却意义深远;而阅读教学的职责,就是要将潜藏于故事之内的深刻思想揭橥于故事之外。细味之,这几组故事不仅没有疏离“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一轴心,而且在痛砭这个贵族之家政治生态污浊、道德沦丧、箕裘颓堕、危机四伏的严峻现实时,拉大了人性被扭曲、青春被毁灭、生命被践踏的历史景深。
哪些人物能够成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重点目标,应该不成其为问题。早在20 世纪40 年代,王昆仑已经聚焦人物形象,先以单篇文章系列解读诸多重要形象,后集成专书《〈红楼梦〉人物论》[9]。除了宝、黛、钗、凤、探、纨、秦等一众居于主体位置的人物之外,贾母与刘姥姥、袭人与晴雯、平儿与小红,“《红楼梦》中三烈女”鸳鸯、司棋、尤三姐,“大观园中的遁世者”妙玉、惜春、紫鹃、芳官等五组人物也是重点解读的对象;另有“贾府的太太奶奶们”“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贾府的奴仆们”等三组群像。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对当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富有多种启发意义:一是对每一形象品质或性格的善恶优劣均予以深刻的解剖分析,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善恶并存思维;二是主次分明,且以类比关联的思维方式,阐述同一类属人物的同中之异,又揭明不同类属人物的质的差异,有助于训练学生的连类比较思维;三是语言优美,融感性的温情与理性的深刻为一体,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感语理程度。教师恰当的点拨与引导,不惟锤炼学生关联阅读和贯通阅读的品质,提升其对比阅读和类比阅读的水平,亦更能促进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与人格的养成。
“场景”一语涵盖“场面”和“情景”。从场景入手切进《红楼梦》文本阅读,理当关注小说中那些至为经典的场面情境。宝黛共读《西厢》、黛玉独聆《牡丹》,是以“戏中戏”的艺术技巧描写宝黛爱情发生的精彩场景,将《西厢记》《牡丹亭》戏曲文化穿插在《红楼梦》小说的叙事进程中,令戏曲文本和小说文本产生了互文性,启发了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黛玉葬花,葬的原本是自然界的落花,但它却又是大观园女儿青春生命行将飘零的象征,因此葬花之景便成为《红楼梦》“以花喻人”手段运用得最为经典、最为至情的凄美情境。宝钗扑蝶、湘云醉眠等,无不是小说中深涵传统文化韵味的优美场景。叙事过程亦有很多精彩场面,如宝玉挨打故事中众人救场,场面激烈而又层次井然;鸳鸯抗婚故事中鸳鸯哭诉激发贾母痛斥,探春辩冤引出熙凤调侃,十分生动真实,有移步换景之妙;抄检大观园故事中晴雯掀箱、探春反击,都写得出神入化,令人击掌称绝。
小说的语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既是读者接触小说文本的最表层介质,它又是读者深层解读文本时不可或缺的意义载体。笔者一直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文质兼美,读者鉴赏时可以从描写语言、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等多个层面进行;基于提高阅读性价比,语言鉴赏应与故事情节解读、人物形象剖析、场面情景鉴赏等同步进行,注重其聚合性与纵深感,而不必单独另选语言材料展开分析。在曹雪芹笔下,景物描写渗透诗情画意,肖像描写富含文化韵味,心理描写则细腻生动、层次丰富,人物语言描写则达到古代小说个性化的至高境界。然而阅读一部经典小说,仅分析《红楼梦》语言表层的意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穿透语词层面去探讨文本深层的东西,去触摸去感悟那些蕴涵小说主题的内容。美国教育家艾德勒认为,分析阅读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优质阅读,主题阅读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阅读,读者需要进行关联性阅读并形成主题分析,它是一种最主动、最有收获的阅读[10]20-21。
《红楼梦》中有一种值得读者进行关联性深层阅读的特殊语言,那就是小说中的诗词曲赋。有学者认为明清小说中的诗词曲赋都是一种“寄生的”文体,这实际上是因为不了解古代小说与生俱来的韵散结合叙事体制而导致的误解。不过《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其韵文与散文的配合多有彼此疏离的状况,而《红楼梦》中的韵文却与散文的叙述结合得非常紧密,如果跳过了这些诗词曲赋,可能不影响常态化阅读,但却一定不能到达主题阅读的深处。以《好了歌解》为例,它在书写世事沧桑、人生无常方面,与《好了歌》同样具有哲理的高度,但较之《好了歌》又更具直指生命现实的宽度与厚度。甲戌本侧批将这种生命的悲凉逐一揭明:从首句“陋室空堂”开始,直到“今嫌紫蟒长”句止,每一句都有确指的对象和事件,从宝玉到钗黛,从贾赦到巧姐,从家族到个体,忽起忽落,或荣或衰,倏痛倏爱,悲欢交替,句句落实,句句触目惊心。读者可以视之为作者的一种预示手段,但当我们将诸条侧批和同页眉批进行关联阅读,对所涉人物进行整本书故事的贯通阅读,就会感受到人世的诸般悲欢中深涵的青春悲剧、生命悲剧和家族悲剧彼此交融的深刻主题。
进而言之,《红楼梦》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并非彼此独立的存在,故事或许呈现为一幅幅场景,而人物性格始终处于故事与场景的核心,语言是作者通向读者心灵世界的桥梁。无论从何切口进入,也无论选取哪一专题,整本书阅读教学都需要对文本材料进行解构重组使之再生;文本资源内涵的丰富深厚,为主题阅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歌德所说,经典的作家作品,总是会“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让后来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已经有一个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优异作家在那里”[7]14,在欣赏时艺术家人格的这种雄伟力量,开扩了我们的心胸,把我们提升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7]211。经由关联阅读、贯通阅读而获得的主题意涵的把握,必能助成青少年读者优良的思维品质的培养和才智情感的成长。这是《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真谛。
三、确定评价维度,筑牢教育质量观
当教学与指导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进程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时,一个问题自然浮出水面:什么样的阅读教学才是符合课程标准要求的“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教学?这就需要确立教学评价的维度。笔者以为,评判整本书阅读教学指导课的优劣高下,关键看他是否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立足课标。教师有没有“对标”寻找切口,设计选题,开展阅读;能否激发中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其良好的阅读习惯,拓宽其文化视野,训练其发展思维。二是观照整体。教师能不能抓住重点选题设计教学内容;是否从“整体性”出发,将专题内容与整本书作关联性阅读和贯通性阅读。三是体现研讨。教师有没有在共识、通识的基础上,通过话题设置,引导和驱动学生开展研讨式学习;能不能锤炼学生的连类比较思维与创新思维,促进其思维品质的提升。四是促进迁移。教师能不能通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促进学生阅读经验方法的有效迁移;是否借助经典文本的阅读体悟,促进学生写作思维与写作水平的整体提升。
前三条笔者已多有阐明[3][6],此不赘述。第四条有关阅读经验的迁移,仍属“对标”实施教学;而促进写作思维水平之说,不仅基于读写结合的语文教学原则,而且也基于名著文本的本质特征及其资源效益。《红楼梦》是一座丰富的阅读资源库,也是一个宝贵的写作资源库。原著本身就给出了文学资源转化运用的至佳范例。即使笔墨不多的人物出场,在曹雪芹笔下,也都会处理成意境化的生动场面。第三回王熙凤出场,一句“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旁,甲戌本眉批曰:“未写其形,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8]120第二十五回贾宝玉想再见到林红玉,“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11]336。甲戌本双行夹批道:“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8]381第三十回写五月蔷薇架下,蔷薇花盛叶茂,贾宝玉隔着篱笆洞,看到龄官用簪子在地上划着“蔷”字;雨起时,龄官反观宝玉,“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11]416,一时认作是个丫鬟。这一场景,恰似一幅双面绣,将“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的情境写了个十足十。《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教学,须特别关注这些从前人诗词曲句中化用而出的散文文本,在体味语言美感、实施文学教育的同时,也在理性地指向经典资源转化运用的写作指导。
借助考评手段来引导高中生的整本书阅读,是多个省市尝试过的语文教育策略。课程评价或许仅面对语文教师,而语文考评却又无不是师生双方的面向。在各级各类考评中,高考是最大的总结性评价。高考语文卷出现《红楼梦》试题,“进一步明确各类课程的功能定论,与高考综合改革相衔接”[2]3这一国家意志和教育思想的导向性措施。2017 年,北京市将《红楼梦》等名著作为高考必考项目明确写进《考试说明》。此后数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高考语文试题也越来越贴近《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导向意图。2023年高考语文北京卷10分的微写作选题之一,即预设了一个情境:文学社社刊拟开设“花开纸上”读书专栏。要求考生“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选一个与花卉有关的场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写一段短评”。尽管北京卷名著阅读明确在《论语》《红楼梦》两者间轮换命题,而2022年已考《红楼梦》、2023 年考了《论语》,但熟悉《红楼梦》的考生十有八九仍然会选取这部名著中的材料来完成这道微写作题。2017年北京卷10分的微写作题之一,是要求在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香菱之中选择一人,用一种花来比喻并说明理由。如果说这道题乃以人物为中心,联系相关情节画面来写形象的话,那么“花开纸上”的命意,则是以场景为中心,联系人物特质来写感受。两者形异而质同,目的都指向经典名著的关联性阅读。
《红楼梦》进入高考语文试题,有其宏观上的战略意义;就它对语文教育的示范意义而言,微观命题的精当妥帖仍需要多加斟酌思考。经典文学作品固然有其多元化的阐释空间,但微观文本的解读,仍当有其内涵的确定性意义。
2022 年高考语文全国甲卷60 分写作,选取《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关于园中水面桥上亭子题名的情节场面,要求评判“翼然”“泻玉”“沁芳”三个选项的艺术效果,结合学习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材料同时给出了“直接移用”“借鉴化用”“情境独创”三种已然判断作为引发思考的逻辑起点,为考生提供了选择与发挥的足够空间。但如果命题者带有引导“《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潜在意向,那么照顾到原著题名优劣及作者构思意图来解读三词,就会将“沁芳”作为最优选择项。一是因为亭在清流之上,压水而成,题名意宜近水,“翼然”疏离了“压水”情境,且已被贾政否定;二是因为“泻玉”意境粗陋,与省亲颂圣的目标产生违和之感,且亦被贾宝玉否定;三是因为这道清流春天时,两岸柳条嫩绿、扶风照水,桃花纷飞、水面沁香,因此“沁芳”二字最贴近亭边水岸景致。宝玉所拟七言对联“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写出了亭子压水的空间位置特征和柳垂花覆、芳香四溢的景象画面,是故上联脂批云“要紧,贴切水字”,下联脂批云“恰极,工极”[8]276。如果联系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七回以及小说主题可知,“沁芳”系宝玉独创,不惟新雅,而且为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等情节和“落红成阵”“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等画面埋下伏笔,更应和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题。因此,如果有考生选“沁芳”为中心词,阐释后再展开联想,力推“创新”,立意准确高远,且贴近时代精神,应是最佳思路。兼顾命题的起点和落点,考查学生的思维品质,初衷毋庸置疑;但命题材料本身包含了“选最优”与“可多选”的矛盾,倡导“亲近名著”和制造“阐释空间”彼此悖逆,这就反映出名著阅读实施进程中的一种踌躇与局促。
2022年高考语文上海卷有一道3分的选择题,设置了一个学生小组改编“宝玉挨打”情节参加学校演出的情境,规定的目标是“力求台词符合原著中人物的身份与性格”。题干要求在4 个台词选项中选出“最恰当的一项”,可见这是一道单选题。考生如果不熟悉原著,势必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问题在于4 个备选项答案中,正确项并非是唯一的一个:
A.黛玉对宝玉说:早就对你说过,你真是执迷不悟啊。
B.宝钗对宝玉说:这次活该,你挨打就是自食其果。
C.贾母对贾政说:你想想你父亲是怎么管教你的。
D.王夫人对贾政说:我现在就死给你看,一了百了。
显而易见,A 和B 都不符合小说文本的既定内容,但C和D却都能找到相应的文本根据。宝玉挨打,王夫人救场时抱住贾政说:“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贾母训斥贾政时说:“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11]447、448这道题小口切入,用陌生的问题情境考察学生对名著的熟读程度及其转化思维,出发点和考评目的都十分明确。从命题意图看,自然不会在单选题里设置两个正确项;干扰项失效,答案不唯一,应是命题者自己对文本不够熟悉之故。后评分细则以选C 得3 分、选D 得2 分来调整命题不精当所可能导致的失衡局况。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进入“新课标”、新课程、新高考,是语文教育改革的进步,也是文学教育实施的过程。如何筑牢语文教育质量观,在中学生、语文教师与高考命题之间获得阅读、教学和评价的平衡;如何融道于术,在共识、通识基础上充分利用学术资源,推动大中之间基于问题讨论的应用式贯通;如何在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之间获得文本解读的确定性和一致性等,都是值得教育者深入研究的问题。歌德曾言:“人的全部意识和努力都是针对外在世界及周围世界的……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苦痛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7]178如果教育过程让每一个体都能深切感受到经典文本那种种触动心灵的审美体验,借此获得感悟欢喜或苦痛的见识力,提升了思维品质和人格力量,并将这种见识表达出来,这也就是文学教育或语文教育所要达至的理想目标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