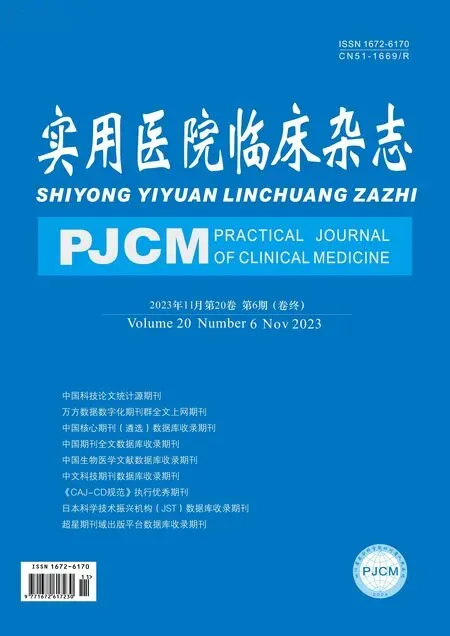超声心动图评估乳腺癌患者化疗相关右心室心脏毒性研究进展
杨 瑞,邓 燕,2△,张 硕,卢 蕊
(1.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成都 611731;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研究所,超声心脏电生理学与生物力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72;3.电子科技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四川 成都 610041;4.西部战区总医院,四川 成都 610083)
据统计,2020年全球大约有230万新发乳腺癌患者,目前已经超过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及第5大癌症死亡原因[1]。蒽环类药物(阿霉素、柔红霉素及表阿霉素等)及曲妥珠单抗是乳腺癌患者最常用的化疗药物,在减少乳腺癌复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均存在明确的心脏毒性作用。研究表明,若心脏保护性治疗在出现心脏损伤6个月后才开始,此时的治疗效果几乎为零,因此,对乳腺癌患者心脏功能早期动态监测显得十分重要[2]。有学者认为右室壁较左室壁更薄,肌原纤维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右心室心肌更容易受到化学毒素的影响[3]。Grover 等[4]发现乳腺癌化疗患者左心室功能在开始化疗第4个月后便保持稳定,而右心室功能在开始化疗第12个月后仍继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右心室的结构和功能与心血管疾病患者预后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评估左心室功能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右心室功能变化[5]。
1 心脏毒性分类
化疗药物所致心脏毒性根据其致病机制可分为两大类:① I型心脏毒性——不可逆性心脏损伤,以心肌细胞坏死或凋亡为主,其中以蒽环类药物为代表;②II型心脏毒性——可逆性心脏损伤,以心肌细胞功能障碍为主,其中以曲妥珠单抗为代表[6]。
蒽环类药物所致心脏毒性根据其临床表现被分为三大类:①急性——初次输注蒽环类药物后发生的可逆性心肌功能抑制,该类型比较少见;②早发性慢性进行性——最常见的类型,通常在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后1年内出现,最常见的表现是左心室功能进行性下降,即使在停止蒽环类药物输注后仍会持续存在或继续发展;③迟发性慢性进行性——指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后1年以上发生的不可逆性心脏损伤[7]。
2 主要化疗药物致病机制
尽管蒽环类药物已经使用了60余年,但其所致心肌毒性的分子机制仍未被完全了解。目前公认的机制有两个:①氧化应激;②对拓扑异构酶 IIβ的抑制[7]。右雷佐生便是通过竞争性抑制蒽环类药物与拓扑异构酶 IIβ的结合,从而降低蒽环类药物引起的心肌毒性,达到保护心脏的目的[8]。
曲妥珠单抗通过抑制肿瘤细胞中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来发挥治疗作用。该药物心脏毒性致病机制主要包括: ①对心肌细胞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直接抑制;②对心肌细胞中细胞能量调节器(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的抑制。有研究显示激活或增强AMPK的表达可以减轻曲妥珠单抗所致心脏毒性的症状及增强心肌收缩能力,这表明AMPK可能成为治疗曲妥珠单抗所致心脏毒性的治疗靶点[9]。
【基金项目】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3NSFSC0120)
△通讯作者
3 癌症治疗相关的心功能不全(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ac dysfunction,CTRCD)
CTRCD是指南推荐描述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的术语,包括了抗肿瘤治疗可能出现的广泛心脏疾病症状以及涵盖了与抗肿瘤治疗相关的各种病因[10]。该指南根据有无心血管毒性临床症状将其分为有症状CTRCD和无症状CTRCD,其中无症状CTRCD根据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室整体纵向应变(left ventricular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LVGLS)及心脏生物标志物的相对变化将其分为了轻、中、重三级。
4 超声心动图评估化疗相关右室CTRCD
目前,可用于早期监测CTRCD的监测手段包括有心肌酶谱、心肌肌钙蛋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心脏磁共振(CMR)、核素心肌灌注及血池显像、心内膜心肌活检等。超声心动图因其经济、方便、无辐射、可重复实时动态观察的优势,成为当前评估右室CTRCD的一线选择,超声心动图新技术如斑点追踪成像技术(speckle tracking imaging,STI)、压力应变环技术(pressure strain loops,PSL)及血流向量成像技术(vector flow mapping, VFM)的发展也为更敏感准确地评估右室CTRCD提供了多种新的参数。
4.1 常规超声心动图利用常规超声心动图技术现可获得右心室结构、收缩和舒张功能及血流动力学信息,但目前国内最新指南仅推荐了右心室收缩功能指标来评估右室CTRCD,包括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ricuspid annular plane systolic excursion, TAPSE)、三尖瓣外侧瓣环收缩期峰值速度(tricuspid annulus sy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 of tissues,S′)、右心室面积变化率(righ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area change,RVFAC)及三维超声测量的右心室射血分数(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RVEF)[6]。
TAPSE与S′均是对于右心室纵向收缩功能进行一维量化的指标,两者最大的优势为即使在二维图像不理想的情况下,也能简单的测得高度可用的数据。TAPSE利用M型超声心动图技术来测量外侧三尖瓣环从舒张末期到峰值收缩的纵向偏移,正常人群一般TAPSE ≥17 mm,具有良好的特异性,但敏感性较差;而S′则是基于组织多普勒技术对外侧三尖瓣环进行测量获得,S′<10 cm/s被认为有异常[11]。TAPSE与S′两者局限性类似,均以单个节段的位移或速度来代表有着复杂结构的右心室功能,均未考虑室间隔和/或右室流出道对右心室功能的影响,均具有角度和负荷依赖性[12]。RVFAC则综合反映了右心室纵向和径向收缩功能,与角度无关,正常人群RVFAC>35%。Abdar等[13]发现乳腺癌患者在开始化疗第6个月后RVFAC(49.83% vs 43.59%)、TAPSE(18.8 vs 17.7 mm)及S′(12.59 vs 10.57 cm/s)均出现了显著降低。在Shi等[14]的系统综述中, 主要代表右心室纵向收缩功能的指标TAPSE及S′在化疗后的确是有减小的,但RVFAC在乳腺癌化疗前后并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右心室纵向收缩功能受损后,径向收缩功能代偿性增强导致RVFAC整体并没有明显变化。但也有多项研究表明TAPSE、S′及RVFAC在化疗前后并无明显差异[15, 16]。
LVEF是评价左心室功能最常用的指标,但RVEF在评估右心室收缩功能时的作用较为有限。因右心室解剖结构复杂及声窗受限,在二维超声下通过简单的几何假设计算后得到的RVEF是明显不可靠的,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较大的变异性也不能够满足临床需要[17]。而三维超声心动图可对右心室进行全容积成像,对于心腔容量大小的测量不需要几何假设,理论上更接近实际解剖大小,尽管可能会低估右心室体积,但三维超声所测量的RVEF与“金标准”——CMR依然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由于RVEF有明确的后负荷依懒性,仅通过RVEF来估计右心室收缩功能依然较为困难[18],建议结合其它二维超声参数综合评估。尽管Grover等[4]的研究显示CMR测量的RVEF在化疗后有较为明显的降低,但同时也有其它研究认为RVEF在化疗后并没有明显下降[19]。
目前右心室舒张功能指标如E/A、E/e′等在国内外的指南中均未得到明确推荐[6, 10],导致化疗患者出现右心室舒张功能障碍的原因也暂未得到充分认识,可能是药物对于右心室的直接影响,也有可能是化疗药物引起肺循环改变导致的肺动脉高压[20]。在右室CTRCD相关研究中,右心室舒张功能也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 Abdar等[13]发现右心室舒张功能参数 e′/a′及e′在开始化疗第6个月时出现了明显降低。然而Xu等[21]测得的右心室舒张功能参数E/A及E/ e′在化疗前后无明显差异。
4.2 STI技术STI的出现显著改变了评估心肌功能的方法,该技术无角度依赖性,且重复性较好,在大量的左心室相关研究中已经被证实可以用于评估化疗药物所致亚临床心脏毒性[22],当前欧洲心脏病学会关于无症状CTRCD的区分便主要依据了STI中的LVGLS参数。在肿瘤患者中,使用STI获得的右心室纵向应变是唯一具有与LVGLS一致和同质的收缩性能参数。右心室的纵向应变主要指右心室整体纵向应变(right ventricular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RVGLS)及右心室游离壁纵向应变(right ventricular free wall longitudinal strain,RVFWLS),两者主要区别在于RVGLS包含了左右心室共用的室间隔部分,但关于右心室应变分析中是否应包含室间隔尚存在争议。
Laufer-Perl等[23]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蒽环类药物治疗结束时,RVGLS及RVFWLS均发生了显著减低。Shi等[14]系统综述中同样也认为抗癌治疗后的RVFWLS及 RVGLS与基线相比均有明显差异。Chang等[3]研究发现乳腺癌化疗患者在第3周期化疗后所测量的LVGLS与RVFWLS相比于基线均显著减低,且第1周期化疗后RVFWLS的减低与呼吸困难的发生成正相关(r=0.53,P=0.02)。另有研究发现RVGLS与LVGLS遵循相似的时间趋势且RVGLS预测心脏毒性的截断值与已建立的LVGLS截断值相似,使用RVGLS 相对降低 14.8% 的截断值可以检测出 90%发生CTRCD的患者,且LVGLS及RVGLS的基线值越低,则化疗后LVGLS及RVGLS下降幅度越大,发生CTRCD的可能性越高[24]。Mazzutti等[25]研究发现LVGLS变化明显早于RVGLS,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三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3D-STI)结合了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2D-STI)及三维超声心动图的优点,理论上能更准确的评估整体和局部心脏结构、运动及功能。两者均可获得纵向、径向、周向应变,3D-STI还另新增了一个应变参数,即面积应变,该参数是对纵向及周向缩短运动引起的相对面积变化的反映[26]。目前将3D-STI应用于评估乳腺癌化疗患者右室CTRCD的研究较少。
Xu等[21]研究发现与基线相比,3D-STI测量得到的 RVGLS 和RVFWLS 在化疗期间和化疗结束后均有所下降,证实了3D-STI可以用于右室CTRCD的鉴别,该研究还发现 RVFWLS是无症状CTRCD的独立预测因素,3D-STI模式下的RVFWLS诊断无症状CTRCD的最佳截断值为-17.5%,敏感性80.5%,特异性65.8%。有研究将乳腺癌患者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加右雷佐生)及对照组,并使用了3D-STI技术进行随访,结果显示在化疗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RVGLS及右心室整体面积应变均显著降低,且实验组下降幅度更小[16],证明了3D-STI测量的右室应变参数甚至可以灵敏地检测出右雷佐生对右心室的保护作用。
上述研究对STI技术均给出了肯定的评价,证实了STI是目前较为理想的评价右室CTRCD的技术,右心室纵向应变参数——RVGLS 和RVFWLS是目前较为理想的参数。该技术主要局限性包括: ①图像质量要求高; ②帧数依赖性;③负荷依赖性;④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变异性[14]。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获得可靠的右心室纵向应变参数,且CTRCD的检查需要尽量满足同一超声诊断医师且使用相同供应商的超声诊断仪。
4.3 PSL技术2D-STI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负荷依赖性,因此Russell等在2D-STI(分层应变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了PSL。该技术负荷依赖性小,可量化分析心肌功能,图像分析时需要输入肱动脉血压数值,结合应变参数后可自动生成多种心肌做功参数,如整体做功指数、整体有效功、整体无效功、整体做功效率等[27]。该技术目前已用于高血压、心肌病及冠脉动脉疾病等心脏疾病。崔瑞雪等[28, 29]将PSL应用于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地乳腺癌患者中,结果均显示LVGLS与左室整体做功指数、整体有效功均呈正相关,证明了PSL可以应用于早期发现无症状CTRCD。但目前尚无将PSL应用于评估右室CTRCD的研究。
4.4 VFM技术STI的关注点在心肌(固体)上,VFM结合了常规彩色多普勒成像技术与STI技术,可在二维彩色多普勒的基础上对实时平面的多普勒频移信息进行追踪,其关注点在心腔内的血流(流体)上,理论上能够可视化以及量化心腔内血液流场状态及血流动力学,如VFM现已能够可视化定量评价左心室的能量损耗(energy loss, EL)和循环强度等。然而对于VFM的研究目前大多集中于左心室。有学者[30]利用VFM监测乳腺癌患者化疗前后左心室功能变化后认为VFM相关指标对于化疗相关心脏毒性的评估有较高的诊断效能。Chen等[31]通过VFM测量了正常儿童右心室的EL参考值,发现EL值与年龄和RVGLS呈负相关,证明了VFM可为定量评估右心室功能提供参考依据。张键等[32]应用VFM技术评估了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患者右心室功能后认为迹线和波前成像可用于分析右心室内血流的流动效率和运动速度,相对压成像可以定量评估右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以上研究均表明VFM可用于评估右心室功能,但尚需更多的研究验证其在右室CTRCD评估中的作用。
超声心动图评估右心室功能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于右心室复杂的三维形状及其胸骨后位置导致有限的成像窗口,不能够获取清晰的右心室心内膜面及在单个切面中获取整个右心室图像,且右心室负荷情况对于右心室的大小、几何形状及功能影响特别大,即便使用最新的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成像技术,也会经常出现右心室流出道和右心室游离壁的图像缺失,获取的图像时间分辨率较低[12]。
5 小结与展望
由于右心室复杂的解剖及受限的声窗,传统的二维超声技术在评估右室CTRCD时存在着诸多不足,研究者间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结果;实时三维超声可以提供比二维超声更多的信息,但图像丢失及操作较复杂等缺点同样限制了其使用;新的技术如VFM及PSL技术的实用性问题尚需更多的研究;几乎所有研究都肯定了STI在评估右室CTRCD中的作用,部分研究也给出了相应截断值,RVGLS 与RVFWLS是目前较为理想的评估右室CTRCD的参数。人工智能技术现已成为当前各行各业的研究热点, 其可参与超声心动图的所有检查环节,包括图像采集到最终的结果解释环节,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识别到图像中人眼所看不见的细微的差异,例如可将其应用于心肌病的鉴别,可以期待,未来超声心动图新技术结合AI后或许可以更加准确敏感的评估右室CTRCD[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