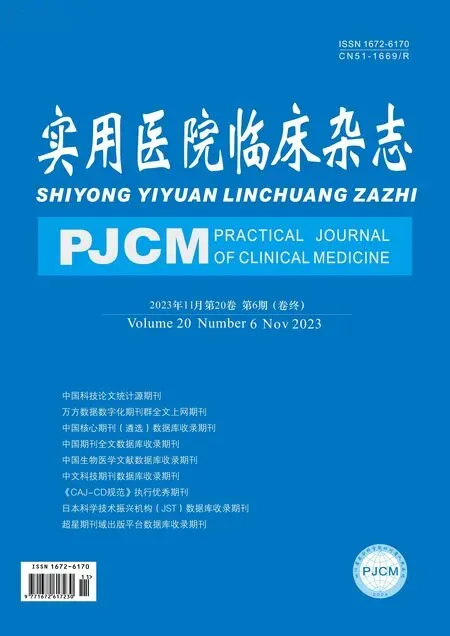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遗传研究进展
常艳宇,邱 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广东 广州 510630)
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类以自身免疫性细胞、自身抗体及其他免疫分子直接或间接攻击自身神经系统,造成神经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损伤为特点的疾病。该类疾病表现复杂多样,可以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或轴索损伤、髓鞘脱失等病理改变,主要包括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 MS)、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euromyelitis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NMOSD)、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相关疾病(myelin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IgG associated disorders, MOGAD)、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E)等疾病。这类疾病往往好发于中青年人群,具有较高的致残率,且多数容易出现复发,是我国中青年人非创伤性致残的重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存质量,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均带来了巨大的负担。CNS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机制复杂,目前普遍认为,遗传易感因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导致其发病。本文对几种主要CNS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研究的进展进行综述。
1 MS的遗传研究进展
1.1 概述MS是一类以累及白质为主的CNS炎性脱髓鞘病变,在病理上表现为CNS多发髓鞘脱失,可伴有神经细胞及其轴索损伤,其病变具有时间多发和空间多发的特点。MS好发于青壮男,男女患病比例约为1:1.5~1:2[1],CNS各部位均可受累,临床表现多样,可表现为视力下降、复视、肢体感觉障碍及运动障碍、共济失调、直肠及膀胱功能障碍。根据其临床病程可分为复发缓解型、继发进展型、原发进展型等多种临床类型。由于多于青壮年起病,并可能给患者留下不可逆的神经功能缺损,MS对青壮年人群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MS的发病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据统计,MS具有家族聚集现象,约15%MS患者的亲属也患有MS,MS患者的兄弟姐妹患病风险高达普通人的7倍[2]。但缺乏累及多代的MS大家系报道,一个家系中出现超过4个患者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其遗传模式往往不符合孟德尔遗传特点。因此我们推测,MS的发病与遗传因素相关,但其发病是由多个风险基因共同介导的,而非单一基因突变控制。这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存在一定的患病风险,具有更多风险基因型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因子如低维生素D水平、暴露于Epstein-Barr 病毒(EB病毒)和吸烟等影响下更容易发病。
1.2 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基因与MS的关系HLA基因复合体是位于人类6号染色体短臂上的基因簇,表达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 MHC)。HLA基因簇编码的分子多态性强,重组频率低,其等位基因变异可作为疾病保护性/易感性的标志物,对适应性免疫和固有免疫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被认为与人类自身免疫疾病密切相关。HLA基因多态性与MS的关系早在50年前就已经被重视和描述。随着对MS遗传基础的研究不断深入、基因检测技术发展和精度不断提高,更多与MS发病相关的HLA位点被发现,而其中,HLA-DRB1*15:01等位基因型与MS发病的关系最为被重视。一项人类基因组流行病学综述回顾了1993~2004年发表的72篇相关文章,发现除少数针对非高加索人群的研究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发现HLA-DRB1*15:01在患者中出现的频率高于对照组[3]。而近年来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研究则也发现,与MS主要相关的易感信号定位于HLA-Ⅱ类区的HLA-DRB1基因,这可以解释高达10.5%的潜在风险遗传变异,其中,HLA-DRB1*15:01的效应最强,其平均优势比(Odds Ratio, OR)值达到3.08[4, 5]。
HLA-DRB1*15:01与MS的关联符合加性模型(additive model),即风险等位基因的拷贝数与MS发病风险增加和严重程度相关;除了在HLA-DRB1*15:01纯合基因型人群中观察到MS风险显著增加外,HLA-DRB1*15:01/*08:01杂合基因型被观察到可能存在显性上位效应,其发病风险相对于其他杂合HLA-DRB1*15:01基因型有所增加,而HLA-DRB1*08:01自身并不能导致发病风险增加,但它可以增强HLA-DRB1*15:01的作用。HLA-DRB1*15:01常见于欧洲人群,携带它的MS患者多为女性,具有更早的发病年龄,更有可能合并寡克隆区带阳性和脑脊液IgG水平升高[6]。近期有研究发现,HLA-DR15单倍体型(包含两个DR等位基因,分别为HLA-DRA*01:01P/DRB5*01:01和HLA-DRA*01:01P/DRB1*15:01)携带者在感染EB病毒的情况下,激活的T淋巴细胞可以迁移到大脑中诱发自身免疫反应,诱发MS发病[7]。这可能解释了HLA-DRB1*1501在MS发病中的潜在机制。然而,并非所有的MS患者都携带HLA-DRB1*15:01,该等位基因性也可出现在约30%的正常人中,这表明HLA-DRB1*15:01并非MS患者所特有,也不足以单独诱发MS。HLA-DRB1*15也可能是东方MS人群的易感单倍体型,但是它在东方M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OR约为1.39)显著小于西方人群(OR约为4.00)[8]。在一些非高加索人群,如非裔美国人、巴西人、伊朗人及某些日本人群中,HLA-DRB1*1501与MS易感性无明显关联[3]。
对于除HLA-DRB1*15:01外的其他DRB1等位基因型对MS发病和严重程度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果,可能在不同人种中存在不同的MS易感等位基因型。HLA-DRB1*04:05可能与亚洲MS患者相关,但携带这一等位基因性的患者临床上具有相对特异性的病程,即发病年龄更早,疾病严重程度相对较低,颅内病灶相对较少[9],HLA-DRB1*04:05也被发现与非裔美国人、地中海地区人群(高加索人种)的MS发病相关[10]。HLA-DRB1*04:05多见于日本和地中海人群,但在欧洲人群中分布较少,这可能是在欧洲人群中并没有发现这个等位基因型与MS显著的关联的原因。此外,一种在各人群中分布都很广泛的等位基因型——HLA-DRB1*03:01被发现是地中海地区人群MS的易感基因;与之相反的HLA-DRB1*13:03在各种群中均比较少见,但也被发现与以色列人群(包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非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群体)的MS发病相关[6]。HLA-DRB1对MS的保护作用同样引起关注。研究表明,HLA-DRB1*09:01为东方人群MS的抵抗基因;而HLA-DRB1*01、DRB1*04和DRB1*07则分别为西班牙、澳大利亚及意大利人群的保护性基因[8]。
除HLA-DRB1外,位于HLA-Ⅱ类区域的HLA-DQB1也在MS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一项中国MS研究发现,HLA-DQB1*06:02是中国MS患者的易感基因等位基因型之一[11]。2015年,国际多发性硬化症遗传学联盟(International Multiple Sclerosis Genetics Consortium,IMSGC)分析了来自11个欧洲人群队列的17465例病例和30385名对照HLA等位基因数据,以构建HLA遗传风险的高分辨率图谱,研究发现,HLA-DRB1*15:01、HLA-DRB1*13:03、HLA-DRB1*03:01、HLA-DRB1*08:01和HLA-DQB1*03:02为MS的风险等位基因,HLA-A*02:01、HLA-B*44:02、HLA-B*38:01和HLA-B*55:01为MS的保护性等位基因;他们也发现了两对存在互相作用的等位基因:在HLA-DRB1*15:01存在时,HLA-DQA1* 01:01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HLA-DQB1*03:01的存在则消除了HLA-DQB1*03:02的风险,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经典HLA等位基因和非HLA风险基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12]。
与HLA-DRB1和DQB1相比,HLA-DPB1基因与MS的关联研究较少,原因之一是基因较DR和DQ基因表达水平低,以往的血清学方法很难检测到,且DP基因与其他位点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早期研究认为DP基因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联性不十分明显;但随着研究进展,关于HLA-DPB1 基因与MS相关性的报道逐渐增多。2010年MeElory等报告,HLA-DP基因内含子rs3135021 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与非裔美国人MS紧密相关[13];2011年澳大利亚的一项大规模相关分析亦证实,SNP rs9277353位点与澳大利亚MS显著相关 (OR=1.27), 而该位点与HLA-DPB1*03:01基因呈紧密连锁[14]。HLA-DPB1基因多态性仅次于最富多态性的HLA-DRB1基因,它在抗原呈递及表位扩散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对 HLA-DPB1基因的探讨可能为MS的遗传学机制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1.3 非HLA基因与MS的关系近年来,随着GWAS技术应用于MS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MS遗传因素的认识。GWAS的结果也提示HLA基因和MS的发病的显著相关,同时,GWAS还发现了一些与MS相关的非HLA基因,与HLA基因相比,这些基因对MS易感性贡献较小。近年来,一些更大规模的GWAS研究有了更多的发现,2018年,IMSGC通过GWAS研究了32367例MS患者和36012名对照者的所有常染色体外显子中的120991个编码变体,确定了与MS风险相关的独立于常见突变之外的1个罕见突变:NLRP8(SNP rs61734100)和6个低频蛋白质编码等位基因突变:半乳糖基神经酰胺酶(galactosylceramidase, GALC)基因的SNP rs11552556)、酪氨酸激酶2(tyrosine kinase 2, TYK2)基因的SNP rs34536443、穿孔素1(perforin 1, PRF1)的SNP rs72360387、干扰素诱导蛋白激酶EIF2AK2的蛋白激活因子(protein activator of interferon induced protein kinase, PRKRA)基因的SNP rs179315031和rs179315726)和组蛋白区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 7, HDAC7)基因的SNP rs148755202。这些突变参与了调节T细胞的稳态和调控、干扰素-γ和NF-κB信号转导通路,且与其他突变不存在明显的连锁不平衡,但这些突变对MS的发病贡献也都较小,OR均小于1.04[15],因此,MS 的遗传易感性是由多种低外显率的等位基因共同决定的。2019年,IMSGC再次报告了一项GWAS研究结果,该研究比较了47351例MS患者和68248名人群对照组基因组中数百万个常见SNP的等位基因频率,鉴定出233各不同的风险变异,包括200个常染色体SNP和1个X染色体的SNP,以及多达32个位于6号染色体上MHC区域内的统计学上独立的变异[16],其中研究筛选出551个可能的易感基因位点,这些位点多定位于在参与固有免疫的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巨噬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的细胞(T细胞和B细胞亚群)反应中激活基因的启动子和增强子区域,但少见于表达在神经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上的基因;许多突变是MS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共有的,表明其介导的病理过程并不是CNS特异性的。这种突变的定位和共享表明,MS发病主要是由基因调控变化介导的外周和组织免疫细胞功能的变化不断积累,直至进入病理状态(伴或不伴有诱发事件)。这些遗传效应是否与环境因素一起起作用尚不清楚,但有证据表明,基因型只在特定环境下表达或表达水平发生变化[5]。
1.4 儿童起病MS的遗传研究对于儿童起病(<18岁)的MS患者的遗传学基础研究也显示,HLA-DRB1*15:01与儿童起病的MS密切相关,而与成人MS相关的非HLA基因突变中23%与儿童起病MS相关[17, 18],因此,儿童和成人起病MS存在很多相同的遗传突变,可能存在着相同的病理过程。
2 NMOSD的遗传研究进展
2.1 概述NMOSD是一类由免疫介导的,主要累及视神经和脊髓的CNS炎性脱髓鞘疾病[19]。NMOSD多发于中青年人群,呈复发-缓解病程,发作时临床症状重,且复发率极高,每次复发均可能遗留有不可逆的神经功能缺损,甚至导致失明、瘫痪等严重后果,是一种高致残性的疾病。NMOSD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被阐明,目前普遍认为患者体内存在的可与星形胶质细胞足突表面的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AQP4)特异性结合的自身免疫性抗体AQP4-IgG是NMOSD发病的关键。
目前普遍认为,NMOSD是一种遗传因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疾病。NMOSD在不同种族的人群中均有发病,但非高加索人种(亚裔、拉丁美洲、非洲、西班牙裔和美国原住民等)较高加索人种更为易感[20],因此种族因素可能影响NMOSD的发病。同时,目前存在许多家族性NMOSD的报道,Matiello等估算家族性NMOSD病例约占NMOSD病例的3%左右,我国家族性NMOSD病例比例估算为0.87%,NMOSD患者的家族成员发病率较一般人群高,但家族性NMOSD的临床特点、发病年龄、性别等特点与散发NMOSD无明显差异[21~24]。以上事实皆提示遗传因素在NMOSD发病中起重要作用,NMOSD是一种复杂的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疾病。
2.2 HLA基因与NMOSD的关系不同人种之间的NMOSD的易感基因可能不同,既往我国及日本科学家的多项研究表明,HLA-DPB1*05:01和HLA-DRB1*16:02是东亚人群NMOSD的重要等位基因型[25],其中HLA-DPB1*05:01可能通过改变外周血抗原呈递细胞表面HLA-DP分子的表达水平影响NMOSD发病[26]。而美国、法国等国的科学家则发现,HLA-DRB1*03:01、HLA-DQB1*02:01则与高加索人群中NMOSD的发病相关[27]。2021年一项纳入13项研究,568例NMOSD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HLA-DQB1*03/*03:01是NMOSD患者最多见的HLA等位基因型,发生频率为10%~26.2%,是对照组的2.46倍,且在不同人种中差异显著,可见于多数拉丁美洲人、1/4的白种人和1/4的亚洲人;东亚人群NMOSD的遗传易感性还与HLA-DPB1*05:01等位基因性有关[28]。2021年,一项对228例我国NMOSD患者的HLA测序结果显示,HLA-DQB1*05:02是最显著的风险等位基因型,模型分析显示,HLA-DQB1*05:02在加性效应模型和显性效应模型中与NMOSD显著相关;单倍型“HLA-DQB1*05:02-DRB1*15:01”在NMOSD患者中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25]。
2.3 非HLA基因与NMOSD的关系在非HLA基因方面,AQP4基因3’-非编码区的基因多态性可能与NMOSD的发病相关,推测AQP4分子结构或数量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了NMOSD的发病[29, 30]。此外,免疫调节基因,如CD40[31]、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4, STAT4)[32, 33]、一般转录因子2I重复域1-一般转录因子2I(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 2I, GTF2I)[33, 34]、肿瘤坏死因子配体超家族成员4(tumor necrosis factor ligand superfamily, member 4, TNFSF4)[35]、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1A(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superfamily, member 1A, TNFRSF1A)[36]、CD58[37]、CD226[38]、IL-17基因[39]、IL-2受体基因[40]、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5(glypican5, GPC5)[41]、细胞色素P450家族成员7A1(cytochrome P450 family 7 subfamily a member 1, CYP7A1)[42]、粘胶样分子2(nectin-like molecule 2, NECL2)[43]、核仁蛋白16(nucleolar protein 16, NOP16)、人免疫球蛋白G1(human immunoglobulin G1, hIgG1)[25]、白细胞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interleukin-1 receptor-associated kinase 1, RAK1)[44, 45]和B细胞支架蛋白与锚蛋白重复序列1(B cell scaffold protein with ankyrin repeats 1, BANK1)[33]等基因的多态性可能显著影响NMOSD的发病风险。
2.4 家族性NMOSD的遗传研究虽然存在家族性NMOSD病例的报道,但是家族性NMOSD相关基因研究较少,一项对来自7个家系的13例家族性NMOSD患者及13例家族内健康对照的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提示,位于泛素特异性肽酶(ubiquitin-specific peptidase 18, USP18)基因内含子区的SNP rs2252257突变可能参与家族性NMOSD的发病,进一步在228例散发NMOSD和1400例健康对照种验证USP18基因多态性,发现rs2252257、rs361557和rs5746523三个基因多态性位点均可能与散发NMOSD的发病。临床研究显示,具有rs361553 T/T基因型的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C/T及C/C基因型,这进一步验证了USP18基因内含子区的多态性与NMOSD的发病相关[21]。
3 MOGAD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MOGAD为近年来确立的一类自身免疫性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以血清可检测出抗全长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yelin-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MOG)自身免疫性IgG为关键诊断标准。MOGAD与MS、NMOSD和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cut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ADEM)等CNS自身免疫性疾病在临床表现上有重叠,但其具有相对特殊的病程、病理学以及影像学特征,因此已被作为独立的病种去探讨和研究。MOGAD的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与MS和NMOSD类似,遗传因素对于发病具有潜在作用[46]。
目前对于MOGAD易感基因的研究相对较少,2019年,我国研究人员对95例MOGAD患者(包含51例儿童期起病患者和44例成人起病患者)和481例健康对照进行HLA 基因分型,结果发现,HLA-DQB1*05:02-DRB1*16:02是儿童起病的MOGAD患者的风险单倍体型,且临床上携带单倍体型的患者复发风险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更高,而未发现明确的成人起病MOGAD单倍体型。计算机预测发现MOG细胞外肽段“VGWYRPPFS”可与HLA-DQB1*0502紧密结合而相互作用,体外实验结果则表明,这一肽段的突变降低了抗原-抗体结合,说明该肽段含有重要的抗原抗体结合位点,HLA-DQB1*05:02等位基因参与儿童起病的MOGAD的发病[47]。
在HLA基因方面,我国一项研究纳入102例MOGAD患者和541例健康对照,对中国常见的免疫相关SNP进行基因分型,结果发现,位于BANK1基因上的SNP rs4522865、位于核糖核酸酶T2(Ribonuclease T2, RNASET2)基因上的SNP rs9355610和肿瘤坏死因子α诱导蛋白3相互作用蛋白1(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induced protein 3 interacting protein 1,TNIP1)基因上的SNP rs10036748是MOGAD的易感位点;MOGAD与NMOSD和MS的遗传基础存在差异[33]。
4 AE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AE是指由一组由自身免疫性抗体造成神经细胞功能障碍引起脑功能受损症状的疾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精神症状、癫痫发作、脑病、认知和运动障碍等。在AE中,最常见的是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脑炎,这类脑炎患者体内存在自身免疫性针对NMDAR GluN1(NR1)亚基的抗体,该类抗体与NMDAR结合介导受体内化,减少了NMDAR在细胞表面的密度从而导致谷氨酸能突触功能障碍,最终引起神经元功能障碍。虽然自身抗体介导神经细胞功能障碍的原理相对清楚,但NMDAR自身免疫性抗体的产生和调控机制尚不明确。
在韩国一项纳入17个病例的小样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抗NMDAR抗体脑炎与HLA基因多态性的关系[48]。而德国一项纳入96例NMDAR患者和1194例对照的GWAS研究发现,抗NMDAR抗体脑炎的发病和位于HLA-Ⅰ类区域的HLA-B*07:02相关,但没有发现HLA-Ⅱ类相关基因[49]。我国一项研究对61例抗NMDAR抗体脑炎患者和571名健康对照进行了HLA-Ⅰ类和Ⅱ类基因分型,结果发现,HLA-DRB1*16:02与我国抗NMDAR抗体脑炎的发病相关,且这种相关与是否合并肿瘤无关;与携带其他等位基因型的患者相比,携带HLA-DRB1*16:02的患者治疗反应更差。生物信息学分析也显示,HLA-DRB1*16:02可与NMDAR的NR1亚基紧密结合,提示了其致病作用[50]。
另外一种相对常见的AE,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蛋白1(leucine-rich glioma-inactivated 1, LGI1)脑炎与HLA基因的关系也得到了多项研究。抗LGI1脑炎是由LGI1抗体介导的,LGI1抗体干扰LGI1和突触前受体A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ADAM)信号通路,降低突触前Kv1.1钾通道和突触后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唑丙酸受体(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 receptor, AMPAR)的表达,增强突触兴奋性,降低突触可塑性,造成严重的记忆损害。韩国一项纳入11个抗LGI1 脑炎和210例癫痫患者对照、485例健康对照的研究中发现,DRB1*07:01-DQB1*02:02单倍体型和 HLA-B*44:03、HLA-C*07:06等位基因型在抗LGI1脑炎患者中出现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8]。而德国一项纳入54例抗LGI1脑炎和1194例对照的研究则发现,抗LGI1脑炎与HLA-Ⅱ类基因区域27个SNP高度相关,其中SNP rs72961463与双皮质素样激酶2(doublecortin-like kinase 2, DCLK2)基因位置接近,rs62110161与锌指基因簇存在潜在关联,但不具有显著意义;也发现与包含HLA-DRB1*07:01、DQA1*02:01和DQB1*02:02的单倍型相关[49]。我国研究者则发现HLA-DRB1*03:01和DQB1*02:01等位基因型以及HLA-DRB1*03:01-DQB1*02:01单倍体型是抗LGI1脑炎的重要风险基因型,HLA-DRB1*08:03-DQB1*06:01和HLA-B*08:01-C*07:02 等位基因型也与可能抗LGI1脑炎相关[51]。2022年,一项多中心纳入269例患者和1359例对照的大规模研究验证了HLA-DRB1*07:01对LGI1的发病具有剂量依赖关系,此外,HLA-DRB1*04:02对抗LGI1脑炎的发病具有独立的风险,且与较小的发病年龄相关[52, 53]。
综上,基因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加深了我们对CNS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学发病机制的理解,但距离全面掌握这一类复杂疾病的遗传背景还有很远的路途。展望未来,CNS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遗传学研究将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基因位点与疾病易感性的相关性。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例如评估疾病易感基因的基因与基因相互作用和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对更深入了解疾病的遗传背景和发病机制意义重大。而疾病预测和治疗靶点开发也将成为CNS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