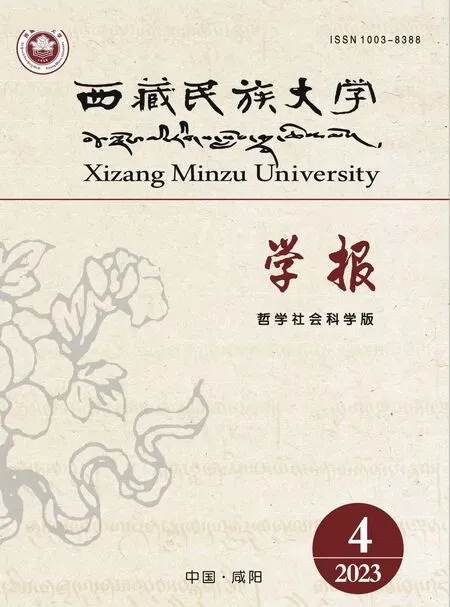近代日本人与中国西藏
——以寺本婉雅三次进藏为中心
陶云静
(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2.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引言
20 世纪初,一位名为寺本婉雅的日本僧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离开故乡,只身一人跋涉异域山河,几千里路程挨饿受冻、与野兽格斗、遭当地人袭击,好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在冰天雪地、极寒缺氧的环境中一步步向我国西藏迈进。他为何要历经千辛万苦前后三次尝试进藏?背后是谁在支持他?他的进藏活动对中国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带来何种挑战?深入分析这些问题,需要擦亮历史之镜,对个案做系统化解读,且不能只从汉文、藏文来搜集文献。本文将通过寺本婉雅亲笔日记等一手日文资料,对他的进藏活动做一梳理和研究。
一、日本人进藏活动的背景
(一)英俄在亚洲的势力抗衡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形势动荡不安。英国以印度为殖民地,不断向亚洲扩张。俄国也将魔爪伸向中亚和远东地区。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喜马拉雅地区和俄国势力范围内的蒙古地区历史上都有藏传佛教的传播,重要的宗教地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西藏成为列强虎视眈眈的目标。1870 年到1901 年,俄国多次派遣考察队企图进藏搜集情报,期间制造血案数次。英军1888 年袭击西藏隆吐山哨卡,1903 年又派远征军入侵西藏,1904 年8月攻进拉萨,9 月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的情况下强迫西藏官员签订不平等的“拉萨条约”,规定除英国外,他国代表不得干涉西藏一切事宜等旨在否定中国在藏主权、使西藏成为英国独占势力范围的条款[1](P93)。围绕西藏的英俄之争愈演愈烈。
(二)日本军队开始收集西藏情报
甲午战争后,列强开始加速瓜分中国。1897年俄国强占大连、旅顺并取得了从哈尔滨、长春至大连的铁路铺设权,英国强行租占威海卫和九龙半岛北部。列强在各地扩大势力范围的行为引起日本的强烈戒备,日本参谋本部负责谍报工作的核心人物福岛安正①提出在这一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大局势下,分割清朝最大的威胁是英国,其次是俄国[2]。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西藏,收集有关西藏的情报、窥探英俄在西藏的渗透情况②。唯恐在列强分割中西藏被英俄控制,影响最终波及日本利益。
(三)日本佛教界对西藏的关注
其实早在日本政府行动之前,日本佛教徒已开始关注西藏。明治维新后由于废佛毁释政策③,日本佛教处于危机状态。日本东本愿寺为改善现状,想到了与藏传佛教的联合。但当时外国人很难进入西藏。在这一情况下最初抵达中国的是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④,他根据自己在北京雍和宫以及山西五台山的所见所闻写成《喇嘛教沿革》(1876)一书,此书是日本最早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籍之一。之后欧美的佛教研究进展迅速,甚至有观点提出“大乘非佛说”,这使得大乘佛教的日本面临存亡危机,日本佛教徒深感前往西藏寻找佛教原典的必要性。1886 年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普通教校成立反省会⑤,在该会杂志《反省会杂志》⑥上,出现了前往西藏的计划。1898 年,僧人能海宽⑦和寺本婉雅开始实施进藏计划。⑧
二、寺本婉雅的第一次进藏
寺本婉雅(1872-1940),日本爱知县海东郡人。16 岁进入真宗大谷派高仓大学,23 岁进入真宗大学第二部,毕业前夕退学,开始为前往西藏做准备。
关于他即使是中途辍学也要前往西藏的动机,其弟子橫地祥原⑨曾问询过寺本。因为年轻时的寺本在学业上非常精进,同时还学习剑道。中途放弃多年的努力前往西藏,一定有非常强烈的目标。根据寺本的回答,他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后,“靠蛮力得不到永久和平,唯有依靠佛陀的慈悲教导,才能促进相互的觉醒。这也是佛教徒的当务之急”[3](P363)。这听上去好像是一名佛教徒强烈的使命感。寺本作为一名佛教徒,在日本佛教面临危机之时,也时常思考佛教的历史和变迁。并认为如果调查从印度、尼泊尔、锡金等地传入西藏的佛教历史,便有可能发现大乘和小乘的联系。同时如果开始东西佛教间的交流与联络,也能知晓“隐匿在黑暗中的蒙古和西藏”的情况[4](P754)。但是查阅寺本婉雅其他作品发现在其口述的《西藏秘密国事情》[5](P9)一文中,第三章标题就是“在喜马拉雅山峰树立日本国旗”。这又是何等的野心?寺本的这种想法后来也被日本军方利用,让他的所作所为渐渐偏离他作为佛教徒的初心。
(一)最初进入中国涉藏地区的日本人
寺本婉雅于1898 年6 月从日本京都出发,7 月抵达上海,8 月经由天津到达北京。到北京后寺本先跟随雍和宫的仁钦尼玛喇嘛学习蒙古语和喇嘛教,向沃塞嘉措喇嘛学习藏语。同时师从吴汝纶⑩学习易学等,为进藏做各方准备。1899 年3 月,寺本收到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介绍信,内容如下⑪:
西藏达赖教主狮座,恭维教祺安吉,福寿圆满,易胜额庆。西藏自古佛教盛行,风俗淳朴,唯因山河辽远,交通不便,未曾闻有敝邦人到境观光者,少洵为可憾。本寺兹遣派寺本婉雅,亲问教主安好并究教法之源流,考经文之异同,该员始到贵境,未通人情风俗而探教求经之业,固非容易,如蒙慈航指导,保护远人,俾伊得窥一斑,则不啻本寺之幸,实斯教之幸也。肃此布恳,并请崇安统希,慈照不戬。
大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
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虽有东本愿寺法主的介绍信,但其实寺本的此次进藏计划并没有受到东本愿寺的重视,也没有资金支持,此次进藏为寺本自费。当时日本在北京的特命全权大使矢野文雄为寺本办理了进藏手续,并给驻藏大臣文海写了介绍信,安排寺本与能海宽汇合。做好充分准备后,寺本于1899 年3 月出发,途经上海、重庆、成都,于同年6 月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与同为真宗大谷派的僧人能海宽汇合。二人选择的路线是沿金沙江畔向西北前进的最短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崇山峻岭、大河流淌,气候变化剧烈,能海宽在途中还被藏犬咬伤,一路上天灾人祸不断。二人于1899年7月20日抵达里塘,8月11日抵达巴塘,成为最早进入我国涉藏地区的日本人。虽持有护照,但在巴塘二人的进藏行为受到当地民众强烈反对。根据寺本记载,和他们同行的廓尔喀人(尼泊尔使节团)一路诽谤他们为洋鬼子,致使他们遭到当地民众和喇嘛的厌恶,若再让藏族群众得知他们是外国人,必惹来杀身之祸[3](P78)。于是寺本决定暂时返回打箭炉。而能海宽则决定寻找其他路线进藏。1900年3月寺本从重庆出发,经宜昌、上海,返回日本神户。
(二)引诱雍和宫喇嘛访日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后,寺本被委任为日本陆军第五师团翻译跟随日军再次前往北京。虽然是名翻译,但是寺本进藏的念头一刻也没有消失,在等待时机的同时开展西藏各方面的研究。寺本认为“邀请西藏喇嘛访日,会对将来有益”,于是积极奔走,与有关方面商议谋划。1900 年1 月,寺本在日记《新旧年月事记》[6](P20)中记录到“发电报给本山谷局长询问是否可以和喇嘛一起回国”(22 日记)”“得到本山回电,暂缓带喇嘛回国一事”(26 日记)[7]。可见寺本很早就产生了邀请喇嘛访日的想法。但其实刚开始,寺本邀请的并不是阿嘉呼图克图,而是受达赖喇嘛之命派遣到雍和宫的沃塞嘉措喇嘛以及担任雍和宫学长的蒙古僧人仁钦尼玛喇嘛[8](P5)。最后在寺本积极奔走下,雍和宫最高位置的阿嘉呼图克图决定访日。根据“宗教关系杂件”⑫记载,此次访日活动的人员有阿嘉呼图克图、雍和宫堪布喇嘛沃塞嘉措、代管秘书巴噶达尔,巴撒尔,从僧阿尔潭、大穵、文书刘明琨、从者何镇卿8 人。在寺本以及大河内秀雄的率领下,一行于1901年7月8 日抵达日本门司港后前往广岛。11 日抵达京都,寺务总长石川舜台、文书科长土屋观山等东本愿寺僧侣200 名前往车站迎接。车站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行在京都期间,到访了正传院、清水寺、袛园、南禅寺等京都名胜,还参观了第一绢纺织会社、京都织物会社等工厂。21 日前往东京,各宗派僧侣、东亚同文会会员等前来迎接,车站内外人潮涌动,欢迎气氛非常热烈。到东京后与山口中将、福岛安正少将等重要人物会面。访问团在东京期间,寺本身体抱恙,一直在东本愿寺浅草别院卧床休息。8月2日一行从神户出发,返回中国。
对于阿嘉呼图克图访日一事,寺本在日记中记录到:“此事不应被看作是宗教闲事,在蒙古西藏方面具有政治意义,受到朝野政治家的欢迎。”可看出寺本这名佛教徒的意图不仅在于佛教交流。
三、寺本婉雅的第二次进藏
(一)窃取大藏经
成功引诱阿嘉呼图克图到访日本活动后,寺本与阿嘉呼图克图建立联系,试图通过他的帮助再次进藏。同年11月寺本从日本出发,12月抵达北京雍和宫。在北京停留期间,寺本为查明是否有蒙古语版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经,前往大黑神庙,获得蒙古语经典,即大般若经、第二大般若经、第三大般若经、般若经、戒行经、诸品经、大宝积经、华严经、秘密经等。其实早在义和团运动后寺本作为陆军翻译来到北京时,他已在北京资福院发现藏语甘珠尔丹珠尔经典并带回日本,一份由宫内省(东京帝国大学)保管,另一部在东本愿寺(巢鸭真宗大学)保管。
(二)从塔尔寺到拉萨
1902 年3 月,寺本收到参谋本部东大尉来信,其中包含一份西藏地图⑬,上面有西藏和西宁之间的驿站名称,还有与打箭炉之间各站的距离。9 月末收到雍和宫来信,说阿嘉呼图克图送来的马匹骆驼已到北京,等待寺本一同前往西宁。
1903 年1 月29 日,寺本从北京雍和宫出发,踏上第二次西藏探险的旅程。同行者有阿嘉呼图克图之兄阿氏、刘喇嘛、王喇嘛及其弟子共5 人。一路上寺本详细记录沿途的地名、当地风土人情,军事情况等。途中经过草原、高原、荒漠,草原上“白天以野兽为友,夜晚以北斗星为伴”[3](P112)。高原寒冷无比,甚至有同行者冻伤。沙漠地带口渴难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2月26日抵达塔尔寺。抵达塔尔寺之后就进藏一事经常与阿嘉商议,但多不得要领,只能停留此地,研究藏文,等待时机。
在塔尔寺停留整整2年后,1905年2月24日寺本从塔尔寺出发。“这两年左右无一亲戚,没有知己,与藏人一同起居,共同生活,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迫害,孤独无人依靠。一直指望的阿嘉呼图克图也为俄国的怀柔政策所心动,中途将我抛弃。这种失望无法名状。在此我下定决心,不再依靠别人,靠自己。下定必死的决心,决然开启西藏的大门,从塔尔寺出发,踏上探险的道路。”[3](P150)
从塔尔寺到拉萨的旅途更加艰辛,一路上穿越无人区草原、到空气稀薄的高原时,甚至有同行者窒息死亡。一路上寒冷至极,途中行李掉落时,冻僵的手指都无法动弹拿起。终于在5 月19 日抵达拉萨。到达拉萨后,因为是阿嘉呼图克图弟子,寺本被邀请进入色拉寺。又因为伪装的身份是蒙古喇嘛,也收到哲蚌寺的邀请。寺本称自己只是暂时进藏,拒绝了入寺邀请。
在拉萨,寺本获得如下政治外交情报:
1、在格拉山麓溪流处有银币铸造局[3](P176)。这是前几年达赖喇嘛串通俄国,以参林堪布(侍读经师德尔智)⑭为顾问,从俄国引进的银币铸造机械。由于该银币交换率很好,藏族百姓对这位堪布的信任度提高,俄国势力也开始多方渗透西藏。
2、西藏上层中亲俄派占据优势。西藏领导层受参林堪布煽动,亲俄派较多,经常催促达赖喇嘛脱离清朝投靠俄国。而寺本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更多的喇嘛、僧官成为亲日派。
3、布达拉宫内部机密。寺本在日记中详细介绍了拉萨的概况、寺院情况、寺院教育制度等。还参观了布达拉宫。本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后不允许外人进入,但是喇嘛们想打听达赖情况,所以允许寺本进入宫殿。“我犹如进入宝山获得宝藏。得知了达赖喇嘛出逃的真相、俄国的关注、藏民对达赖喇嘛的信仰,以及达赖喇嘛和藏民对英国以及清国的感情,藏民的归向等。”[3](P183)
停留14 天后,寺本从拉萨出发,先是前往日喀则、扎什伦布、江孜,后又到甘托克、加林朋,最终抵达加尔各答。途中还捡拾石头,想作为日本矿物学参考带回日本[3](P192)等。此外最重要的还是收集情报。如到日喀则后记录当地军事情况:“有军府,常备汉兵百余人,携带旧式枪支,藏兵不满百人,携带弓箭火枪。操练如同儿戏。”[3](P189)到达江孜后,对英国的渗透情况有如下描述:“该地英领印度兵携带的枪支名为ENFIELD,五连单发,与日本造相比较小。英兵至今在此驻屯。”[3](P192)在帕里,“有汉兵十名,士官一名,英国人两名。设有电报局[3](P193)”“附近各山有银矿”。在国境地带“有英领印度兵驻屯。有临时兵房,士兵112 名,英兵若干,藏人使丁百余名。”[3](P194)在甘托克“有印度兵二百余,工人三百余。”[3](P195)寺本还拜访了甘托克王子。到加尔各答后受到英领印度总督寇松的欢迎。日本学者泽田[9]推测寺本应该是受到日本领事馆委托,作为日英同盟的一环,向英国提供有关西藏的情况、特别是俄国势力渗透情况,因此才受到英国政厅的欢迎。
1905 年10 月寺本回到日本后,先向小村寿太郎⑮外相作报告,后又在参谋本部做演讲⑯,向参谋本部提交报告书⑰。一直与参谋本部和日本外务省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四、寺本婉雅的第三次进藏
1906年9月,寺本再次抵达我国西宁塔尔寺,根据他在日记中的记载:“日本没有西藏教史相关史籍,我希望把原典翻译并介绍到日本,开始东亚佛教的联系,携手将释尊慈光撒满全世界。因此我来到安土⑱,将日本佛教介绍给藏蒙佛教徒,让他们认识到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及日本佛教的胜利。[3](P203)”可见此次寺本到我国涉藏地区,目的之一是寻找佛教原典并翻译,二是向藏蒙佛教徒灌输日本的强大。
此外,根据寺本原话:“学资并非由东本愿寺支出,也并非由官方支出研究费用,只是我为实现西藏研究的目的,历经前后十年的风霜,实现西藏探险之行,稍有名气。福岛少将见我胆量比常人大,忍耐力非常强,认为我的志向是东亚问题不能等闲之事,便给我支付资金,让我得以充分研究,弥补我不能全部购买西藏各参考书的遗憾。大隈伯爵⑲、儿玉大将⑳也称赞我的志向并支援我。”[3](P240)参谋本部次长、宪政本党总理、陆军大将甚至日本外相为何要支援一名僧人?不难看出寺本此行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参与。寺本所谓佛教交流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的觊觎。
(一)翻译藏文经典
再一次来到塔尔寺的寺本拜师学习,整日研究藏语、学习蒙古文。甚至抱怨做饭吃饭浪费了三分之一的研究时间。每天投身于藏文经典的翻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寺本完成了《喇嘛教史》○21的翻译、新旧喇嘛教各派大纲的大部分、日本密教和喇嘛教的关系等研究。
(二)接近达赖喇嘛
寺本的老师索帕桑布喇嘛是塔尔寺秘书官,又是阿嘉住宅的管家,当地人称老爷,在喇嘛社会中颇有名气。寺本借助这一知己关系,每日每夜诉说日本的威力和日本佛教的状态。“师父逐渐了解并为日本佛教之兴盛感到震惊,开始相信我说的话。我也得以接近当地有名大喇嘛,他们也渐渐开始相信我说的话。”[3](P219)寺本通过不断游说,向当地喇嘛灌输日本国力强大的思想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1906 年10 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抵达塔尔寺。得到消息的寺本立即写信给福岛安正少将。并积极展开活动,企图接近达赖喇嘛。整日混迹于朝拜队伍中的寺本成功引起达赖喇嘛的注意,达赖秘密派人邀请寺本,二人于11 月22 日会面。寺本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的介绍信递交给达赖喇嘛并送上净土三部经七祖圣教及日俄战争画帖一册。之后寺本多次拜访达赖的基巧堪布及僧官,大肆宣扬日本,离间他们与俄国的关系,劝说他们仰仗日本的援助。极力邀请他们派人前往日本调查宗教、政治、军事等文明制度。
1907 年9 月15 日,日本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写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寄到寺本手中,寺本随即翻译成藏文并呈交给达赖喇嘛,书信原文○2是:
大日本国大法主写信给达赖喇嘛台下
华历丙午十一月初六附贵翰并附赠品四种。台下日夜挂念的西藏佛教革新政策,我深表同感。观察时运趋势,佛教也需要世界范围传教。若台下有意愿派人到我国视察佛教,将不甚欣喜,并给予便利和指导。以此加深东亚佛教徒的情谊,汲取一源分流之教水,共同振兴法运。
大日本国本愿寺大谷光莹
明治四十年八月朔日
对此,达赖喇嘛回信道:
拥有广大智慧的大日本国大法主
日本帝国四十年八月初一的书信在藏历丙未八月二十日收到,内容已阅。就您提到的目前需要在全世界传播佛教,特别是联络东西佛教的思想,与我精神一致,非常欣喜。目前有意愿将有才之士派往贵国,但现在还没有准备恰当的方法,待我返回西藏后再派遣。希望对眼下的佛教联络给予帮助。
丙末八月二十三日吉日塔尔寺佛教总主达赖喇嘛之信
在寺本的撮合下,双方基本达成派人前往日本的共识。
从1906 年9 月抵达塔尔寺,到1907 年11 月回国,寺本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会见达赖喇嘛,撮合日本东本愿寺法主与达赖喇嘛的联络。向达赖亲信及当地有名喇嘛宣传日本,拉拢他们向日本倾斜,通过赠送物品、谈话等各种方法向他们宣传日本佛教和日本国力。同时认真钻研、学习藏语、研究喇嘛教,发现日本密教和喇嘛教的同缘关系,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交给日本学术界。
五、寺本婉雅成功进藏的原因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入侵西藏、俄国派遣考察队进藏考察。日本同一时期除了寺本婉雅,也有数名日本人成功进藏。日本人进藏活动相较于英国和俄国,有以下特征:1、基本都是个人进藏。相较于俄国多次派遣考察队,日本人的进藏活动都是由个人完成的;2、日本人进藏活动非常隐匿。英国明晃晃地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俄国考察队在考察过程中制造血案,与他们相比,日本人的进藏活动非常隐匿,多是乔装成僧人秘密进藏;3、日本10 名入藏者○23中有9 名成功进入西藏并达到各自目的。这与俄国六次派遣考察队一次都没有成功进入拉萨形成明显对比。可见日本人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与英俄一样的野心,在外交方面也是小心翼翼、很在乎与他国的交情。但是却在暗中想方设法接近西藏,获取情报、拉拢高层,企图从内部瓦解,在西藏内部形成亲日派。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
而寺本婉雅的进藏活动是日本人进藏活动的典型代表。他既与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等僧人一样有着佛教徒背景,又和成田安辉、野元甚藏等间谍一样收集西藏的各类情报。观察寺本婉雅的三次进藏经历,不难发现他最终成功进入拉萨并靠近达赖喇嘛、实现自己的目的是有原因的:
(一)个人因素
1、准备充分。第一次进藏前,他就先到北京雍和宫学习蒙古语和喇嘛教,还学习中文、易学。第一次进藏失败后,寺本没有像能海宽那样继续留在中国寻找其他进藏路线,而是先返回日本,等时机成熟再到北京,进出清朝皇室,与醇亲王、肃清王、李鸿章等人物来往,构筑强大的人际网络。其次,他通过邀请雍和宫最高位置的阿嘉呼图克图访问日本,建立日本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联系。由此,寺本也引起福岛安正、大隈重信等军事、政治人物的注意。这为他今后进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进藏前往拉萨之前,寺本更是在西宁塔尔寺停留两年之久,学习藏语、充分了解西藏、摸清进藏路线之后才开始行动。
2、坚韧刻苦的精神。寺本婉雅前往西藏并没有得到东本愿寺的资金支持。前期都是他父亲和其他一些支持他的人给他筹措资金。可以想象寺本一路上的窘迫。这些还是次要,前往西藏的道路困难重重,翻雪山、过大河、缺氧、冻伤、风餐露宿、饿了就吃冰块、累了就睡在旷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原野。过关卡时还要接受盘问检查,这些对身心都是巨大考验。但最终寺本都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进入拉萨。
3、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北京结识醇亲王、肃清王、李鸿章等皇室高官,在涉藏地区又能接近达赖喇嘛、阿嘉呼图克图,日本方面又有福岛安正、小村寿太郎等政府中枢人物支持他。这都离不开寺本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他构筑的这一人际网络不仅让他成功进入西藏,而且还窃取了大藏经、引诱藏传佛教高僧阿嘉呼图克图访日、成功斡旋日本西本愿寺法主代理大谷尊由与达赖喇嘛会谈(1908 年五台山会谈)○24。这些都是其他进藏的日本人中所看不到的。
(二)历史背景
1、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的影响。1904 年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进攻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外蒙古。在逃亡路途中,听闻了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此前一直有一位名为德尔智的俄国间谍在达赖喇嘛身边鼓吹俄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让西藏投靠俄国。但是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让原本倾向俄国的达赖喇嘛产生动摇。寺本婉雅第三次到达塔尔寺并成功会见达赖喇嘛,离不开日本胜利对达赖喇嘛的影响。加上寺本的大肆宣传和煽动,使得西藏内部逐渐产生亲日的倾向。
2、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需求。寺本第一次进藏没有东本愿寺的支持,更没有日本政府的援助。北京日本公使馆只是照例给他办理了手续,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支援与帮助。当他们到达巴塘受到当地僧俗群众排斥时,日本公使馆也是鞭长莫及,只能劝他们返回。因此在第二次进藏前,寺本通过寺务长石川舜台的介绍先找到了东京海军军令部子爵小笠原长生,向他表示了进藏的希望。小笠原长生敏锐地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并立即写介绍信给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少将。此后寺本多次拜访福岛安正及外务省政务局长内田康哉,多次与福岛互通书信,商议第二次进藏事宜[6]。因为当时的日本为防止西藏被英俄控制,正好也开始加紧关注西藏、搜集西藏情报、探查英俄在西藏的渗透情况。此时出现的僧人寺本婉雅正好成为他们获取情报的最佳人选。日本企图通过佛教这一渠道,与西藏建立联系,并借助寺本婉雅的藏语能力和他在西藏的人际关系网获取一手情报。寺本也不辱使命,成功进入拉萨后,记录当地风土人情、军事情况,在布达拉宫打探到了达赖喇嘛动向和藏族百姓的信仰等外界无法得知的机密。此外,在寺本撮合下,达赖喇嘛与日本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互通书信,初步达成派遣西藏使者访日的共识。在此期间,寺本及时联系福岛安正,汇报达赖动向及他本人在此地所作的工作。虽然寺本口口声声说都是为了东西佛教的联络,但他的这些行为,与间谍并无差异。
寺本在多次进藏的活动中,活动重心逐渐偏向为日本政府搜集情报、拉拢西藏高层亲日,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日本需求。寺本婉雅这名僧侣最终也没有逃脱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命运。
结 语
怀揣联络东西佛教、振兴日本佛教的目的,日本东本愿寺大谷派僧人寺本婉雅从日本出发,踏上艰难的西藏之旅。第一次进藏,1899 年抵达我国理塘、巴塘后,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拦阻,未能继续前进,以失败告终。寺本于1903 年再次从北京雍和宫出发,踏上第二次进藏的旅途。这一次先抵达塔尔寺学习藏语、等待时机,等了整整2 年后才从塔尔寺出发,一路上历经艰难险阻、冻伤缺氧,终于在1905 年5 月抵达拉萨。1906 年寺本以翻译西藏经典的名义再次到达塔尔寺。在此一边翻译经典,一边等待时机。待十三世达赖喇嘛抵达此地后想方设法靠近,并成功会见达赖。通过寺本婉雅的三次进藏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佛教试图走出国门与藏传佛教联合,以此摆脱废佛毁释带来的存亡危机和被欧美的佛教研究颠覆根基的危机。寺本婉雅是最初到达我国涉藏地区的日本僧人之一。先是窃取珍贵的大藏经,后又翻译西藏原典,研究喇嘛教,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尽心尽力。
其二、随着列强开始加速分割中国、在各地扩大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产生强烈危机。寺本婉雅为了实现艰难的西藏之旅,上下求索,建立各方人脉。而他高明的外交手段、坚韧刻苦的精神引起刚好需要西藏情报的福岛安正、儿玉源太郎、大隈重信等军事、政治人物注意。得到日本军方及外务省援助的寺本在研究藏学的幌子下获取西藏情报、拉拢西藏高层亲日,扮演了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的角色。
比起英俄明晃晃地入侵,寺本婉雅为代表的日本人进藏非常隐匿,难以发现。正因如此,这也对中国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带来巨大挑战。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寺本婉雅的鼓吹下开始相信日本的实力。在五台山会谈后也决定亲自访日并派留学生考察日本。但当时的日本非常在意自己在西藏的举动会引起他国戒备,于是寺本奔走已久的达赖喇嘛访日最终未能实现。根据寺本原话:“当时的访日活动并不是简单的日本旅游团那样享乐性质的交往。这次访问有外交言外之意,不仅可以让两国收获亲善和幸福,同时也可期待东西永远的发展。依据这一国际关系,日本民族将作为世界的救世主,将理想中的日丸旗插到喜马拉雅山顶。然而我十年的努力和效果全归于灰烬,实乃千古遗憾。”[5](P13)比起外敌入侵,这种内部的瓦解更需要我们及时发现和制止。寺本婉雅的进藏行为从这一层面也为我们敲响警钟。
总之,寺本婉雅是日本与我国西藏地方关系史上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注 释]
①福岛安正(1852-1919),日本信州人,曾任日本殖民机构关东都督府都督,陆军大将。此时为少将。
②同一时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指示潜入西藏开展谍报工作的代表人物有成田安辉、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
③发生于日本明治元年(1868),是明治政府为巩固天皇为首的中央政权而采取的神佛分离、神道国教化、排斥佛教的政策。
④小栗栖香顶(1831-1905),号莲舶,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学者。1873年到北京,1874年登上五台山。精通汉语。
⑤1886年,以学生禁酒和肃正佛教徒纪律为目的而成立。
⑥1887 年由反省会创刊。是一部主张禁酒、探索青年人生活方式的杂志。
⑦能海宽(1868-?),出生于岛根县净土真宗大谷派寺庙,12岁成为僧人。进入本愿寺派普通教校学习佛教知识,对西藏产生兴趣。1899年1月抵达重庆。在此获得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的旅行许可证。5 月12 日前往打箭炉等待成田安辉和寺本婉雅。6 月27 日寺本抵达打箭炉。二人于7 月8 日从打箭炉出发,经由理塘抵达巴塘,在此停留50 多日。寺本回国后,能海继续寻找新的进藏路线。1900年5月,能海未能前往德格,离开打箭炉后从成都前往西安,又从兰州到达西宁。原计划与商队一起进藏,但是遭遇盗贼,只得返回。再经由循化返回重庆。1901 年从贵州到达云南,到达大理后给老师南条文雄写的信成为绝笔,后下落不明。
⑧同一时期为寻求佛教原版经典、联络东西佛教进藏的日本僧人除了能海宽、寺本婉雅外,还有河口慧海、多田等观和青木文教。
⑨橫地祥原(1910-2010),日本大阪人。原名丰岗六助。1927年考入大谷大学预科,同时加入僧籍,改名祥原。经寺本婉雅推荐,在伪满洲国兴安北省公署文教科工作,后前往西伯利亚。回国后从事西藏研究。
⑩吴汝纶(1840-1903),近代文学家、教育家。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1902 年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
⑪笔者译。
⑫即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宗教关系杂件》。
⑬这份地图是寺本1901 年给福岛的,参谋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⑭德尔智出生于1853 年,俄籍布里亚特人,自幼聪颖有才。由于他会俄语、蒙语,了解欧洲形势,被认定为俄国在蒙古经营上最有为的人物。1873年德尔智进入拉萨哲蚌寺学习15 年,1888 年获西藏佛学格西学位。经哲蚌寺推荐,由他担任十三世达赖喇嘛侍读。
⑮小村寿太郎(1855-1911),日本明治时期外交官,1884 年进外务省,自1895 年起历任朝鲜、美国、俄国、中国全权大使,1902年出任桂太郎内阁外务大臣。
⑯《藏蒙旅日记》卷末略年谱。
⑰即寺本婉雅《西藏蒙古旅行报告》([日]和田大知.寺本婉雅《西藏蒙古旅行报告(1905 年)》翻刻[J].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021)。
⑱指安多地区。此处专指青海。
⑲大隈重信(1838-1922),明治时期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此时为宪政本党总理。
⑳儿玉源太郎(1852-1906),日本近代陆军名将,被誉为明治时期第一智将,曾任桂太郎内阁的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台湾总督等重要职务。此时为参谋总长。
㉑即《律史》(“西藏喇嘛教史”《佛教研究》1(1)~(3),1920)。
㉒笔者译。
㉓按照时间顺序,1899年8月11日,能海宽和寺本婉雅抵达巴塘,成为最早进入中国涉藏地区的日本人。1901 年3 月21 日河口慧海成功进入西藏拉萨,是最早抵达西藏首府的日本人。同年12月8日成田安辉抵达拉萨。1905年5月19日,寺本婉雅抵达拉萨并停留2 周。1911 年3 月4 日,矢岛保治郎进入拉萨。1912 年9 月22 日青木文教成功进藏。1913 年9 月28 日多田等观进入拉萨,他在拉萨色拉寺修行十年,是在西藏停留时间最长的日本人。1939 年5 月24 日野元甚藏到达日喀则。1945 年9 月2 日木村肥佐生抵达拉萨,10月西川一三进入拉萨。
㉔1908 年五台山会谈,详情参考:白須浄真.1908(明治41)年8 月の清国五台山における一会談とその波紋―外交記録から見る外務省の対チベット施策と大谷探検隊―.広島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二部第56号.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