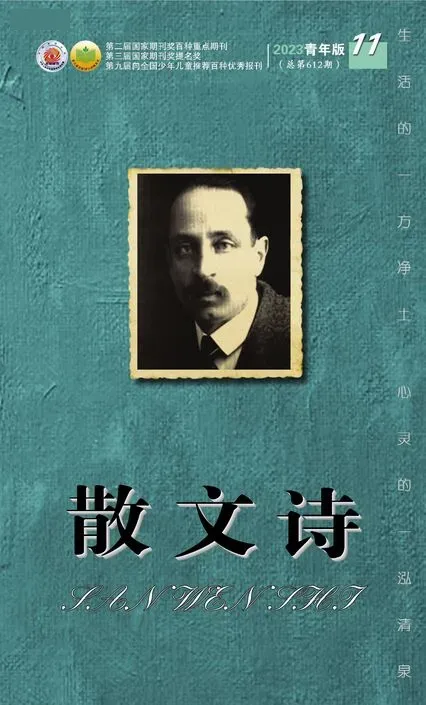永耀时空的一道闪电(节选)
◎张少恩
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1854.10.20-1891.11.10),又译阿瑟·兰波,19 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
1
19 世纪70 年代初,普法之战爆发,法国惨败。法兰西充满了屈辱而悲愤的情绪。整个社会剧烈动荡。
那时,塞纳河左岸的咖啡沙龙灯火微明,求变的思想火花四射,许多诗人、艺术家、自由主义者崇尚标新立异,新的主张和文学艺术的流派都急于扬帆。而位于巴黎北郊的小城镇夏尔维勒,有一个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兰波,他 “热爱理想之美”,热爱缪斯,崇尚自由,一颗心早已躁动不安。他厌倦了空气里挤满了石头的故乡,向往外面的世界,并嗅到了巴黎繁华的灯火和风云激荡的气味,仿佛雏鹰的翅膀对未知的天空般如饥似渴。
那年葱郁的7 月,不羁的灵魂携兰波出走。一定是瞒着母亲,或者负气,他身无分文,却登上了去往巴黎的火车。但因有逃票的嫌疑而被拘留,后来,老师伊赞巴尔出保这才获释,回到故乡。
铩羽而归的少年分外地落寞和沮丧。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2
9 月,夏尔维勒身披斑斓秋色。浆果喜获了甜美的阳光;红叶满枝,叙说热血在风雨中的传奇。
天空的蓝还是梦想的力量。
兰波的心,再次按捺不住。
鸟儿从林间飞出,嘹亮的啼叫一再强调飞翔的意义。这些,兰波早已领会,他出走的思想频频潮涨。
他依旧梦想着巴黎,澎湃的热血与激荡的风云同道。但他忌恨火车,讨厌警察钢铁一样的冷酷无情。这次,他绕开了火车,步行前往杜埃。新的道路,陌生的景象,让16 岁的少年自由的心变得雀跃起来。
一路赏玩,一路幻想,一路写诗……
他早已迷上了缪斯。14 岁开始写诗并屡次获奖。他曾将诗作寄给拿破仑第三个儿子,但却没收到回音。16 岁的他写出了《奥菲利亚》,耀眼的诗才如一道光喷薄而出。他真的应该走出故乡,见见世面,去巴黎沐浴艺术与文学的光芒!
警察又发现了他,视他为问题少年。飞起的翅膀再次被遣回。
纯洁的眸子里又增添一层阴云。血液里,叛逆的思想是狂奔的马蹄声。
也是!如果他是温顺的羔羊,缪斯就不会垂爱他,让他成为天赋异秉的通灵者。
他,天生就该颤动、高翔、闪耀……他对世界充满怀疑——小学时,就在校园的墙上写过“让上帝去死”。
甚至“他因不懂得动物学原理而希望飞鸟有五只翅膀”,母亲对他早已伤透脑筋,不然,怎么会希望他 “不停地离家出走”,仿佛他不上路,家,乃至夏尔维勒,就都不得安宁!
3
1871 年2 月,夏尔维勒还在寒冷的梦中。炊烟缠绕狗吠与鸡鸣,水轮的磨房如冬眠的蛰虫,乱石覆雪,道路冰冷。
这时,兰波身在夏尔维勒,心却在巴黎盘旋。受挫的翅膀又跃跃欲试。这次,他终于如愿了,巴黎用灿烂的灯火和满城的风雨接纳了他。
他来不及漫步和观赏风景,立即投入到了工人运动的洪流中。
他一直向往自由,这次,他名副其实成了自由的射手。他瞄准太阳,瞄准天狼星,瞄准巴黎的公敌……这位御风之人意欲扫荡黑暗的残云!
巴比伦兵营汇聚了青春的热血,激昂的情绪,但没有约束,是个大染缸。酒壮英雄胆,也壮狂野之心。洁羽的少年变得凌乱。
兰波——他不由自主地燃烧,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行动欢呼,奋笔写下了《巴黎战争之歌》 《玛丽亚的手》 ……
激烈的火焰却不由自主地沉沦,叛逆的灵魂在愤怒的风云和光怪陆离的灯火中变得迷茫……一颗闪耀的星,已偏离了轨道。
4
巴黎水深,激流暗涌,波诡云谲。
轻歌曼舞中藏着刀光剑影。争取自由的翅膀一次次掠过血色黎明。巴黎充满艺术和诗歌浪漫的气质,但也散发着固执、老朽、铜臭,以及浓稠的欲望,世俗的气味。
兰波继续放纵,轻狂的心涉世未深。
他恣意地挥洒自己:
无羁中,夹带着彷徨。
睥睨时,流露出卑微。
对于巴黎,他属于异质的介入,犹如古典而玲珑的杯水兑入电火,发生了激烈的反应。兰波给颇有名气的诗人魏尔伦写信,并寄去诗稿,令魏尔伦惊喜万分——
他正苦闷于自己沉滞的笔找不到突破口。
1871 年9 月,魏尔伦将兰波请到家中。他喜欢上了这个英俊而迷人的少年,欣赏兰波诗中那种傲然的,扫荡一切的灵异之光。
不羁的心,与求变的思想一拍即合。
漂泊的孤鸿有枝可依,于是,他们溅出了惊世骇俗的火花……
7
“我曾经被彩虹罚下地狱……” 那彩虹,就是他自由之自由的虚词,是幻想的悬帆预订了莫测的风浪和多舛的命运……而狂热和放纵离地狱最近——“我该为我的愤怒而拥有地狱,为我的骄傲而拥有地狱”。
他的心在深深地忏悔。他说自己是一头野兽。
单纯的灵魂与狂热的头颅狭路相逢,羞耻与忏悔在觉醒中飞溅、缥缈…… 《地狱一季》 由此诞生。但恰似一粒奇异的蚌珠遇见了有眼无珠的时代。
通灵的诗篇被堆放在故纸堆里,接受漫长而寂寞的蒙尘。
8
兰波的眼睛盯上了远方,匆匆的脚步又归入无主的行云。心灵急于开辟新的天空和命运,“自由地支配灵与肉的真理”。
他先是在欧罗巴的大地上游历,并不断地与艰辛和困窘交手。
为增加本领,他又回到斯图加特学习德语,并将《灵光集》的诗稿交给魏尔伦。这是诗的更为惊险的一跃——语言的炼金术愈加玄奥。
之后,他便断崖式地告别了文学的梦,参加了荷兰雇佣军,而后借着酒醉开了小差,漂泊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他去了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亚丁、蛮荒的非洲,与野性世界交往,不断变幻生命的场景。
他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角色——监工、保镖、勘探队员、摄影记者,咖啡出口商……他辗转于欧、亚、非的大地和山川,领略了异域风光,奇花异草,善人恶人,不同肤色的男人女人……
一个睥睨世界的蓬勃少年,变成了一个满面沧桑,瘦削而冷峭的男人,浑身都是孤独、落寞和失败的气味。
9
苦难与艰险消磨着兰波的躯体和精神。他不幸患上了恶性的腿疾。道路,成了他的畏途。未至的远方,已是绝境。
焦虑的兰波,时刻渴望回归。
1891 年,这个御风之人雇人护送,艰难地回到了巴黎,并做了截肢手术,但又迅速恶化。临终时,他对妹妹说:“已经是秋天了,是离开的季节。走吧,我需要太阳,太阳会治愈我。”
他不情愿地离开了自己热爱却又无比疑惑的人间。
——“横空出世的一颗流星,毫无目的地照亮自己的存在。转瞬即逝!”
10
他的诗龄,只有短短6 年,但却是法兰西印象派诗歌的奇峰,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也一直是文学、艺术可汲饮的甘泉。
年少的他,推开了诗歌沉重的大门,星光溅落一身,门楣上的银铃和清风使他茅塞顿开:民间艳丽的色彩,粗糙的装饰,祈福的绘画,工匠的招牌,古老的歌剧和小曲,都成了他诗歌的知音。司空见惯的事物在他的眼里都化成奇迹——牛粪成了玫瑰;尺蠖丈量至福;鼹鼠有童贞的睡眠;热气腾腾的鸟粪连着生动有趣的翅膀……
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平庸的生活,平凡的人间,最爱生花的妙笔。洁白的羽毛兑换燃烧的大海,大海,仿佛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波涛四起!
鹰为高远的天空立传;梦想为多舛的生命献祭。
11
诗歌因他而绮丽。
语言的断崖、裂谷,壁立千仞。
语言的飞燕灵巧,紧贴着地面又急速地弹回云中。
貌似疏离,零散,却又藕断丝连,气息贯通。灵动、缥缈、幽邃、神秘,宛若谶言和符文。
他制造虚幻,又利用虚幻抵达世界的本质。他让诗和语言返回到存在的意义,不固执,不恒定,变化无常。他混合所有的声音、色彩、形态,也混合人的一切感觉——生命的官能。
他是对的!
——语言和语言总会碰出火花,并将隐匿的事物照亮。语言的精灵;语言的幻彩;语言的星辰大海;语言的闪电……
我们需要闪电——没有闪电,世界真的会窒息。
而这一道闪电,永耀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