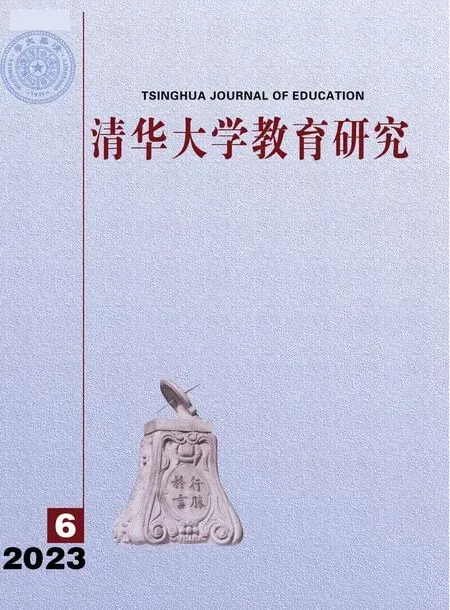企业教席的设立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
彭颖晖 刘涵滨 王慧聪 廖锌超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数字经济与管理系,江西 南昌 330052)
作为大学“心脏地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所在。我国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十分重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创新。《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创新基层教学科研组织和学术管理模式”。在实践层面,我国许多大学通过设立学部、学域等,对基层学术组织进行了诸多探新。
揆诸海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同样万众睢睢。近些年来,欧美尤其是法国大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基层学术组织——“企业教席”。相较于传统基层学术组织而言,这种新的基层学术组织有哪些新的突破?这一改革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机理?其对完善我国基层学术组织来说,又有哪些启发与借鉴?
一、 企业教席: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新现象
“教席”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Cathedra。它原指中世纪时期“主教座椅”,是主教布道时的“专座”。后随着教会法改革,教堂高级神职人员亦可受领“主教座椅”,因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兼具“大学教授”身份,这把“椅子”便流向了中世纪的大学(1)威廉·克拉克.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M].徐震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不过,在中世纪大学,“讲座”作为“权威”与“身份”的象征意义,大于作为“组织”的实际意义。直到16世纪前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唤醒了世俗权力,在政府掌控下,“讲座”被形塑为具有制度意义的正式组织;再到19世纪,柏林大学赋予它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功能结构,“讲座”才成为今天意义上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纵观世界大学发展史,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虽历经变革,但“讲座”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组织形态存在于大学中。“企业教席”是“讲座”这一组织形态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作出的自我革命。
企业教席,法文为“Chaires d'entreprise”,是法国为推进产业界与高等教育界深度融合,通过会聚产业界与教育界的资源禀赋,在基层学术组织层面进行的跨界合作。一般情况下,它由大学和一家或数家企业联合设立,并选聘一位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者担纲“教席教授”,由该教席教授与数位学界、产业界精英人才组成跨界团队。企业教席是一个跨界融合的团体组织,而非教授独占的个人岗位。正如,欧洲高等商学院学术和科学协会主席阿兰·奥利维耶(Alain Ollivier)所强调的:“教席是一个团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生产”(2)Frederique Letourneux,“Chaires d’entreprise: qui controle qui?”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chaires-dentreprise-qui-controle-qui.html.。通过团队协作,企业教席需围绕校企双方共同关切的行业企业问题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活动运行经费一般由企业捐赠资助。但它并非常设基层学术组织,而是根据校企双方协议约定设定的临时性基层学术组织,设立时长为1-5年不等。企业教席主要分为“教学教席”“研究教席”“教研教席”三类,“教学教席”专事人才培养,主要就课程开发、师资共享、企业奖学金、实习实训等进行深度合作;“研究教席”主要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科研攻关,或者直接承接企业外包的研发项目,它涵盖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生产转化等各种各样的研究(这些研究均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教研教席”则兼具“教学”与“科研”双重职能,融合了前两类教席的特点和优势,使校企合作易于实现多途径、全链路、深融合发展。(3)李敏等.高等工程教育产教融合实现路径探析——法国工程师大学校“企业教席”案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4):188-193.如法国国立高等信息企业学院的“工业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教研教席,它在开展“机器学习与海量数据分析”研发工作的同时,承担着为数据建模、数学技术和算法为主的硕士提供周期培训的任务。
自1986年法国埃塞克高等商学院设立全球首个企业教席以来(4)Frederique Letourneux,“Chaires d’entreprise: qui controle qui?”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chaires-dentreprise-qui-controle-qui.html.,近10年,企业教席在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法国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里昂商学院、克莱蒙高等商学院等各类“工程学院”及“商学院”中广泛设立。可以说,企业教席作为基层学术组织新样态,在法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建设范式。
二、从传统讲座到企业教席: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新突破
阿什比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5)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企业教席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新样态,同样离不开“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从“遗传”方面而言,企业教席脱胎于作为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初始样态的“讲座”(为了区别于企业教席,我们将在此之前的“讲座”统称为“传统讲座”);从“环境”方面而言,企业教席受惠于历史环境的大变革。脱胎于传统讲座的企业教席,折射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新突破,主要表现为组织理念由“自由探索”转向“服务需求”,组织形式由“封闭的常态化”转向“开放的非常态化”,学术质量控制由“同行评议”拓展到“外行参与”。
(一)组织理念的突破:从自由探索走向服务需求
长期以来,大学被视为“一个可以无条件地以各种方式追求真理的地方”(6)Karl Jasper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London: Peter Owen,1960),75.,由此导致传统讲座秉持“学术自由”的运行理念,探求纯粹知识。为防止社会世俗欲望对知识纯粹性造成“侵扰”,传统讲座反对一切知识的功用性,抵制承担任何公共事务,主张将“自由”视作探究高深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7)唐世纲.大学制度价值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153.。在传统讲座看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对纯粹真理性知识造成“牵绊”,必须隔绝在“知识伊甸园”之外,这一点可以从洪堡那得到印证。传统讲座创建初期,洪堡提出要“聘请最优秀的学者,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不管他们的研究可能得出什么结论,而政府的责任只是负责挑选合适的人员”(8)陈桂香,赵佳蕊.柏林大学讲座制及其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3):95-99.。此后,尽管“传统讲座”不断变革,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自由”仍是其坚守不变的基本理念。
然而,企业教席则将企业引入“知识伊甸园”。企业不再被视为牵绊知识生产的“局外人”,而是与大学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合作伙伴”。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勒图尔纳(Frederique Letourneux)指出,企业教席从启动研究路线,到参与研究生产,再到推广研究结果,企业是整个研究项目的利益相关者。(9)Frederique Letourneux,“Chaires d’entreprise: qui controle qui?”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chaires-dentreprise-qui-controle-qui.html.从这个意义来讲,企业向“教席”捐赠运行经费,并不是“纯粹公益”行为,而是夹杂着回报期望的“投资”行为。企业会对教席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出诉求,而教席会根据企业要求来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以及科研攻关主题。显然,“企业教席”不能孑然于企业现实需求之外,而必须将企业现实需求深嵌其中。譬如,卡斯特兄弟等企业与法国英塞克高等商学院共建的“葡萄酒与烈酒教席”,创建之初就确立了服务“葡萄酒与烈酒行业”宗旨,通过不定期为企业开展定制化培训、召开服务企业特定需求的主题研讨会、开展企业设定的任务式研发等(10)OMNES Education,“Les chaires d’entreprise,”https://recherche.inseec.com/activites-du-laboratoire/les-chaires-dentreprise.,为合作企业提供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知识服务。由此可见,企业教席是以服务企业需求为主导逻辑的,而不是像传统讲座那样以学术自由为基本理念。
(二)组织形式的突破:从“封闭”的常态化走向“开放”的非常态化
从组织形式来看,传统讲座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基层学术组织。一方面,传统讲座围绕“讲座教授”,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中心化”权力结构。教授对“讲座”主攻方向与设立时间具有绝对掌控权,讲座内部其他成员几乎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更遑论讲座外部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决策的可能性。以“讲座教授”为基石所形成的微观权力结构,扩散至整个大学层面,便形成了“教授寡头式”的大学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教授们“集体控制着院校内部的管理和财政预算,以及使用拨款……没有各讲座教授的同意,大学不能控制经费的分配或再分配”(11)伯顿·R. 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39.。另一方面,讲座制围绕学科,形成了封闭的中心化知识结构。它遵循学科逻辑,强调学科自主及其稳固的边界,主张学术组织间的不可通约性。因此,讲座与讲座间、讲座与外部社会间均竖立着无形的“高墙”。
随着知识走向经济社会中心,成为社会发展动力引擎,加快知识创新及转化速率,成为经济社会对知识生产新的诉求。但作为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大学因传统讲座与社会间横亘的“高墙”,在响应社会需求上反应迟滞。为提升大学响应速度,组织制度改革成为推翻“高墙”的重要路径,“企业教席”应此诞生。就具体举措而言,一方面,企业教席形塑了开放权力主体。与传统讲座对外部主体的“拒斥”形成鲜明对比,企业教席从制度上要求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教席”建设与治理。行业企业“曾经只作为外部的被征询者或相关群体,而现在已经被重新定义为‘用户’”(12)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不确定性时代的知识与公众[M].冷民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80.,受邀进入到原本“以教授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场。这样一来,企业教席通过提高主体异质性,打破了教授“一言堂”,进而使企业教席的权力结构更加开放。另一方面,企业教席构建了开放运行机制。与传统讲座作为稳固的“常态化组织”不同,企业教席是校企双方以项目为支点建立的“非常态化组织”。以项目作为组织建设支点,具有重大变革意义:首先,企业教席源起于实际项目,教席因项目需求而设立,亦因项目完成而终结。这使企业教席有效规避了学术权力僵化与组织机构臃肿。其次,以解决问题为本质的项目,推动企业教席建构“应用情境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社会催生了直面复杂现实问题的动态知识需求,这与以学科为单元所建立起来、具有稳固性组织结构的传统讲座形成巨大张力。有鉴于此,企业教席以具体项目为“武器”解构了传统讲座的稳固性,从而能灵活地吸纳跨界主体与跨学科知识,生产直面“问题情境”的定制性知识。例如,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联合滚动轴承制造企业斯凯孚公司(SKF)设立的“斯凯孚研究教席”。2013年双方签订了为期6年的合约,针对斯凯孚公司生产具体问题,例如“提高组件耐用性”“机械系统能耗最小化”等,召集了各领域专家学者与企业工程师,对上述问题展开跨界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合约期满后,校企双方选择续约,就企业发展的新问题,组成新的企业教席。虽然教席名称仍为“斯凯孚研究教席”,但在内涵上已然不同,新的企业教席基于“介质流体润滑”“预测材料摩擦系数”等新项目,形成新任务、组建新团队,在动态问题情境中发生了新更迭(13)INSA,“Chaires de recherche,”https://chaires.insa-lyon.fr/chaire-skf.。
(三)学术质量控制的突破:从同行评议拓展到外行参与
传统讲座的学术质量控制通过“同行评议”来实现。它“通过仔细选拔有能力的人来担当评议人得以维持,评议人的选择部分地由其先前对学科所做的贡献来决定”(14)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是一种典型的“专家型”质量控制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公众意见”作为影响“科研效率”的主观性因素,受到了教授共同体拒斥。他们通常认为,唯有共享内部科学范式的“专家”,才具备“解题”与“质疑”的能力。是故,他们的“创造性”也往往“只向这一专业的其他成员提出,也只由他们评价”(1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7.。以至于,他们主要乃至唯一的成果呈现形式,也都是渗着“专家气息”的学术论文(16)蒋喜锋等.从知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看高校职称评审改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89-94.。显然,在传统讲座中,学者们通常只在意学术同行的认可,并不在意成果是否“大有作为”、公众是否“喜闻乐见”。
“企业教席”的学术质量控制则主要依托一个由“外行参与”所拓展的共同体来实现。20世纪90年代,福特沃茨认为科学活动进入了“后常规科学”阶段,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决策风险,及系统不稳定性的研究阶段(17)Robert Costanza, ed.,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ustainabil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137-152.,科学与社会利益的联系愈发紧密,科学活动的评价主体,除学术共同体外,还容纳了企业、政府、公民在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塑造出一个“拓展的同行共同体”(18)理查德·惠特利.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M].赵万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8.。“企业教席”中的“指导委员会”,便是这一“拓展的同行共同体”的重要表征。它由高校和各合作伙伴的代表组成,除了教授以及大学研究部门的有关代表外,还包括了来自企业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等,他们共同负责设立“教席”具体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方向,以及后续质量验收等事务。在拉萨尔博舍综合理工学院的农业风险管理教席中,“指导委员会”还增设了“风险经理”岗位,以便强化对教席项目的效益控制(19)UniLaSalle,“Chaire Management des risques en agriculture,”https://www.chaire-management-risques-agriculture.org/projets-d-etudes/projets-d-etudes-en-cours?template=chaire_jul2019&is_preview=on.。此外,在评价成果上,“企业教席”虽然也注重学术论文,但不同的是,它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对合作伙伴产生实际效益的科研成果上,比如专利技术、调查报告、解决方案等。可以说,“企业教席”形塑了一种“对话型”质量控制模式,它将原本由“教授独占”的知识质量控制权共享给了利益相关的公众,使得知识生产不再囿于科学家共同体,从而具有鲜明的主体“异质性”。
三、知识转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内在机理
任何组织变革都有其社会变迁意义上的逻辑规定性(20)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1):94-108.。换言之,任何组织变革均不是“物种突变”,而是宏观社会变革的微观写照,它随着外部环境变迁而发生变革,具有丰富社会学意涵。相应地,从“传统讲座”到“企业教席”的微观组织变革,同样有其宏观社会变迁上的特定依据。具体而言,知识转型便是驱动其变革的重要社会过程之一。诚如有论者言:“知识转型”不仅改变了知识观念,更改变知识组织等(2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第2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25-29.。大学组织变迁一条重要逻辑就是“知识模式的变化……引起机构的革新”(22)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9-20.。
(一)知识生产的价值理念由“追求真理”到“满足用理”
长期以来,大学被视为“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高地。在洪堡看来,传统讲座要生产的是“纯粹的科学知识”,要进行的是纯知识、纯学理的探究,是以“真理性”作为知识的价值取向与衡量标准。它“仅仅同发现真理和关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像”(23)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由此,它被视作人类为解放自身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其本身就具有终极意义。那么,“为了获得真理……他或者她必须是一个摆脱了任何束缚的工作者,不接受外界企图灌输的或炮制的证据的指挥,不被收买”(24)胡克.学术自由原则[J].文摘,1985,(9):21-22.。正是在这一点上,传统讲座的“学术自由”理念获得了合法性。
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学“追求真理”的价值理念不断受到社会冲击,在内外部双重力量的裹挟下,知识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知识内部开始质疑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以“知识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为主的研究领域对科学的“真理性”形象发起了猛烈抨击。比如,波普尔指出经验主义认识论在“证实”上的固有缺陷:“科学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或得到了很好的证实的陈述体系”而是一种“猜测性的知识”(25)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 Hutchinson &Co.,1980),278-280.。是故,他认为“所有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26)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 Routledge,1962),34.。再如,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无政府主义”、曼海姆倡导“社会学决定的知识”等等,这些批判性的新思想、新观点从本质上肢解着科学的真理性幻想,进而打破了大学“不问世事”的知识论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外部环境变动,知识的功能角色亦发生了改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石油危机”诱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了法国在内的西方世界,靠资源驱动的“规模经济”策略宣布走入困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缝隙市场”引领,以创新为引擎的知识经济。在这一时期,知识被迫走出真理象牙塔,成为振兴经济的密钥。相应地,“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被视为大学知识生产的一项新任务(27)亨利·埃兹科维茨,劳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M].夏道源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1984年时任法国教育部长阿兰·萨瓦里制定了以提振就业、加速经济进步为导向的《萨瓦里法案》,其中提出高等教育要“加强与各公私立社会-经济部门的联系”,“实施与工业研究以及所有生产部门合作并共同发展的政策”(28)瞿葆奎,张人杰.法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15.。基于此,在内外部压力的双向挤压下,大学知识生产的价值理念开始由“追求真理”转向“满足用理”。这一转变表现在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上,便是“企业教席”所高扬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理念。
(二)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由“分立-稳固”到“整合-流动”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学知识生产都是一种“分立-稳固”的组织模式,它拒斥异质性组织间交互,并缺乏灵活性。首先,“分立性”是其主要特征。一方面,大学以学科为微观载体,在学科“社会建制性”影响下,塑造了“分立性”的学科共同体。它们划定边界,确立了独有的研究脉络与学术规范,在彰显各自“学科领地”独立性的同时,强调学科规训间的“制度壁垒”。另一方面,大学以“孤立的”基础研究为使命,在“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线性模式影响下,规制性地形成了与社会间的“分立性”关系。它强调“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先行官”(29)V. 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4.,基础研究最终会“无意识地”引领应用研究的进步,尽管基础研究本身只遵从学者自身的研究兴趣,绝不考虑任何社会效益。其次,由于内部共同体形成了封闭稳固的权力网络,以及外部社会维持了长期平稳发展,这一“分立性”组织模式在长期实践中得以维持,并形成了路径依赖。这样一来,组织的分立性被不断强化,组织本身也变得越发固化。最终大学以“象牙塔”的姿态在社会边缘伫立,其内部则是一个个松散林立的“学术部落”。
然而,随着20世纪进入最后25年,经济危机在破坏中孕生转机,新的生产方式解构了旧有的知识生产组织模式,催生了新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影响下,知识生产重心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一种“整合-流动”的组织模式应运而生。不同于旧有模式在“学科认知情境”中生产“普遍知识”,新的知识生产组织模式主张在“现实应用情境”中,开展“个性化”与“定制化”的知识生产活动。在这里,将科研理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资源,而不管不顾这些资源怎么使用,是否会有人使用”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30)彭颖晖,刘小强.学科评价:从学术导向走向服务需求导向——从知识与经济双重转型看学科评价改革[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17-124.。在应用效益观的牵引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超越了学科的无形边界,也超越了“基础研究”至“应用研究”的线性等级,是一种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互非线性作用”(31)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3.的知识生产模式。一方面,基于应用情境的复杂多样,不同的研究类型、不同的知识主体被“整合”进知识生产的核心地带,去中心化的多主体协作模式成为主流。在这一模式中,“跨学科研究”“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企业、政府等主体不再是大学“公共知识”的偶然受益者,而是“专有知识”的共同创造者。它以“开放整合”为渠道,充分激活了知识的经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基于应用情境的灵活多变,“旨在对长期合作战略进行战略性管理的思想正让位于以更分散的投资方式的研究和开发”(32)亨利·埃兹科维茨,劳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M].夏道源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33.,知识组织的工作方式向着“异乎寻常的、不连续的、短暂的、不稳定的”(33)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3.方向发展。在加速化的社会中,如何塑造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流动性”,使其更灵活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已经成为知识组织变革的时代性议题。总之,正是在这一“整合-流动”的组织模式影响下,“企业教席”消解了“学科与学科”“大学与社会”在理念与体制上的壁垒,形成了极具开放性的组织架构。
(三)知识生产的质量评判由“客观事实”到“多元价值”
近代科学革命后,科学取代神学成为人类认识和解释自然的新权威。在实证主义的引导下,“客观事实”不仅是科学自我标榜的“重要设定”,还是一切知识价值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由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所掌握。为确保知识的质量,一方面,他们遵从默顿的规范结构,并将此视为现代科学应有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他们以“同行评议”为机制,依据所受训练和专家知识,推选代表并授予权力(34)达里尔·E·楚宾,爱德华·J·哈克特.难有同行的科学:同行评议与美国科学政策[M].谭文华,曾国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6.,共同把控着科学知识的生产关口。在此,有两个隐含的逻辑预设:第一,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知识,它提供了关于世界最可靠的解释图示;第二,评价科学是一项职业性的活动,有且只有科学共同体能够胜任。两个逻辑相互支撑,形塑了现代科学“可靠”的自我形象,并赋予了人们“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本体性安全”(3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0.。
然而,随着知识生产的转型,上述两个逻辑被逐步解构,知识生产的质量评判由“客观事实”转向了“多元价值”。一方面,以“石油危机”为节点,社会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过去,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文明,使得人们乐观接受了“科学”所擘画的未来图景,“科学”已然成为利奥塔口中对人类具有解放与进步意味的“元叙事”。但是,当石油危机超乎预料地,对全球工业社会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以及生态秩序造成冲击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不确定性”“风险”等并不是“美好科学社会”的对立面,而是来自科学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不安,使得社会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产生怀疑。是故,进入科学评议的“黑箱”,将科学纳入公共议程便成为一项广泛性社会诉求。另一方面,由石油危机导致的政府资助下降,最直接地成了知识质量控制的转捩点。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后退,撕毁了科学与国家间的“社会契约”——过去,国家给予科学“慷慨的公共资助与不受控制的自由”,以换取“公共知识”的“约定”不再行之有效(36)古斯通,萨雷威策.塑造科学与技术政策:新生代的研究[M].李正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在新管理主义影响下,“效用规范被注入研究文化的每个关节”(37)约翰·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M].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89.,大学等知识机构不得不敞开大门,寻求市场与社会资助。因此,一个新的“契约”在科学与社会间订立。在这一“契约”中,科学必须向它的“雇主们”负责,并接受他们的审视。换句话说,评议科学不再是一项单纯“职业性”活动,而是基于投资效益理念,与资助者密切相关的“日常性”活动。这就使得,科学的成功不再取决于是否契合“客观事实”,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价值需求”。显然,伴随着“社会心理”与“制度机制”的双线转变,知识质量评判发生了内外部的双重松动,“大众科学”“后常规科学”“科学进入广场”等理念渗透进大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地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教席”将其学术质量的控制权交予了广泛的“阅听人”。
四、知识转型趋势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进路
知识转型是传统讲座向企业教席变革的“内在动能”,面向知识转型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将“变革”嵌入社会环境,以确保路径设计“合理性”的必要前提。在知识转型趋势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改革进路应诉诸以下几点。
(一)树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体使命
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第三职能”。毫无疑问,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第三职能”,是大学对知识经济兴起的响应。但随着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纵深发展,“第三职能”这一表述显然缺乏视角笼罩力,难以概括知识转型下大学的时代精神。这体现在,“职能”或“功能”一词有着明显工具主义倾向,以“第三职能”称述“服务经济社会”往往无法彰显大学作为服务者的主观“意向性”。换句话说,功能仅是表现“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者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38)彭漪涟,马钦荣.逻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63.,但这一“特性”和“能力”,有时与事物的主体性意志无关,无法有效、直观反映出主体能动性。如,尽管布什模式提倡的基础研究,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引领技术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实际重要作用,但其意向性上,这些非但没成为其目的,反倒被打上了“世俗偏见”与“有害压力”的标签(39)V.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4.,被其隔绝在外。不得不承认,“第三职能”视角下的大学社会服务,已然超越了传统大学“象牙塔式”的角色设定。但它显然是不足够的,在知识经济当道的时代,“功能性的”社会服务难以充分激活知识创造性及其价值,它更像是大学向社会的“妥协”,是一种失却灵魂的服务。
在知识转型背景下,“服务”不再是与教学与科研并列的基本职能,而是上升至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主导理念,成为“范导性的本体”渗透在教学与科研职能中。所谓“范导性的本性”,就是说“服务”不再是一项选择性的外在职能,而是组织必须坚守的内在本质。它所要求的是,大学基层组织必须重置旧有功能设定,将“服务”确立为本体使命,而非职能之一;与此同时,要以“服务”为导向统筹“教学”与“科研”,使大学学术在“服务导向”下实现范式革新。唯有如此,大学才能真正彻底贯彻“四个服务”精神,成为面向社会需求、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
(二)构建开放灵活的非常态化组织形式
“制度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可能就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导致制度惰性。”(40)毛加强.政府经济学[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231.近年来,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已经出现内部组织结构不断僵化的态势。为了适应不断加速发展的知识社会,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应该通过构建开放灵活的非常态化组织形式,防止组织结构的僵化,以此保障组织适应性和内在生命力。
一是由“学科目录逻辑”转向“超学科逻辑”。“学科目录逻辑”是一种参照“国家学科制度”,以“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层级划分为依据,来设置“学院-学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逻辑。权威的学科制度而非知识本身,成了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圭臬。但问题在于,知识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它不仅体现在知识量上的积累,更表现在知识生产方式本身的演化,而“学科目录”只是一种人为且相对静态的社会建制,在人类的有限理性下,它无法全然概括,甚至还会遮蔽知识自身逻辑。实际上,随着知识转型,学科内部分化与交融之势已然超出了“学科目录”边界,知识生产正朝着“跨学科、跨学校、跨界别、跨国界”的方向发展。因此,基层学术组织必须转向“超学科逻辑”,即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走出学科建制的“条块分割”,根据不同问题情境,在大学、企业、政府、公民社会之间,构建“多元交互”的知识组织网络。这一点我国大学多有践行,它们通过联合“异质性”学科和组织,建立了各式超学科“联盟”。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随着“联盟之风”日盛,大学必须时刻意识到,超学科“联盟”的实质,不仅在于组织形式上的“超”,更在于知识实质上的“联”。巴林杰(Bruce R.Barringer)曾指出,组织间形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就在于通过联合产生知识学习的机会(41)Bruce R.Barringer and Jeffrey S.Harrison,“Walking a Tightrope: Creating Value Through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no.3(2000):367-403.,那么联盟组织间的知识背景、知识需求是否“门当户对”,即知识间是否能够兼容、互嵌,就成为结成联盟的关键。因此,正如“多样性限度定律”强调:“系统的多样性不可能超过其所在环境的多样性”(42)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 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1.。结成任何联盟必须基于知识生产的实质性需要与可行性条件,而这些必须经过充分考察与论证,断然不能“为跨而跨”“为联而联”,只有确保组织间知识结构耦合,“联盟”才能实现知识价值共创。
二是弱化“蜘蛛式组织”逻辑,强化“海星式组织”逻辑。奥瑞·布莱福曼(Ori Brafman)曾用“蜘蛛”与“海星”,隐喻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其中,“蜘蛛”代表一种“中心化组织”,它有“大脑”般的中心控制系统,“触手”般的科层化组织建制,以及预设于“基因”里的稳定行动模式。面对平稳环境,其模式化行动可以高效地处理大部分事务,但在加速化环境中,“模式”反而成为“桎梏”,阻碍了自我进化。而“海星”则代表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组织”。它没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而是像海星一样,将主要“器官”遍布每条“腕”上,是一种分散式、扁平式的组织形式。并且,正因为它足够“扁平”且“分散”,它不像“蜘蛛”,它并没有一个既定的任务结构及权力结构,随着外部环境变动,它可以嬗变出适应性的组织形态,进行自我调整。因此,二者明显的差异在于,“砍掉蜘蛛的头,蜘蛛就死了;但如果把海星切成两半,你会看到两只海星”(43)奥瑞·布莱福曼,罗德·贝克斯特朗.海星式组织[M].李江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6.。简言之,去中心化组织是流动的。虽然乍看之下,它不具备中心化组织的有序性,也没有那么高效且稳定,但身处充满不确定性的知识社会,正是其流动性赋予了它快速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应强化“海星式组织”逻辑,突破传统学术官僚组织及其科层结构,以“非常态化”组织建设,来直面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依托“项目”“计划”等设立多主体灵活参与的动态机构,建立高效退出机制,以消解组织的固化和定式,确保组织的弹性和灵活。譬如,企业教席就没有一个固化的事权结构,它通过校企双方订立合同,明确自我的主要任务与运行期限。在合同期满后,它可以依据合同履行效度决定是否续约,亦可以根据市场变动,纳入新的合作者,结缔新的契约,进而重塑自身结构。
(三)形塑以服务需求为基准的质量控制机制
在知识转型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质量控制必须从价值取向到具体举措均立足“服务需求”。首先,从价值取向而言,要从过去“事实上的对”转向“价值上的好”,即从过去以“客观真理”为标准转向“效率效能”为圭臬。这就是说,基层学术组织不应仅追求知识在“客观事实”上的绝对可靠,更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现实经济社会的“价值需求”,以此作为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的重要依据。
其次,就具体措施而言,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拓展评价主体。我们并不否认同行专家对学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但今天,仅仅依靠学术同行是完全不够的。随着知识经济兴起,知识越来越作为“产品”流向市场与社会(44)吉川弘之,内藤耕.产业科学技术哲学[M].王秋菊,陈凡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0.,政府、企业、行业等成为知识产品的“消费者”的同时,亦逐渐扮演着知识评价者的角色,这些消费者的偏好无不影响着学术产品供给走向,是故,他们理应成为知识生产的“阅听人”。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社会到来,知识镶嵌于社会的各种生活场景,对普罗大众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正如派翠克·冯(Patrick Feng)所言:“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有权参与这种决策的制定”(45)古斯通,萨雷威策.塑造科学与技术政策:新生代的研究[M].李正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9.。对于“置身事内”的社会团体、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拥有知识生产活动的知情权及参与权。因此,必须也将他们纳入“阅听人”行列。二是改革评价参与方式。非学术同行参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评价,已逐渐成为一种惯常做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大多数非学术同行评价,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参与”评价,即非学术同行是在学术同行确定框架与标准体系后,按照既定的、烙印着浓厚学术底色的评判体系进行评价。这就导致非学术同行评价,只是拓展了评价主体的数量,并未彰显非学术同行的真实意志。归根结底,这种非学术同行参与的“多元评价”,依旧是学术标准主导下的“一元评价”。有鉴于此,为了扭转这种“走过场”的局面,推动非学术同行评价的“实质参与”:首先,评价体系制定初始阶段,邀请非学术同行深度参与评价理念构建、具体指标设计等,将非学术同行的评价标准融入整体评价体系,而不是在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后,邀请他们来彰显所谓的异质性评价。事实上,只有将“非学术同行”的利益诉求嵌入评价体系,重塑学术质量标准,非学术同行的“参与”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其次,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后,召集评价具体实施专家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在这一方面,国外评价机构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譬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在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评价前,通常为评价人员提供培训,使其充分了解评价理念与意图,并就评价计划达成一致。又譬如,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的大学“认证评价制度”规定,评价工作实施前,评价机构必须组织评审专家研修会,就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说明与研讨,以此深化专家们对评审方案的理解。对于建设“服务需求”质量控制机制而言,如若评价人员,尤其是学术同行对“服务需求”评审理念未彻底认同,对评审指标体系存有偏见及误解,那么即便是“服务需求”指标嵌入评价体系、“非学术同行”参与评价过程,所谓的“以服务需求为基准的质量控制机制”终将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