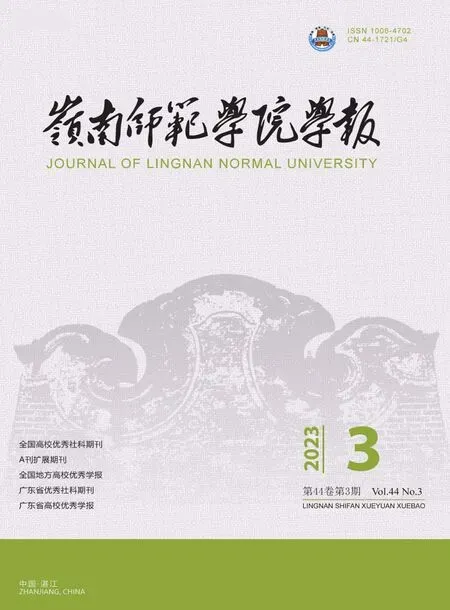体大思精,见微知著
——评张建军教授《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
乔 志 强
(岭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山水画不仅是自然丘壑山川风物的写照,而且与各时代社会变局、政治情势息息相关,更直接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等文化精神相映照。长期以来,山水画也因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受尊崇的画科,引发人们广泛讨论。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著述卷帙浩繁,成果丰硕,然亦良莠参差,真伪杂糅,迫切需要研究者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张建军教授积十数年之心力著成《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一书,无疑是该领域最新最重要的一部力作。作者以山水画论著述文本为研究对象和基础,聚焦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的核心命题、重要概念及其美学嬗变,探讨和辨析了诸多重要的学术论题,勾勒出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呈现出山水画创作与理论相互促动、赓续创新的生动图景。该著体大思精,中西互观,持论精审,见微知著,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突破与创新。
一、内容宏富,体大思精
《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一书,由“导论”和“正文”组成,共80万字,诚为皇皇巨著。“导论——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的历史脉络”在山水画艺术史、思想史和美学史的框架下,勾勒出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选取山水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代表人物、重要著述和理论观点进行阐释与剖析,力求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作者认为,六朝宗炳的《画山水序》一文,指出山水“质有而趣灵”的特性,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画山水之法,而且从欣赏的角度提出“澄怀味象”的观点,肯定了山水画“畅神”的审美内涵,在山水画理论发展史及其美学思想的建构进程中具有奠基之功;五代荆浩的“图真”论,强调山水画要明物象之原,主张在深入探索山水本性的前提下将“似”与“真”相区分,实现了对“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观念突围,是中唐以来山水画理论探索的结晶;北宋郭熙“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的艺术主张,综合了视觉提炼、情感投入、灵感激发、创意构思等多种艺术手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创作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是对山水画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的系统总结,为山水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苏轼“诗画一律”说及其“常形”“常理”分野论,深刻阐明了山水画创作中“形”与“理”的关系,引导后世山水画逐渐走上诗化之路;赵孟頫“作画贵有古意”说和“书画本同”论,投合了元代山水画发展的实际,不但为明清山水画的崇古和笔墨自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提升了中国画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笔墨”和“丘壑”之间的董其昌,创造性地提出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南北宗论”,其说风行一时,影响明清山水画创作达数百年之久。
作者将宗炳、荆浩、郭熙、苏轼、赵孟頫、董其昌等六位理论家视之为山水画理论发展史上的六座“高峰”,其余论说则组成山水画理论的“群岭”。“高峰”与“群岭”相互依存,彼此映照,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的宏大架构和丰富内涵。“导论”是总论,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及规律进行概括和提炼,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正文”4章为分论,依朝代次序,分六朝至唐、五代与宋元、明、清四个时段,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别从哲学、文化学、历史学、语义学、训诂学、美学、宗教学、比较学、接受学等视角,对山水画理论展开具体论述和评析。这样的内容及结构安排,将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研究置于文史哲综合交错,中西古今互跨无碍的宏大学术背景之下,既彰显出高屋建瓴的理论思辨色彩,又体现出见微知著精审考证的学术功力,可谓内容宏富,体大思精。
二、立论精审,新见迭出
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具体而言更是直接针对山水画理论著述的各种文本,但作者并非就文本而谈文本,而是在一个极为宏阔的学术视阈下,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层层深入地分析问题,进而提出新颖的学术见解。例如,中国绘画史上的“山水之变”,学界向来都以吴道子,王维为关捩人物,但该书作者却能在绘画艺术史、画论发展史和美学史的框架下,对此陈说提出质疑。作者通过回溯中国早期山水画发展的史实,剖析自六朝至初唐山水画发展缓慢的原因,认为这一时期山水画虽然在理论和精神上取得了独立地位,但其艺术技法和表现语言上却依然依赖于人物画或“山海图”之类的勾线填色,其所用“语言”与自身形象传达所需“语言”扞格难合,这是六朝以来山水画发展迟滞的症结之所在。作者通过对画史画论的再梳理、再解读,证实了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甚至于王维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山水画语言”,不能成为真正代表“山水之变”的关键人物。“王维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之变’中作用,来源于自苏轼以来中国历代文人画家对王维的推崇,尤其是董其昌南北宗论中对王维在中国绘画史地位的议论,王维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明显有后人拔高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而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1]165直至中唐时期,张璪专门研究“松石”,着力表现松石的质感,有了真正的皴法语言,从树石到山水,张璪偏师独胜,促成了“山水之变”。“对于张璪来讲,在‘树石之状’上穷极变态,达到神品的高度,固然是其重要成就,但为山水画开创独立语言,才是其在绘画史上更具有根本意义的贡献。”[1]170作者不囿成说,由画史及于画论,通过对山水画独立技法语言的深入讨论,于不疑处存疑,提出了改写山水画史的学术新见,这对于我们理解绘画史发展的复杂性,摆脱既有“线性”绘画史观的影响,正确认识中国绘画史的真实面目,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在考察诗画关系时,作者并不局限于提出“诗画一律”说的苏轼,而是从李白、杜甫、张九龄、李洞、皎然等人散见的诗歌中深度思考诗画关系,明确诗画相通之实,早在唐人那里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阐释欧阳修的绘画理论时,将“画画意”与“诗言志”相对举,运用文献学、训诂学的方法,对“意”与“志”的内涵及关系进行系统梳理,进而突显出欧阳修“画意”说的重要价值及意义,“这一方面为‘诗画一律’之说开了道,另一方面更从基本功能与特性上将绘画提高到了与诗歌同等的高度上”[1]295。作者还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传统哲学中的“言意之辨”,指出欧阳修的“画意不画形”实际上是创作论上的“言不尽意”论,“忘形得意知者寡”则是鉴赏论上的“得意忘象”论。艺文融合、文史互证,多学科领域间的交叉融汇,充分体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创见。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对明清时期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近代以来,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该书注意到了詹景凤的“逸家”“作家”之说与董其昌“南北宗论”的相通之处:“逸家”接近于董氏的“南宗”,“作家”接近于董氏的“北宗”,在画家人选划分方面也多有相合,最突出的是“南北宗”之祖与“逸家”“作家”之始均为王维和李思训。可见,二者理论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不同的是,詹景凤考虑到一些交叉情况,又列出一个“兼逸与作之妙者”,并将范宽、郭熙、李公麟等人列入其中。詹氏之说对画家风格的认识更加全面,或更能反映山水画发展的客观实际,但却远不如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广泛。作者对个中缘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认为除了詹氏之名望不如董其昌外,更重要的还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南北宗论’的核心是悟性,此点最能抓住明清山水画家的心,最能投合明清画家的观念;其次,‘南北宗论’更多模糊与歧义,这一点不仅没有影响它的传播,反倒扩充了其内涵,让不同倾向的艺术家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观念之点”[1]488。董氏以禅家的“南北宗”来比附山水画中的两种不同艺术倾向,但这两种艺术倾向的内核所指究竟是什么,是写意与工笔?是水墨与青绿?是文人画与画工画?是业余画家与职业画家?这些都充满了模糊性,也为后人不同的解读与取用留下了余地。董氏“南北宗论”模糊之中却又有一个清晰的立足点,那就是禅家“南顿北渐”的悟性之说,这一点则又最能契合明清画家的观念与心理。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但使詹景凤在中国古代画论史上的地位愈加凸显,而且使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内涵、外延及其影响愈显明晰,不得不叹服作者缜密的思考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令读者茅塞顿开。诸如此类的学术观点,立论精审、新见迭出,方寸之间显功力,细微之处见真章,给读者以拨云见日、耳目一新之感。这也是该书虽然体量巨大、文献浩繁,但阅读起来却并不会感到枯燥和单调的重要原因。
三、思考通脱,见微知著
学术研究中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辅相成,宏观结论只有建立在扎实有效的微观研究基础上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主观臆想,而微观研究也只有在宏观视野的指导下才不会流于零碎散漫面面俱到。该书可以说是宏观思考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例如,南朝宗炳《画山水序》一文,是断简还是全璧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该著参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纲领性的《原道》《徵圣》《宗经》3篇,以文本细读之法,指出《画山水序》的首章也是按这个套路展开的,开篇“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一句,是要将全文的主旨归结于道,也就是“原道”;接下来“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一句,用圣人的行为来说明事情的合理性,这是“徵圣”;“又称仁智之乐焉”,运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典故,这是“宗经”。原道、徵圣、宗经之后,才是本文的具体内容,最终以“畅神”赋予全文升华性的结尾,“其全篇有头有尾,逻辑连贯、思路清晰,虽篇幅短小,但结构完整,应当是一篇完整的全篇,而非断简”[1]69。这样的立论大处着眼、小处分析,思考通脱,见微知著,得出的结论也更加令人信服。
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一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文凡鄙,不类六朝人语”,又因萧绎为人物画家而非山水画家,断其为伪托之作。对此,作者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六朝文体语言趋于新、俗,唐宋古文对六朝语言的新、俗进行了反拨,进行了文学中的复古运动。“《山水松石格》的语言没有唐宋一些文章典雅,可能恰恰说明它是从隋代开始的文学复古运动之前的作品。另外就文章类型来说,《山水松石格》是‘格法’类的书,偏重于绘画技法方面的讨论,本来就有一点口诀的性质,这种口诀追求浅俗、明快,便于背诵,是其文体决定的。因此说其凡鄙,进而否定其为六朝作品,是没有道理的。”[1]115作者结合中国语言文体的发展历史,并从标准文体与通俗文体的应用之别方面,对传统陈说不惧权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体现出可贵的学术探索精神。现代学者谢巍说:“在《山水松石格》中,确有若干不符时代之言,如‘褒茂林之幽趣,割杂草之芳情’两句,所言‘幽趣’‘芳情’为文人画所宗之风格,尚未有见记载谓梁代已倡此风,当属伪文。”[2]39针对谢氏此论,作者检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不仅证明“幽趣”一词为六朝语,而且根据《南齐书·王融传》及《画汉武北伐图上疏》等文献,大胆推测《山水松石格》中的“幽趣”一词有可能是受王融上书论画的影响。画论、文论相互考证,文体语言相互比对,往复辩难,见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作者还将300余字的《山水松石格》分成19小节,在思想史、美学史、绘画史的视野下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进一步明确了该文为萧绎作品无疑,通过解读,发现原文脱漏且顺序颠倒情况明显,并以行文逻辑和语义内容对全文进行结构重排。这种尝试与探索,亦见出作者深入的思考与细密的解读,予人以极大的启发。
通脱的思考,细密的辨析还体现在作者对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等题画诗的解读中。杜甫赞王宰“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山”,后人据此多误认杜甫是精工山水之颂扬者,而对“畅神”之说无感。作者通过对杜诗的详细解读,指出杜甫的本意是在强调山水画要苦心经营,在心中丘壑内营,丘壑营于胸中,落墨自然一挥而就。杜甫将宗炳观画之畅神,拓展至作画之畅神,更能见出山水画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情状及规律。后人误读,“显然是把写意时代的创作理念上推到杜甫那里了,对杜甫诗义实是一种曲解”[1]150。这一论述澄清了人们对杜甫画学思想的误解,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又如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陈传席先生认为此说来源于南朝陈代姚最的“心师造化”,并由此引申出画家的人格、气质、心胸、学养以及风格等等,进而得出姚最的“心师造化”四字不仅比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字更简练,“且其义更甚”的论断。若仅从字面意义索解,陈氏此论似乎不无道理。但该书作者联系姚最《续画品录》中关于萧绎的段落,将“心师造化”置于上下文的特定语境中考察,进而明确指出:“姚最这里称颂萧绎的话,实际上来自老子,是称颂其能够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泛泛的赞誉之词,根本不是落实在绘画上的主张。”[1]156“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虽然与前代的某些主张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绝非仅仅是对姚最观点的发挥。事实上,张璪之说肯定了艺术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道出了主客观因素的互动关系,突破了早期画论中“以造化为粉本”,单纯模仿自然的观念,在绘画中引入主体心灵,使绘画与文学、书法一样成为一种“心印”,为文人画创造了理论基础。显然,该著联系上下文,综合文化学、语义学的文献与方法,点面结合、层层辨析,逻辑更为严密,立论也更为客观公允,不仅纠正了现有学术观点的偏狭与谬误,而且彰显了张璪绘画理论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四、中西互观,视野宏阔
画论研究显然属于“国学”研究的核心要义,在文史哲等传统“国学”范畴内揭示其美学内涵与精神价值已属不易。然而,该书的写作非限于此,而是在中西艺术学的比较和互观下,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揭示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独特的美学意蕴与文化价值。注重中西互观,跨文化比较也是该著在研究上的一个显著亮点。
在讨论苏轼关于山水画“常理”与“常形”的关系时,作者很自然地拈出法国汉学家、哲学家朱利安对此问题的见解:“‘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可它们的‘常’属于另一种秩序,即‘常理’。画家必须上溯到该常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捕捉该常理以形之。”[3]37作者认为:“朱利安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轼与郭熙之相通之处,即山水自然之物象的丰富性应当是画家关注的核心,无穷变化的自然需要在‘常理’层面上的贯通,而不是常形意义上的描摹。”[1]324引述西方学者对这一命题的阐述,显然也为人们理解苏轼的画学思想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阐述黄庭坚、米芾等人“墨戏”创作观时,作者引述康德、席勒等西方学者艺术“游戏说”的思想,找到绘画艺术与游戏之间相通性的理解。荷兰文化学者赫伊津哈在总结游戏的特点时说:“我们总结游戏的特点,称之为一种自由活动;作为‘不严肃的东西’有意识地独立于‘平常’生活,但同时又热烈彻底地吸引着游戏者;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靠它不能获得利润。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有序的方式,它有其自身特定的时空界限。”[4]15作者根据赫伊津哈的这一界定,进而指出文人“墨戏”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行为,“它与文人士大夫所热衷的从政、治民等严肃行为拉开距离,却又对文人士大夫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游戏活动,它有自己的规则,对于文人画家形成自己的社会团体具有重要意义”[1]321。文人“墨戏”艺术创作观的审美特征与精神实质在中西艺术理论的比较和互鉴中愈加明晰。
明代艺术理论家王世贞提出了“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的思想,形模是山水的轮廓,是山水画的基础,但山水的核心是气韵,二者结合,“乃为合作”。作者明确指出,“形模”之于山水画和人物画,意义完全不同,人物画的“形模”建立在具体的个体基础之上,而山水画的“形模”来自“对山水之形质的总体性把握与情感化理解”。为进一步阐释山水画“形模”与“气韵”的关系,作者援引西方著名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希关于西方风景画中“模具”与“情感张力”的论述,指出“形模”乃山水画创作的程式,犹如西洋风景画中为艺术家倾注想法提供容器的“模具”,山水画之气韵,亦即艺术家“情感张力”的表现。在中国山水画和西洋风景画的异同辨析中,“气韵”与“形模”的关系也变得愈加清晰。
明代沈颢《画麈》一文中提倡画家要有“孤踪独响,尤然自得”的自立精神,反对在“因袭”与“矫枉”的循环往复中形成的流弊与派系之争,所谓“流弊既极,遂有矫枉;至习矫枉,转为因袭,共成流弊”。为讲明“因袭”与“矫枉”的关系,作者引入了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姆诗学理论中“影响的焦虑”这一术语,即指“作为后来者的诗人,一边接受前人的影响,一边力图强调自我,形成与前代诗人相区别的艺术自我的这种‘焦虑’”。尽管布鲁姆讨论的西方诗学与中国山水画有很大距离,但用“影响的焦虑”这个词来分析明清山水画家的精神状态,则十分贴切,“沈颢谈到了明代山水画‘因袭’与‘矫枉’两种倾向的循环,如果以‘影响的焦虑’来解释,就可以看到,这两种倾向皆出于对前人伟大影响之焦虑。”[1]582通过中西互观,在中与西、诗与画的比较分析中,沈氏画学思想的内涵也就显得更加清晰。
再如,董其昌论绘画“下笔便有凹凸之形”与西画在物象上讲求立体感与质感相通。在此,作者特别提到了西方艺术史家班宗华关于董其昌接受欧洲艺术影响的观点:“董其昌当然知道那些欧洲书中的形象是绘画,并且认识到这些形象与几乎所有晚近中国绘画传统戏剧性的不同之处。这个认识与洞见迅速地转化为董其昌艺术与理论中重要的基本元素:‘石分三面’‘树四面皆可作枝着叶’‘下笔便有凹凸之形’‘分轻重、向背、明晦’。”[5]346作者虽然认为班宗华的论证,并没有确切证据,大部分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但也承认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览全书,康德、席勒、罗斯金、韦伯、海德格尔、赫伊津哈、布鲁姆、贡布里希、高居翰、班宗华以及米泽嘉圃、伊势专一郎、泷精一等国外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时现笔下,或为其理论依据,或为其比较研究之参照。中西互观之于该著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方法论,更是著者宏阔学术视野和渊博学识的体现。《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一书,研究对象虽然传统而且小众,但作者却能以之为纽带,架构起中西美学、艺术文化学之间的桥梁,实属难得。
五、结 语
总体而言,该著体大思精,中西互观,展现出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同时又立足于文献,以文本细读之法,反复辩难,见微知著,体现了著者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当然,该书在写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斟酌与商榷的问题。比如,全书洋洋80余万言,从大的结构上一级标题只有“导论”和“正文”4章,二级标题有38节,下含158个三级论题。章的篇幅及内容过大,节的数目偏多,若能根据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进一步的拆解和细化,全书在写作架构上则会更加合理与紧凑。再有全书文字体量巨大,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境。当然,客观上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著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研究山水画理论史不得不征引这些文献,有时为了阐明某一论题,还要重复征引,一部系统而又深入的《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史》部头小不了。但在写作中若能对部分论题进一步提炼,使之简洁化、精炼化,对那些重复引用率较高的文字作一些技术性的省减,则读者的阅读体验则会更好。然则瑕不掩瑜,该著的出版无疑将中国古代画论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