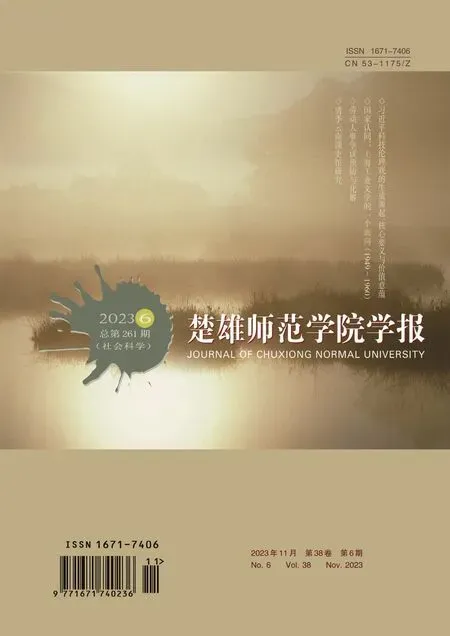从跨文化的视角看丝绸之路上的中原音乐传播
林雪莲
(福建省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中原音乐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以汉族为主体,融合清乐、燕乐等多种音乐风格。跨文化指具有两种及其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际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原音乐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接受。
一、敦煌曲子辞中的中原音乐
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①参见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发现、整理由中原传入的敦煌曲子辞作品二十六调,包括《还京乐》《竹枝子》《凤归云》《浣溪沙》《望江南》《洞仙歌》《更漏长》《长相思》《虞美人》《西江月》《拜新月》《破阵子》《柳青娘》《南歌子》《山花子》《望远行》《临江仙》《杨柳枝》《献忠心》《抛毬乐》《渔歌子》《喜秋天》《鹊踏枝》《天仙子》《梦江南》《送征衣》。
综合敦煌曲子辞作品,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中原作品中,抄写时间主要在曹氏归义军时期,以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时期为多,张氏归义军时期较少。除《南歌子·风流婿》《南歌子·奖美人》《南歌子·赏春》《南歌子·消暑》《南歌子·风情问答》《南歌子·长相忆》只大致可确定抄写于晚唐之后。《还京乐》四首抄写于张氏归义军时期外,其余曲子辞均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而所抄曲子辞也多创作于盛唐。河西本土作品中,曹氏归义军时期抄写的曲子辞仍占多数,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抄写时间集中在张承奉时期。同时,敦煌所抄中原作品多为中原南方地区曲调,河西文人也多以南方曲调作辞。敦煌曲子辞用调最多、传抄次数最多者,有《浣溪沙》《渔歌子》《南歌子》《望江南》,皆为南方曲调。河西文人以《望江南》《浣溪沙》二调分别创作六首、七首曲子辞,足见河西文人对南方曲调的喜爱。由此反映丝路音乐先由南至北,再由北到西的传播方向。
其二,敦煌写本中的中原曲子辞调中有来自西域曲调,如《倾杯乐》《菩萨蛮》,二者皆见录于《教坊记》。《唐音癸签》卷十四②参见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8页。与《通典》卷一四六均记载,贞观末,疏勒音乐家裴神符以琵琶作《倾杯乐》,太宗悦之,盛行于时。①参见杜佑:《通典》卷一四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61页。《明皇杂录》云“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其曲谓之倾杯乐……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②郑处海:《明皇杂录》,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3页。又宋膺《异物志》言“大宛马有肉角数寸,或有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相应”,可知《倾杯乐》自裴神符后流行于唐,因其作为西域乐舞节奏强烈、鼓点明显,故玄宗用于马舞伴奏。《菩萨蛮》见苏鹗《杜阳杂编》③参见苏鹗:《杜阳杂编》,江苏:广陵书社,1995年,第23页。云:“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人亦往往声其词”。《大唐西域记》卷四④参见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245页。云:“东女国,在吐蕃西,于阗南”,《资治通鉴》⑤司马光著,陈明星主编,梅凤华编注:《资治通鉴》,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第178页。贞元九年条引胡三省考订,东女国就是女蛮国,属西域。事实上,除上述二调外,《教坊记》所载各种曲目还有《凉州》《伊州》《霓裳》《拓枝》《龟兹乐》《怨胡天》《羌心怨》《西河狮子》《兰陵王》《剑器子》《醉胡子》《胡渭州》《胡相问》《胡僧破》《蕃将子》《穆护子》《大面》《醉浑脱》《南天竺》等西域曲调。这些西域曲调先东传至中原,又从中原西渐至河西,体现出丝绸之路上的胡汉相融与文化传播的双向度。
其三,敦煌写本中的中原曲子辞调多有变形。音乐文化传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还会受到多方传统的影响,比如《望江南》,《尊前集》录李煜二首(“多少恨”“多少泪”),均为“三五七七五”句式,《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载河西本土文人撰辞《望江南·负心人》(“天上月”)则变为“三六七七五”句式,第二句从五言变为六言。又有《定风波》,李珣《定风波》(“志在烟霞慕隐沦”)为“七七七三七、七二七七二七”,下片第二句“深处”当表示节奏停顿,敦煌曲子辞《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服偻俪未是功”)为“七七七二七、六七七二七”句式,中原曲调下片第一句七言变为六言。
曲子辞倚调而生,文句的改变反映曲调本身的变化,我们认为这里可能与西域音乐“急三拍”的影响有关。六言句式节奏不稳定,一般来说六言句式的节奏有“三三”“二二二”“二四”或“四二”,多是双音节连续出现,如《上陵》“山林乍开乍合”,《远如期》“累世未尝闻之”,而三、五、七言句式多“二三”“三四”“一二”这类单双音节交替出现,如《渔歌子》“春风澹荡看不足”“身闲心静平生足”。葛晓音发现,六言句搀入奇偶相间的三、五、七言句中不容易找到一致的节奏感。⑥参见葛晓音:《先唐杂言诗的节奏特征和发展趋向——兼论六言和杂言的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为使六言找到节奏感,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单行三句六言连缀、句句相押,如曹丕《黎阳作诗》(“奉辞罚罪遐征”),或六言与其他句式整齐间隔、规则交替,如曹丕《大墙上蒿行》是六言与七言的隔句交替产生节奏感。但是无主导节奏的杂言中的六言若不规则出现,就难与其他句式取得协调全篇的感觉。
以敦煌曲子辞《望江南·负心人》为例,曲子辞依曲调的节奏旋律而生,曲调固定而后文辞句式固定,以此辞、乐相谐。《望江南》为中原南方曲调,由此而生的文辞句式“三五七七五”与节奏最为协调,而敦煌曲子辞改变句式为“三六七七五”,很可能在传播过程中曲调发生了变化。葛晓音认为,六言曲调为促拍,若曲辞含六言则必然有相应的节奏变化,使其与三、五、七言曲辞节奏产生区别。⑦参见葛晓音、户仓英美:《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王昆吾认为,六言句是由三拍子组成的乐句,北朝以前的汉族歌辞六言句甚少,自北魏以来骤兴,六言调歌辞如《高句丽》《轮台》《回波乐》等都有胡乐之渊源,可视为急三拍子输入汉地之表现,①参见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8页。所言极是。敦煌舞谱多有“急三”,西域土族人的《安召》舞曲,即是用“急三”拍子节奏。“急三”者,彭松认为其节奏时值与“三拍当一拍”之义同。②彭松撰:《敦煌舞谱残卷破解》,《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敦煌谱中的“三拍子”多表示“急三”,即促拍。
西域胡曲多促拍,《隋书》卷十四有云:“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这里以“繁手淫声”描述“胡戎之乐”,指其节拍之快、密。举例而言,龟兹乐《疏勒盐》,《朝野佥载》卷一云:“麟德以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族’应作‘簇’,同‘促’,快拍也”。③张鷟撰,袁宪校注:《朝野佥载》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龟兹乐多为大曲形式,大曲由“艳”“解”“趋”组成,“趋”是节奏快速紧张的部分,《疏勒盐》既用于曲终,又是舞曲,《疏勒盐》当属于“趋”的部分。姜夔《大乐议》云“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王风桐、张林考证隋唐以前没有产生四拍子为一节的诗律,至隋后七言诗盛行才产生七言四击的节拍。④参见王风桐、张林:《中国音乐节拍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302页。辞、乐配合时,四拍子节奏多用于七言辞。我们不妨以此推测,以三拍子节奏用于六言辞也甚有可能。以上,我们可知中原曲调在西传的过程中节奏旋律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受胡乐之影响而产生。可见,若以河西为据点,中原音乐东来过程还会受到西域曲调的冲击与改造。
其四,敦煌所抄曲子辞多关注现实、歌颂英雄、热爱祖国,语言通俗平实、朴素自然,与精致浓艳的中原传世曲子辞形成鲜明对比。敦煌所抄中原作品中,《云谣集杂曲子》《洞仙歌》二首,虽是写思妇哀怨,却也言及现实府兵制。《望江南·娘子面》写劳动人民工作场景,女工兼任硙、磨,事忙工短,致使留麸于面侧,买者不来。《献忠心》有“自从黄巢作乱”“京华飘摇”等句,可知此辞写唐僖宗赴蜀以后长安之景。
如果说中原作品尚还有部分艳情酬唱,那么河西文人作品则几乎都是现实题材之作。《望远行》,所谓“年少将军”者,当指张淮深。“为国扫荡狂妖”“马蹄到处阵云消”云云歌颂淮深年少有为、建功立业,参建义军、收复伊州。津艺《临江仙》“大王处分靖烽烟,山路阻隔多般”“早晚夺山川”歌颂曹议金称大王,带领归义军出兵甘州回鹘,亲征张掖以静东羌的威武精神。《望江南·龙沙塞》涉及后晋天福三年中原王朝派遣张匡邺等人册封于阗国王途经敦煌之事,还有通使中原时周边蕃部多家阻挠之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以上总体概括敦煌写本曲子辞的传抄特点及中原曲子辞调的传播与变形,反映中原音乐沿丝绸之路西渐过程中华胡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更由点及面地体现丝路文化南北合、东西传的多向路径。
二、中原音乐西传的途径
中原音乐西传,大抵可分为两种,一是上层统治阶级传播;二是民间僧侣、艺人流通。
上层统治阶级以武力干预者,包括东亚境内音乐传播与境外音乐传播两种。首先,东亚境内中原音乐西传。西周穆王西征犬戎,带去《广乐》。《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登昆仑演奏《广乐》,与西王母瑶池唱和。⑤参见郭璞注,洪颐校:《穆天子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此虽为神话,但结合《史记·周本纪》周穆王西征犬戎(即今甘肃)一事,⑥参见司马迁:《史记》,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17页。以及《史记·赵世家》穆王向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一事,⑦参见司马迁:《史记》,第268页。可知早至西周穆王时期,统治阶级就曾征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并带去中原《广乐》。《后汉书·东夷传》①参见范晔:《后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18页。《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②参见陈寿:《三国志》,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第382页。记载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赐鼓吹伎人,男女群聚作倡乐。《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单于遣子诣阙,光武帝刘秀诏赐乐器鼓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单于亦遣子诣阙,更求乞和亲与竽、瑟、箜篌等诸音乐。③参见范晔:《后汉书》,第860页。《北史》卷九八《高车》载,永平元年,高昌国王麹嘉向魏请求内徙,宣武帝调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以迎接。柔然军队的伏图可汗以为孟威军是高车国援军,惊惧而逃。弥俄突趁机转败为胜,杀死伏图可汗,献贡方物于北魏,宣武帝遂以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赐予高车。④参见李延寿:《北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0页。《隋书·音乐志》⑤参见魏征等撰,吴宗国、刘念华标点:《隋书》,1995年,第237页。《旧唐书·音乐志》⑥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13页。载前凉王张重华时期,天竺乐传至凉州。公元384 年,前秦吕光攻克龟兹,次年携西域奇伎异戏等归姑臧,建龟兹乐部。吕光据守凉州时,留居河西的中原乐师改编流行的龟兹乐,遂成“秦汉伎”。公元386 年,北魏建国,逐步统一北方。公元435 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二十人出使西域,带回疏勒、安国乐伎的同时也带去中原音乐。公元439 年,灭北凉、平河西,将凉州诸乐谓为“西凉乐”,而后迁入平城。晋宋之际,五胡入侵,中原丧乱,前凉占河西,前秦通凉州,又将一部分中原音乐带至西北。
其次,中原音乐传播至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印度。塞种、乌孙、大夏、月氏、嚈哒、匈奴等民族原住地都是甘肃、青海一带,本身习得中原音律,随着他们的民族迁徙,中原音律随之流布中亚、西亚。公元前163 年月氏征服北印度,建立贵霜王朝,月氏人的南迁促使“羯鼓”传入印度。嚈哒在公元六世纪统治西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其南迁又促进龟兹五弦传播。突厥击败嚈哒,统治中亚,龟兹音乐随之传播。据此,本采·索博尔切发现印度的威拉瓦利(Velavali)和卡尔纳提(Knrni)调式是中原五声音阶的残余。⑦参见本采·索博尔切撰,司徒幼文译:《五声音阶体系和文化的历史》,《外国音乐参考资料》1978年第4期。《大唐西域记》分别借羯若鞠阇国戒日王、迦摩缕波国的拘摩罗王之口言称殊方异域乃至印度诸国咸唱《秦王破阵乐》。⑧参见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第248、535页。《明史》卷二十六云榜葛剌(即天竺)之技艺悉如中国,乃因前世流入。⑨参见刘毅:《明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国(经张星烺考证,指叙利亚首府安梯俄克⑩参见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旌旗击鼓,一如中原。⑪参见陈寿:《三国志》,第389页。西域音乐由于汲取中原、西亚、中亚文化的菁华,形成璀璨夺目的龟兹音乐,反过来说,中国音律得以传至中亚、西亚,南至印度,很可能是以龟兹乐为媒介,通过征战与民族迁徙实现的。
上层统治阶级以和平的方式文化输入者,如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王室成员的婚嫁联姻。公元前139—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朝设西域都护府,辖区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费尔干纳盆地,保证丝路畅通。《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10—105年,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为细君公主,联姻乌孙王猎骄靡,随行的乐舞艺人将中原音乐传至西域赤谷城。⑫参见班固:《汉书》卷九十六,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971页。晋傅玄《琵琶赋》序、《旧唐书·音乐二》又载,因细君公主作悲歌自伤,汉武帝闻之怜悯,使乐工以中原琴筝、笙筑之形作马上之乐以慰公主之乡思。为使其易于流通,以方外俗语命名为“琵琶”,至此,据琴筝改造的中原四弦琵琶、宫廷乐舞和江南楚声随细君公主传入西域。①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12页。细君公主死后,汉武帝又将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军须靡死后,因乌孙习俗,她先后嫁给翁归靡和泥靡。《汉书·西域传》记载,解忧公主与翁归靡的长女弟史,曾短暂地回长安学习鼓琴,回乌孙时途经龟兹,比宗室入朝后嫁给龟兹王绛宾。公元前65年,绛宾至长安入京朝贺,汉宣帝又赐歌吹数十人,绛宾回国后遂以汉室之礼乐治宫,将汉室中原音乐带入龟兹。②参见班固:《汉书》卷九十六,第972页。《北史》卷九九《突厥》载阿史那·处罗侯继位东突厥可汗,遣使向隋朝禀报继位事务,隋文帝杨坚赏赐中原鼓吹、幡旗。处罗侯以隋所赐之旗鼓西征,敌人望风投降,最终生擒西突厥阿波可汗。③参见李延寿:《北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6页。《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④参见许嘉璐主编,曾枣庄、分史主编:《旧五代史》卷一三八,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309页。载唐时有宁国、咸安、太和三位公主远嫁漠北回鹘可汗联姻,极大加深两国文化交流。其中,太和公主时,回鹘迎亲人马则部渠数千人,马二万匹,骆驼千匹,公主从中原亦带去随行大批乐工、艺伎,规模之大,自古从无,《旧唐书·回纥》云:“四夷之使中国,其众未尝多此”。⑤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旧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50页。
民间僧侣、艺人流通中原音乐者,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洛阳太常乐工避难西迁凉州。安史之乱后,盛唐时太常及鼓吹署、乐工数万人,梨园伎上千人流散民间,一些西域曲调随之西回,如曲调《何满子》《霓裳羽衣曲》。另外,因吐蕃人切断丝绸之路,大量西域使者、商贾、乐人不得不留居中原,与中原汉人通婚,造成胡汉文化进一步相融,比如此时回鹘人“改变衣服,一如华夏”,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北京:华龄出版社,2000年,第3893页。至丝绸之路重新开通,这群留居中原的胡人后裔又将所习中原音乐文化带回西域。僧侣西行传播中原文化者,如,保存智严和尚在沙洲巡礼圣迹后写留后记传播中原五台山文化,荣新江认为曹议金第一次遣使朝贡中原的深层原因正是智严大师的到来。⑦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0页。有同光二年定州开元寺归文和尚的牒文,牒文记载大唐阎浮提的名山简况,起五台,终华山。同一时期,还有留存《大唐五台山曲子寄在苏幕遮》,大抵也是由僧侣带至沙洲而流传开。事实上,曹氏归义军时期,经过曹议金、曹元德几次政变,有效震慑甘州回鹘,河西与中原通使的道路相对畅通,民间商贾、僧侣往来频繁,中原音乐也随之流入西域。
三、中原音乐接受影响的文化心理
丝绸之路上,中原音乐西渐的过程,是不断接受冲击与改造的过程,更是西域音乐不断华化、本土化的过程。外来音乐只有与华夏传统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艺术活动相结合,才能真正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换句话说,中原音乐西传所接受的外来音乐,实际上是其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如前说,早在隋唐胡乐入华之前,中原音乐就通过种种途经对西域音乐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贞观年间整理完成的十部伎中的“西凉伎”,之所以为华乐吸收、整编,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特征接近汉制。《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均提到,西凉乐是凉州人所传中原旧乐,是在以中原音乐为主体的情况下夹杂羌胡之声创制而成。更进一步说,当地凉州人接纳、改造西凉羌胡之声的深层原因,凉州的民族成分中汉族人占绝大多数。因此,中原音乐对外来音乐的自主选择性,一条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音乐文化有相同的文化渊源、音乐背景,这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中原音乐接受外来音乐影响的深层文化心理。
(一)西域音律与中原音乐传统之契合
龟兹乐是中外音乐的桥梁,融合多种西域音乐的菁华。我们分析龟兹音乐和中原音乐相合之处,可以探得西域音律中的汉乐传统之大观。《隋书·音乐志》云:
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从突厥入中原,善琵琶,听其所奏,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曰:“夫人在西域,称为知音,以七调,米若合符,又有五旦之名”。①魏征撰,吴宗国、刘念华标点:《隋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苏祗婆七调指娑陀力、鸡识、沙识、沙侯加滥、沙腊、般赡、俟利蹇。对苏祗婆所传龟兹乐,郑译云:
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访求,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一均之中,间有七声……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蹇,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②魏征撰,吴宗国、刘念华标点:《隋书》,第216—217页。
郑译发现隋唐宫廷旧乐“三声乖应”,若以苏祗婆的龟兹七调,则“冥若合符”。言“三声乖应”者,由于隋代宫廷旧乐律所用固定调唱名对一般乐者难度稍大。《隋书·音乐志》记载郑译与苏夔习惯主张雅乐当以黄钟为调首的固定调唱名法,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修一百零四曲,以每一种结声为一调,成“宫、应、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八调。③魏征撰,吴宗国、刘念华标点:《隋书》,第218页。但是,这种固定调唱名法虽然对每个音高形成严格标准,难免在音与音之间形成半音关系,这就要求乐工要有绝对音高来辨别、表演。囿于大部分乐工仅有相对音高,故郑译在听其演奏时难免有“三声乖违”之感。言“冥若合符”者,龟兹音阶是纯律七声音阶,与传统七声音阶相比,它的相邻两个音阶之间是纯律关系,不存在半音,听起来是极完全协和音程,人耳容易识别且易于演唱。另外,郑译还向苏祗婆学到首调唱名法,“黄钟”不但可以为宫,还可为商、为角、为徵、为羽,何昌林称之“为调”型音律,即旋宫转调。④何昌林:《苏祗婆的“五旦”理论》,《新疆艺术》1984年第1期。
在此基础上,郑译推演出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陈应时发现,《周礼·春官·大司乐》已有“黄钟为宫、太吕为角”等记载,说明旋宫体系“为调”型名法在中原本已存在,但到隋代可能被遗忘,苏祗婆到中原则重新促使恢复使用这一传统调名法,使仅具有相对音高的乐工也可演奏出音级相同的旋律,⑤参见陈应时:《论西域“五旦七调”》,《新疆艺术》1985年第3期。故云“冥若相符”。除“七调”外,苏祗婆的“五旦”也有中原音乐传统。旦,可看作均,西域五旦,即五个主音宫、商、角、徵、羽各自为调,应用在琵琶上,或指五次的琵琶定弦以保持空弦为五正声。据周菁葆考证,先秦中原音乐已使用“旦”作为“均”之术语,龟兹人借用“旦”字以称呼“五弦”。⑥参见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值得一提,龟兹音阶毕竟是以一个八度平均分成七个全音,它与中原传统三分损益的七声音阶相比,角、羽、变宫都低一个古代音差,苏祗婆所传龟兹七调中仅鸡识一声能与中原雅律中的南吕完全相合,故只能说“冥若相符”,大体相近。另外,阿斯塔纳(古代回鹘语,指“京都”)第206 号墓,即高昌王麹文泰时左卫大将军张雄夫妇的合葬墓,据金维诺和李遇春的介绍,墓有雕木为戏的乐舞戏俑,从制作与形象看,这些绢衣木俑都是表演歌舞戏弄的傀儡,⑦参见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吐鲁番古墓葬出艺术品》,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77页。可见中原文化曾对高昌乐与高昌回鹘汉国音乐文化之影响。
西域乐除乐律有中原传统外,所使用的乐器也颇有华夏渊源,比如筝、鼗、笙。筝在西域库木图拉石窟第63 和第68 窟顶部画面中出现,库木图拉石窟是汉僧居住最多的石窟,如前说,汉宣帝时解忧公主长女弟史来京师学鼓琴,后与龟兹王绛宾联姻,绛宾来汉学礼乐,归国以汉制治宫室,可能此时筝已传入西域。笙在西域石窟多有出现,但因年代久远,有些漫漶不清。据《渊鉴类函》可知,西域使用的当为十七簧的笙。①参见张英、王士祯:《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乐部七,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本。鼗出现在日本西本愿寺中亚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的绢画中,林谦三认为鼗是西域各族受之于汉族的,②参见林谦三著:《东亚乐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观点中肯。鼗在先秦文献中已出现,如《尔雅注疏》卷五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③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五,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周菁葆推测鼗可能是在纪元前后随塞种和月氏人迁徙入西域的。④参见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第99—100页。
以上可知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在乐律与乐器上的冥符之处,也是中原音乐接受外来音乐最重要的基础。
(二)西域曲度与中原音乐传统之契合
“曲度”,代表音乐的内在规范,包括乐调风格与曲体体制。曲子辞是为中原隋唐燕乐所配之歌辞,燕乐的内容包括胡乐、清乐和新兴俗乐。清乐,又名清商乐,曹魏设立“清商署”将清乐与太魏、鼓吹并立,北魏宣武帝将中原旧曲和江南吴声西曲合成“清商”,隋代又合南北音乐而为七部伎。由此可见,南方音乐是中原曲子辞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宫廷至民间沿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大量中原曲调合南北而西传。如前说,中原曲调传至河西所保留的大多是南方曲调。敦煌曲子辞中南音的留存,是中原音乐面对胡汉文化交融自主选择的结果,其深层原因是当地流行的西域音乐与中原南音的曲度特点相契合,即乐调风格清新、篇章体制短小。
具体而言,裕固族是回纥人与新疆人融合后南迁至河西走廊,与丝路上的汉人、蒙古人、藏人等再度融合聚居的民族。敕勒作为回纥的先民,裕固族仍保持着敕勒人游牧的生产方式,且继承其能歌善舞的传统,裕固族西部短调民歌有《垛草歌》《擀毡歌》《催眠歌》等,乐调流畅、体制短小、节奏鲜明、结构均衡,与中原南方音乐相近。西北地区的昌吉、宁夏、甘肃河西、青海的河湟流域是最大的回族聚集地,其先民是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华的蕃客、贡使和商人。回族民间音乐基本属于小调,题材内容包括生活感情与生产活动。《花儿》是其最广为传唱的曲目,单乐段结构、体制短小,采用五声音阶,其中徵调和商调居多,与江南民谣颇为相似。
正因为河西地区当地流传的民族乐曲有南音的特点,故中原南方音乐传至此处得以保留、传唱,这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四、余论
河西曲子辞传抄与创作,与丝绸之路东西通使的地域联结息息相关。我们发现,敦煌曲子辞的抄写较多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而较少在张氏归义军时期。据荣新江分析,张氏归义军晚唐时期还处在四处征战时代,而中原也局势动荡、战争频繁,这一时期的敦煌留存的中原典籍多是归义军使者得自京城长安及关内道北部文人之手。
曹氏时期,归义军政权已在瓜、沙地区站稳脚跟,执政者也着力于与中原地区联系,故多有中原传抄之作品。⑤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同时,我们也发现,曹氏归义军时期除多有传抄自中原的作品,河西文人的创作热情也在这一时期高涨。敦煌曲子辞河西本土的作品有明确曲调者五十七首,十九首抄于曹议金时期,十六首抄于曹元深、曹元忠时期,这可能也与通使中原有关。事实上,曹氏归义军历任领导人都积极希望通使中原。首先,敦煌是河西地区汉文化的代表,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既是民心所向,也是文化寻根;其次,自唐王朝覆灭后,河西诸少数民族纷纷独立,给归义军政权造成巨大威胁,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也是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慑和制约。
曹议金通使中原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甘州回鹘的征讨。甘州回鹘一直是归义军入贡中原的阻碍。公元914 年,曹议金求取甘州回鹘可汗之女,贞明二年(公元916 年)终于得到甘州回鹘的许可通使中原。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曹议金被正式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并于年底趁甘州回鹘内乱之际在肃州、张掖发兵征讨,终于彻底打通归义军与中原的联系。清泰元年(公元934 年)前后,曹议金去世,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又变得非常紧张,归义军内部甘州回鹘天公主的势力一再坐大。曹元德陈兵东界,对外震慑甘州回鹘,同时,曹元德在归义军内部发动一起针对甘州回鹘派系的政变,结果是甘州回鹘天公主的势力被清洗,其儿子可能全部遇害,至此,曹元德带领的归义军彻底压制住甘州回鹘,通使中原的道路也变得通畅。
在曹元德、曹元深的基础上,曹元忠时期归义军势力稳定,与甘州回鹘、于阗都保持较好的关系,甚至还帮助于阗通使中原。可以说,在曹氏归义军几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丝绸之路东西打通,从中原到西域的道路保持相对稳定、畅通,双方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在中原文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同时,河西文人由此激发创作热情,故河西本土曲子辞大多创作于曹氏归义军,尤其是曹议金、曹元德、曹元忠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