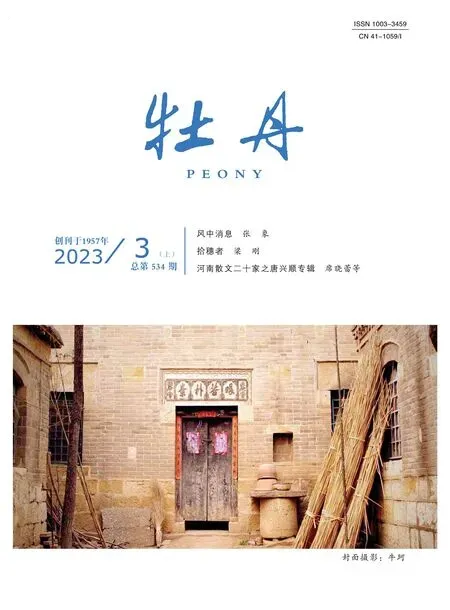水云天
羽瞳
许晴霁是唯一一个坐着救护车去大学报道的学生,这事儿挺稀奇,可以当作谈资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一辈子,虽说她本不是个话多的人,虽说她其实挺爱笑,长相也透着一股青春期女孩儿的亮。把她连带着行李一起捎送到大学的是她邻居,救护车司机,比她年长十四岁,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话不多,也爱笑,但笑得含蕴,名字朴素了些,古沐阳,朴素却不常见。
古沐阳的二手救护车本来是朋友承包的,挂在私立医院,机动性强些,后来朋友改开网约车,他便接过了这份临时工作。挂靠的医院许晴霁很熟悉,她小时候时常去那里的牙医门诊矫正牙齿,知道牙医门诊走廊最右侧的门轴有点儿故障,一直吱呀作响,听得牙疼的患者更加牙疼。许晴霁知道古沐阳不清楚这扇门的轶事,就像她也不清楚后者的往事。古沐阳是外地人,北方人,冬季很长的那种北方,即使在湿热多雨的南方,他身上依然残留着属于故园的干燥凛冽,是温度,也是烟草气,许晴霁闻到过,如同燃烧的具象化,北方雪后薪柴碳化的那种,像是室外对室内的渴求。
古沐阳的救护车不会开去牙科,他车上拉载过的人大多进了急诊,上个冬天的某个夜晚,许晴霁因为发烧去医院输液,裹着大衣晃荡出门诊大楼时,她撞见古沐阳靠救护车抽烟,车擦得很干净,这个人也干净,烟头火星明灭,人影被路灯拉得长长,像拔地而起的火种为他点了一支烟,顺势掠起他额前蜷曲的发丝。医院外隔条马路,做殡葬生意的门店密密匝匝,招牌黑白灰蓝,也被路灯映亮了。许晴霁注意到古沐阳正在打量那些招牌,唇间吐出的烟雾与他上下错动的喉结呼应,和往日一般讳莫如深。
当了大半年邻居,古沐阳会主动在打个照面时对许晴霁笑,同她寒暄,甚至嘱咐一句,太瘦,多吃点儿,要不高考遭不住。许晴霁不知道古沐阳具体从哪里来,却喜欢他有些轻俏亲昵的口音,好奇里头浑然天成的,属于一方陌生水土的关切。救护车旁的古沐阳先看过来,许晴霁挑了一下眉,年轻人总会更活泛些,她先抬了抬手,小跑过去,打了个招呼道,怎么了哥,哪里不舒服吗?
古沐阳很轻地摇了下头,这车,我的。
许晴霁哦了一声,探脑袋打量救护车,刚送人过来?
嗯。古沐阳把烟掐了,含混着,刚送来一个,二百多斤,帮忙抬了一下,累一身汗。他说到这儿,抬起嘴角笑了一下,眼尾也跟着抿出一丝深痕,那人要是像你这么瘦就省事儿了。
许晴霁下意识反驳,我挺重的,就脸小显得,前几天体检,我们班女生比我瘦的一大堆。
小孩儿总在莫名其妙的地方较劲,古沐阳被她逗乐了,顺着她的意思点点头,嗯是,女孩儿脸小好看。他糊弄完孩子,接着问,你这是?生病了?
许晴霁吸了一下鼻子,嗯,发烧,晚自习都没上完。
她身后还坠着硕大的书包,一动起来稀里哗啦地响,带着马尾辫也一翘一翘的。她妈工作忙,常年往外地跑,放养她十多年,小病小灾感冒发烧的,许晴霁都习惯了。不知道是不是下意识反应,人们在听到发烧俩字儿时都会伸手往病号额头上探,古沐阳也不例外,他用拿过烟的手贴上来,一股烟草燃烧完全的苦涩直往许晴霁不通畅的鼻腔里钻。她个头儿比古沐阳矮,于是她微微踮起脚往前探了探身,把额头往手背上送。这也是某种下意识,属于年少者对年长者的下意识,有点儿像撒娇,即使她独来独往惯了,却依然无师自通。
古沐阳说,还有点儿热啊。许晴霁听见了,她接,那您送我回去?我还没坐过救护车。
车内一样干净,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气息,很冷,尖锐而透彻。许晴霁坐在家属坐的折叠凳上,书包搁在一旁,两条腿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她有点儿好奇,也有些无措,她和古沐阳做了小半年邻居,今晚是第一次从陌生走向相熟。车窗外路灯拔地而起,星辰如一场旷世大梦,车辆自身边飕过,远比白天迅捷,也毫不留情,夜晚的出租车和城市灯光幻化成烂漫光斑,绚丽而寂静,便将月亮衬得孤独了。
月圆夜,月亮总是这样,越是圆满越是孤独,勾月清泠泠的,更似不屑。
古沐阳背对着他,车内没有病人,救护车便显得比普通车辆更加沉默了。许晴霁望了一会儿古沐阳裹在深色短袄里的背影,听了一会儿他哼的不成曲调的歌,后门车窗逐渐漫上哈气,涂抹了一层不规则的白雾。他鬓间也有些白,许晴霁想,背影和笑容不同,没那么温和,有些严肃,和他的车一样沉默,像是要把一段路,自身后斩断。
车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古沐阳回头瞥了她一眼,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许晴霁摇摇头。也许就是这样,她用烧得混沌的大脑混沌地想,因为有许多人在他的车上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绿灯闪烁,车辆同时开始移动,许晴霁想起古沐阳哼的那首曲子,应该是一首俄罗斯歌曲,但对方明显不懂俄语,也抓不准节奏,倒是不怎么跑调,在灯光不足的车厢内,像电影里上战场前最后的松弛梦呓。许晴霁笑了一声。古沐阳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坐坦克。
古沐阳也笑了,你是不是烧糊涂了?许晴霁双手撑着座椅,肩膀陡峭,脑袋却耷拉着,发辫也耷拉着。她没把发烧的事儿告诉家里人,反正打小儿就是这么过来的,家里人都太忙,她就像株营养不良的树苗似的,缺少年长者的呵护,浇点儿水就能生机勃勃。夜色总是蛊人的,她就着这个角度偏过头,将目光放置于框住夜色的前窗以及狭窄夜色中的背影,这个人比她年长,有些英俊。
应该是吧。许晴霁回答古沐阳。
他比我年长。许晴霁告诉自己。
到了家门口,两扇门相对,许晴霁家门上贴了福字,已经开始发脆卷边,古沐阳家的门上只有几张开锁通下水的小广告,上一个租客什么都没留给他,看上去他也没打算留下什么。门锁被拧开,进门前,许晴霁听见古沐阳顿了顿,还是开口道,我今晚在家,难受了就敲门。
十七八岁的少年人,总是会因一些来自陌生人陌生的亲切而雀跃。
许晴霁趴在书桌上写了一会儿作业,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被离家不远铁道口的警示音惊醒时,碳素笔在英语报纸上拖了一道细长的印子,她半张脸印在报纸上,油墨味儿直呛鼻子。许晴霁睁着眼茫然了片刻,夜里十点半,挂钟滴答作响,时间的流淌因夜色加重为凿刻,在熟悉的房间烙下深痕。嗓子很干,有点儿疼,每一个细胞都因升高的体温变得轻盈,骨节却又灌铅般沉重,她探了探自己的额头,还是有些热。冬天,房间里却很冷。
有火车驶过,车轮碾过铁轨,带来轰鸣与振动,也带来无数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素昧平生,面容模糊。许晴霁将自己撑起来,她不知道火车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楼外横亘马路的这截铁轨不过是旅途中的一段造访。人和人也一样。女孩儿想。
于是她敲响了古沐阳家的门。
许晴霁有点儿紧张,她只敲了一遍,多等了一会儿,门那边传来拖拖沓沓的脚步声,接着门开了,先是一股烟味儿,不重。男人比她高了一个头,同她说话时微微垂下了眼,不舒服?
许晴霁嗯了一声。古沐阳安抚地笑了一下,进来吧,晚上刚好熬了粥。
他的房间也一样干净,同自家一样的布局,东西几乎少了一半,许晴霁坐在古沐阳卧室床上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白粥发愣,属于单身男人的整洁与凌乱共存在狭小的房间里,被子堆在床角,枕巾开着两朵艳俗的大牡丹,许晴霁嗅到一股肥皂味儿,还有散得差不多的烟味儿。烟灰缸香烟和火柴都放在桌上,旁边放着一本掀开的笔记本电脑。她其实已经不怎么烧了,疲乏的胃袋也感觉不到饥饿,她只是疲倦,或者说孤独,那列火车很长,现在才彻底远去,古沐阳拿了一罐白糖进来,他说药苦,他小时候吃药,得往粥里拌糖才能哄下去。
许晴霁没往粥里拌过白糖,但她乖乖照做了,她想当个小孩儿,就现在。古沐阳坐在桌前椅子上叼了根烟,没点燃。他话音里含笑说,那时候糖还放在搪瓷缸子里,上头画鸳鸯那种,搁在厨房柜顶,家里大人不让碰。
许晴霁喝了一口粥,米香和甘甜顺着干哑的嗓子向下滋润。她发现古沐阳多很善谈,也许是出于敏锐,很多事他能看得出,便不过问。许晴霁靠着床头看他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他头发半长,将小半张脸遮掩起来,发尾下延伸出颈项温和的弧度,松垮垮的白毛衣暴露出两痕锁骨,腰胯陷入椅子,两条长腿随意搭在一起,脚踝细瘦踝骨突兀,足弓勾着拖鞋摇摇欲坠。
他偶尔甩甩头发,微垂的眼尾拨云见日,那双眸子亮得剔透,眼尾却无限收敛,稳妥成一丝细长的纹路,蕴藉着他有所指摘的喜怒悲欢。
许晴霁问,您在写小说吗。
古沐阳顿了一下回答,剧本。
许晴霁哦了一声,您是编剧?
古沐阳先是摇了一下头,别老您您的,都把我叫老了,你就行。接着他回答,不算编剧,算枪手,拿钱办事,有活儿时少,没活儿时多,就如今晚我就得赶进度,估计没的睡了。
许晴霁半懂地点头,可以问问剧本叫什么名字吗。
古沐阳沉吟着,叫《越轨》,不过以后肯定不叫这个。
兴是因为胃里有了东西,或者两个人的房间就是比一个人温暖,许晴霁昏昏欲睡,她想说,我先回去了,您……你也早点儿休息。但困倦突然如潮汐一般涌来,在意识到时已经淹没通往岛屿的天桥。古沐阳敲了几下键盘,正好看过来,目光像长辈,低哑的嗓音在深夜有种石子沉入河沙窸窣。他好像说了句什么,许晴霁没有听清,他只听见火车即将到来的气流声,仿佛海浪拍打沙滩。
她想,睡吧,睡醒病就好了。
许晴霁时常会回想起那个夜晚,昏沉的梦境里,她听到古沐阳哼唱的那首俄罗斯歌曲,她的外语天赋令她回想起曾经听过的那几句歌词,想起被她放弃的芭蕾和即将选择的外语专业。半夜时她又被火车吵醒了一次,半睡半醒间看到古沐阳仍然坐在电脑前,指间夹着一直未点燃的香烟,他用拇指抵着眉心,微微弓着背,昏黄灯光下,线条流畅如勾月。许晴霁突然觉得这个夜晚很是荒唐,车声隆隆,不知始终,似某种越轨。
她记起歌词里唱。
叶子从白桦树上落在肩膀
它就像我一样地离开了生长的地方
和你在故乡的路上坐一坐
你要知道,我会回来,不必忧伤
救护车停在大学门口,打断了许晴霁的回忆。她考了本地的大学,法语专业,已经定了日后出国留学。报道这天家里还是只有她一个人,母亲出差在外,她只提了一个行李箱,收拾了些换洗衣物,古沐阳送她也是顺路。果不其然,从救护车上跳下个新生这事儿引得不少人侧目。古沐阳从车窗冲她摆摆手,让她注意安全,有事儿打电话。许晴霁应下来,目送车辆远去。古沐阳要接的患者是个诗人,早些年喝大酒喝成了肝硬化,长期脸色蜡黄,靠找上门输液熬着日子过,他说他不愿意死在医院,那显得不够自然,人得静静地死在家里死在自己的床上才叫死得其所。他话是这么说,可每次觉察出一点儿不对劲立刻就打120,折腾了几次之后,他发现了这种挂靠在医院的私人救护车,能省去一部分防护、途中护理等费用,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古沐阳车上的常客。
许晴霁听古沐阳说过,这人某次出院,对着医院大门吟诗,说什么这里也许是终点,或许更是起点。说这话时古沐阳正坐在她对面扒拉碗里的面条,说完他先笑了,笑时有点儿孩子气,笑纹从嘴角到眼尾,蔓延开一种烟火味儿的俏皮。那天是高考百日誓师,许晴霁也已经和古沐阳熟识了一百多天,她偶尔会往古沐阳家里跑,对方早出晚归,她边写作业边留个耳朵听动静,每次都能蹭顿饭,比自己泡方便面奢侈太多。
卧室的二手打印机吱吱作响,在打印不知道第几版修改过的剧本,古沐阳说甲方讲究,不仅要电子版的,还要纸质版的,否则费眼睛还不方便批改。不少废稿都成了许晴霁的草稿纸,背面写满数学公式英语单词,课间空闲许晴霁会将草纸翻过来阅读,文本不全,故事断续,是一个属于北境小镇的遥远故事。
许晴霁咀嚼着葱油拌面,抬眼往古沐阳脸上瞧,对方吃饭时话尤其多,爱讲一些北方,一些过去。许晴霁能听出他去过很多地方,她问过他为什么离家。古沐阳说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二十多年一直活在一个地方,觉得倦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想着出来走走,看看外头,找找理由。
救护车。许晴霁想问,生死、悲喜、起始,你是想要从此之中找到理由和答案吗?
古沐阳吃到一半,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起身进卧室拿了支钢笔出来递给许晴霁,许晴霁有点儿愣,下意识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她把笔接过来。古沐阳重新坐下,语气随意地开口道,过去单位发的,有些年头了,虽然你们现在也用不上钢笔了,但思来想去的,百日誓师还是送个笔啊本儿的,寓意好。
许晴霁无措地捧着笔,英雄牌,墨绿笔杆银色笔帽,银色氧化了些,泛起古铜色。她说我不能要。古沐阳已经开始继续吃面,语气快而热络,拿着吧,也不是啥贵重玩意儿,就当个纪念品,小玩意儿。他掀起眼皮,嘴角勾了一下,别看了,快吃面,一会儿再坨了。
许晴霁将钢笔收进校服口袋里,她望着古沐阳的发顶,没头没尾地说了句,有件事我从小就想做,但到现在也没做。
古沐阳嗯了一声。许晴霁说,往钢笔水瓶里插白玫瑰,我忘了在哪本书里看到的,把白花插进有颜色的墨水里,花瓣就会变成墨水的颜色。
古沐阳含糊地笑了一声,我这儿还有半瓶蓝黑钢笔水,一会儿你拿回去试试。
许晴霁也笑了,回了句谢谢阳哥。古沐阳摇摇头,停了停问,你想好考什么专业了吗。
小语种吧。许晴霁回答,其实我学过芭蕾,学了好多年,本来打算走这条路,但后来发现看不到希望,我就放弃了。
挺好。古沐阳轻声,他说好时,发音总会绵软圆润一些,他补充道,放得下比拿得起更不容易。
钢笔放在背包夹层里,被许晴霁带去了学校,报道后就是一阵兵荒马乱的分宿舍,九月份的天气热得不清不楚,夏季的酷热与秋季的躁动混杂在一起。亏得她行李少,去得也早,坐在床铺缓缓收拢一身热汗时,其他三个床位还空荡荡的,门外走廊传来凌乱的讲话声,学生和家长都有。许晴霁把宿舍钥匙挂在钥匙链上,那里还有两把钥匙,自家的和古沐阳家的。她向古沐阳讨一把备用钥匙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儿不明用意的忐忑。古沐阳却大咧咧把钥匙递给她,没问原因,只嘱咐她自己可能随时会退房搬走,到时候麻烦她把钥匙还给房东。
许晴霁想,这居然是他们之间唯一的约定。
临近中午,太阳逐渐向树尖之上移动。古沐阳给她发了条消息,问她忙完了没,有没有吃午饭。许晴霁回了消息。她不怎么饿,也没打算吃。古沐阳又回了一条,有事打电话。
其实也没什么事,上大学而已,许晴霁想,况且是本地的大学。空间上他们的距离并没有被拉长太多,多的是时间上的节点。古沐阳是个很擅长顾及人心的人,很懂察言观色,也因此将寡言与健谈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来的路上,车内很是安静,许晴霁盯着担架发了会儿呆,突然笑了一声说自己小时候练芭蕾抻断过脚踝筋腱,拄拐上了一个月的学。古沐阳说那可得多注意,阴天下雨的别着凉,再落下病根。他的关心向来水到渠成,许晴霁缺少这些,也想要牢牢抓住这些。
气氛使然,抑或为了改变气氛,有时古沐阳的话匣子打开了便关不上,他喜欢天南地北地扯皮,不知是不是因为他枪手的身份,他知道不少乱七八糟的知识。他说,说起芭蕾我想起来,前几年我去哈尔滨,那儿有个哈尔滨铁路博物馆,前身是中东铁路俱乐部,俄国人建的,据说就是从那儿,表演了中国的第一支芭蕾舞。
许晴霁歪了歪头,笑了,我看过人家专业芭蕾舞团的演出,人家是黑天鹅,我不行,我像大白鹅。
古沐阳的剧本里也有不少纷杂的点缀,他心思活泛,是他写的那种,即使被杀死,也无法杀死心里想法的人。剧本的男主角也自称枪手,步枪。那是20 世纪90 年代的北方故事,关于法警和铁路巡道工,距离年长的法警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不远处是条废弃的铁轨终段,即使多年无车通行,年轻的巡道工还是例行养护的职责,这段铁轨是他每日巡查的终点,也是返程的起点,每日既定的轨道上一成不变的风景令他只能在脑海中同自己对话,再在休班时将它们一股脑讲给法警听,同样废弃的赤红色水鹤、松动的道钉、生满野花的枕木、某棵树上聚集的乌鸦、掩藏在山野间俄国人留下的教堂、一场出殡、冬去春来凝固又沸腾的冰河。
寒冷,炙热。
在南方溽热潮湿的教室里,许晴霁在复习之余翻看这些来自遥远北境的文字,人会成为语言的猎物,身处语言编织的幻境,不理会任何客观的现实,相信不存在于自我际遇中的东西。剧本里的法警问,你天天琢磨这么多,谁会在记得你想了这些东西。巡道工回答,那也要想啊,即便如此。
许晴霁枕在宿舍叠好的被子上闭目养神,室友风风火火地来,打了个招呼又风风火火去置办生活用品。午后半凝固的空气令人昏昏欲睡,来自外界的嘈杂也将人从陌生的环境远远推开。录取通知书到的那段日子,正值酷暑,母亲难得休假,在家陪了她一段日子。母亲带她下馆子庆祝,她有些心不在焉。母亲问她是不是对学校或者专业不满意。她摇头。母亲想了一会儿笑着问她是不是谈恋爱了。她夹着一筷子菜思忖片刻,还是摇了摇头。
但是。许晴霁轻咳一声说,有喜欢的人。
那阵子古沐阳很忙,每天接送因高温突发疾病的患者,忙得几天不见人影。许晴霁会站在窗前往下看,但古沐阳的车向来不开顶灯,小区里路灯又昏暗。许晴霁第一次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古沐阳家的门,明明只隔了几米远,他们之间的距离却要用南北与岁月来丈量。许晴霁坐在沙发上,房屋是小计量的领地,充斥着属于古沐阳的气味,像干燥的秸秆,也像燃尽的烟草。窗外成串的路灯仿佛发光的鱼漂,将沉入夜色的城市一网打尽,许晴霁恍觉摇摇欲坠,有些晕船。
除了气息之外,现在的这个房间里并没有多余的,属于它临时主人的必须要被带走的东西。
古沐阳开门进来时并没有惊讶,他先挑了下眉,笑着说你过来了,要不你先回去等我一会儿再过来,我去洗个澡,这一身臭汗。他亲切随意的态度反而令许晴霁有点儿无措,有些暗喜。她提高嗓音说我通知书到了。古沐阳在浴室间回了句,好啊,好事儿,明天带你下馆子庆祝庆祝。许晴霁听见淋浴的水声,她没动,只是扯着嗓子回,不用,我妈带我下过馆子了,我想吃面,就你做的,什么样的都行。
古沐阳回问,就吃面啊?许晴霁说,对。古沐阳好像是笑了,那行,听状元的。
许晴霁想说自己不是状元,但她喜欢古沐阳刚刚的语气,痛快、酣畅、骄傲而热烈。
古沐阳随便擦了擦头发,换了身宽松干净的短袖短裤,径直奔了厨房。厨房门没关,许晴霁望着他的背影,他一把窄腰一双长腿,脊背算不得宽厚,却是时光沉淀过的可靠。略长的发丝垂在后颈,水滴在衣料上濡湿成一片深色水渍。食物烹饪的香味儿和热度悄无声息地氤氲在房间内,和许多世间事一样润物无声。
这顿饭许晴霁吃得心猿意马又心无旁骛,她恨不得每一口都细嚼慢咽,杂乱无章的心绪又像碗里的面条一样搅在一起。白天刚下过一场雨,小区隔一条马路开了二十来年的音像店清仓甩卖,承载古往今来、世间万象的屋子关了门,贴满了促销的大红色字报。它们的世界崩塌了。许晴霁站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里,音响嘶吼着,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雨下得很大,如天河倒灌,雨水凝聚成河流,冲刷着尘世,将人间置于孤岛,许晴霁想试试找一找古沐阳哼唱过的那首俄语歌,不出意外没有收获。
古沐阳从冰箱里拿了罐啤酒,他说明天休息。许晴霁瞥了两眼啤酒罐,在上头凝结的水珠滑落时,她抄起啤酒灌了一口。古沐阳赶忙拦了一下,小孩儿家家别喝酒。
许晴霁被呛了一下,不小了,前阵子刚过十八岁生日。
古沐阳收回手,眼睛眨巴了两下说,那就抿一口。接着他望过去,眼尾敛出一丝弧度,嗓音放得很柔。他说,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生日快乐。
刚说完自己不是小孩儿的许晴霁很想像个小孩儿一样撒娇,她也忽闪了一下眼睛,那阳哥送我个礼物吧。
古沐阳说,行啊,你想要啥。
许晴霁埋头吃面,还没想好,想好了告诉你。
古沐阳的床是房东留下的双人床,木板搭的,躺在上面翻身吱嘎作响。许晴霁留宿那次,古沐阳果然彻夜赶稿,一大早便出去上班。那天凌晨四点多,许晴霁因窗外的鸽鸣醒来,发现古沐阳在椅子里将自己蜷成一团,他抱着自己,呼吸很平,很浅,线条清晰的嘴唇抿得很紧,皱着眉,眼睫微微颤动,像是对梦境不满。这令他拥有某种孤独而漂泊的气质,说孤独也许并不准确,那是种孤身一人的决绝,且衍生出了对旅程中偶遇的同行者浑然天成的亲切。
他身上闪烁着坚硬而喑哑的光芒,沉沉夜色吻过他的嘴角,不带任何欲望,也不懂许多心思,仿佛少年人表达喜爱时最单纯直白的冲动,和吻一支旧钢笔一样,仿佛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奇与留存。
那天醒来时,古沐阳已经出车了,许晴霁甚至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梦。
四角锋利方正的录取通知书摆在古沐阳堆满书稿的书桌上,许晴霁特意回家拿来的,古沐阳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毫不吝啬夸赞的同时,他语气亲昵地开玩笑说,果然是小孩儿,爱显摆。
许晴霁瞪了瞪眼睛,那你别看。
古沐阳笑了,略长的头发干透了,被他用黑发圈在脑后扎了个小辫儿。他把通知书放好,用长辈的语气交代,成年了,也长大了,以后就是你照顾你妈妈了,当然,也别怠慢了自己。
剧本后段,年轻的巡道工犯了法,杀了人,他从废弃铁轨的终点启程,完成最后一次养护,风景仍是风景,一成不变。他唯一的朋友在法场上举起步枪之前,他说,今早我看见窗花了,就那么冻在窗玻璃上一动不动,然后太阳出来了,窗花化了,开始动了,我就想啊,这东西真有意思,它重新活过来的时候,就是它死的时候。
她说,我知道你是个神枪手,哥,以后别怠慢了自己。
许晴霁问,阳哥,你不会留在这里的,对吗。
古沐阳点了支烟,你也不会的,孩子。
夜色缭绕,窗外偶尔有车辆缓缓驶过,车灯刺破漆黑的帷幔,制造黄昏般的错觉。床上除了被褥和许晴霁,便是古沐阳的软包烟,烟蒂林立的玻璃烟灰缸摆在桌角,旁边是半罐啤酒。古沐阳和开始那天一样坐在椅子上,这次香烟点燃了。
许晴霁没有看到剧本的结局,也不想多问了。也许未来的某天,她会在电影院看到这部本该叫作《越轨》的电影,被称为神枪手的法警在铁轨尽头吸烟,年轻人从不远处奔跑而来,他在短袖外套了件黄色反光背心,背着叮里咣当的工具包,扳子扛在肩上,道旗插在后脖子,跳格子一样在轨枕上灵巧地辗转腾挪,他抬头望见他的朋友,眉眼瞬间舒展开来,咧开个大大的笑容,拼命挥了挥手,扯着大嗓门喊道,你猜我今天又看到了什么。
镜头拉远,他们之间电缆纵深,铁轨横陈,线与线在时空上钩连成体,他们相互遭遇,他们隔着雷雨前燥热湿润的空气,也隔着以牙还牙的岁月凝视彼此。
那时的自己会想起现在,此时此地,许晴霁望着近在咫尺的古沐阳。她说,阳哥,我想到要什么礼物了。
古沐阳吐出一口烟,你说。
许晴霁盯着他的眼睛,刚刚成年的女生一双眼透彻得令人羞愧,下垂的眼型却像只小狗,笑起来有点儿弯,会将眼里湿润的光漾出来。眯起来时却显得可怜,甚至有些压迫感,被这双眼凝视的人会在瞬间明白,她对自己是有所诉求的。
许晴霁说,让我抱你一会儿。
古沐阳把烟按在烟灰缸里,站起身走到许晴霁面前,说,好。
这个拥抱更像是来自父女、师徒,或者兄长之于胞妹。古沐阳给了许晴霁一个俯身成海的拥抱。许晴霁慢慢抬起手臂,揽住他的腰背,衣褶里的洗衣粉味儿和烟草味儿同样环抱住了她。她闷闷地开口,阳哥,我喜欢听你说好。
那样特殊的咬字,许晴霁从未听到过,且再也不会从第二个人那里听到。
古沐阳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只浅笑着说,好。
也许某一天,许晴霁坐在宿舍床上想,她从大学回到家,对面的房子已经搬空了,会有另一个人住进来,取代她已经熟悉的气息。
两个已经报道的室友问她要不要去食堂,她本想拒绝,想了想还是点了头,抓起钥匙时,金属撞击叮当作响。她穿过走廊、楼梯,新生、家长、学长从他身边上上下下地穿行,第一次相遇的人们挤在大包小裹的行李之间,喧闹而嘈杂。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年轻人聚集的生机勃勃的地方。与生死攸关的医院、护送患者的顶灯灼灼的救护车截然不同。
如果是在孩童时代,那些废稿应该会被自己折成纸飞机。许晴霁微微眯起眼睛望向天空,它们划破青天,也许会被陌生人捡拾、阅读。那个自称枪手的人所写的枪手的故事会在阅读中一次次复活,命途一次次开始,又一次次结束,和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与分别一样,不断相互区别、衬托、作用,怀揣着每一段只属于彼此的影响与踪迹,永远行走,永远延宕下去。
剧本里曾经写过一笔,法警的桌前用罐头瓶养了一条银色热带鱼,巡道工说看上去像是暖气片掉的那块儿漆活过来了。后来这里被改掉了,改成了半瓶蓝黑色钢笔水,里头插着一支白色的花。
许晴霁突然很想给古沐阳打一个电话,她突然很想去一趟花店挑一支白色的玫瑰,完成那个儿时便期冀着的愿望,她想告诉古沐阳自己的心绪,告诉他自己想留下的不只是一支钢笔,告诉他那首歌曲名叫《白桦林》,这种树她还没有见过,因为它们来自比故事里的北方更北的地方。
她在黄昏夕照的喧嚣中轻轻哼起那支曲子。
和你在故乡的路上坐一坐
你要知道,我会回来,不必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