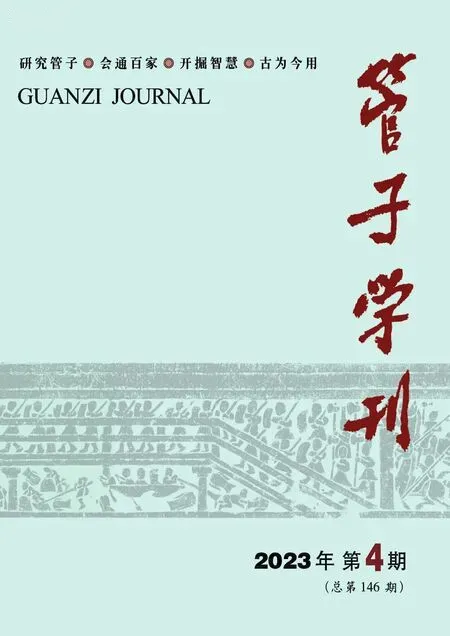从乾坤易到礼乐易
——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赵法生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小戴《礼记》之《乐记》,历来为学者所重。程子认为:“《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3页。朱熹亦推重《乐记》,认为其中“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极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辞”,指出:“《乐记》文章颇粹,怕不是汉儒作,自与《史记》《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26、1964页。朱熹看出《乐记》文章非汉儒能作,固是慧眼,但又将《乐记》作者分别与子思和荀子联系起来,也反映了作者问题的复杂性。从思想内容看,《乐记》深受《易传》影响,却又包含着对《易传》思想创新性发展,由此建构起系统和独特的礼乐思想,成为古典礼乐论的代表和古典美学典范,同时也给易学发展以新推进。
一、《乐记》与公孙尼子
关于小戴《礼记·乐记》作者,主要有战国公孙尼子和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两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列在儒家,注云“七十子之弟子”,排在魏文侯之后、孟子之前,似乎意图表明公孙尼子为春秋战国间人物,早于孟轲、庄周、荀况。《隋书·经籍志》儒家部分有“《公孙尼子》一卷”,注云“尼似孔子弟子”,语气并不肯定。经刘向整理的《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大概在汉魏之际就已佚失(3)郭沂:《先秦文献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310页。。清人马国翰和洪颐煊有《公孙尼子》辑本,分别收入《玉函山房佚书》和《问经堂丛书》。
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书》《诗》《礼》《春秋》皆有经,独《乐》无经,而以“《乐记》二十三篇”冠其首,未注明作者。《叙》云: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4)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6页。
西汉说据此认为传世《乐记》为西汉刘德所作,认为所谓“与禹不同”仅指刘向所校与王禹所传的汇辑不同,二十三篇与二十四卷比较也仅有一篇之差。但这种说法明显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说法不一致,班固“乐类”对《乐记》的著录方式为“《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表明二者并非同一部书,书名与篇目均不同,不能混淆。而“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也明确说明刘向校书所得二十三篇《乐记》,与《王禹记》二书不同,差异之处却不得而知。但“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对于二书不同之处或有所提示,因传世《乐记》未有涉及《周官》内容,丘琼蓀认为“河间所采者‘事’,此所传者‘义’也”(5)丘琼蓀:《〈乐记〉考》,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可备一说。
学者陈野分析认为:“刘向在校中秘书时得此古本二十三篇,遂加校勘。班固为表明此两书的根本不同,除在‘乐类’分别著录外,又于其后小序再作论述,以明‘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之义。”此说有理,反映了班固在小叙中说明河间王《乐记》来历的真实意图,在于辨别二书。陈野又引用后汉荀悦《汉纪》云:“乐自汉兴,制氏以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但纪铿锵歌舞而已,不能言其义。河间献王与毛公等共采周官与诸子乐事者,乃为《乐记》。及刘向校秘书,得古《乐记》二十三篇,与献王记不同。”陈野分析说:“此处明言‘古《乐记》’,则其成书显然早于刘德《乐记》;其后又径说‘与献王记不同’,则比班固‘与禹不同’之文更为清楚明了地说明了刘向《乐记》非刘德《乐记》。”(6)陈野:《〈乐记〉撰作年代再辨析》,《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第105页。此说颇有理据。以上史料与分析证明了刘德所献《乐记》,与古《乐记》并非一书,西汉说难以成立。
传世《乐记》为小戴《礼记》第十九篇,孔颖达谓:“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也。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7)施丁主编:《汉书新注》,第1256页。由于小戴《礼记》仅收入十一篇,其余未收入的十二篇遂佚失。《礼记》并未注明《乐记》作者,且《乐记》许多内容又见于《荀子·乐论》《史记·乐书》以及《吕氏春秋》,说明其影响深远,也使其作者问题益加扑朔迷离。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乐记》取公孙尼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郭沫若因此断定《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认为“两个人的说法可以为互证”。但他认为《乐礼》篇可疑,其中一节与《系辞》中一段差不多完全相同,这一节“应该不是公孙尼子的东西,至少应该怀疑”,由此引发了《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争论。郭沫若同时指出:“我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但主要的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还认为“《荀子》的《乐论》差不多整个是公孙尼子的翻版”(8)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乐记〉论辩》,第1、3、16页。。

关于公孙尼子与《乐记》的关系,除了前引资料外,王充《论衡·本性篇》说: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9)王充:《论衡》,《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汉书·艺文志》载“《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而宓子贱、漆雕开为孔子弟子。《汉书·艺文志》也将公孙尼子列为七十子弟子。王充这里并未涉及公孙尼子与《乐记》之关系,而是将公孙尼子与宓子贱、漆雕开和周人世硕并列,说他们“亦论情性”,表明他们生存时间相近,且都具有情性思想,而现有《乐记》恰好重视情性与礼乐之关系,有“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之语,恰与王充所说呼应印证。
另外,《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引用公孙之养气说:
“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至,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1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7-448页。
《太平御览》卷467引《公孙尼子》“君子怒则自悦以和,喜则自收以正”,正好与董仲舒所引公孙养气说之中和思想相合,表明这里所说公孙可能就是公孙尼子。《乐记》亦重气且重中和,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以中和作为乐论礼论的核心所在,这也与公孙尼子养气说中的中和思想一致。
另外,马国翰所辑《公孙尼子》佚文中,有“众人役物而忘情”一句话(11)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页。,可与《乐记》中如下一段话相参: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12)本文《礼记》及《乐记》引文,均见《礼记集解》,以下不再一一标注。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役物”即役于物,导致人丧失其本质而“物化”,结果就是“人化物也”。“忘情”是人丧失了“人生而静”时本有理想之情性,解决之道就是用德音雅乐感动人心、用礼来规范人之行为而复归于中道。因此,《乐记》此段话的思想也可以与马国翰所辑佚文涵义相通。
综上内容,如果说沈约、张守节、马总、徐坚所言,为公孙尼子作《乐记》提供了文献证据,而王充、董仲舒相关资料以及马国翰所辑《公孙尼子》佚文,则为《乐记》和公孙尼子的关系提供思想内容方面的论据。结合文献证据与思想内容两方面资料,以《乐记》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是佚书《公孙尼子》的部分,这是相对比较可靠的结论,尽管不排除《乐记》中有后人附益的内容。
丘琼蓀则在公孙尼子和刘德之外另立新说,认为小戴《礼记》之《乐记》“其思想亦驳而不纯,兼儒、杂、道、阴阳,有浓厚之汉儒气息,不若仲尼再传弟子所为”,因而否定《乐记》乃公孙尼子作。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杂家类有《公孙尼》一篇,列在东方朔之后,臣说之前,此人当是武帝时另一属于杂家之公孙尼。丘氏据此认为《乐记》乃杂家公孙尼所作(13)丘琼蓀:《〈乐记〉考》,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乐记〉论辩》,第69-71页。,而顾实已指出此乃二人,这两种书“盖非同书”(14)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丘氏显然将二者混同了。
丘氏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虽相信唐人张守节、马总、徐坚之说,却又提出诸人“又岂不见《乐记》《荀子·乐论》《吕氏春秋》之理,而犹标举为公孙尼子,其故又何耶?此中矛盾,不能解决,则此一重公案,亦必无法澄清”(15)丘琼蓀:《〈乐记〉考》,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乐记〉论辩》,第71页。。也就是说,既然张守节等人同时能看到《荀子》与《吕氏春秋》中的乐论,为什么不言《乐记》是荀子或吕不韦所作呢?因为《乐记》的许多内容同样也在这些书中出现了。丘氏还指出,如果《乐记》作者真是春秋战国之间的公孙尼,他怎么可能综合庄周、荀况、尸子、吕不韦等人的学说,去作成《乐记》呢?他感到自己似乎面临着文献陷阱,于是干脆跳出文献的桎梏,而另辟蹊径。可是,其观点虽然新颖,却同样于史无征。
实际上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分析,《乐记》内容,是否果真如丘氏所理解的那样,是杂取《荀子》《吕氏春秋》《诗序》《系辞》《祭义》《庄子》《尸子》等相同者而成?果真如此,则《乐记》便可归属杂家,他的结论也就有了成立的可能,于是“千古疑云,为之一扫。愿执此说,以就正于郭先生暨当世贤者”(16)丘琼蓀:《〈乐记〉考》,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乐记〉论辩》,第71页。。行文至此,丘氏推论的动机已经清楚了。因为儒家类的《公孙尼子》与杂家类的《公孙尼》同时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不可能是同一本书,但如果能断定《公孙尼子》内容属于杂家,它的作者就可能是杂家的公孙尼,而与作为孔子再传弟子的公孙尼子无关,公孙尼与公孙尼子也就可以合二而一。
可是,以《乐记》文本来看,其思想属于正宗儒家无疑,丘氏有关杂家之说难以成立。另外,就文献关系而言,有无可能是荀况、《吕氏春秋》等吸取了战国晚期前形成的《乐记》呢?丘氏显然并未考虑这一选项。可是,历代文献资料却更加支持这一说法。陈野对《乐记》《荀子》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乐记》并非全如持西汉说者所认为的那样思想驳杂、结构混乱,它自有其大致统一的思想主题和内在结构规律。而凡《乐记》与《乐论》、《适音》、《音初》诸篇相同相似的文字段落,均为后者对《乐记》的袭取引用。荀子引用《乐记》的目的,正在于借前人之言以驳墨子,增加自己论述的力量。”(17)陈野:《从文献比较看〈乐记〉的撰作年代》,《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101页。沈文倬对比分析《乐记》与荀子《乐论》相关内容后认为,当是荀子引用《乐记》之文以驳墨子(18)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李学勤亦认为《荀子》《吕览》都征引《乐记》(19)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14页。。笔者认为以上分析颇为精审,其说可从。
二、《乐记》礼乐哲学与《易传》方法论
学者早已关注到《乐记》与《易传》内容相同之处,并有《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不同解读(20)黄晓萍:《〈乐记〉袭〈易〉考》,《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第105-109页。。但是,如果仅仅将问题定位在是《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这样的层面,就无法超越已有的讨论。实际上,《乐记》并不是简单地袭易。《四库总目·经部·易类》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乐记》乃是创造性地援易以解乐,以建构新的礼乐哲学。《乐记》的乐论,应是早期儒学中易学形上学的一次成功运用。比较可见,《乐记》和《易传》之间存在广泛和密切的思想联系。
(一)《乐记》与《易传》“一物两体”论
《周易》之天地阴阳论,既是宇宙论,又是方法论,其中包含“物生有两”的阴阳思维,《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21)本文《易传》引文,均见《周易译注》,以下不再一一出注。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是其典型表达,张载概括为“一物两体”:“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张载又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22)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10页。这是对《易传》阴阳思想的精要总结。《乐记》将一物两体的方法运用于礼乐分析:“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本段一气推出了内与外、盈与减、反与进、放与销、反与报、乐与安六对范畴,借以辨析乐与礼,初看起来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仔细检视却一一对应,是对《易传》“一物两体”方法的成功运用。
打开《乐记》,会发现众多的对子,如天与地、礼与乐、阴与阳、刚与柔、心与物、中与外、动与静、明与幽、圣与明、述与作、和与序、情与文、鬼与神、同与异、爱与敬、流与离、德与艺、上与下、先与后、道与欲等。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对子,不仅用于自然,也用于人文;不仅用于乐与礼之间,也分别用于乐和礼内部,成为《乐记》的基本分析方法。《乐记》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既打开了乐与礼的“两在故不测”的分殊面向,又导出其“推行合一而有化”一体功能,将“一物两体”的方法运用到极致。
(二)《乐记》与《易传》“易简”之道
《易传》将举一统万的方法称为“易简”。《系辞》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阝贵然示人简矣。”《系辞》又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传》以乾坤为易之门,阴阳之道即乾坤之理,天下万物本于一理,宋儒称为“理一分殊”:由一知万,故乾坤之道乃易简之道,天下之理为易简之理,贤人以此成就其可大可久之事业。《乐记》以礼乐为乾坤,则礼乐亦涵易简之理:“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乾坤之道易简,故能成就大久之业;礼乐之道易简,故能“揖让而治天下”。《易传》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易明乾坤之理,令君子以此恒常其德,破除险阻,以定天下之大业;礼乐易知易从,故能感化人心,使天下无怨无争。易简思想源自《易传》形上学,注家谓易有三义,易简为其一,《乐记》中有关礼乐易简的思想,是以礼乐代乾坤的结果,是对于《易传》易简之道的引申与运用。
(三)《乐记》与《易传》感通论
《乐记》强调乐是“人心之感于物”的结果,其乐论以感通为中心展开,而最早对于感通作出形上分析的是《易传》。六十四卦本身就是一个感通的系统,《系辞》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韩注》注“摩”为“相切摩也,言阴阳之交感也”;《韩注》注“荡”为“相推荡也”。刚柔两爻相感而生八卦,八卦之相感推荡而生六十四卦,故易乃一感通的体系。
具体而言,《易传》感通包括异类相感和同类相感两种类型。“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属于异类相感,乃万物化生之源。《咸·彖》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此乃异类相感的典型,阴阳相感被视为宇宙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以泰卦和否卦为例,前者乾下坤上,乾以尊处卑而交通坤象,则成阴阳通泰之和;否卦乾上坤下,乾居尊位而拒不与坤交通,导致阴阳离决,天地否塞,生机熄灭,故《易传》虽然强调阴阳刚柔之差异,但从未将二者的差异与斗争绝对化,而是以感通之“和”作为自然和人道的价值理想,而实现“太和”的关键在于阴阳刚柔双方的感应交通,故《系辞》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乐记》将此感通思想作为乐的形上学依据,认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将乐视为阴阳二气“合同而化”的结果,乐因此具有了宇宙论意义。
除了阴阳刚柔的异类相感,《易传》还有同类相感。《乾文言》引用孔子的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讲的即是同类相感,这对《乐记》产生了深刻影响。《易传》象数采取比类取象方法,《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文言》认为万物“各从其类”,《乐记》也认为“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正是“通伦理者也”的乐教感动人心,引发大众同类的情感反应,由此“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这正是同类相感的效果,这种效果已经预先由《易传》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作了经典表达。正基于《易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理,才有《乐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的成效。
(四)《乐记》与《易传》的中和观
《周易》尚“中”与“和”。凡爻象居中,多为吉利之象。“中”又与“正”相联系,象征着人事方面的中正之德。《易传》之“中”并不是个单纯数量问题,而是居其位而守其德,所谓“正位居体”。家人卦《彖传》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强调的乃是家庭成员各正其位,以德自牧且彼此感通所形成的和谐局面。
前引《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公孙之养气”说中,总结了气的十种失衡,都是因为违背“中”或中和,并因此提出了相应的对治措施。可见,中和是公孙尼子最理想的气机状态,这与《易传》中和观一脉相承。
《乐记》又说: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这段乐论,也包含了养气说在内,“合生气之和”即保合中和之气。“阳而不散”与“喜则气散”相关,“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则与“怒则气高”“惧则气慑”相联系,都指气的不中和之弊。由此可见,公孙尼子的养气说和乐论与《易传》中和思想是非常相近的。《春秋繁露》与《太平御览》所记载的公孙尼子养气说,与《乐记》的礼乐养气论重点虽有所不同,却可以互相补充。前者以中和作为气的理想状态,以“反(返)中”作为养气的路径,也涉及心气关系,但从引用的思想片段中,尚看不出究竟该如何“反中”。这一不足恰好在《乐记》中得到补充。《乐记》主张保持四气中和并由中发外的关键在于“稽之度数,制之礼义”,通过乐来调养阴阳刚柔四气之中和,使得宫商角徵羽五声各安其位,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将《春秋繁露》与《乐记》中的论述综合起来,或许更能窥见公孙尼子养气说之全豹,它不同于孟子、庄子或者《管子》四篇的养气说,公孙尼子养气的重心显然落到了礼乐上。
《乐记》上述一段话的意思,似乎与《易传》如下一段内容有关:“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这两段话都是“诚于中而形于外”之意,其中“正位居体”“畅于四肢,发于事业”,与《乐记》“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安其位而不相夺”,意思与语汇皆有明显相关性。不过《易传》的说法更为简约,提供了一种宏观思想架构,而《乐记》则在这一思想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气论与礼乐的引入,将《易传》文本所蕴涵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乐记》又不只是在照本宣科,它对于《易传》的中和思想又有发展,这尤其体现在“中”与“和”的关系上。人们解读《易传》,往往重其“中”而轻其“和”,《乐记》则对“中”与“和”两方面的关系有深入体察,并将“和”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后面将对此重点分析。
(五)《乐记》的乐以象德与《易传》“作乐以崇德”。
《易传》说“易者,象也”,将易归于象思维,这里的象包括卦爻象以及太极图、河图洛书等易图象。象思维首先是“象其物宜”,是仰观俯察、取诸身物的结果,但其涵义并不限于物本身,《易传》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是表达圣人之意的手段,圣人之意则是圣人对于天地之道的觉解。
《易传》的象思维影响了《乐记》对乐的看法。《乐象》篇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以心为乐之本而以声为乐之象。《乐记》还依据春秋时期五声为气说,将乐声成象的依据落实到气:“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和乐乃是正声顺气成象,而淫乐则是奸声逆气成象。《易传》认为“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乐记》则说乐“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如果说《易传》是以天地为法象,《乐记》则是以礼乐为法象。另外,在《易传》中,天地之象乃乾坤;在《乐记》中,天地之象则是礼乐,这显然是以礼乐代乾坤而入易,在易学思想框架中重构礼乐形上学,并将礼乐提升到本体论地位。
《豫·象》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是就西周以德配天思想以言乐,《乐记》综合《易传》的“作乐崇德”和“立象尽意”说,发展出乐以象德说:“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故乐并非为了极耳目口腹之欲,而是为了象先王之德以化民,《乐记》引用孔子的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揭示古乐中的先王之志,以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易传》对《乐记》的影响深刻而广泛,《易传》的思想痕迹在《乐记》中无处不在,甚至连许多用语都明显相似,它为后者提供了基本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学者已注意到公孙尼子和《乐记》与易的联系,陶潜《圣贤群辅录》说“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或有所本(23)转引自董健:《〈乐记〉是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乐记〉论辩》,第94页。;李学勤认为“《易》学为公孙尼子所属一派学者所禀承”,“《乐记》和《易传》的关系,比子思的《中庸》等篇要密切得多”(24)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15、109页。。本文分析认为,公孙尼子通过《乐记》援易以解乐,是易学哲学在乐教领域的成功运用,是二者思想的深度结合,也使得《乐记》思想伊始就具有性与天道的哲思高度,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乐论。但《乐记》援易以解乐,并不只是简单地袭易,而是有取舍有辨别的思想创造,也是对《易》学的重要发展,这是后文所要继续分析的内容。
三、天地之道与礼序乐和
《乐记》的学术宗旨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礼乐哲学,它首先须面对既有的礼乐思想。西周时期的礼主要是指祭礼而言,而具有伦理法则性的礼,当是称为“彝”。周初诰辞中常批评殷末“民彝”大乱,在今天看来,其实是礼的瓦解。春秋时期,宗教性天命观日趋衰微,礼的地位日益重要,礼不仅是天道之体现、治国之手段,几乎所有的伦理道德也统统纳入礼的名下(25)赵法生:《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0-151页。,春秋时期的礼已成为文明的代名词,如孔子所谓夏礼、殷礼、周礼等,都是文明论意义上的概念。
古人曰礼,又常兼乐而言。《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里的礼是祭礼,自然包括乐,古礼包括诗歌、舞蹈和音乐等多种因素在内。《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八礼皆须用乐。在古代礼的概念中,乐是礼的组成部分,相对于礼而言,乐似乎只有附属意义。礼在春秋时期的崇高地位,可在《左传》中有关礼与天地之道关系的论述中见出: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26)陈戍国:《春秋左传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35、1059、1058、1084页。
按以上说法,礼是天道或天地之道的显现,又是各种伦理法则的统称,但《左传》中有关礼与天道的关系多泛泛之论,且言礼不言乐,或者说是举礼而统乐,这也是当时思想界的一般情形。
在这样一种以礼为主导的儒家思想叙事中,《乐记》的出现就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因为它力图从宇宙论上证明,乐实际上比礼更重要,而当它试图进行这样的论证时,其理论依据正是《易传》形上学。《乐记》中有一段话,历来被认为与《易传》关系密切: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
《乐记》这段话的内容明显与《系辞》开头一段有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这两段话的思想与文字均有明显共同处,那么到底是《乐记》引用了《易传》,还是相反?张岱年先生认为:“《系辞》在这里是讲天地和万物的秩序和变化,写得比较自然。《乐记》此段从天地讲到礼乐,讲得比较牵强,看来是《乐记》引用《系辞》的文句而稍加改变。”(27)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廖名春选编:《周易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高亨、沈文卓、李学勤等也认为是《乐记》引用《易传》(28)高亨说:“《系辞》论《易经》,其文是天衣无缝。《乐记》论《礼乐》,其文有抄袭牵改之迹象。然则是《乐记》作者酌采《系辞》,事甚明显。”参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11页;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09页。。笔者赞同以上学者观点,并试图通过对《系辞》和《乐记》的内容比较,进一步厘清其思想联系。
《系辞》中这段话的主旨,意在打通宇宙论和象数论,表明易道本于天地之道。相比而言,《乐记》这一段试图在《易传》宇宙论基础上建构其礼乐论,二者内容既相关又相异。
《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一段讲天地化生万物之道,其中的乾坤、刚柔、吉凶都是象数概念。但《乐记》的一段内容却有所变化。《系辞》中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乐记》中变成“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前者以宇宙论合象数论,后者将天地之别落实到君臣关系。《系辞》中“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乐记》则是“动静有常,小大殊矣”,以“小大”取代更具象数色彩的概念“刚柔”,依然服务于从象数论到礼乐论的目的。《系辞》中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重在讲吉凶之所由,这是象数学的目的所在;在《乐记》中,“吉凶生矣”则变成了“则性命不同矣”,论述重点由吉凶占断转向更为哲理性的性命之学。《系辞》中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讲天地生化万物之道;在《乐记》中则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由天象地形引出礼以别异,应是对《系辞》原文的引申。《系辞》接着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讲的是八卦取象明变之道,阴阳相对而物生有两之理,人事方面只讲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乐记》中相应的一段则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虽然也是从宇宙论讲起,却取消了“八卦”“刚柔”“乾道”“坤道”等象数内容,突出了阴阳气化思想,《系辞》中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变成了“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以突出时的重要以及男女在礼制上的差异,形成了礼序乐和思想,是以《易传》天地观解释礼乐的产物。
比较可见,《系辞》这段话的目的在于将象数论与宇宙论合一,以证明“易与天地准”,却相对未能凸显伦理道德的意义。鉴于《易传》主旨在于揭示天人一贯之道,于是《乐记》作者删除了《系辞》原文中的象数内容,而增加了与礼乐相关的内容,将天道与礼乐直接联系起来,以重构儒家的礼乐哲学叙事,这正是《乐记》引用《系辞》却又在文字上加以若干改动的原因。与《系辞》文本相比,在调整后的《乐记》文字中,“天地”一词的频率与地位明显提升。《系辞》一段中“天”“地”对举与“天”“地”并称出现两次;而《乐记》一段中,“天”“地”对举和并称则出现七次,后者贯通天地与礼乐的意图至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乐记》中“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天地之情也”这段话,其中包含三层意思。从“天尊地卑”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为第一层意思,是说天地差序结构,生成种类繁多、形性各异的无数个别事物。“性命不同矣”令人想起《乾卦·彖传》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里突出的是事物的差异性,此差异性内在于宇宙生机与秩序本身。“则礼者天地之别也”一句,乃是对这一层意思的总结。礼本为人道,这里却说礼是天地之别,意在将价值秩序追溯到天地秩序,实现自然与自由的统一。这种对于礼的解读,不同于强调礼的规范性的传统看法,而是将礼与宇宙之多元与个性化的存在形态联系在一起,而礼的别异功能源自天地生生所导致的差异性,这显然是借鉴《易传》哲学对于礼作出的新解释。
从“地气上齐,天气下降”到“百化兴焉”为第二层意思,是说二气摩荡交和、化生万物,构成宇宙深处天然的生命和谐,故曰“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前面讲礼之异,这里则讲乐之和,礼乐便被纳入到天地大系统,成为天地之别与天地之和的表征。于是,《乐记》对于礼乐的功能作出了不同于既往的说明:“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记》认为,乐的作用在于统合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礼的作用在于辨析差异并彼此相敬,而优良的秩序依赖于和同与别异两方面的平衡。如果和同过头就会模糊事物的差异,使得事物丧失本真自我;如果别异过头就会离心离德,导致事物的瓦解崩溃。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为第三层意思,这句话总结以上两层意思,以实现同与异的统一。所谓化,即天地和同而化的功效,是天地之和;辨则是天地万物之异及其差序规定,是天地之序,而天地之和与天地之序分别通过乐和礼来表现,故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别异方有秩序,和同化生万物,由此才有宇宙的无穷尽的变化与生机,故“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与礼之同与异的功能,于是转化为礼序乐和的秩序建构,这便将作为人文制作的礼乐,提升到天地境界,礼序与乐和便成为“天地之情”的本质内涵。在《系辞》的言说中,“天地之情”通过乾坤、刚柔的象数来展现,在《乐记》中则是通过礼序与乐和来体现。
《乐记》根据《易传》的比类思想,以乐为天而以礼为地:“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天地万物既彼此差异又互相联系。礼以道名分而见差等,体现万物之异而应地;乐则泯合个体差异,使万物在生命的感通中和谐共鸣,合同为一而配天,形成作为《乐记》思想核心的礼序乐和说,将人文礼乐植入到《易传》之天道秩序中。从天地万物之差异中领悟到礼的缘起,从阴阳和合的生命流淌中,闻听宇宙深处大美的乐章及其在人文世界的动人回响,从而将人文礼乐提升到形上高度,具有了形上学意义。礼序乐和是天人之道的联结处,天人之际因此相与为一。这是《乐记》对于礼乐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儒家道德观与宇宙观的新突破,其意义不容低估。
如此,天地是自然界的礼乐,而礼乐则是人文界的天地。从天人授受之际看,固然是“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从人能弘道以及《易传》裁成辅相的角度看,则是唯有礼乐才打开了天地之道的内涵与意义。所以《乐记》又说:“礼乐明备,然后天地官矣。”陈澔引刘氏注:“圣人作乐以应助天之生物,制礼以配合地之成物。礼乐之制作既明且备,则足以裁成其道,辅相其宜,而天之生,天地之成,各得其职矣。”(29)陈澔:《礼记集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以《易传》之裁成辅相说诠释这句话的意思,解说甚精。“天地官矣”,孙希旦注:“天地官,言天地各得其职,犹《中庸》之言‘天地位’也。”(30)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2页。陈澔注:“官,犹主也。”(31)陈澔:《礼记集说》,第298页。陈注显然较孙注为优。“官”有主宰义,天地各得其职乃自然义,而天地各得其主,更能凸显礼乐作为人文化成的优先性与主体性,天道只是自然的礼乐,礼乐却是自觉的天道。缺乏礼乐的存在既没有差异,又没有和谐,犹如天塌地陷,只剩下一团混沌,《易》所谓“天地闭,贤人隐”是也。
关于礼序乐和的形上意义,程颐有深刻论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固有礼乐,不在玉帛钟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固是礼乐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畜多少义理。”又问:“礼莫是天地之序?乐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问:“如此,则礼乐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阴阳,其势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须而为用也。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32)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25页。
在程子看来,先儒只抓住了礼乐之用,却遗失了礼乐之本。礼乐之本在于“序”与“和”二字,二者既是人文世界的基本规律,又是天地之道的基本规律,所以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他以两把椅子必得有个摆放秩序为例,指出无序便乖,乖则不和,说明“序”与“和”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割,就如同有阴必有阳,有一便有二一样,也是以易道言礼乐。他认为连至为不道的盗贼都须有礼乐,否则“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3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25页。。因此说“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正是打通礼乐与形上学之意。余敦康先生认为,这便将礼乐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永恒性的价值本体”(34)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程子更进一步将礼序乐和的思想总结为理一分殊,以乐和为理一而礼序为分殊。郑汝谐曾在《易翼传序》中指出:“古今传《易》者多矣,至河南程氏始屏诸家艰深之说,而析之以明白简易之理。”余敦康认为:“所谓明白简易之理,其实质性的内涵,无非是一个‘序’字与一个‘和’字。序者言其对待,和者言其交感。”并认为“这是一条普遍的原理”,此即程子之以理解易(35)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第425页。。程子的易学观,尤其是礼序乐和思想,明显是受《乐记》启发。本段中弟子问他:“礼莫是天地之序?乐莫是天地之和?”程子本人又曾谈到“礼胜则离”“乐胜则流”(3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57页。,这都是《乐记》中的话,成为程子新易学的关键内容。
四、《乐记》与新易学
在礼序乐和的思想中,礼与乐的关系发生重要改变,即乐的地位显著提升,《乐记》中“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等说法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儒家哲学中天的地位历来要高于地。如果说,传统观念是以礼统乐,《乐记》则是以乐统礼。以乐统礼有两个思想源头,首先与孔子的乐教思想有关。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国以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都是强调礼的作用。在孔门后学所传《礼记》中,礼依然处在至高无上地位,《礼运》引孔子的话“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情,夫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还说:“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这类说法在《礼记》中比比皆是。但孔子又往往礼乐并举,《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为政》“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等等,礼乐相连指向理想的治道秩序。在论述人格修养时,孔子尤其显出对乐的高度重视,《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乐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论语·述而》“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以艺表达道德修养的终成性意义。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爱好,它本身就具有形上学意义。以礼统乐是一种文明史的叙述,它具有充分的历史文化证据;以乐统礼则是哲学理念与修养境界的表达,这在孔子那里已有思想苗头了。
其次,真正将乐的地位提升到哲学层次的,是《易传》的太和思想。乾坤两卦《彖传》说: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乾元坤元彼此交感,使得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性,自由自在,和谐发展,使宇宙焕发出无限生机。这种“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的宇宙图景,《易传》称之为“太和”,并发出由衷赞叹。“太和”乃是最高之“利贞”,而“保合太和”的前提,首先是乾坤各居其位,各行其道,所谓乾健坤顺;其次是乾坤彼此感应相交,以成生生之德。如果说乾坤正位居体为“中”,则乾坤彼此感通为“和”。《易传》尚“中”,但“中”不是目的,居体正位的目的在相互感通以成天地通泰之象,否则就会天地否塞而生机灭绝。故“中”之目的在于“生”,不能生生,中正何益?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生”的关键又在于“和”,能“和”才能生生不息,唯有“保合太和”,才有“大生”“广生”之效。所以“太和”是《易传》天人观的最高价值理想(37)余敦康:《易学今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易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由此可见“太和”之重要。故《易传》之“中”与“和”的关系,实际是以“中”归“和”,“和”在价值上更重要,它事实上可以融摄“中”,故称“太和”。
《乐记》以礼为“中”,以乐为“和”,“太和”的重要,正说明了乐的重要,如果说“和”代表着社会的终极价值,那么这一价值的实现形式便不能不首先归于乐。《乐记》说: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不但能和合君臣、长幼、父子、兄弟,还有“比物以饰节”的功效,实际上是将礼的功能内涵于乐。因为《乐记》中的乐本身就是合歌词、舞蹈、乐声为一体,礼所表达的名分之异,自然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乐记》又说:
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郑玄注“纪,总要之名也”,孙希旦注“纪,言其各有条理也”(38)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35页。,两相比较,郑注为优。以乐为“中和之纪”,正是以乐作为致中和的关键,也是以“和”摄“中”、以乐摄礼之意。本段前面讲的是乐之内涵,其中有雅颂之声、干戚之舞、容貌之庄、行列之正、进退之齐,言乐则礼自在其中矣。这是广义的乐,是礼乐合一之乐,表明乐教可以融摄礼教。《乐记》以礼乐配天地而重构礼乐哲学的结果,是乐的地位的上升,它使得乐可以兼容礼的功能。
除了天地,《乐记》还将仁义与鬼神一并整合到其礼乐哲学架构中。《乐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一段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何以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除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外,还在于乐由情生,而礼为规范,《乐记》所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是也。故《乐记》又说“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以仁、义配乐、礼,也有高看乐的意思。此外《乐记》又以乐为神而礼为鬼,陈澔注:“敦和,厚其气之同者。别宜,辨共物之异者。率神,所以循其气之伸;居鬼,所以敛其气之屈。”(39)陈澔:《礼记集说》,第298页。《系辞》引用孔子的话“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屈者必伸而伸者必屈,乃是事物自身内在的感应所致。战国儒家以气之屈伸解读鬼神现象,《乐记》发挥此说,以礼乐与鬼神相配,以乐通气敦化而为神,以礼敛气成物而为鬼,从而将鬼神纳入礼乐哲学。“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乐是显象的人文制作,而鬼神则是隐微的气化流行,二者共同构成天地之道的组成部分。于是,礼乐自然具有通乎鬼神的功效,而用于宗庙和山川鬼神的祭祀了。
至此,《乐记》有取舍地引入《易传》哲学以重建儒家礼乐哲学体系的目标已经清楚显现出来。我们注意到,《乐记》虽然有众多的天地概念,也有阴阳概念,却没有一个乾坤概念,在引用《系辞》一段话时,《乐记》不仅将“乾坤”二字去掉,甚至连“乾道”“坤道”的字样也去掉。这当然并非不经意间所为。在分析了《乐记》礼乐哲学的内涵后便会明白,公孙尼子恰是要以礼乐代乾坤。且看《系辞》如下内容: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乐记》则说:
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系辞》认为易包罗天地之道,其阴阳之义贯通天地、幽明、死生、鬼神之道,所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之间,只是一易耳。《易传》尤重乾坤二卦,以乾坤为一之门,所谓易配天地即乾坤配天地。
与《易传》比较,在《乐记》里面,“弥纶天地之道”的已不再是乾坤而是礼乐。礼乐合于天地,行于阴阳,通乎鬼神,见乎动静。此时的礼乐,不仅“与天地相似”,而且“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因为天动地静,乐始礼成,天地之间只是一个礼乐而已,天人合一的意义也因此而改变。如果说,《易传》以易为天人合一的形式,现在天人合一的媒介就是礼乐。易道规律在《易传》中以象数形式呈现,在孔子以德解易后,尽管象数规律也具有了道德意义,但这种道德意义是曲折地表现的,天人之间尚未建立直接的联系。经由《乐记》以礼乐代乾坤而合天地之后,价值世界与本体世界便获得直接统一,在礼乐与天地之间,也就无需一套神秘的象数体系来作中介了。反观《系辞》中的这段话,如果现在将其中的“易”改换成“礼乐”,倒是十分贴切,这正是公孙尼子重构礼乐哲学的关键所在。
这当然是一种创新的礼乐哲学,它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易学。如果说《易传》以乾坤为易之门,而《乐记》则以礼乐为易之门、以礼乐为天地之象了。它借鉴了《易传》的宇宙观与方法论,继承了《易传》天人合德的基本理路,充分消化吸收了《易传》哲学的形式化法则、《易传》的太和之道等,却有意识地去除了乾坤等象数内容,而用礼乐取而代之。在《乐记》中,礼乐就是乾坤,而《乐记》则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礼乐版的《易大传》。所以,在《乐记》中随处可见易的精神气质、理念方法,只是用礼乐概念来表达,礼乐即是阴阳,即是天地,礼乐之道即是阴阳之道、天地之道。就此而言,《乐记》堪称公孙尼子的新易学。如果说《易传》的天人观是经由象数的形式来表达而可称之为象数易,以象数呈现义理,那么《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则可称之为礼乐易,将儒家道德与本体直接合一,成为以礼乐为核心的新易学。这既是孔子以德解易原则的进一步贯彻,又是易学本身的创新性发展。
《乐记》中所论述的天地之道,具有得意忘象的还原论意义。《系辞》引用孔子的话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冒天下之道”即包罗天下之道,易是通过独特的象数体系来达到此目的,《乐记》作者似乎对于易的象数系统并不完全满意。王弼倡导“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担心言与象反而遮蔽圣人之意。公孙尼子似乎也有相似的忧虑,他担心象数语言虽然看上去高深莫测,却有可能成为把握圣人之意的障碍,反而使真正的天地之道隐而不显。所以,在援引前述《系辞》中的那段话时,他预先进行了一次清理象数的实验,以期重返真正的天地之道,为礼乐文明重新奠基,论证礼乐文明的天然合理性。
既然《乐记》礼乐以代乾坤而象天地,在《乐记》中屡屡发现礼乐所具有的神秘性特征也就可以理解了。天地有多少奥秘,礼乐就有多少神秘。
从远古时代,祭祀鬼神的音乐就被赋予一种神秘力量,《乐记》中子夏答魏文侯问乐说:“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将德音雅乐看作是自然与社会一种理想和吉祥状态的特有产物。师乙告诉子贡:“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音乐能感通天地,让万物处于最理想的秩序与生命状态。如果说以上是古宗教时代特有的观念,乐的这种神奇功能,同样为哲学突破后的《乐记》所强调: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
这种颇为神奇的效果描述,不禁令人想起庄子笔下藐姑射山上“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的神人和《管子》四篇中“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的圣人。但儒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乐记》并没有将这种神奇功效过多地归于个人魅力,而是将其归于礼乐。大人所制作的礼乐,会将天地之间最神奇的内在力量唤醒,能令动植飞潜、卵湿胎生的所有生物各个遂性达生、欣欣向荣,使宇宙处于最佳生命状态。在《乐记》看来,这才是大乐的真正功能与目的。这样的乐绝不仅仅是普通的丝竹之音,它是宇宙深处的生命律动,是和谐天地发育众生的创造之母。这样的乐与师乙口中“动己而天地应焉”的乐同样神奇,但是,深通易理的公孙尼子,却对之给出了与师乙全然不同的说明论证。这种基于《易传》天人观的乐论,虽然肯定了乐在巫文化时代的神秘功能,却重新给予其哲学形上学的论证,标志着儒家思想的轴心突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易传》确立了以德解易的原则,也说过“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以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但它并未对天地之道与礼乐之关系作出具体论述。就此而言,《易传》的天人观依然是敞开的和未完成的。因为孔子所心仪的宗周礼乐文明,战国时期却成了杨墨等批评的主要对象。在这样的思想形势下,《乐记》以礼乐代乾坤而象天地,借鉴《易传》形上学重构礼乐哲学以论证礼乐文明的合法性,这自然使得《乐记》思想显示着浓郁的易学风格。《乐记》是易学原理的一次出色运用,但这一运用是如此深入与成功,它不仅创新了礼乐哲学,同时也创新了易学本身,从基于象数原理的乾坤易发展出更具人文色彩的礼乐易,以至于《乐记》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易学理论。一种哲学如果具有普遍和必然性意义,它就一定会不断为自己开辟出新的思想领地,易学通过《乐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乐记》体现了对于孔子乐论的深刻把握,虽然文字上较少提及孔子,但通篇义理不出于孔氏乐论规矩之外,而又予以形上学的提升,令人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感,非同时深契于《易传》与孔子礼乐之教者,孰能至此!因此,当公孙尼子进行这项创造性工作时,他同时遵循着孔氏传易与孔氏乐论的双重家法,并致力于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在这一结合中同时推进了易学和乐论,使其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其杰出的创造性与永恒的思想魅力盖源于此。《乐记》也因此具有洪钟大吕的思想风范,其思想非秦以后的儒家所能道,其言辞则与《易传》《中庸》风格相近。这显示了公孙尼子对于易理的深刻理解与娴熟运用,同时也显示了巨大的创造力,使公孙尼子成为七十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也使《乐记》成为儒家礼乐思想典范。《荀子》《吕氏春秋》《史记》均引《乐记》,显示了它在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所显现的思想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