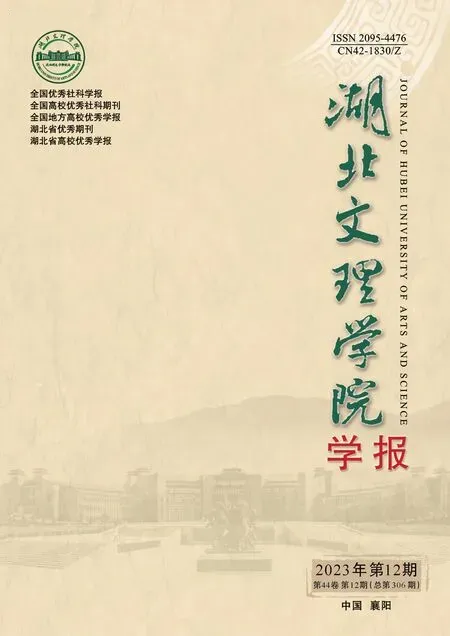南朝襄阳“卫敬瑜妻王氏”人物形象辨析
郭明强
(襄阳鱼梁洲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湖北 襄阳 441000)
襄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几千年来涌现出了许多风流人物。有的记载于正史,有的记载于方志或其他古籍,有的传颂于民间。南朝“卫敬瑜妻”王氏,就是一位既记载于正史,又记载于方志和其他古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古代襄阳奇女子。在以贞义闻名的王氏见诸《南史》之后,又诞生了小说版“娼家女姚玉京”的文学形象。由于情节更加离奇,故事更加曲折,从而产生了比正史更大的传播影响力。以致今人在读这一传奇故事时,往往难以分辨哪些是史书记载,哪些是文人的演绎或民间传说,常常出现误解或被误导。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书刊,特别是大量网络文章,采用的也几乎都是这一文学版本,对所谓“南朝襄州名妓姚玉京”津津乐道,而真实的王氏则很少被提及。
颇为尴尬的是,故事原发地的一些文史专家和媒体,甚至也被文学传说版本带了节奏,只知有“娼家女”姚玉京,而忽略了活生生的“贞义卫妇”王氏。在发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推进文化旅游时,对这一以贞义著称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导致历史的真相几乎被完全湮没。
笔者认为,地方人文资源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在研究发掘本地人文资源时,不应人云亦云,盲目从众。特别是对一个品德高尚,忠贞不二,崇孝重义,在当今仍有一定正面教育意义的历史人物及事迹,应通过深入研究厘清事实,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笔者不自量力,试对“卫敬瑜妻王氏”的形象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辨析:
一、“卫敬瑜妻王氏”是记载于正史的民间奇女子
王氏的传奇故事,见于《南史·孝义传》的记载:
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遂手为亡婿种树数百株,墓前柏树忽成连理,一年许还复分散。女乃为诗曰:“墓前一株柏,根连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城何足奇。”所住户有燕巢,常双飞来去,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更来,犹带前缕。女复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于台。[1]450
在《南史》之前,还有一部典籍记载了王氏事迹,就是鲍至所撰《南雍州记》。《南雍州记》成书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比《南史》早130年左右,是一部专门记录南雍州(侨置于襄阳)山川名胜的地理杂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过,原书约在金元时期散佚。当代学者黄惠贤著有《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其中的《贞女楼》篇,是根据宋初《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雍州·襄阳县·贞女楼》,《太平广记》卷二七0《卫敬瑜妻》,整理校订还原。全文如下:
王整之姊,卫敬瑜妻,年十六而亡夫,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乃止。墓前柏树,为之连理。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2]166-168
此篇虽比《南史》的记述简略,但主要内容基本吻合,应该是《南史》王氏传的重要来源。《南史》和《南雍州记》中记述的王氏,十六岁便失去丈夫,忠贞爱情的她决心为夫守节,侍奉公婆,并截耳明志。后与孤燕为伴,同病相怜。因触景生情,写出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咏柏》《咏燕》诗。
关于王氏的出身,《南史·孝义传》的记载是:“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南雍州记》也仅有:“王整之姊,卫敬瑜妻,年十六而亡夫。”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记述。文中提及的王氏亲属有王整、卫敬瑜和“父母舅姑”,对这些亲属未提供任何身份和家境方面的信息,说明王、卫两家既非官宦之家,也非名门望族,没什么值得介绍的。由此可以断定,王氏就是一名出自民间的普通女子,因忠于爱情,专于婚姻,守于孝义,而受到官府表彰并被正史列传。
其人其事也被后世的襄阳地方志普遍收录入内,如乾隆《襄阳府志·列女》[3]369-370和光绪《襄阳府志·列女》[4],基本都照录了《南史·孝义传》中的王氏传。
二、“娼家女姚玉京”纯属小说家言
由于“卫敬瑜妻王氏”的故事曲折传奇,生动感人,于是引起了古代文人的注意,将其纳入文学创作领域,一个来自正史,又有别于正史,孝义感天的“娼家女姚玉京”文学形象随之诞生,影响深远,流传千古。
最早出现的以“卫敬瑜妻”王氏为人物原型的文学作品,是唐代文人李公佐根据《南史·孝义传》记载创作的笔记小说《燕女坟记》。经过李公佐的改编和演绎,原本传奇的人物和故事更加离奇,也更加神奇,很快便广为流传,其真实人物与文学形象由此开始分离。后世历代文人编撰的古代小说集和有关书籍,如北宋张君房的《丽情集》[5]861,南宋祝穆的《事文类聚》[6]1037,明代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7],处囊斋主人的《诗女史纂》(1)处囊斋主人,《诗女史纂·卷之四》,国学知识文库·集部·诗藏·诗女史纂,电子版。以及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物犹如此》等,大都辑录了取材于《燕女坟记》的故事。虽然《燕女坟记》原文早已散佚,但通过宋代以后的小说文本,基本上可以还原其本来面目。经过文学加工的小说,与正史记载最大的不同,是主人公“卫敬瑜妻”由贞义化身的普通民间女子“王氏”,变身为孝义感天的“娼家女姚玉京”。
现在所见最早的小说文本,是北宋张君房编纂的传奇小说集《丽情集·燕女坟》,全文如下: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姑舅。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定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复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葬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上。[5]861
比此稍晚,南宋祝穆的《事文类聚》也收入了小说《燕女坟》。祝本与张本正文基本相同,但在正文后特别注明:“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按,《南史》载,襄阳霸城王整之姊嫁卫敬瑜,亡,截耳守志,余略同。”[6]1037不仅点明了出处是《燕女坟记》,还点出了小说与《南史》记载的不同之处。然而,这两篇《燕女坟》并非李公佐《燕女坟记》的原本。顾名思义,《燕女坟记》就是记“燕坟”和“女坟”。可这两文中都只提到:“燕遂至坟所,亦死。”后面并未述及为孤燕筑坟立碑之事。如果原本中本来就只写“女坟”而不写“燕坟”,小说篇名便名不副实了。由此推断,《燕女坟记》原本至迟在北宋已散佚。根据祝穆的记述,可知李公佐在小说取材时,有意删去了“截耳守志”情节,增写了“燕女生死相伴”的结尾。
其后历代录入的小说文本,也均未描述“燕坟”之事。直到清代徐谦所著的《物犹如此·燕冢》,才补足了这一情节:“燕春来秋去,殆七霜矣。后复来,女已死。燕绕舍哀鸣,人告之葬处,即飞就墓,哀鸣不食而死。因葬其傍,曰‘燕冢’。唐李公佐有《燕女坟记》。”[8]49将这一情节与《燕女坟》等版本拼接在一起,才符合李公佐《燕女坟记》的全貌。小说原创者李公佐在加工过程中,通过对正史记载的增删取舍,减弱了夫妻情义,增强了燕女之义,保留了奉养公婆之孝,“娼家女”的开头和具有神话迷信色彩的结尾,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传奇性,也更符合市井百姓的意愿。一个原本生动凄惨的故事,变成了哀婉凄美的故事,并逐渐成为民间传说的蓝本。
通过以上考证,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燕女坟记》问世之前,只有“卫敬瑜妻王氏”的传奇故事,并无“娼家女姚玉京”的神话传说。身世曲折,红颜薄命,化为仙子的“娼家女姚玉京”,纯属唐代李公佐小说中塑造的文学形象。尽管唐人传奇小说一贯标榜的是其记事之确实,以史家的态度记叙。实际上是“有闻加工,无闻虚构”,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李公佐借用虚构和夸张的文学手法,形成了主人公低微的身份与至情至孝之举的巨大反差,使之散发出更加夺目的人性光辉,吸引和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李公佐创作《燕女坟记》的本意,是借助文学的力量,倡导女子秉持“孝义”的价值取向,并无贬低王氏的恶意。但客观上却是模糊甚至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并成为以讹传讹的发端。如万历《襄阳府志·列女传》[9],就采用了笔记小说与民间传说版本。
三、“卫敬瑜妻王氏”的身世分析与推断
历史人物王氏与与文学形象姚玉京,既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原型,后者是经过文学加工的艺术形象。古代官修正史和古代笔记小说,笔墨都极为简练,尤其缺少细节描写。对于民间之事,无论是正史采集,还是小说素材的搜集,显然都离不开民间传说和对传说内容的取舍。因此,正史未必全面,小说未必不能拾遗补缺。将史料与小说综合分析和校补,基本上可以推断出王氏的主要身世。
(一)王氏“娼家女”身份难以成立
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王氏本就是“娼家女”出身,只是正史不便记录罢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依据小说文本所作的推测,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从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
“娼家”,原指以歌舞为业的人家,后谓妓院。无论是以色艺娱人的艺妓,还是以出卖肉体为业的娼妓,在古代封建社会一直都是出卖色相的低贱职业,从业者为世人所不齿,更为统治者所不容。从封建统治者对王氏的态度来看,可以绝对排除王氏“娼家女”出身的可能性。
其一,官府公开表彰。《南史》载:“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于台。”[1]450一个“美节”,一个“贞义”,足以排除王氏娼妓出身的小说家之言。古人强调的“贞”,对妇女而言既有忠贞之义,更有贞洁之义,是封建礼教所推崇的一种道德观念,指女子不失身、不改嫁。因此,娼妓是无论如何不能与“贞”字联系在一起的。
“西昌侯藻”是梁武帝萧衍之侄萧藻,梁天监元年封西昌侯,时任雍州刺史。雍州为古代九州之一,原在长安一带。东晋至南北朝时期,雍州一直侨置在襄阳。萧藻就是在雍州刺史任上追授王氏“贞义卫妇”,立贞节牌楼。州一级行政区划的衙门表彰一名民间女子,审查把关不可能不慎重。
《南雍州记》中明确记述,萧藻所起之楼名“贞女楼”。鲍至于公元523年追随时任雍州刺史的萧纲(梁简文帝)来到襄阳,此时距萧藻旌表王氏不过上十年。将贞女楼作为襄阳名胜记载于地理专著中,说明此楼尚在,正史的记载完全可信。一个“贞女”,更证明“娼家女”之说绝不成立。
其二,正史中为其立传。《南史》是唐初官方修编的信史,能被正史立传的妇女,绝对要符合封建道德标准。之所以将王氏事迹收入《孝义传》中,前提是曾经被前朝官府公开旌表,而民间尚无王氏本“娼家女”的传言。与王氏同时代、同样以美貌和文才著称、名气更大的钱塘名妓苏小小,不仅正史中未立传,甚至没有任何记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职业与身份卑贱。
其三,入选御敕官修女教读物。清初,顺治皇帝遵孝庄太后之训颁旨,命大学士傅以渐主持编纂女教读物《内则衍义》。王氏事迹收入《礼之道》篇,该文开头记述:“梁王氏,灞陵王整之妹,冒母姓姚氏名姚玉京,年十六,归卫敬瑜。”[10]437-438寥寥数语,将姓名来历交代得十分清楚,并未涉及青楼出身。傅以渐是清代第一个状元,学富五车,治学严谨。《内则衍义》又是奉最高统治者之命编纂,是朝廷教化天下女子的读物,书中淑女烈妇事例,全部从正史列传中挑选,稗官野史、近代杂刻者一概不录。钦定之书,不可能允许一个不符合封建礼教的青楼女子,作为教化天下妇女的“道德楷模”。傅以渐主持编纂此书时,显然摒弃了小说家言和影响巨大的民间传说。
(二)王氏平民出身毋庸置疑
前文已经论及,《南史·孝义传》和《南雍州记·贞女楼》记载的王氏,就是一普通民间女子。但是,近年来冒出的一种新说法,混淆了人们的试听。在一些网络平台和自媒体上,出现了不少文章和网贴,称姚玉京本出身官宦人家,为“寿安(今河南宜阳县)知府姚远之女”,其父死于战乱后随母流落至“襄州(今河南方城)”,其母病故后沦为“怡情馆”营妓。在这一版本里,襄阳“卫敬瑜妻王氏”被篡改为方城“卫敬瑜妻姚玉京”,从“娼家女”出身,又变成了“官家女”出身,然后沦落为妓,其身世更加曲折离奇。此说无论是旧编还是新编,都十分荒谬。
其一,果真如此的话,正史就不会记载卫妻为“王氏”,而应称“姚氏”。也不会称其“王整之姊”,而应直接称“寿安知府姚远之女”。
其二,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府,是在南北朝几百年后的唐代才出现的建制,而且无论是寿安还是宜阳,古代从未设置过府衙。既无“寿安府”,何来“寿安知府”。将“襄州”标注为“今河南方城”更是移花接木,历史上的襄州治所从未设置在河南方城县,襄州也从未管辖过方城县,二地毫无关联。
其三,《南雍州记·贞女楼》中记载的“父母舅姑欲嫁之”[2]166-168,《南史·孝义传》中记载的“父母舅姑咸欲嫁之”[1]450,都说明卫敬瑜去世之后,王氏的父母仍在世,不存在其嫁与卫敬瑜之前父母已亡故。
传奇小说中所称“嫁襄州小吏卫敬瑜为妻”(有的版本称“嫁襄州小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小吏”的身份仍比较低微。古代的官与吏大有区别,官为朝廷任命有品级的官员,而吏则是地方官府雇佣的差役等低级办事人员。需要指出的是,王氏生活的时代并无襄州,襄州的设置是公元554年,西魏吞并襄阳之后的事情。此前的襄阳有雍州、襄阳郡、襄阳县几级官衙,不管是哪一级官衙的“小吏”或“小校”,都属低级雇佣人员,在正史中与其他市井小民一样不值一提。因此,王氏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就是一个普通民间女子。
(三)王氏是梁初从霸城迁居襄阳的北方流民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王氏具体生活在哪一王朝,哪一地区,《南史·孝义传》中并未具体说明。因此,给后人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也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例如,《丽情集》《事文类聚》等称“宋末”,《内则衍义》则称“梁”。从《南史》中所载萧藻旌表之事分析,王氏生活的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梁初。因为地方官府一般不会旌表前朝的人或事,更不可能跨越南齐而追溯到刘宋王朝。萧藻任雍州刺史是公元511年至512年间,南梁建立于公元502年。那么,王氏应当是病故于梁初。病故时多大年纪正史未载,《燕女坟记》等记述的是:燕“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5]861《物犹如此》称:“春来秋去,殆七霜矣。”[8]49《内则衍义》称:“如是者五六年。”[10]437-438无论按哪个时间推算,王氏病故时都不会超过26岁。傅以渐所称的“梁王氏”是可信的。当然,王氏完整的生活时代,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齐末梁初。
至于王氏生活的地区,正史也未明说,只是点到“霸城”和“雍州”两个地名,以及萧藻旌表之事,等于间接交代王氏原籍霸城,后迁居于雍州。
霸城西汉时为霸陵县,古属雍州,故城距今西安市东北35里。西晋五胡之乱,北方被少数民族占据,晋室被迫南渡,是为东晋。北方士绅庶民为避战乱大量流落南方,其中雍州一带流民主要落户在襄阳一带,晋廷随之将雍州侨置于襄阳。南朝刘宋时又划实土置雍州,治所仍在襄阳,这一时期的雍州即指襄阳。当时霸城属北朝地域,该事迹既然记入《南史》,就说明霸城只是王氏的原籍,而非故事发生地。不然的话,其事就应该载入《北史》了。
萧藻先后担任过益州刺史、雍州刺史和兖州刺史等地方要职,在朝中担任过仆射、侍中,官至极品。王氏传中不点他所担任过的其他官职,却点了任职仅一两年的雍州刺史。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雍州刺史旌表本州贞女节妇。与萧藻同时代的鲍至,在《南雍州记》中,明确把萧藻旌表王氏的贞女楼记为襄阳名胜就是铁证。
《燕女坟记》及其他古籍中,姚玉京(或王氏)“嫁襄州小吏”及燕女“同游汉水之滨”的记述,均一致指向襄阳,依据的无外乎是《南史·孝义传》及《南雍州记》。对此,《事文类聚·燕女坟》描述得最清楚:“按,《南史》载,襄阳霸城王整之姊嫁卫敬瑜。”[6]1037点出了南史所载的就是祖籍霸城的襄阳之女王氏。
(四)王氏幼年时的家境应该不差
王氏家族南迁襄阳的原因,就是战乱。正史惜墨如金,不可能面面俱到,对王氏从前的家境虽未记载,但透过文字应该可以作出推断。王氏不仅识文断字,甚至也可称为才女。最能代表其文才的,是她留下的两首诗。
一首是《咏柏》:“墓前一株柏,根连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城何足奇。”[1]450作者思念亡夫,情思绵绵,以比兴的手法,将眼前之景比自身境遇,真切感人。前两句写墓前的一棵柏树本是树根相连,忽然树枝相交纠缠在一起,然后又分开,如同作者和亡夫一样。后两句用对比的手法,强调自己对丈夫的思念能够感化树木。那么,杞梁之妻因痛哭亡夫以致城墙崩塌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撼人心魄。近年重刊出版的乾隆《襄阳府志》[3]369-370中,将“颓城”印成了“秀城”,估计是因原本字迹模糊而导致核校错误。后来不少文章也以讹传讹,写成“秀城”,造成文意不通,诗味平淡。这恰好说明作者用典太过巧妙,平实自然,不露痕迹,致参与整理乾隆《襄阳府志》的学者和一些附庸风雅者都走了眼。有人说,诗中用的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典故。此说不确,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在唐代才由杞梁妻哭夫颓城演化而成。
其二是《咏燕》:“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1]450同样是比兴的手法,作者将孤燕比作同病相怜,情意深重的老友。既是拟人,也是双关。表面写燕子,实则写自己。该诗句遂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千古流传。明代处囊斋主人所辑历代女诗人的《诗女史纂》,将姚玉京及《咏燕》诗收入卷之四。民国早期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中年丧妻,一直坚守对亡妻的承诺,不再续弦。就是借“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婉拒了劝其续娶的诸多亲友。
相较于同样才高貌美的钱塘苏小小之诗《钱塘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咏柏》《咏燕》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透过这两首诗,足可证明王氏幼年曾受过比较好的文化教育或熏陶。说明王家在南迁之前家境不错,要么是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要么是家境殷实的地方士绅。
《南史》中的王氏,传奇小说与民间传说中的姚玉京,均为“卫敬瑜妻”。而真实的王氏与姚玉京是否为同一人,古人也有论及。清傅以渐在《内则衍义》中称:王氏“冒母姓姚氏名姚玉京”[10]437-438。傅以渐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精通文史,曾任国史院文学士,先后参与《明史》《清太宗实录》纂修,还是清太祖、清太宗《圣训》及《通鉴全书》的总裁官。在朝廷修编的“教科书”中,对王氏“从母姓”说得如此肯定,不会没有可靠的根据,只不过今人尚不知其出处。清徐谦《物犹如此》中记述:“或云:玉京即王氏乳名,加姚者,从母姓也。”[8]49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古代女子只有乳名而无大名的现象相当普遍。傅以渐、徐谦所言若成立,那么,王氏的本名就应该是王玉京。
王氏因何故“从母姓”,《内则衍义》和《物犹如此》均未提及。有人认为,王氏“从母姓”,是因其堕入风尘羞于以本名姓示人。而其孝义之行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导向,故有意回避其出身,以本姓加以褒扬。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前面已经分析了王氏出身娼妓绝不可能,避娼妓之耻的前提便不存在。古人确实有为“避耻”而隐姓埋名的习惯,但以母姓和乳名示人并不能与娼女身份划等号。古人所避之“耻”,不仅有所从事职业带来的“耻”,也有官宦士绅之后,因家道中落而落魄所带来的“耻”。冒用母姓姚乳名玉京如果成立,只能属于后者。从其嫁作常人妇来看,王家南迁到襄阳后家道中落了,沦为寒民,落差巨大。这实际上也是当时许多北方流民的真实写照。王氏因此而羞于以本名姓示人,当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南朝襄阳王氏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个极具传统美德、孝义感天的民间奇女子。王氏的传奇故事已流传一千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古代传奇小说与当地民间传说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发生在王氏身上的故事本身就十分传奇而又感人。传奇小说与民间传说中的化良为娼和孤燕绝食、化仙同游的情节,虽为故事安上了一个市井百姓期望的美好结局,但“娼家女”身份不仅画蛇添足,而且破坏了王氏冰清玉洁的形象。尤其是删去截耳明志、对柏咏叹两个情节,更是削弱了主人公性格刚烈、孝义无双的形象和才女的风韵。
王氏的短暂人生,充满了极度寂寞和痛苦,深深地烙上了封建社会的印记。但就此便简单地将其视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也未必客观。因为南朝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开化的时期,孀妇再嫁并不像后世那样受到谴责。况且,她还得到父母和公婆的主动支持。王氏之所以坚拒再嫁,是出于对亡夫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甘愿青春守寡来侍奉公婆,是一种至孝与担当。与孤燕同病相怜,情深义重,是排遣孤寂心情的一种自我心理疏导。按照现代道德标准来看,有些行为并不值得仿效。但其忠于爱情,孝敬尊长,善良重义的品格则值得称道。作为故事发生地的襄阳,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以民间传说为蓝本(避免以妄构的“娼家女”作噱头),以历史记载为支撑,开辟相应的景点,使其在公民道德教育和推动文化旅游方面发挥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