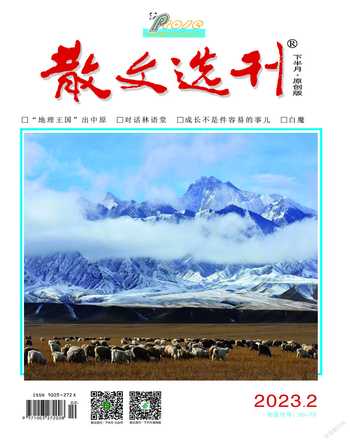指甲花开
李学志

指甲花蹑手蹑脚地开了——像一不小心吹破了泡泡,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直往叶片里钻。薄透的花瓣,蝉翼似的打着颤,把盛在里面的一盅阳光打翻了,斜斜地倾泻下来,泼了一地碎影……
妈妈闭着眼睛,沉浸在梦中。
输液管里的点滴,一个接一个往下跃,像数着妈妈的心跳:一、二、三……晶莹的药滴滚映着周围的一切,红的花、绿的叶、红砖围墙、青砖瓦房……轻盈而沉重,一滴一滴落下来,流进了妈妈的心脏——妈妈的心里到底装着多少个这样明媚的世界?一阵风吹来,指甲花尖叫了一声。妈妈醒了。妈妈说,她做了个梦,和童年的小九一起去摘茅芫……突然,妈妈转过头,笑了——指甲花开了!妈妈说,做梦的工夫,指甲花就开了,是不是指甲花托的梦?妈妈笑得就像童年刚打她眼前走过。
我轻轻按住妈妈的手,小心揭开胶布,一层又一层,趁妈妈捋头发的当儿,按住药棉,快速拔去针头。一点儿都不疼,妈妈按住针眼儿,慢慢坐起了身,眼角晕出笑纹——那里折叠着一大把幸福,好像那并不是她最后一个夏天。
妈妈踱到门前,蹲了下来,指甲花扑扇着玫红的翅膀,像停歇的蝴蝶,打着手语招呼妈妈,妈妈苍白的脸映出了红润。
纤细的花蕊像蝴蝶的触须,微微翕动,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小时候,妈妈也给我染过的——梦里的笑都被染红了的。
我小心翼翼地摘着花瓣,像摘着满夜繁星,只一下,只一下就不疼了,我对指甲花说。叶片举着大锯,沉默不语。
妈妈撮上白矾,我轻轻地在瓦罐里捣碎,红色的汁液洇了一片,阳光泼洒下来,树影斑驳,麻雀在枝头懒懒地啼鸣,长了翅膀的小鸡跑着跑着,骤然停下,侧着耳朵倾听。一下,两下……是一串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扑追着蜻蜓去了?
瘦小的媽妈乖巧地坐在台阶上,伸出双手舀上一勺黏稠的碎花糊,敷在指甲上——妈妈反复嘱托,要严严实实才好,只染大小拇指就行,老了,不能像年轻时,一伸手十个指头火红火红,像啥样儿。看着一个个指头被裹上麻叶,用麻线五花大绑,小粽子似的,妈妈笑了——闺女真个儿中用了。“筛罗罗,打汤汤,谁来了,俺姑娘。哩啥?狗尾巴,扑甩扑甩你害怕。”妈妈俏皮地哼唱起了她亲口教过的儿歌,唱到最后,我们一齐笑了。
一觉醒来,妈妈已经在院里了。满地的枣花像走累了的星星,睡得正酣。妈妈的脸有些浮肿,却是喜悦的。她给我看她的染红的指甲,刚从麻叶里剥出来,深红、明艳,手指肚也浸得通红。
要不是你捣鼓,我都不想染它了——从你爸过世,多少年没染过了,怕被人笑话。妈妈一副后悔的神态。
哪里?很好看的。人家大城市里的老太太,都穿一身红呢。
妈妈不言语了,翻来覆去地看着指甲,脸上现出羞赧。
我突然灵光一闪,摘了两朵澄黄的大麻花,掐去绿色的花萼,就着渗出的黏液,粘在了妈妈的耳垂上,一对明黄的耳坠——我们小时候玩过上百遍的游戏。妈妈指着我的脑袋,笑骂,又翻精,胡起鲜点子。
我总结似的,摘下麻的钟型果实,蘸上余下的汁液,在妈妈的胳膊上盖下一个印章,圆圆的,像手表——小时我们哭闹时,妈妈常这样哄我们欢喜:“几点了?”
妈妈扑哧笑了。挪着脚步取来镜子,左看右看,用小木梳慢慢地梳着头发,梳着梳着,停下了,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面孔,半晌不语。蓦地,叹出一口气,你爸去世的那一年,还说给我买耳环手镯来着……谁知这么快就老了!
妈妈的话沉甸甸的,听落了许多指甲花的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