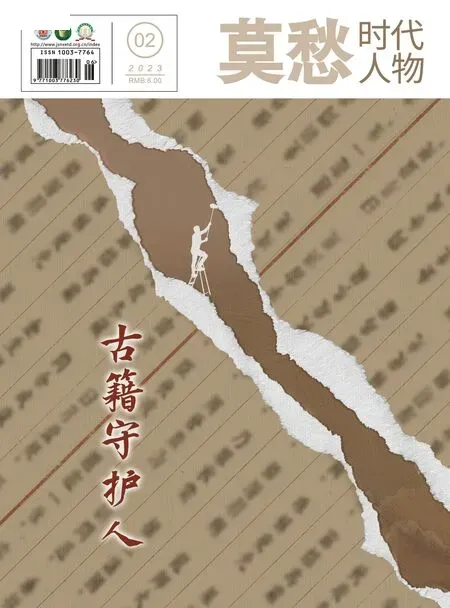行走的学校
文王若宇
历史经过了自然的发酵,在时间的错落长河里,被无数人重新审视和反思,才能酝酿出思想的佳酿。这个发酵的周期,控制在七十年到九十年之间为宜。在这个时间段里,既能够感触到过去留下的温度,也能够相对冷静地评价一个人、一段事。邹雷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行走的学校》,恰好就在这样的时间间隔中,回望了1935年江苏淮安河下镇新安小学的孩子们自发组织成旅行团,用足底丈量祖国大地,用歌声唱响抗日战争胜利黎明的恢弘事迹。
这一步步走出来的历史,该以什么样的笔触去勾勒?邹雷先生必然费了一番心思。尤其是他在创作《行走的学校》时,面临的思考远比旁人深刻,因为他此前已经充分地研究了新安旅行团的历史文献,同时也进行了访谈和走访,形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少年“新旅”路》和《新旅中队》。在这样的背景下,邹雷先生别开生面地选择了用儿童化的、彩色的笔触去创作。正是这样的生动性,让历史中泛黄的陈迹活化了。
活化,是小说艺术最动人的特征。只有鲜活的、生动的人和事例,才具有感染力。无论是“牧童”“小盆友”,还是章枣、“刘鸡鱼”,都在我的阅读体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印记不光有后天的,比如“刘鸡鱼的秘密”,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的生命历程中,总会有一两件藏在心中的事情;也有先天的情绪上的共鸣,尽管小说叙述了八十年前孩子们的故事,但却触抵到了我此刻的内心世界。比如“小盆友”第一次面对大千世界的惶恐、第一次当小老师的紧张。这种紧张感,让我不免回想到多年前课堂上,语文老师也践行着“小先生制”的做法(如今恍然大悟,原来这也是新安小学教育生命的延续)。轮到我初次登台讲课时,我慌乱地将40分钟要讲的内容,囫囵吞枣地在10分钟里自顾自讲完了,引得大家一阵笑场——我不就是那个慌乱的“小盆友”吗?

对于一部好的作品来说,不仅要有情感的共鸣,更要有高尚的情操。作为一群为抵抗外侮而离开家乡,走向广阔天地、走到革命根据地的孩子而言,他们的行为就叫作高尚。邹雷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让这种高尚更加丰盈。他并没有一味地回避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而是用小说的方法阐释和揭扬这个群体生活中掩饰的不足。
对于行走在中国大地上,背负着抗日救国责任的新安学校而言,更有一种“启迪民智”的意义,在邹雷先生的笔下,我们既看到了混沌中的国人和旧官僚,也看到了新人的成长与成熟,两相对比,不难发现,成长是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而给成长提供养料的,则是“教育”。这样的教育,让孩子不会被“苦难”埋葬,而是能够寻找自己的信仰,追求真正的人生。
《行走的学校》中,邹雷先生有意识地突出了新安旅行团所奉行的“教育”指针:“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种教育观念的培塑,成就了新安旅行团,成就了刘纪宇这样的英烈,也成就了一批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我们正在追溯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样也是现实。我们能够透视过去,同样也会被未来透视。《行走的学校》描述了新安小学的过去,但也并不仅仅表述了新安小学和那些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团员。它更透露着一种对未来的期待,这种期待值得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也值得每一个人重新包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