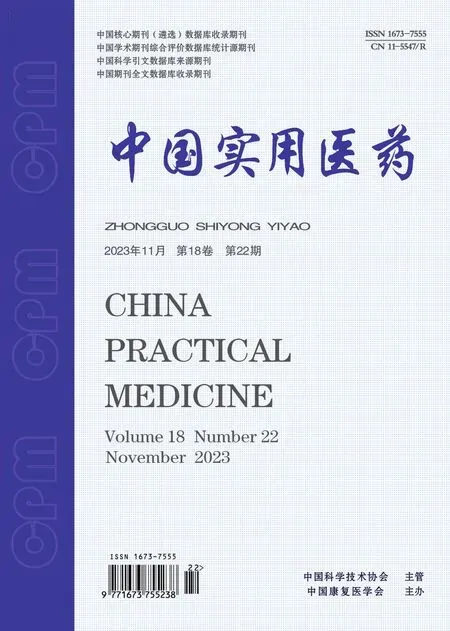中药治疗恶性肿瘤原理再探讨
魏龙艳
1 中药物种基因与治疗疾病的关系
1.1 基因是人体生长发育的本原物种 基因是细胞核染色体具有遗传效应的DNA 片段, 是调控生命形态性能的基本遗传单位, 储存着种族、血型、孕育、细胞生长、凋亡等生命信息, 是细胞分裂、复制和蛋白质合成, 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疾病与死亡等一切生命活动现象的生理过程, 决定着人的健康生死内在因素, 有着自我复制保持生物特征的性能。基因突变、变性、缺乏、免疫、调控能力下降, 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 基因是一切生物遗传生命本原的活种物质。中药也是从古老物种基因遗传下来的物质, 具有强大生命力, 完美的保留了调控人类生长发育的基因。中药治病遵循“药食同源”的原则,弥补了人类遗传基因退化缺乏与免疫力下降的不足。中医通过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作用方式的内涵规律和经验的总结, 适应于人体所需基因的补充、激活、纠偏、修正作用, 从物种基因的根本上解释了中草药治病原理。上海沈朝斌教授就是从中药煎煮液中找到了黄芪补气的微小核糖核酸(miRNA)基因, 解释了黄芪补气培土益肺的原理[1]。沈氏指出:“miRNA 是生物进化过程中最早产生的, 比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都要早, 所以miRNA 在生命起源时是植物与动物共有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基因受多重影响而发生突变或病变, 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这就需要补充原始的基因修饰自身不好的基因, 从而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2]。“如果人体疾病靶基因上的信息能够被吃下去的某些基因片段改写, 使疾病基因的表达被抑制或直接被降解, 自然会‘药到病除’, 就是基因调控作用”。沈氏从基因分子实验的说明是解释中药作用原理的最好例证。
1.2 基因学说与肾藏精理论探源 中医理论关于“肾藏精, 主生殖与发育, 主骨, 生髓......”, 无不道明了基因与肾系藏象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中医“肾”的概念, 涵括了现代分子医学基因遗传, 储存人类种族、繁衍的全部信息, 构造人体合成蛋白质、调控细胞分裂复制, 催生个体生命的形成, 疾病与死亡等一切生命活动现象过程, 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先天原始基因和后天遗传基因的物质, 即中医理论的阴阳水火交蒸,能量气化源泉之所在[3]。因此, “肾藏精”与基因调控生长、发育、衰老、病死规律密切相关。如恶性肿瘤就属于基因失去有效调控, 不能控制细胞分裂、复制过程才出现细胞组织“突变”的疾病。从发病学年龄看,肿瘤多起病于40 岁左右男女, 根据《内经》对人体肾气发育关于“男子五八肾气衰, 发坠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 面焦, 发鬓颁白;女子五七阳明脉衰, 面始焦, 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 面皆焦, 发始白”生长发育衰老规律的论述, 说明人一般在35~40 岁开始阳气逐渐下降、肾气虚衰的生理性衰退现象, 此时基因免疫系统容易出现变化或崩溃, 不能有效地调控细胞的生长, 容易出现组织突变, 发生恶性肿瘤[4]。
1.3 中药治病原理, 即是基因补充修复的作用过程中药治病原理是“药食同源”地利用天然物种基因补充、激活、纠偏、修复的作用过程。①人类起源是从海洋生命到陆地, 从树上到地下, 从狩猎到农耕, 从猿人到智人, 直到现代人, 是个基因遗传进化的过程;②人类生长形成的个体, 通过摄取动植物补充机体所需能量,不断进行基因补充, 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完善其进化质变的过程。起初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结构多为食草、果蔬、少肉、五谷杂粮, 远远不同于现代人生活饮食结构, 处于“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足”并存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其“营养不足”, 即是指人体正常发育的基因的缺乏、退化之不足;③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现代人已不能适应现代饮食结构, 现代人之所以多病, 根本原因是基因失去对人正常生长发育的调控和免疫抗病能力[5]。如现代人体体温从平均37.0℃下降到36.6℃(免疫抗病能力下降30%), 是因为人的劳作运动减少, 肌肉产热能量不足;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失衡, 人体需要的营养基因摄取不足, 导致原本的基因退化、缺乏、免疫力下降的结果;④中药是生长在地球上有着古老强大生命力遗传基因保留下来的物种, 有着完整的遗传基因片段和各种适宜生长的微量元素, 虽然中医药理论上有着“寒热温凉”、“四气五味”药性之说[6], 但毫无例外的真正治病原理, 就是天然中药中原始物种基因在人体不断得到补充、激活、纠偏、修正、修复、自愈能力的结果。
1.4 恶性肿瘤辨治的标与本 中医理论体系以人的“整体观念”为本, 以疾病的证候性质进行“辨证论治”为标, 即人的整体是本, 疾病是标, 整体是本, 局部是标, 人的整体性是固定之本, 灵活地辨证论治是不定的标。现代医学对“细胞癌变是基因突变或基因功能失调结果”的论述, 可以说任何疾病的发生, 都是人体基因免疫调控、修复能力失衡变态的结果。肿瘤的定义是人体在内外有害因素作用下, 使细胞组织器官遗传基因DNA 损害, 丧失了生长调控机制和功能, 产生“以细胞过度增殖为主要特点的新生物”[7]。其病理机制是人体在内外有害致癌因素作用下造成DNA 修复调节功能损害, 从而激活原癌基因、灭活抑癌基因和凋亡调节基因的表达异常, 使调控细胞组织生长机制和功能丧失, 发生异常转化或过度增殖突变而形成恶性肿瘤, 可见恶性肿瘤发生的本质是基因性疾病。西方医学对恶性肿瘤的治疗, 主要从生物细胞分子学局部点位入手, 着眼于微观细胞的“物”质上, 在思维方式和行为认知方面, 并不认为细胞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整体性, 不是从人的整体属性的细胞基因本质原因上着眼,将“人”和“细胞”分离, 只是讲究一味局部的毒杀肿瘤细胞, 就避免不了“肿瘤细胞杀完了人也就去了”的结局。思维逻辑认知观念的迷失, 必然导致错误方法的错误结果。
2 肾虚为本, 是恶性肿瘤论治的基本原则
恶性肿瘤本质上属于细胞突变基因性疾病, 是病理机制的本质现象之本, 所谓痰浊毒瘀寒热气血诸邪夹杂为标, 都是自由基代谢产物和使DNA 基因受到损害的结果。因此, 从“肾虚为本”的观点入手, 是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论治的纲领性法则。在实施治疗的选方用药上, 围绕以“肾”属系统功能的生理病理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 注重药物的归经、性味和升降浮沉的作用方式, 以及脏腑经络表里、五行母子生克、虚实补泻关系。如肾与膀胱是相为表里的功能关系, 肾在脏属水, 藏精, 为生命源泉之性能, 主生殖与生长发育, 其脏腑经络功能部位受纳自然界阴阳物质精华, 外行背部受太阳膀胱经诸脉之阳气温煦, 内敛行于腹部受诸脏经脉之阴精滋养, 通过水火交蒸(水湿精津与人体温度发生生化反应, 即包括现代微观医学细胞质、核和染色体、DNA 基因调控细胞分裂、复制、纺锤体形成等生长发育系统生理功能)气化变物, 催生细胞组织器官形成人体, 是生命新陈代谢的核心枢纽。中医理论上适于咸味归肾药物, 分辨虚实以行补泻之法;肾水以肺金生我者主水, 尊肺主气, 四布朝百脉和卫气屏障, 上下内外宣发肃降沟通、调节水道功能为母, 适于味辛归肺药物, 虚则补之;以我水生木之肝, 化精涵木使之藏血, 且主疏泄, 克我脾土运化而化生万物, 遇实则泻之等。
3 重视利用药材物种基因意识
动植物药材之所以能够经过长时期的四季寒暑、风吹雨打留存下来, 是因为中药有着完整的遗传基因和各种适宜生长的微量元素。如红豆杉就是史前植物基因遗传物种, 其抗癌是经科学实验研究证明, 具有天然植物药材性质, 属于“细胞毒”类化合物“紫杉醇”药物, 是继阿霉素等抗癌药之后, 至今发现的唯一能够调控癌细胞生长, 可作为广谱、高效、治疗多种晚期恶性肿瘤的天然植物药。治癌原理可能就是红豆杉基因能与微量蛋白质结合, 靶向性的作用于细胞分裂复制的G2期和M 期, 阻止细胞有丝分裂及纺锤体生成,抑制癌细胞分裂增殖、转移与扩散, 而不影响肿瘤细胞DNA 及RNA 合成而治疗肿瘤, 可能正是因为红豆杉具有天然植物基因性质而很少有治疗恶性肿瘤副作用的优势, 被誉为“治疗恶性肿瘤的最后一道防线”。
4 论治组方应注重药材基因特点
恶性肿瘤公认的病理机制是“细胞基因突变与功能失调”。中医理论认为其病位主要在肾, 相关肺、肝母子关系等整体相互联系的次要脏属, 因此在治法配方上, 一是以“补气扶正, 益肾增免”为主, 配伍具有鲜明动植物基因特色药材, 如归经肝肾的脊椎动物龟甲类、无脊椎特殊环节生物的地龙、沙漠植物寄生生长的肉苁蓉、真菌繁殖的灵芝等一组具有强大物种基因的特色药材, 与经科学证实的抗癌专属药材组成配方起主要作用的为组方主药(如红豆杉);二是根据寒热痰浊毒瘀气血夹杂辨证性质, 分别选用清热、温化、活血、利湿、解毒诸药。在诸邪之中, 以“寒凝气血”性质为多, 因为肾阳命火本虚(基因功能下降), 不能温行气化使物以常形, 所致气血寒凝而赘生肿瘤, 符合恶性肿瘤“寒凝血瘀”的病机特点, 其病程中伴发的阴虚火旺的“发热”, 也是“真寒假热”现象。因此选用具有温性扶阳之药是配方中不可缺少的药物(如肉苁蓉配伍砂仁, 性平味咸入肾温里, 肉桂峻热伤阴, 只宜少量作引使用);三是“补气、益肾、解毒”三者是基本固定的用药模式(简称2+1)法则。“补气益肾”是不变病机之本, “解毒”是夹杂病邪性质灵活辨证过程之标[8]。鉴于癌变细胞组织是诸邪所化之毒最终损害机体的结果, 因而“解毒”是贯彻始终的治疗法则, 可根据病邪证候性质, 分别选用清热、温阳、化痰、利湿、活血、解毒等性质的中药灵活辨证组方论治。
5 中医药抗癌保健需注意适于患者
源于古老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天人相应”,运用宇宙观的整体观念与个体化证候的辨证论治诊疗疾病, 与西医思维认知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认知, 从本质上并不单看作是一种病, 而看作是某种病的一个症状, 或一种病的结果, 而不是恶性肿瘤发病起源的病因, 治疗上不只是要设法消除疾病, 而是注重消除疾病的病因, 针对疾病所反映的客观证候信息进行辨证论治, 真正消除疾病的关键在于人的“正气”(基因)的调控、修复、自愈抗病能力。从中医整体理论而言, 就不能、也没法、局限地存在治疗“恶性肿瘤”一说。因此, 癌症在古中医疾病学上属于“积聚”、“癥瘕”等范畴, 属于中医诊疗的慢性疾病。后受西医影响, 出现了以肺、胃、肝、肠等组织器官命名的各种“癌症”诊疗名词。现代中医药学家虽然也建立起了“中医肿瘤学”, 还出版了不少的书籍[9], 基本上是西医学者做中医的文章, 没有脱离西医的思维模式、体例, 不过是“结合”了一些中医的论述而已,都还是强调以“细胞病理学为依据”。目前中医药进入保健抗癌行业还是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10]。为避免医患纠纷和言行违规, 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为此建议:临床接诊以“知情自愿”为原则, 可以“保健抗癌防病”进行中医药服务的口径接待患者;行为方面把握“同情而不宜过度热情, 做到患者为客, 肃敬礼貌,医患关系分明”, 营造情同家人的人文氛围, 以示尊重患者隐私, 减轻患者心理压力;要把“心理疏导与科普培训”做到有专业专人日常健康教育内容, 作为临床工作重要组成部分, 贯穿于保健康复治疗过程的始终;注意患者心理情绪稳定开朗, 必要时首先进行心理治疗与疏导, 鼓励树立战胜病魔的意志, 共同制订康复方案。在不影响治疗顺利的原则情况下, 不排除、不评价患者与其他方面建立的治疗康复关系;建立医患信任合作关系, 签订有家庭监护人约定谅解保障备忘录, 遇到心理阻抗、不信任或经过一定时间治疗感到用药无效时, 即行终止治疗活动, 必要时就此通过公证以取得有效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