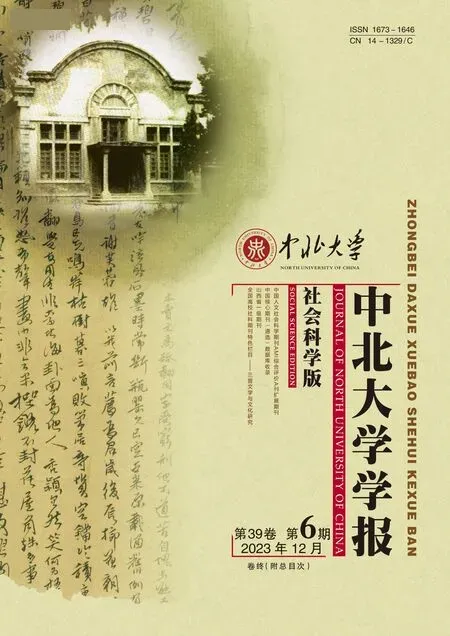民族化及其悖论
——《梁祝》与十七年时期“民族形式”问题
李子豪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民族形式”问题是考察中国20世纪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目前学界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一,将“民族形式”视为政治话语,从思想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高度进入。尤其在史学界,如李建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将“民族形式”放置在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分析,突出了其中的政治文化内涵。二,文学界相关论述集中在“史”的高度、现代性的视野。如汪晖的《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讨论》[2]、贺桂梅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3]等文,对“民族形式”背后反映的文化进程做了深度分析,并从文学的视角提供依据。三,作为政治文化话语的“民族形式”落实到文学艺术领域,“民族形式”原本宏大的能指随即有了具体的所指。周维东的《革命文艺的“形式逻辑”:论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4]一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从文艺界对“民族形式”的争论进入,梳理了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形式逻辑”,进而说明“民族形式”论争进入文艺界的必然性。以上研究,从政治文化高度到艺术形式逻辑,构成了“民族形式”研究的问题谱系。本文沿着周维东的研究继续追问,“民族形式”创作实践与理论上的范式是否一致?换言之,那些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是不是按照“民族形式”理论而创作的?如果不是,又对理论范式造成了什么影响?“民族形式”从政治领域进入文艺领域,既包含一般理论问题,还有更具体的现实诉求——以理论上的“民族形式”指导艺术实践。本文以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音乐作品《梁祝》为个案,考察理论范式与创作实践之间的联系与脱节,进而为理解“民族形式”本身以及十七年时期艺术的现代进程提供新视域。
1 “民族形式”的理论路径
十七年时期的“民族形式”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延安时期的延续,其理论倾向基本一致,但过程并不相似。1938年10月,毛泽东首次提出“民族形式”概念之后,1939年延安《文艺突击》杂志便设置专栏促进争论。此次大讨论波及全国范围,参与人数众多。学界对此问题的梳理较多,本文不再赘述过程,而是做一总结。此次争论,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本自有其语境和理论谱系,并非专对艺术而发。但延安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重大意义,将作为政治话语的民族形式关联到艺术方面。语境的转换造成了语义的变化,“民族形式”中的“形式”明确为作为艺术“语言”(1)汪晖在《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文中分析了“民族形式”争论中语言的“方言土语”特征。在艺术领域,作为艺术“语言”的“形式”同样具有这种特征。的创作技法与创作原则。二、以延安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为代表,“民族形式”出现两条理论上的建构路径。以周扬、艾思奇、柯仲平等人为代表的延安主流观点,批判接受“五四”新文艺经验,以通俗文艺为目标,强调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加入新内容,进而创造出新形式。所谓旧形式,“指的是传统中国已经成型且流传广泛的文艺形态,在许多讨论中,‘旧形式’与‘民间形式’常互相重叠”[5],由此形成具有“方言土语”特质的“民族形式”。以胡风、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派”坚持新文艺传统,以启蒙大众为目标,强调融合外来的、先进的艺术形式,从而创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形式”(2)将其划分为两种对立的倾向是为了明确基本立场,事实上双方都存在不彻底性。比如,“五四”新文艺的影响要比想象中大,延安知识分子对它的批判并不那么决绝。身处延安的冼星海、何其芳都曾肯定外来形式的优越性。冼星海说:“旧形式和旧内容虽然调和地能配合,但绝对不合适于现在,新内容配合旧形式是有点不调和……参考西洋最进步的乐曲形式,从事改良中国的民族形式,建立中国乐曲的新形式。”何其芳也认为:“欧洲的文学比较中国的旧文学和民间文学进步,因此新文学的继续生长仍然主要地应该吸收这种比较健康,比较新鲜,比较丰富的养分。”分别参见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号,1939年11月16日。。
两种观点在争论初期表现出分庭抗礼态势,随着争论的深入延安主流观点逐渐确立合法地位。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中提出的废止洋八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要求,事先已经为延安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提供了不可置疑的意识形态保障[6]。1942年的《讲话》更是明确提出了运用旧形式的观点:“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7]855在文艺大众化的要求下,“民族形式”的“方言土语”特质愈发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五四派”坚持的“民族形式”实际上是拒绝讨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或是拒绝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的革命想象[5]。
1949年后,现实景观的改变,两条路径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对民间旧形式的推崇出现了回落。旧形式在革命时期具有通俗的优势,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其中封建、落后成分同样明显。在表演形式上,应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8],坚持形式改造过程中的历史观、实践观,基于实际需要吸收运用,“教条主义的无批判的旧形式利用,很有害于应有之新风格的形成的”[9]。此外,对外来形式的遮蔽也出现了松动。“积极学习西洋古典音乐,这是普遍都需要的,对于过去老解放区的干部尤为重要。”[10]“为了使我们新的表现形式的完美健全,除主要地接受中国自己的旧有遗产之外,不用说,还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成分。”[11]在新阶段、新内容的要求下,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具有封建色彩的、感性的、抽象的一面被扬弃,西方艺术形式理性的、写实的特点被吸收。后者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等新内容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曾被遮蔽的“五四”新文艺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解蔽,至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对外来形式的推崇达到高潮。江丰担任中国美术学院代理院长时创建“彩墨画系”,将西方的写实技法与中国画融合起来。李凌提出“不中不西,又中又西”观点,认为“‘不中不西’就是不全象中国,也不全象西方。换句话说,就是‘又中又西’。这也是创造新的民族音乐形式难以避免的情形”[12]。高潮之后,事情很快发生变化,以李凌、江丰为代表的新文艺观点在1957年被视为民族虚无主义而遭到批判。潘天寿批评道,我向来不赞成中国画“西化”的道路,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13]21。庄映等人批评李凌,“移植论是要外国音乐和民族音乐作机械的混合,是对待民族形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14]。一时间,“中西合并”的“民族形式”路线成为众矢之的。
批判事件表明,接受外来形式很大程度上是艺术家的一厢情愿,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来形式始终非常谨慎。周扬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就明确指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的表现之一,这种思想就是必须加以批判的。”[15]1957年之后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更是直接排除了“五四”以降几十年的新诗传统[16],至1960年代,外来形式更是作为资产阶级形象而出现。可见,十七年场域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基本延续了延安主流观点的“民间”导向、通俗文艺立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新文艺观点偶有抬头,但始终没能从根本上造成改变。由此追问,那些被公认为民族化、大众化的典范之作是否符合以“民间旧形式”为核心构成的“民族形式”?创作实践与理论路径是否一致?这一切都要回溯到十七年时期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中一探究竟。
2 本土与外来之间:《梁祝》的再创造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首演于上海兰心大剧院,时年18岁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俞丽拿独奏。演奏结束后,观众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俞丽拿不得不返场再次演奏全曲。她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演出中完整地拉了两遍《梁祝》。观众的热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只是一个学生,面对观众不可遏止的热情有点不知所措,只想竭尽所能缓解观众高亢的情绪。”[17]《梁祝》首演后观众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亲切地将其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18]。而就是这样一首被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音乐作品,与以“民间旧形式”为核心构成的“民族形式”理论完全不同。
《梁祝》创作时期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由何占豪、丁芷诺、朱英、张欣等人组成的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考虑创作一首作品向国庆献礼。小组内部初期拟定了三个题材,分别是大炼钢铁、全民皆兵、梁祝。小组将题材上交给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孟波看了这三个题材之后认为,最接近、最适合的就是《梁祝》,何占豪对越剧非常熟悉。于是,这样一首不太符合时代背景的作品被确定了下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经由同名越剧改编。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很强的叙事性,《梁祝》中包括了同窗、相爱、抗婚、化蝶等几个重要情节,在创作初期,何占豪与陈钢商量最多的就是怎样将故事情节与曲式结构达到完美的统一[19]。在这样的目标下,何、陈二人最终确定了奏鸣曲式结构。奏鸣曲式是西方古典主义时期一种重要的器乐曲形式,主要包括呈示部、展开部与再现部三个部分,相互之间有着较强的逻辑性与关联性。采用奏鸣曲式与梁祝进行结合,既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心理与思维方式,前后又富有逻辑性,全曲紧紧把握住几个重要的戏剧场面,爱情与反抗贯穿全曲[20]。在呈示部,音乐表现了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情节,利用器乐营造歌唱性的对话。展开部利用板腔体音乐的发展原则。用散板与快慢交替的嚣板的紧拉慢唱形式以及板鼓强烈的节奏形成全曲的最高潮——祝英台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21]。再现部利用竖琴的琶音与钢琴的华彩音型表现“化蝶”情节,最终结束。何、陈二人在创作“化蝶”部分时顾忌其中带有封建迷信思想而考虑取消,孟波建议说:“不能只讲英雄主义也要讲浪漫主义,‘化蝶’完全是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19]于是“化蝶”被保留了下来。
在调性使用方面,《梁祝》建立在徵调式上,延续越剧的基本调式。调性转换使用奏鸣曲式“主—属—主”原则,既将西洋形式融合其中又保障了民族色彩,以至于主流话语都曾给予较高评价:“这首作品在应用民族民间音调和创作手法,以及吸取世界音乐文化成就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21]纵观全曲,将西方奏鸣曲式与中国传统戏剧结合起来,正是音乐评论家李凌提出的“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模样。
与知识分子从理论层面思考“民族形式”不同,何占豪、陈钢的“民族形式”来自于他们的创作实践。在《梁祝》创作之前,何占豪找到“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丁芷诺进行首次民族乐曲西洋化的尝试。何占豪改写一段二胡曲《二泉映月》的旋律,然后交给丁芷诺配上和声。据丁芷诺回忆,改编后的曲子在实际演出中反响很好,对他们鼓舞很大。演出结束后,又有人专门找到他们为河南梆子《梆子风》和扬琴曲《旱天雷》进行改写和配器。之后这三首曲目一齐在当年七一党的生日作为献礼曲目进行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何占豪等人的先期创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梁祝》的出现。
《梁祝》的成功的确让人意外。1957年,民族虚无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一年之后《梁祝》利用西方形式元素表现中国故事没有被批判反而被视为民族化、大众化的典范之作。作为一首长达25分钟的“枯燥”的严肃音乐,俞丽拿能够在演奏一遍之后再次返场,足可见作品本身承载的民族意义非凡。早在1940年代,贺绿汀就曾提出:“所谓‘民族形式’在音乐方面讲应该是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形式。”[22]十九年后,《梁祝》或许是与贺绿汀所谓“民族风格”距离最近的作品,它承载的民族意义遮蔽了形式上的“缺陷”。不只是音乐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被肯定的绘画作品,赵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王式廓的《血衣》等,都在创作原则以及形式技法上借鉴了西方形式。相比之下,诸如焦点透视、素描等西方形式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外来形式的加入既不是僵硬的土洋结合,也不是被动地服务于内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呈现。与《梁祝》一样,这些反主流理论的作品得到了主流的认可,表面上看是对“民族形式”的延续,实际上完成了外来形式的运用与再创造。
3 历史发展与革命现实:差异的根源及其意义
一部不是——至少不是循着民间旧形式的“民族形式”理论路径创作的作品获得了认可,理论范式与创作实践出现了脱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有必要回溯“民族形式”首次提出的情形。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首次使用“民族形式”这一术语:“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7]534在毛泽东的语境中,所谓“民族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宏大的文化能指,包含语言、心理、思想等所有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它可以落实到各个层面,从而产生具体的所指,文艺界的“民族形式”即是一例。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毛泽东继续强调,在运用“民族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宏阔的视野,就像他反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来不在“西方”乃至“现代”的外部讨论“中国”的命运一样[23],将中国文化放置于世界文化之中审视。毛泽东的“民族形式”论述更倾向于哲学层面的总体关切,不直接指向文艺界的“形式”问题,但仍然为其提供了方法论与价值观的指导,即独立的民族意识与宽广的文化视野。在后续的“民族形式”大讨论中,能够从这两方面契合毛泽东高度的人并不多,杨松与郭沫若即是两例。
时任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副部长杨松的《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一文,是刊发在1939年延安《文艺突击》杂志“民族形式”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文章虽然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但通篇都没有使用“民族形式”一词,而是代之为文化。在他看来,目前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特别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宝藏,去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殊性与全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性,以便扬弃旧的部分,继承一切优秀民族、民主的文化传统,建立真正革命的民族主义新文化[24]。显然,杨松没有局限于“形式”问题,而是上升至文化高度、世界范围予以思考,文章内容触及了毛泽东论述的核心。
相比杨松,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中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入,更接近毛泽东哲学意义上的关切。郭沫若一上来就参透了“民族形式”宽广的文化能指,他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这儿充分地包含有对于一切工作者的能动精神的鼓励,无论是思想、学术、文艺、或其它。”[25]同时,这种文化决不能故步自封于当下,“中国目前固须充分吸收外来的营养,但必须经过自己的良好的消化,使它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而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事物来,就如吃了桑柘的蚕所吐出的丝,虽然同是纤维,而是经过一道创化过程的”[25]。落实到文艺形式,郭沫若以敦煌变文、国乐、绘画等艺术为例,指出这些民间形式实际上都与外来形式密切相关。如“国乐比之西乐,其乐理、乐调、乐器、强半都是外来的,而且自南北朝以来,这些外来成分在国乐中实占领导地位。这些艺术部门,元明以后便衰颓了下来,现在要拿来和西方的技巧比较,公平地说,实在是有逊色[25]。”郭沫若的落脚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在强调以西为师。但实际上郭沫若认为,这不是向西学还是向北学的问题,而是旧之于新、落后之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新兴文艺要离开民间形式,而接近最新阶段的西式,同一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一人的好恶或主张所能左右的。”[25]因此,郭沫若呼吁:“不要以为用外来便是‘欧化’,世界伟大作家的遗产,我们是更当以加倍的努力去接受,我们要不断的虚心坦怀地去学习,学习他们的方法,促进我们的形式的民族化。”[25]郭沫若没有将中、西视为个别,而是从一般的视野出发,将其看作总体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要艺术反映的是现实主义、时代精神,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那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民族形式”。
总体地、历史地看待“民族形式”问题,在哲学高度没有问题,但如果同时观照其中的特殊性,即中国当下的革命现实,不做区分的“一般”视野就变得有一些不合时宜。换言之,文艺的发展应始终坚持与革命实践相关联,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7]534。因此,在革命现实的要求下,文艺创作必须兼顾人民大众的接受问题,也即“普及”问题。“民族形式”的中西问题就要做出具体区分,过分强调西洋形式不仅不利于大众接受而且还有欧化风险。如此一来,郭沫若的“历史必然性”结论虽然贴近毛泽东的哲学内涵,却与革命现实存在分歧; 相反,以“民间旧形式”为核心构成的“民族形式”理论虽然不及毛泽东哲学层面的高度,但却深刻捕捉到了“革命文艺”的真谛。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1940年代向林冰与葛一虹的争论,虽然向林冰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受到了文艺界的严厉批评,但事实上他的观点被大众化运动接受下来的原因; 1950年代江丰、李凌等人被批判为民族虚无主义的原因。以向林冰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不及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哲学思索,但却深度契合革命现实下的民族化、大众化路线。
由此出发,我们或许更能确定《梁祝》所处的位置及其意义。《梁祝》既不是完全意义“革命文艺”要求下的大众化产物——对民间形式的“过分坚守”,也不是完全延续“五四”新文艺——对外来形式的“盲目崇拜”,而是二者各取其一的辩证综合。从表面上看,《梁祝》似乎背离了文艺界兼顾革命现实的“民族形式”理论路径,但无论如何都应将其视为对“民族形式”的创造与发明,因为它更贴近毛泽东、郭沫若等人哲学层面的思索,具有独立的民族意识与宽广的文化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梁祝》具有一种“复杂性”,它既符合——同时也违反了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判断。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梁祝》才得以在1950年代被认可,并以一种“看似反主流”的姿态实现了对“民族性” “世界性” “现代性”的想象。
4 结语:发现“当代性”
《梁祝》没有遵循以“民间旧形式”为核心构成的“民族形式”理论路径,反而从被排斥的外来形式入手,创作出了民族化的典范之作。这一悖论再次指向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文本的理论能否真正指导创作实践?这似乎一直是理论的期望,但始终没能真正实现。即便如此,《梁祝》没有局限于理论,而是出色地完成了民族化的任务,直到现在《梁祝》依然是卓越的、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伟大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时期艺术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要区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以《梁祝》为代表的创作实践完成了对“民族形式”理论的修正与超越。
《梁祝》对“民族形式”理论的修正和超越,正是“当代性”意识的体现。所谓“当代性”,即是对历史与当下的不断反思和对未来的不断叩问。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的“当代性”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符合人类发展的“真理性”凸显,它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颠覆,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现代性的延展和修正。具有“当代性”意识的作品,永远活在时间的河流中,活在“过去”和“未来”之中[26]。与《梁祝》同时期的作品,大都已经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些作品在传统价值与外来冲击、个体自由与集体精神的龃龉中丧失了反思的能力,没能突破时代精神的局限。人们虽然在当下接受了这些作品,但很快就因为意义的缺失而遭到拒斥。“当代性”意识使《梁祝》的精神内涵与审美意义具有“前瞻性”与“真理性”。
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看来,一件作品是文本,作品所处的社会情境是上下文,二者的关系是静态的。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始终处在相互衍射中。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方式审视《梁祝》,通过作品去寻找与它相关的上下文,并指认十七年时期的社会情境产生了作品,这种静态的、认同的、匹配的方式将会掩盖作品的真正价值。而“当代性”的发现,正是基于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动态的不同文本的互文中确认作品的价值。《梁祝》的“当代性”意识根源于一个核心特征:以“人性的价值标准”去构建作品的基调[22]。正是对“人性”的坚守,《梁祝》才能突破传统与外来、个体与集体的时代局限,重建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涵。在后结构主义的时代,沿着《梁祝》的路径,挖掘“当代性”意识在历史中的存在,将其嵌入当下艺术创作与批评,并进一步探索其未来建构,无疑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依靠《梁祝》一个个案显然过于单薄,应该继续追问与寻找,在浩如烟海的艺术史中,又有多少具备“当代性”意识而尚未被确认的作品。它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价值资源和历史支撑[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