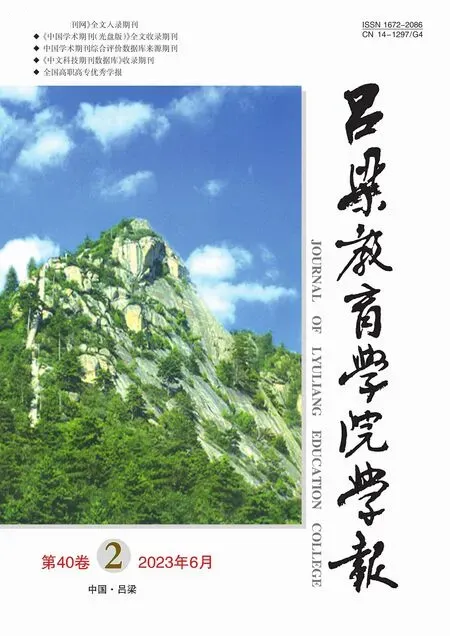《生死场》与《松花江的浪》中的“抗战叙事”比较
安 宁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引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惨痛和残忍的一页,“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不同方式的书写。所谓“抗战叙事”,指的是用一定的叙事形式、叙事手段,对“抗战历史”进行表现。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系统,保存了人类求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质异化和分裂的种种非常表现形式。[1]对于“抗战小说”,《小说大辞典》下的定义是“1937年到1945年前进步文艺界所创作的小说”[2]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作家群和1949年随蒋介石来台的东北作家都有在东北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都目睹或参与过东北的抗日斗争。然而,由于创作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叙事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东北作家群笔下的“抗战叙事”更多地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例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抵抗侵略的英雄事迹,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史诗规模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内外矛盾。而台湾的东北作家笔下的“抗战叙事”则更多地采用追忆的视角,具有“怀乡迷惘”的情怀,例如齐邦媛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以史诗的规模追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纪纲的《滚滚辽河》叙述了国民党东北地下组织青年的抗日活动。萧红和赵淑敏作为其所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其创作与以往的男性作家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
萧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作品一方面呼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东北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宏大历史;更重要的是,她以女性的独特眼光和悲悯情怀关照历史,写出了时代语境和父权压制之下女性生存权的压抑,具有文化自省和人道主义的情怀。赵淑敏出生于东北,成长于台湾,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得她的作品具有台湾作家独有的怀乡情结。萧红和赵淑敏同样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见证人,其作品表现了东北沦陷的生存苦难和心理负重,是文学精神在现代和当代的汇合。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表现内容三个方面,分析二者“抗战叙事”的不同。
一、叙事视角的不同
在创作叙事性作品时,叙述视角是作家切入生活的入口,是作家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方式。[3]在叙事视角方面,萧红通过女性的视角反映抗战历史,在抗日战争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将目光转向女性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女性的悲剧命运,使得宏大的战争历史在女性的视角下得以重构;赵淑敏采取了童年视角,用少年高金生的视角重现东北人民的抗日历史,体现了一种时代感召和个人命运的结合。二者叙事视角的不同使得“抗战叙事”体现着作者不同的情感指向和人生体验,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4]。
(一)《生死场》:女性视角下的抗战叙事
萧红作为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代表,其女性的身份也使得她的作品带有独特的叙事视角。鲁迅先生曾经对《生死场》作出这样的评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5]
女性因其本身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她的弱势地位,在《生死场》中,萧红放弃了对抗日战争的史诗性书写,而是将目光下移到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性别、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给女性带来了多重障碍。小说并未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人民抗战历史展开大规模的叙述,而是通过描写王婆、金枝等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从女性的怀孕生子、劳动乃至出走的角度反映抗战历史。萧红笔下的农村女性形象均具有坚韧的性格,她们对抗日战争积极、沉着,但由于女性的特殊身份,这种个人层面的反抗都以悲剧告终。
以王婆为例,面对压迫和不公,她表现为愤怒,继而把愤怒转化为反抗。她的早年经历极其辛酸苦楚,但她的不幸命运恰好映衬着她的坚韧。三岁儿子的意外死亡给她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在悲痛绝望的低谷,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在革命中阵亡后,王婆选择了悲壮地死去,在女儿的呼唤声中又奇迹般地生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的民族意识得以激发,以女性之躯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她给义勇军的半夜集会放风,站在窗外的王婆无限接近了专属男性的“屋里的世界”,王婆辛勤培育的女儿也在她的鼓舞下加入了军队,因“背着步枪爬山爬得快”受到黑胡子的赞赏。波伏娃曾说:“少女就是这样显得绝对被动,她出嫁,在婚姻中被父母献出去;男孩子则是结婚,娶妻。他们在婚姻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扩大和确认,而不是寻找生存的权利本身,这是他们自由承担的一项义务。”[6]988然而,在经历了前半生的苦痛和抗日战争的爆发后,王婆不再满足于做家庭妇女,她放弃了洗衣做饭等往日的“义务”,把精力转向培养女儿“复仇”和革命。王婆以及村中的其他寡妇在日军入侵的现实之下觉醒,她们的悲剧命运也促成了绝望之中的反抗,女性的生存危机也是对国家苦难的回应[7]。金枝同样是挣扎在“生死场”上的女性,她的反抗以出走的形式表现出来。金枝的出走,一方面反映了外敌的入侵导致自然经济的解体,迫使以农耕为生的农民外出以其他方式谋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金枝在命运的“馈赠”中明白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残酷,看穿了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发出了“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8]100的感叹。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金枝踏入了哈尔滨城,试图用这样的方式与过去的生活告别,但是迎接她的却是新的悲剧。在小说的第十四章,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金枝乔装打扮,小心翼翼地躲避日军的注意,不曾想却被城里的单身汉侵犯,所以听到王婆说日本人破开孕妇的肚子杀害婴儿的恶行时,金枝只是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8]100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女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在父权体制下,男人是家庭和女性的主宰者,“女性的家庭对于她来说是她的世俗命运,是她的社会价值和最真实自我的表现”[6]1046;战争加剧了女性的苦难,让她们进而失去了“家园”的庇护,成为失去土地的流民,女性的命运悲剧和家国存亡的民族悲剧在这样的视角下得以融合。金枝的结局同样留下了悬念,作者只用了“金枝又走向哪里去?她想出家,庙庵早已空了”一句话交代金枝的命运。金枝做尼姑而不得,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九一八事变给乡村带来的灾难,这背后也蕴含着作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当国破家亡,一个女人的命运是否还能够由自己主宰?
由此可见,在《生死场》中,宏大的战争历史在女性的视角下得以重构,对战争场面的叙述极少,往往粗笔带过。作者叙述了女性视角下的自然灾害、阶级压迫,抒写了农民从“蚊子似地为死而生”到“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从而走上民族解放斗争前线的历史性转变,女性的命运也使得这种反抗带有了悲剧意味。在这里,“抗战”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境遇,其背后是人无力自主的悲剧命运。生命的孕育、生产与生长都意味着灾难,贫困和苦涩的人生无情地消解了生命的意义;女性视角下的反抗尽管结局悲惨,透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战争的残酷性得以展现。
(二)《松花江的浪》:童年视角下的抗战叙事
不同于《生死场》中的女性视角,赵淑敏在叙述抗战历史时采用了童年视角,将小说的整体架构设置于少年高金生的视角之下。“童年视角是一种与成人视角较为不同的叙事策略,一般意义上的童年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9]小说的开端,高金生只是一个初到哈尔滨的十二岁少年,他的成长过程与抗日过程相交织,他目睹了老叔高铁屏投笔从戎和故土沦陷的全过程,最终由一个稚嫩的学生转变为了抗日洪流中的一名战士。用一个尚未成熟的孩子的眼光透视抗日这段宏大的历史,使得这段历史的叙述更具真实感[10]。
金生的童年视角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用高金生的视角叙述抗战历史,根本上依旧是为人物形象塑造服务。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高金生的“老叔”高铁屏,以金生的视角来连缀高铁屏的人生片断,以金生的心灵感知高铁屏的人格风范,高金生对他的精神启蒙者的依恋和追随也从侧面烘托出高铁屏的英雄形象,同时也使金生觉醒直至投入抗战的心灵成长历程更符合逻辑。其次,高金生的童年视角融汇着东北人民独有的情感意义。从一个乡村家庭的长房长孙到流亡他乡的读书人,金生的视野里容纳了东北“故乡人” 与“失乡人”全部的家园情结。以金生的童年视角去叙述故乡由安定到失守的全过程,故乡生动可感的形象得以显现。透过金生的视野,作品意在凸现东北人的那种大乡土观念,让人体会到 “安身立命的土地是乡,先人萌发的‘老根儿’是乡,后世子孙开辟的新天地也是乡。”同时,金生作为一个敏感而早熟的少年,外敌入侵给故土带来的灾难更是在他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因而金生身上托着作者赵淑敏的童年经验。对于赵淑敏而言,童年的流离失所以及对陌生故土的向往外化在高金生身上,既构成了他的性格血肉,也是作者以理性的间接经验对抗战历史的回溯。
总之,这样一种隐性童年视角的存在避免了小说叙述视角的单调,作者意在通过高金生视角下的东北人民抗战历史回溯那段不堪但热血的年代,以写实性的叙述重现历史,反映了动荡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也体现了一种时代感召和个人命运的结合。
二、叙事结构的不同
在叙事结构方面,《生死场》采用了片段化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线的叙事模式,把“抗战”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微观化,借助“生死场”上空间的变化来呈现沦陷区人民的抗争历史[11]。《松花江的浪》采用了双线叙事结构,以时间为轴,把东北人民的抗争历史和个人的人生经历结合,两条线索互为补充,呈现出史诗性的审美效果。
(一)“到都市里去”:片段式的叙事结构
《生死场》在内容方面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但《生死场》又不同于传统的抗战叙事,正如胡风对《生死场》的评价所说:“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12]200这样的评价正指出了萧红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的特点——片段式。
《生死场》描绘了不同空间之下不同人的悲惨境遇和抗战经历,叙事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没有明确的故事主线。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以线贯穿的叙事模式,以空间和场景的转换连缀小说,每一个章节都有各自的主人公和情节,不同的章节像是通过作者的情绪和个体感觉组织起来的零散的片段。
首先,从标题来看,《生死场》的章节标题都是人物的活动空间或中心意象。小说在整体上分为两个大的叙事空间,以《十年》为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军侵略之前的农村景象,第二部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农村景象,“抗战叙事”集中于第二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王婆为李青山等人掩护、金枝的出走、“爱国军”的失败。尽管《生死场》取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北沦陷区抗战前后的动乱生活,但这部小说并不是对历史的现实描述,而是萧红以自己的个体感觉串联起来的。反映抗战的这一部分叙事空间仍然十分模糊,缺少情节主线,只有通过一些特定的词句才可以捕捉到历史背景的影子。
其次,《生死场》中描写抗战的内容也以片段化的方式呈现。作者没有以常规的方式交代故事的时间脉络,而是以一条隐形的时间链条穿插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场景中。《生死场》前八章是连续的,故事开始于夏季,又结束于夏季。九至十一章叙事发生了中断,以日军的侵略为界,年轮向前拨动了十年,空间也随之发生了转换。在第16章《到都市里去》中,金枝到都市里去,人物的活动空间发生了转换,正如巴赫金所说:“在道路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有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在这里,通常被社会等级和遥远时空分隔的人可以偶然相遇;在这里,任何人物都能形成相反的对照,不同的命运会相遇一处相互交织。”[13]445小说中金枝走向都市,“被迫”选择了另外一种人生,人物的活动空间不断发生着转换,但金枝依旧逃不出反抗失败的结局,叙述者意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揭示战争给人类命运造成的悲剧。除此之外,《生死场》运用时间的断裂造成叙事的中断,来呈现其碎片化的形态。在第17章——《失败的黄色药包》中,在这一章的开始,叙述者交代了一个自发的革命军奋起抗日的场景:“他们的衣装和步伐看起来不像一个队伍,但衣服下藏着猛壮的心”。[8]163随后并没有交代战斗场景,仅凭人物的对话“听说青山他们被打散了”预示着惨败的结局,最后话锋一转,用“二里半的麻婆子被杀,罗圈腿被杀,死了两个人,村中安息两天,第三天又是要死人的日子”[8]165匆匆交代了反抗失败的事实,至于战争的进行过程、人员伤亡的程度、战争持续的时间等,叙述者统统都未提及,但读者又分明可以感受出一种悲剧性的氛围。
除此之外,叙述者在章节的分布方面也呈现出片段化的特征。在小说中,《到都市里去》和《尼姑》两章本身存在着逻辑联系,正因金枝出走,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才使她萌生了做尼姑的想法。但叙述者在这两章中间插入了《失败的黄色药包》一节,使故事主线人为地被中断。小说中叙事时间的更替同样呈现出片段化的特征,除了四季更替,时间似乎对叙事的进行没有影响。萧红对于抗战题材进行的独特处理,把“抗战”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微观化,将其缩小为大小人物在“生死场”上的生死和空间场景的变化[14]。作者叙事手法虽然还不够圆熟流畅,但小说文本仍是一个完整的自足体,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一种不事雕琢、淳朴浑厚的审美风格[15]。萧红正是借助这样一个个的空间来呈现奴隶“非人”的生存形态,表现在生死场中痛苦而又强韧的生命形态和沦陷区人民的抗争历史。
(二)背水一战的反抗:双线叙事结构
与《生死场》不同,《松花江的浪》呈现出双线的叙事结构。这部小说承续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手法,人物与环境达到了高度自然的契合,故事有序展开。这部小说的结构单纯而严谨,高铁屏的抗日历程和高金生的成长故事贯穿始终,虽然其中不乏心理世界的刻划,但对人物抗战经历的描写仍旧是作品的情节重心,这样的叙事结构也使得小说具有一种宏大的史诗性[16]。
首先,从整体上看,《松花江的浪》的叙事结构呈现出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以某一人物为塑造对象的小说往往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叙事的时间过程也是人物的生命过程,时间意识和生命观念由此得以揉合。在时间上,小说呈现出线性的特征,追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两代人的抗日史,同时,小说也是少年高金生由稚嫩到成熟的心灵成长史。同时,叙述者在线性的时间范围内选择了“除夕”这个新旧年交替的节点,而省略了一年中的其他时间节点。例如小说中反复出现“又是一年除夕”、“旧历年的最后一天到了”,在这两个相邻的时间点之间出现了间隔和空白,使得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中断。在这里,时间和空间被融合在一个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此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中。[13]274在空间上,小说中空间的转换以情节发生的逻辑为衔接,横跨了黑龙江、北京、南京、重庆等地,呼应着“流亡”的母题,展现出了东北大地抗日的宏阔场面。
其次,高铁屏的抗日经历与高金生的成长历程看似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线索,但二者在“抗日”这一主题下互相交织并行,反映着同一时代两代人抗日的艰难。高铁屏作为时代先行人,在叙事中充当高金生的启蒙者。他从东北乡村农家走出,接受了进步思想。如果说,他最初逃离东北只是求生欲望的驱使,那么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目睹祖国沦陷的全过程后,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驱使他返回东北继续抗日,小说也由此形成了一种“离去——归来”的模式,同时,依仗高铁屏的性格发展历程来展现抗日经历,使得叙事呈现出客观化的特征。高金生作为被启蒙的对象,见证了“老叔”曲折的抗日历程和自身的流亡生涯后,也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在高金生身上,时间的转变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从一个稚嫩的少年成长为求学的青年,最终成为抗日斗争中的年轻战士,这个过程的逐步展现正是通过时间的推移得以实现的。每一年的时间节点除夕夜,高金生对自身成长和家国责任的体会都会更进一步,叙述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出高金生的成长历程。
由此可见,《松花江的浪》在抗日战争这一主线之下,通过高铁屏的抗日经历和高金生的成长历程揭示了抗战的艰难。对于抗日战争,叙述者也避开了金戈铁马的场面,而是把东北大地的自然、人文景观与人物的人生经历相融合,以舒缓徐纡的笔触描绘了“浮世绘”般的风俗画卷,展现了东北人民壮烈的抗战历史,具有史诗性的审美效果。
三、表现内容的不同
同为表现“抗战叙事”,萧红与赵淑敏在表现内容上各有侧重。《生死场》表现了王婆、金枝两代女性的不同反抗方式,叙述者以女性的敏感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来透视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在表面的“抗战叙事”之下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松花江的浪》则对个体的生命进行了深度审视,叙述者选取了抗日起义军中的典型,将其置于人和社会的关系中,展示出了时代精神对个体人生的召唤。
(一)《生死场》:聚焦于女性命运
《生死场》不仅在结构方面没有明晰的情节线索,在人物设置方面同样面目模糊。正如胡风所说:“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12]200在日军入侵农村之前,“生死场”上的众多女性如同动物一样苟活度日,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奴隶,她们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愚昧的农村,不仅家畜重于亲生子女,“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8]43人的生命价值在这里被无情地扼杀,人物呈现出一种朴素的原始状态。日军入侵后,死亡开始威胁到了这种无秩序的群体人生,这种独特的时代境遇使得女性觉醒,才有了“不做亡国奴”的反抗。
在叙述东北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时,萧红弱化了男性主导下的抗战叙事,将笔墨集中于以王婆、金枝为代表的两代女性身上,塑造出北方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使得其抗战叙事更具悲壮意味。这些女性的反抗具有原始的野性,以此来回应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女性的生存危机。在战争语境下,女性不仅受到父权的压迫,更失去了自然和家园的庇护,女性的命运在这里受到了双重的压迫。
以王婆为例,在儿女双双为革命毙命后,她的民族意识终于得以觉醒,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抗日之路。在小说中,王婆作为一个挣扎于生死之间的普通妇女,为李青山召集的秘密会议站岗放哨,掩护了革命组织派来的黑胡子男人,她的反抗是自觉的。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寡妇”意指丈夫去世的女人,因此,缺乏劳动力的寡妇是牺牲得最彻底、也是被压迫得最彻底的女性。李青山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动员后,“回声先从寡妇们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8]50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以王婆为代表的寡妇们毫不犹豫地走到了抗日救亡的前线,这不仅仅是一种绝境中的反抗,更体现着她们视死如归的决心。
金枝同样拥有悲惨的命运,她起初也有过甜蜜的爱情生活,但随着嫁入夫家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一名寡妇,她不得不走出乡村,在城市中尝试谋求生存。她本以为这是一条重新找到自我和幸福的坦途,却遭到了来自父权社会的另一场暴行。在冰冷的城市中她受尽耻笑和凌辱,最后只能返回被战争毁掉的“家”,含恨遁入空门。
金枝的反抗方式不同于王婆,她采取了“娜拉式的出走”的方式独自踏入城市谋生,并发出了“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的呼号,这种“恨”推动着金枝去挣脱当下的困境,她意识到自己是以一种“他者”身份存在的,却尚未踏上寻找“自我”的存在之路。金枝渴望用走向城市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她仍未走出旧社会的藩篱;她在男性世界的压迫下苟活,却缺乏反抗的决心和勇气,她与生俱来的懦弱束缚着她反抗的脚步,在城里挣到钱以后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对自己百般苛刻的母亲。她的反抗表面上是失败的,但是从更深层次上而言,她是用自己的行动控诉了民族危机和父权对女性的压迫。
(二)《松花江的浪》:“中国人的精神”的典型揭示
在《松花江的浪》中,赵淑敏选择了与萧红截然不同的聚焦对象——即聚焦于个体生命。小说同样叙述了两代人的反抗——先行者高铁屏与后继者高金生。高铁屏是一个关心国家和人民的时代先锋的形象,他从东北乡村来到北平学习,在省城女子师范任教,他的人生经历使他更容易接受进步文化圈的信息,对时代的变化更加敏感。他从决定抗日到英勇献身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性格发展历程。他最初逃离东北只是为了谋求生存,在经历了从北平到重庆的流亡生涯,目睹祖国沦陷的全过程后,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驱使他返回东北继续抗日,从他留下的遗言可以看出,他此次返回东北是带着必死的信念归乡的。在这一次离去——归来中,他的性格得以重塑,英雄形象也得以进一步崇高化。另一方面,在旧式婚姻造成的不幸无助情感境遇的驱使下,高铁屏压抑的生命能量和情感郁积转向了社会层面的释放,因此在民族危机下,他的爱国情怀和生命意向就能自然而然地与时代发生共鸣。高铁屏投笔从戎、流亡他乡最终被捕牺牲的经历,造就了抗战背景下的时代英雄。
小说的第二主人公高金生作为一个时代后继者,受到了“老叔”高铁屏的精神感召,由一个懵懂的读书人成长为抗日新生代的主力军。日军的侵略使他也经历了流亡关外的困苦,“流亡的孩子四处无家,自觉像被日本鬼子赶得无处可去的丧家之犬”[17]。经历流亡和心上人病逝的考验后,高金生对此后身处何地再也不在乎了,他的参军可以看作是对生存的更高层次的期许。在小说的结尾,高金生最终回答了“未来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未来”尽管还是一座难以攀登的大山,但因为有先驱者点亮的烛光,所以他永远不会迷失方向。高金生在时代的“大我”中舍弃了“小我”,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他的存在也可以看作是高铁屏的精神延续。
由此可见,叙述者赵淑敏在对聚焦对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把抗日起义军看作一个整体来塑造,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将其置于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来阐述对象行动的基础和缘由,从而展示出了时代精神对人生的召唤[18]。尽管高铁屏和高金生两代人的抗战经历不同,性格也各有特色,但二者存在着精神的贯通,即作者所说的“东北精神”——“我们的先祖斩荆披棘征服了大自然,以及上代的乡人亡土不亡心永做中国人的精神”[19]。高铁屏和高金生可以称之为这种精神的具象化,通过聚焦于英雄个体,东北人民的抗日历史得以在当代重现。
结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泉源。无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抗战叙事”,还是当代台湾或大陆的新抗战文学,都在叙写抗战沧桑、认识时代全景的过程中揭示了战争中民族巨大的生存潜力和人性深度,发掘了战争与人的诸多命题。正如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兀自转侧于诡谲的时间之流里,对这段血泪战史,既未在文学上给它一个定位,更没有透过现代文学形式,创作出反映抗战精神的世界级文学作品;这应该是整个民族的憾事。”[20]萧红将目光聚焦于女性,反映了女性的个体命运和灾难;赵淑敏通过追忆历史,塑造了抗战的英雄形象,揭示了中国人的抗战精神。同时,二者基于不同的时代语境,在进行“抗战叙事”的架构时也有着各自的关注重点,呈现出不同时代下东北女作家战争书写的不同风格。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