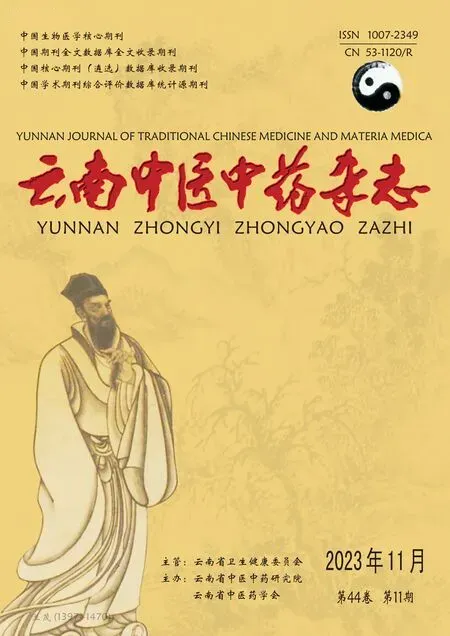浅析“升阳法”*
李荣慧,何清湖,黄海平,雷晓明,吴结枝,张国民,刘平安
(1.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5;2.湖南医药学院,河南 怀化 418000;3.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升阳法”理论基础源于《黄帝内经》,其应用发展于张仲景,至金代李东垣其理论体系与临床应用趋于完备,后世张锡纯等医家对其多有发挥。“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升阳之雏形来源于内经对于气机升降理论的认知[1],《素问·经脉别论》之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更进一步阐发升阳法的生理基础,从脏腑之气机升降角度为升阳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即脾气之升清功能,宣发水谷之精输布于上,布散周身充养机体。《伤寒论》有云:“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 太阳阳明合病之下利,仲景以葛根“起阴气”升提津液止泻利;太阴病脾胃虚寒,水饮内蕴之下利不渴,仲景用甘草干姜汤、理中丸温升中阳,温化水饮;少阴病肾阳虚寒之自利而渴,以桃花汤、真武汤温升肾阳,仲景初步将升发阳气、升提津液之法应用于方药。李东垣在其著作中言及:“春气升则万化安”;“是六腑之气,生长发散于胃土之中也”;“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2]李东垣明确提出升阳法,将脾胃升发之气与春之木气相类比,将其具体、明确化,并创制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补气汤等系类方剂,拓展升阳法之临床运用。近代医家对于升阳法亦颇有发挥,其中以民国中医泰斗张锡纯先生尤为见长。张锡纯所创之升陷汤、升麻黄芪汤皆为升发阳气之方,运用于治疗气机不升所引发的诸多病症[3]。
1 《内经》论水液之输布
《内经》注重阐述升阳法对水液代谢的作用。“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意在阐发水液经过脾气之升清输布于肺,肺气之肃降作用将水液输布于膀胱,即通过气机之升降浮沉实现水液的代谢过程。《素问·玉机真藏论》云:“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脾为土脏,脾之阳气升发有力则水液布散有度,它脏可得濡养,此为脾阳升发对水液输布的作用;《素问·逆调论》云:“肾者水藏,主津液。”水液入膀胱,经肾阳之气化作用则可蒸腾疏泄,其清者借助肾阳升发作用蒸腾于脾,浊者下输膀胱,疏泄而出,此过程与肾小球滤过、肾小管重吸收作用颇为吻合,此为肾阳对水液输布之作用。《景岳全书·肿胀》言:“凡外感毒风,邪留肌肤,则亦能忽然浮肿。”邪气阻塞肌腠,导致肺气宣发受阻,进而水液停滞,发为浮肿,此段补充了肺阳对于水液代谢的影响。
2 仲景论外感及杂病
仲景之“升阳法”以附子剂、麻桂剂、葛根剂最具代表性,以温振心肾阳气、输布水液、宣散表邪效果为多见,针对的疾病既有内伤亦含外感。如《金匮要略》中肾气丸条“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 附子性热味辛,《药类法象》谓附子“性走而不守,亦能除肾中寒甚。”《药性赋》言“其性浮而不沉,其用走而不息。”可知附子之热性可温肾阳,其辛味又可升腾肾阳。张锡纯谓桂枝“力善宣通,能升大气,降逆气,散邪气。”桂枝辛甘味温,其性偏升发散越,甘味又入中焦,故可升发脾之清气。桂枝附子合用则下焦阳气得温,脾肾之阳得升。膀胱得温则水液气化有力,阳气之升发又可助水气之输布,津液得升,则小便频数可止。《伤寒论》第32条云:“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葛根汤之下利机理在于寒邪束表,津液不升。脾气上输水谷精气的重要条件是肺气的宣发功能正常,而肺主皮毛,当寒邪束缚肌表,肺气宣发受阻,则脾气升清无力,水谷之精趋向于下,发为下利。葛根汤中葛根、麻黄则分别体现出仲景对于升阳法的运用。《本草备要》谓葛根“能鼓胃气上行,上津止渴。”《神农本草经》言其可“起阴气”,可知葛根能升发胃中津液上潮口中以止渴,其为葛根汤“升阳”之一也。《日华子本草》言麻黄“开毛孔皮肤”,桂枝又具备辛甘散越之性,二者合用则具有开泄腠理,发越表邪的作用,此为葛根汤“升阳”之二也。
3 东垣论脾胃之内伤
脾胃内伤学说为李东垣“升阳法”的应用基础[4]。“脾胃内伤,阳气升发无力,水谷精微布散失常,则诸脏腑皆失于濡养,形成内伤杂病。较能突出体现李东垣升阳法运用思维的方剂包括补中益气汤、升阳顺气汤、升阳补气汤、升阳散火汤、升阳益胃汤。具备升阳功效的药物包括黄芪、升麻、柴胡、羌活、独活、防风、白术等。《药类法象》云升麻:“若补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能补。”脾气以升清为用,胃以通降为顺,升麻善升阳明之气,助脾升胃气,进而升降相因,脾气得升,胃气得降,故云其“补脾胃”。《神农本草经》谓柴胡“主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可知柴胡具有通行之性;东垣云柴胡“能引清气而行阳道……又能引胃气上行”柴胡升发胃气的功能,结合“主治心腹”之言,可知柴胡可升提胃气上奉心系以滋养心肺之气。《日华子本草》言羌活“通利五藏”,《药类法象》谓其“治肢节疼痛,为君,通利诸节如神,手足太阳风药也。”可知羌活之功效类于麻黄,其升阳之功用亦偏向于宣透表邪。《日华子本草》云羌活治“五劳七伤,虚损冷气,”,可知羌活尚可解虚人之表,而《本草经疏》云“羌活气雄,独活气细”。可知独活之气更弱于羌活,并且《金匮要略》所附千金三黄汤言及“治中风……经日不欲饮食”,亦证明独活可以宣散脾胃虚弱“经日不欲饮食”之人表位之邪气;《药性论》云防风“益神……五劳七伤,羸损,盗汗,心烦体虚,能安神定志,匀气脉。”可知防风宣散风邪的同时兼可固护正气,而东垣更是明言其为“风药中润剂”,因此李东垣升阳诸方中多舍麻黄而取羌活、独活、防风,以此三者升阳解表。李东垣又善用白术升发阳气,散越水湿。白术升阳之功可从《神农本草经》“治风寒湿痹、死肌”之言窥测一二,风寒湿三气交感杂至,合而成痹,白术可解,说明当对表位邪气有一定的宣散作用,而《名医别录》言其“主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则明确提出白术可去除身、头、面的风邪。《药类法象》又谓白术“利腰脐间血……去诸经之湿,理胃。”更加强调白术如中焦,通利水血之能,结合《本经》、《别录》之言可知白术之功效与《素问》“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下输膀胱”的生理过程十分贴合,即白术可助脾气升清,上输津液,又可渗利水液,输于膀胱。白术通上达下之能,配合诸位升阳药物可以更好的输布津液,宣散、发越水饮。黄芪升提津气,补益肺气。《名医别录》谓黄芪“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止渴,腹痛泄利,益气,利阴气。”津液得升则止渴,亦是“利阴气”之能的体现,肺与大肠相表里,黄芪升提津液入肺,固护肺气以摄大肠之气故可止“腹痛泄利”。
4 寿甫论多脏之升发
张锡纯将升阳之法论述于诸多脏腑之中。张锡纯云:“盖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芽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升阳法直接体现于对胸中大气的升提,《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升陷类方、升降汤、升麻黄芪汤、集中反应其对于升阳法的运用。张锡纯认为胸中大气即宗气之别称[5],并提出大气下陷可由劳力过度、中气虚乏、外感六淫导致。如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言:“力小任重,或枵腹力作……或服破气药太过,或气分虚极自下陷,种种病因不同……外感证亦有之。”由此可知张锡纯强调大气下陷的原因更偏向于肺脾气虚,升清无力和邪气外束,肺气失宣两大类。张锡纯所创升陷汤所治主症为肺脾气虚,清阳不升所致的“气短不足以息”,其兼症包括肺气怠惰,卫气失和所致的“寒热往来”、脾气不升,津不上承所致的“咽干作渴”、脾气不升,心系失养所致的“满闷怔忡”以及“神昏健忘”,升陷汤之脉象为“沉迟微弱,关前尤甚”为中焦之气升提无力,上交心肺失于供养之象。通过分析可知,升陷汤中升阳之药包括黄芪、柴胡、升麻、桔梗,回阳升陷汤以黄芪、干姜升阳;理郁升陷汤以黄芪、桂枝、柴胡升阳;醒脾升陷汤以黄芪、白术、炙甘草、桑寄生、续断升阳;升降汤以黄芪、白术、桂枝、厚朴、川芎升阳,而培脾舒肝汤则运用生麦芽升阳。可知张锡纯所用升阳之药物,除了黄芪、柴胡、升麻、白术、川芎等李东垣善用的药物外,还以干姜、桑寄生、续断、麦芽作为作为升阳之品。对于厚朴张锡纯赞同叶香岩“多用则破气,少用则通阳”之言,并认为厚朴力不但下行,又能上升外达,可除在表之风寒,可通脾胃之阳,又善宣发肺气。张锡纯认为桑寄生善于补胸中大气而续断与黄芪同用可升补肝气,麦芽为补益脾胃之品,又为谷物之萌芽,与肝同气相求,生用可舒发肝气。张锡纯喜用桔梗引清气上注于胸中以供养心肺,指出:“桔梗为药中之舟楫,能载诸药之力上达胸中” “能引诸药入肺”。张锡纯亦认为桔梗可升提肾中真阴上济浮游之火以解肺脏咽喉处的火热之证[6]。张锡纯重视肝胆气机之升发,并常常将肝胆并称,认为相火寄存于肝胆[7]。柴胡善升提肝胃之气,而麦芽通过疏解肝气,使肝气自然升发而不碍胃气下行。升麻升提气分,兼升血分,茵陈升提之力逊于柴胡,且有宣散少阳郁热之效,适合不耐柴胡升提夹杂火热者。川芎为升提气分之品,善升提气分入脑窍,使脑中热浊之气下降[8]。
5 “升阳法”之当代研究
当代医家对于升阳法的运用。黄智斌等[9]认为岭南地区气候湿气显著,湿邪犯及肺脾则导致阳气不升、不畅,“阳气不能生长”是岭南湿病的核心病机。刘明认[10]为湿邪困脾,阳气升发无力,浊邪下陷导致下肢血脉不畅为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的重要发病机制,并提出益气升阳配合利水渗湿、活血化瘀的治疗思路。谢建谋等[11]依据《脾胃论》中“脾之精气旺,则目能明;脾胃升降正常,则目能视”的理论,总结出“益气升阳”针法治疗眼睑下垂。谢佳芯等[12]认为小儿慢性唇炎的关键病机为阳气不升引发的津液输布失常以及火热内郁攻冲于上,并擅以诸升阳散火之风药对治本病。刘光伟教授[13]擅用温升肝气、助脾升清、温煦肾水之法对治临床中的肝郁证。谢强教授[14]以益气升阳,散寒通窍之法治疗变应性鼻炎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董奇等[15]学者提出运用风药升发宣通气机,调畅玄府以恢复气血津液的输布流转对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治疗具有积极效果。郑冬雪[16]发现临床中部分内有郁热的妇科患者,多存在火热炎上,下失温煦的表现,其运用升阳散火汤对治此类患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雷玉凤等[17]通过实验发现补中益气汤可增强心脏收缩力,增强心功能,使心衰症状得以缓解甚至好转,并认为柴胡、升麻是起效的关键药物。毕珺辉等[18]学者通过实验发现升阳益胃汤可能通过降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模型大鼠结肠及下丘脑组织中5-HT的含量来改善大鼠体质量变化率,改善腹泻症状,降低内脏敏感性,保护大鼠结肠黏膜形态。李玲玲等[19]的研究显示升阳散火汤可以通过保护骨骼肌及其线粒体膜结构的稳定性,提高慢性疲劳小鼠的抗疲劳能力,且效果优于单独补虚及升阳散郁疗法。郦芳等[20]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治疗,益气升阳愈疡汤联合康复新液的疗效要优于单药康复新液,可明显缩短治疗周期,降低溃疡的复发率。杨丹华等[21]的研究表明升阳举陷法艾灸对于肾阳虚型压力性尿失禁老年女性患者的1 h尿垫试验漏尿量以及日均尿失禁次数有较为明显的降低作用。彭丽丽等[22]发现与单纯运用四联疗法相比,四联疗法联合升阳益胃汤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胃癌前病变,更能降低CRP及肿瘤标记物水平,并提高幽门螺杆菌根除率,更利于胃黏膜病变的延缓。
6 小结
纵观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锡纯对于升阳法的论述,升阳法不拘泥于某一方药,重在理法的运用,其功在于振奋阳气、布散津液、宣通水道、驱逐邪气。仲景将升阳法运用于寒邪束表之外感、津不上承及下元虚寒之杂病,所选升阳之品性味及功效较为迅捷;东垣用升阳法所对治的疾病以脾胃虚弱,内伤杂病为主,因此所用升阳之药物性味相对平和,药效相对缓和,且用量亦偏轻灵;张锡纯将升阳法应用于脾、胃、肝、心、肺等脏腑,进一步拓展了升阳法之应用,所选用的升阳药物亦有所增多。后世医家将“升阳法”应用于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等多方面的疾病,通过现代科学基础研究进一步证实升阳法的多方面效用机制,为升阳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