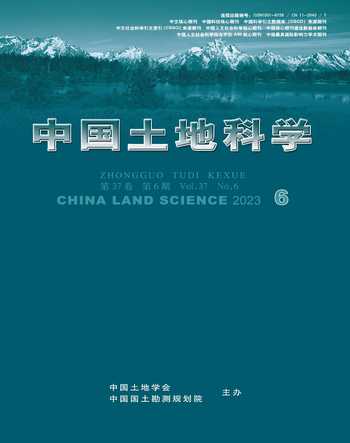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制度的立法指向与规范构造
摘要:研究目的:探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制度的应然目的,并厘清准成员的群体定位、认定规范与权利构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准成员制度不是集体基本保障功能的延伸,而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引入”、助力农村地权制度科学化的功能制度。准成员群体定位不应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16条所局限,而宜以非集体成员中的产业农民与乡土成员群体为核心;其认定规范宜构造为逐级具象的多层次规范体系,且应设置准成员登记簿与权利附注规范。在准成员权利构造上,不仅应排除集体成员专属的土地权利,还应排除所有以集体地权为基础之收益的分配权;结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指引,宜赋予准成员有偿取得附期限与义务之新型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研究结论:创设准成员制度可使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更加周延,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不足,立法应予完善。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乡村振兴;认定规范;权利构造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1-8158(2023)06-0012-08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重大科研项目“湖南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实现机制创新研究”(ZFCG2022068004)。
2022年12月30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以征求意见。据中国人大网显示,建议总数达23 333条,除影响同样甚广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外,同时征求意见的其他法律多只有数百条建议,可见该法的重要性和关注程度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集体土地公有制的核心,其承载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简称“集体成员”)的基本保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其立法安排关乎农村及其几亿居民的未来,不可谓不重要[1]。
以往的集体经济组织视域中,只有集体成员与非成员的二分法,个人要么可享有一揽子成员权利,要么完全被隔离在集体经济组织外。基于二分法的制度设计,是集体基本保障功能的演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集体成员的核心利益,但也产生了多种不良反应。如“空心化”背景下,集体成员资格封闭性与乡村振兴所需人员开放性的矛盾[2-3];成员身份或土地权利变动时,地权专属、“一户一宅”等管制规范与民事规范存在的冲突。这些问题又与宅基地“三权分置”等农村改革深度交织[4],造成改革的困顿。本次《草案》第16条独创性设计了准成员制度——不是集体成员也可享有部分成员权利的制度②。相比于集体成员认定规则的争执不休[1,5],准成员制度似乎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焦点核心,但这种设计却为集体成员认定标准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争议打开了一条新通道,为解决争议背后的乡村振兴“人才困惑”提供了新途径。准成员的设计在准入端和权利端“适度放开”,从而人员加入可有序实现,“一揽子权利”可按需分拆,在保障农村稳定与集体成员核心利益前提下,农村发展的实践需求得以满足。不仅如此,三分法的设计使农村融入了新的主体,协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可“拆除”二分法下成员身份与农村地权完全捆绑的架构,使成员身份回归基本保障功能演绎下的宅基地权利,不附基本保障的宅基地实现“适度放活”。新规则体系下,地权管制与民事规范之冲突可实现调和,宅基地改革目标亦在此基础上促成。
笔者拟剖析《草案》第16条设计的准成员制度,厘清该制度立法的应然指向,探析准成员的群体定位与认定规范,并就《草案》构造的准成员权利内容提出改进方案,供学界及立法者参考,以期助益立法的更好展开。
1 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制度的立法指向
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其存在的依据,也是立法具体展开的指导。准成员制度设计是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目标的实践展开,也是其功能体系的制度要件。这就要求探究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目标,以及准成员制度在其中的体系定位。明晰“齿轮”所在,才有《草案》第16条立法功过的评判标准,才能为制度设计的修缮提供依据。
1.1 准成员制度不是农村集体基本保障功能的延伸
诚如《草案》第1条首句所指,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所谓成员合法权益的根本,便是《草案》第12条陈明的以集体土地为支撑的“基本生活保障”。无论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前身——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其组织的第一功能都是为集体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6]。
原则上,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要么为该功能的一部分,要么为该功能所服务。成员制度是基本保障制度体系中的枢纽,集体成员认定规则之所以争议不断,就是因为该规则是核心功能的核心。在《草案》之前,无论是《民法典》集体土地的物权体系规范中,还是《土地管理法》的集体土地规范中,只有集体成员这个概念,并无准成员概念,更无配套的制度。法律体系将自然人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区分为两种,即成员—集体经济组织、非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法律规范的展开围绕三种主体建构,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成员。《草案》打破了这种设计理念,三主体转变为了四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准成员—非成员。
成员与非成员的区分是为了保护成员的核心利益,服务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保障功能。有学者将非基本保障范围的“自治性成员”纳入集体成员体系[7],本质上就是对该集体功能的认识偏差。为何《草案》第16条从“非成员”中提取特定群体,构造准成员制度呢?这是基本保障制度覆盖的范围扩大,抑或其他呢?从《草案》第16条看,立法者关注的特定人群是本地长期工作、生活且对集体有贡献的群体,赋予该群体部分成员权利,也是提供该群体一定的权益保障,这是否理所应当也是基本保障职能的制度延伸呢?
結合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设计看,准成员制度并不属于该组织基本保障功能的延伸。作为特别法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其特别之处在于拥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并以所有权上的用益物权承载集体成员的基本保障。而基本保障功能的覆盖群体,一直也只有集体成员。无论是《草案》第11条所述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还是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其所指均是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权利关系。基本生活保障是集体经济组织对成员的公法义务,而这种公法义务也限定在集体成员之内。成员制度与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深度绑定,绑定的动力因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反言之,这种制度绑定建构了保障功能的实现形式。准成员虽然享有部分成员权利,但《草案》第16条的但书规定,排除了成员的专属地权及其衍生利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分配土地补偿费。申言之,基本保障功能的覆盖仍是以成员为核心,准成员被排除在外,因而该制度并非是基本保障功能的延伸,其存在应另有它意。
1.2 准成员制度的功能应定位于乡村振兴戰略的“人才引入”
无论是成员还是准成员,都指向于人。如果说成员是集体经济组织要“保护”的人,那准成员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所“需要”的人。《草案》第1条为集体经济组织设定的功能,不仅有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支撑保障水平的“乡村全面振兴”。集体成员的范围具有封闭性,“空心化”更是加剧了这种封闭性[8],但乡村振兴事业,无论是经济产业还是人才培养、文化传承,无疑离不开更多的人[2]。吸引更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的要求,更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直接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9]。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8条明确提出,政府“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集体经济组织应为各类人才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经济基础是事业发展的根基,乡村事业发展虽然也需要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等支持,但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吸引,更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保障[10-11]。纵令如此,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以参与乡村振兴,为何一定要构造准成员制度呢?“稳慎”的改革思想无疑是其设计的重要诱因。无论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还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央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稳慎推进”,完全市场化从来都不是农村制度改革的手段①。保持农村的稳定发展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寻找”稳定式策动乡村振兴的群体,而不是将农村资源完全市场化的主体[12]。集体成员资格的强封闭性,注定成员制度不可能为该群体“大开绿灯”。从非成员中“圈出”这一类群体并赋予其新身份,便是准成员制度存在的重要缘由。
申言之,准成员制度的目标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而制度的着力点是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嵌入“合适的人”。具体而言,该制度的应然定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引入”:引入不具有成员资格,但属于“稳慎推进”模式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即有学人论及的农村应然之“新鲜血液”[13]。这种制度设计没有挤占集体成员的核心利益,反助益了集体成员利益的增长,促进了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的更好发展。
1.3 准成员制度还应有协同地权改革助力规范科学化之功能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典》等法律,将集体地权设计在一个较为独特的法律空间,相较于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上有更多的国家管制。管制规范与民事规范的结合地带常常伴有龃龉,静态的管制规范设计困不住动态的成员变动和权利变动,龃龉表现即管制规范部分失效,背后的深层原因则在于集体成员权利制度与民事规范之间并不匹配。
首先,集体成员的身份变动会为管制规范制造“麻烦”。制度设计中,集体土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均为集体成员所在农户家庭专属。虽然专属地权与成员身份深度绑定,但当身份发生变动时,这些专属地权并不会产生相应变化。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与《土地管理法》第62条,集体成员进城落户而身份变动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或退出均是以自愿有偿为原则,并不会带来“关联效应”。成员身份变动的结果——非集体成员享有了成员专属地权——在事实上瓦解了地权的专属性管制。不同于有期限和继承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可继承且“无偿、无期限限制的特殊用益物权”[4],其“后遗症”更加凸显。
其次,专属地权的继承也会造成管制规范的失效。依《土地管理法》第62条,“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已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成员,便不能获得其他宅基地使用权。当宅基地上的房屋发生继承时,依据房地一体原则[14],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共同发生转移,若继承人属于本集体成员,则其可能突破“一户一宅”的限制;若不属于,则宅基地使用权又转移至非集体成员处。《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第10.3.5条业以说明,继承行为可以突破“一户一宅”与成员专属的管制规范。虽然自然资源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中也明确表明,城镇户籍的子女可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并进行不动产登记,只是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但这种逻辑并未获得法理与学界的认同[4],毕竟这些权利附带着基本住房保障功能,并不视同一般财产权。管制规范设计围绕基本保障功能所构造,无论是集体成员的第二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城镇居民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突破管制规范也就背离了基本保障功能设计。实践中的操作,并不能解决法理逻辑的问题。
综合来看,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成员专属的土地权利与民事财产性权利的转化通道不明。一者,成员到非成员的变动或专属地权的非成员继承,本质上都是权利人去除基本保障人格,本应伴随着原人格化财产的性质变动,然而宅基地缺乏不附带基本保障的权利状态设计,专属权利到非专属财产权利的过渡无法顺利实现[15];二者,超出规范管制的宅基地权利不属于基本保障范围,但也因宅基地使用权形态的单一而无法转化。成员制度与土地制度设计并未考虑到这些情况。制度设计的缺陷带来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16],催生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然而,较承包地改革不同,宅基地“三权分置”指向“适度放活”,这表明不是所有非成员都能成为宅基地权利主体。故而,解决该规范冲突问题不仅需要适宜的“权利新形态”,还需要满足“适度”标准的“新人格身份”——不同于成员与非成员的新主体资格。作为《草案》的创新设计,准成员定位于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一类群体,天然有着两者身份之间的过渡性质。也因此,准成员立法还肩负另一功能:协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以合理的制度设计调和管制规范与民事规范的矛盾,弥合成员—非成员二分法留下的学理裂缝,使之科学化。
2 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的群体定位与认定规范
立法指向是准成员制度设计的“目的因”,目标决定了准成员制度的演绎方向。该制度的构造存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准成员的资格制度——准成员的群体定位及其认定的实体与程序规范,二是准成员的权利制度——复数的准成员权利应包含哪些内容。群体定位为准成员认定划定了原则方向,具体到认定规范时还应注意,规范设计既要考虑适应各地不同情况,也要保准原则的不偏离,还要以科学的程序规范实现认定之主体及其权利的公示。
2.1 准成员范围宜以产业农民与乡土成员为核心定位
准成员的认定范围,《草案》第16条设置了三个并列标准:在本地长期工作生活,对集体有贡献,经过成员大会四分之三的人同意。该标准分别在地理维度、价值维度与稳定性维度上圈定了准成员的范围。设计思路上,地理维度突破了户籍地限制,以工作、居住为标准;价值维度突出“过去”对乡村振兴的贡献;稳定性维度则以同意程序为要件,设定农村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前提——稳定。
《草案》第16条的准成员群体定位有偏差,立法设计没有呼应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在制度导向上,准成员制度更应关注谁“现在和将来”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8条的人才振兴理念是“鼓励、支持与引导”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因此价值维度的设计是存疑的。地理维度设计的前思考,则是将“长期工作居住在此”、“服务乡村振兴群体”与“准成员权利需求”三者深度绑定,这种理念无疑也存在较大误区。
科学而言,准成员的群体定位应该遵循人才的供应与需求规律。这就要追问农村集体有何种资源可以吸引人才,而哪些群体会在遵循农村稳定理念的基础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财产是土地,农村产业主要集中于涉农产业,因此以集体的农地资源吸引合适的产业农民加入,振兴集体农产业经济,符合准成员制度的设计。《草案》第16条列出在本地长期工作的群体,就是主要对应产业农民的身份通道。
除了农地资源之外,农村集体最有吸引力的资源供给,便是其天然附带的乡土文化。这种人文与地理的互动产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也是准成员群体定位的重要指引。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生长于本乡本土或者与本地有亲缘关系的人员群体,即便在经济与地理上已脱离乡土,但乡土文化已成为其人文主义情怀的一部分[17]。这凝聚了一个特殊群体,即具有本地乡土文化人格属性的成员(以下简称乡土成员)群体。以乡土文化衍生的“衣锦还乡” “落叶归根”等恋地情节,催生了乡土成员助力本地发展的无形动力。其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就提出过“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①,相关部门也出台了政策实施支持意见[18]。诚如学者所言,这类群体是“现代乡村社会资本的‘人化凝聚,也是汇集乡村振兴强大合力的重要媒介”[19]。同时,相同习俗、传统等文化内核使该群体易于获得集体成员的认同,被视为“本地人”[20],这也正契合了农村改革发展的“稳慎”思想。囿于集体成员与非成员的二分法,脱离集体的乡土成员与乡村失去了有形的连接,而准成员制度能够重建这种连接,强化乡土成员的故土情节,创造集体的归属感。准成员制度定位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服务,乡土成员无疑应是准成员群体定位的另一核心。
2.2 准成员认定宜构造逐层具象的多层次规范
准成员群体定位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规范主张,但原则走向规范实践需要更加具象化,以切合各地的实践形态。规范过于严格,各地发展情况不一而致,则难以适应各地不同的实践需求;规范过于宽泛,则又难以达到规制的效果。因此,准成员认定不可能在法律层面将之规范过细。
本质而言,准成员制度是为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一条可选路径,而非必选项。文化背景、地域位置、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都会造就准成员认定标准的不同,如乡土成员这一原则性范围,在各地表现的形态参差不一。地区文化不同,对于何者属于乡土成员范畴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涉及到如何构建乡土成员判别的实践标准。针对该问题,法律不应直接圈定范围,宜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逐级具象,最后具体到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确定何者适宜。应予指出的是,通过继承获得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非集体成员,理应作为准成员。一则,这类群体本就与集体成员存在亲缘关系,具有乡土性;二则,将之纳入准成员范畴,可以协助解决法规范体系内部的龃龉。
其實《草案》第16条的规范形式也是如此,无论是工作生活的“长期”,还是对集体的“贡献”,都不是确定而具体的标准,而只是原则性规范,这是农村改革中“基层探索—充分试点—顶层设计—因地制宜”[21]原则的实践运用。这种成员认定的规范方法,系以法律构造原则,而以原则的张力适应各地不同情形。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性质保证了原则的无偏演绎。集体经济组织属特别法人,其章程本非完全自治的团体纲领文件[22],而是要经过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最后到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备案①。这些审核、备案程序承担了准成员认定标准的合法性审查,保障了逐层具象的规范体系末异但本同[23]。当然,规范体系的建构仍应在法律框架之内运行。结合乡土成员的血缘普遍性,《草案》第16条的认定规则,除同意规则外,可修改为“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长期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工作、生活,或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直系亲属或继承人,或依据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与本集体有其他重要关联,且能为本地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
2.3 准成员认定应设置准成员登记簿与权利附注规范
相比集体成员认定,准成员认定的程序要件设计明显不足。准成员享有部分成员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缺乏公示手段则难以形成对内对外效力。而且,准成员是一个复数群体,群体内不一定人人都享有标准的准成员权利,“部分成员权利”意蕴“不同准成员可能享有不同部分的权利”。
《草案》第16条仅仅设计了准成员的同意程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通过,并未设计任何公示手段。虽然第16条排除了准成员享有专属地权的资格,但权利内容仍极为宽泛,如第13条第1项、第4项的权利,会影响到其他成员权利,也可能会产生对外的效力问题。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准成员应如集体成员一般构建公示制度。公示形成的效用,类同于不动产登记的对抗效力[24],既有准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及第三人的权利对抗力,也有集体经济组织对准成员义务的约束力。参照集体成员公示方法构建准成员登记簿,可达公示之作用。
此外,登记簿还应设置权利附注。准成员的权利并非单数权利,而是复数的权利集合体。而且,准成员的群体并不是单一的,可以享有的权利不一定赋予所有准成员。换言之,同一集体内不同准成员可能享有不同权利,不同集体准成员的权利设置也不一定一致。因此,除了要编制登记簿,还应设置权利附注以载明其具体权利。当然,这种权利配置以准成员类型区分更为便捷。实际上,集体经济组织本就伴有公法职能,设置准成员登记簿与权利附注也有利于行政机关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因此,《草案》第16条可单列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编制本条第一款规定人员的登记簿,登记簿应包含权利附注。”
3 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的权利构造
《草案》第16条的设计,将成员权利区分为准成员可享与不可享两部分,避免侵犯集体成员的专属权益,这属于准成员权利的一般构造。该二分结构的权利设计理念并无问题,但不可享部分的外延定位存在弊漏,准成员仍存在分享专属利益的空间,该立法设计应有所调整。权利的一般构造是原则性的建构,第16条的立法设计也限于此。然而,从立法指向看,准成员制度还应有协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助力地权制度科学化的功能,准成员权利构造的立法不应限于此,权利设计还应有围绕宅基地问题的特殊构造。
3.1 一般构造:准成员权利应完全剥离集体成员专属地权及核心利益
《草案》第13条罗列了成员权利的内容,第16条将该内容分为两部分:以第13条第5、6、8项为成员专属权利,以第13条其他项为非专属权利。专属权利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土地征收征用时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将成员核心利益排除在准成员权利之外,以保护集体成员利益,这种理念契合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功能定位,但理念到规范的转化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征收征用时成员专属利益仅考虑土地补偿费过于狭隘。目前来看,按照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计算方法,似乎只要控制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便可基本保证成员专属利益[25]。实则这种看法不仅与实践有违,而且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虽然征收补偿的计算项目不会改变,但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分配却是各地有别。如安置补助费本属成员专属利益,但并不会全部发放予成员,存在一定的集体经济组织保留部分①,这会造成准成员可能变相参与土地征收的补助分配。诚然,征收时这类费用本就属专用,该问题属于地方实践可能带来的衍生问题,更宜通过补正地方实施办法以避免,但该问题应予强调。
第二,成员专属利益应是集体土地产生的全部收益,而不应仅限于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时的补偿。易言之,《草案》并没有考虑其他利用方式下集体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如集体流转非承包地(如“四荒地”)的收入,亦应是成员专属利益。随着农村“三块地”的改革,这种收入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是位于城市周边的)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如果不厘清该种利益的归属,将来会引发更多的纠纷[26]。依法理而言,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构成集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这类集体地权的衍生收入仍应属于成员专属的地权收益,准成员不应参与分配。
申言之,对于准成员的权利一般构造,《草案》第16条排除第13条第5、6、8项规定是不够的,规定的不周延将会破坏设计理念的实现,其还应附加兜底性规定:以集体经济组织地权所获收益,准成员均不能参与分配。具体而言,《草案》第16条应将不可享权益的但书规定修改为“但是不得享有本法第13条第5、6、8项规定的权益或参与分配土地出让、出租、入股等产生的集体土地收益”。
3.2 特殊构造:准成员权利宜构造有偿且附期限与义务的宅基地使用权
于特殊构造而言,准成员的权利设计还应思考,如何契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使之制度体系科学化。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症结在哪,准成员又应在其中解决何种问题呢?农地“三权分置”的思路是在保障农户承包經营权的基础上,以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7]。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虽已提数年,但却并未如农地改革般顺遂,仍处于探索阶段②。关键问题便在于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指向不是完全市场化,而是“适度放活”,“适度”是范围的问题,而“放活”是方式的问题,“放活”可通过权利构造解决,但“适度”却不是。应该说,直到《草案》的准成员构想,才配出了“适度”的药方。“适度”的本质是“稳慎”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思想,准成员也正因为符合了“稳”,才可以成为“适度”的答案。《草案》第16条设计的“同意程序”体现着“稳”,而准成员定位于乡村振兴中的“人”,无论是产业农民还是乡土成员,其实也均有“保稳”的基因。因此,准成员制度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划定了“适度”的范畴,也就是为可“放活”的宅基地权利“找到了”合适的主体。
那准成员又应配置何种性质的宅基地权利呢?有学者主张宅基地照搬农地“三权分置”的构造[28-29],也即是将该权利设计为次级用益物权,但其并不可行。一者,部分宅基地上附基本保障,若设立次级用益物权便会失去保障作用,故而“放活”的范围只能是非保障型宅基地,而这类宅基地上无须构造多层物权。二者,从宅基地“三权分置”构造看,资格权更倾向于是一种公法债权,“分置”之使用权设计则只能是用益物权。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草案》第13条表述为“申请取得”;关于该权利的法定重新取得,《民法典》第364条为“重新分配”,《土地管理法》第62条为“再申请”。可见,“三权分置”表达的资格权内涵是:集体成员有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分配”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30-31];请求集体经济组织为特定行为的权利,性质应为债权——因其系《土地管理法》第62条“户有所居”之公法义务衍生,可称为公法债权[32-33]。肇因宅基地存量等客观原因,集体经济组织无法履行该公法义务,实践中资格权可转化为其他实现形式[31,34]。“三权分置”分离资格权的重要意义在于,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仍为用益物权,但因资格权而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与其他方式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可形成不同的构造,从而可科学应对不同的情形。
准成员的宅基地使用权又应有何种特征构造呢?不同于集体成员,准成员不是基本保障覆盖群体不能取得资格权,若要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应以有偿的方式,且该权利应附带期限与义务。在体系上,新宅基地使用权区分为两类,类似于划拨与出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是“划拨类”绑定在资格权上,而不再是成员身份。如成员的“一户多宅”情形,因资格权取得的“一宅”为无期限宅基地使用权,其他则应转为期限型宅基地使用权[4]。此外,准成员的宅基地使用权构造还应附带一定义务,如集体经济组织集资修建基础设施,相关准成员则应履行集资的义务。这种设计在“稳慎”中实现了宅基地“适度放活”与制度科学化,契合了宅基地改革的多元价值逻辑[35],而且也有利于准成员制度的第一功能实现。结合《草案》第16条的立法结构,可在第一款之后增列一款:“符合前款规定的个人,可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但应附带使用期限并履行相应义务。”
4 结语
集体成员与非成员的二分法,造就了立法图景与事实之间的偏差,也让刚性的规范制造了乡村振兴的地权、人才壁垒。准成员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上的重大突破,这为解决乡村振兴中“人”的问题、农村地权的管制规范与民事规范龃龉问题,提供了制度利器。但《草案》第16条的设计,对准成员制度的目标认识不足,在准成员的群体定位、认定规范与权利构造上还有待调整。既要结合《土地管理法》《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也要结合“三权分置”等中央农村政策指引,才能够构建兼具事理与法理的制度规范,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科学立法。应予提醒的是,乡村振兴是有序发展乡村的战略,并不拒绝非农村居民的进入,特别是存在人口“空心化”的农村。制度设计的要领在于:确守农村稳定,实现有序发展。对本乡本土有恋土情節的乡土成员,有着先天的文化亲近性,无疑应成为制度设计重点考虑的振兴乡村群体,而这一直是立法有所忽略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何宝玉.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内涵与成员确认[J] . 法律适用,2021(10):9 - 21.
[2] 蒲实, 孙文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J] . 中国行政管理,2018(11):90 - 93.
[3] 杨一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J] . 中国农村观察,2015(5):11 - 18,30.
[4] 宋志红.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宅基地权利制度重构[J] . 法学研究,2019,41(3):73 - 92.
[5] 秦静云. 农村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标准研究[J] . 河北法学,2020,38(7):159 - 176.
[6] 陈锡文, 罗丹, 张征. 中国农村改革4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1 - 93.
[7] 肖新喜.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标准[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6):51 - 58.
[8] 宇林军, 孙大帅, 张定祥, 等. 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J] . 地理科学,2016,36(7):1043 - 1049.
[9] 肖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属性的再思考——以《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中心[J] .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6):126 - 133.
[10] 房绍坤, 袁晓燕. 关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几点思考[J]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1):70 - 81.
[11] 何宝玉.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思考[J] . 法律适用,2023(1):95 - 105.
[12] 黄少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J] . 经济研究,2018,53(12):4 - 19.
[13] 戴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制度研究[J] . 法商研究,2016,33(6):83 - 94.
[14] 孙宪忠, 朱广新. 民法典评注·物权编(第3册)[M]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184 - 187.
[15] 陈小君. 宅基地使用权的制度困局与破解之维[J] . 法学研究,2019,41(3):48 - 72.
[16] 耿卓.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本遵循及其贯彻[J] .法学杂志,2019,40(4):34 - 44.
[17] 段义孚.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M] .宋秀葵, 陈金凤,张盼盼,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68.
[18] 黄爱教. 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J] . 理论月刊,2019(1):78 - 84.
[19] 徐学庆. 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 . 中州学刊,2021(6):67 - 71.
[20] 段义孚. 恋地情结[M] . 志丞, 刘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92.
[21] 高鸣, 郑庆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改革进展与深化方向[J] . 改革,2022(6):38 - 50.
[22] 赵新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认定[J] . 农业经济问题,2018(7):57 - 69.
[23] 屈茂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J] . 政法论坛,2018,36(2):28 - 40.
[24] 程啸. 不动产登记法研究[M] . 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7 - 15.
[25] 阎巍. 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的影响[J] . 法律适用,2022(7):89 - 98.
[26] 吴昭军.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试点总结与制度设计[J] . 法学杂志,2019,40(4):45 - 56.
[27] 孙宪忠. 推进农地三权分置经营模式的立法研究[J] . 中国社会科学,2016(7):145 - 163,208 - 209.
[28] 刘国栋. 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中农户资格权的法律表达[J] .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37(1):192 - 200.
[29] 席志国. 民法典编纂视域中宅基地“三权分置”探究[J] .行政管理改革,2018(4):45 - 50.
[30] 管洪彦.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与立法表达[J] .政法论丛,2021(3):149 - 160.
[31] 宋志红. 宅基地资格权:内涵、实践探索与制度构建[J] .法学评论,2021,39(1):78 - 93.
[32] 吴俊廷. 乡土文化视角下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建构[J] .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2(2):102 - 118.
[33] 吴珏. 论公法债权[J] .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5):27 - 32.
[34] 吴宇哲, 沈欣言.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设置的内在逻辑与实现形式探索[J] . 中国土地科学,2022,36(8):35 - 42.
[35] 孙晓勇. 宅基地改革:制度逻辑、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J] . 管理世界,2023,39(1):116 - 127,137.
Legislative Direction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of the Semi-membership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mments on Article 16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Law (Draft)
WU Junting
(Law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esirable purpose of the semi-membership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clarify the group positioning, norms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ights of the semi-member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norm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i-membership system is not an extension of the basic protection function of the collective, but a functional system that serves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introducing talent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scientific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rights system. The group of semi-members should not be limited by the Article 16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Law (Draft), but should focus on the industrial farmers and rural members without collective membership status. The norm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mi-members should be structured into a multi-level normative system with hierarchical concreteness, and contain a registration of semi-members with a statement of rights.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emimembers rights, the exclusive land rights of collective members and the right to distribution of all proceeds based on collective land rights should be excluded. Combined with the guidelines on the tripartite entitlement sys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he semi-members should be granted with the qualification to obtain the right to use rural land as a residential plot with duration and obligations in return. It concludes that the creation of an semi-membership system can make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ystem more comprehensive, but the scientific design of the system is insufficient and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legislation.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emi-memb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identification of norms; rights structure
(本文責编:仲济香)
①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自2021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表述一直采用“稳慎推进”。“稳慎”思想隐含着农村集体的开放不是无序的,而是只能有序引入适合本地发展的人。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第48条。
① 参见《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第8条规定之情形。
②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