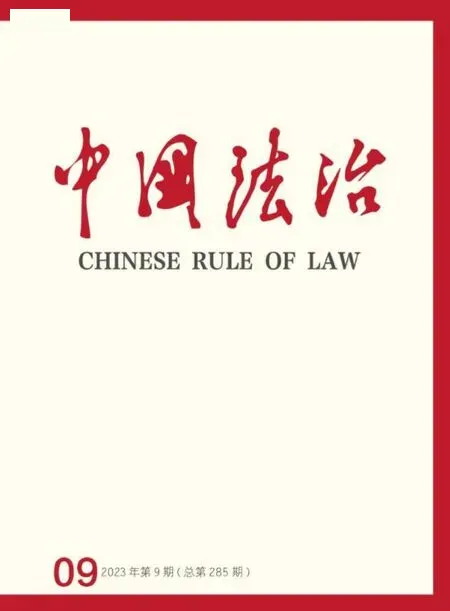浅议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喻 中(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教授)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按照这个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千头万绪中,有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环节应当先行予以建构,那就是关于法学自身的法学知识或法学理论。
在史学学科,就有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环节。按照正式制度,史学包含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样一个独立的史学二级学科。根据刘家和教授的看法,“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是对史学的反思,这是二者的相同点。不同点在于,史学理论是对史学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史学史是对史学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和反思。先有了史学,然后有史学史,史学理论的反思要比史学史的反思层次更高一些。但这两者是不可分的。”①张越、何佳岭:《史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比较史学——访刘家和教授》,《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正是因为两者不可分,才把两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单独的二级学科。
以史学为镜映照法学,可以看到,在法学学科体系中,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堪与史学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相对应的、独立的、制度化的法学二级学科。在法学界,关于“法学史”的研究已经受到重视。“法学史”大体上可以对应于“史学史”。譬如,我们可以读到以“中国史学史”冠名的论著,也可以读到以“中国法学史”冠名的论著。但是,“法学史”并不是一个制度化的法学分支学科。就中国法学学科体系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学史”的研究者主要是在“法律史”这个法学二级学科内耕耘的学者,这就是说,主要是法律史学者或法律史家在研究“法学史”。
如前所述,在史学领域,“史学史”是与“史学理论”共同组成了一个二级学科。如果说,与“史学史”相对应的“法学史”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与“史学理论”相对应的法学分支,在法学领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面对这样的追问,人们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法学理论”,似乎法学领域中的“法学理论”,就可以很好地对应于史学领域中的“史学理论”。
其实不然。“法学理论”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意义,并不能等同于“史学理论”在史学学科体系中的意义。因为,在史学领域,注意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史学理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史学”,“史学理论”是围绕着“史学”而形成的理论,按照前引刘家和教授之见,是从理论的角度反思“史学”而形成的理论。相比之下,法学领域内的“法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化的法学二级学科,虽然曾经被称为“法学基础理论”,但它更加通行的名称是“法理学”,顾名思义,它主要研究“法之理”,而不是“法学之理”。这就是说,“法学理论”或“法理学”,本质上是关于“法”的基础理论,而不是关于“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
譬如,在现有的法理学的知识体系中,主要研究法的概念、法的历史、法的价值、法的创制、法的实施、法的解释等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会涉及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譬如法与政治、法与经济、法与社会、法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法为中心而展开的。众多的法理学教科书,虽然也会在“导论”或“引论”部分设置一节专述“法学”,但是,法理学或“法学理论”的主体内容,并不围绕着“法学”而是围绕着“法”而展开。概言之,“法学理论”或“法理学”主要是以“法”作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理论。法学领域中的“法学理论”并不能与史学领域中的“史学理论”完全对应。进一步来看,在法学学科体系中,也没有形成一门可以与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史学理论”相并立、相对应的法学分支学科,还没有形成一门专门研究“法学”自身的法学分支学科。
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其一,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在“六经皆史”、经史难分的固有传统中,史学一向发达,史学与经学相互捆绑,在知识体系中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见:“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2页。相比之下,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的历史相对短暂,较之于“最发达”的史学,积淀还不够深厚,也不够“发达”。其二,近现代以来,“史”主要是由史学家操持的,“法”主要是由法律家操持的;“史”源于写作,“法”源于行动;对于“史”来说,怎么“写”是最重要的,对于“法”来说,怎么“办”是最重要的。譬如,写《史记》主要在于“写”,但是,“办案子”却主要在于“办”。这就是史与法的区别,同时彰显了史学与法学的差异。因而,在史学领域,“怎么写”极为重要,“笔法”极为重要(如“春秋笔法”),但是,在法学领域,尽管也需要面对“怎么写”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被降低,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的“做法”“行动”更为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虽然关于“法”的理论是重要的,但是,关于“法学”的理论,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关于“法”的理论那么重要,这也是针对“法学”自身的“法学理论”不那么发达的一个客观原因。
不过,当代中国的法学及其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也像世间万物一样,总是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十年间,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在国家法律制度逐渐成形的基础上,随着法学知识的积累,随着法的理论越来越复杂,随着法学日渐成为“显学”,随着法学从业者日益增多,随着法学研究专业化、职业化进程的加深,在法学领域,“怎么写”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出来。在这种新的背景、格局下,法学领域已经像史学领域那样,催生出对于“怎么写”的需求,针对法学自身的“法学理论”由此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以法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法学自身的理论知识,或者是关于法学的法学,简言之,就是法学之学。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法学之学的兴起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最先兴起对于法律的需要,接下来,在法律发展的基础上,就会兴起对于法学的需要,最后,在法学发展的基础上,将会兴起对于法学之学的需要。在相当程度上,法学之学的兴起,乃社会发展、法律发展、法学发展之后的必然产物。反过来说,法学之学的兴起也可以促成“自发的法学”转向“自觉的法学”,在“自觉的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下,法律的发展也可以在一个更高水平上行稳致远。当然,更高水平上的法律也会促使社会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文明。
更进一步来看,以法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理论”,虽然没有像史学领域中的“史学理论”那样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然而,无其名却未必无其实。一百多年来,在中国近现代法学生长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法学自身的研究,在不同的时代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关切。
在中国近代法学初兴之际,梁启超较早对“法学”自身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早在1896年,他就写成了一篇堪称“中国近代法学导论”的文章《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以之对“法律之学”或“法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予以新的界定。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群体,其“智愈开力愈大者,则其条教部勒愈繁”。梁启超在此所说的“条教部勒”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法律规范。进一步来看,“其条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坚定者,则其族愈强,而种之权愈远。人之所以战胜禽兽,文明之国所以战胜野番,胥视此也”。他还提出,“此其理至简至浅,而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不外是也。”③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对“条教部勒”之“析”,可以理解为对法律的研究,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法学研究。简言之,精微的法学有助于人人守法,能够推动一个民族走向强盛与文明,这是“治法学者”应当具备的学术自觉。
在20世纪初,沈家本撰成的《法学盛衰说》一文,既是法学名篇,同时可以视为关于法学自身的专论。此文认为,“虞廷尚有皋陶,周室尚有苏公,此古之法家,并是专门之学,故法学重焉”。从总体来看,沈家本把传统中国的法家之学与律学都归属于法学。尤其是到了汉代,律学为当时所重,“法学之兴,于斯为盛”。关于法学盛衰的规律,沈家本还说:“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④沈家本:《寄簃文存》,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4~116页。沈家本关于“法学盛衰”与“政治盛衰”相互关系的这番观察,正好可以从法学的角度,解释张之洞的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⑤冯天瑜、姜海龙译注:《劝学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9页。
在20世纪40年代,蔡枢衡关于中国法学自身状况的批评,对那个时代的“法学之学”亦颇有贡献。在他1947年刊行的《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一书中,蔡氏写道:“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譬如,在法哲学方面,“无一为自我现实之反映;无一为自我明日之预言;无一为国家民族利益之代表者;无一能负建国过程中法学理论应负之责任。此种有人无我,有古无今之状况,即为现阶段中国法律思想之特质”。在法规范学方面,“总而言之,一无对象,二无方法。不仅法规范学,至此已不复能维护其存在,即整个法学,亦成一塌糊涂”。总体来说,“初期模仿日本,后来效法西洋,此为数十年来中国一切制度文化之写照,亦即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制度蓝本之说明”。⑥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00页。
接下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兴,遂以新思想改造旧法学,期与新社会、新观念相一致。五十年代后半,风波迭起,法律被目为无益之事,法律研究亦无所依托。此后二十年,无法律职业,无法律教育,法制一项,仅存刑律。七十年代末,国人重修法制,遂有法学复兴。惟浩劫之后,不独学术荒废已久,心智亦遭败坏。法学十年,功在补阙,而驱除陈腐观念,摆脱教条束缚之努力,未尝有一日止息。”⑦梁治平:《法学盛衰说》,《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此处所说的“法学十年”,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在此期间,关于法学自身的研究,亦开始兴起。
在1989年出版的《法学变革论》一书中,立足于对法学自身的研究,着眼于法学的自我认识,直接提出了“法学学”的主张:“法学学是法学自我认识的系统化、学科化,它可以有许多称谓,如‘法学的法学’‘元法学’等。法学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既在于时代的必然要求,也在于它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研究内容”,“法学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法学。法学学是对法学进行探讨的学科,是法学的‘自我意识’或‘反思’”。⑧文正邦、程燎原、王人博、鲁天文:《法学变革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这种关于“法学学”的定位,与“史学理论”颇有同工异曲之妙。
当然,“法学学”这个概念,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可以看到关于“法学学”的提议。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为了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法学,完善我们的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法制体系和法治体系,正确处理好法律规范与其他行为规范、法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部门、法与经济基础,以及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法学与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关系,我们应当建立一门新的综合性的法学学科——法学学,应当重视和加强法学学的研究。⑨耘耕:《法学学刍议》,《法学杂志》,1983年第5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法学学”的思考还有进一步的延伸,“中国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重视对有关法学学‘问题’的研究。首先,就法学学自身含义来讲,它是研究有关法学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因而,凡是有关涉及这一领域的问题,都应该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其次,就法学学的学科性质来讲,它“是以研究有关法学发展规律问题为其中心任务的,其中涉及大量的法学发展问题”。⑩刘作翔:《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应当重视法学学问题的研究》,《法学》,1996年第4期。
自20世纪末期以来,20多年间,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学自身的研究一直都在不断拓展、不断延伸。这就是说,在一百多年的中国法学演进史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法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已经积累起来的这种旨趣的“法学理论”或法学知识,在事实上可以对应于史学领域中的“史学理论”。
在接续百年以来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不断完善、持续建构关于法学自身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可以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理论基础。毕竟,关于法学自身的法学知识,乃是整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