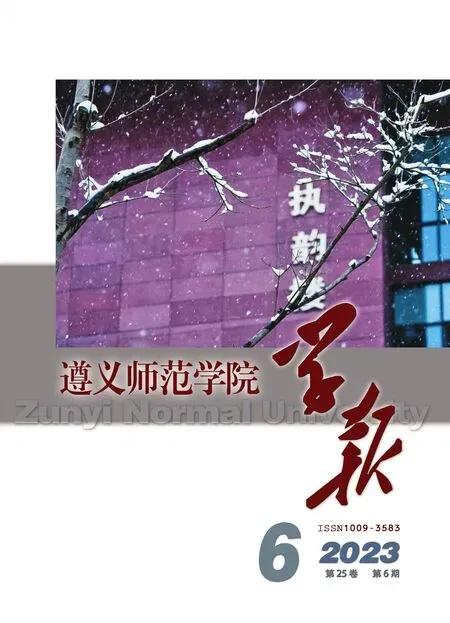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共情传播探索
任庆亮
(1.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2.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外交话语是一个国家外交理念的重要载体,关系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传播效果与国际话语权建设。质而言之,“外交话语属于机构话语中的政治话语,是指外交主体为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话语行为,主要包括关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外交谈判、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等”[1]P7。为全面、准确地向世界各国介绍我国的外交政策,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国历来重视外交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工作。然而,受“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的限制以及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法律制度、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外媒体、民众或政府对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核心概念所承载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心存疑虑甚至抵触”[2]P99,不利于中国外交话语走出“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传播困境。基于此,在深刻把握中国外交话语对外传播特点与规律的基础上,本文将跨文化共情传播引入到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与传播中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四卷)中文版为例,挖掘共情资源,探讨中国外交话语在跨文化共情传播中实现价值共享的创新路径,为提升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提供一种思路。
一、跨文化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
共情(empathy)是一个活跃于美学、心理学、哲学和传播学等不同领域的概念。它强调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同向解读和情感共鸣,“有利于解决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3]P72。同时,将共情与跨文化交往活动相结合,即为跨文化共情传播。
1.共情的基本内涵
共情的相关研究多见于美学、哲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关共情的定义,由于研究者所属学科领域不同,阐释视角各异,至今未达成共识,但通常认为共情“能够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主义的行动。共情是人类根源于基因的一种天赋。共情不是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4]P3。“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同理心有相似之处,但从作用机制上来说,比同理心要复杂得多”[5]P78。可见共情既是行为主体的一项能力,也是行为主体在人际活动中与他人的互动过程。“此外,共情必须通过传播活动来实现。从传播的过程来看,共情的实质是主体在识别、理解他人情感后产生共鸣,并将这种情感共鸣反馈给对方。从传播的互动性来看,共情实际上是传受双方对彼此心理和情感的理解与反馈”[6]P66。因此,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共情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2.跨文化共情传播的基本内涵
同传播一样,共情也需要至少两方的参与,具有信息分享的动态性、行为主体的交互性以及接受效果的不确定性。将共情应用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加以考察,文化间的传播活动就具有了跨文化共情传播的属性。同理,跨文化共情传播也离不开聚焦于社会实践的各类跨文化传播活动。关于跨文化传播,孙英春曾指出“跨文化传播既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7]P14。如何同异质文化中的他者进行交流?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在政治制度、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各维度的差异?如何通过拥抱差异,实现文化相通?这些均为跨文化传播所关注的重要命题。而共情作为一种互动过程,作为一种交际策略,对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实现具有启发意义。
基于学界当前对共情及跨文化传播的讨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可定义为“传播者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巧妙地培养和运用共情,力求传播的信息内容获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他者’的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进而引发‘他者’的行动反馈。实际上,跨文化共情传播就是一种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的策略或技巧,人们可以将其在个人、组织、国家等各个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付诸实践”[6]P66。
二、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共情传播的独特优势
长久以来,由于“中国外交话语既有汉语的表达特性,又有政治话语的敏感性、含蓄性等特点”[8]P45,增加了中国外交话语对外传播的难度,制约了其在海外国家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将共情引入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传播中来,能够帮助我们探索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创新路径,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
首先,建立情感通路,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推进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争端时有发生,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中心思潮持续蔓延,跨文化交流多元路径受阻。而跨文化共情传播倡导通过创新共情传播媒介,来培养和借用共情,拉近国家间的距离、增加信任感,能够为准确传达中国外交话语内涵、构建可爱、可信、可敬的国家形象提供思考。
其次,讲好普通民众的故事,促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阐释好中国的外交政策、讲好中国的外交故事离不开海外亿万民众的积极关注和正向解读。但现实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群体或组织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地理环境、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作为桥梁的交流是一种真实的幻觉,作为沟壑的交流是一种残酷的现实”[9]P3-4。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偏见、歧视等错误认知和行为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推向了误解的深渊,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对全球资源的攫取和积累,牢牢占据了全球信息流动的高位并主导着国际舆论,并借助传播力量建构起非西方文明对其的附属关系”[10]P119。而跨文化共情传播强调受众意识,提倡选择能够激发共情的传播内容,有利于破除传播过程中“我”与“他”的对立局面,从而建立“我和你”的交流共同体。通过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四卷)中文版里中国外交话语的表达形式与价值意蕴,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善于根据不同的演讲对象和不同演讲主题,广征博引中国俗语、谚语、格言和比喻等修辞手法,将极为严肃的政治话语转化为逼真形象的平民话语,增加了受众的青睐和情感认同”[11]P93;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还擅长挖掘海外受访国家的民族特色,对受众耳熟能详的当地名人名言、英雄故事、历史遗迹、优势产业等加以赞扬,拉近了话语言说者与听众的距离。例如,2018 年11 月30 日,在对巴拿马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巴拿马《星报》发表题为《携手前进,共创未来》的文章中赞扬道:“巴拿马运河举世闻名,瑰夏咖啡声名远播,香蕉等热带水果享誉世界”[12]P1。这种话语风格有利于激发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在话语建构上体现了共识、共情、共享的受众意识,符合跨文化共情传播理念。
最后,着眼世界发展,反映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话语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是对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的阐释与升华,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观层面的意蕴。而当下,“对于旨在打破西方话语体系藩篱,建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来讲,一个能够超越种族、文化、国际和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大局,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和追求,具有共同性、全球性共识的价值观尤为重要”[10]P121-122。因此,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译介与传播需要以共情为基础,找到中外共同关注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基点,以增强共情视域下的传播活力,努力建立共知、共情、共通、共享的跨文化交往伦理。
三、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共情传播的路径选择
系统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四卷)中文版内中国外交话语的构成特色、翻译技巧和传播机制,深挖共情资源,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背景下的人们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三个阶段入手,通过更新理念、拓展渠道、关照受众、注重反馈、调整方式等策略将跨文化共情传播付诸实践,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提升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1.跨文化共情传播下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
跨文化传播关注的核心是如何与异质文化交流的问题。长久以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因素影响,一种话语表达式及其所承载的理念进入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经常遭遇“被怀疑”“被过滤”“被选择性接受”,甚至处于“被误读”的尴尬处境,带有政治意蕴的外交话语更是首当其冲。为消除误解,促进沟通,以文化间性理念引领中国外交话语的跨文化共情传播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实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妥协、平等、互动。因此,“跨文化共情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都应树立文化间性理念,超越文化中心主义局限,尊重异质文化的‘他者’,并坚持从‘他者’出发,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平等交流的桥梁,促进双方之间的互惠性理解”[6]P68。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四卷)中,诸如“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3]P259“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14]P457“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15]P440等外交话语不论是语言内涵还是价值外延都很好地诠释了文化间性理念在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共情传播中的应用,也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家领导人外交话语的魅力,以及话语背后浓厚的跨文化共情意识。
2.跨文化共情传播下中国外交话语的翻译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16]P5,强调对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研究。根据传播区域,可以分为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根据传播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可以分为同语传播和异语传播。本文讨论的中国外交话语的对外传播属于借助翻译、向海外受众传递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可称为翻译传播。翻译是该项传播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影响传播效果;传播是翻译的目的和归宿,衡量翻译价值。二者关系密切,是中国外交话语实现跨文化共情传播目标的重要环节。而纵观中国外交话语的运作机制可知,翻译处在中国外交话语生产与传播的中间环节,直接制约着中国外交话语的内涵能否被准确、全面地传递到文化的“彼岸”即异语受众。因此,译者“为了实现原文意义在目标语环境中的重构,就必须基于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审美取向,有针对性地融通语言,实施灵活多样的翻译手段和策略”[17]P18。具体而言,译者就是在准确解码原文外交话语内涵的基础上,挑选有利于激发目标语读者共情的翻译方法,赢得异语受众的同向解读和情感共鸣。
3.跨文化共情传播下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
中国外交话语要让海外受众了解和接受,除了树立文化间性理念、选择能够激发共情的内容、采取多样的翻译方法外,还要尊重对外传播规律,重视跨文化共情传播下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渠道建设和传播效果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5 月31 日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18]P1。尊重传播规律既是工作原则,也是实践需求。中国外交话语的对外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翻译阶段,不能错误地认为“完成了翻译工作,就完成了传播工作”或“传播得不好,都怪翻译得不好”。因为翻译只是中国外交话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要想从“走出去”发展到“走进去”“走下去”,“作为传播的中间桥梁,翻译人员不仅要把控翻译的语言质量,也应当丰富对外传播途径”[19]P71,并根据受众反馈,实时调整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能。多语种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四卷)出版发行以来,中国外文局多次组织海内外力量、利用海外国家主流媒体平台举办线上线下发布会、圆桌论坛等活动,推介中国外交话语,并针对该著作外文版中国外交话语的核心概念不定期开展读者访谈,了解海外受众的反馈,为调整传播方式和优化传播内容提供数据支撑,充分体现了重视受众、促进沟通的跨文化共情理念。
四、结语
“每个历史时代的历史主体,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存在的境遇不同,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20]P28。中国外交话语作为我国外交理念的载体,借助跨文化共情传播能够增强其对外传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共通性。同时,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共情传播跨越政治学、翻译学和传播学三大领域,是向海外各国传递中国外交理念、培育“知华”“友华”“爱华”国际力量的重要方式,对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四卷)中文版为例,充分挖掘共情资源,明确中国外交话语跨文化共情传播在推进国家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优势,并探索在传播理念、传播渠道、传播方式等方面实现价值共享的创新路径,助推中国外交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一体化建设,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交流与文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