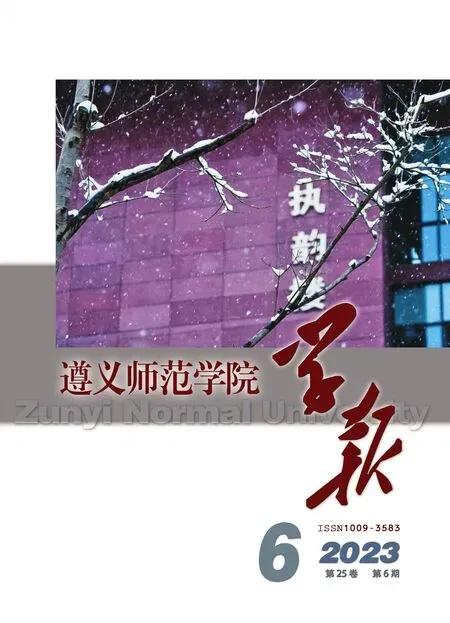揭开播州土司历史面纱的力作
——评李飞等考古学报告《海龙屯》
李 琛,陈季君
(1.贵州省镇宁民族中学,贵州 安顺 561200;2.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2012 年11 月17 日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2015 年7 月4 日,第39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遵义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科学出版社于2022 年出版的《海龙屯》[2]四卷本考古报告是贵州省文物研究所,现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研究员为首的海龙屯遗址考古团队自2012 年到2020 年八年间在海龙屯进行实地艰苦考古工作的最终成果,报告全面梳理并分析了海龙屯的格局、城垣与关隘等遗址、砖石和铭文等遗物、岩土与动植物的分期、播州山城防御体系,并附有大量考古分析图和实物照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海龙屯这一播州土司的重要遗址。
一、山城要塞——海龙屯遗址所见军事职能
海龙屯位于龙岩山首,建于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被称作“龙岩新城”。它是在宋蒙战争背景下,由播州杨氏和南宋朝廷共同营建的,以抵抗元军为主要目的山城要塞。至元十二年(1275),播州杨氏向元廷请求归顺,播州与元朝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内附。《元史》云:“播州安抚杨邦宪、思州安抚田景贤,未知逆顺,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诏封爵。从之。”[3]P171播州与元朝的战争结束以来,海龙屯的军事功能逐渐下降,直至明代万历时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出于武装对抗明王朝的需要,才将海龙屯重建为拥有城垣、关隘、墩台等完善的防御体系的山城要塞。
《海龙屯》考古报告揭示,目前在海龙屯就已经探明“不同时期的城垣共计5786.45 米……明代关隘9 座、南宋门道4 座。墩台8 座,哨台19 个”“屯上现存关隘13 座,含明代9 座,南宋4 座。名之为‘关’,实即城门。尚存匾额与文献记载具称海龙屯明代城门为关,当以此彰显防御性”。[2]P19海龙屯是明代平播战争的决战战场,而由播州军驻守的铁柱等各关,曾给予攻屯明军较大损失。李化龙《六报音疏捷》称:“我兵追至屯前铁柱关,被贼滚木礌石弩箭射打,阵亡兵四名,轻、重伤兵二百六十名。”[4]P111
明军在进攻海龙屯时,为了应对播军扼守险关,减少士兵的伤亡,使用了大量火器破坏屯上关隘。《六报音疏捷》亦称:“连日用大将军炮、灭虏炮打进城……二十五日发兵攻屯,有我南川一路官兵直冲屯之前门,用铳炮冲打,破酋之铁柱、飞龙二关。”[4]P111海龙屯考古团队经过清理发现,“屯上所见兵器有礌石、铅弹、铁弹、铁镞、铁刀、铁甲片等,出土于铜柱关、铁柱关、朝天关、飞凤关、万安关、西关、后关等明代关隘,以及新王宫与土城墙南门道内。”[2]P108海龙屯出土的大量火器遗物,证明了《平播全书》记载的明军使用火器的情况。《海龙屯》考古报告认为可从明、播两军火器的装备程度,看出播州方面在军事上的败因。
平播战争中,播州军明确拥有火器的记载,仅有李化龙《叙功疏》[4]p154载明军破海龙屯时夺播军百子铳一门,且无充分证据表明此百子铳为播军旧有之物,可能系播军夺自明军,此后再度为明军所复夺。其次,《海龙屯》考古报告也认为播军缺乏使用火器的意识,其证据即播军并未在防御工事中预留火铳射击孔,“关隘城垣上不见炮台、枪眼等设施,表明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火器防御并未进入建屯者的战术意识”。[2]P119
《海龙屯》考古报告进一步证实了《平播全书》记载的真实性,可以向平播战争的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的考古史料,并向研究海龙屯的学者提供有关海龙屯的布局、军事职能与战略意义的第一手最详实的材料。
二、家衙一体——海龙屯遗址所见国家认同
播州杨氏于明代世袭播州宣慰使一职,其官署原则上置于播州宣慰司城(今遵义老城),而海龙屯遗址上出土的一些房址,主要包括老王宫、新王宫及一些配套建筑,被认为是播州杨氏海龙屯上仿照播州宣慰司城的格局,建造的第二个统治中心。老王宫、新王宫居于海龙屯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建筑遗址,包括转山(玉皇阁)、金银库(城隍庙)、教场坝等。《海龙屯》考古报告通过分析这些零散分布的建筑,进而注意到“明代海龙屯就是按照一座城的规制进行规划的,营建时参考了位于遵义老城的宣慰司司治的诸多要素,除另立衙门外,还移植了玉皇阁、城隍庙、教场坝等仪式性建筑和练兵场所”。[2]P647
老王宫的称谓是相对于新王宫而言的,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老王宫常被视作宋代播州杨氏的遗址。《海龙屯》考古报告并不拘泥于“老王宫系宋代旧址”的旧说,运用考古手段分析出“目前揭示的房址均应为明万历时期的遗迹。”[2]P538然而《海龙屯》考古报告也提到,现阶段的考古很难完全排除“老王宫”为南宋遗迹的可能性,但《海龙屯》考古报告的新说,确实有利于学界对于老王宫认识的多元化,可以期待未来老王宫考古发掘的成果。
《海龙屯》考古报告所提到的杨氏在海龙屯上修建的“另立衙门”即新王宫,“结合建筑格局、其他衙署资料与文献记载,可知新王宫为明代海龙屯的内城,其性质为土司衙署。”[2]P512而新王宫在布局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家衙一体”的设计理念,“土司住宅即其衙署,其衙署即其住宅,两者合二为一。”[2]P513新王宫是播州土司除了宣慰司治所以外的第二个统治中心,杨氏在主持新王宫的修建时,希望以土司衙署这一带有官方色彩的建筑,向土民彰显来自明王朝的国家权力,凸显杨氏土司作为国家官僚的身份,因此,“新王宫土司衙署的营建可能是以播州宣慰司司治为蓝本进行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也留有时代与风尚的烙印。”[2]P513
新王宫内一并建有杨氏土司的家庙。《朱子家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5]P2播州杨氏家族自称起源于太原,长期以“中原人”的身份自居,在文化上积极接受中原文化。“播州宣慰司司治与新王宫土司衙署均将家庙设于正寝之左,即与《家礼》要求一致。”[2]P513新王宫的杨氏家庙,除了拥有定期举行家族祭祀,强化家族联系的功能外,同时也有彰显祖德的功能。播州杨氏十分重视传承自始祖杨端的“中原人”身份。《平播全书》载杨氏经常自称,“太原诗礼旧家。”[4]P475播州杨氏始祖“杨端”在杨氏土司的历史叙述中,是自愿从中原地区迁徙到位于边疆的播州,为中原王朝戍守边疆的英雄祖先。杨氏的子孙后代继承了始祖杨端“守土”的职责,“杨端”实际上成为杨氏在播州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海龙屯》考古报告认为,衙署与家庙这两组礼仪性建筑“遂成土司合法性的政治与血缘表达。”[2]P513而“家衙一体是由土司‘世守其土,世袭其职’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构成土司衙署与县府衙署的最大不同。”[2]P513
海龙屯以新王宫为首的建筑体系,本质是将播州宣慰司城的格局转移到屯上,进而制造出杨氏土司的第二个“统治中心”。新王宫“家衙一体”的格局,则集中反映了播州杨氏土司的国家认同观念,即杨氏土司主动认同明王朝赐予的播州宣慰使一职,以明王朝官员的身份统治播州,同时不断强化其家族内部的联系,凸显出家国同构的意识。
三、财丰物阜——海龙屯遗址所见社会经济
宋元、元明鼎革时期,播州的统治者都选择了归附新的统治者,进而避免了战争对于播州经济的破坏。明太祖在播州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仅向播州征收适当的赋税和贡品。《明史》谓:“洪武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二十年征(杨)铿入朝,贡马十匹。”[6]P8040明代中期以来,经过播州各族人民的努力,播州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则可直观体现于《海龙屯》考古报告之中。
马匹是明代播州重要的特产之一,也是播州土司向中央朝贡的主要贡品。万历十五年,时任播州宣慰使的杨应龙仍按要求向中央朝廷进贡良马。《明神宗实录》言;“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差长官何汉良等贡马二匹,庆贺万寿圣节。”[7]P3576播州出产马匹的质量,要好于西南其他地区的马,这可从海龙屯的考古工作找到依据。《海龙屯》考古报告认为可以通过检测海龙屯出土的马骨,进而分析出马的平均体型,而屯上马的平均体型远大于川渝地区的普通马以及云南的矮马,推测这批马极有可能是播州饲育特有的良马,而马骨还可以反映出“海龙屯出土的马以成年体(>4 岁)为主,部分马的年龄在9~12 岁左右,恰好属于最健壮的年龄。”[2]P732至晚,杨氏土司于平播之役时,仍然在海龙屯圈养着一批播州良马以役用,可见杨氏土司雄厚的财力。
万历时期,播州宣慰使杨应龙重修海龙屯运用了多元化的建筑材料,兼有石、砖、瓦、木等,其中除木质建材早已不存外,砖、瓦均有出土实物。海龙屯的石料究竟从何而来?海龙屯考古团队先后在2014年与2019 年在其石山上进行了两次勘察,发现了大量采石遗存——楔眼,经过岩性对比,基本认定为明代采石场遗址。《海龙屯》考古报告据此认定,“采石场的发现确证了建屯所需石料均就近采用,岩性的对比也支持这一认识,楔眼的发现则使之成为铁证。”[2]P613杨应龙重建海龙屯使用的砖石材料,大多为在屯上就近筹调,而非自远路运送石料上屯,同时也可看出,明代播州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采石体系。
海龙屯使用的砖件、瓦件,也主要由播州本地烧制。海龙屯考古团队通过释读一部分带有铭文的砖件,进而辨识出砖件上的“模印铭文”极有可能代表责任标识,以示该砖为“合格品”可以入窑烧制,进而得出“海龙屯砖料烧制,有一套完备的质量监控系统。”[2]P31海龙屯出土的瓦件则兼有宋、明两个朝代遗存,总体上以明代为主。现阶段,海龙屯考古团队已经在屯上发现砖窑三座,而在屯下发现有瓦窑三座。《海龙屯》考古报告认为,“多数窑址应砖瓦兼烧,同时可烧造脊砖、脊兽等陶质建筑材料。”[2]P33明代播州已经具有自主烧制建筑材料的能力与工艺,并且拥有一个稳定的匠人群体,专门为杨氏土司服务。
海龙屯的生活用器主要包括瓷器、陶器与玻璃器三类,而瓷器在海龙屯的分布较为广泛,其余两类则集中见于“新王宫遗址”。海龙屯考古团队通过对海龙屯遗址清理发现,“屯上出土瓷器数量较丰,分布甚广,几乎俯首皆是……出土碎片多达数万片,可计件者5000 余件,可复原者500 余件。器类有碗、盘、杯、碟、匙、罐、壶、瓶、盒、香炉、笔山、茶船、烛台、瓷塑等,以前三类最多。”[2]P052海龙屯出土瓷器大概涵盖了由宋至清代四个时期,明代瓷器最多,而清代次之,宋、元瓷器最少,这恰好与明代播州杨氏在海龙屯的统治情况重合。
瓷器有粗瓷、细瓷之分,细瓷多为内地窑口烧制,粗瓷则为播州本地烧制,而细瓷应为播州土司及其家人使用。明代播州土司通过各类手段,积累了大量内地瓷器,甚至包括景德镇民窑用于外销海外的瓷器——克拉克青花瓷。海龙屯共发现明万历时期的克拉克瓷器残片49 片,其中带有开光装饰的39片被确定为克拉克瓷器,另外10 片无开光装饰的则推测为克拉克瓷器。《海龙屯》考古报告认为,海龙屯出土的克拉克瓷器应为“带有克拉克瓷器特征的内销瓷器”。[2]P82这组克拉克瓷器的出土,不仅可看出播州土司拥有与时俱进的审美观,并且生活奢靡,不惜在奢侈品上耗费巨资,而且还可为明代播州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提供新的材料。
四、五味俱全——海龙屯遗址所见饮食文化
海龙屯考古团队在海龙屯遗址进行实地发掘时,清理出了一定数量的动物、植物遗存。当代考古学中,考古学者常常借助动植物遗存判断古人的生活方式,而海龙屯的动植物遗存多为土司时期的遗留,可以进一步揭开土司时期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图景。
海龙屯上的肉食,主要供给土司、土司家族及其亲信,而一般土民则较少享用肉食。考古队员在海龙屯遗址中清理出了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包括牛、马、猪、麂、鹿、鸟等动物,其一部分动物主要用途为食用,占比重较大的主要为牛。《海龙屯》考古报告通过海龙屯遗址出土的牛“角芯断面形态,及部分长骨”,[2]P722基本确定了海龙屯的牛种主要为贵州常见的黄牛,而通过检测牙齿的磨损程度,再结合解剖位置分析,推测出海龙屯的黄牛以青年个体居多,更多用于食用,而非役使用。海龙屯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役牛,但海龙屯考古团队在观察出土牛骨的病变程度后,认为“海龙屯黄牛的役用病变很少见,且程度不高,未反应明显的役用倾向。”[2]P725《海龙屯》考古报告在综合上述观点后,得出“海龙屯出土黄牛以青年个体为主,主要用于肉食”。[2]P725
考古团队在海龙屯还发现了以炭化的农作物种子为主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水稻、大麦等,均为我国本土作物,暂未发现原产自美洲的高产作物。历史时期内,杨氏土司在播州拥有大量田庄,并通过剥削土民来获取利益,以维持奢华的日常生活。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称:“杨辉将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园二十六处,蜡崖二十八处,猎场一十一处、鱼潭一十三处作四分,均分与杨友、杨爱、杨孜、杨敏。”[8]P21
明代万历时期,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与明王朝的关系日趋紧张,杨应龙遂选择于海龙屯上囤积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与明军可能发生的持久战争。考古团队选择在海龙屯上的“新王宫”“老王宫”与“金银库”三地进行局部采样,采样完成后,分两批先后送至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进行浮选,得种子样本26987粒,以农作物为主,而非农作物较少。采样标本显示,“(农作物浮选标本)共计25236 粒……可分稻、麦、豆、小米和荞麦等几类。”[2]P740播州地处西南腹地,湿热多雨,有悠久的稻作历史,而海龙屯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海龙屯“共计出土炭化水稻19782粒,占植物遗存总数的73.3%,占农作物遗存的78.39%,充分显示了水稻在播州农作物中的统治性地位。”[2]P750明代播州除种稻外,也种植其他粮食作物,包括“田禾”“麦”“豆”等,进而建构了以稻为主的粮食种植格局。稻米也成为土司时期播州各族人民的主要口粮,而土司及其亲信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肉食、河鱼、蜂蜜、野味等多元化的食物。
《海龙屯》考古报告根据现有的材料,作出以下结论:“16 世纪末,播州以水稻为主粮,以大麦、小麦、燕麦、龙爪稷、栗、黍、高粱、甜荞、苦荞、栽培稗为辅助性杂粮,大豆、红豆、绿豆等则用以代菜,充分展示了播州农作物的多样性,亦反映出当地以水稻为主、各种杂粮为辅的食谱结构。”[2]P752
综括全文,近年来,随着土司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土司遗址的考古也逐渐成为土司研究中的热点内容。以李飞研究员为首的海龙屯遗址考古团队在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不仅能向国内其他地区的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提供宝贵经验,还可以向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供参考的宝贵样本。
通过《海龙屯》考古报告,我们可以得知:明代海龙屯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其军事职能。末代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将祖先遗留下来的山城扩建成军事要塞,并选择在此与朝廷顽抗到底,而播州军缺乏使用火器的意识,无疑成为其军事上的败因之一。明代海龙屯以播州宣慰司治城为蓝本进行重建,杨氏土司将城内的礼仪性建筑移植到海龙屯上,进而创造了一个战时播州的军事与行政中心,而“家衙一体”的建筑格局,则体现了播州杨氏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海龙屯遗址上出土的明砖、明瓦多为本地烧制,而石材亦就近凿取,可见明代播州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建筑技能。考古团队通过海龙屯的马骨,分析得知明代播州畜养的马匹具备较高质量。海龙屯遗址大量出土的各类瓷器,既展示了明代播州与内地频繁的商贸往来,又彰显了土司家庭日常生活的中原化。海龙屯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炭化植物种子,可以使我们一窥传统史料记载较少的明代播州的饮食文化,特别是屯上暂未发现自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可证至明万历时期,今日黔北地区普遍种植的马铃薯、玉米等作物尚未被引入。
《海龙屯》考古报告的出版,相信可以加深学界对于播州土司遗址——海龙屯的整体认识,并有益于土司研究的整体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