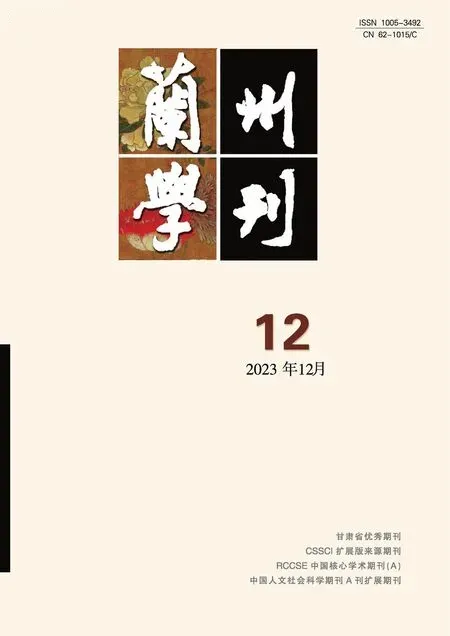人民战争概念发展史与中国化考论
靳书君 何益婧
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劳动人民作为独立的等级阶层进入近代战争,突破了旧式王朝战争的模式与形态,代表早期无产者的革命家巴贝夫提出了“人民革命”的口号,号召在富人革命之后进行一场多数人的穷人革命。“人民革命”口号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研究暴力革命的战略方针时,历史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十月革命得到充分运用,并经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汉译入华,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少胜多、由弱到强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原著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上,恩格斯提出了“关于真正的战争的概念”,即“人民本身参加的真正的战争”(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08页。,而不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1849年4月,恩格斯首次使用“Volkskrieg/人民战争”的概念,是回顾法国大革命颁布《全民皆兵法令》形成的战争形态,即“1793年法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人民战争”(2)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6,Dietz Verlag Berlin,1961,p.389。。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共有八场斗争被称为人民战争,即1793年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普鲁士民军反抗拿破仑的战斗、巴登—普法尔茨军民起义、克里木战争中的英军暴动、武装黑人参加的美国南北方葛底斯堡决战、巴黎公社保卫战、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反英斗争。综观经典作家关注的八场战争,可见他们对人民战争的内涵规定性。
(一)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体人民成为战争主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大革命时期法国无产者、农民、劳动群众甚至老弱妇孺夺取巴黎管理权的战斗看作人民战争的肇始,八十年后巴黎公社彻底实现了全民皆兵,更是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盛赞。从阶级阵容看,除了无产者,恩格斯还强调农民、农奴、黑奴,乃至旧军队的中下层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1848年巴黎工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发动广大农民;普法尔茨和巴登二百五十万全体居民起义的同时,驻军像一个人一样转到了人民方面,恩格斯称赞“人民的战争正在叩门”(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25页。,并亲身参加了战斗;在参加克里木战争的英军内部,恩格斯指明从上校至普通士兵都在控诉他们的长官;林肯政府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后,恩格斯立即分析了武装黑人在南北决战中的意义。列宁对比18世纪和19世纪战争性质和形态的深刻变化,认为以往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用做盲目的工具,而19世纪开始,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4)《列宁全集》第6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8页。。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展开军事斗争,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劳动者在内的最广大人民,成为战争的主体。
(二)领导战争的是新兴革命阶级
战争的性质取决于领导者和指挥者,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在于是由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新兴阶级领导。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列宁指出,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发生在1789—1871年的时代。(5)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26/В.И. Ленин.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7,p.215.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革命,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性从高涨到没落的历史周期,劳动人民从追随资产阶级进行战争,到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武器,掀起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从阶级阵容看,法国大革命之后八十年,资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是巴黎工人起义、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以及葛底斯堡决战的实际领导者。恩格斯认为,在19世纪中叶,“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这是唯有共和国才会采取的手段,1793年就证明了这一点。”(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3页。意大利皮蒙特是君主国而非资产阶级共和国,王室不敢依靠起义民兵开展人民战争,是王国军队战败的根本原因。而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是全德民主派光荣起义的曙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护法运动,因此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热烈地支持起义军,但不接受担任临时政府任何文职或武职的邀请。马克思指出,英国贵族力图将克里木战争限制在“局部战争”,就是惧怕高价购得“新贵族”头衔的新兴资产阶级,害怕战争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军事目标,担心失去对政府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只有在人民战争——只有同俄国的战争才可能是这样的战争——把外交政策变为人民的事业以前,才能保持得住。”(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南北战争后期,恩格斯给在美国的友人写信说:“这种人民战争(双方都是)是有了大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它的结局无疑地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8)《马克思恩格斯写给美国人的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北方资产阶级不仅领导了北方人民参战,实际上也领导了觉醒的南方奴隶起来战斗,从而使内战成为资产阶级共合众国的国运之战。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镇压巴黎公社暴露资产阶级走向没落,通过公社保卫战、彼得堡工人起义等战斗历练,无产阶级日益成为人民战争的主导者和领导者。列宁考察了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到1905年俄国革命,在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历史性创造中,无产阶级日益成长为人民战争的领导者,列宁以巴黎公社精神为莫斯科工人呐喊:“让我们用法国革命歌曲中的话来说,Vivelesonducanon!(“炮声万岁!”),革命万岁,反对沙皇政府及其追随者的公开的人民战争万岁!”(9)《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深入研读自拿破仑第一以来的世界战争史,在钦佩拿破仑军队依靠人民力量的支持屡建奇功的同时,深刻地指出,拿破仑战争还不是“全体人民的事情”,“有一点不准确:是资产阶级的,或许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事情”(10)《列宁全集》第6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8页。,战争真正成为全体人民解放事业的前提条件,是无产阶级的直接领导。1848年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各阶级在革命战争中的政治表现,发现无论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都不愿将社会革命进行到底,一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谋得本阶级利益,就要尽可能结束革命战争,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联手对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列宁进一步指出,在东方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当中,资产阶级更加软弱和动摇,更容易和本国封建势力甚至外国侵略势力妥协,所以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无法发动和领导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领导权历史性地转移给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让国际垄断资本统治链条出现薄弱环节的革命条件下,列宁在《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提纲中写道:“人民战争”,是的!(11)《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号召无产阶级领导最广泛的人民战争代替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而战斗到底。在资产阶级领导和指挥的战争中,人民的力量常常受到各种限制,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人民战争的军事伟力才能充分激发出来。
(三)武装力量由正规军与国民自卫军相配合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推动废除常备军制度,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僭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在雾月政变前后,法国资产阶级依靠正规军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自卫军,而后解散了自己的自卫军,国民自卫军被扫荡一空;与此相反,巴黎公社开始就废除了旧式的常备军,人民武装起来建立了国民自卫军。马克思既看清资产阶级对人民武装的惧怕,也指明了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的人民武装性质,但同时批评公社不善于协调首都的国民自卫军和外省各地起义部队间的作战行动。恩格斯非常注重人民自卫军、志愿军的武装力量,亲身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志愿军团,同时强调正规军始终是人民武装的核心力量,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是民军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障,他指出:“应该希望,无论是志愿兵,或是公众,永远也不要以为志愿兵有一天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正规军。”(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5页。对于全部人民武装力量的组成,恩格斯明确指出:“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的乡村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2页、第278页。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任何一种合理的军事组织不能不是介乎普鲁士制度和瑞士制度之间的东西”(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2页、第278页。,人民武装要善于把普鲁士的正规军传统优势和瑞士的民军传统优势结合起来,就能构成合理的军事组织形式。
(四)人民游击战争的战术战法
在反抗拿破仑入侵的战斗中,普鲁士民军创造了机动高效的自由射手战法,陆军元帅格奈泽瑙为此制定了《民军条例》,把自由射手战争系统化,所以恩格斯说:“人民战争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17页。,但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国王的圣谕作战,所以自由射手的战术战法让威廉三世根本无法接受。马克思后来回顾说:“事实上,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在堂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看来,简直是眼中钉”(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48页。,因为这是人民解放的战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认定清朝军队通常的作战方法根本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民众的罢市、偷袭、夜袭、苦力暴动、焚烧商馆等抵抗方法,几乎掀起了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灭绝战,恩格斯评价说,不要拿封建骑士的标准指责中国人的抵抗,“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别的任何抽象标准来衡量”,“最好承认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第146页。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全世界弱小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战斗实践,写下多篇战争评论,指明了弱小民族依靠游击战抵抗强敌的战术战法,论证了“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不仅可以开展山地游击战,也可以开展平原游击战(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05页、第557页。;人民游击战不仅适合于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更适合于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恩格斯既看到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在军事上的特殊表现,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63页。在普法战争第二阶段,恩格斯分析指出:“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最大的军队逐渐地损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看不到这一点能因对方的相应损失而抵消。”(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24页。巴黎公社革命就是这种人民战争集中的和最终的表现,以游击战见长的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通过消耗强敌兵力逐步赢得战争优势的独特战法。无产阶级在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中,创造出新的街垒战术,列宁总结说:“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23)《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0页、第319页。在反革命势力和反革命武装仍然居于优势地位的条件下,“在这种持久的游击战争中,无产者将学会作战,而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24)《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0页、第319页。,列宁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战术层面,并指出了通过持久的游击战,逐渐达到敌我双方优势转换,是无产阶级革命总决战的根本条件。
二、《波斯和中国》原著概念popular war自西向东传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四篇文章、两封书信、一次会议文献使用了人民战争概念:马克思1854年在《克里木战局的回顾》中讽刺英国贵族畏惧政府垄断权的丧失,因而尽一切可能避免人民战争,1870年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直言普鲁士国王将反拿破仑的人民战争视为眼中钉;恩格斯1857年在《波斯和中国》中高度认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多次战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1864年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坦言美国独立战争中葛底斯堡守卫战是古今未有的人民战争;列宁1905年在《“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者”序言》中盛赞法国大革命期间夺取城市管理权的人民战争,1917年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保卫战分别看成是西方人民战争的起始和高潮,1918 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提出拿破仑式的侵略战争必然会被人民战争所取代。这七处文本中恩格斯的英文社论Persia-China(即《波斯和中国》)汉译最早,对人民战争术语定译产生直接影响。1857年初,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请他关注波斯和中国的战况,恩格斯复信表示将收集新闻材料写一篇文章(25)《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26页、第227页、第230页。,最终于5月22日写成社论Persia-China,并将初稿寄送马克思。文稿获得马克思高度认同,马克思回复说:“你关于中国和波斯的论文,我只间或去掉一点,间或换些转折字眼。”(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26页、第227页、第230页。经马克思审阅之后,Persia-China发表于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文中使用a popular war指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斗。(27)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5:Marx and Engels:1856-1858.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的遗稿由其小女儿艾琳娜保存。艾琳娜及其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共同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英文报纸文章集《东方问题》, 1897年在伦敦出版,次年艾琳娜去世,马克思遗稿转交二女儿劳拉保管。1909年,流亡北欧的梁赞诺夫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托,主持《东方问题》的德文译介项目,第二年,劳拉·马克思·拉法格夫妇邀请梁赞诺夫前往巴黎参阅马克思遗稿。凭借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室保存的恩格斯遗稿和劳拉夫妇家里的马克思遗稿,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时的交流信件,发现恩格斯1857年撰写过社论Persia-China,梁赞诺夫辗转伦敦大英博物馆稽考《纽约每日论坛报》原件,找到了Persia-China报纸原文。至此,梁赞诺夫决心将《东方问题》项目拓展为马克思恩格斯报纸文章集,计划编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致力于将此十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论文章公之于世。 1917年出版至前两卷时,俄国二月革命爆发,计划中的第3、第4卷未能面世,第2卷收录至1856年社论文章,写于1857年的Persia-China未能公开出版,原稿被梁赞诺夫善存。梁赞诺夫出任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后,依靠马克思女儿女婿艾威林夫妇、拉法格夫妇的信任,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的所有著作权和出版权,着手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MEGA1)以及俄文第一版《全集》。然而,由于苏联内部政治风波,梁赞诺夫去职,之后由阿多拉茨基接任院长并重新规划了MEGA1和俄文第一版《全集》的出版。在新方案中,计划在MEGA1的第 Ⅰ 部分第13、14卷中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报纸社论,然而,直到1939年MEGA1项目完全“夭折”,这两卷一直未能出版。虽然Persia-China英文原著没有出现在MEGA1中,但在俄文《全集》工作小组的努力下,它被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这一版本中约有430部(篇)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发表过但未及收录至其他相关文集中的著作文章。(28)姚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版,《出版始末及其历史意义》,《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1933年,俄文第一版《全集》第11卷出版,Persia-Chin收录在该卷第1册,译名Персия и Китай,英文母词popular war被直译为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29)Маркс, Карл.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1, часть 1 / 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 Под ред. В. Адорат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Партиздат, 1933, p.166.,与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使用的народной войне(30)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26 / В.И. Ленин,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7, p.215.相同。народной系形容词“人民的”原形,народная为其第一格、做主语,война系“战争”的名词原形,войне为其第三格,这就贯通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概念,人民战争原著概念完成了自西欧向俄国的传播历程。
首个《波斯与中国》汉译本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1卷译出,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海版)1934年第73期,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1934年第68期全文转载,起初将俄语词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译为“民众战争”。1937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译者方乃宜,该书第二章收录了《波斯和中国》新的汉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汉口出版,以延安解放社名义在延安出版,方译本使用“人民战争”术语对译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31)《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方乃宜译,延安:延安解放社,1938年,第82页。,这个翻译在马克思主义汉译史上具有拓荒地位,首次创译出“人民战争”术语。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战争概念的成熟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党在幼年时期偏重民众运动的斗争形式,1924年参加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才初步意识到掌握军事武装力量的紧迫性,但也没有明确提出建立自己的军队。大革命失败表明,单纯依靠民众运动,无法取得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国民党反动时,所有的民众运动都崩溃了,惨痛的教训促使党彻底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八七会议决定转向武装斗争,但还没有充分讨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领导开辟井冈山道路到工农武装割据,开始使“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3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第136页。苏区采用两种方法建立工农武装:一种是在已经有一定民众武装的根据地发展党、政权和正规军部队;另一种是在民众武装非常薄弱的新根据地,由正规红军帮助发展人民武装、建立割据政权。在这过程中,注重政治教育启发阶级觉悟,让“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3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第136页。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推动工农政权波浪式地向前扩大,党在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群众的战争”,他指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3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第136页。中央苏区依靠“群众的战争”,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但此时在“左”倾中央领导下,党的中心任务仍然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反映出党的工作重心当时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党中央迁入苏区以后,战争和战略问题上升为全党的工作重心,在反“围剿”战争的实践力量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军事论述,特别是有关中国战争问题的著作,被译介和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第五次反“围剿”激战的关键时刻,党的机关刊物《斗争》译载了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将原著概念popular war/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译为“民众战争”。这样翻译一方面是基于母词字面的直译,popular/народная字面义即是“大众”“民众”;同时也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主觉醒和社会运动勃兴,普通“民众”而非仅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被描述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新主体,并为国共两党所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由于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原则性错误和认识,“左”倾中央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民众战争”与苏区“群众的战争”在联系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与苏区战争的具体实践结合不够的状况,一直到遵义会议才从根本上扭转。
遵义会议标志着全党正式“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3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8页。,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军事战略问题首次进入党的会议文献,全民族抗战爆发,毛泽东连续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标志着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在正确的军事路线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同时开展军队作战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工作,致力于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民众战争”(36)《红藏·斗争(苏区版)》,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1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提出:“弱国战胜强国,必须发动广大的民众战争,分散强国的兵力”(37)《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6页。,《斗争》杂志沿用的恩格斯原著概念popular war的译词“民众战争”,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人民军队坚持自卫军、赤卫队的组织方式,并发展新的民兵组织形式,如敌后武工队、纠察队、锄奸队、学生军、支前运输队、抗日青年先锋队等,广泛运用袭击战、伏击战、破袭战、围困战、 地雷战、地道战、 麻雀战等战法打击和消灭敌人,游击战被提升到战略地位,真正检验出兵民乃胜利之本。毛泽东、朱德将之前提出的“群众的战争”,明确凝练为“群众战争”命题,他们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战争,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3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388页。“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游击战争的本质就是群众战争”“落后的国家民族只有通过广泛的群众战争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39)《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第325页。刘少奇、邓小平也指出:“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战争”(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我们进行的是民族的正义的群众战争,我们动员了一切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41)《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43页。党的领导人使用“群众战争”术语突出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负责人则从全民族各阶级动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展开、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的配合等战争形式,归纳出“全民战争”的口号,新四军将领彭雪枫提出:“我们是全民战争……,不分东西南北,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阶级党派的全民战争。”(42)《彭雪枫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494页。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明“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43)《叶剑英军事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是八路军能屹立独存于敌后并制胜敌人的秘诀。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指出:“真正的全民战争,只有在巩固于扩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其威力。”(44)《谢觉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1页。
党内负责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和翻译家、理论工作者汲取《波斯和中国》《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作中的军事战略思想,极大地推进了经典作家的原著概念popular war/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具体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共产党人表述战争性质和形式的本土术语的融合。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党内的总负责张闻天即编著了教材《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引用了《波斯和中国》关于“谋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奋起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45)《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张闻天编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页。等论述,1934年张闻天曾任《斗争》(苏区版)主编,但他没有沿用恩格斯这段话,在1934年《斗争》中的译词“民众战争”,而是新译为“人民战争”。这部教材传播面很广,在最初油印本的基础上,1937年、1938年又连续出了铅印版,张闻天使用这部教材在党内亲自授课。与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方译本出版,鲜明地将恩格斯原著概念译作“真正的人民战争”(4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张闻天编著,延安:延安解放社,第75页。,特意超脱原文在“人民战争”译词前冠以“真正的”,足见译者对“人民战争”术语的持重和笃定。方译本流传也很广,周恩来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抱病阅读了方译本,并于5年后在延安重读此书时在封面签名。(47)赵洁敏、黄霞:《北京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的过去与未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4期,第9-14页、第79页。方译本和张闻天编著的教材,首先在理论战线上使“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流行译词。1938年,著名翻译家、《群众》主编华岗编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材,大量引用方译本,特别是引用了“人民战争”概念出现的段落。(48)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重庆:鸡鸣书店出版,1940年,第80页。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摘引了方译本:“我们中国方面,却曾进行了‘真正的人民的战争’。(《马恩论中国》第五十三页)。”(49)《杨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2页。长江局宣传部长何克全(笔名凯丰)在《马克思和中国》一文中引用了方译本的“人民战争”表述。(50)《红藏·解放》第2册,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1页。直到1940年11月,《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的社论,追忆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称赞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争取自己的战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51)《新华日报》第952号,1940年11月28日。这时,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明确指出:“关于战争性质的问题,共产党和抗战派都主张这个战争应当是人民战争,应当是持久战争。”(52)《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这表明,从恩格斯原著概念中译出的“人民战争”术语,逐步从思想理论战线向现实斗争中的军事政治战线延展和融合。
1943年中央总学委下发通知,学习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其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中指出:“民族战争的三条件就是人民战争,民主民生,反对投降派。”(5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9页、第660页。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爱尔科里(即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在某个时候不得不用武力去保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可是一看见战争有变为人民战争的危险,看见工农群众像怒潮一般起来要求满足他们的阶级要求,它就总是想滚到敌人营垒中去。”(5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9页、第660页。翻译这些文本时,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均使用“人民战争”一词,词语所指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也囊括世界各国维护独立自由的全民族战争,衍生为世界历史层次的概念。到延安整风后期,毛泽东已经阅读过列宁的著作《第二国际的破产》,他认同列宁所指明的第二国际破产的根本原因,即欧洲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运用人民战争的力量。(55)《毛泽东读书集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99页。在恩格斯《波斯和中国》一文中,同样是面对外敌入侵,波斯单靠政府军抵抗遭遇失败,而中国人民自发组织的人民战争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无独有偶,二战前夕,第二国际违背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方针,导致本国陷入战火。而在中国,因为有了共产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逐步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通过持久战获得了战略决战取胜的契机。到抗战胜利前夕,“人民战争”术语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而由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专节阐述“人民战争”的概念内涵,即首先,动员、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通过政治教育将人民群众由社会历史主体塑造为军事战争主体,用长期的军事战争的斗争方式夺取政权;其次,建立一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形成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军事武装力量体制;然后,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地形又有利的农村地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战胜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灵活机动地采取游击战、运动战、消耗战等战略战术,把战略上的劣势,逐步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能动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后,所有的政治动员、军队组织、政权建设都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坚持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坚定依靠人民群众。同时,毛泽东清晰地将人民战争界定为人民政治斗争的最高形态,“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说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5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9-310页、第1075页。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反人民战争”(5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9-310页、第1075页。,这就厘定了概念的外延。
四、人民战争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
1914年“一战”期间,英国人在上海的报纸《北华捷报》就刊登过一篇题为A People’s War的文章,题目从字面本来可以直译为“人民战争”,但实质并非马克思主义术语,也未引起中国人的注意。1930年,美国在华报纸《大陆报》报道了一则关于德语战争片的禁令,标题为Alsace-Lorraine Bans Popular War Film Of Germany,法国当局禁止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上演有关德国人民战争的电影,此处popular war的所指范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论及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但是此处使用该词组显然还达不到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所指,也没有在国内被汉译或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战争的原著概念汉译,是1934年从恩格斯《波斯与中国》俄文版开始,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popular war的译法从直译为“民众战争”,到1938年意译为“人民战争”,再经过《波斯与中国》汉译本在延安的传播和阅读,不仅贯通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概念,并通过恩格斯的英语术语popular war贯通他同义使用的德语术语Volkskrieg,在Volkskrieg/народная война/popular war/“人民战争”之间建立起术语对译关系,还会通中国共产党和军队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提炼的“群众战争”“全民战争”等术语,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事概念。从概念发展史看,“民众”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脱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成为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的常用术语,用来囊括工人、农民、小工商业者和工薪阶层,以此来搪塞工人阶级的作用。共产国际对这种能指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在苏联留学回来的张闻天,特别是在莫斯科从事编译工作的中国同志,同时放弃了“民众战争”的译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都使用“全民战争”作为动员口号,这个口号性的术语侧重从数量上和面积上突出参与战争的广泛性,而不容易表达战争主体的阶级性,以及阶级阵容内部的结构性,也不容易表达战略战术的独特性和灵活性,因此宜使用于战斗动员,但难以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军事概念的科学术语。“群众”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术语,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革命战争最终是历史主体用暴力手段决定问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引用毛泽东的重要论述:“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5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388页。“群众战争”是相对于单纯的政府军作战而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战争的主体既有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还有规模性的民兵组织,又有工农联盟作为阶级基础,“群众”术语的所指尤其能够覆盖广大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59)《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9页。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话语中,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克服了自发性的“群众”,就组织成“人民”,因此相比较而言,“人民战争”术语比“民众战争”更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比“全民战争”口号更突出了参与战争的阶级阵容,比“群众战争”术语在能指上更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超越字面直译而从原著概念内核上意译,人民战争概念的定译过程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术语转换力度和话语建构向度。
正如列宁所说:“拿破仑式的战争一定要被解放战争、阶级战争、人民战争所代替。”(60)《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从克劳塞维茨军事名著《战争论》,特别是《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中,汲取思想营养,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战争”命题,是人民战争原著概念中国化的智慧结晶。列宁肯定拿破仑式的战争依靠人民武装力量屡建奇功,但他深刻指出民众参与战争数量的多寡,并不能说明某一战争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国大革命尽管有广大民众参与,但至多代表全体资产阶级的利益,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关于战争本质的论断,强调战争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特定政治矛盾和实现政治目标的特殊手段。当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仅仅通过非暴力手段如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渠道无法解决阶级矛盾或无法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时,人民群众作为政治主体,有能力选择使用武力,从而组织成战争主体。结合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战争的实际,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1)《毛泽东选集》,第511页。这一论点的突出表明,“人民战争”不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描述的游击行动和军事辅助手段,它本质上是人民自己创造历史的生动展现。在深入分析战争的本质时,毛泽东、邓小平由此将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战界定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62)《毛泽东选集》,第1041页、第1038页。,后来邓小平回顾总结革命战争的制胜因素时也指出:“问题是这种战争必须是真正的人民战争。”(63)《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0页。党的领导核心用“真正的人民战争”命题,标明了人民战争深厚的制胜因素,毛泽东深刻地总结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6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8页。统治阶级惧怕在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遭受人民的反噬,不可能将人民战争作为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无法释放战争的自然力量,只有“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激发现代战争的全部历史伟力。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现代战争的作战手段、战争样式和战法深刻变化,邓小平、江泽民等提出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重要命题,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一战争本质没有改变,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保持人民战争的制胜因素没有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6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页。。同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也不是以前战争手段的简单重复,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6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把民兵提到战略地位,促成民力与兵力相结合,实现“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与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相对接。 “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正确认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提升广大官兵驾驭现有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实现人与武器最优结合。同时,大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完善国防动员体制,依靠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最大程度地集中和释放战斗力。
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6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18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6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5-56页。随着战争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战争的途径、方法、手段越来越多,从有形战场到无形战场,网络战、舆论战、信息战等都将成为人民战争的新形式,人民群众左右战争进程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和考验,习近平将人民战争法宝运用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极大地拓展了“人民战争”概念的外延。201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恐怖主义法》,将人民战争思想引入反恐斗争,开展全民反恐。2019年,环保部门与各界力量群策群力,实行群防群治,成功赢得污染防治的人民战争。2020年,党和政府专职机关,包括禁毒委、政法委、派出所以及禁毒办,与民众力量合作,开展禁毒人民战争。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69)《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55页。,党政专职机关和人员、各地医疗从业者、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亿万民众携手同心,最终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2022年,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在新时代,“人民战争”概念成为一种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战胜来自自然领域、社会领域的风险挑战和来自外部的挑战的生动表述,在军事领域之外,“人民战争”术语的所指为由党和政府专职机关和专职人员发动组织,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攻坚克难的大规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