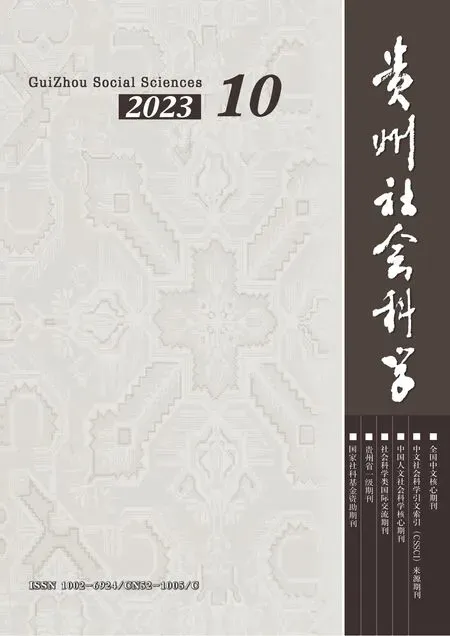宏大而多彩的人文叙事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地域特色
徐 圻 李直娴
(1.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 贵阳 550001;2.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千百年来,受到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的多重影响,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呈现出博大的多元形态,具备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具体来说,贵州本土的少数民族生态观念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儒、释、道生态思想互鉴互补、相融共生,生活、生产和生态融为一体,维系手段和传承方式别具一格,使贵州成为一座“生态文化千岛”,在整体上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良好格局。
一、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与儒释道生态思想相融合
在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少数民族生态观念与儒、释、道生态思想相互影响、彼此渗透、融合共生,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双向、多元互动的态势。此外,在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中,民间信仰与儒释道杂糅并“敬”,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
(一)儒家生态思想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儒家生态思想逐渐融入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之中,并成为其重要成分。儒家生态思想以“仁民而爱物”为出发点,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价值目标,以达致天地人“一体同仁”为归宿。[1]明清时期,贵阳、遵义、安顺、铜仁以及黔东南的岑巩、镇远、黎平等地汉族移民较多,“儒教渐兴,人文日盛”,其民“务本力穑”“男耕女织”,遵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律令从事农林生产,反对焚林而田、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等短视行为。
明清时期,汉族移民遍布贵州各地,儒家思想及其生态思想也传播至少数民族地区。在黔东南黎平县一带,侗族“女善织纺,男读书,丧葬礼多与汉人同”[2]280。黎平县肇兴侗寨的五个自然寨团,根据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义理,分别称为“仁团”“义团”“礼团”“智团”“信团”,其选址背靠山脉,面朝溪河。这既与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主张高度契合,又承续了侗族本土的生态观念。黔东南苗族和侗族、黔北仡佬族以及黔南与黔西南布依族普遍供奉儒家的“天地君亲师”或者“天地国亲师”牌位,把“天”当作万物本源,把“地”当作衣食父母,视敬天为正事,视勤耕为正业,在利用自然和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极力保护乡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明清以来,儒家主导的天文历法丰富和拓展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产知识。黔东南苗族经过“改土归流”,接受儒家教化,汲取儒家生态思想尤其是天文历法并把它作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态知识,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力田务农的生产方式。苗族理辞说:“十二月为一年,三十天为一个月,一天有十二时辰,一夜有十二时刻。六个月是冬天,六个月为夏天,就得汉族的汉历,就得苗族的苗历。就向村寨张扬,敲鼓告诉地方。”[3]6汉族农历传入贵州之前,许多少数民族使用自然历法,把岁首定在收成时节,一般在十月,苗年、彝年、布依年等皆是如此。农历传入民族地区之后,一些村寨也逐渐以正月为岁首,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林生产和日常生活。
(二)道教生态思想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明代,实行“拨军下屯,拨民下寨”的政策,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少数民族地区,道教也随之传入。道教的生态思想对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远甚于儒家和佛教。道家从“道法自然”出发,提出了道生万物、天父地母、天地人共同体等思想,表达了善待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更加肯定了天地万物的平等地位和同一价值。
黔东南侗族和苗族、黔南水族和毛南族笃信道教风水。在锦屏、黎平、天柱、镇远、麻江、榕江等地的清代林业碑刻中,多有“风水”“后龙”“水口”“朝山”“玄武”“龙脉”等堪舆学或者风水学术语。侗族、苗族人家往往按照一定的风水观念建村立寨。譬如,从江县增冲侗寨,四面依山,三面临水,山清水秀,林木丛生,其空间格局和建筑样式充分反映了侗族传统与汉族文化的高度融合。水族倡导阴阳合一、五行相配和天地感应,追求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共生、共存、共荣。水族历法有“月日满,换春夏,翻阴阳”的俗语,体现了系统、辩证、平衡的观念。水族村寨依山傍水,楼房的方位忌讳朝向穷山恶水。
黔西北彝族的自然崇拜与道教的“道法自然”多有共通之处。《彝族史诗》说道:
稀米遮时代,产生了万物,有命物产生,有血物产生;青气和赤气,也在这时产,也在这时生。青气绿油油,赤气红彤彤。青气有阴阳,赤气有阴阳。阴与阳之间,时常在变化,变化不分离;阴与明变化,分出坤与乾,阴阳与乾坤,两者紧相连。……阴阳分出后,乾坤分出后,分出五行来。五行生五运,运动生血气,运动生生命,人类才产生。[4]
(三)佛教生态思想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佛教生态思想为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佛教生态思想主张“同体大悲”,推及至自然万物、芸芸众生,要求“不杀生”“放生”“素食”等,体现了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救济众生的慈悲精神。不仅如此,佛教寺庙泛称“丛林”,常建在山高地僻、林深木茂之处,僧俗以植树造林作为广施福田的法门,有着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
清代贵阳、遵义、安顺一带汉族较多,信奉佛教者也众多。僧俗建丛林,不杀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弘福寺第四任住持惺慧在黔灵山养鹤驯鹿,广植名花树木,并向官府呈请严禁人、牛践踏山林。为此,官府特立两块“护法碑”。安顺古刹圆通寺山林清幽,通达禅意。明代以降,铜仁佛教盛极一时,寺庙遍布其地。梵净山为佛教名山和弥勒道场,历代建有多所寺庙,仅主峰山麓就有“四十八大脚庵”。在佛教浸染下,贵阳、遵义、安顺等地汉族信奉“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不杀生”,常“放生”,多素食,反对为了口腹之欲而随意捕杀青蛙、燕子、喜鹊、乌鸦、锦鸡等野生动物的行为。
黔东南苗族、侗族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也接受了外来佛教,但却以本地文化为基础。清代剑河、锦屏、玉屏、台江、施秉等地均建有寺庙,许多苗族村寨也建有小庙,供奉观音菩萨,当人生病尤其是孩子生病时,乡民都要祈求观音菩萨祛病消灾。在丹寨,“男子头戴狐尾,披发于后,最喜敬弥勒佛,每逢三月三日,男妇老幼各携什物供佛,欢歌三日,不食烟火”[2]278。在不少信奉佛教的苗族地区,忌抓青蛙、癞蛤蟆,忌射燕子,忌杀狗,忌打鱼超过三网。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以降,贵州各民族对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包,出现民间信仰与儒释道杂糅并“敬”的独特现象,这对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成多有影响。譬如,黔北汉族、仡佬族在古树下、巨石边、山垭口设立“山王菩萨庙”,“山王”是民间神祇,“菩萨”则是佛教大士,二者联名则是多神合一,共同发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作用。显然,“多元会聚,和而不同”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鲜明特征,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与多民族文化共存融合,生态文化与民族文化、山地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了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亮丽底色。
二、生态、生活和生产相融共生为一个整体
与现代社会把生活、生产和生态相分离不同,贵州先民坚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在一定范围内实现高效生产、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的有机统一。在他们看来,生产高效则乡民富裕,生态优美则环境宜人,二者兼顾则生活美好,生活、生产和生态是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
(一)生产实践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在贵州先民看来,优美生态与高效生产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生态是保障,高效的农林生产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产是基础,合理的农林生产方式又有助于维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由此,必须坚持在发展生产中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中发展生产,实现生产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侗族、苗族创造的“混林/混农”生产方式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得到较好记载的人类“混林/混农”的生态文化。清水江流域山多田少,林粮争地矛盾突出。为克服这一困境,早在明代万历年间,侗族和苗族乡民便创造了“开坎砌田,挖山栽杉”的山田互补、林粮间作、农林结合的生产方式。混林作业既有利于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系统,又能解决农林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真正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侗族建立了“稻豆兼种”“稻鸭鱼共生”的立体复合生态农业。在稻田里,水稻为鱼类遮光挡阴和提供有机物,而鱼类通过搅动增氧、吞食害虫和排便肥田以促进水稻生长,雏鸭能够除去害虫和杂草,种植在田埂上的黄豆则固化淤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能够实现所有物种的自我发展、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做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为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范例。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因地制宜从事农业生产,缓解了当地石漠化区域生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兼顾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众所周知,黔西南石漠化严重,常伴有水土流失、生态多样性降低等生态灾难。为了克服石漠化,当地少数民族乡民统筹布局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在贫瘠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地种植耐旱的苞谷,或者在低海拔地区的石旮旯种植花椒,或者在中海拔地区的石旮旯种植金银花,做到石尽其用、点石成金。望谟县麻山地区苗族乡民种植多种耐旱作物可以实现作物的优势互补,种植多种作物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种植耐旱作物可以克服供水不足、土壤涵养水分能力差的弱点。[5]
安顺西秀区鲍屯村将水利工程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生产与生态高度融合的优美环境。源自徽州的明代鲍屯汉族移民受到徽州水口园林文化的影响,根据地形和水利对村寨布局和引水方式进行了周密设计。鲍屯先民在三铺村流进鲍屯的河道处构筑了一道既可拦水灌溉又可泄放洪水的拦河坝——水仓坝,采用“鱼嘴分流”的方式在此形成三个河道:一部分河水通过河坝向下游流走,这是古河道;一部分河水通过水渠流经碾房和田坝;一部分河水通过人工河道流经鲍屯村前地块,最终三部分河水在回龙坝汇合。每条河道又包含若干小渠道和蓄水坝,使不同高度的田地都能得到充分的灌溉,形成“一道坝、一条沟、一片田”“十道水坝,十座碾房”的黔中江南水乡景观。鲍屯完善的灌排系统,保证了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兼顾排污和防洪,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水利条件。可以说,鲍屯村水利工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贵州样板。
更为重要的是,贵州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只有处理好生产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才能实现生产与生态相融共生。苗族先民认为:“鸟多巢难容,人多地难纳,砍树吃光叶,砍藤吸光汁,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拍手无法子,顿脚无计策,商量去涉水,商议去跋山,寻足食地方,觅丰衣处所。”[6]苗族是这样,侗族也是如此。黎平县地扪侗寨古歌唱道:“人口发展落满寨,又愁屋坐又愁粮吃,田地越来越嫌少,祖公商议分出去。”[7]这反映了地扪侗寨的历史演变和生态观念。布依族,旧称“仲家”“水户”,其人口分布为“小聚居”,其村寨大多傍水而建,就依据其种植水稻的生产方式和追求良好生态的选址方式之间相互协调的生存理念。
(二)生活实践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在贵州先民看来,优美生态是追求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优美生态与美好生活相得益彰、息息相关。离开了良好生态,美好生活无从谈起;没有良好生态,美好生活难以为继。
黔东南和黔南一带苗族、侗族、水族、壮族、瑶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生态宜居,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大多选择背风、依山、临水、靠近耕地的地方居住。他们建造房屋尽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其干栏式木建筑具有通风透气、冬暖夏凉等特点。苗族认为,作为生活空间,村寨应“藏风聚气”,不准葬阴地、架桥梁、开田地,而要蓄养树木,不准砍伐。为了营造良好的风水景观,苗族尽力在村寨的“后龙”和“水口”等处培植风水林或者风景林。苗族吊脚楼建造在斜坡之上,沿山布局,顺应地形,采用架空、悬挑、叠落、掉层、错层、分层、镶嵌、跨越、附岩、倚台等方法,既不占用宝贵的坝子和稻田,又可减少开挖土方对地表的破坏,形成了“占天不占地”“天平地不平”“天地均不平”的剖面,很好地做到了顺应自然。侗族村寨约80%以上属于山麓河岸型[8],其选址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光热充足,强调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体现了侗族的生态智慧和主观努力。
黔北地区的仡佬人家,房前屋后竹木葱茏,以木板搭建为楼,屋面覆盖青瓦,四周安装木板,如果是篾条墙、篱笆墙,则粉刷白灰,与当地环境浑然一体。务川县龙潭村是典型的仡佬族村寨,已有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其自然布局为“靠山而居,石林掩映”,三面环山,一面临潭。当地民居没有统一朝向,似乎杂乱无章,实为地势所限。这一带为喀斯特岩溶地貌,即所谓“岩旮旯”,在此修建房屋只能“见缝插针”。各家以石板巷连接,房屋沿山势拾级而上。当地民居多为三合院,每家每户相当规整,一般一间正房两边厢房,中间是石院坝,外围是石垣墙,形成封闭式的宽敞院落。垣墙多以片毛石垒砌,间以方整石砌筑,形成条条“麦穗纹”。当地下水道的处理特别科学合理,以“阴沟”排除污水,以“阳沟”疏导雨水,居住理念极为超前。
在贵阳、安顺一带的布依族和汉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从岩层上剥落出一层一层的薄石板,薄者用作瓦片,厚者代替砖块,高低叠加,错落有致,形成一个石头构筑的世界。不少布依族村寨喜欢使用裁切得比较工整的鳞状石面板,每块石板的厚度为二厘米左右,像瓦片一样从高向低叠铺,层次分明,井井有条。石板在屋顶形成天然的弧线,利于排水,而不必像瓦片屋顶那样留出排水沟。镇宁县、平坝县、关岭县、西秀区和花溪区一带布依族和汉族屯堡民居,多以石材为主体建构:除椽子、楼枕、门窗和神龛等处使用木材之外,从顶盖、外墙、内壁到门廊、院坝、巷道,用一色青石造就。乡民们用碎石砌成围墙,区分了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石板房冬暖夏凉,不惧水火,不藏鸟虫,坚固耐用,只是采光较差。这种非常环保而又节俭的建筑方式,体现了布依族人和汉族移民“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三、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往往通过显性规约和隐性习俗得以维系
长期以来,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往往外化为简单且容易操作的显性规约,具体体现在官府公告,少数民族的贾理、榔规、款约以及各地村寨的乡规民约中。这些显性规约生于本土,成于民间,一直伴随乡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极强的认同感维系着一方水土的生态治理秩序。
(一)显性规约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黔东南苗族有着通过贾理、议榔并“立石”为记来建立生态制度的悠久传统。“贾理”是苗族传统习惯法的说理依据。“贾”是处理自然万物关系的法则,而“理”则是调解纠纷时根据“贾”衍生出的辩论和判词。在此基础上,苗族寨老或者理老根据“贾理”共同议榔,并“栽岩”“立石”“刻碑”为记,成为当地习惯法。一个典型事例是,锦屏县苗族文斗村有涉及林业生产、生态保护等内容的古代碑刻100多通。正是借助于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通过显性规约构建了生态产权、因地制宜、集体协商、有效监督、分级制裁、解决冲突、组织认可等机制,当地乡民持续数百年对山林资源成功实行了自主治理和有效保护。其生态规约的显著特点是,“承诺与监督在策略上是相连接的,监督不仅对监督者产生了私人利益,也为其他人带来了共同利益”[9]。
与苗族榔规类似,黔东南侗族款约是习惯法口头传承的一种形式,是侗族传统生态文化代代相承的“法律保障”。历史上,侗族有“款”无“官”,结款自治,联款自卫。为了维护款约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每次款组织协商之后,乡民们都会在侗族款组织的议事场所——款坪中“栽岩”,后来逐渐演变为立碑刻字,以保持款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每逢农闲季节,全体乡民聚集在款坪,聆听款首诵念款约,提醒乡民们不要忘记款约,是谓“说款”。如果有人违反了侗族款约,款首立即组织全体乡民召开宣判大会,是谓“开款”。在“开款”中,全体乡民根据款约和具体情节,充分讨论,提出建议,最后由款首进行民主集中,给予违反生态保护款约的人以应有的惩罚。
在黔南水族地区,以“翁”“洞”“水”为基层组织拟订乡规民约,以榔规碑约的形式来确立生态制度比较常见。黔南都匀市套头一带近百个村寨公立的乡禁碑较具有代表性,其中规定不准损毁稻田用作安葬地。相传,立碑时曾召集百余寨老聚会,宰牛杀马,发誓共同遵守所立条款,对违反者罚银,严重者将其驱逐。水族村寨依山而建、沿河分布,立有众多井泉碑,一些井泉碑用水文字书写,碑上刻有梅竹、兰菊、松柏、龙凤、鲤鱼等图案,碑约明确要求乡民加强水源保护、确保井水水质、合理利用井水,对破坏古井、污染井水的行为进行劝阻和惩罚。
黔西南布依族信奉“山管山兮水管水,山管人丁水管财”,注重通过共同协商制定乡规民约保护山林川泽,兴义市绿荫村“永垂不朽碑”和水淹凼村四楞碑、兴仁县曾家庄“禁约总碑”、安龙县阿能寨公议碑和谨白碑、贞丰县长贡村护林碑和必可村“众议坟山禁砍树木碑”以及册享县马黑村“永垂千古碑”、乃言村乡规碑和秧佑村乡规碑等便是极佳的历史见证。
在贵阳、遵义、安顺、铜仁等汉族为主、多民族杂居地区,生态保护规约官立和民立并重。明清两代,贵阳把“严禁砍伐竹木,以培山林”作为官府要事。黔灵山护法碑记载:“山内一切竹木,务须任其长养,勿得作践砍伐。倘有差役等谎称官用及奸民等公然砍取,并游人等顺便攀折,许寺僧扭禀地方官,先行枷号山前示众,从重究办。”[10]在安顺一带,各民族先民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物为化碑,制定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相关规约。在西秀区鲍屯村,汉族乡民公议立碑规定:“禁止毒鱼挖坝,不准猎鹰打鱼、洗澡,不准赶罾、赶鱼,违者罚银一两二钱。”[11]铜仁一带的生态保护规约常常加持官府的权威印记,通过省、府、县授权,具有明显的公共约束力和法律强制性。明清两代,官府先后在梵净山立下数块禁止砍伐山林的石碑,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梵净山赐敕碑”“梵净山禁树碑”“严禁采伐山林碑”“梵净山汪家沟禁砍林木碑”等。
(二)隐性习俗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生态制度既通过官府公告、乡规民约等得以彰显,也潜存于各种习俗和禁忌之中,口耳相传,潜移默化,具有小地域范围内的规范性、实效性和稳定性。
黔东南、黔南一带少数民族有义务植树造林的习俗。每年农历二至三月,苗族、侗族和水族都要过“买树秧节”“讨树秧节”。20世纪60年代之前,镇远县涌溪一带苗族未婚男女则互换桃李等果树苗作为爱情信物。招龙节是剑河县苗族植树造林的节日。雷山县苗族举行“招龙谢土”仪式,每人要种上一棵树。在锦屏县三江等村寨有“植春树”的习俗,每年开春乡民习惯上山开荒、植树造林。特别是喜得贵子或者大病痊愈的人家,每逢春天便自发到村寨后龙山、水口、路口、桥头等种植几株常青树木,以修积阴功和德行,替家人消灾解难。此外,在清水江流域尤其是锦屏县、天柱县等地有栽培“女儿杉”的习俗,黔东北土家族也有栽“喜树”的习俗。一句话,植树造林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乡民的美好追求和情感寄托。
贵州各地各民族有崇敬古树、爱护树木的习俗。黔东南苗族、侗族普遍崇拜古树和大树,村寨一般都有一片风水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破坏,因为它是保护全村寨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神林”。瑶族祖居山林,与白云为伴,对于古树、巨树、怪树和风景树,敬若神灵,从不轻易触摸,更不敢随意砍伐。在遵义、安顺一带,民间有为神树“挂红”的习俗,将一段红布挂在树干上,树下设神龛,每到逢年过节人们都要烧香祭拜。每年正月十五,土家族有“喂树粑”的习俗,孩子们端起粑粑、豆腐、熟肉等,来到果树下,拿起斧头在树上砍一条缝,然后往缝里塞入一些粑粑和好菜,一小孩问果树“结不结”“甜不甜”,另一小孩则对答“结得早”“熟得快”“好清甜”等等。与之类似,部分仡佬族支系也有“喂树”习俗。每年吃了年饭之后,仡佬族人要为房前屋后的果树“喂食”饭菜,让树也过上“好年”。在这一砍一饭、一问一答中,彰显了仡佬族人崇敬树木、企盼丰收的淳朴愿望。
贵州多地苗族、侗族、水族、土家族有“打草标”的习俗,即用芭茅草、芒冬草或者稻草等打成圆结、田螺或者箭头等形状的“山标”,并插在特定物品或者地块上,表示“禁止入内”,或者“物已有主”,或者“驱魔镇邪”,或者“祭拜神灵”,或者“充当钱币”,有着标记生态产权和加强生态保护的多重意蕴。在村寨边、河岸边和水井边,当人们看到这种“草标”,就知道不能进入此地砍伐。在锦屏县苗族文斗村周边,凡手腕粗以下的小树都打有草标。这种草标具有神圣的约束力。凡打有草标的树木,从来无人去故意损坏。此外,布依族人在平整稻田、播撒谷种之后,往往在稻田中插上若干小树枝作为标识。这个标识的含义是,此田已经播撒谷种,严禁牛马、鸭鹅践踏。小树枝作为标识,其含义依靠乡民口耳相传进行解释和传承,乡民看到这种约定俗成的标识,都能自觉遵守。
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壮族、仫佬族等均有开展群众性消防活动的习俗。有的苗族、侗族村寨不管是否发生火灾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扫寨”,有的几年举行一次,大体上在每年十一月。各村寨在发生火灾后必须“扫寨”。布依族特别重视防火,每年三月三、六月六都要举行“扫火星”仪式,在由寨老宣布的村规民约中,就有要求各家各户教育孩子不要玩火的内容。贵州壮族的“退火殃”,也叫“送火神”。每年深秋时节,人们收割完毕,便选日子“送火神”。每年正月第二天,仫佬族举办“打保寨”活动,每户人家出资几元钱,买些食物“打平伙”。领头师傅带上一只鸡和一只鸭,在全寨内扫寨。当天,各家各户均要对房前屋后清理一番,开展卫生大扫除,把柴草整齐堆放,将屋内火塘的火引全部灭掉。“打保寨”相当于一次卫生意识和用火安全教育,这对全村寨每个人都起到了消防安全教育的普及作用。
贵州各地各民族都有爱护动物的习俗。在很多苗族地区,不允许任何人随意打骂家养的狗,凡逢年过节,主人必以好肉给狗吃一顿。侗族禁止伤害鸟类和蜘蛛,禁止捕食青蛙和蛇。居住在贵州麻江、凯里、黄平、福泉一带的仫佬族,以牛为伴,视牛为友,爱牛如命,他们有两条独特的习俗:一是不杀牛,二是有牛王节。铜仁一带土家族有大年初一祭祀之后听鸟语、爱护鸟的习俗。在土家族人看来,每一种鸟管理一种庄稼。任何鸟叫都意味着喜庆吉祥,就怕没有鸟叫。在黔北,汉族人家的堂屋几乎都有燕子窝,有的人家甚至有2—3个。这些燕子窝有的是燕子飞进人家自己搭建,有的是房主先做好框架等待燕子入驻。燕子们自由地飞来飞去,哪怕燕子把家里弄得遍地鸟粪,乡民们也不会驱赶燕子。从小时候起,父母就告诉孩子不要驱赶进家的燕子,因为燕子进家做窝是一种吉兆。显然,这种习俗对益鸟的保护比明文规定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更加具体、更加生动和更加有效。
四、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主要通过口头叙事方式得以传承
由于多数贵州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独立文字,其生态观念、生态知识和生态技能的传承只能依靠世代口耳相传。对于没有文字或者很少使用文字的侗族、苗族、土家族等贵州少数民族来说,人人爱唱歌,事事有歌唱,通过民间口头流传的古歌、神话、史诗、传说、民歌、巫辞、理辞等传承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知识。
(一)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叙事
“汉家有文靠记载,侗家无文靠口传。”对于侗族来说,“饭养身,歌养心”,唱歌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人人爱唱歌,处处有歌,事事有歌,歌中掺杂着大量生态叙事。侗族大歌《人定胜天此话错》唱道:“人定胜天此话错,天恶地怒人难活。天地人和乐相处,客莫欺主要记住……别把山水撕破碎,百孔千疮也泪落。多给山河添锦绣,少让人间受灾磨。”[12]92诸如此类的生态认知融入侗族乡民的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不仅如此,侗族地区的生态碑刻注重碑文的口语化和叙事化,符合乡民的语言习惯,符合乡民的判断力和领悟力,能够很好地发挥规范和约束作用。
苗族认为,万物有灵,物我平等,人与万物之间可以通过史诗、古歌、巫辞、理辞等口头叙事形式进行沟通,从而对自然万物产生敬畏之心,进而生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朴素情感。在苗族地区,“贾教地方,歌教村庄”,传唱着丰富的生态知识。苗族理辞唱道:“一年一季推一季,一岁一月推一月。来到了暖季,上到了三月,水里鱼儿游,坡上草木生,蕨菜遮山岭,蕺菜绿山冲,山岭有衣穿,山冲得被盖,山岭就秀美,山坡才秀丽。灰鹤飞蓝天,鸽子来土边,燕子飞仓脊,家燕落屋梁,浑水进田里,火种到土边。水田使钉耙,坡地用挖锄,塌处把泥撮,垮处去砌好,粪堆坪子晒,种播到地里。”[3]8-12这种极富韵律、通俗易懂、易学好记的生态叙事唱诵起来朗朗上口,为苗族乡民喜闻乐见,便于传唱、传播和传承。
布依族传播、传承和扩展生态文化尽量使用口头叙事,做到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觉。作为布依族“百科全书”式的古老文献,摩经具有语言质朴、排比对仗、韵味琅琅等特点,其中蕴含不少言简意赅、记忆犹新的生态观念。《嘱咐词》说道:“三月做地里活,四月做田里活,妻约夫早起,夫约妻早起。”不仅如此,布依族民歌更是把传唱生态知识和生态技能作为重要主题之一。荔波一带布依族的《十一月生产歌》唱道:
正月不出门,在家做织活,多织土花布,织花布祭母。到了二月春,赶紧把地整,鸟欢叫叽喳,请花园保种。三月野菜生,找黑猪来养,满厩肥壮壮,等花园来尝。四月到立夏,赶紧撒匀秧,多撒粘稻种,春来把酒酿。五月暖洋洋,筑塘把鱼养,多养点鲤鱼,等母神来尝。到了六月天,造水车抽水,发蔸苗又壮,糥饭祭谷神。七月到立秋,找肥猪来杀,做肉馅肉粑,等共园来拿,八月谷子黄,人人打谷忙,要新米煮饭,等花园来尝。九月米到家,各家把酒酿,新米或旧米,酿酒等花园。十月到立冬,买坛来腌肉,新坛或旧坛,腌肉等花园。十一月隆冬,人们上山去,要柴与割草,杀猪祭祖宗。[13]
白云区布依族民歌唱道:“原始森林拼命砍,树木砍尽挖草坡;树根草根全挖尽,从此清河变黄河;年年时逢下大雨,泥沙随水到处踔;好田好水全冲走,剩下石头光坡坡;君问江河有何苦,江河有苦难得说;上游河山荒了废,下游泥沙塞了河。”[14]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贵州土家族其传统生态文化大多保存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类叙事中。乌江流域土家族在稻田或者苞谷地锄草时,主人往往会请很多亲友或者邻居来帮忙,并专门安排几个能说会道的歌师,手执锣鼓,唱起富于韵律、歌词有趣的打闹歌、采茶歌、农事歌、扯白歌等。清代土家族文人彭施铎所写的竹枝词对打闹歌有如下生动描述:“栽秧薅草鸣锣鼓,男男女女满山坡。背上儿放荫凉地,男叫歌来女接歌。”[15]这种歌词有固定模式,也可随兴而作,其内容涉及农事、狩猎、生活等,因地因人而异。譬如,在思南县一带,就有《大号》《小号》《太阳号》《送郎号》等,有长有短,共有四十几种曲牌。后来,这种习俗逐渐融入生产劳动中,一人敲锣,一人打鼓,众人唱歌,相互响应,你追我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很好地干完农活,也很好地传承了生态知识。
彝族生活在山区中,依然保留了青山绿水,其中彝族古歌对生态观念、生态知识和生态技能的传承作用不可小觑。彝族古歌多采取五言体结构,注重押韵,大量运用比喻、类比、拟人、夸张、排比、对仗等表现手法,给人以极大的接受度和强烈的感染力。彝族古歌唱道:“山头啊山头,以什么为发?以松柏为发。山腰啊山腰,什么为腰带?藤蔓为腰带。山脚啊山脚,什么做鞋穿?田地做鞋穿。”[16]在这里,把松柏比喻为山的头发,把藤蔓比喻为山的腰带,把田地比喻为山的鞋子,既形象又生动,很好地诠释了生态要素的重要内容。又如,“因为地方不长树,鸟儿失去栖身处。因为地方无水流,鸭儿失去水凫处。”[17]387“齐整的黄松,成排的青松,中间是杜鹃。黄松未开时,青松未开时,杜鹃开三回。给黄松福分,给青松福分。齐整的燕麦,成行的小麦,茅草在中间。燕麦未开时,小麦未开时,茅草开三回。送燕麦福分,送小麦福分。”[17]429-430这些歌词是彝族先民对树木、作物、虫子、鸟兽和山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朴素生态认知,反映了彝族先民主动适应生态环境、积极维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智慧。
水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融汇在日常生活交流的水语中。无论是巫祝鬼师还是黎民百姓,均能娴熟掌握和运用民歌、格言、俗语、歇后语等口头叙事,去叙述本民族的生态观念、生态知识和生态技能。三都县水族民歌唱道:“吃山不养山,聚宝盆会干”“杉木树砍倒主干,老桩兜还发嫩芽”。同时,水族注重对生态知识、生态技能的总结提炼并使之口语化。水族俗语说:“云打架,冰雹下”“月戴笠,天下雨”“谷雨不雨,种稻少米”“立夏不下,犁耙高挂”“立春若下雨,清明不缺撒秧水”“稻田要好,水肥要饱”“煮菜要盐,种田要粪”。[12]191-192由于民歌、格言、俗语、歇后语等口头叙事均是民间所熟悉的常用的精炼短语,极大增强了水族生态叙事的特色和效果。
(二)贵州汉族的生态叙事
贵州汉族也通过谚语、歇后语、顺口溜等口头叙事方式来传承生态技能、生态知识和生态智慧。贵阳、遵义、安顺一带汉族了解“二十四节气”,结合当地气候和实践经验,编出许多谚语,用以指导农林生产,更好地促进生产与生态相协调。譬如:春天来了,“立春后断霜,插柳正相当”“雨水前后,种瓜种豆”“过了惊蛰节,耕田不停歇”“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点瓜豆后插秧”;夏天到了,“立夏小满正插秧,秋前秋后遍地黄”“芒种芒种,样样要种”“夏至栽苕,一窝一瓢”“夏至不挖蒜,定在泥中烂”“小暑前,草拔完”“大暑不收禾,一天脱一箩”;到了秋天,“白露打核桃,秋分下枣梨”;至于冬天,“寒露到立冬,翻地冻死虫”“寒露霜降,胡豆豌豆把坡上”“霜降点麦,不消问得”“冬至萝卜夏至姜”;等等。在民国时期《续修安顺府志》中,安顺汉族农谚对四时节令、春耕秋收等都有所涉及。譬如:
谷雨要淋,清明要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不怕重阳十三雨,只怕立冬一天睛。芒种打田不坐水,夏至栽秧少一腿。八月大,萝卜白菜卖肉价;八月小,萝卜白菜当粪草。四月八,冻死老母鸭。吃了五月粽,才把棉衣送。有雨四角亮,无雨顶上光。云走东,一场空;云走西,披蓑衣;云走南,雨成团;云走北,雨不得。[18]
这些活态的生态叙事都是经验之谈,具有浓厚的乡土气和较强的感染力,娓娓动听,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对本土生态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纵观古老的贵州大地,虽然“生态文明”“生态建设”等等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广为人知的概念和词汇,但贵州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了丰厚的生态理念、生态认知、生态技能、生态智慧。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生态文化资源全都体现在贵州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的生存、生产和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它构成了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最重要的内涵,也为今后对这笔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起点,更为书写生态文明建设的贵州篇章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