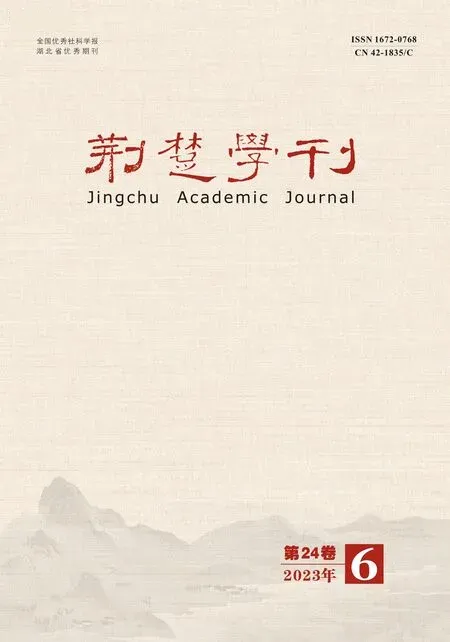电影表演的自由意志
王雪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韩新媒体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自由意志之谱系源流
“自由意志” 是西方学界一个极为古老的概念, 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的先哲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的概念,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在他那里,行善以知善为基础,知善必行善。 知善属于理性领域,行善则属于意志领域,假若说‘知善必行善’能够成立,就必先假定人的理性可以支配意志。 ”[1]到了柏拉图那里,人的意志(激情)则联络着理性与感性(欲望),若要意志正确地行事,就必须要臣服于理性。 亚里士多德则有别于苏格拉底的观点,将“知”与“行”做了彻底的分离,知善不一定会行善,这样就将自由意志重新限定为人的精神活动的层面。 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共性在于将“意志”与“自由”的问题大体放在哲学与伦理学的范畴内探讨,这也为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自由意志成为一种神学伦理问题奠定了基础。
如奥古斯丁、帕拉纠、伊拉斯谟、马丁·路德都对自由意志做出了相应的阐释。 譬如伊拉斯谟就曾谈到:“假如意志是不自由的, 就不能把罪归因于人,因为意志若非自愿,罪就不能成为罪。 ”[1]
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在其著作《道德及其形而上学原理》 中提出符合理性的意志则可称之为自由意志, 而斯宾诺莎则将自由意志比作一块自己决定了飞行轨迹的石头, 从而断然否认了自由意志的存在。进入现代哲学以来,柏格森有感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混乱争斗,在1889 年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对种种错误的观点予以驳斥, 他还创造性地指出:“这是由于整个的人格可以存在于一个单一的意识状态里, 只要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些状态中去把它选择出来。 这个内在状态的外部表现恰恰是所谓的自由动作, 因为只有自我是这动作的创造者, 又因为这动作把整个自我表示出来。”[2]这样就将自由意志与自由动作重新结合了起来。
到了萨特那里,“自由意志” 又重新弥合了“知”与“行”的割裂。在萨特看来,人毫无疑问是自由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绝对自由”(absolute freedom)的:“人是自由的,而且不得不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指不受外在束缚之谓, 也不是作为道德必要预设的意志自由, 萨特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的, 只因他责无旁贷地必须选择自己的未来。”[3]萨特认为人的意识活动的“超越性”指引着我们必须自由地选择行动, 人不能托辞过去的处境而放弃自由的选择。
总的看来, 对于自由意志的探讨仍然大体集中在哲学与伦理学的范畴之中,传统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争论分歧在于:人的意志是否可以自由地决定,从而为自己的行动负有责任?在亨利·柏格森看来, 人的自由意志毫无疑问是可能的, 如果在人意识的能动性纳入时间性的考量之中,所有“物理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一种人为的隐喻, 人的能动性乃至精神是不能被结构化与理论化的, 意志的绝对自由使得人的行动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在表演领域谈论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则变成了:人的意志是否可以足够自由,从而创造出自由的表演(行动),为自己的表演负有责任?对表演活动负责意味着,人是表演活动的作者:我表演,因而我对表演的一切(动机、意愿、过程、效果)拥有所有权,我对表演负责。在艺术范畴内(包括表演)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还隐含着一种假设: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味着创作者拥有完全的主观能动性, 他/她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他/她的作品始终朝着无限的可能性而敞开。
二、电影表演自由意志之涵盖
对于表演艺术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 既往的表演理论家们则有着不同的观点。 譬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没有明确地谈过自由意志的问题,但他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无意志但却自由。他曾经谈到:“因为,舞台上最好的效果就是演员完全随着剧情走,完全不受意志控制,演员在体验这个角色本身,他不用刻意地想他该如何表达、他该如何做动作,而是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表演,凭着直觉,下意识地表演。 ”[4]15斯坦尼道出了表演艺术的吊诡之处:即最高级的表演是自由的表演,而最自由的表演却是无意识的表演。 他随即说:“不可否认,这(无意识动作)需要极其复杂的创作能力。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具有意识的控制力,更需要我们的潜意识,不能随意为之。 ”[4]15在斯坦尼那里,与其称之为演员的自由意志,倒不如说是演员在寻找自由状态, 但斯坦尼也并未否认意志对于演员控制表演的意义。 另外一位表演理论大师布莱希特则有着不同的观点, 布莱希特没有直接提及自由意志, 但他却明白地指出了意志对于演员的重要性:“演员应当像一个很好的技术员那样掌握他的演技,就像一个精确的司机,他能很好地驾驶他的汽车,没有声响地漂亮地开动它,而且不慌不忙地嚼着他的口香糖。”[5]布莱希特强调演员需要有创造力,但却反对演员过分地投入感情,相反, 演员要保有一种反思的审慎:“演员若想打动观众,他就必须不要轻易被感动。”总的说来,布莱希特本质上还是赞成自由意志的, 他认同演员是一门兼具技巧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职业, 但他更多地希望自由意志是一种更理性的、反思性的、不那么过火的意志状态。 另一位重要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曾谈到:“关于现实主义的表演体系, 我认为在京剧改革上是非常重要的,上面说过:活的布景就在演员身上, 因此演员的艺术创造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许多老前辈们,虽然不知道现实主义的名词,但是他们的表演,恰符合这个道理,他们对钻研戏情戏理, 体会人物性格是下了极深的工夫的。 ”[6]钻研人物戏情,自然也离开不了演员本身的自由体悟。
中国学者彭万荣则试图从戏剧本源去谈论自由意志,他认为,戏剧动辄谈论冲突,但冲突又因何而来? 他指出:“冲突源于个体的自由意志遭遇挫折之后的抵抗,换言之,是个体之间自由意志的较量与对峙……自由意志就是人与自我和外界长久的刺激反应形成的心理状态和意识状态。 ”[7]100彭万荣先生显著的贡献是, 他将自由意志视作戏剧中的人的一种状态,从而统一了演员表演、角色塑造、观众审美这三个维度,戏剧活动中的任何一环,都离不开自由意志的参与。因为自由意志是人与一切事物相遇前后的必然存在:“它产生于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长久的刺激与反应的绵延中,每一次刺激与反应都在累积、修改和磨合出独特的人格结构, 人的自由意志会通过语言和行动把这种人格结构表现出来。 ”[7]102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 阐述戏剧表演中的自由意志相对较为容易被人接受, 而电影表演中的自由意志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这是源于戏剧与电影是不同的媒介, 不同媒介下的表演活动其自然特性也不同。首先,戏剧是即时性的表演活动,电影则是非即时性的表演记录。由于电影经受了摄影机记录以及剪辑重组的二度创作,我们在谈及电影表演的自由意志时, 亦需得先明确表演者是谁,不然,自由意志也就无从谈起。其次,戏剧是连续的、完整的表演活动,电影则是非连续的、 组装的表演创造。 戏剧由于其连续性与完整性,实则赋予了演员一种完整的时间体验。彭万荣认为,柏格森关于“绵延”的时间意识正是自由意志的本质特征:“自由意志就是自由动作在绵延状态里的不断展现。 柏格森这个自由意志最接近戏剧中的人物自由动作的状态, 人物的行动就是当下戏剧情境中的自由活动。 ”[7]102但在电影中,我们很难说某个演员有这样一种“绵延”般的时间体验,演员的表演被切碎,其表演状态始终处于置身角色或回归现实的切换之中, 演员的自由意志也只能是断断续续的。最后,戏剧是高度演员主体性的,而电影却绝不能说是演员作为主体的艺术。在戏剧中,无论编剧如何撰写剧本,导演如何训练以及调度,只要演员一登台,他/她就是表演活动的绝对承载者,他/她的动机、意愿、思考与想象对于表演活动的成败起着绝对的影响。而电影则不然,演员绝非唯一的表演主体, 就如同好莱坞一位摄影师曾豪言:“并非演员在表演, 而是摄影机在表演。 ”同样的话,自然剪辑师也可以说:“不是演员在表演,而是剪辑在表演。”由此可见,相较于戏剧的即时性、 连续性与演员主体性为演员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充分的体现空间, 电影表演由于是表演者、媒介与观众三者的共同参与,那么谈论电影表演的自由意志自然也得将表演者与媒介、 观众与媒介同时纳入考量。
三、表演者的自由意志:自我与符号
在讨论电影表演之前, 必须首先阐释电影表演是什么? 事实上,相较于戏剧表演来说,电影表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电影表演经过摄影机”对演员的纪录,再由后期进行剪辑处理,最后被投射在电影院的银幕上被观众观看, 其媒介过程的特殊性必然带来如下问题:(1)电影表演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戏剧表演就是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的行动与呈现, 但我们却不能给予电影表演同样的定义。当银幕上最终呈现的只是一系列运动着的“拟像”,电影表演或许只是观众通过意向活动所虚构的艺术主体,这也即是说:电影表演是银幕影像与观众相遇之后所生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2)电影表演是谁的表演,谁才是电影表演的承载者和所有者?就这个问题来说,很多理论家不假思索地将表演者等同于电影演员。譬如李·斯特拉斯伯格就曾谈到:“为舞台表演与为电影表演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大。”[8]诸如斯特拉斯伯格这类传统的表演理论家是从实践经验的角度上看待电影表演的,在电影表演的历史上,戏剧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很难截然分开, 比如格里菲斯就曾让手底下的演员去丹尼斯·肖恩学校学习舞台表演。 再如李·斯特拉斯伯格于1931 年在纽约成立戏剧组织团体剧院(Group Theatre)直至1948年执掌演员工作室,也曾培训过许多电影明星,如马龙·白兰度、保罗·纽曼、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达斯廷·霍夫曼、杰克·尼科尔森、哈维·凯特尔、詹姆斯·迪恩、玛丽莲·梦露、丹尼斯·霍珀、梅丽尔·斯特里普等鼎鼎大名的明星演员,都曾受到过演员工作室的恩泽与影响。 对于以表演实践为出发点的理论家来说, 电影表演可以当作舞台表演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对待,通过训练,电影演员理解了电影表演的特性, 并由此做出适宜银幕特性的表演。但事实上,这也只能证明一些演员在电影表演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却不能证明演员是电影表演的全部所有者。 譬如一些欧洲的电影导演就排斥演员的主观创造, 费里尼就曾要求马斯楚安尼只是摆出造型而不告诉其用意;罗伯特·德尼罗曾参演过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1900》(Novecento,1976), 他对贝托鲁奇的执导方式也颇有微词:“某些导演告诉你该做些什么,是常见的事。 我和贝尔托卢奇在一起时也有此感觉,他总是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9]在这一类的情况中,导演同样对电影表演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而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诸如库里肖夫、罗伯特·布列松的电影作品里, 演员本身只是被导演任意操弄的模特,人与一把椅子、一只宠物狗没有区别。再比如在当下数字技术大量介入电影创作的情况下,很多影片(比如动画电影)要么根本就不需要真人演员,要么就只把真人当作二度创作的材料,譬如电影《魔戒》系列里安迪·瑟金斯扮演的角色咕噜, 不可否认安迪·瑟金斯的表演异常精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银幕上的角色咕噜与作为演员的安迪·瑟金斯截然不能画作等号。 这也意味着,在数字技术时代的当下,演员与角色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割裂, 电影表演归属于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3)在电影表演不能直接归属于演员之时, 电影表演的自由意志也就成了一个复合性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电影表演视作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活动, 那么电影表演的自由意志也就不是一个仅关乎演员与演员、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的关系, 而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创作共同体的自由意志问题。
这个创作共同体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写”的表演者,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摄影师、剪辑师以及任何一个对电影表演能够施加影响的人, 都可以视作表演者的一部分。那么,当我们谈到表演者的自由意志这个问题时, 我们究竟谈论的是演员本身的自由意志, 还是包含着其他表演者的自由意志的相遇亦或相融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大写”的表演者之中,导演与演员依旧是最重要的一组关系: 演员是银幕呈现的表演影像的承担者,没有演员,也就不可能有表演;另一方面,导演则是表演影像的决定者, 导演决定了演员的表演能不能被纪录、选用乃至剪辑重组,演员的自由意志与导演的自由意志是共同作用于表演活动的。所谓银幕上出现的一切表演, 本质上体现的则是作为角色的个体的存在样式, 以及其存在样式背后的各方自由意志的相互关系。
演员与导演始终是一组博弈的关系, 当演员表演的自由度越大、完整性越高,同时也意味着导演对于表演的参与越少。相反,当导演对于表演的掌控越多,演员的自由度也就大大降低。甚至可以说,电影表演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导演与演员的自由意志角力的过程, 演员自由意志的两极恰恰就是自我与符号。 当演员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自我,并被导演所尊重并保留之时,演员的自由意志也就能够最大程度地释放, 并最终呈现在作品之中。反之,当演员只是被导演视作一种彻彻底底的工具,那么演员也必然会沦为布列松式的模特,这种模特本质上是无主体性的、 高度符号化的表意工具。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在一些表导演者统一(主演和导演为同一人)的电影作品中,演员能够释放最彻底的自由意志, 获得最大程度的创作自由,譬如卓别林、基顿、雅克·塔蒂、周星驰这类导演兼主演皆属此类。 相反,在一些高度商业化、类型化、 动画电影或是借助于动作捕捉技术的数字电影中, 演员的自由意志常常被限制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断然不能说汤姆猫、机器人瓦力、长江七号这些虚拟角色体现的是演员的自由意志,我们至多可以说它们作为角色本身有些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但是,它们同样可以体现创作者的自由意志,即导演、画师以及数字工作者的意志,但最根本的还是体现导演的意志, 导演可以在这些角色上倾注全部的自我, 让其高度符号化的表意过程变成一种创造性的表演活动。我们发现,随着电影数字媒介化的加剧, 电影演员的自由意志越来越被限制, 导演与数字工作者的自由意志则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从无实物表演到虚拟角色表演的发展过程, 本质上也正体现了电影演员自由意志逐渐削减、弱化直至完全隐没的历史。
所以,由于电影是一种高度媒介化的、历史性的艺术形式, 其高度的媒介中介性与异变流动性决定了电影表演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创作。 学者潘家云指出:“一个具有完全主体性、 自由意志的存在物按照自己对美与真的设想, 创造出一个完全符合自己意志的另一个存在物, 并且对自己的造物感到满意, 随后对其进行逐一命名, 使其符号化,这个过程就是创造或创作。 ”[10]电影的媒介特性决定了,无论是演员、导演还是其他参与表演创造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具有完全的主体性,他们带着历史与经验的痕迹形成的自由意志, 在创作的过程中彼此相遇、合作、碰撞、龃龉,在银幕上共同创作出鲜活的角色与栩栩如生的表演现象。
四、观众的自由意志:感知、阐释与创造
在既往的表演研究史中, 常常有一种忽略观众乃至对象化观众的倾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嫡传弟子波列斯拉夫斯基就认为, 演员表演时应当忘记一切, 眼中不该有观众的存在,“在你登台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没有人敢打扰你。正在作画的画家是没有人敢去打扰的,所以如果演员的创作受到了观众的侵扰, 那完全是演员自己的错。 ”[11]方法派的代表人物,同样曾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短暂学习的斯特拉·阿德勒也持类似看法, 她认为演员应该全身心投入舞台构建的情境之中,“在发现自己在担心观众的时候,那是因为你没有被剧本中的世界所吸引。 ”[12]在这些表演理论家的观念里, 演员对自我与情境的高度投入是表演活动的前提, 这并非是说观众不重要,而是潜意识里将观众视作一种干扰表演的、对象化的、不融于表演活动的挑战。另外一些表演理论家则意识到了观众的重要性, 譬如格洛托夫斯基虽然认为“演员的表演技术是戏剧艺术的核心。”但他也同时认为探索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才是戏剧艺术的无限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探索适于每种类型演出及体现形体处理具有决定性的观众与演员间独特的关系。”[13]11格洛托夫斯基将表演视作一种间性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他打破了传统表演研究者们一种既定偏见: 演员的行动是表演的唯一主体,即使观众不存在,演员所处的假定性情境也依旧使得表演成为一种客观事实。
电影表演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电影表演中并不存在一种没有观众目光介入的、 客观存在的行动事实。当我们谈论电影表演的时候,已经预先假定了电影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戏剧舞台的表演活动, 但事实上, 电影上出现的一切都只是影像之流,从客观上来说,电影只是一种运动的流逝,只有当观众参与之后,银幕上的一切才称得上是“运动的幻觉”。 就如同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谈到的,“电影不是一套图像的总和而是一个暂时的格式塔。 ”[14]在他看来,电影是一种整体化的经验感知,观影者通过格式塔抓住电影的某种基本结构,用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将自己抛入电影之中,激发自己对于电影的全部感觉。梅洛·庞蒂所谈论的经验感知,其主体就是作为普遍性的、整体性的、大写的观众。 无论是梅洛·庞蒂、德勒兹、索布切克、维利里奥还是其他的学者,只要谈及电影经验之时,就预先设定了主体作为观众的身份。这也进一步佐证了,相较于戏剧舞台表演,电影表演更加离不开观众经验的介入,没有了观众,压根就不存在我们言语所谈及的电影, 也就更不存在所谓电影表演了。
但在电影经验的研究中, 表演作为一种现象却被惊人地忽略了。 事实上, 如果没有被观众感知、阐释乃至在头脑中虚构创造的表演活动,绝大多数的叙事类电影都不复存在。 波德维尔的“主体/位置”理论暗示着观影者必须在影像中获得一个位置,从而构建起自己的主体身份。但他没有谈及的是,如果观众要获得这种主体性,他就必须借助于表演:(1)他必须将银幕上出现的人的运动影像格式塔化, 从而感知到一种表演的存在;(2)他必须借助于这种表演活动, 从而在影片的叙事层面获得一种主体性, 无论是扮演旁观者或是移情于某个角色;(3)他必须借助自由意志去与剧中人物相遇,这是他理解角色、阐释角色乃至创造角色的前提。
首先,观众需要自由地感知影片中的表演。就这一点来说,决定论者肯定秉持着反对的意见,在决定论者看来, 任何一部影片的象征语言系统实则都已经先决了观众的经验, 影片特定的符码刺激观众得出特定的反应,无论是“缝合效果”还是“间离效果”, 本质上都是被这种语言系统所决定的。 梅洛·庞蒂也部分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电影的视听语言总是对应着人类生理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视听结构。但事实上,虽然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有着相似的视听结构, 但作为个体的观众始终带着个人独有的历史与经验感知电影, 这种基于自我与外界长久的刺激与反应所形成的自由意志,必然使得每个人对电影表演产生不同的感知。不同的观众,基于不同的自由意志,会把握到电影表演的不同结构特征, 产生不同于他人的审美感受,在感受角度、强度以及深度上都大不相同。 譬如在一些恐怖电影中, 有的观众会被剧中的表演吓得魂飞魄散,而有的观众却无动于衷,这是因为不同的观众有着不同的自由意志, 他们哪怕面对同一部影片时, 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刺激反应将引导他们通向不同的电影感知。
其次, 观众需要自由地理解并阐释影片中的表演。 在既往的研究中,基于信息交换的视角,观众理解影片的过程被定义为“解码”过程。 在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里,观众知觉和理解影像中的代码其实是一件事,观众的知觉过程就是一种解码。基于再现的电影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它们‘再现了接收者的感知条件’。 这些观众的感知条件构成了所有文化成员都能分享一些最基本的知觉代码”[15]。 但在具体到每一个观众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观众固然可以分享同样的知觉代码,但是由于个体自由意志的存在,观众的“解码”过程中常常不会那么原封不动地参照创作者的编码设想, 而是往往会在私人经验的参与下, 部分地偏离、甚至拒斥既定的解码进程。自由意志决定了观众在面对同一个表演现象之时, 会产生不同的刺激反应,继而产生不同的好恶、不同的理解路径以及不同的阐释结果。另一点,对于电影表演的阐释既是一个当下的即时理解, 同时也是一个事后的“再编码”过程。 当我们阐释一部电影的表演活动之时, 实际上谈论的是我们记忆中对电影表演的再现, 是观众的自我与回忆相遇后自由意志的再创造。 同时,由于电影是高度媒介化的艺术,这也使得观众在阐释戏剧舞台表演与阐释电影表演时是截然不同的,在戏剧舞台表演中,表演对象相对更容易确定, 而电影表演却是多重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个场域,因此,观众的自由意志在阐释过程要扮演的角色就更为重要, 也为他阐释电影表演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与可能。
最后, 观众需要自由地参与电影表演的创造活动。在格洛托夫斯基的理念里,演员与观众构成的关系尤为重要,“演员可以在观众中间演戏,直接和观众接触, 使观众成为剧中的被动角色(例如:我们演出拜伦的《该隐》和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演员可以在观众中间进行各种造型,从而把观众包括在情节结构之中……”[13]10格洛托夫斯基是从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界限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 但是, 电影观众与舞台艺术的观众并不一样, 电影观众天生就是在银幕所构建的表意空间之中的。离开了观众,电影不存在表演,同理,观众的观看, 正是银幕上表演得以创造不可或缺的要素。 甚至可以说, 观众也是电影表演的创造者之一, 如果说演员与导演是从素材出发去创造表演的,那么观众则是从感知、理解与审美出发,从而将银幕上转瞬即逝的人类影像深深地领会、 完形并创造,最终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如果观众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动物, 就如同观看露天电影的猫一般,那么“猫”又岂能把银幕上流逝的运动理解并创造成一种表演呢? 更不用说在数字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当下,在许多3D 电影乃至4D电影中, 观众就在坦坦荡荡地承担着过去本由一部分演员所承担的职能,在那些大量的主观镜头、负视差涌现效果、 快速的镜头运动与转场的画面中,影片中的角色、动作与炮火正是将观众视作表演的“对手”才得以具有表意功能的。 观众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他会如何刺激/反应以回馈影片的叙事, 亦决定了电影表演的效果乃至整部影片审美的评价。
五、结语:走向一种更广阔的自由意志
目前, 电影的制作已经从胶片时代彻底地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时代并不仅仅意味着影像生产的数字化, 更代表着以一种大数据的算法思维介入电影生产的开始,“后现代文化、新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算法共同造就了观众自我意识与情感机能的凋敝。 ”[16]还有学者发出隐忧:“新技术所带来的传播潜力,在资本逻辑的垄断下,可以导致‘算法’霸权与人的本质能力的退化……”[17]在不远的未来,当算法可以自主生产电影之时,银幕上的表演活动亦不再需要演员甚至导演的存在, 那么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就像围棋研究中的“阿尔法狗”一样,它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未来电影的表演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