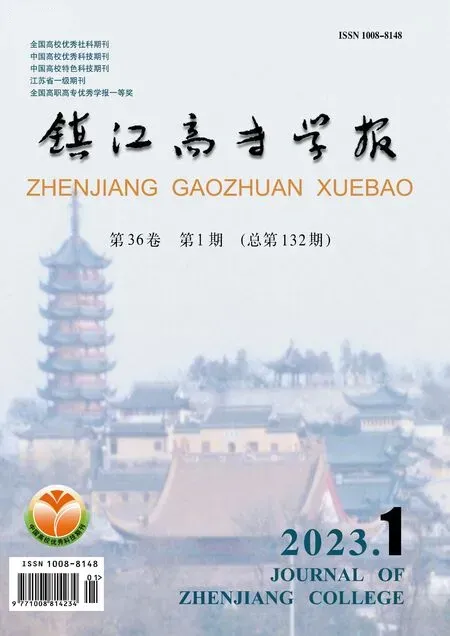吕凤子书风演变概述
房 容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镇江 212028)
吕凤子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美术史论家、画家、书法家。吕凤子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冲击的历史时期。他早年学习西画,后致力于中国传统书画创作与理论研究,主张“中学为体”“折冲中西”“容古纳今”。吕凤子书画艺术是20世纪初“西风东渐”时期传统艺术“变法自强”的成功典范,徐悲鸿称其为“开当代之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
吕凤子的书法成就在民国时期已被充分认可,当代著名书法史学家祝嘉认为“近来书家,仅得三人:四川谢无量先生、浙江马一浮先生、江苏吕凤子先生”[1]121。吕氏书法风格属于碑学范畴,其风格演变主要经历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是吕凤子书法的“取法期”和“蓄势期”,主要受晚清书坛巨匠李瑞清影响,取法金石、碑版,以“平正”为主要特征,表现了对个人风格的初步探索,但尚处实验阶段;第2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此时吕氏书法具有“奇拙”的风貌特征,并“引画入书”,形成了“诸体合一、和而不同”的“凤体书”,在现代书法界独树一帜;第3阶段为新中国建立后,在当时文艺政策的感召下,吕凤子放弃了繁拙的“凤体书”,改以行、楷书体示人,其书风“返璞归真”,但笔墨间仍保留了早年研习碑学所具有的金石气息。吕凤子书风的演变显示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书法艺术审美思潮的变迁,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1 “金石铸基”“融碑纳帖”的早期特征
吕凤子的青少年时代正是碑学大兴时期,康有为称“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言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2]72。碑学兴盛主要得益于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清初以来大量出土的金石、碑刻拓宽了书法家视野,此时出现了金农、郑燮、邓石如、何绍基、吴昌硕、李瑞清、康有为、黄宾虹、曾熙、于右任等一批碑学书法名家。他们推崇钟鼎碑版,痴迷于碑学书法所表现的金石气,追求用笔的苍茫、浑穆、朴拙,在书法美学和艺术实践中与以“二王”为宗的帖学形成强烈对比。清中期,书坛掀起了“崇古尊碑”的新风尚,晚清至民国出现“以碑破帖、碑帖融合”的发展新趋势,近代以来书法因碑学兴盛而呈现中兴气象,这些时代思潮与审美新风尚促进了吕凤子早期书风的形成。
吕凤子的书法由丹阳名家殷墨卿开蒙,后入学两江师范学堂,受教于晚清书坛巨匠李瑞清,与胡小石、李健并称李派三大高足。李瑞清是晚清碑学的主要倡导者,他提出“求篆于金、求分与石”“以器分派”“纳碑入帖”等一系列重要理论,从美学理论与技法实践等方面构建了完整的“李派”金石书法体系。当代书法理论家孙洵认为李派书法“熔铸古今,不偏不倚,至博且精,永开风气,所播深远直至当代”[3]223。李派书法在美学上以“尊碑尚古”为宗,李瑞清曾自述“喜其瑰玮,遂习大篆”“遍临诸铜器铭文,长学两汉碑碣”“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毡墨”[4]76,表现出对碑学的推崇。在取法上,李派“求篆于金、求分与石”,认为研习书法应以篆书为基,尤为推崇大篆金文,力求博采众长。这些观点促成了吕氏书风的形成与演变,影响了吕凤子的早期书法风貌。著名画家顾莲邨曾评价:“凤先生早期书法,颇受梅庵先生的影响,小行楷的风貌,基本相似。”[5]223
吕凤子的诸多作品鲜明体现了上述观点对其早期书风的影响。泰州市博物馆藏有吕凤子在1917年前后节临的《费凤碑》《阳泉使者舍熏炉题字》《李阳冰篆书》《魏李苞阁道题名》《杨淮碑》,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吕凤子在1921年前后节录的《横渠西铭斯二言》,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他早年以金石为宗对不同风格秦汉篆隶的广泛学习;作于1920年前后的《生查子·雨打江南树》、题《赏秋图》款识等,凸显了他对诏版、权量等偏僻书体的取法;1914年撰写的《风景画法》书稿、1921年节录的宋代张载《西铭》句、1929年《中阿空谷联》中“颤掣”的大量运用,体现了李派“方巧古拙”“朴拙雄肆”的金石意趣。可见,吕凤子在早期书法实践中直接延续了李派的取法主张,对金文、诏版、权量、汉魏碑刻、唐人写经等各类金石书法形式均有学习与借鉴,这使其早期书法具有“古朴”“平正”的金石气息,也为日后“诸体合一”的变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吕凤子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书法创作中已出现“多体合一”的变法尝试。此时的“多体合一”以“篆”“隶”书体结合为主,笔法略带行草笔意,字形奇正,变化强烈,于平正中含流动,具有明显装饰意味,表明吕凤子开始尝试“奇拙险绝”的书风。代表作品有1925年的《凤先生画人物画册》题款、1928年的《致韩国钧信札》、1929 年的《王安石词轴》等。这一时期的实践奠定了吕氏书法“诸体合一”“以画入书”的变革方向,可视为吕凤子盛年变法前的“蓄势”阶段。客观上而言,此时作品“奇拙多变”,但整体气息还不够连贯,文字造型的装饰意味稍显浓厚,字体变化也较为突兀,具有鲜明的“美术化”倾向,因而具有明显的实验性。
2 “诸体合一”“和而不同”的鼎盛风貌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吕凤子书法中字形与笔法的“诸体合一”之势愈发明显,这种探索至40年代完全进入“诸体合一”“和而不同”的境界,吕氏书法进入盛年变法期,逐步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后人谓之“凤体书”。所谓“凤体书”,是指吕凤子将篆、隶、行、草诸体杂糅化育而成的一种新书体,既有篆、隶的成分,又有行、草、楷书的笔意[6]133。成熟的“凤体书”笔力强悍老辣,线条遒劲,运笔于涩拙中见流动,结字造型奇拙,章法布白既有传统金文意趣又有现代美术的构成意味。“凤体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2个阶段。
第1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末,以“诸体合一”为主要探索目标。1935年所作的《摹庄子》中行草书体已明显增加,多见以篆隶笔意写行草,气息自然流畅,字形更为和谐统一,笔法上方圆相济,章法布局错杂多姿,较之20年代中期的作品气息更为流畅,显示了“凤体书”的初成样貌。1936年的《摹唐朝名画录》为此时期代表作品之一。早年较为突兀的字体逐步被篆、隶、行、草的调和体所取代,诸体高度融合,笔意互通,气息生动自然,章法上强化金文特征,布白疏松散落,线条苍劲、古朴,已达“诸体合一”之新境。1939年前后所作的《致陈中凡先生信札》、题《堪笑书生心胆怯》款识、题《辛弃疾词意》款识虽非正式书法作品,但章法险绝,结体自然,造型意识显著增强,线条凝重古朴,气息自然流畅,堪称30年代精品之作。
第2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此阶段“凤体书”更为成熟,并加速向“和而不同”的阶段发展。这时期吕氏书法出现众多精品,1943年所作的《凤先生韵语》堪称为代表作品,也是少见的宏大之作。作品内容为吕凤子在入蜀后所作自制诗,显示了其厚重的旧学基础。作品以行草书体为主,篆隶体虽数量减少但仍明显存在,以行草笔意写篆隶字体也更为常见,字形上具有强烈的造型感。吕凤子十分注重文字的造型感,为求文字造型之趣,常打乱原有笔顺“势随字形”,以求“由生则拙”,因而文字呈现图案化的视觉效果。章法上通过巧妙运用“取势”“疏密求变化,让就相迎迓”[7]471,使得字与字之间上下互为牵连、左右相互依靠,作品的整体感较为突出。
属于这一系列风格的作品还有1942年的书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题课徒画稿款识、题《群山写松》款识、题《如此人间图》款识,1943年的题《现代张书旂吕凤子花鸟合册》款识,1944年的《书张惠言水调歌头四首》、题谢孝思画款识,1948年的题《雍和宫打鬼》款识等。这些作品在章法布白、文字造型、线条表现方面也颇具现代美术构成感,达到和而不同、自然生动、浑然天成的境界。
“凤体书”书法风格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明末“多体杂写”的盛行与晚清“碑帖兼容”的书学观,为“凤体书”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审美基础和理论依据;吕凤子的画家身份与现代美术视野,为“凤体书”的出现提供了内在动力。
第一,明末清初以来“杂体书”流行。此时出现了赵宦光、傅山、石涛、郑板桥等“杂体书”名家,清末俞曲园的草篆更促进了“杂体书”的长足发展。“杂体书”主要以篆、隶相融,吕凤子的早期变法尝试显然受到“杂体书”的启迪。当代书法理论家葛鸿桢曾言:“发现与之最为接近而且有可能吕凤子先生直接师承或受到启发的是俞曲园的草篆……,如果把吕凤子先生书法作品中的草篆与之相比较,可明显地看出吕先生直接得力于曲园草篆,尤其是线条的质感与草意、凝重、执拗、直中带曲,行中有留,并带有草书中的游丝,气韵贯通。”[8]94
第二,李瑞清“纳碑于帖”思想的影响。李瑞清早年以鼎彝为宗,对金石碑学极为推崇。晚年为改变“碑学”程式化倾向,他提出“纳碑于帖”“碑帖兼容”的书学思想,意在融合碑、帖之长,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新路径。“碑帖兼容”的主张成为民国书法发展的主流,也是“凤体书”“诸体合一”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吕凤子“改良”画家的身份是促成其书风演变的关键性因素。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大变革的时代洪流,相较于徐悲鸿、林风眠的大胆变革,吕凤子的人物画选择了较为稳健的“改良”之路,以民族传统审美为基础,积极吸收西方美术中的积极因素,使他的人物绘画在现代中国画坛别具一格。30年代起,吕凤子人物画在题材和笔墨技法上都有很大转变,早期工整精细的仕女题材绘画逐步减少,高士、罗汉题材绘画增加,其中罗汉题材绘画尤为精彩。此时的高士、罗汉题材多借陆放翁、辛稼轩词境,以含蓄的手法表达对国家危难、生灵涂炭的关切,显示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线条遒劲老辣,人物造型质朴高古,用笔放多收少,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作为传统文人艺术家,吕凤子十分推崇“书画同源”的观点, “观殷初文字大小参差,间以图画(象形字),以全文为一字,每个字与字间就已具有巧妙的组织,相互照应,一气贯通,由此看来,可谓‘书画同源’”[7]471,“画之有法是后于书,而又同于书的”[7]471。吕凤子据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进行考证,认为“号称‘画圣’而为后世宗法的顾、陆、张、吴用笔,就是有时取法于草篆而作气疾驰,有时取法于楷隶而凝神徐进的”[7]471,并认为“画笔的‘横变纵化’,‘前矩后方’,却非书所能赅,故工画者多善于书,工书者不必多善画”[9]471。由此看来,“凤体书”所具有的造型意识、章法构成、线质特征与他40年代后“放多收少”的绘画风格有密切联系,表现出“在意不在形”的强烈文人审美特征,呈现民族危亡下的抗争精神。
第四,西方现代美术学习经历的影响。1932年,吕凤子发表《中国画特有的技术》一文,称“中国书无异是一种纯粹形的构造画,中国画无异是一种最进化的形象书,二者竟成异名同质的东西”[9]。吕凤子提出“构造画”的观点,说明他已尝试运用现代美术的构成观点解构书法,他将书法中的线条、墨色、字体、章法进一步纯化为视觉元素,以便在更大的思维空间内思索元素的分解、组合之趣。这种“引画入书”的观点强化了书法的艺术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束缚,拉近了书法与时代审美的距离,使得吕氏书法在形式语言层面得以自成一家。
3 “返璞归真”“灵朴飘逸”的晚期气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艺术发展开始进入新纪元。1952年,吕凤子将历经坎坷办学多年的私立正则艺专交给人民政府,自己赴苏州文化教育学院任教,专职从事教学和艺术创作。解放后,吕凤子先后担任苏南政协会议代表、苏南文联委员、中苏友谊苏南分会理事、江苏省人民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南京分会筹委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任、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等职务。吕凤子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3个历史阶段,由衷感受到新旧社会的变迁。他在给亲友的书信中曾表示:昔日作画是“用寄愤慨”,今日作画是“用当欢喜”,并刻“今而后有生之乐”印章以代替过去的“如此江山”“如此人间”[10]164。这种“欢愉”的心境直接促成了其晚年“变法”。

4 结束语
20世纪上半叶“西风东进”,西方文化强势渗透至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传统艺术形式处于千年未有之危机中。“五四”运动后,在艺术领域又掀起了对传统艺术的批判浪潮,吕凤子身处其中却始终坚守“中学为体”,身体力行传承民族艺术,同时主张“融通中西”,以现代美术理念改良传统书画,赋予传统艺术以时代新意。
吕氏书法“金石铸基,独树一帜”的独特风格特征,一方面,源自“师出名门”所具有的高古正气;另一方面,得益于其“折冲中西”艺术观念和对“碑帖融合”“引画入书”的不断探索。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吕凤子既是传统碑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书法艺术语言的开拓者。他的作品突破了传统书法固有观念,拉近了书法与现代审美的距离,代表了晚清以来“碑帖融合”发展的新高度,是特殊历史时期下传统艺术变法图强的典范,在当下对传统艺术发展变革依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