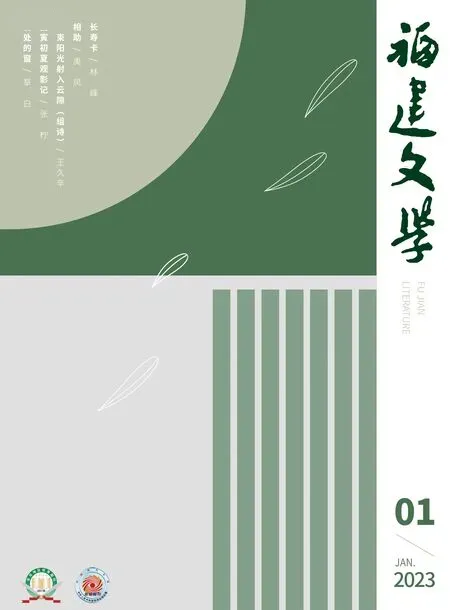破碎的青春,不破碎的爱
——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楚 儿

若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饱含浓重的悲情,那么《病隙碎笔》便已承载着悲情之后“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般的豁达释然。《病隙碎笔》是一本记述作者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的长篇抒情散文集。书中那厚重的思想意义和大气深沉的反思,通过看似质朴实则富有张力的语言传递了出来。若论及史铁生的青春岁月,从坐上轮椅被打上“残疾人”的标签,再到确诊尿毒症终日以透析延续生命,他的整个青壮年时期被疾病穿插得支离破碎,与常人对青春“热血美好”的理解背道而驰。这样的青春,用“破碎”二字形容并不为过,但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不破碎的、饱满完整的爱。即使未曾被命运眷顾,他依然兼具自我的“小爱”与普适性的“大爱”。
史铁生的“小爱”,潜藏于书中有关自我意识的剖析。“爱原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自卑,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步步深陷,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候解放。”坦荡的独白透露出内心的郁结。作为残疾人,哪怕是史铁生也难逃自卑心理,而这种自卑情感成为他追求爱情的阻碍。爱在自卑后无法溢出,而自卑又让爱越陷越深,比爱而不得更辛酸的是自卑到失去爱的勇气。但史铁生仍然是清醒的,“爱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他明了爱的平等性,不因身体的残疾而自降爱情的品质,不愿祈求爱的施舍和情感的苟且,追求与他人无异的体面的爱。也许这是他生命里最后的底线,一种自尊、自爱的保护。他在书中写得透彻而坦荡,毫不避讳自己对爱和性的渴望,有着青春最原始的模样,但冷静地将性、爱割裂看待。
史铁生的“小爱”,洒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在众人为《三国演义》中赵子龙斩上将首级而喝彩时,史铁生关注到那些被斩首而不曾留下姓名的将士们,他们有亲人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吗?“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这是一种细腻的体恤,一种无视尊卑、普视生命的人生观。当一个人已能将视线脱离小说的主线情节,而聚焦于一个个一笔带过、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其深沉的共情令人动容。这样有温情的小爱在当下社会上仍然珍贵。
除了于个体的“小爱”,史铁生还有于社会群体的“大爱”。张路黎在《史铁生哲思文体研究》中如此评价:“在儒道互补为文化主流的中国文明里,忏悔意识是一个外来的异质性因素。近现代以来,随着宗教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从五四起就有一些知识精英接受了忏悔意识,出现了一批剖析灵魂、直指内心罪恶的文学。”《病隙碎笔》记载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亲历者的史铁生将内心的彷徨与矛盾坦诚地呈现,供后世共同思索体悟。他心存忏悔意识,但不是“盲目指责式”的忏悔,而是一种究其根源、以免重蹈覆辙的冷静的忏悔。回顾与忏悔,是史铁生理性的“大爱”。
他的“大爱”也融于对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呼唤。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他以名人的身份提出异于主流的思想,为残疾人呼吁一份理解与宽容。他将残疾人爱情的首要阻碍归因于性功能障碍,提出“性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超前观念,用炽热的语言表达一个残疾人对爱的渴望,削减读者群体对残疾群体的偏见,引人共情与深思。他屡次将社会的少数群体引入读者视野,对每一群体的剖析是他力所能及的无声支持,他的想法宏大而简单,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
《病隙碎笔》还是一部“时代性”与“超前性”并存的作品。
一则则思考扎根于不同的时间段,不论是所述内容还是语言运用,都潜藏着一定的时代特色,使人在阅读的同时于细微处体察一个时代。从“上山下乡”的经历到对“安乐死”的思考,时间的推移暗藏于文字,读者与作者共同在岁月中流转。
而“超前性”的彰显,则在于对社会事件的反思。史铁生的先进思考涉及文化和生态领域。“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只以民族为单位吗?民族之内是否可能有霸道?”他拓展语言文化的边界,不愿以保护之名将文化拘泥于民族的概念内,葆有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风骨,批判部分作家对西方语言结构一味迎合。“史铁生创作的高峰期正值西方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在国内大举流行,特别是在知识界和文艺创作界显得更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对西方文化取舍的程度的把握变得尤为重要,而史铁生的观点显然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
他着眼于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痛心疾呼“贪婪鼓舞着贪婪,纷争繁衍着纷争”,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抨击物质消费的欲望膨胀对环境的剧烈打击。字里行间的急迫,流露出全球化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病隙碎笔》中的多个话题至今仍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经久不衰的讨论,凸显当年史铁生思想的超前性。
对史铁生先生的作品的评价颇多,我最喜欢夏榆在《追思史铁生》中的那一则:“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破碎的青春不因残疾而失去光彩,不破碎的爱充盈万千生命。宁静而热烈的他,为后世留下了思考的“入口”和历久弥新的生命观点。